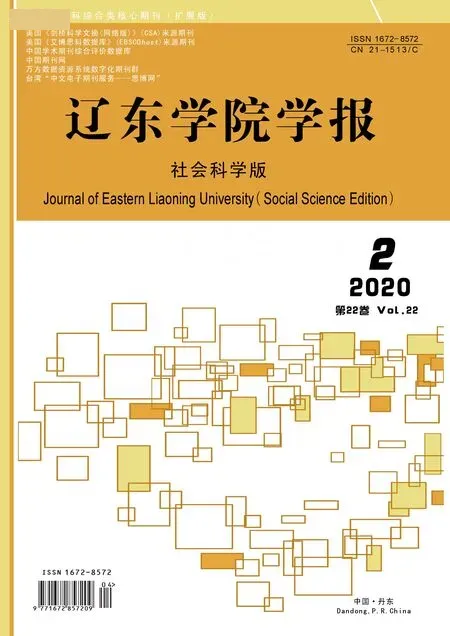论《全是我的儿子》中的代际冲突与悲剧书写
邓世彬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2160)
《全是我的儿子》(AllMySons,1947)是国人所熟知的美国戏剧大师阿瑟·米勒(ArthurMiller,1915—2005)的成名作。该剧一经问世便斩获了纽约剧评界奖(TheNewYorkDramaCritics’CircleAward)和唐纳森奖(Donaldson),真正开启了米勒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之路。剧情讲述了乔的一家人生活在儿子拉里失踪案的阴影中。某天,乔的大儿子克里斯邀请拉里的未婚妻安到家做客,准备向乔的妻子凯特公布两人的恋情,不料安的哥哥前来阻止。由此牵扯出乔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乔向军方出售有裂缝的汽缸盖,造成了21名飞行员死亡,面对指控,却嫁祸给了安的父亲。克里斯得知事件真相后愤然出走。安试图说服凯特帮其挽留被负罪感折磨的克里斯,但凯特坚信拉里还活着,拒绝认可安和克里斯的关系。最后安为了挽回与克里斯的婚姻,说出了拉里因为乔而自杀的真相。乔心生愧疚,最终开枪自尽。
著名剧评家阿博森(SusanAbbotson)曾称,《全是我的儿子》中“人物和复杂的人物关系纯粹是米勒式的”,所聚焦的“特殊家庭和家庭关系”为米勒毕生创作提供了“持续的动力”[1]40。但遗憾的是,这部米勒眼中为他“突然推开大门”[2]134,剧评界普遍认为理应“值得特别重视”[3]的力作,除了收获商业成功外,并未在学界引起足够的关注。梳理文献可见,国内几篇零星的论文着重从戏剧表现手法和伦理主题等方面开展过讨论。国外评论多关注该剧的舞台表演,而对剧本有代表性的研究被布鲁姆(HaroldBloom)收编在专评《全是我的儿子》(ArthurMiller’sAllMySons)的论文集里。书中,论者们主要围绕该剧的结构和语言展开争论,如摩斯(LeonardMoss)认为该剧的“组织和语言不可信”[1]49,然而韦兰德(DennisWelland)却称此剧“做工精良”[1]49。诚然,也不乏有人否定《全是我的儿子》的悲剧属性,批评剧中人物没有“像俄狄浦斯那样实现真正的认识”[1]48。源于上述,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代际关系入手,重新解读《全是我的儿子》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与人物冲突,并在西方悲剧传统中审视其艺术魅力,进而揭示米勒赋予该剧代际悲剧性冲突背后的伦理意义,期待能充实对《全是我的儿子》的研究。
一、代际婚恋观冲突与悲剧的情节建构
众所周知,冲突构成了戏剧情节发展的核心。戏剧冲突往往是以戏剧中人物之间、人物自身、人物与自然、人物与社会等的矛盾和对立形式展现出来。从冲突的表现来看,可以分为人物外在的冲突与人物内在的冲突。两种形式的冲突或单独展开,或互为因果,彼此影响。代际冲突属于戏剧人物之间外部冲突的一种,是“代际关系不和谐的产物,是代与代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4]。这里的“代”既可狭义指家庭中的老幼关系,亦可泛指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群体。
细读《全是我的儿子》可以发现代际冲突贯穿了整个故事情节。其中,子(女)辈与父(母)辈在婚恋观上的冲突成为拉动剧情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剧中,拉里未婚妻安重回小镇成为所有矛盾的引爆点。克里斯与父亲乔交谈时,道出了邀请安返家客居的真正原因,“我想向安求婚”[5]67。面对克里斯的感情诉求,乔只是冷冷地回应“那是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事”[5]67。在乔看来,克里斯一生中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子承父业,能继承和打点好家族企业。由于这个原因,克里斯才会威胁乔说,“娶了安后,会另找住处。也许在纽约”[5]69,乔才会勉为其难向儿子承诺他会争取凯特对他们婚姻的认同。
克里斯不仅没有得到父亲真心的支持,向母亲凯特寻求突破时也是处处碰壁。剧中,克里斯几番欲言又止的冲动,企图向凯特挑明他和安的恋人关系,最终得到的要么是凯特的不予理睬,要么是凯特的大声斥责,“别自作聪明!不要再说了!”[5]78。凯特甚至不惜向安下逐客令,以此了断克里斯结婚的念头:
克里斯:你怎么能把她(安)的东西都打包好了?
母亲:她不能呆在这里。
克里斯:那我也不呆在这里。
母亲:她是拉里的人。
克里斯:我是拉里的哥哥,现在他死了,我就要娶他的女人。
母亲:绝不可能,这个世上绝不能出现这种事。[5]113
凯特之所以阻止克里斯与安的恋情,就在于凯特坚持克里斯在弟弟拉里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不能与拉里的前女友相恋。更为重要的是,凯特坚信婚姻是一种责任,也即妻子对丈夫无条件包容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凯特从一开始就认为安理所应当等待未婚夫拉里的归来,也是为什么凯特一直包庇丈夫乔所犯罪行的原因所在。从这点来看,父(母)辈以家庭为重的婚姻观与子(女)辈的自由恋爱观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即便是在戏剧最后安向凯特宣布拉里已死,力图挽回因负罪感而逃避爱情的克里斯,想得到凯特的认可也不过只是安的幻想罢了。
可以说,克里斯和安向父(母)辈争取婚恋权的过程构成了《全是我的儿子》中主要人物的行动框架。而剧中紧凑的情节结构安排和细致的人物冲突刻画则得益于米勒对传统悲剧创作手法的运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经典之作《诗学》(Poetics)中就对悲剧做了精辟的阐释。依其所见,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6]16。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作为一门艺术应包含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和歌曲六个成分。情节作为“行动的摹仿”[6]17,构成了悲剧最重要的成分。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不是摹仿人的品质,而是对“某个行动”的摹仿[6]18。简单来说,悲剧的情节线索应该有始有终,戏剧中人物的性格、语言和其它表现手法都应依附在情节线上。后来,法国新古典主义剧论家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观”,进一步确立了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的写剧原则,也即时间、地点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代际婚恋观冲突这条线索在《全是我的儿子》的整个戏剧结构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应该说,正是围绕代际间婚恋冲突这条线索才能让该剧遵守三一律的原则,把剧中人物行动时间设置在二十四小时内,使所有事件都集中在乔家附近,也才能抽丝剥茧般将戏剧中其他细节一一交代出来,如拉里失踪之谜、史蒂夫含冤入狱以及乔最后的转变与自杀,等等。这种采用倒叙或插叙呈现过去事件的方式符合米勒一贯的写作风格,如《推销员之死》(The Death of a Salesman)中的威利头脑中闪回的往事亦可作同样的解释。《全是我的儿子》除了遵循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外,米勒剧中还巧妙地运用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突转”与“发现”两种情节建构的技巧。
“突转”是指人物从顺境转为逆境,“转向相反的方面”[6]28,发现是指人物“从不知到知的转变”[6]29。安的哥哥乔治的入场可以被视为剧中重要的突转事件。乔治连夜赶到乔家,就是为了带走安,不让安同克里斯一家来往,因为乔治从狱中父亲史蒂夫口中得知乔推卸责任栽赃陷害的事实。显然,在乔治和他父亲看来,仇人之子不可为亲,对安来说更不可为夫,因为“他(克里斯)的老爹毁了你的家庭”[5]100。尽管安没有听从哥哥的建议,但乔治的到来打断了她和克里斯两人向克里斯父母摊牌的计划,从情节发展来说造成了一次突转。不仅如此,为了铺垫戏剧的高潮,米勒还特意将乔治与乔夫妇的交谈,以及后来安拿出拉里的遗书生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好的‘发现’”,也即是“‘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6]29。拉里的遗书虽然彻底“发现”了乔隐藏多年的罪行,但也意外“突转”了克里斯和安的关系。
克里斯和安对婚姻的理想追求无不因父辈们的干预变得岌岌可危,子(女)代显然成为父(母)代仇恨和冲突的牺牲品。对于执着于爱情,不惜“背叛了亲生父亲”[5]95的安来说更是如此。因此,米勒将代际间婚恋分歧设置成《全是我的儿子》中一条重要的线索,不仅串联了剧中各处细节,增强了戏剧的艺术张力,更重要的是丰富了该剧表达代际悲剧性冲突的内涵。无独有偶,米勒在他十年后的另外一部力作《桥头眺望》(A View from the Bridge)中,长辈与晚辈在婚恋问题上的对峙直接生成情节发展的动力,剧中主人公埃迪因否认侄女的婚姻而犯下了弑亲的伦理禁忌,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二、代际价值观冲突与悲剧的社会批判
《全是我的儿子》中父(母)辈与子(女)辈婚恋观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由两代人价值观的差异所致。价值观,顾名思义是指人对外在事物以及自身行为结果的效用和意义的总体评价。两代人因生活所处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价值观上的冲突在西方悲剧传统中并不鲜见。上有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和其生父对解开怪兽斯芬克斯之谜作用的不同认识,下有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和叔叔克劳狄斯、李尔王和他的子女们对王位权力的不同理解,近有诺贝尔奖剧作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长日入夜行》(A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中一家四口两代人爱恨情仇的故事。
可以说,西方悲剧传统中从不缺乏对家庭代际间人物冲突的描写,这也充分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影响力。《诗学》就悲剧中的人物关系有过这样的阐释:“只有当亲属之间发生苦难事件时……儿子对父亲、母亲对儿子或儿子对母亲实行杀害或企图杀害时”,悲剧才能产生“怜悯之情”[6]37。然而,悲剧中家庭代际关系的描写从来都不是“真空的”,不能脱离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20世纪最重要的文论家之一)坚持悲剧的社会属性,提出了“社会悲剧”[7](Social Tragedy)这一现代悲剧的子类。苏奎教授也指出“文学中的父与子之间的亲情关系”虽然以家庭为平台进行交流,但两代人之间的“对话超越了家长里短”,负载了“文化与历史价值”[8]。简单来讲,悲剧中的代际冲突含有的社会批判特性既是悲剧的重要功能,又是悲剧主要的审美要素。
作为一部反映现实的悲剧,《全是我的儿子》中的代际价值观冲突呈现出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剧中的乔是一位精打细算的商人,“离开工厂之前首先要四处转转,确保所有的灯都关了”[5]102,也知道他的每个工人“每天总共在厕所里呆的时间”[5]102。不难看出,乔是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坚定信奉者,这解释了戏剧开场时乔读报为什么从不关心新闻时事,只关注报纸中刊登的各种需求广告,也解释了乔为什么对儿子克里斯的婚姻诉求还附带条件。确切地说,乔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5]59,靠自己多年打拼才当上了工厂老板,对成功的沾沾自喜让他难以摆脱物欲的控制。正因如此,乔才会向军方销售有瑕疵的汽缸盖谋取利益。然而,乔不顾一切追求物质利益不单单折射其个人私欲,而是“反应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9]问题。
二战后的美国经济空前繁荣,远离战场的老一辈希望通过奋斗能“回到富裕的二十年代”,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更大的安全感”[1]47。这一代人往往把金钱当成衡量人成功与否的标尺,视追求物质富裕为人生的价值所在。剧中,乔回应儿子克里斯的质疑,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道:
战争中有谁没有捞好处的?如果他们白干,我也会白干。在拿到钱之前,他们有没有把一把枪或一辆卡车运出过底特律?那样又干净了吗?这些是美元和美分,五分和一角的钱;战争与和平,无非就是五分和一角的钱,何来的干净?如果我要蹲大牢,这个该死的国家有一半的人都要和我一起去![5]125
显然,剧中沦为金钱奴隶的远非只有乔,同辈的史蒂夫直接参与粉饰汽缸盖的裂缝,出售不合格产品,致死21名飞行员的劣行也同样出于利益考虑,更别说长期包庇乔罪行的凯特。争执时,乔彻底揭露了妻子凯特作为帮凶的心态,“你想要钱,所以我就赚钱……那个时候你不是想要钱吗?”[5]120。
与追名逐利的父辈们不同,《全是我的儿子》中的克里斯代表了年轻一代对理想价值的追求。苏奎教授认为“子一代对旧有东西的叛逆,也迎合了他们对新世界的渴望与梦想”[8]。经历战争洗礼的克里斯像自杀的拉里一样,看清了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认为人的理想应该超越金钱之上。鉴于此,克里斯才会愤怒反驳父亲固执子承父业的观点,“生意!生意并不能激起我的兴趣……我想创造某种我能为之奉献的东西”[5]69,也会因为父亲“多收两分钱,怒发冲冠”[5]121。然而,克里斯的这种理想追求无不时时刻刻饱受父辈价值观的侵蚀。他虽厌恶这个满是铜臭味的社会,却又表现出对父亲赚钱能力的崇拜,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继续在乔的工厂留任。克里斯与安交谈时,吐露了心中长期压抑的惆怅与苦闷、彷徨与无助:
后来我回家了,真是难以置信。我——这儿没啥意思;整件事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场车祸。我跟爹一起做事,又是残酷的商业竞争……因为人们根本没有改变。这似乎把很多人当成了傻子。即便是活着、开银行账户、开新车、看看新的冰箱对我来说都不对劲。[5]85
剧中,除了克里斯在叛父路上走得磕磕碰碰外,克里斯的同龄好友吉姆也陷入了“理想主义”者不彻底的困境。医生吉姆将克里斯奉为“偶像”[5]94,认为克里斯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而吉姆本人也追求过自己的梦想,他曾远赴奥尔良两个月靠着牛奶和香蕉为生,专心研究某种疾病,吉姆觉得那段日子“很美妙”。后来,顶不住家人哭闹的吉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回到家里努力多赚钱,被迫为无病呻吟的人看病。吉姆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感到迷茫:“现在我又活在以往的黑暗中;迷失了自我;甚至有时记不清自己到底想成为哪样的人”。吉姆对理想和生活“终究会妥协”[5]118的判断,以及克里斯痛苦的认识“现在我像其他人一样了。我现在现实了。你们把我变得现实了。”[5]123无不折射出父辈错误的价值观给子辈带来的冲击和精神伤害。
由此可见,《全是我的儿子》中父辈追求物欲与子辈追求理想的冲突表现出米勒对美国社会金钱至上价值观的否定。显然,剧中父辈抑或子辈都成为这种美国神话下物欲崇拜的受害者,其正好解释了米勒对悲剧的看法。在《论社会剧》(On Social Plays)一文中,米勒评价古希腊悲剧“更世俗;表达了一种社会关注”[2]53,认为希腊悲剧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就像家庭矛盾那样,是一种具有共同情感和责任的不同派别的对立”[2]52。《全是我的儿子》中父辈扭曲的价值观带给子辈的困惑也预示了在《推销员之死》中米勒将进一步批判父辈虚构的成功梦想对子辈教育的误导,就像艾辛格(Chester E. Eisinger)评论《推销员之死》中的父子关系说的那样,父亲“虚假的商业格言”污染了“儿子们在家里呼吸的空气”[10]。
三、代际道德观冲突与悲剧的伦理维度
两代人持有的不同价值观势必会造成他们选择不同的道德立场处理与人关系。斯宾德勒(Michael Spindler)认为《全是我的儿子》探讨了“经济个人主义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11]。剧中,米勒通过描写代际间关于行为道德与否的相悖观点,践行了他长期坚持的戏剧的伦理指向。在其戏剧理论中,米勒阐述了悲剧的本质,他认为悲剧有别于情节剧(Melodrama),后者只需利用“实体暴力就自然而然达到戏剧的顶峰”[2]8,而悲剧不仅使人“伤心、同情、认同,甚至恐惧”,更重要的是悲剧能带给人“知识或启迪”[2]9。在米勒看来,悲剧产生的知识或启迪可以向人们“展现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以及我们必须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应该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2]11。米勒探求悲剧的道德功能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延续了西方悲剧传统中由来已久的伦理维度。
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悲剧“净化说”(Catharsis),声称悲剧的情节构建和人物塑造目的在于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使人们产生“特别能给的快感”[6]37,从而让人的“情感得到陶冶”[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散文家锡德尼(Sidney)也在《为诗一辩》(A Defense of Poetry)中提到,“严肃而出色的悲剧,会揭开最大块的伤口,呈现组织覆盖下的溃疡;这样的悲剧使国王害怕当暴君,使暴君不敢表现暴虐的情绪……也教授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12]。可见,不管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净化恐惧之情让人陶冶,还是锡德尼关于悲剧震慑暴君的行为或情绪,其实质都是有关悲剧的道德教诲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全是我的儿子》中的人物冲突更能体现其伦理指向和悲剧性表达,米勒在《戏剧集》(Collected Plays)前言介绍了该剧的创作背景。米勒谈到他将前期草稿中人物的“朋友关系”调整为“兄弟关系,有同一个父亲”,这样的改动帮他“省了不少麻烦”,也让米勒能以描写“父子关系,以及儿子追求与他人的关联性”来构建该剧的“关键点”[5]15。由此可见,《全是我的儿子》中人物关系的重新组合使米勒得以借用代际冲突传达出悲剧的伦理意义。确切地说,剧中两代人在道德立场上的对抗源自父辈们曾经犯下的罪行,也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物悲剧性“过失”(Hamartia)。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不是纯粹的“好人”与“坏人”[6]6,而是“与我们相似的”受难者,他们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6]33。
不难看出,《全是我的儿子》中代际间有关道德问题的矛盾正是围绕乔授意,凯特认同,史蒂夫直接参与的贩卖不合格零部件造成多人死亡这一“过失”而展开。然而,剧中父辈们追求物质利益并非为了一己私利,也不是故意为之。面对儿子斥责自己谋财害命的行径,乔代表父辈们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意图:
你(克里斯)是个孩子,我能做啥!我是做生意的,一个生意人;一百二十个裂缝,你就破产了……克里斯,我完全是为你才这样做,那是次机会,我为你把握的机会。我已经六十一岁了,何时才能另有机会为你谋取点什么呢?六十一岁,你不再另有机会,不是吗?[5]115
显然,就像凯特认为孩子们参军不如在家结婚,生大胖小子,“看看你(乔治)都变成啥样了,因为你不听我的!我告诉过你娶那女孩,远离战争!”[5]107,也像“深爱着你(安)”[5]101的史蒂夫一样,“每天花二毛半钱就能活下来”[5]120的乔为后代拼死赚钱的行为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父辈以家庭为重的道德观念。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坚信为家庭即便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也只是一种“世故人情”[5]121,也才会固持“老子就是老子”[5]120,子辈不能违抗父令的想法。很显然,剧中父辈们以家庭为中心,全然不顾他人死活的道德观不能为世人所接受。这种狭义的家庭道德信念除了让父辈自身“深陷背叛和随之而来的内疚感”[13]外,更让他们直面伦理上的悲剧性冲突。哲学家和美学家黑格尔(Hegel)将之称为“对立的双方,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14]137冲突。换言之,悲剧冲突是两种既合理的又片面的伦理力量不可避免的冲突。
《全是我的儿子》中子辈代表了另一种“比家庭更重要的”伦理力量。作为安心仪的伴侣、年轻一代的楷模,克里斯述说了“人人为人人”[5]120道德理想的缘由:
因为他们不只是士兵。例如,有一次连续下了几天雨,有个年轻的士兵给我送来了他最后一双干袜子。塞到我的口袋。虽然这是件小事——但……我身边都是这样的兄弟。他们并没有死;而是为了彼此牺牲了自己。我说的都是实话;要是他们自私一点,现在都还活着。……对我来说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一种——责任。[5]120
克里斯出于对社会责任的认识,用辛辣的语言攻击和鞭挞父亲乔自私自利的道德观,“你甚至连畜生都赶不上,畜生都不害同类”[5]116。剧中加入反叛队伍的还有安和乔治兄妹,两人对狱中关押的老父亲不闻不问,“圣诞节一张卡片也没给他送。退役后一次也没有探望过他”[5]101。应该说,剧末正是由于克里斯和安的穷追猛逼,才促使乔选择了开枪自杀,而乔自杀的悲剧性结局带有非常明显的伦理指向。
依黑格尔所见,悲剧中两种“善”的伦理冲突会在“永恒的正义”[14]138解决片面的合理性后达到新的和谐。乔在自杀前最终意识到不仅拉里和克里斯是他的儿子,因他而死的飞行员们也“全是我的儿子”[5]126。乔社会责任意识的苏醒让他摒弃了狭义的只重视家庭的道德观,预示着父辈对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矛盾的调和。显然,在乔看来,自己以死谢罪不仅解决了他个人内心的道德冲突,也为两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和谐,让安、乔治和史蒂夫一家人不再记恨,让儿子克里斯不再以他为耻,“我(克里斯)不能正眼看你(乔),也不能正眼看我自己了!”[5]125。
然而,《全是我的儿子》并不像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终结于乔的自杀,丹尼逊(Patricia Denison)就曾指出“乔的枪声在舞台背后响起,但需要注意的是剧情并没有以他的自我审判和自杀而宣告终结”[15]。听到乔饮弹自尽后,克里斯几乎放声大哭,倒在母亲凯特的怀里悲痛道“妈妈,我并不是真的想——”[5]127。显然,乔的死让克里斯认识到他所谓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德理想已经完全忽视了疼他爱他的父亲。克里斯参与弑父后内心的愧疚和纠结也充分说明了克里斯责任意识的转变。其实,年轻一代这种兼顾家庭的社会责任意识早已在乔治身上萌芽,尽管乔治憎恨父亲的罪行,但仍然选择到监狱听父亲述说。
因此,如该剧剧名所暗示的那样,“全是我的儿子”本身就指人不仅应承担家庭责任,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而两者并不矛盾。正因如此,剧尾凯特安慰儿子“不要责怪自己。现在忘掉一切。好好生活”[5]127的劝言也别有蕴意,暗示了代际冲突在理解和宽容中能够实现真正的和解,两代人责任意识的转变也最终预示了一种新生。
结 语
从代际关系审视全剧可以看出,《全是我的儿子》并非如论者指出的结构松散或语言不可信,也非是一部纯粹的社会剧或说教的道德剧。应该说,米勒以两代人在婚恋问题上的冲突串联了剧中各处细节,使该剧呈现出古典悲剧情节发展的结构,其艺术张力不言而喻。不仅如此,米勒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悲剧中关于悲剧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伦理启示意义。该剧也进一步佐证了米勒倡导的戏剧艺术服务社会和教育大众的写剧理念。确切说,《全是我的儿子》两代人在婚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冲突表现了米勒悲剧书写中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对人们伦理道德丧失的关注,以及对家庭内部关系和谐的渴望。而这种米勒式的悲剧表达贯穿了其毕生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勒是当之无愧的美国戏剧界良心。
此外,作为一部反映社会现实和人伦困境的悲剧,《全是我的儿子》不单单向人们传递了狭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终究会给个人以及家庭代际关系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敲响警醒之钟。更为重要的是,如若考虑到家庭乃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米勒剧终描写两代人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复苏以此实现矛盾的调和,也不失为解决社会道德冲突和平衡各种伦理关系的一种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