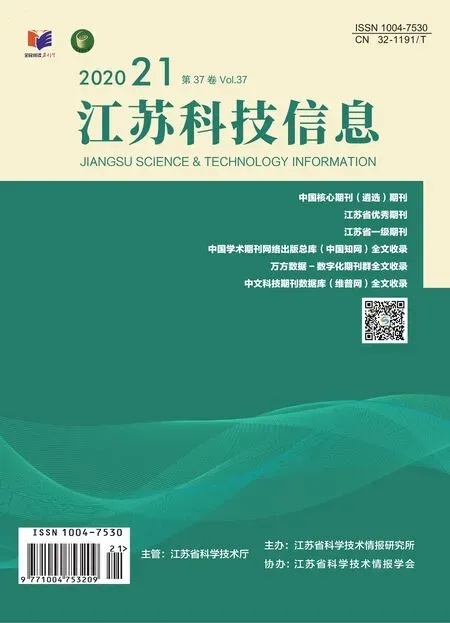图书馆导向系统的技术应用研究
曹泰峰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贵州贵阳 550025)
0 引言
图书馆面积的增大和功能的丰富为读者带来了寻路困惑,几乎所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都会让初入读者感到恐惧和迷失[1],进而形成焦虑。为了解决读者的空间迷失问题,学者们对图书馆的导向系统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其中,新技术应用最常被研究,几乎每出现一次技术变革就会有与之相应的导向系统研究文献出现。那么,学者们主要关注哪些技术,又是如何应用于图书馆导向系统之中?为了把握我国内图书馆导向技术应用的研究现状,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梳理有关图书馆导向系统技术应用研究的关注焦点,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思考和建议,为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1 概念界定
1.1 导向系统的概念
导向系统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工业化以来,城市结构越来越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为了避免迷路,找不到方位,于是出现了道路识别的系统设计,英文中称为“wayfinding”,直译为“找路”,本意为帮助人们在某个特定空间中判断位置和方向,并采取计划和行动以到达目的地的过程。作为一个学术术语,“wayfinding”首先出现于城市规划领域,1960年被凯文·林奇定义为:“针对外部环境设计的一个具有持续使用性、准确的视觉系统组织。”[2]之后,这个术语被引入国内,“wayfinding”被翻译为导视系统或导向系统,它是存在于一个基本的空间信息架构之上,利用各种元素和方法,有效地传达方向、位置、安全等信息,帮助人们了解从此地到达目的地并且知晓返回路线的媒介系统[2]。导向系统不是简单的标识标牌,而是围绕某个特定空间而设置的一套体系,既包含一系列标识标牌,又可以涵盖功能说明、导航定位、行为提示等内容。
1.2 图书馆导向系统
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界就已经引入了导向系统的概念[3]。早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导向标识的探讨之上,认为图书馆导向系统的基本功能在于“空间”的揭示与指引,从而帮助读者在空间移动。这种认识延续了导向系统共性的探讨,却缺乏了对图书馆特定风格、属性以及特定群体的寻路行为的思考。在图书馆,导向系统不仅有助于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还有助于提高或实现空间的根本功能。美国杨百翰大学图书馆评估馆员佐格·霍尔特[4]透过“空间”看到了导向系统背后的“价值”,他认为“导向系统是指帮助读者快速、便捷地找到所需资源或服务的方法和工具”,能为读者带来满意的、减轻压力的图书馆体验。它正满足了阮冈纳赞[5]图书馆学五定律中的第三项和第四项,即帮助读者找到他们所需的书(或其他资源),并节省读者的时间。
2 关注热点
在导向系统的设计中新技术应用主要体现在其传播媒介的应用上。传统的导向系统往往以实物为承载信息的媒介,如纸张、竹木、塑料、石材、金属、玻璃等,它们的应用往往随着其材料合成技术、切割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其基本的展示方式没有太大差异,并且难以改变其不够灵活的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灯光技术、声控技术也加入到导向系统的应用之中,为视线较差的地区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导向系统的发展带来了质的飞跃,既可以展现丰富的内容,又可以经常更换“主题”;既可以室内定位,又可以实现交互,成为理论和实践中常常关注的焦点。
2.1 数字标牌
受承载信息材质的局限,传统标识标牌具有展现形式单一、更新不够灵活、缺乏与读者的交互等问题,难以适应信息时代图书馆不断发展的需要。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难题提出了思路,即数字标牌系统。它是一种不受时间限制向读者发布公共信息的多媒体视听系统,有人称它为平面媒体、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之外的“第五媒体”[6]。数字标牌系统由显示终端、媒体播放器、管理系统、中央服务器等多个部分组成,具有很多优点,其一是功能丰富,不仅可以指示方向、揭示馆藏,还可以发布信息、推荐服务;其二是形象直观,不仅可以通过图形文字展示信息,还可以通过图表、视频、音频、flash动画、网页等多种形式展现内容;其三是交互性强,数字标牌系统可以实现信息的双向流动,尤其是触摸屏技术的发展使得读者也可以便捷地向平台发布信息。
2.2 物联网标识
导向系统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读者寻找资源,因此很多学者建议为资源加上电子标签的方式帮助读者定位资源。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利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以非接触读写的方式识别具体的物品。图书馆界将之运用于图书的收藏和流通管理中,一方面为每一本图书设置一个独立的电子标签,另一方面通过智能管理系统对图书进行定位、上架、排架、盘点以及跟踪图书借还记录,既节省了图书馆的人力,又提高了借还效率[7]。黄辉[8]建议有必要对图书馆的文献资源、设备设施,甚至人员和服务进行标识实现资源的优化与改造,推动图书馆的智能化,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图书馆、物与物之间的交互,实现即时管理、智慧管理。
2.3 二维码定位
鉴于无源RFID只能单向定位,有源RFID标签成本较高的原因,一些学者建议采用二维码实现图书馆导向系统。彭吉练[9]认为,可以为重要区域和关键位置的标识上附以二维码,读者在通过传统标识无法定位时可以使用手机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而访问图书馆的虚拟导向标识系统。在系统中,根据需要设置目的地,系统将自动绘制具体的导航路线,指引读者快速到达目的地。实现二维码定位导向系统的关键技术为二维码生成技术和路径导向算法。由于QR编码内部容量仅有2 953字节,难以进行读者交互,张莉娜等[10]依托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接入其Open API实现信息之间的传递与交互。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发的二维码定位导向系统不仅具有传输延迟低、定位精度高等特点,还具有方便操作、便于推广协同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带来由点状阅读向关联性阅读转变,帮助读者节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4 VR与AR
虚拟现实技术(VR)是利用计算机模拟的一种虚拟仿真系统,它可以通过模拟环境的方式,增强用户的环境沉浸感[11]。目前很多图书馆通过三维图形模拟图书馆服务情境,通过游戏通关的方式解决读者在利用图书馆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增强读者的空间体验。增强现实(AR)是另一种情境模拟技术,它可以使真实世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综合在一起,形成虚拟情境与真实场景的叠加,从视觉感受上来说,相当于把虚拟的世界呈现于人所处的真实环境之中[12]。AR与导向系统结合将能极大地提高了导向系统的直观性和功能性,帮助读者确定目标信息的位置,辅助读者在图书馆展开寻路活动。美国迈阿密大学图书馆的ShelvAR、印度国家设计学院图书馆的LibrARi是AR技术在图书馆导向领域成功的应用;武汉工程大学的陈哲[13]开创了国内图书馆界AR技术应用于导向系统研究的先河;郝琳琳等[14]建议在图书馆建立“信息亭”呈现AR情境,激发读者的内隐记忆,为了突破信息亭人数限制的瓶颈,开发相应的手机APP将是必然的选择。
3 主要问题
3.1 深度问题
技术为导向系统带来了方法和技术上的突破。然而,由于先前的研究过度关注于技术应用本身而忽略了导向系统的本质。实际上,导向问题归根结底是用户的问题。在新技术应用中只有了解用户的内在要求,契合读者的认知才能建设成高水平的图书馆导向系统。在智慧图书馆建设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模式识别技术、传感技术等技术的发展为收集、存储读者数据带来了新的机遇。届时,不仅可以形成对图书馆内读者、资源及其所处的环境进行识别,还可以形成对读者行为产生的信息进行计算、分析,以期实现对读者的类型的自动判断,对读者需求的自动回应。
3.2 互联问题
技术应用是管理的延续,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而进行的方法上的改进。之前的文献大多关注于某项技术的应用,而缺少对技术关联的研究。在技术快速更新的时代,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其他技术的应用,传统介质与信息介质共存,新技术与旧技术共存将成为图书馆导向系统的常态。那么,它们如何共存以及系统之间如何互联互通成为下一步研究的核心问题。
4 结语
信息技术将持续的更新,将会引领人们走进更加智能、更加智慧的时代,图书馆及其导向系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在未来的导向系统新技术应用中,一方面需要紧紧围绕用户、发掘用户需求、了解用户认知、分析用户行为;另一方面,需要注重新老技术的融合与更替,注重系统之间的妥善衔接,形成有价值的数据链。在此基础上,未来的图书馆导向系统将能通过对读者行为数据的挖掘与分析,自动识别读者的寻路需求,并根据所在位置和行为为读者提供寻路方案,高效智能地指引读者到达目的地,获取所需的资源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