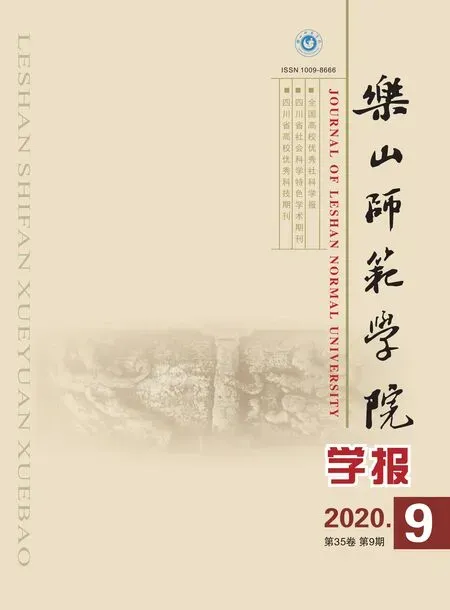论梁实秋介绍白璧德文艺观的缘由
于 惠
(苏州大学 文正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梁实秋在其文学批评论文集中虽然很少提及“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等字样,但丝毫没有影响其对白璧德文艺观的介绍。介绍白璧德的文艺思想,是梁实秋五本文学批评论文集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梁实秋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梁实秋在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介绍白璧德的文艺思想,仅仅是因为深受其文艺观之影响吗?
一、追问之缘起
梁实秋在大多出版于上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批评论文集中,很少提及“白璧德”三个字。一方面,由于学衡派造成的负面影响,梁实秋紧随其后在当时的中国推介新人文主义必然要尽量减少这种不良影响,所以他甚少提及为新文学阵营“妖魔化”了的白璧德;另一方面,梁实秋自觉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的时间不长,“亲炙未久,难窥堂奥”[1],未能真正全面把握白璧德的全部学说及思想,所以对鲁迅等人讥讽其的“白璧德的门徒”之语觉得愧不敢当,在其文论中更是很少像学衡派那样直接贴上“白璧德”的标签。在其文学批评文字中,梁实秋只在三处提及了“白璧德”:其一是在白璧德逝世的第二年(1934年)发表于《现代》杂志上的《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白璧德的主要著作、新人文主义内容、新人文主义文艺观及批评方法、新人文主义的优缺点等;其二是在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的序言部分简短地向师从白璧德研究西洋文学批评表达了谢意;其三就是为1929年出版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所作的序言,简单介绍了自己与白璧德的因缘、出版此书的与白璧德相关的背景、白璧德的主要著作。但是,甚少提及“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等字样,并没有妨碍梁实秋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及其文艺观的肯定与言说。晚年的梁实秋坦言,他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文艺观影响极大,而且正是在此影响下早年写出了《文学的纪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等文章。如果仔细考量梁实秋与白璧德的文艺思想,我们会发现,白璧德古典主义文艺思想中的诸多观点都渗透在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集中,而梁实秋的许多文学批评文章体现、彰显的正是白璧德的主要文学主张。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研究者们就注意到了此点。王集丛在1935年就曾指出“要了解梁实秋的文学理论,首先便须知道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2],也有研究者认为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其实是对白璧德之著作《卢梭与浪漫主义》的缩写,梁实秋的许多文论文章具有浓重的白璧德语言色彩,是对白璧德所授课程“16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的读书报告[3]212。甚至有研究者表示,“如果将梁实秋的批评与白璧德的批评进行比较,那么,人们看到的是照搬而不是发展与背离,看到的是更为教条化而不是理论的勃勃生气”[4]146。显然这些评述中的某些观点较为偏激,未能看到梁实秋对白璧德文艺思想的修正、补充与发展,但它们都注意到梁实秋的许多文艺思想受到白璧德文艺观的直接影响,并且彰显、言说的正是白璧德的文艺主张。
换言之,针对梁实秋在上世纪上半叶介绍白璧德文艺观之原因的问题,上述的研究者们其实从文艺思想的师承、影响方面给出了答案。但是梁实秋在诸多文论篇章中介绍白璧德的文艺思想,仅仅是因为深受其影响之缘故吗?细读梁实秋的文论文本,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表面、浅层的答案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而这必然得从白璧德的文艺思想谈起。
二、抨击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新人文主义文艺观
白璧德主要的新人文主义文艺观点,并没有在梁实秋的文论篇章中系统、整体性地呈现出来,而是随处散见于其五本文学批评论文集中。梁实秋通过用自己语言转述白璧德文艺思想、巧借儒家观点扩展性地阐述白璧德文艺思想等方式介绍了其文艺观点,而这些都清晰可见于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等著作中。
其一,在文学的性质上,主张标举“模仿”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反对标举“独创”的浪漫主义文艺观。梁实秋认为文学是模仿人生、现实的,推崇被他称为古典主义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之“模仿”论。他反对逃离人生、皈返自然的浪漫主义,抨击其沉溺个人独特性情、感觉的“独创”文艺观。而白璧德在《卢梭与浪漫主义》中就已指出,浪漫主义“只有通过否定模仿,它才能恢复自己的权利”[5]42,即浪漫主义反对与人生密切相连的文学模仿论,倡导建立于自发冲动与情感之上的“独创”文艺观。白璧德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他尊崇的是他认为体现了最好的古典主义理论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尤其是其中的模仿论。
其二,在文学的对象上,主张表现普遍人性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反对表现个性的浪漫主义文艺观。梁实秋认为文学应该模仿变动不居的人生背后之“较高的真实”,即健康普遍常态的人性,他也承认文学中存在个性,但指出它们的关系并不在于都可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而在于作家们表现普遍人性的方式因为个性差异而千差万别。因而在他看来,文学表现的对象只能是普遍常态的人性而非个性。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中他甚至认为普遍人性与个性是背道而驰的,批判了浪漫主义将非常态、标新立异的个性作为表现对象的文艺观。对于普遍人性与个性的问题,白璧德也早已提及。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解释为对普遍性、“更高的真实”的直接感悟。针对浪漫主义主张的个性、独特性,他指出应该从个性、独特性中注意到普遍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但除了他的面貌、感情自我或个人自我外,每一个人还都有一个与别人一致的自我。甚至最具独特性的个体或天才,例如卢梭,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中都表现出这个普遍的自我”[5]30。
其三,在文学表现的方式上,主张理性与想象融合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反对想象自由扩张的浪漫主义文艺观。梁实秋认为文学想象是有纪律的,即需要用理性节制想象、约束情感。梁实秋文艺思想中的“理性”,具体指的其实是常态普遍的人性[6]。也就是说,文学想象应该是符合常态普遍的人性的,受到常态普遍人性的指导与制约,“在想象里,也隐隐然有一个纪律,其质地必须是伦理的常态的普遍的”[7],所以,建基于常态普遍人性之上的文学想象才能为不同时代、国度的人们所理解。他抨击浪漫主义中不受理性约束的想象的无政府主义,认为文学想象如果沉溺于脱离常态人性的情欲、本能,只会陷入“浪漫的混乱”。他的这种主张,其实完全源自白璧德的文艺思想。白璧德认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中的想象的特性不同,前者为道德的想象,后者为无序状态的想象。他认为前者是符合人性法则的,会使文学彰显道德的效果,而后者脱离了正常的人性,据此“人们或许会学到沉落到理性层面之下的本能区域的艺术,而不是努力进入理性层面之上的认识区域”[8]93,进而导致精神、道德的懒散与混乱。
其四,在文学的审美风格上,主张稳健均衡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反对偏畸的浪漫主义文艺观。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是以理性、节制、均衡为精髓的[6],即体现了稳健均衡的审美风格。如他认为理性应该成为指导与制约想象、情感的枢纽机关,这样才能使文学中的理性、想象、情感等各种元素均衡合理的发展。他不反对浪漫主义文艺观中的情感、想象元素,但反对它们在缺乏理性制约情况下的过度发展,认为这样只会造成文学的偏畸性发展。梁实秋判定、臧否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审美风格的观点,完全来源于白璧德。白璧德不仅指出古典主义均衡的审美风格,“这种对限制和均衡的坚持不仅可以正确地确定为希腊精神的本质,而且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古典主义精神的本质”[8]11,而且强调了这种风格的重要性,认为其就像“谦卑在宗教中一样至关重要”[8]71。同时,白璧德认为浪漫主义只是“情绪的专制主义”[8]97,只会导致文学的畸形发展。
因而,虽然梁实秋在其文论篇章中很少提及“白璧德”等字样,有时还会指出白璧德文艺思想存在含混笼统等缺点,甚至在白璧德文艺思想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文艺主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较为准确地介绍了白璧德关于文学的性质、表现对象、表现方式、审美风格等方面的文艺观点,概而言之,即主张古典主义文艺观、反对浪漫主义文艺观。这就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文艺思想的主要内涵,它建立在驳斥浪漫主义文艺观点的基础上,也是为了抨击浪漫主义文艺思想。
三、批判“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想
梁实秋在文论文章中并没有仅仅介绍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文艺观,还“别有用心”地言说了他所理解的隐含在文艺观背后的意图:“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不限于文艺,在他手里文艺只是他的思想的注脚,只是一些具体的例证,他的思想主要的是哲学的”,“白璧德毕生致力于文艺批评,但是骨子里他是提倡一种不合时尚的人生观”[1],“人文主义并非仅仅是一套浅显的文艺理论,而实在是一种人生观”[9],即在梁实秋看来,白璧德虽然在构建其文艺思想上颇有建树,但他实质上是用文艺思想为其人生观作注,通过建构文艺思想的方式提倡其新人文主义的人生哲学。具体而言,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文艺观,致力于抨击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想,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人生哲学,主要为了批判浪漫主义的学说,因此,梁实秋其实想要强调的是,白璧德建立新人文主义文艺观,主要是为抨击浪漫主义的人生哲学服务的。基于这种言说、强调,梁实秋介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文艺观的深层原因便一目了然了。他在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介绍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文艺观,从根本上是为了抨击白璧德所反对的浪漫主义人生哲学。
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卢梭与浪漫主义》等著作中认为西方现代思想的源头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及以卢梭为代表的情感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指出加速西方渐趋远离文明的主要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并重点批判之。
在白璧德看来,情感的浪漫主义是一种脱离理性、纪律束缚的激进主义,它否定人性的善恶二元论,认为人性本善,是人类文明、社会约束等外在之“恶”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只有解除对人的本能、情感的种种制约才能获得人性的释放、自我的解放,真正达到“皈返自然”。因而,浪漫主义推崇的“自然”并非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中的理性、规则等“自然”,而是与之对立的人的情感、欲望、冲动等的无政府主义的放纵和漫无目的的游移。卢梭的浪漫主义在剥离理性、纪律等内在制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普遍性标准的同时,无限地扩张情感、沉湎于自己的本能需要,要求一切价值取向都服从于个人的性情、冲动等。因而,白璧德视这种缺乏理性、纪律制约的情感的浪漫主义为激进主义,将卢梭称为“激进主义之父”[10]28。
白璧德认为卢梭的“自由”“民主”“博爱”等观念,正是在此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在白璧德看来,卢梭的“自由”理念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当时已暴露出弊端的美国大学的选课制度正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它摒弃融会各时代最好智慧的人文标准,提倡完全根据自己的性情、喜好等选择课程,忽略了学生的懒散惰性;白璧德抨击卢梭的“民主”是伪民主,缺乏冷静客观的选择性,一味沉溺、服从于个人或群众的冲动、情感;他还批判了卢梭的“博爱”观念,认为其忽视对个人的人性改造,妄图通过爱、同情等改造别人及全人类,并在兄弟友爱的同情中制衡个人欲望及自私本能,只会导致乌托邦色彩浓烈的幻境。
白璧德指出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卢梭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极为深远,这早已超越了他仅作为一名文学家所具有的影响,他几乎达到了与宗教奠基者比肩的位置”[10]27。他虽然认为浪漫主义以其扩张的情感、释放的自我在对抗新古典主义拘谨的教条、法则方面做出了贡献,但认为它对后世产生更多的是危害性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想易与“人的法则”相混淆,并严重损害了人文标准。情感的人道主义相对于科学的人道主义而言,不似后者一味追求物质而忽视“人的法则”,而是强调自我的解放、性情的张扬,提倡同情、博爱等“美德”,从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非常容易被误认为人文主义的“人的法则”[10]43。白璧德指出人道主义与立足于“人的法则”的人文主义之间事实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就情感的人道主义而言,它置形成内在控制的人文性纪律于不顾,将美德等同于无拘无束的情欲放纵;而人文主义提倡有选择、纪律的同情,用“更高的自我”控制“一般的自我”,致力于在人性的内在控制中改造自我。另外,白璧德认为,科学的人道主义在促进科学、功利主义发展的同时,虽然造成了人性的片面发展,但如果没有以卢梭为代表的任情纵性的情感人道主义的推波助澜,其根本无法产生实际的广泛的影响,也不会对人文标准造成严重的损害。
(2)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想容易造成道德的败坏。白璧德认为卢梭的浪漫主义崇尚皈返摆脱一切束缚的自然并形成了其异类的美德价值观。在白璧德看来,卢梭摒弃了视美德为对本能、冲动的内在控制的传统人文思想,将美德看作无拘无束的本能、奔涌的情感和恣肆的欲望等自然人性,逃避了人文主义意义上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其将道德建立于自我感受的流沙之上,势必会造成西方世界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异化及颓败。白璧德还对当时科技、工业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中不断增多的谋杀、自杀、发疯、离异进行了人文主义反思,指出相对于科学自然主义而言,主要是浪漫主义在人性异化及道德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应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3)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想容易引发战争。浪漫主义的同情、博爱等观点认为,一个人需要将自己的性情发展至极致,随后便能与同样如此的人产生同情,并能够在兄弟友爱的同情中制衡人的自私本能。在白璧德看来,浪漫主义的这种大同的“同情观”,只不过是一首乌托邦狂想曲。浪漫主义思想引导的现实却并非如此,而且与此大相径庭。信奉浪漫主义的个人、民族在现实中只会是利己主义的,任意妄为地放飞性情,追逐感官、财富、权力等欲望。白璧德称这种违背人性法则而无法用意志控制冲动的浪漫主义者为“有效的夸大狂”[8]220,认为其必然会引发个人或民族之间的冲突、革命与战争。
因而,白璧德视卢梭的浪漫主义为一味强调自我情感无政府主义的恣肆与放纵,一种容易造成道德败坏、冲突战争等灾难性后果的激进思想,从而对此持否定态度并大加批判。
梁实秋基本吸纳了白璧德对于情感的浪漫主义的界定与看法。梁实秋曾说,他在哈佛求学时受到了白璧德很大的影响。有些研究者着眼于文艺思想的层面来理解这种影响,认为在白璧德文艺思想的洗礼下,梁实秋从原先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彻底转向了古典主义文艺思想。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对“影响”的理解不够全面而且比较浅显。因为梁实秋将白璧德的文艺思想视作对其人生观的具体例证,所以从根本上讲,梁实秋受到白璧德影响最大的不是文艺思想,而是白璧德的人生观。而且梁实秋认为白璧德最著名且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卢梭与浪漫主义》,并将此书视为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在其所谈及的对其影响最大的八本书中,唯一的一本白璧德著作即为此书),换言之,《卢梭与浪漫主义》所显现出抨击情感的浪漫主义的思想、提倡新人文主义的思想,是白璧德给予梁实秋一生影响的人生哲学,也是白璧德影响梁实秋的最大之处。由此可见,梁实秋服膺于白璧德的人生哲学并接受了白璧德对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想的理解及态度。
正因为接受了白璧德关于情感浪漫主义的观点,梁实秋指出“感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精髓”[7],并也以卢梭为浪漫主义思想的代表,视之本身即为对浪漫主义的最好注解。在他看来,卢梭极端地排除理性,一味地推崇情感,其倡导剥离社会文明、回归人的本能的“皈返自然”的根本思想就是感情用事的表现,其放浪形骸、荒诞不经的行为更是受感情主义的驱使,其《忏悔录》中处处弥漫着感情主义的色彩,其对欧洲思想造成最大的影响便是奔涌的感情主义。
对于浪漫主义思想,梁实秋也持有与白璧德相同的态度。在晚年回忆徐志摩的文章中,他称徐志摩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11]341:唯情至上、崇尚免于束缚的自由、追逐理想的浪漫主义之爱,认为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的揭示当时文坛弊端并标举“健康”与“尊严”之义的《我们的态度》,也可以看作是对其浪漫主义思想的纠偏,同时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缺乏理性节制、脱离现实人生的浪漫主义思想,最终导致了其悲惨的命运。在这些情真意切的缅怀文字中,我们对徐志摩栩栩如生的形象清晰可见,更可以从梁实秋对徐志摩英年早逝的扼腕中感受到他对浪漫主义思想的否定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梁实秋对卢梭、郁达夫的批判中,看出其对浪漫主义的抨击。梁实秋认为郁达夫、卢梭都是浪漫颓废的文人,任由浪漫流于无行,即缺少常态的人所应具备的道德之心以及以此对行的约束,在情感与欲望的恣肆中有着性欲横流、骇俗震世等恶习。他抨击郁达夫过着浪漫主义颓废的生活,其作品呈现出沉溺于情感、欲望、冲动的文学颓废主义。他还抨击了郁达夫在其《卢骚传》中对卢梭的诸如“人类解放者”“真诚之人”等赞语,指出这些都只是郁达夫的“成见”“偏心”[12]。在他看来,卢梭的思想、行为都彰显出其是“最无行的文人”[13]332。
同样的,梁实秋在抨击浪漫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与白璧德相似但迥异于卢梭的“自由”“民主”观念。晚年他在接受访问时,说:“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14]也就是说,梁实秋崇仰的自由,并非是浪漫主义倡导的免于任何束缚、遵从个人性情冲动的自由,而是由理性制约的、限定在健康常态人性范围内的自由;他所希冀的民主,也并非是浪漫主义倡导的听凭个人、群众任情纵性的民主,而是蕴含着纪律、负责、服从等品质的民主。
综上,梁实秋虽然在诸多文论文章中甚少直接提及“白璧德”等字眼,但实质上介绍了白璧德的反对浪漫主义文艺观的文艺思想。梁实秋在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之所以介绍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文艺观,不仅仅是因为服膺于其文艺观而受到了极大影响,更是为了抨击隐藏在其文艺观背后的白璧德所反对的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