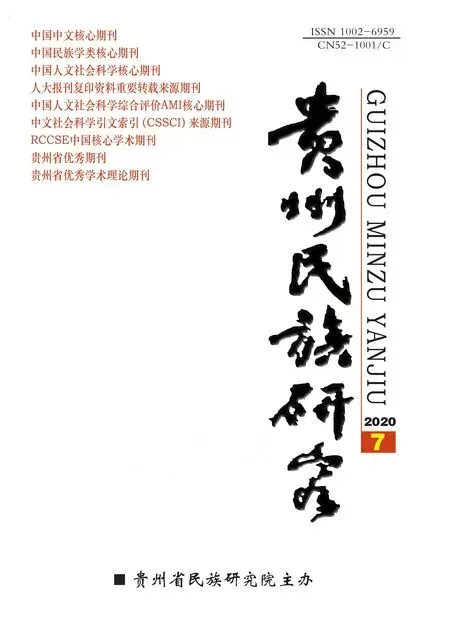从多民族地区的无字方言谈语言翻译的悖论
——以贵州方言为例
张湖婷
(贵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 550000)
一、语言翻译定义与语言翻译标准的讨论
翻译理论的核心内涵是翻译定义和翻译标准。
最初人们虽然没有对翻译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自打有翻译的历史以来,历代译家都自然而然地认为翻译是语言翻译问题。以至于现代,中外都不言而喻地围绕语言为中心对翻译一词进行定义。《现代汉语词典》1999年7月修订第三版345页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学生新华大字典》2016年第1版第172页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新华汉语词典》2017年8月第二版第266页也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 对翻译的定义是:“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用汉语翻译过来,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 对翻译的定义是:“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风格) 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1]。可见,中外翻译的定义,都是以语言为基准,围绕语言路线进行的讨论。
数千年翻译研究说明,语言翻译定义既是数千年语言翻译的理论概括,又是数千年语言翻译标准研究的方向标。不管译者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认识语言翻译定义,语言翻译定义作为一种无形的方向标,始终导引着历代译家按照如何将原语转向为译语的方向去研究语言翻译标准问题。
翻译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范畴,中外翻译标准的研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文字翻译”标准阶段。“文字翻译”标准阶段主要从文字层面研究翻译活动。最初的翻译活动,由于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环境因素简单,人类交流沟通的需求简单,翻译未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认识。翻译活动仅仅只局限于佛经翻译,而且是字对字、词对词的硬译。在中国,最早的翻译是从佛经翻译开始,“早在东汉年代(公元2世纪) 就开始了系统的佛经翻译活动”[2]。在国外,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西塞罗之前,处于字对字、词对词的硬译阶段。
第二阶段:“语言翻译”标准阶段。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翻译标准的研究从文字层面上升到语言层面。这一阶段,翻译活动逐渐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译者以句子、话语以及整个作品为翻译单位,以语言规范和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研究翻译,产生了大量的语言翻译标准。“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后汉三囯时代的译经大师们一般都采用直译方法;而后秦时代的译坛盟主鸠摩罗什一改以前译家古直风格,主张意译;初唐时三藏法师玄奘则自创‘新译’”[3]。近现代,清末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翻译标准,八国联军以后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民国时期梁实秋、赵景深派提出“宁顺而毋信”的翻译标准,鲁迅派提出“宁信而毋顺”的翻译标准,王佐良提出“照原作”的翻译标准等等。改革开放以来,系统理论逐渐引入翻译标准的研究,司显柱、陶阳[4]搜集梳理了国內2004年以来10余年数十篇相关论文,这些论文,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立足于对语言使用的研究”。这些翻译标准,都是紧紧围绕语言翻译进行的讨论。在“语言翻译标准”中, 尤以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真经影响深远,至今仍发挥巨大作用。在严复的三字真经影响下,翻译的定义有人就理解为:“翻译是在准确(信)、通顺(达)、优美(雅)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在国外,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西塞罗“明确地使用了‘以词译词’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即‘逐词翻译’) 和‘以意译义’ (sense for sense translation,即‘意译’) 等术语概念。他提倡‘意义对意义’而非‘词对词’”[5]。之后,贺拉斯(Horace) 提出“灵活翻译”、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提出“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标准,等等。20世纪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引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这批学者被称为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6],其翻译研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国外主要的语言翻译标准还有:尤金·奈达(Eugene A.Nida) 的“动态对等”、纽马克(Peter Newmark) 的“两种方法、克特福德(J.C.Catford) 的“语言学观”、克里斯蒂娜·诺德(Christiane Nord) 的“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ism)”等。
第三阶段:“文化翻译”标准阶段。这是一个刚开始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高速发展,文化环境因素高度复杂化,人类交流沟通的需求也高度复杂化,从语言翻译规范和语言学理论角度研究翻译标准已不适应翻译需要,有学者尝试寻找新的翻译理论“元”泉,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标准。与前两个阶段不同,文字、语言翻译阶段直接针对文字、语言研究翻译标准,而“文化翻译”阶段则是针对影响、制约文字、语言翻译的文化环境研究翻译标准。在中国,1933年,林语堂在《论翻译》 一文中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翻译美学观”,“将美学引入翻译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美学对翻译都有着特殊的意义”[7]。“傅雷在1951年《高老头·重译本序》中便提出了‘独树一帜、卓然成家’的‘神似’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8],对翻译研究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但其“神似”说的理论基础仍是“语言翻译”。比较有影响的,还有钱钟书在“化境说”中借用佛经的“投胎转世”,许渊冲提出“三美论”美学准则, 都是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实质仍未跳出语言翻译定义的框框。在国外,鉴于语言翻译标准的局限性,国外译家极尽努力想从文化层面探讨新的翻译标准路径。从1972年霍尔姆斯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描述性或结构性范式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标准。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在20世纪70年代从形式主义出发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将系统理论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从文学本身的运作来讨论翻译标准。1990年,英国学者巴斯奈特(S.Bassnett) 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Lefevere) 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翻译”理论和“文化转向”说。认为翻译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不应以语言为单位而应以文化为单位,以语言为单位的翻译应向以文化为单位的翻译转向。国外“文化翻译”标准,还有图里(Gideon Toury) 的“文化制约规范”、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 的“综合法”、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的“改写理论”和“三因素论”,等等,都比较有影响。这些讨论,都似乎要寻找新的翻译理论“元”泉,但都未跳出语言翻译框框的束缚。
以上翻译标准的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文字翻译→语言翻译→文化翻译”三个翻译标准层次,但都未脱离语言翻译理论定义下的语言翻译标准的讨论。
我们把语言翻译理论称为“一元翻译理论”,“一元翻译理论”的元定义称为“一元翻译定义”,“一元翻译理论”的元标准称为“一元翻译标准”,“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认为是“语言翻译”理论的“元定义”和“元标准”。
二、从贵州无字方言的翻译谈语言翻译的悖论
国家推广普通话,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汉语言文字使用的都是统一的普通话汉字。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6个民族语言融合发展、交流互鉴,形成了无数具有地域特点的汉语言无字方言。“方言发展轨迹受少数民族语言、外来语言和自身演变的渗透及影响,形成了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融合发展的特殊反映形态”[9],这种特殊反映形态往往只有语音表达而无文字记载。
以多民族地区的贵州为例,据多彩贵州官网[10]介绍:贵州2017年末常住人口358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36.3%,有苗族、布依族、侗族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另据贵州大学杨军昌教授等[11]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人口总量在全国位居第四,比重位居第五,在我国56个民族中,除塔吉克族和乌孜别克族外在贵州省均有居住”。多民族聚居必然形成多民族语言的交流互鉴,汉语言中必然融汇出许多地域性的无字方言。多民族地区无字方言的翻译,对面向世界全方位人文交流开放的翻译带来挑战。贵州作为多民族地区,如何翻译多民族地区的无字方言,显现出翻译的难点,也折射出语言翻译理论的缺失。
贵州汉语言在长期的多民族语言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在汉语言中没有对称性文字表达而仅有语音形式的无字方言。贵州方言,不太注意卷舌音,不太注意儿化音,声调大多为第二声,而且不少发音在汉语拼音中没有规范的拼读方法。贵州无字方言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汉语字词典中完全查找不到对应字词但有相似音调的汉字替代发音的无字方言。这种替代方言发音的替音汉字仅发音相似,且替音与方言发音并不完全相同,而意思与替音汉字也完全不同。如:“一哈哈”,贵州方言的发音是“yí hā hā ”,普通话的意思是“一会儿”;“我喝”, 贵州方言的发音是“wó hō”,普通话的意思是“完蛋了”,是贵州方言的感叹词;“作不住”,贵州方言的发音是“zuó bú zú”,普通话的意思是“受不了”;“假巴耳饰”,贵州方言的发音是“jià bā ér sí”,普通话的意思是“假仁假义”;“惯实”,贵州方言的发音是“guán sí”,普通话的意思是“溺爱”等等。这些方言的发音,即使我们采取了不规范拼读法,实也难以达到原音的“原生态”。无论我们是将贵州方言翻译成任何文字,或者是我们将任何文字翻译成贵州方言,我们在翻译时都无法做到“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因为,这些方言的替音汉字仅是一个抽象的替音形式,无表达文字。
二是汉语字词典中完全查找不到对应字词又无相似音调的汉字替代发音的无替音汉字的无字方言。这种方言,只能以不规范的汉语拼音拼读方法去发音。这类方言的翻译情况又如何呢?如贵州人邀约朋友:“我们明天要kí打鸡洞玩,你kí不kí”。这个读音“kí”的方言,在汉字中不仅无对应文字, 也找不到“kí”字读音的字来替代发音, 只能以不规范的汉语拼音拼读方法去发音。这个读音“kí”的方言发音,是“去”的意思。“kí”是“去”,贵州当地人都知道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虽无文字表示,但却是贵州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对人的行为方式共同认可的一种思维习惯。如果我们要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kí”是无替音汉字的无字方言,外语也就没有对称性的语言文字可供择用,翻译时就只能进行思维习惯的转换,然后在译入语中寻求最贴切(妥帖、确切) 的语言文字来表达,语音、文字只是思维习惯的表达形式。
三是用方言发音说汉语字词的无字方言。如“角落”,普通话的发音是“jiǎo luò”,而贵州方言的发音则是“guó luō”。这类方言与第二类有相似之处,不容易区分,区别在于该类方言是直接用贵州方言发音“读”汉字。因“读”音不同,方言和汉民族共同语的思维习惯也就不同。
由于地域性方言是仅有语音的无字方言,在翻译时,无论我们是将方言翻译成任何文字,或者是我们将任何文字翻译成方言,我们在翻译时都无法做到“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因为,方言本身是无字语音,与其他语言没有意义对称的语言文字,无法做到“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可以举一个贵州方言语音语句,将其翻译成规范普通话文字,从翻译过程来讨论其折射出的理论问题。
例如,方言:我喜欢吃“maó lá gó”。
译文1:我喜欢吃“西红柿”。
译文2:我喜欢吃“番茄”。
这句话中的贵州方言的发音是“maó lá gó”,它的替音汉字是“毛辣果”。如果将这句含方言发音的方言语句翻译成普通话文字,我们怎样翻译呢?译者如果通晓普通话,那么例1中属普通话的发音“我喜欢”的意思不言自明。但如果译者不是贵州方言区人,而“maó lá gó”由于属于贵州地域方言,译者汉语共同语的知识储备中肯定搜索不出“maó lá gó”这一地域性方言发音的词语。这时候,这句话中的方言语音“maó lá gó”一词,在译者思维状态中反映的只是“maó lá gó”这一抽象的语音形式。“maó lá gó”这一抽象的语音形式,只是地域方言区人群在长期的相互交流中,对交流对象这一种蔬菜在相互大脑中形成的共同认可的思维习惯的一种思考方式。要将“maó lá gó”翻译成普通话文字,译者需要知道这句方言的“maó lá gó”语音在原语人群中的思维习惯即思考方式指的交流对象是什么,才能将方言语句的思维习惯的语音表达的“我喜欢吃‘maó lá gó’”的意思,翻译转向为思维习惯高度相似的普通话的语言文字“我喜欢吃‘西红柿’”或者“我喜欢吃‘番茄’”的意思。在翻译过程中,“maó lá gó”只是地域方言区人群对交流对象共同的思维习惯的语音表达形式,译者要将“maó lá gó”的语音翻译成普通话,译者需要确切知道原语“maó lá gó” 的语音表达形式是一种蔬菜交流对象的思维习惯,才能从汉民族共同语的思维习惯中去寻找同一交流对象思维习惯最佳相似度最贴切(妥帖、确切) 的语言文字“西红柿,番茄”来表达。
“西红柿,番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实际上翻译的是交流对象的思维习惯,而不是方言语音,翻译并未实现“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实现的只是将原语交流对象语音的思维习惯转向为译入语同一交流对象语音文字的思维习惯,“maó lá gó”、“西红柿,番茄”只是不同思维习惯的表达形式。这一过程,并非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而是把一种思维习惯转向为另一种思维习惯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方言音节和普通话字词的意思,是不同思维习惯的表达形式,方言语音和普通话文字的意义,起到的只是同一交流对象的思维习惯的表达作用。显然,这里讨论的思维习惯的翻译与语言文字的翻译就有了本质区别,思维习惯翻译的翻译对象是同一交流对象的思考方式和方法,语言翻译的翻译对象是语言文字的意义,一个翻译的主体是内容,一个翻译的主体是形式。
同理,将任一语言文字翻译成另一语言文字,也都是一个寻求思维习惯的最佳相似性理解的翻译转向过程。由此追溯数千年的翻译历史,翻译开始也并非是直接就能“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而同样是先通过认识同一交流对象原语人群的思维习惯,再将原语人群的思维习惯作为参照物,再在译入语中寻求、判断、选择两种思维习惯的“最佳功能契合点”[12],最后在译入语中寻找最贴切的文字、语言表达形式,才能形成思维习惯的翻译转向。后人将表达这些思维习惯的相似点的对称性的语言文字逐步整理出来,才根据思维习惯的相似度逐渐形成两种语言文字意思相对应的字词典和语言规范。不同字词典中的多种释义和多种语言规范,只是不同人群文字语言表达形式的多种思维习惯。翻译过程应先寻求、判断、选择同一交流对象两种思维习惯的“最佳功能契合点”,才能在文字语言多种释义的多种思维习惯的表达形式中,去寻找译入语最佳相似性理解最贴切的文字、语言表达形式。
至此,对无字方言的翻译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翻译是思维习惯的翻译。由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思维习惯翻译”理论,将思维习惯翻译理论称为“二元翻译理论”,其元定义和元标准称为“二元翻译定义”和“二元翻译标准”。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对思维习惯翻译理论的“二元翻译定义”和“二元翻译标准”作出界定:
思维习惯翻译理论的“二元翻译定义”是:翻译是将交流对象原语的思维习惯转向为译入语的思维习惯。
思维习惯翻译理论的“二元翻译标准”是:将交流对象原语的思维习惯作为参照物,在译入语中寻求、判断、选择两种思维习惯的“最佳功能契合点”。
这样,翻译就存在语言翻译、思维习惯翻译的两个“元翻译理论”“元翻译定义”“元翻译标准”的悖论!
三、语言翻译悖论的解悖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13]
我们认为:思维习惯翻译“悖论”和语言翻译“原论”,是翻译内容与翻译形式、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不对称。我们可以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得出这样的认识:语言翻译理论的“一元翻译定义”与“一元翻译标准”是翻译形式,思维习惯翻译理论的“二元翻译定义”与“二元翻译标准”是翻译内容。形式和内容形成对立统一的对称性逻辑关系,也就实现了语言翻译、思维习惯翻译悖论的解悖。
当我们将语言翻译的“一元翻译定义”“一元翻译标准”界定为翻译的形式,将思维习惯翻译的“二元翻译定义”“二元翻译标准”界定为翻译的内容,就可以用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来认识原论和悖论的关系。按照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矛盾双方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思维习惯翻译理论决定语言翻译理论,语言翻译理论反作用于思维习惯翻译理论,其定义和标准亦如此。
实现解悖以后,我们可以根据以上的讨论提出一个“两元翻译理论”及“两元翻译定义”“两元翻译标准”的概念,对语言翻译理论和思维习惯翻译理论的概念进行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作出“两元翻译理论”“两元翻译定义”“两元翻译标准”的界定。
“两元翻译理论”是两合一基础翻译理论:翻译是语言翻译形式的元定义、元标准和思维习惯翻译内容的元定义、元标准的统一。
“两元翻译定义”是两合一基础翻译定义:翻译是将交流对象原语的思维习惯转向为译入语的思维习惯,用最贴切的语言文字表达。
“两元翻译标准”是两合一基础翻译标准:翻译是将交流对象原语的思维习惯作为参照物,在译入语中寻求、判断、选择两种思维习惯的最佳功能契合点最贴切的语言文字表达。
四、结语
论文通过对多民族地区无字方言翻译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语言翻译理论”的“一元翻译理论”“一元翻译定义”“一元翻译标准”和“思维习惯翻译理论”的“二元翻译理论”“二元翻译定义”“二元翻译标准”两个悖论。论文用形式和内容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进行了解悖,提出了“两元翻译理论”“两元翻译定义”“两元翻译标准”的概念,进行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作出了“两元翻译理论”“两元翻译定义”“两元翻译标准”的界定。论文认为翻译理论、翻译定义、翻译标准应存在形式和内容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对翻译研究和翻译评价,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