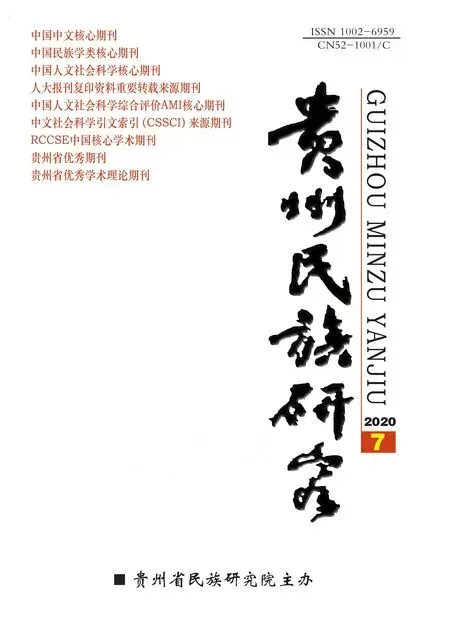外来移民群体的日常饮食实践与文化认同
——基于宁夏银川的人类学考察
马成明 崔 莉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宁夏银川从古至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介于农业和牧业带的交汇地带,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国家建设需要等原因,又有大批的外来人口进入这里工作生活,因此一直是典型的多元族群文化共存共生的社会。族群饮食文化的多元性也成为宁夏银川地区“移民文化”体系一个重要的表征。为理解外来移民群体的日常饮食实践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笔者以宁夏银川为个案进行民族学人类学考察,具体对生活在银川的不同民族、籍贯群体的饮食生活进行观察和个案访谈,因而本研究中的族群概念包括了民族性和地域性两个层面。饮食实践是在人们的家庭和社会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与饮食相关的制作、传播、共享等等行为活动。饮食实践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自觉饮食行为,背后与特定的文化思想相关联,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而特定的饮食实践又反作用于个体或群体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移民群体的饮食选择与适应
在发展着的社会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源源不断涌入,并以各种形式成为社会的一员,尤其是当今都市社会,以迁入为主的人口流动是最明显特征。银川地区饮食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不同时期大量移民进入本土,对当地饮食习俗的融合与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有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一些从江南来的南方人到银川后发现黄河里的鲤鱼和河渠里的小鱼、小虾一抓一大把,但当地人都不怎么吃鱼,这可高兴坏了这些外来的南方人,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当地人也开始爱吃这些东西,以至于银川逐渐鱼市购销两旺[1]。传统的西北回族人由于自然环境条件所限,极少接触到海鲜一类的食物,但随着近年来经济水平的提升,鱼虾等大量的海鲜产品涌入,在餐馆中被制作成各色美味。由此,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环境条件及其所能提供资源的改变对于一个群体饮食习惯、选择偏好的影响,更能够看到不同群体在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饮食文化方面的涵化。这种涵化体现在一定程度的生活习惯的相互影响和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生活方式接受过程中对自我身份文化的重新认识。一些从宁夏南部地区来到银川的中老年人说,以前他们总觉得鱼之类的海鲜都是城里人才能吃到的,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慢慢地接触多了,此类海鲜也逐渐进入日常生活,有时回到老家,发现家乡人在节日等期间也会制作一些海鲜食物。以海鲜为代表的“外来饮食文化”对于传统的银川本土饮食习惯的影响和改变,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虽然我们不能上升到像西敏司(Sidney Mintz) 分析蔗糖在欧洲传播过程中背后的政治与权力层面,但至少应该看到饮食文化发生涵化背后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市场导向与消费者选择之间,以前人们选择肉食品时主要以牛、羊肉等为主,现在人们的选择变得多样,加之市场和媒体广告对于海鲜营养价值的大力宣传,使得人们逐渐将对海鲜的选择和消费变成当代饮食生活的一种健康时尚,可见市场对于地方饮食消费习惯的影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银川市的移民在本地大量迁入,有人总结出一种特殊的“孤岛现象”,在三线建设移民群体中,由于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其内部特殊的管理体制使得一些企业内部的员工与外界极少来往,一切日常生活只限制于可以自我满足的内部社区中,内外文化供应链的断裂造成的自我封闭性使其并未融入当地社会,在文化上也体现出内在的一致性和独特性。体现在饮食习惯方面,有一部分人后来逐渐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但大多数人仍然以其来源地(籍贯) 的饮食习惯为主[2]。一位受访者颇有感触地对笔者说:“银川人嘛,南腔北调的饮食习惯都有。上午米饭下午馍馍,偶尔来顿洋芋片片。”受访人TX说:“在老家的时候不吃牛羊肉,因为农耕思想影响,牛是神圣的用来耕作的,羊是温顺的,到银川后牛羊肉成了主要食物,聚餐少不了。平时会有意识地选择去家乡风味特色的餐厅,比如经常去六盘红饭店吃炒面,因为味蕾从小就习惯了这些味道。六盘红的炒面延续了六盘山区面食的特点,手擀面,面皮薄,口感舒适,臊子也是羊肉搭配土豆、萝卜等西海固地区的特色食材,保持了农家炒面的口味。”另一位受访者MJL说:“小时候没有海鲜吃,也就是偶尔会吃鱼,家里父母也做,后来到银川上学、工作,渐渐开始吃其它海鲜,比如虾和鱿鱼,家里老人不吃虾之类的,但是我受周围朋友影响,觉得这个没啥不能吃的,而且很多清真餐厅都有供应这类海鲜食品,我就放心吃了,自己也挺喜欢吃的。”如此情况者不在少数。
虽说现代化技术和物流的发展,极大地便捷了人们对于食物的可选择性,但整体看,一个地区内部也存在饮食喜好的差异。中国北方以面食为主和南方以稻米为主的生活习惯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银川地处西北内陆,虽然有黄河水的灌溉,但自然条件仍相对干旱少雨,因此原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论哪个民族,在饮食结构上以小麦和杂粮为主,日常生活中对面馍、烙饼、汤面、拌面、包子、饺子等较为偏爱。
在银川生活的来自南方地区的多数人,因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原来是不习惯吃牛羊肉的,南方地区的牛羊肉大都膻味重,但是西北较干旱区的牛羊肉少膻味,尤其是宁夏地区的手抓羊肉,鲜嫩可口。在《知青在宁夏·永宁卷》 中专门用“饮食记忆”一辑收录了多位知青对当年饮食生活的记忆。一位当年的知青写道:“我在永宁吃过了我在杭州不曾吃过的,也吃过了我在杭州不敢吃的。我在永宁曾疯狂地想吃我在杭州时并不稀罕的,也吃到了我在杭州时想吃而没有条件吃的。”在那个缺少食物的年代,当地的苦苦菜成为很多人的共同记忆,由于到银川后没有菜吃,一些杭州的知青们也慢慢学着和当地人一样去挖野生苦苦菜。在制作苦苦菜时,最先仿照杭州荠菜的做法,可吃起来味道太淡,又觉得按照银川当地人的做法没有创意,最后大家各自创新,把一个简单的苦苦菜做出五花八门的味道,给劳累枯燥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当地人也觉得新鲜,反主为客,来尝他们制作的菜品。这样的饮食生活经历塑造了他们独特的苦苦菜情结[3]。苦苦菜是宁夏地区很多地方都有的一种野生菜,也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曾有民谣:“甜苦菜,麻苦菜,婆姨挑汉子卖,卖给城里的老奶奶,老奶奶笑呆呆,香油拌的苦苦菜,说它好吃是好菜。”[4]而今,当年用来做救济的苦苦菜已经变成银川市各大餐饮店中的筵席特色,当地人在邀请外来的客人就餐时大都会用作招待的特色菜。笔者曾在银川市内见到很多来自河南、四川等地的家庭妇女在苦苦菜生长的开春时节挑菜回去食用。
二、移民群体对原有饮食习惯的追寻和传承
如果说个体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性和特别的味蕾爱好共同决定着“吃什么”的问题,接踵而来的就是“去哪吃”的问题。同样一道面食或菜肴,在不同餐厅、厨师的手下却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味道。在这样一个文化交融日益加深的时代,人们对于味道的选择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超越了对于食物本身的喜好。作为一个移民型都市,银川跟国内其他很多城市一样,具有全国各地乃至国外风格的餐饮业在这里百花齐放、流派纷呈,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人口流动过程中人们对于各自业已形成的饮食方式和口味的传承和追寻。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菜系,不同的菜系可以理解为不同地缘群所习惯的“地方口味”。“地方口味”除了表达对传统地方饮食的认可外,同时也形成对外来口味类似的“监测制度”[5]。例如受访人SWJ说:“银川没有我家乡风味的特色餐厅,也不会去,因为都没有家乡的味道。”另一受访人HYZ说:“家乡的饮食不太习惯吃过辣,大部分都是清淡为主,我自己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银川有一部分家乡的特色餐厅,但不会选择,因为都不正宗。关于饮食,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对于家乡的情怀,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可以让外乡人在外地体会到故乡的温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对银川西夏区“马敏祥生汆面”餐厅的观察中,笔者发现大多数来这里吃饭的人在与老板谈话中都使用的是宁夏南部地区方言,可见这些顾客也都同样来自宁夏南部地区。这样的餐馆中回头客很多,尤其籍贯是宁夏南部地区的顾客,在知道该餐馆制作的面食是纯正的“家乡味”后,会经常来这里寻找“家乡的味道”。而在西夏区另一家固原风味的面馆里,笔者就餐时无意中看到餐厅的经营者闲暇时在抽烟,而他自己也参与后厨工作。笔者就此现象问旁边另一位就餐的食客,不想到食客轻轻一笑,说:“嘿,咋说呢,都是老乡么,我经常来他们家餐厅吃,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个味道,以前在我们那儿吃惯了这种味道,这个面食就应该这么做嘛,不知道为啥其他餐馆都做的是另一种方式,不好吃……”可见,有的时候,人们对于味道的追寻甚至可以超越餐饮环境本身,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在那些大街小巷里的流动小吃摊上,既没有经营许可证也没有卫生合格证,却依然有那么多人排队去吃。在西夏区的另一家主打生汆面的饭馆中,菜单上列着“西吉生汆面”和“三营生汆面”,西吉和三营是固原市内两个相邻地区,但在同一面食的制作上形成两种地域风格。在这家店里,两种面的汤和味道一样,但“西吉生汆面”是扯出来的长面,而“三营生汆面”是揪出来的面片,制作方式不一样,满足了不同地食客的喜好。这种餐饮经营者本身的选择在很多餐厅中都体现了出来。在金凤区另一家同样是以生汆面受欢迎的餐厅里,因为老板是固原三营人,所以其在制作方法上则是揪面片的方式,同时还在味道上做了调适,汤和肉丸味道相对清淡许多。
饮食消费也与个体的身份、性别、地位差异存在关系。这种关联性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身份认同。从宁夏南部地区来的人,大部分到银川后仍然带着浓浓的“洋芋情结”,在家里时保持着吃洋芋面、炒洋芋菜的习惯,外出聚餐时菜单上总是少不了一道洋芋做的菜品。很多人喜欢吃大盘鸡,更喜欢里面的洋芋。宁夏西吉被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但当地人几乎没人把它叫马铃薯的,都是叫洋芋,偶尔叫土豆,足以说明民间对于食物称谓的特殊方式,意味着这些东西最初都不是本地产的。“洋芋比肉香”,这是宁夏南部地区人的日常话语,因为在人们什么也吃不到的特殊历史年代里,是这些“土疙瘩”救了人们的命。后来,人们可以就一种洋芋,能做出五花八门多种口味和形式的菜来,煮洋芋、烤洋芋、蒸洋芋、凉拌洋芋丝、炒洋芋丝、洋芋琼琼、洋芋片片……而把洋芋和其他蔬菜搭在一起制作出来的食物就更多了。所以直到现在,宁夏南部地区的人到了银川生活工作后,日常饮食中仍然少不了洋芋。有的人说自己可以几天不吃肉,但不能几天不吃洋芋。
由此看人们对“家乡味道”的认识,有的为追寻而可以选择有特殊标识的,有的人则不轻易认同此类餐饮,背后其实也无疑是对家乡饮食味道另一种“守护”。
乡土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的重要存在形式,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秩序延续的主要场域空间,故乡的概念对于中国人而言,意味深长,不仅仅是曾经成长生活的地方,也是个体对于自己族群身份追寻的重要源头。正如有学者所言:“推动历史发展,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单是价值理念、观点主义,还有乡愁别恋,对酒当歌。”[6](P4)所谓乡愁,便是一种记忆。对于故乡的记忆,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在新的社会中生存的个体的精神寄托。从宏观来看,不同族群及其个体的这种独特饮食文化,是其社会存在和发展延续的一种符号,“一种沉淀着特定文化价值的非语言符号”[7],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群体的饮食文化图式,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认知与实践。
三、移民群体日常饮食实践中的文化认同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身份”的痕迹,既有先天的文化身份,例如民族属性;也有后天的文化身份,例如在成长过程中所习得的饮食习性或语言特征。当人们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活久了,其文化身份也会趋向于稳定。而人口的流动逐渐打破了这一稳定性。当个体从原来的群体中离开到了一个新的群体中生活时,不论是出于生存还是发展需要,都必须通过与新地方群体的交往互动来实现。英国人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 结合自己在中国生活期间有关饮食的经历写成《鱼翅与花椒》一书,其中提道:“沉浸到新的文化中,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其中风险很大,可能会破坏你内心深处的自我,甚至对你的身份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8]所谓“身份”,是“某一个人表示自己的具体标志,或者是某一事物自身独有的品质,指向的是某种自我认同的同一性和这种同一性得以表示的独特标记”[9]。此处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文化身份。显然,任何移民在进入新城市后都将面临着“文化适应”即新的身份认同构建问题。
受访人MJL说:“我自己喜欢吃有味道的甜食多一些,烫面油饼,麻花,面条多一些,以面食为主,这些都会受到民族习俗的影响。我父亲爱吃简单的面食,我们年轻这一代喜欢吃甜食,例如糕点之类的,两代人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在谈到现在的个人饮食跟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时,受访者SHX说:“要是仔细一想,变化还真的好多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饮食习惯跟地域有关系。比如说,和以前相比,主食上改变了,到银川后,米饭吃得多了,受城里人影响,吃的东西种类也多了。蔬菜吃得多了,水果也吃得多了,肉食吃得越来越多。”
显然,个体的身份具有流动性和建构性。当个体从另一个地域或群体中来到新的社会环境中时,在与他者的日常往来中发生种种关联,并产生身份的转换问题,每个个体都被自身或他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贴上各种标签,这种标签化的身份会进一步影响到不同个体间的交往等社会关系。从“某某地方的人”变成为“银川人”的过程,便是身份的流动与新的建构之一。人们通过对饮食的选择,也重新建构着自己的身份。一个原本来自农村生活环境的人,在银川生活并选择到高档的餐厅就餐后,或者偶尔去吃一顿西餐,可能会在心理上逐渐产生自己已经是“城里人”的感觉。去不同消费档次和类别的餐饮店,不仅取决于个人口味喜好,也体现着人们对于自身地域、阶层等不同层面身份的预设和文化认同。
身份的确立往往基于自我的认同和他人感知的统一。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移民群体为获得融入感,会寻求与当地居民相一致的社会身份认同。在银川这样的城市中,很多人都是“移民”,因此籍贯多元。城市居民众多,相互之间的交往也分为多个不同的交际圈[10]。当下的银川,虽经过许多年的城区改造,上世纪的人口居住格局已经被打破,但依然能够发现在一些居住区域内生活着具有一定地源或族源的人群。如果说上世纪中后期来到银川的那一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银川的移民一代,那么如今移民二代都已迈入中年,移民三代正式成为了这个城市发展的主力军,乃至于一部分移民四代已经在出生成长之中。
人口的流动使得族群身份不再是单一的,出现了民族群体、血缘群体、地域群体,建立在一定社会工作活动中的共事群体乃至网络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虚拟的“情感共同体”等。群体身份认同在不同层面都得以显现,而认同程度和表现因人而异。全球化与数字化的生存环境下,人们接触、交往的频率增高。“他们根据不同的对话者和交往者不断调整身份,不断变换认同,而族群意识和民族意识也得以强化”[6](P304)。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看到或感受各种差异,这种差异性在一定情境中会产生对自我认同意识的建构。饮食习惯的在地化与人们身份认同转化之间相关联,群体自身也完成从“客”到“土”的“在地化”过程。移民及其后代的族群身份认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而是在其长期与世居(或久居) 者互动的“在地化”的实践过程中,因时间、空间、族群关系以及国家政治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多重性[11]。全球化背景下,族群自我的文化认同究竟能否“有助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彼此间相互理解的问题”[12],我们在银川这一地方性社会中人们的日常饮食实践中便可得以窥见。
在银川地区的大街小巷,只要有人群聚集和流动的地方,大都会出现各类小吃店或流动摊点。“小吃的地域性强,各地域小吃对当地口味模塑能力极强,本地正宗优越感非常强,食客虽然不排外,在遇到其它地方小吃的时候也会尝鲜,但往往总是与本地小吃进行比较和评判,而往往都会贬低其他地方的小吃,高评本地小吃的独到与正宗。”[13]
正如受访者NRAL说:“我是因为上大学从新疆来银川的,因为在银川会呆4年之久,时间较长,要入乡随俗,成为其中一员。因为新疆美食太多了,这边相对比较少,这里有家乡风味的餐厅,但是很贵,所以很少去,而且也不正宗。兰州拉面会去吃,感觉还可以。”
在西夏区文昌北街一家“新疆村”饭馆里,其经营者和厨师都是宁夏同心人,餐厅内部有多处新疆风景展示,为数不多的几个包间也是以新疆的部分特色风景区命名。而相隔不到1公里的一家名曰“阿凡提”的小型餐馆,经营者和厨师是银川本地人。笔者注意到,在这两家餐厅的常来食客中,基本每天都有来自新疆籍大学生就餐,尤其是“阿凡提”餐馆,常有三五成群一起到这里聚餐聊天。如果说“新疆村”是和“阿凡提”一样,在面食尤其是大盘鸡和大盘鸡拌面的味道上与其他很多餐馆有差异,其味道更加劲道,植物油和辣椒的使用上与新疆地区的做法更贴近外,“阿凡提”餐厅则在文化呈现上更富特色,其屋内墙壁上悬挂着一个较大的卡通“阿凡提”图像。众所周知,阿凡提在新疆地区尤其是维吾尔族文化中有着特殊影响。这家餐厅就是充分利用了顾客的这一心理(文化认同) 作用,吸引新疆籍和其他对此文化感兴趣的顾客。
李旭正(Wook-jung Lee,韩) 在对面条传承历史进行的考证后认为,当小麦与中国古代汤文化和蒸食文化相遇后,“面条”制造出现了。虽然最早的长寿面出现在中国,以细长的面条代表长寿,这种象征意义却已遍及整个亚洲地区[14]。文化根基于土地,但也在流动中形成[15]。显然,文化没有绝对性,因人而存在,因人而变迁,而流动性是当代人口的最大特征。饮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成为一个群体的特征符号。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16]。在这一意义上,他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一定观念即“符号化思维”的影响下发生或进行的,并由此而构建出“人——符号——文化”的哲学逻辑。这些直接影响人类行为的“符号化思维”,实质上就是“文化指令”。各族群相互间的交往互动,就是在各种“文化指令”的影响或指导下进行的[17]。显然,个体对于族群身份的认同与归属也可以认为是在对种种文化符号的认同与建立中逐渐确立的,即便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个体被动地进行某些生活习性上的调适,但终究很难摆脱某些文化符号的影响,并可以在日常饮食实践中表现出来。
四、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族群共生逐渐成为所有都市社会的共性。通过对银川地区移民群体日常饮食实践的民族学人类学考察研究,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中,饮食作为一种重要存在,已经不仅是满足着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不同族群在特殊自然环境与历史进程中形成各自独特的饮食文化。当不同族群由原来各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空间进入同一社会生活时,饮食作为一种最明显的文化符号影响着人们对他者的认知,以及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建立、维系,并由此对文化边界的存在产生工具性作用。透过对日常生活中饮食实践的考察,能更进一步看到族群文化边界的现实复杂多样性,在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中,饮食更多地能够成为族群间相互理解和接纳的重要实践方式。人们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一种地方性的共生智慧,体现为尊重差异、追求共识、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