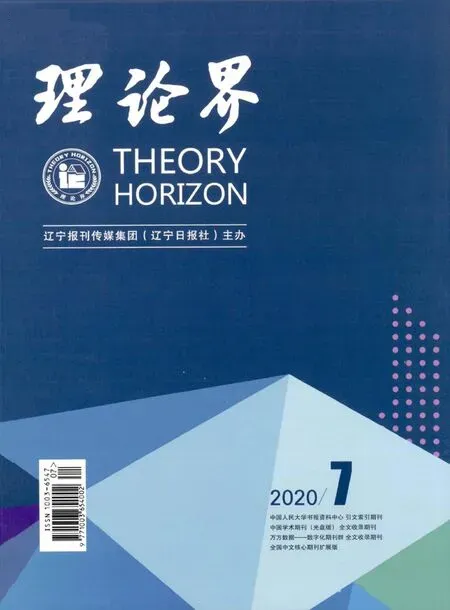康有为“性有善有不善”思想探究
——以《孟子微》为中心
吕箐雯
康有为(1858-1927)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更多的是作为政治思想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这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相关。其所有政治思想都以学术为本源和基础,“吾注有《礼运》《中庸》‘四书’《春秋》及《礼记》选,可以宣讲,发明升平、太平、大同之义”。〔1〕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中,又以人性思想最为根本。梁启超曾谓其师康有为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2〕“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的义理阐发必定以人性理论探究为基础,可见人性思想在康有为总体学术思想中的地位与价值。但康有为的人性学说十分庞杂,前后也经历了多种演变与发展,《孟子微》作为康有为流亡海外时集中完成的著作,可以更清晰、全面地呈现康有为对孟子的认知与理解。因而本文以《孟子微》为研究中心,以康有为关于“性有善有不善”的思想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这一思想,明确康有为将人性论与政治学说相结合的部分问题。
一、康有为“性有善有不善”思想概述
“性有善有不善”的表述出现于《孟子·告子上》:“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性本然就有善与不善的区分,尧为君,象为臣,但至善之尧也不能使象为善;瞽叟为父,也不能化舜为恶;纣为君,又与微子、比干有兄弟之亲,也不能使二子为不仁之人,故“善恶不可化移,是亦各有性也”,〔3〕这种理论强调绝对的善与恶。
对“性有善有不善”思想继承较多的是王充,他在《论衡·本性篇》中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并通过商纣、羊舌食我等人之例,来反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说法。他认为:“九州田土之性,善恶不均,故有黄赤黑之别,上中下之差……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有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4〕显然,王充以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为基础,将人性划分为三个层次,强调上等根器者性则善,下等根器者性则为恶,而大多数人,则善恶相混。
康有为亦继承了王充将人性划分为三个层次的思想,在早期的《万木草堂口说》(1896年)中,他论述道:“孟子言性善,扩充不须学问。荀子言性恶,专教人变化气质,勉强学问。论说多勉强学问工夫,天下惟中人多,可知荀学可重。”他将“中人”与荀学联系了起来,认为“性恶”是针对“中人”而言的,那么按照这一逻辑,“性善”便理应指向“中人以上者”。〔5〕
在后期,康有为进一步对其思想作出修订,认为“性善”指向“中人以上者”,“性恶”针对“中人以下”者,二者是绝对的性善与性恶,无法改变;而中人之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随后天环境改变。康有为对人性的划分主要体现在他对孟荀的调和中,“孟子之言性善曰:‘其情可以为善’,则仍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之说耳,并非上智之由仁义行也。荀子之本始质朴,但未加纹饰耳,亦非下愚之不移也。孟荀所指,仍皆顺就中人言之也……无善无不善,即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也,皆就中人之姿言之,说亦相近”。〔6〕与王充将孟荀之学视为“上智与下愚”之性不同,在康有为看来,孟子所论性善,不是“上智”之绝对的性善,而是可以为善为不善的中人之性;荀子之性恶,亦非“下愚”之绝对的“性恶”,亦是针对中人而言。而“有性善,有性不善,则孔子所谓上智下愚不移”,〔7〕上智与下愚才是绝对的性善与性恶,无法被改变。
在康有为的人性理论中,中人之性除了有“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两个向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人人都有成善的可能性,即“善质”。这一思想来源于董仲舒,“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董仲舒将“善”比为“米”,将“性”比为“禾”,就像禾能够长出米一样,性也可以有成善的表现,但“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亦如同米与禾不能等同,“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8〕性有成善的动力,但不能说性已然全善。康有为亦持这样的观点,结合《周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率性之谓道”“尊德性”等的说法,认为“夫曰天性、德性、尊之、率之、弥之,皆就善而言。其当节、当修、当继成之者,以性虽有善质,而非至善”,〔9〕正因为人天生有善质,才有为善的可能;也正因为人有善质而并完全表现为善,才有后天努力的必要。因此,康有为将孟子性善思想概括为“人性之质点可以为善”,“孟子独标性善,就善质而指之”,〔10〕认为孟子所言性善,不过是人心自身的向善力量,而非善之外显。
综上所述,康有为的人性理论建立在董仲舒、王充等人学说的基础上,从层级角度,可以进行两个部分的划分:第一部分首先区分了人性的三个层次,从“上——中——下”三种品性层级来述说,并继承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认为“上下”两种根器的人体现出绝对的性善与性恶,是无法改变的;而中人之性,虽不已然表现为善,但含有向善的动力,有成善的可能。
二、康有为“性有善有不善”思想的部分问题及其“三世进化说”
康有为著《孟子微》,表面上是阐发孟子之微言大义,实质上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其中有一项,便是宣扬其平等理论。“传孔子《春秋》之奥说,明太平大同之微言,发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隶天独立之伟义,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钳制之中,莫如孟子矣。”〔11〕在明确“性有善有不善”思想的问题所在时,需要先明确康有为的平等思想。“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12〕他阐发了“平等”“自由”“进化”等现代价值,而其“平等”与“自立”观念则主要引申自孟子“尧舜与人同”(《孟子·离娄下》)的思想,康有为注释此句说:“人人性善,尧、舜亦不过性善,故尧、舜与人人平等相同。此乃孟子明人人当自立、人人皆平等,乃太平大同世之极。而人亦不可暴弃自贼,失其尧、舜之资格矣,此乃孟子特义。”〔13〕在康有为看来,“性善”是人人平等与自立的基础,因为人人天生都有成善之“善质”,故“平等”;因为善性是不假外求、反求诸己的,故“独立”“自主”“自由”。
康有为其实是在以“平等”等现代价值附会传统的“性善论”,从而为其政治学说进行辩护,这样的附会与嫁接,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其思想存在诸多漏洞与矛盾之处:一方面,如果坚持其“人人性善”故“人人皆平等”的观念,那就与他“有性善,有性不善,则孔子所谓上智下愚不移”的思想相背离,与他将人性区分为“上——中——下”的三种层级的做法相矛盾,既然人人都平等地具有“善质”,为何还会有“不移”(不可改变)的“性善”与“性不善”?另一方面,如果秉承其层级之性的理论,则便又与其“平等”观念相悖。性善论针对的是“上根人”,只有“上根人”才能承当“性善”的理论。不是说“人人皆性善,人人皆与尧、舜同,人人皆可为太平大同之道,不必让与人,自诿其责任也”〔14〕吗?为何只有“上根人”性为善?由此可见,无论坚持哪一种解释路向,康有为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自己构造的矛盾中。李泽厚先生就是看到了康有为的上述矛盾,因此,认为康之“自然人性论”有资产阶级性质,“性善论”乃封建正统思想,前者倡导人欲、平等,后者强调天理、等级。这样来看,康有为的《孟子微》可谓“回到了以‘心知’和‘义理’为本体的传统老路”。〔15〕
康有为对该问题并没有明确作出解答,但其提出的“三世进化说”或许可以视为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尝试。“《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16〕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社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进化的轨道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并且人类社会毫无例外都要经过这三个阶段,社会的发展就是由这三世循序渐进地进化推动的。
在明确了“三世进化说”之后,康有为就将其人性论与三世说相结合,在三世说的“立体结构”中分别予以对应。不过虽然由数量而言为三世,但从性质来看,则“春秋三世,亦可分为二”,〔17〕主要在于“乱世”与“平世”的区分,“大概乱世主于别,平世主于同;乱世近于私,平世近于公;乱世近于塞,平世近于通”,〔18〕二者的社会环境是不同的,因此,相配的人性也是不同的。
康有为将荀子之人性论视为乱世的人性论,而孟子的性善论则为大同世立说。首先,从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功能考量,“盖言性恶者,乱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检制压服为多,荀子之说是也。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进化向上为多,孟子之说是也。各有所为,而孟子之说远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19〕康有为将荀子之性恶论与“乱世”相匹配,认为荀子的性恶论讲求“检制压服”在于扭转“乱世”;而孟子的“性善论”力倡“平等自立”,乃“平世之法”。其次,不同世中,人性亦不相同。“其时不同,故其理亦不同也……方当乱世升平,经营人道之未至,民未能仁,何暇及物?至于太平世,众生如一,必戒杀生”,〔20〕平世的人性皆善,人人都有同样的善性,“然生于浊世,激于恶风,举国皆饮狂泉,掩鼻而解臭,举扇以避尘,卒无能出之者”,〔21〕而乱世中,囿于环境的局限,则“民未能仁”。故“孟子以扩充普度,直捷放下,如飞瀑满流,冲沙徙石,开成江河而达于海,气势滔滔浩浩,此仍为上根人语,为太平世说,粗下之人,乱世之时,不易承当耳。然直证直任,可谓无上法门也”。〔22〕“平世”均为上等根器之人,因而可以实行孟子之性善论,直接发明本心,明心见性;而“乱世”均为下等根器之人,无法直接体认自己的善质,故需要依赖外在的制度教化,依靠荀子之性恶论。
如此,将三世进化说融为人性论中,“表面上”可以解决康有为人性层级说与其平等思想之间的矛盾。坚持其“性有善有不善”的观点,则可以说平世之人为上根人,人人皆有善质;乱世之人为下根人,其善性受到拘束。从同一世的角度来看,人人都是平等的,太平世为上根人,乱世中为粗下之人。如此就可以跳出性善和性恶“平面化”的比较,而在三世说的“立体结构”中找到“平等”。
综上所述,康有为“性有善有不善”的思想与其“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无论坚持任何一方,都无法圆融地兼顾另一方的合理性。虽然康有为自身未做明确说明,但其将人性学说与“三世进化说”相匹配的做法,可以视作为解决上述问题而进行的努力。将平面化的人性学说升华为“立体结构”,将同一世的人性归为同一类,可以在表面上解决上述矛盾。但从更深角度来看,这样的解决方法,仍是不究竟的。
三、康有为“三世进化说”的部分问题及其“命论”
首先,不同世间的平等如何保证?“故君主之权,纲统之役,男女之别,名分之限,皆为乱世法而言之。至于平世,则人人平等有权,人人饥溺救世,岂复有闭门思不出位之防哉?”〔23〕为何有人生于平世,就为“上等根器”之人,就“平等有权”?而有人生于乱世,就要遭遇“下根人”性恶之苦,要接受“君主之权”等一系列的限制?
其次,即便在同一世,也不一定全为同等根器之人,那同一世中的平等,又如何保证?“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孟子·告子上》)。康有为自己也说“夫人之性有万亿之不同……即就性善言之,尧舜、孔子、伊尹之上圣,及颜子、黄宪、高允、元紫芝之纯德懿行,季礼、子臧、华盛顿之高蹈大让,以及乡里善人,其等固有千百级之殊”,可见善性也有千百种区分,“人之性亦不有与人性同者”,〔24〕那这样的平等,又如何保证?
再次,三世进化并非简单的单线条式的递进,康有为自身亦言“一世之中又有三世,据乱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据乱……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为九世,又可推为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25〕因而制度与人性之间,也并非单向度的直线关系。康将人性论与“三世进化说”相匹配,以制度决定人性,也必定会产生极大的混乱与矛盾。
最后,从哲学思维的层面而言,康有为将人性与三世说相结合的做法,与孟荀从人性出发来建构秩序的行为不同,会“令人认为是不同的制度需要不同的人性原则,从而使其人性论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维度”,〔26〕因此,康有为对“性善”的现代阐发会使人认为他只是在字面意义上将平等、自立、进化等注入到了对性善的解说之中,只是简单的比附,缺少哲学义理层面的建构。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性有善有不善”思想与其“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之间存在矛盾,其“三世进化说”可以视为弥合二者张力的一种努力,但这种努力的效用较弱,其“三世进化说”本身就存在与“平等”思想的冲突,亦涵盖了混乱、缺少形上思维等其他问题,无法解决其思想之间本然的矛盾。或许,我们可以再进行视野的转向,从康有为的“命”论来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康有为认为,人会从上天处获得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我们受之于天的,是“仁义礼智天道之性”,是天所赋予的“知气神明,合于人身而不系于死生”之部分,对于这一部分,我们“则求扩充之,以其仁施于父子,以其义施于君臣,以其礼施于朋友,以其智施于贤,以其天道施于圣”;另一方面,是“声色臭味安俟之命”,对于这一部分,我们无法自主掌握,已“有预定者也”,“以寿夭穷通,富贵贫贱,荣枯得丧,皆有天数,非人力所能为”。〔27〕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康有为则言“性由天命”,性亦是由天所规定的,亦不是行为主体能够自主决定与把握的,从“非人力所能为”的角度而言,“性”也可以归于“命”的范畴。
康有为继承并发展董仲舒以“阴阳”名“性”的思想,认为“性”的“善恶”主要表现于“魂”与“魄”的关系上,“魂魄常相争,魂气清明则仁多,魄气强横则贪气多”。在康有为看来,“魂”是全然尽善的,“《传》谓人既生魄阳曰魂,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孔子所谓魂气则无不知”,“魂气之灵,则仁”;而“体魄之气,则贪”。绝对性善的“上智之人”,就是完全去除掉了体魄之气者,“若神人者,肌肤若冰雪,清明在躬,不为魄累,故死而犹存,盖魄死而魂存也”。相反,“只知食色,不识母妻”的“性恶”之人,则“魂尽去而魄犹存”。对于“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中人而言,其有不同的人性表现,就在于“魂魄之清浊、明暗、强弱、偏全,互相冲突牵制”,若“使魂能制魄,则君子;使魄强挟魂,则小人”。〔28〕由此可见,无论是不移之“上智与下愚”之人,还是“性善恶魂”的中人,其人性是善是恶,都取决于“魂与魄”二者间的比例。
既然如此,那“魂与魄”又是何者所决定的?康有为继承董仲舒“天地之所生为性情”“天两有阴阳之施”的思想,认为“魂与魄”亦皆秉自于天。一方面,就“魂”而言,他结合“体魄则降,知气在上”的说法,认为“人既生魄阳曰魂……知气游魂不随体魄而化,无死生之可言,亦不因父母而始有”,〔29〕人之魂,具有恒常性、独立性的特点,是每个人天生就具有的;另一方面,“魄”则指人的“形色体魄”,包含了“声色臭味”等外在方面,更是我们所无法把控的。因而从“非人力所能为”的角度而言,“魂”与“魄”也可以视为是由“天命”所规定的。
而“命”又受何种力量支配?康有为认为,“其命之因,远而难考”,他引用《孝敬纬》“善恶报也”的说法,参考《易传》“精气游魂”的表述,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归魂游魂”为基础,结合佛教业报轮回的思想,“则其善恶之因,以为立命之报,盖在前世矣。前世善恶之大小,以为今世受报之大小……非人浅短所知耳”。〔30〕同样结合佛教“命由己做,福自己求”的思想,康有为认为人之性命也是可以变化的,“若夫造命造因,则当积仁积智,以流恩泽,发光明,成浩气,与造化相流通而更变之”。〔31〕
如此,我们或许可以解释康有为“性善性不善”的人性学说与“人人皆平等”的政治主张之间的矛盾。他将人性区分为“上—中—下”的三种层级,正是因为天生的魂魄比例不同,才造就了“性为绝对之善与不善”的“上智与下愚”之人与“性可以为善为不善”的中人,魂魄之比例则“非人力之所为”,由天命决定;而“天命”则与前世善恶业报相关,换言之,正是每个行为主体自己前世的行为本身,决定了其自身此生之性善与否。同理,若要改变自己来世之性,则可以从当下开始,“积仁积智”以更变性命。从“此生受命”与“来世造性”的角度而言,人人都有改变自己性命的机会,因而人人皆平等。同样,康有为之“命论”,亦可以解释其“三世进化说”与“人人皆平等”间的矛盾。不同人之所以会生活在不同世,或者说同一世之人有不同的性与命,这些也都源自于前世之善恶因果。但人人皆可自立,通过行仁义礼智来改变性命。
综上所述,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既庞杂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混乱,以其“性善与不善”思想为例,他的人性层次学说与其“人人皆平等”的政治思想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或许为了缓和这一矛盾,他将人性学说与“三世进化”的政治学说又进行了匹配,如此却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最终,笔者试着以其“命论”缓和其思想的张力,但亦会产生其他问题;即便没有逻辑缺陷,这种依靠了外力的“天命观”与“报应论”的解决方法,还是会与其“平等”“自主”“自由”“民主”的启蒙意图存在不甚融洽之处。或许,康有为思想混乱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他总是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对儒家经典进行外在社会效应的解读,以为其政治思想服务。但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相联系,他对经典由外而内的解读方式亦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