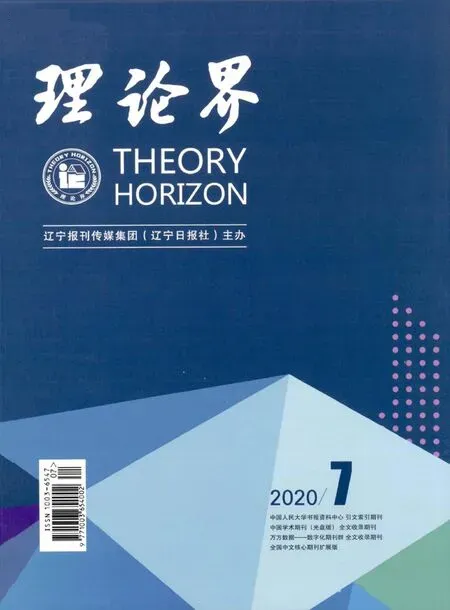略论稼轩词中的魏晋典故
姜彦章
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提出:“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也……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1〕据此,本文“典故”所指包括用古事和用成辞两个方面。“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2〕所以引经据典自古以来就是文士们写诗作文惯用的手法。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从创作角度看,一则作者运用典故可间接体现己之怀抱情志,避免过直过露,从而使诗文显得含蓄蕴藉,婉而成章;二则利用典故与当下时空的距离感言己之不敢言,不愿言。另外,从欣赏的角度看,典故因其本身沟通古今的“包孕性”而使诗文深沉厚重,进而引发读者无限联想和思考。当然,典故使用不当也会出现滞重凝涩等“隔”的毛病,难免“掉书袋”之嫌。此则须大才之人用之方显得自然熨帖。辛弃疾就是这样一位大才。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山东历城人,以词名世。他继苏轼后于词坛开豪放之风,这实则是他一生虽屡遭贬抑却赤诚不变的英雄性情之流露,然贵在豪而不粗,刚柔相济,于慷慨热烈中不乏幽深曲折之致。叶嘉莹曾指出稼轩表达自己对生命意志之感发大多通过两种形象:一是大自然界之景物,二是历史中之古典。〔3〕而这“历史中之古典”即指稼轩用经用史,通过对历史上人事之兴发感喟以抒己之襟怀胸抱的作词之法。而他这种用经用史却风流自得、如从己出的浑圆笔法也被历代词论者称道。宋末词人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就曾这样评价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4〕清刘熙载在其《艺概·词曲概》中亦曾谓:“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资是何敻异。”〔5〕赞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于词中大量用典的手法在词史上是一种开拓,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种手法本无可无不可,辛之伟大在于他以大才深情使之,用得熨帖自然。而在这些典故中,魏晋时期的人事占了很大一部分。
一、稼轩喜用魏晋典故之原因
据粗略统计,在辛弃疾600 余篇词作中,共有近200 篇作品用有魏晋时期的典故,涉及魏晋时期的人物60余人。其中仅与陶渊明一人关涉的典故就有60 首,97 处。〔6〕这足以证明辛氏对魏晋典故的情有独钟。这里举其《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一首简要说明稼轩使用魏晋典故的密集性:
君莫赋幽愤,一语试相开: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斜日透虚隙,一线万飞埃。
断吾生,左持蟹,右持杯。买山自种云树,山下斸烟莱。百炼都成绕指,万事直须称好,人世几舆台。刘郎更堪笑,刚赋看花回。
本词开篇“幽愤”暗用嵇康因吕安事被系狱后忧愤难平作《幽愤诗》之典,接着以直白体抒己对渊明归去来兮之欣羡追慕。而“素壁”一词又蕴含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一段轶事:王子敬(献之字)过戴安道,酒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辞翰虽不如古人,与君一扫素壁。”过片一句用毕茂世典,因毕曾说过“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的话。而“买山”之词亦与东晋支道林预就深公买印山相隐而遭讽之事相契。接下来“百炼都成绕指”化用西晋刘琨《重赠卢谌》中“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成句。“万事直须称好”似暗用汉魏之际司马徽品评人物“每辄言佳”之典。若宽而观之,短短一首小词竟用了七个魏晋时期人物的典故,词人对魏晋文章人事之谙熟亦可由此略窥一二。另外,此词用典之浑化自然亦可有助于我们对辛词用典高妙之理解。全词以情驭事,既是宽人,亦是慰己。用嵇康与刘琨典暗寓英雄失志之悲,而强用魏晋人物风流自适之情状勉人勉己又使词作平添了几许风流蕴藉。这两种力量互相冲击碰撞,词人之矛盾痛苦之形象也就跃然纸上,而词作本身也因其张力而显得更富层次感,更杳渺多姿。读者在欣赏此词时亦会因着这些典故而兴起古今之联想,在这些古人古事之参照下更深入地理解辛弃疾,而词味亦因此显得更加深厚绵长。这都是稼轩用事之好处。
使用典故实则是作者对历史有意无意之选择、接受,自然体现着作者之好恶取舍。那么稼轩缘何对魏晋典故如此偏爱呢?
首先,这是因为稼轩与魏晋人物特别是东晋诸人所处之时局环境相似。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异常纷乱的一个时期,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永嘉南渡之后的情形更是被晚唐李商隐讥为“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南朝》)。而稼轩所处之南宋一朝偏安一隅,外患不断,其“南与北,共分裂”(《贺新郎·细把君诗说》)的时代环境实与此有相似之处。稼轩平生志愿即收复神州,一统南北,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就曾称赞三国时称雄江东一时的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借以抒泻南宋无人的悲愤。另外他在词中也常用曹操、刘备、谢安、诸葛亮、杜预等魏晋时期名将贤相的事迹来表达自己的英雄之志。从心态来看,魏晋时期看似风流的时代风尚之后深蕴着一代士人托身无所,忧谗畏讥的强烈悲剧感和只手难挽狂澜的无力感。而胸怀为国为民一点孤忠和建功立业之壮伟抱负的辛弃疾亦因种种原因屡遭挤压贬抑,其词《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一首即可见其平生悲辛愤懑: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着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
这首词虽曰“戏语”,实则是他一生仕途心境之真实写照。所以稼轩词中多用魏晋典故实则因为他对魏晋时局和魏晋士人惺惺相惜的英雄沦落之悲,所谓“自古英雄惜英雄”是也。今古同怀,岂不然乎?魏晋士人与辛弃疾的人生都具有深沉浓烈的悲剧性底蕴,只不过魏晋士子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把这种悲升华为一时代之风流,而辛弃疾则将己之悲楚杜鹃啼血般注入他那酣畅淋漓的词作之中。连接两者的就是稼轩词中屡屡出现的魏晋典故。通过这些典故,稼轩与魏晋士人有了一种深刻的对话和交流。而深入探寻这次跨越近千年历史的对话即是本文主旨所在。
不过稼轩“羡君人物东西晋”(《鹧鸪天·吴子似过秋水》)更大程度上实缘于魏晋风度本身之魅力。相似之时局环境只不过是稼轩惯用魏晋人事的一个强烈的助推性因素。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7〕刘师培先生亦曾撰文指出:“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此其证矣。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朝士既倡其风,民间浸成俗尚,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何则?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卑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8〕而李泽厚先生亦对魏晋风度之精神行迹有如下描述:“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喝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休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环。”〔9〕魏晋风度是一个涉及哲学、历史、美学等学科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笔者无力在此作详细论述,且前贤之论亦颇精深,兹录几条,以会其义。不过魏晋风度外之狂放纵逸与内之超脱自然实是史有定论的。然此亦难以说明稼轩对魏晋风度已有此等见解,其喜用魏晋典故即因于此。但通观稼轩词作,笔者认为他对魏晋风度之理解与上引三种观点是颇有暗合之处的。
二、稼轩对魏晋风度的接受
魏晋士人以其生命之奇姿异彩令稼轩倾心。以其在词中所欲效仿的人物而论,既有出将入相、仕隐两宜的谢安、诸葛亮,又有思念家乡鲈鱼莼菜、遂命驾便归的张季鹰和归园田居的陶渊明。仕隐的揪扯影响稼轩至深。同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王子猷、酣饮为常的魏晋饮士亦经常出现在稼轩词作之中。下面略举酒、深情、陶渊明三例详叙之:“酒”为其行迹层面之一例,“深情”为其精神内涵之一种,而陶渊明则是魏晋风流之代表人物。
1.酒
李太白“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看似妄语,实则道出了“酒”在中国文化和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魏晋时期饮酒之风大盛。而提到魏晋风度,总会使人想起一段段关于酒的风流故事。王瑶先生在《文人与酒》中提出这种现象产生的两个原因:精神上追求饮酒酣畅时所达到的“真”的境界与现实情遇中为了避祸全身。〔10〕辛弃疾亦是好酒之人,其词中大量运用与酒相关的魏晋典故。人物涉及孔融、张翰、刘伶、山简、毕茂世、陶渊明等人。现举陶渊明一例说明酒之于辛弃疾的内涵。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曾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11〕而陶渊明在《连雨独饮》中亦对饮酒之至乐作出了说明:“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12〕可见,陶渊明寄酒为迹实则是一种追求任真“天全”的行为。《庄子·达生》篇中有一段关于醉者的著名论述:“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迕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13〕相较于酣饮无常或借酒全身,陶渊明对庄子这种“得全于天”则有更深的领会。这对辛弃疾是有深刻影响的,试看下例:
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沁园春·城中诸公载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为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韵》)
倾白酒,绕东篱,只与陶令有心期。(《鹧鸪天·重九席上作》)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从“终全至乐”“浊醪妙理”等句子来看辛弃疾是理解陶渊明酒中之深味的,而他也在酒中寄托了一片自然真淳之性。然而,辛之饮酒更多是伴随着英雄失意之悲的,而正因此,他对陶渊明的深羡之中也就多了几许借古人自宽自慰的意思。所以辛弃疾词中之酒也具有与魏晋士人之酒相同的双重意蕴——既是全天任性之精神追求,亦是逃避环境抒泻愤慨之现实需要。而辛弃疾在与魏晋名士以酒相交的过程中既收获了一种志同道合的自我认可,亦可在追随古人的脚步中暂时卸下英雄的抱负和悲慨,在酒给他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刺激中体会一下生命的欢欣。当然,更多时候,他得到的却是“举杯销愁愁更愁”的清醒,就像阮籍酒后之哭,令人感喟。
2.深情
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4〕其实,对自然山水之由衷赏爱又何尝不是深情之一种呢?魏晋士人之深情已非简单的儒家忠孝仁义等伦理之情,而是情动于中、形之于外的对自然、生命、存在的关怀和眷顾。竹林名士王戎曾说过:“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辛弃疾多次用到这一典故,如《临江仙·莫向空山吹玉笛》之“山林我辈钟情”,《水调歌头·酒罢且勿起》之“我辈钟情休问”等。所谓刚正之人怀情正深,英雄词人将他对自然山水之热爱,对生命时光之珍爱,对家乡故土之莼鲈之思,对家国人民之无限厚爱一一倾注于词,而这种种深情都浸透着魏晋人物的流风余韵。
以其对自然山水之热爱而言,辛弃疾曾经说过“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他也创作了很多有关自然山水的词作,著名的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丑奴儿·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等。而他这种对自然山水的喜爱通过魏晋典故与魏晋士人一道有了一种集体的抒发和呈现。如他在《水调歌头·醉吟》中直用左思《招隐诗》中的“山水有清音”表达自己对山水景物的爱赏。而《水调歌头·十里深窈窕》中“王家竹,陶家柳,谢家春”一句连用王子猷、陶渊明、谢灵运三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辛弃疾之眼前景物已经渗透进太多魏晋士人的体验和性情。除此之外,辛弃疾还常用潘岳“栽花满县”、谢鲲“一丘一壑”、王羲之“茂林修竹”、孙子荆“枕流漱石”等魏晋人物爱好自然山水的典故。另外,辛弃疾还经常通过用桓温见己种之柳皆已十围而慨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典故表达自己对生命时光的怜惜不舍,而用张翰莼鲈之思的典故寄托他对故乡的眷念。这些都是辛弃疾与魏晋士人在精神上之相同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稼轩在对自然山水的赏爱中也有借此消愁的愤慨,正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而他在对生命时光之珍爱和对家乡故土之眷恋中亦寓有词人功业未成之感喟和进退忧惧之无奈。而这也更显其情之深沉厚重。且看他的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首词作实可看作稼轩一生写照。词的下片亦用到魏晋时期张翰、刘备、桓温三人之典。通观全词,江南美景在词人眼中只不过“献愁供恨”,徒增凄凉罢了,而效莼鲈之思,求田问舍又使他心存不甘和对家国之不舍。然而流年似水,时不我与,纵使词人对生命无限珍爱,哪里又经得起如此蹉跎?想至此,稼轩不禁英雄泪落,可悲可叹。他在效仿魏晋人物时不想像张翰一样风流而愿像刘备一样慷慨,但谁又给他慷慨的机会了呢?抚今追昔,令人感伤。整首词情深意婉,充满一股郁勃之气。由此可知,纵使他热爱山水,眷念家乡,珍爱时光,纵使他也曾感叹过“人情辗转闲处看,客路崎岖倦后知”(《鹧鸪天·莫避春阴上马迟》),“而今老矣,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行香子·归去来兮》),词人胸中也始终忘不了他的家国天下,晚年复出即是明证。而这也是他的深情大爱和英雄性情使然。且不论深情之对象为何,单就深情言之,辛弃疾较之魏晋士人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魏晋深情对他的影响,不过稼轩之深情因有了他对家国天下的一份担荷而更显坚实厚重,可谓大气磅礴。
3.陶渊明
辛弃疾词中多用陶渊明的典故上文已经提到,这些典故涉及陶渊明的方方面面:事迹如饮酒、桃源路、采菊东篱、五柳先生、北窗高卧、葛巾漉酒、抚无弦琴、归去来兮、白衣送酒、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诗文如《停云》《责子》《止酒》《游斜川》《归园田居》《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等,详参袁行霈《陶渊明与辛弃疾》。可以说,陶渊明作为魏晋风度的集大成者对辛弃疾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上文已简要论述过陶与辛在“酒”上的共通性。而关于陶渊明与辛弃疾之关系,其他学者亦多有论及,如叶嘉莹先生、巩本栋教授等。需要指出的有两点:一是辛对陶的理解是逐步深化的,是随其人生阅历之深入与或仕或隐的经历而有所变化的;二是陶对辛之影响是两方面的——隐士之高远与内蕴之豪情。
鉴于论者对陶辛渊源已有颇多深见,关于此点本文从略。下面则主要谈谈罕被人论及的陶对稼轩词风影响的问题。前已提及陶渊明其人有豪放一面,而其诗如《读〈山海经〉》《咏荆轲》等在风格上亦是颇愤激热烈的。历来论者多有论及。如清龚自珍就曾作诗曰:“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三分梁甫一分骚。”其将陶渊明与诸葛亮并举就源于辛弃疾“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把酒长亭说》)一句的启发。与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在接受陶渊明时多看到其平淡一面不同,辛弃疾已能较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陶渊明其人其作。这当然首先缘于南宋一朝之现实遭际促使稼轩对生活于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的情怀心境有更切身的体验。其次便是因为稼轩自身之豪情壮意使他对陶之豪更易接受。而在这种接受中,稼轩主动在词中学习这种风格也就不在话下了。而稼轩之豪放词风的形成多少应有陶渊明的一些影响吧,更不用说他那种本色自然的平淡之作了。其对渊明诗风的认可赞赏在其词中亦有直接体现。请看《鹧鸪天·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
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词上片对渊明安贫乐道的高远情性进行了歌颂,下片则主要论及渊明之诗作,而他对渊明诗所下“清真”二字之断语实为知言。文如其人,此二字本是渊明淳朴自然性情之外露。而这二字亦可用来评价稼轩词风,只不过“清”由渊明之清醇干净变为辛之清刚壮大。而在诗词中抒发真性情真怀抱亦是二者深相契合之处。这种“真”即将自己的生命志意真切地投注到作品中,不虚不假,真正做到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正如《庄子·渔父》篇中所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辛陶同为精诚情深之人,辛由此赏爱陶诗、陶人也就不以为奇了。不过渊明真气内潜,故渊深朴茂;稼轩真气外显,故酣畅淋漓。看似两种不同的风格其实源于相同的文学观念。故“清真”既是两人性情相近之处,亦是二人诗词风格相合之点。而从诗词风格方面理解陶渊明对辛弃疾的影响不失为一条新的路径。
三、结语
本文从稼轩词中所用魏晋典故入手,分析了稼轩喜用魏晋典故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稼轩所处之时局环境与魏晋相似,故易引起惺惺相惜之感;二是魏晋风度本身之强烈魅力使稼轩倾倒。接着,通过酒、深情、陶渊明三例深入分析了这些魏晋典故中所蕴含的深层内蕴——稼轩受魏晋风度之影响非常深刻,然此中亦有他所处时代和本人性情所赋予他的新的东西。另外,通过陶渊明一例,笔者提出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风度不仅影响了稼轩其人,亦对其词风有重要影响的观点。所谓“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通过辛弃疾词中的魏晋典故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稼轩对魏晋风度的态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稼轩其人其作,这即是本文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