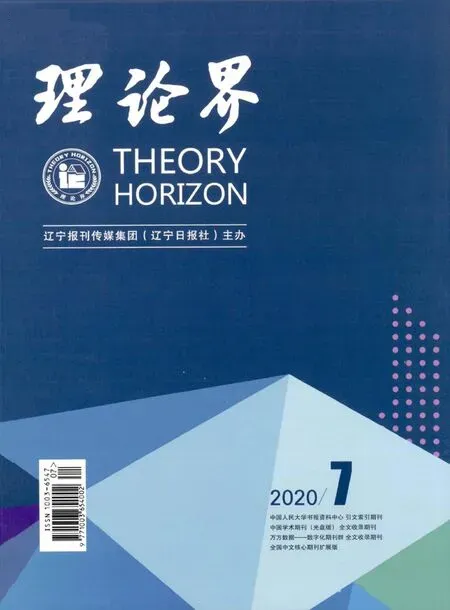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建构的传统资源研究
牛思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承接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把“自由”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既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基础上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借鉴与超越,也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积极的扬弃。因此,在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的同时,有效挖掘中国传统自由观的内涵,有利于进一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让古代哲学精神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焕发生机。
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初创期,其核心性理念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无为”思想是先秦诸子的共有主张,张舜徽先生指出:“吾尝博观周秦诸子,而深疑百家言主术,同归于执本秉要,清虚自守。”〔1〕儒道两家哲学理论中的“无为”性倾向虽有共通之处,但也存在显著差异,从儒道互补的视角着重阐发“无为”理念的当代价值,关注其与现代“自由”思想的内在契合,有助于传统文化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现有研究,或多从整体性视角探讨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或多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进行论析。相应地,对传统文化中具体思想的深入解读尚显缺乏,较少在中国哲学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理念之间展开研究。本文以作为中国哲学原发性观念之一的先秦儒道“无为”思想为基点,从三个维度分别论证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本质关联。
一、自由的前提:个体性的“无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虽在社会层面提出,但出发点和落脚点还应体现在每个个体上。对儒道“无为”思想的解析发现,其显著特征之一便是以个体性指向为前提,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思想在发生机制、本质内涵以及外在表现上有一定程度的相融性。
第一,“无为”思想和“自由”理念来源于对个体自身不自由状态的抗争。从“无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看,自西周以降的礼乐文明,当它成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后,带给被统治阶级的不是自由与解放,相反是束缚与控制,对人类自然之性的压抑,使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地位彻底丧失。在老子哲学中,礼乐文明施加给个体自身的不自由体现在三方面。首先,物欲膨胀使自身不自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其次,政事严苛使自身不自由。“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最后,礼法繁杂使自身不自由。“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义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庄子则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中种种不自由现象的体察,进一步提出了“人为物役”的观点,具有原始朴素的异化论色彩。他所主张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相忘于江湖”(《庄子·天下》)、“无待于外”(《庄子·逍遥游》)、“心斋”(《庄子·人间世》)、“坐忘”(《庄子·大宗师》)等境界,便可看作是对“人为物役”状态的反拨和个体自由的向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理念,以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为本源,继承了“无为”思想对个体自由的追求。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保障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削弱物欲方面施加给自身的不自由状态;建立并完善各项国家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减弱因政事严苛造成的自身不自由程度;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不断提升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水平,防止法令繁杂带来的自身不自由境况。总体而言,使个体自身从外在的束缚下得以解放,才是通达社会主义自由的前提。
第二,“无为”思想和“自由”理念指个体本性的复归。这在道家思想中体现为对个人“自然之性”的尊重。老子认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可见,将“自然”作为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也隐含了通往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即“功成事遂”的社会自由是在没有外在压迫,百姓获得“我自然”的个体自由基础上建立的;而其视为道之本性的“朴”,更是指未经雕琢的本然状态,是在去除人为的“华”“伪”“巧”“薄”后,向事物自身本质和规定性的回归。庄子“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庄子·骈拇》)的观点是对个体自由意向在更高层次的体认,“正”指事物的本真之性,按照郭象的《庄子注》“正”亦可指“各得其正”,〔2〕即让天下之人根据各自的天性自由发展,各展其性,给予个性自由舒展的空间。质言之,“天下大治”的社会自由状态,一个题中应有之意是保证个体具有真实的自然本性,这是作为独立个体其自由属性的重要标识。
在社会主义的“自由”价值观中,个体自由指人掌控自身本质的主体性,使每个人能依照自身天性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加深,个人根据兴趣、专业、特长等从事劳动,进而满足个体的生活需要,不断拓展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这与传统“无为”思想中强调对个人“自然之性”的尊重有着相通之处,是对个性自由在更高现实基础上的体认。人只有“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才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真实个体,才具备完全自由地发展自身的能力;否则,占有自身本质的片面性,人便无法拥有全面的主体自觉,仍旧是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个体,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前提受到某种束缚,人始终生存于各种依赖性桎梏之中,不能通达本体规定性上的个人自由。
第三,“无为”思想和“自由”理念表现为人生修养和社会治理中个体性的先在指向。儒家“忠恕”之道式的“无为”思想讲求“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将“仁”“义”“礼”“智”“信”等社会伦理约束,从外在强制转化为道德主体发乎本心的自觉追求,建构起“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个人主义自由观,以内心“无为”通达行动自由,实现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自主性;并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推己及人”式方法论,以独立个体的自由带动一切个体从社会性束缚中解放出来。道家“无为”则更多表现为人生取向的目标价值,用理想人格的设计实现社会治理中的和谐。道家理想人格的本质特征是“无名”“无功”“无己”,其中最根本的是“无己”,因为人所追求的名利、权势、金钱等都以“己”为前提,只有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彻底忘记“自我”,才能达到“逍遥游”的淡薄养神之“道”。而“乘万物、御群材之所为,使群材各自得,万物各自为,则天下莫不逍遥矣,此乃圣人所以为大胜也”,〔4〕让万物“各当其分”“各自得”“各自为”会使诸事物之间形成一种自发协作式的和谐,通过“忘我”的个性舒展完成主体的人生修养,从而能“物各率能,咸自称适,故事事有宜而天下治也”。〔5〕
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表现形式,应将公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儒道“无为”思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带动社会的和谐,与之相类似,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自由,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思想道德修养的目标也应是促进人的个性解放,这既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指向。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6〕通过“有意识”的主体自觉将外在法律约束转化为内心道德规范,保障最基本人权;而内化于心的主体性道德,因其对个人生存与发展权利的促进,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自由活动,即具有社会实践基础的普遍性社会治理,用个人道德修养带动社会治理中广泛自由生成。
二、自由的保障:有限度的“无为”
在对个体性给予肯定的前提之下,“无为”和“自由”代表了一种主体自觉的自在、自为状态,但解除依赖性关系限制却不意味着为所欲为,“有了限度并在限度之中就有了自由,同时自由也就得到了存在”,〔7〕“有限度的自由”正是自由得以成其为自由的根本。事实上,无论是主体自身或是更广阔的社会群体,实现自由的过程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制约,这是儒道“无为”思想与社会主义自由在条件限定上的共通之处,也是全面、完整、真实自由的保障。
自由的规律问题其实质是把握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超越,自由与必然因相互依存而辩证存在,二者的统一才是真正的自由。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关键,就是先要对自由的必然性进行体认。有必然性的自由是对主体以及主客体双方,在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多重规律之内的理性尊重。
主体上,“无为”和“自由”都尊重人自身的内在必然性规律。儒家“无为”建立在“修身”基础上,以正确价值导向为限定,融入个人修养中,促进身心和谐与个体完整性的升华;而“惟其心无欲而静”的“正心”主张,则是要摒除各种意欲杂念,不因一己之私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道家以“尊道贵德”为条件,强调尊重人的自然之性,对人的类特性在最大限度内予以提升,亦是鲜明的人本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人自身内在必然性,一是指对人之生理、心理、精神等方面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认和充分发展;二是指在个体自由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即个体的内在必然性以他人的自身内在必然性为保证。用联系的观点看,自由从来不是个人行为的肆意妄为,无限制的绝对自由其实质是不自由,在破坏他人自由的同时,使自身的自由亦不可得。因而具备高度的思维自觉与理性选择,用内心的道德尺度妥善衡量自身潜能的充足发挥,才是自由的真正彼岸。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尊重人内在必然性的自由,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为本,切实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以满足某些抽象个人或少部分人的需要为价值指向,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主客体之间,“无为”和“自由”的限度性体现为以下两点:
一方面,“无为”和“自由”都尊重自然界的必然性规律。儒家的宇宙论重视物质世界的客观秩序与法则,顺应其运行的内在必然性,强调对“天命”的敬畏。尊重“天理”“天道”基础上的“无为”,落实到现实层面上就是以天制人,注重“天人感应”,使人在“自然”“天道”面前知所畏惧、不胡作非为,从而达到人天和谐的内在自由。道家的自然哲学,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将“天人合一”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最高境界。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地人三者遵从共有的规律,处于一个共生共存的统一体中,要对自然天道心怀敬畏,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获得发展、实现自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理念,也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首先,人类要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规律为开展自由的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其次,人类不能忽视客观世界的先在性与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在自然界所能承受的合理限度内符合规律地改造自然。从现实意义上讲,要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决定论”两种极端化泥淖之中。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与自然的矛盾却愈发凸显,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威胁人类向自由之境迈进。于当下中国而言,尊重自然界的必然性规律,促进社会自由,一个重要指针就是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优先、人与自然相和谐,是中国哲学的深刻内涵,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指导,是人类历史教训的经验反思。归结来看,以“天道无为”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传统“无为”思想与社会主义自由价值观的融通之处。
另一方面,“无为”和“自由”都尊重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曾有学者断言,“历史之于东方恰如宗教之于西方”,中国文化中信仰历史的传统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儒家的“无为”思想中。对此后世曾有论及,“古之天子未尝任独断也,虚静以慎守前王之法,虽聪明神武,若无有焉,此之谓无为而治。”(《读通鉴论》卷13)儒家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构成,就是以历史为限,建立起对前代史实、圣贤权威与后世史书工笔的双重敬畏,防止统治阶级专制独裁,以“守虚主敬”式的“无为”保障社会“相对”自由。“无为”思想顺应历史的合规律性又一体现是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作为传统哲学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为”思想诞生于古代自然经济的条件之上,稳定性是农业社会得以维系的首要依据。在此背景下,统治者维持社会安定有序,没有利用统治规则在政治上有过多作为的必要性;普通个人只需“各安其位”,也不具备“有为”的内生动力。概言之,敬仰历史并受社会发展规律限制构成了对社会历史必然性的尊重,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即是“无为”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其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律。从实践背景看,使古代“无为”思想与现代社会相承接,应做到如下两点:第一,尊重历史,这是“自由”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与西方自由价值观之间的明显区别。西方自由观凭借普世价值的外衣,实际是在宣扬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断同化乃至消解非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无为”思想具有建构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让各国的历史文化获得多元化发展的空间。第二,将“自由”置于现实的历史阶段考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强调尊重社会历史必然性规律,指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限制,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为实现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保障。
三、自由的目标:社会性的“无为”
儒道“无为”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在各自的前提与保障方面具有一致性,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目标相融才是两种思想和价值观念之间得以建构起联系的根本。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普遍性社会自由,个体范围内、有限度的自由还不是真实的自由,它只是全人类解放的过程,社会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必然要将过程性寓于目标性之中,以社会性的全面自由作为终极追求。与之相应,寻觅社会广泛自由的愿景,也体现于古代“无为”思想的某些方面中。
首先,在逻辑指向上,“无为”思想和“自由”价值观具有公共性倾向。儒家“无为”理念的发生机制,展现出 “公天下”的社会期望,而非私独性的抽象“自由”。就儒家政治哲学的角度,“这种无为思想首先来源于儒家思想深处的某种‘幽黯意识’”,〔8〕即“对于君主专制制度固有缺陷的警惕、对于君权不信任感,乃至于对现实展开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悲观态度”。〔9〕因此,落实到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中,便是强调“无为而治”。换言之,儒家“无为”思想与“私天下”的社会现状之间存在着冲突与错位,后者并不是其理想政治模式建构的原初指向,以公有性为标志的“三代之世”或许更利于该治理模式的合理化实践。孔子指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舜的“人君南面之术”正是“垂衣拱手而治”的“无为”思想最生动的践行,亦可看出儒家“无为”思想对尧舜禹时期“公天下”自由社会的渴望。道家认为,“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二十九章》)其中的“天下”可简单理解为“天下人”或“国家政权”,对公权力的谨慎与敬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社会“朕即国家”的“家天下”观念,是道家向往公有社会、憧憬社会自由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价值观反映了传统“无为”思想中蕴含的自由精神。在私有制条件下,对人和物的依赖关系是导致不自由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取代之,才有可能完成全社会的彻底解放。恩格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0〕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物质生活充分发展之下实现的自由,将具有社会性的内涵,是真正的自由。虽然在“无为”思想产生的传统社会中,古代思想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对上古公有社会的追溯,却流露出该思想深处的公共属性,与社会主义的“自由”理念深度融通。
其次,在实现方式上,“无为”思想和“自由”价值观以“德化”形成最具广泛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儒家看来,“无为”和“德政”实为一体两面。《论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将为政者比喻成静止不动的北极星,暗示了儒家“德化”式“无为而治”的治理思想,即拒斥违反“德性”的作为,其“无为”建立在实践道德教化的过程内。儒家社会治理哲学的基本进路是:强调“德化”的优先位置,统治者是通过道德教化民众,而不是用刑罚政令、严苛峻法惩戒之,以懿德懿范来感化被统治者,使其自愿、自主地服从并参与社会事务。要言之,“君主的‘无为’即在于只是通过其个人的修养与民众产生相互的影响,而不需要以专制的方法统辖其臣民”,〔11〕使“无为”与“德化”相配合,用君主和民众之间的某种“相互影响”,在社会中形成最大的治理效能,并带动最广范围自由状态的产生。
“自由”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社会层面的首位,统领“平等”“公正”“法治”。从中国传统自由观的角度,“德化”是实现社会自由的重要方式;那么社会的平等、公正与法治是自由在不同方面的体现,要想达成同样需要借助“德化”的作用。“德化”式“无为而治”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的“相互影响”,故而其潜在预设是承认每个人在道德上的平等地位,道德主体本身不会有所偏私,被化育客体也不会接受到选择性差异,因此,“德化”是维护社会平等与公正最具一般性的手段之一。进一步来看,“德化”是柔性的法治,其主体自觉性的认同感可能比法律制度的施行更具深远持久的生命力,“德化”式“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理解德法关系,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有积极启示。
最后,在生成路径上,“无为”思想和“自由”价值观各自经历了“社会——个人——社会”的衍化过程。如前文所述,“无为”思想的个体性意蕴对发展个人自由有所促进,个人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前提,一切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定要以每个人切实可得的自由来逐步带动全社会的自由,即在自由实现的操作性层面上经历“个人——社会”的变化。但整体社会向度的全面自由才是真实自由,因而社会自由既是应然上的目标又是实然的出发点,最终呈现出“社会——个人——社会”的演进路径。
在儒家由“无为”到“自由”的思想演进中,鲜明表现出其社会性的目标。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家族血缘的自然亲情关系为基轴,在重建体现亲疏差序格局、尊卑等级秩序的社会大背景下提出,用社会性的伦理自由当作“无为”的约束前提,通过建功立业达成理想人生境界的设计。分解来看,以社会性价值观念为前提,引导个人自由的实现,呈现“社会——个人”的发展轨迹。现实中,这一整体进程的各部分、各步骤间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即个人与社会之间非彼此对立而存在;相反,中国文化中强调兼顾社会、个人共同发展。“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12〕是其悠久传统,实则是对个人与社会相融共生在更高层次的认同,从此维度上说,无论是注重个体性或社会性的“无为”思想,抑或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都具有同一性,即个人与社会两极相通。
儒道“无为”思想的社会性指向,建构在个人与社会统一的基础上,其自由的目标体现了集体主义倾向,使“无为”思想成为与社会主义的自由价值观相建构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是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一个切入点。从社会主义自由观的视阈来看,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并非实体性的决然对立,而是关系性的:双方“互相决定、相互生成、彼此同构,并历史地发展”,〔13〕是一个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互为目的和手段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一方面,个人自由包含社会自由。“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14〕个人若想实现自由,就必须成为社会化的人,参与到“自由人联合体”当中,利用社会为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使其本质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唯一可靠的保证”,〔15〕要通过制度优势,在社会自由的总目标下最大限度保证个人自由。另一方面,社会自由依赖于个人自由。个人越是自由,社会越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就越是向具体、全面、真实的社会自由靠近。只有以每个人都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个人自由为前提,又不以牺牲他人自由作为保障,让个体性与社会性高度统一、共生共进,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的要义。
四、结语:从“无为”到“自由”的逻辑演进
“无为”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自由”价值的看待,它既肯定个人自由的意义,也注重自由的限度问题,强调尊重人自身、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最终以实现社会整体的自由发展为目标。儒家将“无为”思想融入人生的道德修养和治国理想之中,偏向于伦理自由;而道家把“无为”置于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位置,追求的则是本性自由。在中华文化的发展演进中,儒道“无为”思想通过碰撞交融不断被阐释出新的内涵,二者共同形成了对相关问题思考的逻辑范式和价值理念。从传统“无为”思想到现代“自由”价值观的演进,是结合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以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为条件,创新发展的过程。近代以来,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对“自由”价值的追寻主要表现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将个人“自由”的实现融入国家民族的整体“自由”之中,用国家的自由解放推动个人自由的达成。因此,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鲜明体现了这一历史阶段“自由”的核心价值。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促进人和社会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始终被列为社会主义“自由”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蕴藉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价值的构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它能够反映现实基础之上的美好生活指向,又凝结了对人之生存与发展和意志自由的更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