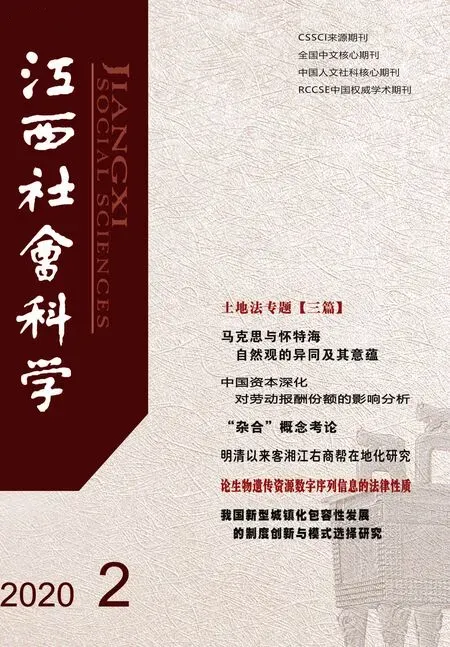明清以来客湘江右商帮在地化研究
“江西填湖广”,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移民活动之一,历经元、明、清,构成明清时期湖广地区人口的主体,成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位,开创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辉煌。伴随着移民浪潮入湘的江右商从行商、坐贾到定居,他们遍布湖南城镇,渗透于各行各业,并因共奉许真君为福主而结帮设馆,逐渐形成了著名的“江右商帮”。作为客商的江右商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在矛盾与冲突中实现在地化过程,并受近代市场环境与制度性因素影响,以同业组织融入地方商会,实现了地缘组织向跨地域业缘组织的转型。商帮的流动性以及渗透性在对湖南商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成为两省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天然纽带。
“江西填湖广”,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移民活动之一。有关它的研究,开启于谭其骧1930年发表的《中国移民史要》以及1933年发表的《湖南人由来考》[1],他依据五种地方志和一些文集中的氏族资料,对湖南七个州县的移民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曹树基在谭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写就一篇《湖南人由来新考》,并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2],对湖南、湖北的诸县氏族人口增长率进行统计分析。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则利用收集到的472部族谱资料着重进行了移民湖北的情况分析。[3]伴随着移民活动的江右商从行商、坐贾到定居,他们遍布湖广城镇,渗透于各行各业,并因共奉许真君为福主而结帮设馆,逐渐形成了著名的“江右商帮”。关注两湖江西商人活动的研究,则最早可推傅衣凌对明代江西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的研究,体现在1956年结集出版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4]。他在《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5](P193-203)一文中讨论了人口外流与江西商人形成之间的关系。方志远则系统地就江西商人的兴衰、经营方式、经营行业、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几个方面进行了宏观总结。[6](P356-421)他在另一研究中,对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商品流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7],认为江西工商业人口的流动,既促进了两湖地区的发展,又激发了本地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上把握江西商人商业活动的还有张小健的江右商帮研究。此外关注江西商人在湖南活动的,还有邵鸿[8]、吴金成[9]、杨福林[10]等,他们从江右商人与经商地、商人与原籍两个角度,揭示了江西商人与明清以来湖南社会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和视野。笔者主要以客寓湖南的江右商和商人组织为研究对象,从移民入手,讨论明清以来作为客商的江右商逐渐融入湖南地方社会,实现在地化和商人组织转型的过程。
一、明清“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活动
中国移民活动古已有之,可以追溯到周礼记载,如《周礼·秋官·士师》中记录:“掌士之八成:……八曰为邦诬。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11](卷三五,P237)这里就提到,如果邦中发生谷物歉收引起饥荒时可采用的救济方法之一,便是可以让受灾百姓迁往谷物丰收、价格较贱的地区。历史上移民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有自觉与制度安排,有被动与主动,涉及迁出地对移民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其迁徙路线因不同时期而不同,大多为内迁、西迁和南迁等就近迁徙,也有定居后再迁的。在众多的移民活动中,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是其中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之一。
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湖广一省,一方面说明两地自然人文地理不可分割,另一方面说明两地以前大部分皆未开发成熟,而此时的江西由于赣江贯穿整个江西南北,田畴较早开辟,人烟最为稠密。同时江西毗邻湖广,因而较早发展的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大多就近移民。最早关注湖南人由来的谭其骧特别提到江西移民湖南的总体原因:“江西人之移入湖南,其原因几纯经济的,江西而外,外省人之移入湖南,则经济的原因之地位较低,另有政治的原因在焉。”这里所指政治原因,主要是明代卫所镇戍制度下的从征、谪徙和从宦落籍。[1](P323-324)
造成江西填湖广移民的因素既有内外因的推力和拉力造成的自觉选择,也有外在制度安排下的被动迁移,可以说是多方因素的合力使然。
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的经济便开始了快速的发展。丰富的物产资源使得江西的粮食、茶叶、瓷器、纸张、油料等产业都在全国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大运河航道与大庾岭商道开通后,特别是随着一口通商的限定,该商路成为连接南北和出海的唯一通道,也是明清时期最繁忙的商路。过境贸易带来了江西市镇的兴起,也带动了江西经济的繁荣[12](P7-51)。《唐国史补》载江西航运之发达:“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沂流而上。”[13](卷三)《宋史》载江西经济之繁荣:“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而茗、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14](卷八八《地理志·江南西路》,P2192)
优越的物产和交通条件促使江西的经济迅速增长。至明代,江西的经济发展依然迅猛。洪武年间,江西的秋粮征收量258万石,在十三布政司中位列第一。[15](卷一九《户部·户口总数》)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人口的激增,根据曹树基统计,洪武十四年(1381)江西的人口为898万,在全国仅次于浙江,而与之接壤的湖广仅为459万,几乎仅为江西的一半。[2](P34)而湖广地区幅员辽阔,耕地面积远大于江西。从田亩数量上看,洪武二十六年湖广地区的田亩数为2.2亿亩,而江西仅为4300余万亩,面积约是湖广的1/5。作为纳税大省的江西,沉重的赋役也促使江西人逃离故土。所以,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就近从人多地少的江西向地广人稀的湖广迁徙,形成向外移民的推力。
元朝末年鄱阳湖地区的战乱,是造成江西填湖广的外在拉力和制度安排的直接因素。元末明初(1364—1368),明太祖朱元璋和陈友谅在两湖地区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战争,使得当地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而江西除了鄱阳湖地区,其他地区几乎未受到战火波及,社会经济状况良好。为了改变地区之间经济人口不平衡的状况,稳定国家对地方的统治,恢复农业生产,明朝政府采取了军事屯田和强制迁徙的方式,将人口从人口富裕的地区迁往饱受战火摧残的地区,并允许“插标占地”。对于湖广地区而言,与之相毗邻的江西,自然就成了主要的人口来源地。如《万历湖广总志》记载:“自元季兵燹相仍,土著几尽,五方招徕,民屯杂置,江右、徽、黄胥来附会。”[16](卷三五《风俗》)此外《明太祖实录》也记载了洪武年间迁江西民到湖南常德等县事,文称:“常德府武陵县民言武陵等十县,自丙申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无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劝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上悦其言,命户部遗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17](卷二五○,P3619)
此外,明朝政府在强制迁徙的同时,还给予了移民一些优惠政策:“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17](卷三四,P615)在政府的强制措施和优惠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大批江西人离开故土,向湖广迁移。
谭其骧1930年发表的《中国移民史要》以及1933年发表的《湖南人由来考》拉开了中国移史民研究的序幕。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一文对湖南人的来由进行了详细考证。他依据五种地方志和一些文集中的氏族资料,考察湖南七个州县的移民情况后认为,湖南除苗、蛮外,无所谓“土著”,凡是汉人,都应该是其他地方徙移而来的,但有些因为徙移既久,子孙或许不能忆起祖先所自来,所以也就成为“土著”了。谭先生在对现今湖南外来移民已知原籍的517族进行考察后,认为:“江西省最多,占全数几及三分之二,湖南本省次之。此湖南诸族若再考求其祖贯,则其中太半当又系江西人也。江西以外之外省移民,合计不过百分之二十六;而其中又以江苏、河南、湖北、福建、安徽诸省为较多。”就江西而言,“泰和最多,丰城、庐陵次之,南昌、吉水、安福又次之。泰、丰、庐三县合计共得百五十族,较之江西以外各外省之总数,犹多十六族。六县合计共得二百二十八族,占全移民数十之四,全省移民数十之七”。并分析其原因为开发先后之程序使然。[1]
曹树基在谭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写就一篇《湖南人由来新考》,并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对湖南、湖北的诸县氏族人口增长率进行统计分析,这样我们既能看到氏族的来源,又能了解到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来源人口的增长率的变化。比如他通过大量资料统计出在湘南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东晋4.1%、南朝5.2%、唐5.7%、五代7.0%、北宋7.6%、南宋8.4%、元9.0%、洪武9.4%、永乐9.5%、明中后10.1%,移民逐年增长。洪武年间湖南湘南三府的人口约103万,加上永州卫、衡州卫及桂阳、郴州、道州三个千户所,共有兵士及家属4.5万人,因此三府人口约107.5万。其中18.3%为元末及洪武移民,即约有移民人口19.7万左右”。又通过统计得出,“长沙地区在洪武年间迁入424个氏族,其中345族迁自江西,占总数的81.3%。”[2](P99、P101)
因为官方资料的有限,大部分学者多采用族谱进行移民的研究。虽然族谱多有附会虚假的信息,如谭其骧所言“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1](P323-324),但其他的内容如迁祖姓名、迁出地、迁移时间、迁入地等情况则比较可信。张国雄有关两湖移民的研究大部分用的是他所收集的472部族谱资料(反映迁入湖北移民的327部,迁入湖南移民的145部),并将之整理成为《移民档案》[3](P257-286)。他指出:“在《移民档案》提供的530个家族中,世居湖南、湖北的有35族(湖南13族、湖北22族),只占总数的6.6%。余者有8族迁出地不明,另外487族迁自以江西为主的十几个省,占家族总数的92%。换言之,今存两湖家族中有百分之九十几为移民家族。其中,江西籍就有404族,占移民家族的83%,占两湖家族的76%。”[3](P35)并且在对迁出地为江西的族谱分析中,他认为湖南的江西籍移民主要迁自吉安府和南昌府,这与谭其骧的结论相同,而湖北的江西籍移民则主要迁自饶州府、南昌府和吉安府。[3](P67)
“北有山西大槐树,南有江西瓦屑坝”,江西填湖广移民中的瓦屑坝传说,与大多数湖广江西人记忆中的南昌筷子巷同出一辙,成为一种当地人的集体记忆[18]和认祖归宗的标签。而伴随着大规模移民而来的是商人的流动和移民。
二、从行商、坐贾到定居:客寓湖南的江右商帮及其分布
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正是江西移民运动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江西移民的特征。明代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中记载:“(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正说明了明代江西移民中有大量从事工商业活动这一特征。[6](P367)商人与移民以及其他流动人口有所区别,移民多是通过农耕直接定居,正如前面提到的“许民垦辟为己业”“迁贫民开种”,其他流动人口更在于短期的流动。而商品的持续输入和输出以及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商人在湖南滞留的时间,都较一般流动人口时间长且稳定。一些行商因商务活动的需要转变为坐商,相当部分商人慢慢从坐商定居下来,便完成了由流动人口到移民的过渡。从明到清这种例子很多。湖南湘潭陈氏始迁祖裴公于永乐年间“自江右贸易于湖广所属之湘潭县,因睹斯邑人心浑厚,风俗朴醇,遂寄藉于潭”①。同样是湘潭的张氏始迁祖张京禄于永乐二年(1404)由江西“货殖而来”,“挟赀贸易,居积累千,家于斯”。②张京的定居不同于陈氏一入湘便爱慕山水而迁籍。他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营,其商业规模扩大之后才定居下来。这是商人转变为商业移民的主要类型。再如湖南龙山县商业移民,“其先服贾而来,或独身持袱被入境。转物候时十余年间,即累赀钜万,置田庐,缔姻戚”[19](卷一一《风俗》),成为龙山县民。醴陵县“赣人习商,后先以贸易至县,因而置产成家者亦不少”[20](《氏族志》,P535)。商业资本向土地资本的转移,个人婚姻状况的改变,是商人转变为商业移民的内在因素。
商业移民的足迹一直深入最基层的乡镇。商业移民在各级城镇的商业活动,构筑起一张庞大的能量级的商业网络,汉口、长沙为一级枢纽,长江岸边的沙市、岳阳、湘潭为二级枢纽,县镇为三级枢纽,无数乡镇则是基点。商品通过商业网络的输入和输出,沟通了分散的孤村僻壤与各级商业城镇的联系。省内外商品的交换,还把湖南区域市场纳入了全国的大市场。
湖南的商业活动,主要依靠商业移民进行,而尤以江西商人移民为甚。清初三藩之乱平定后,湘潭县“城总土著无几,豫章之商十室而九”[21](卷一一《货殖》)。乾隆年间,湖南省会长沙府所在的善化县土著“为商贾者殊少”[21](卷一一《货殖》)。清后期,湖南湘乡、衡阳、邵阳、新化也形成了商业群体。但是从总体上讲,外省籍商业移民仍占有优势,居湖南商业活动的主体地位。与外省的商品交换主要由他们来完成,本帮商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省内。
会馆是移民的标志,“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敬桑梓地”[3](P64)。在这里同样可利用湖南会馆的修建情况反映移民的来源以及分布。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第四、五章中统计了湖南22个州县和湖北28个州县以及汉口镇的会馆数量。张国雄以此为基础将统计范围扩大了近一倍,湖南达到42个州县,湖北增到49个州县镇,在两湖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据张国雄的统计,湖南会馆178座,湖北有295座,共473座。其中有118座为两湖人所建,占总数的24.9%,另外355座会馆的省区构成如表1所示。

表1 张国雄所统计两湖会馆的外省区构成[3]
江西会馆与万寿宫几乎是同一代名词,因江西人共奉许真君为福主而结帮设馆祀奉,会馆多设在万寿宫内,会馆内也必有许真君的祭祀场所。万寿宫遍布各城镇乡里,湖广尤甚,成为客寓在外江西人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和会馆既是江西移民的精神家园,更是跨地区江西商人的行业同业组织,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商帮联络纽带。这里有统一的信仰、统一的规范,有乡音,有交流和扶持。从表1可见,江西会馆有147座,占41%,可见两湖地区江西商人分布之广,人数之众,经营项目之广。湘潭在清朝号称“壮县”,该县知县号称“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一年三万的白银,全靠商人进纳。县城极盛时有56个商人会馆,其中16个属江西商人。[22](P242)
章文焕在2004年查出湖南省46县有万寿宫95所,湖北省有万寿宫44所,共139所。其中武昌1所,汉口1所,武昌时间最早,汉口规模最大;湘潭3所。[23](P409-416)后来其又陆续统计,查出“在湖北、湖南两个邻省,以汉口、沙市、长沙、湘潭、常德为中心建万寿宫153座”③。
邵鸿早期在讨论湘潭地区的土客矛盾时,也提到湘潭江西商人的情况[8](P84、P96)。他检寻上海图书馆所藏湘潭一地家谱的提要,在总计350余种中,除去不详所由的50余种,至少有200种其祖上系从江西迁来,且绝大部分是在明代至清初入迁。此后续有客民入迁,仍以江西人为多。且与此前移民不同,他们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并引用朱克敬在《瞑庵杂议》卷一所言:“湘潭居交广江湖间,商贾汇集,而江西人尤多。”光绪《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东界最近江西,商贾至者有吉安、临江、抚州大帮,余相牵引者不少胜数,牙侩担夫率多于土人,争利才颇仇之。”[21]《清仁宗实录》嘉庆二十四年(1819)六月戊申记载:“据奏湖南湘潭城外,向来江西客民在彼贸易者十居七八,本地居民不过十之二三,各马头挑夫,江西人尤多。”以此进行论证。
关于湘潭县境会馆情况,可以从光绪《湘潭县志》卷七《礼典》篇所作《群祀表》及卷十一《货殖》篇中所记得知大概。《群祀表》会馆一栏,分省籍记载了各地商人所兴建的会馆数量、名称与建立的年代等情况,各地商人在县境内建立的会馆总数计有30所,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为北五省,共1会馆,江苏4馆,广东1馆,福建1馆,湖北3馆,永州1馆,郴州1馆,衡州2馆,安徽2庵,广西1馆,江西13馆。
江西省凡十三馆:万寿宫,在十总,宋宣和间,以旌阳观为万寿宫,顺治七年,江西客商建。乾隆时,杨锡绂、彭元瑞有记。殿堂馆园,最为宽壮,修饰辄用十万金。南城检讨连培基为之记。一都在株洲,十二都在易俗河,十七都在石潭街;昭武宾馆,在十总,抚州公所;临丰宾馆,在十一总,临江丰城县公所;安城宾馆,在蓚行街,安福县公所;……石阳宾馆,在十五总后街,庐陵县公所也。乾隆中刘智贤倡捐千金,众助数千金成之。光绪六年更拓新基,作培兰轩,连培基为之记。又有石阳山庄,在万寿宫后。又有别墅,在六一庵后。袁州宾馆,在梧桐街,袁州公所;禾川宾馆,在梧桐街,永新公所;琴川宾馆,在十六总后街,莲花厅公所;西昌宾馆,在琴水旁,太和公所,刘宗绪有记;仁寿宫,又曰江神祠,在上十八总,临江府公所。六一庵,在十六总,普度庵,并江西省公所;财神殿,在黄龙巷,江西广货行公所。十八总公裕堂公宇,亦名财神殿,铺屋二所,为本街公所。[21](卷七《礼典·群祀表·会馆》)
江西会馆占总数的40%以上,且所建会馆规模宏大,耗资颇多,可见江西商人在当地的实力。
湖南湘潭为全国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有“药都”之称。江西临江、吉安、抚州在此形成三大商帮,控制着湘潭的商业,“临江擅药,岁可八百万”[21](卷一一《货殖》),并形成了完善的药材商业管理组织“八堂”[24],即崇谊堂、金美堂、崇庆堂、崇福堂、福顺堂、聚福堂、怀庆堂、公正堂,分别是药材行老板的组织、药材行员工的组织、药材行买货客的组织、药材行经营川货的组织、药材行经营汉货的组织、药材行经营淮货的组织以及药材行统一校秤的组织。这种成体系的行业组织还不多见,但足以反映江西商人对市场的渗透力。乾隆时期,江西商人涌进湖南凤凰城,形成江右商人居住区——“江西街”。“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这是祖籍高安后居凤凰城的著名作家沈从文,描写江右商人在凤凰城创业的景象。江右商人在凤凰城与常德、长沙和汉口“来往贸易”,并先后出现被誉为“凤凰四大家”的熊祥昌、庆丰祥、裴三星、孙森万四大商号。
在众多江右商从行商到定居于湖南的例子中,吉安刘氏家族亦是一个典型。吉安市吉安县澧田镇清水村如今仍保留了一大片近代建筑,计祠堂6座,祠堂四一墙4处,民居约40栋,书塾2栋,节孝牌坊1座,古墓1座。这些建筑就是由刘氏家族商业移民湖南者出资兴建、修缮的。清水村所属的澧田镇地跨泸水下游两岸,清水位于泸水西岸,经由水路西行,清水可便利地沟通湘江南北以及洞庭湖周边地区,因而这里的居民外出首选湖南。从族谱看,早在明代清水刘氏族人就有徙居湖广临武、衡山、浏阳、宾庆府武冈州以及长沙县等地经商之人。清朝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西深陷其中,时人谓:“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存者惟南昌、广信、饶州、赣州、南安五郡。”[25](卷四《援守江西上篇》,P49)后来成为长沙赣省五府客总的刘省辉就是此时外出谋生,奔波于长沙、湘潭之间的代表。因为刘氏早年曾有人在湘潭等地经商,因而后来者可以通过同乡同宗之人,以及通过姻亲等关系较便利地立足于外地。刘省辉经人介绍经过十余年的学徒习商后,“乃挟资自行设肆,先后组织松茂钱号、天香南货号、保元堂药号、元大南货号、公兴铜锣号、松茂南货号、大兴丝线号、吉庆南货号”。后来在长沙建立万寿宫作为赣省南昌、吉安、抚州、临江、瑞州五府侨商公所,董事为客总,任期三年,刘省辉连任三次。④其后人刘远大、刘远陞、刘凤鸣、刘远清、刘惠我、刘树珊、刘理堂、刘钰生、刘蒨牕等承其后,光大了刘氏在外的商业。刘氏虽远离乡土,出入阛阓,行旅倥偬,时常往来于湖南与故乡清水两地,或省亲、或娶妻、或奉父兄之命而还,至为关键的是,外出经商之人晚年大多返回家乡,如远心、远传、远清、惠我、树珊、钰生等人,可谓衣锦还乡。而在异乡亡故者亦选择归葬家乡,刘省辉“民国三年甲寅岁闰五月十二日亥时商殁长沙吉庆南货号,享年七十。归葬芦径黄鳅塘凤形二排经锡公坟左边,庚山甲向”。如果说按谭其骧在《湖南人由来考》中分析的湖南人大多来源于江西,并在早期就融入地方,甚至土客难辨,但该书所言主要是针对移民,而对于商人,他们中虽有定居而移民的,所谓“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但仍有不少从行商到坐贾乃至于定居后,最终晚年仍会返乡,他们始终视家乡为自己的根基所在,而湖南等地只是他们经商的舞台。
三、矛盾与融合:江右商于湖南地方社会的在地化
客寓湖南的江右商对湖南的商业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湖南湘潭,受三藩之乱影响,商业受损严重,“及复业,城中土著无几,豫章之商十室而九”[21](卷一一《货殖》)。且在康熙年间,“东界最近江西,商贾至者,有吉安、临江、抚州三大帮”[21](卷一一《货殖》)。湖南岳州府,当地的渔业也为江西商人垄断,“江湖渔利,亦惟江右人有”[26](卷一二二三《岳州府部汇考五·岳阳府风俗考·华容县》,P12下)。在长沙、湘潭等中心城市,赖于优越的交通条件,商业繁荣,市场兴盛,众多商贾云集,而这些商人也以“江西人尤多”[27](《嘉庆己卯湘潭朋殴之狱》,P545)。
除了经营足迹遍及湖南各地,湘省商界的各行业中都有江西商人的势力存在。“湘省商人分帮……有以同籍为帮者,如盐帮有南帮(江南盐商曰南帮)、西帮(江西盐帮曰西帮)、北帮(湖北盐商曰北帮)、本帮(本省盐商曰本帮)……钱庄有西帮(江西)、苏帮(江苏)、本帮(本省)。典当帮有南帮(江南)、徽帮(安徽)、西帮(江西)、本帮(本省),以及各种同业,以同籍各为一帮之类皆是也。”[28](《会馆》,P115)湖南的江西商人凭借人数多、经营行业广和渗透性强的特点,遍及湖南省,渗入各业,成为明清时期湖南商界的重要力量,故在当时一度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谚语。
江右商人在湖南进行商业渗透的同时,自然免不了遭受当地人的排斥,土客矛盾时有发生。如衡阳,便“有排斥外省商人习惯,常与江西人不睦”[29](P207)。津市也有类似情况,“当时江西会馆在津市人多店多,财力大……当商定以观音桥码头为义渡地点时,引起了私人板划船主反对,几乎发生械斗”[30](P85)。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嘉庆年间湘潭地区的土客械斗。[8](P83-98)究其起因,便是湘潭当地的商人不满江西客商垄断市场而一再寻衅闹事,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土客械斗。此事件发生在省城附近的商业中心城镇,规模较大,残酷激烈,而且在朝中引起了很大反应和复杂的官场斗争,有关记载也较为丰富。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濮德培(C.Perdue)曾著文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精彩的讨论。[31](P155-201)他主要是对清代湖南城镇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和特征进行了讨论。邵鸿则利用大量资料探讨了清代江西商帮在经商地与土著居民的关系,地方绅士和清政府对土客矛盾冲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及此类事件对地域社会变迁、商帮发展及其与家乡社会关系的影响等问题。[8]
湘潭与湖南其他地方一样,其居民多为明代和清初的外来移民,“尤以江西人更众”[32](P98)。而其中又以吉安、临江和抚州三府人数最多。赣商的经营活动,引起了湘潭本地居民的严重不满。这次事件暴发的导火线,据光绪《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记载:“(辛酉)江西优人演戏火神祠,操土音,土人哗笑之,江西人以为大辱。甲子,演于万寿宫,江西会馆也。土人复聚哄之。丁卯,江西商复设剧诱观者,闭门,举械杀数十人,乘墙倾縻粥以拒救者。”[21]
事件发生在江西会馆内。我们知道会馆除了经济上互助、调解商业纠纷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能即祭祀功能。会馆作为祭祀“江西福主”许真君的场所,既为了寻求许真君的庇佑,又为了在祭祀活动中巩固地缘关系、联络乡谊。江西会馆的祭祀活动具有较大的包容性,除了江西人共同信仰的许真君外,江西不同地区的移民也有当地特有的信仰,如临江商人除了祭祀许真君外,还纪念当地的保护神萧公和晏公。而且,不同行业的神灵也全部供奉在会馆内,如关圣大帝、增福财神等。在祭祀共同信仰的同时,也兼顾了各地、各行业的传统,增强了会馆内部的团结。在祭祀期间也会有些娱乐活动,如此,这次事件发生在会馆内也就不足为怪。
事件发生后,若干恐怖的流言开始四下传播。其一是传说万寿宫内“燔油烹人”,将被关在内的湘潭人不分老幼投入油锅残酷处死[8]。另一种传说更为可怕,谓:“江西公所于纠斗之日,先有妖僧画符数百道,环列于厅屋地上,先缚湖南人倒悬于屋梁之上,砍落其首,颈血遍洒符纸,令所纠之人各怀符一道,仍将余卸冲入酒内共饮,始行殴斗。事后此僧旋即逃逸。”[8]于是,当地人积累已久的对江西人的仇恨顿时爆发,开始了一场残酷的仇杀。按湖南方面的记录,几乎是江西客商血洗了当地人,但实际上,事件虽由江西客民而起,但其在随后的冲突中完全处于劣势,伤亡惨重。近两个世纪后,当地耆老口中仍然对此有所描述,据说本地人令所有关津过客说“六百六十六”,凡不类湘音者即杀之,导致不少江西人开始模仿湘音。这场冲突惊动了县官到巡抚以至京官,湖潭的士绅也参与事件之中。最后经朝廷调查后,认为这些传言有夸大且自相矛盾之处,以中立公允和力求查清真相的立场,调离或罢免了直接官员。此案最终以土客双方“各坐诛倡乱者一人,从者流徙十余人”[8]而结束。在清代,移民和本土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并不罕见,但在邻近省会的商业中心城市发生如此严重的大规模械斗,并在统治上层引起如此严重的矛盾冲突的则属稀有。这场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对湘潭社会和江西商帮都带来了较深刻的影响。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十《商贾论》曰:“谨案邑为四达之衢,四方百货俱集,自昔有小南京之称。至嘉庆而臻极盛,江边货船鳞次林立。及江西会馆斗殴之后,贸易顿减,久之渐兴而难复旧。”尽管这次事件持续时间不长,但江西人死伤惨重,致使土客相仇的气氛很长时间没有缓解,执当地商业之牛耳的江西商人势力受到了抑制,导致湘潭经济衰退。光绪《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土客相仇,江西客商亦谙不得意几五十年,军兴乃始和睦云。”[21]
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在强大的共同敌人的压力下,土客矛盾才得到一定的弥合。然而土客对立并没有消失,而且直到20世纪的40年代仍然明显存在。邵鸿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和颇为有趣的事实是,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湘潭人口大量由江西迁徙而来,而上述极力攻诋江西客民的湘潭士绅,实际上亦多为祖籍江右之人。湘潭土客仇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先后江西移民之间的斗争。诸人对江西客民的仇视态度,似有数典忘祖之嫌,然而正是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强和深化了他们对本土的乡土认同而最终斩断了原先的乡土之链。对抗和械斗也导致了市镇跨行帮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大约在道光年间,湘潭形成了各商帮的议事组织,即七帮福善堂。这一超越地域和行帮的组织,是能够较有效协调各种地域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权利中心。
长沙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客居于长沙的吉安县刘氏族谱里曾有这样的记载:“初于岁暮除夕夜敢以粪书‘见鬼’二字于朱店门,使元旦焚香污流衣冠,既而恃凶掳抢朱店货物,地方官绅不能制。朱愤赴诉于公(刘省辉),公讼长沙县,捕要犯十余人,置狱五年,始屈服求和。至今乔人士犹能称其才而颂其德。”乔口市毗陵湘江,传统时期是重要市镇与水运要津,若顺湘江入洞庭,乔口是必经之地。上湖(今江西吉安县澧田镇西部)朱氏在乔口市设店经营,但屡遭当地恶霸欺凌。“地方官绅不能制”所蕴含的可能是当地头面人物确实没有办法制止,或者说朱氏作为侨寓此地的生意人实属无奈。朱氏只能将原委告知刘省辉,而刘省辉除了是万寿宫主事之人外,其于光绪三年(1877)捐得监生功名,后又捐得从五品的州同知衔,由他将事情讼之长沙县,最终为首的十余人被捕并判“置狱五年”,双方达成和解。
总之,从移入到定居,江右商融入湖南社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商业竞争、利益争斗等冲突。但冲突并不能阻止相互间的融合,本土经济与市场繁荣有赖于江右商的努力,江右商的安定与否离不开本土民众以及地方政府的接纳和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行帮的地域格局逐渐打破,江右文化也逐渐被地方接纳,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江右商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四、地缘到业缘:江右商帮在近代湖南的同业融合
近代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资本的入侵,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传统以会馆、公所为代表的行会制度受到新的挑战,行会组织开始了转型的道路。为提高商业竞争力,湖南各商帮打破了以往的地域界限,走向同业融合。从清末的行会到民国时期的同业公会,同业组织悄然兴起。20世纪初,在政府的主导下,各地纷纷建立商会,以求更好地整合商业资源。江右商在近代湖南同业与商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现了现代转型。
晚清以降,在“商战”思潮下,各地商会纷纷建立。1905年,湖南商务总会开始着手筹建,并于次年六月经农工商部批准成立。[33]此后,常德、宁乡、永州、浏阳、湘潭等地陆续成立商务分会。
初期的商会,实则是由各帮联合的议事组织发展而来。各入会商号,均是原本商帮的成员,在已有的议事机构的基础上,顺应时局,加入商会。如1906年初,常德商务总会成立,其创办基础仍是原来的“三堂八省”组织,入会的商号大多是原各商帮的成员,资金由这些商号负责筹措,会务由原三堂董事选举出的会长和会董管理。其中“被选出的会长多系大商贾和帮派势力强的头面人物”,由于常德商界中江西商人势力庞大,常德商会的历任会长中,江西人占据了大半之数。甚至在商会几经改组后,江西商人的地位也丝毫不减。[34](P1-26)成立于1909年的湘潭商会也是如此,该会会址便设在原联合议事机构福善堂的旧址,会长也由当地势力较大的江西商帮帮董刘福衢担任。即使在1911年商会改组后,继任会长徐云荪亦为江西帮帮董。[35](P5)
宣统三年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钱店公议论条规》中有如下规定:“我行公庙新举总管肆人,本籍客帮各二,敦请贤能练达事理精详者,会同每届散值年经理同行要务。凡属有碍行规及紧要公件,值年即行会商总管,公议事应如何办理,然后出通行单知会同行,则事权归一,以免众心难齐,各怀己见。其寻常公事,仍归总散值年办理,毋庸会商总管。至总管更替,三年一届,满期仍由同行公议酌举总管两人接办,旧总管四人内,酌留客本两籍各一位,新旧各半,轮流交接,以资熟手而免误公。”[28](P233)此时的组织仍是新旧各半,可见本客帮观念仍有存在。
从传统商帮向近代商会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此时的商会,虽名为商会,实则与原本的联合议事组织无异,是一种披着新式商会外衣的传统机构。一方面在于商会设立的基础是那些由传统商帮组成的联合议事机构;另一方面则在于商会中商人亦官亦商的性质。如凤凰的赣籍商人熊玉书、裴彤九等,利用清末实行的捐官制度,以银两捐得候补知县及监生等头衔。有的商人通过送子弟入学而进入政界,如裴三星商号送长子裴晴初入学中举,历任贵州、澧州知事,民初连任三届凤凰县长。商会会长担任官员的也不在少数,如凤凰商会首届会长刘帮熙曾任湘西镇守使秘书长,最后一任商会会长裴庆光也曾担任县参议员。即使其中未涉及官场的,也大都仰仗官员的支持,如陈东恒、杨沅昌二人出任凤凰商会会长,是得到了湘西王陈渠珍的扶植;继任会长的戴滨诚则是国民党师长戴季韬的胞弟。
1918年,农商部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其中规定:“同一区域内之工商业者设立公会,以一会为限。”[36](P986)这一规则的颁布,使得原已松动的各行业内地域特色明显、商帮分庭抗礼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各帮纷纷踏出由地缘关系建构的壁垒,走上了同业融合的道路。
在湖南行业融合中,以长沙旅馆业为例。民国初年,长沙旅馆业分为三帮,其中长沙为云集会,善化为东南会,江西帮为柔远会。三帮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打破了传统的地域界限,共同组建旅业公会。三帮“概隶旅业公会管辖,按牌号捐款,购置房产,共议同业事项。公举总管值年管理会务。会章严格,共同约守,凡开业必先入会,并遵条规”[37](P138-144)。并联合颁布客栈条规,“商贾乃四民正业,无论生意大小,欲沾利益,必赖行规。兹我等贸易客栈,已历多年,前因试馆杂列,致价值高低不一,败坏难堪。爰集我行酌议,禀请出示立章,以昭划一,且使循规踏矩,便易稽查,故迩来客栈一途,颇有条理。第沧桑时局,多有变迁,今特立约会商,续议数条,俾志合规同,各资遵守”[28](商业条规,P506)。同业组织的建立和行业条规的颁布,改变了原本三帮争斗不休的局面,规范了长沙旅馆业内的秩序,促进了旅业内部的同业整合和三帮的商业融合。
与此类似的还有长沙卷烟业。长沙营烟贩始于清代,至民国初年,长沙烟业以建(福建)、西(江西)二帮势力最大。民国二年,为整合行业,湖南人熊桂芳创办湖南烟草公司,与建帮、西帮商人竞争。因其商品物美价廉,迅速挤占市场,销量甚巨,获利颇丰。福建和江西商人利润锐减,只得加入湖南烟草公司,与湖南帮开展商业合作,三帮于1917年组建烟业同业公会。“至民国六年,江西帮始加入该会。查湖南帮烟店共有一百二十余家,福建帮烟店共有三十余家,江西帮共有烟店五六家。”并规定:“凡每店入该公会须缴牌费洋十元。会中组织,每年公举正副总管共二人。正总管管帐簿,副总管管银钱。又公举值年八人,照三帮铺店之多少分配,均系一年一任。”[38]建、西、湘三帮共同组建烟业同业公会,结束了三帮彼此竞争的传统。正副会长由会员公举,打破了旧时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模式,在促进长沙烟草业的行业整合和推进传统三帮的商业融合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近代湖南商界江西商帮破除地域界限,进行商业融合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如在长沙南货业中具有较大势力的江西、湖南两帮于清光绪十六年联组西南财神会,共同应对商业竞争,并于民国时期建南货土果同业公会[37](南货业,P37-44);衡阳纱布业,在本帮(衡阳帮)与西帮(江西帮)的激烈商业竞争中,落后的店铺遭到淘汰,保留下来的店铺于1930年联合成立同业公会,实现了行业整合与商业合作[37](纱布业,P7-11);长期被江西丰城、清江等地商人所垄断的湘潭药材业,在民国时期也迎来了西帮和本帮(湖南帮)互通资本,商业联结的局面[37](药材业,P93-97)。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十六条及《实施细则》十七条规定:“商户不受资本多少、营业性质、入会费的限制,皆可加入同业公会。”自此,湖南同业公会迅猛发展,至1935年,全省批准的同业公会有291个,入会商号1.37万家。[39](P624)之后,国民政府又陆续出台《商业同业公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等法令,以规范和保障同业公会组织的正常运行,至1941年,全省的同业公会数量达到1107个,到1947年,这个数目达到2124个。[40]至此,同业公会的转型基本完成。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融合的加深,地缘关系的纽带作用也就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业缘为纽带的同业组织。传统的地域性商帮团体向跨地域的商会和同业公会演变,是商业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经济和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传统商帮就必然破除地缘壁垒,走上行业整合和商业合作的道路。作为维系湖南江西人的纽带被另一种新型组织——湖南江西同乡会所取代。
五、结语
明清“江西填湖广”的大规模移民,构成明清时期湖广地区人口的主体。经过他们的拓土开荒,成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位,也使湖南成为长江中游的重要粮仓。伴随着移民浪潮入湘的江右商从行商、坐贾到定居,他们弃农经商,足迹遍布湖南城镇,渗透于各行各业,并因共奉许真君为福主而结帮设馆,逐渐形成了著名的“江右商帮”。作为客商的江右商逐渐融入地方社会,虽有矛盾与冲突,但冲突并不能阻止相互间的融合,本土经济与市场繁荣有赖于江右商的努力,江右商的安定与否离不开本土民众以及地方政府的接纳和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行帮的地域格局逐渐打破,江右文化也逐渐被地方接纳,在矛盾与冲突中实现在地化过程,并受近代市场环境与制度性因素影响,以同业组织融入地方商会,实现了地缘组织向跨地域业缘组织的转型。
从明清时期开始迁往湖南的江西商人,经历了一个由商业渗透到商业融合再到商业转型的演变过程,反映出近代以来,在市场环境和政治变革的影响下,湖南地区传统的商帮团体向近代商会和同业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历史性的演变过程,是江西商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商人的地缘观念逐步被业缘观念所取代的过程,并共同推动湖南商业的繁荣。这种自古以来特有的历史渊源也成为两省至今“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的联结基因,也是国家长江中游经济带以及城市群整体战略布局的历史性基础。
注释:
①《两湘陈氏续修族谱》(民国十九年)卷首《源流序》,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中湘云湖张氏三修族谱》(清宣统三年)卷一《旧序:一代世系齿》,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③章文焕《净明伦理与江右商帮精神》,于2008年应中国道协邀请,在江西饭店出席“道教与经济社会”研讨会上发言。
④《吉安清水刘氏八修族谱》(民国三十五年)。本文所用刘氏族谱均转引自唐金翰《离乡守土:晚清民国时期吉安清水村的商人流动》(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后不再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