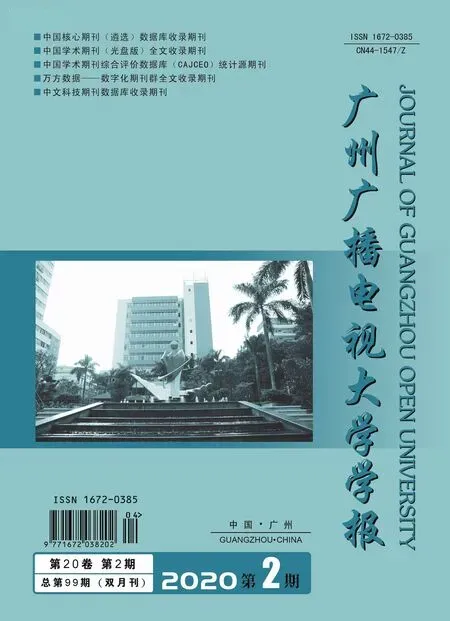明代诗坛对宋诗的重新审视
陈颖聪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专上学院,香港 999077)
宋人以自己的智慧与创新精神,建造了诗坛上又一座高峰,但宋诗自开新面的风格,却引发了宋以后有关唐宋诗优劣的讨论。例如,南宋末年,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一方面教人“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参熟之”[1],同时对宋、尤其是南宋末年的诗歌作出了严厉的批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2]元人在推崇唐诗的同时,对宋诗亦有不少贬抑的言论。四库馆臣称之为“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3]的王若虚(1174—1243)认为“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4];刘埙(1240—1319)的《隐居通议》,四库馆臣认为是“谈艺者所必录也”[5],则更是说“入宋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有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6];至于欧阳玄(1283—1374),《元史》对他亦赞誉有加:“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玄之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重。文章道徳,卓然名世”[7],他既肯定了“诗自汉魏以下莫盛于唐宋”[8],却强调“宋人不及唐人”[9]。
对唐宋诗的讨论,乃至其间优劣之争,自宋以后一直未有停息。至明代,唐诗一直处于优势,即使如陆时雍等曾公开指出唐诗的不足,认为“唐人抛却真情,别求假话”[10],但他们对唐诗是绝无否定的意思的。唐诗在中国古代诗坛中的崇高地位,不可能动摇;唐诗的成就,是值得后人学习和推崇的。这个认识,在明人,乃至明以后,绝无异议。明代诗坛的论争,问题同样集中在宋诗。在以复古诗论为中心的明代诗坛上,宋诗的地位备受否定。然而,正是在这“否定”的论争中,宋诗的支持者经过反复考察后,理出了十分简明的道理,让人们恰如其分地认识了宋诗,认识了宋代诗人的可贵之处。
一、宋诗之贵在于创新
宋诗的出现,是诗歌发展历史中的一个事实;诗歌的发展不可能至某一朝代而止步。宋代诗歌继承、发展了唐诗,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唐诗的不足。袁宏道(1586—1610)所说的“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11],正是指出了唐诗发展至晚唐,暴露出了自身的弊病,这弊病则由宋人作了矫正。在这个矫正的过程中,发展唐诗,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宋诗的出现,与汉、魏、唐诗的出现一样,都不是这个朝代的诗人凭主观意志创造出来的,而是诗歌发展历史自身的要求。历史要求这个朝代的诗人,继承前人的创作,发展前人的创作,纠正前人的弊病,弥补前人的不足。从这个意义来说,宋诗的历史价值只能去探讨、去研究、去认识,而不能只在唐诗标准的视野下,对宋诗视而不见,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明代支持宋诗的诗人,在论争中逐渐取得的认识,这些认识至晚明尤为明显。他们认为宋诗的价值并不减于唐诗。
袁中道(1570—1626)对唐诗情有独钟,对宋诗虽无特别推崇,却同样给予恰如其分、甚至可以说是颇高的评价。他专门为宋元选作序,在序中说:“(宋诗)即不得与唐争盛,而其精采不可磨灭之处,自当与唐并存于天地之间。”[12]他认为,从整体看,宋诗固然比不上唐诗,但亦有唐诗并不具备的,或不可与之相比较的优点,这些优点足以使宋诗与唐诗并存,成为整个诗歌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宋诗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呢?袁中道亦作了简要的说明:“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13]不墨守前人,敢于创新,而这个创新则是为了尽量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意。袁中道这个说法固然是有感于其时墨守汉、唐,摹拟、复制之风而发,但却是道出了宋人的优点。袁中道是在肯定唐诗的同时,以宋人的优点,论复古、摹拟者墨守唐人的不是,并对宋诗作出客观的评价:
才既高,趣又深。[14]
命意铸词,其发脉也甚远。[15]
若秦、黄、陈、晁辈,皆有才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16]
袁中道认为,宋诗的耐人寻味,是因其有风骨,有情趣,有新意,而不是因其词语的雕饰华丽,学舌于汉唐。这是袁中道以宋诗的长处告诉世人,不必盲目崇唐,更不能因看不到宋诗的长处而墨守唐风、唐调,堕入刻板摹拟的深渊。
早在三袁之前,唐顺之(1507—1560)就指出:“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接着又强调“诗思精妙,语奇格高,诚未见有如康节者”[17]。这里虽指的是邵雍,然而宋诗“诗思精妙”“语奇格高”则是不少人已感受到的普遍事实。
例如,被四库馆臣誉为“以乡曲儒生独能支拄颓澜、延古文之一派。其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袭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亦可谓永嘉之末得闻正始之音矣”[18]的娄坚(1554—1631)就有这样的认识:
宋人以议论为诗,诚不尽合于古,至其高者,意趣超妙,笔力雄秀,要自迥绝,未可轻议。[19]
宋人之诗,高者固多有,如苏长公,发妙趣于横逸谑浪,盖不拘拘为汉、魏、晋、唐而卒与之合,乃曰此直宋诗耳。[20]
娄坚正是从“趣”与“妙”认识宋诗,肯定了宋人不拘系、不墨守前人的创新精神。
毕自严(1569—1638),四库馆臣在介绍他时,称“其七言近体,分沧溟、华泉之座”[21]。在诗的风格取向上,他尽管是倾向于后七子,但却能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宋诗。
在《类选四时绝句序》中,他说:
夫宋、元蕴藉声响,间或不无少逊李唐,至匠心变幻,则愈出愈奇矣。昔人谓唐人绝句至中晚始盛,余亦妄谓中晚绝句至宋、元尤盛。如眉山之雄浑,荆公之清丽,康节之潇洒,山谷之苍郁,均自脍炙人口,独步千古,安可遗也。[22]
他认为宋、元诗并不比唐诗逊色,甚至有胜于唐者;至如绝句,则宋、元之作尤胜于唐。在他看来,宋诗的特点是“匠心变幻”“愈出愈奇”。这是从宋诗结构、布局之新奇,诗人构思之精妙,风格之自成一家、超越于前人这些方面去肯定宋诗。
清人吴之振(1640—1717)在其与吕留良、吴自牧合编的《宋诗钞》中,所撰写的序言转述明人曹学佺(1574—1646)《宋诗选序》的内容:“曹学佺序宋诗,谓取材广而命意新,不剿袭前人一字。然则诗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23]吴之振认为,曹学佺对宋诗的评价全在“广”与“新”这两个字上,正是由于做到“广”与“新”,所以能“不腐”,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宋诗不但继承着唐诗的长处,更着意的是创新,扩大诗歌的容量,走上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这不但是从对唐、宋诗的反复比较与思考中得到的体会,也是为汉、唐以来诗歌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经验与事实证明了的正确方向。
二、说理、明礼是宋诗的优点
复古诗论者对宋诗的否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认为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究竟诗中能否发表诗人对身边事物的评论和意见,诗中能否表达诗人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与批判,这同样是贯穿着整个明代诗坛论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支持宋诗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说法起自宋人,例如严羽正是据此而批评南宋末年诗坛的非主流倾向,然而却成为了明代复古论者否定宋诗的口实。
(一)对“以议论为诗”的重新审视
明初,对“以议论为诗”虽未有作出系统性的否定,但受宋末严羽及元人的影响,在一些诗人中,对宋诗已有了主观的偏见。例如,吴讷(1372—1457)说:“若王介甫、苏子美、梅圣俞、苏子瞻、黄山谷之属,非无可观,然皆以议论为主,而六义益晦矣。”[24]他虽然对诗的“议论”及说理,并不如后来复古论者那样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但却是把“议论”、把“理”,与“六义”对立了起来。因而在他的认识中,“议论”的写作手法、“理”的表达和阐述,就不属于传统儒家关于“诗”的基本范畴了。这个意见大体上反映了反对“以议论为诗”者的依据。
后来,谢肇淛(1567—1624)在表达上便有所不同了,尽管他说:“涉议者声卑,牵理者趣失”[25],但却是指出:“诗不可太着议论,议论多则史断也。不可太述时政,时政多则制策也。”[26]
所谓“不可太着”,就有一个“度”的掌握。对“议论”掌握得不恰当,用之太过,则“诗”与“史”无异;反之,若用之恰当,自然就没有这个毛病了。至于所谓“声卑”“趣失”也应作如是观。事实上不少有着鲜明议论特点的诗歌,如朱熹、邵雍等作品,在诗中的议论却是掷地有声,妙趣横生。所以“声”的“卑”否,“趣”之存没,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度”的问题。从“度”上去认识诗中的议论,就较之对议论作绝对的否定有所进步了。
谢肇淛对宋诗的认识虽然还残存着“宋无诗”论的影响,但却是有意从这个影响中摆脱出来。他对宋诗除了作出一个“度”的掌握外,还作了直接的评价:
唐以诗为诗,宋以理学为诗,元以词曲为诗,本朝好以议论、时政为诗。[27]
宋诗虽堕恶道,然其意亦欲自立门户,不肯学唐人口吻耳。此等见解非本朝人可到。[28]
在这两则评论中,谢肇淛表明了对宋诗的总体认识,这就是他仍持唐诗的标准看待宋诗,因宋诗不合唐标准,因而与“宋无诗”论一样,视宋诗堕于“恶道”,但却又不是对“宋无诗”论者的完全认同,他认为宋人之所以不循唐人的路子走,是由于宋人要“自立门户”,也就是说,宋人志在创新,走自己的路。于是出现了宋人不同于唐人的创作,形成了与唐人不同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谢肇淛虽说宋诗“堕恶道”,但却不具有否定之意,相反,他认为宋诗“议论”、言理的特点,探索创新的精神,是明人不可企及的;而宋诗的这些风格却时时影响着明人的创作,故他说“本朝好以议论、时政为诗”,这个评论就直接痛打在以“以议论为诗”为理由,而否定宋诗的明代复古论者的身上了。
稍后的许学夷(1563—1633)在认识上又更进一步了:
嗣宗(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中多兴比,体虽近古,然多以意见为诗,故不免有迹。[29]
复古诗论者推崇汉、魏、盛唐,然而即使是汉魏时著名的诗人阮籍,亦不免“以意见为诗”。尽管许学夷对此以“不免有迹”而论之,明显是维护着对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否定;但却不可否认,许学夷对恰当的议论、恰当的言理,不但没有认真的否定,而且认为是诗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的艺术形式与表达的思想内容。
在围绕着“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论辩中,诗人们不断深化对宋诗的认识,例如,
周瑛(1430—1518)是这样看待宋诗中的“理趣”的:“唐诗尚声律,宋诗尚理趣。”[30]在他的认识中,“声律”与“理趣”,只是“唐”“宋”不同的侧重,不同的特点,并无优劣、取舍的意思。这已经不光是传统的“风”与“雅”“颂”的体裁的辨认,而是从审美情趣的认识上说了。
其后,张吉(1451—1518)则把审美的意义说得更清楚:
盖(朱熹《感兴》)兼苏、李之体制,陶、孟之风调,韦、柳之音节,而其理趣则直与风雅正声相为表里,非汉晋而下词人所及。生乎其后,不根于此而有能诗声者,我不敢知也。[31]
张吉不但没有像吴讷那样,把“理”排斥在“六义”之外,而是肯定了朱熹《感兴》诗中表述的“理趣”“直与风雅正声相为表里”,甚而认为如朱熹诗中的“理趣”乃非魏晋人所可及。他对朱熹诗中的“理趣”给予了甚高的评价,又把“理趣”与“风”“雅”联系起来,亦就是从“理趣”中认识“六义”。不言而喻,对“以议论为诗”他是给予了恰当的肯定。
对诗中的“议论”及“文”的表现手法,明代不少诗人不但没有持否定的态度,而且还把这种表现手法看作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发展与变革。例如,林俊(1452—1527)认为:“迨宋以文为诗,气格愈异,而唐响几绝;山谷词旨刻深,一大变者也。”[32]他是把宋人诗中的“文”的特点看作是诗格变化的一体,认为这个变化虽不同于唐诗,更不同于唐诗的表现方式,但并没有对它采取否定的态度。林俊的这个认识,是得到不少诗人支持的。
薛应旗(1500—1575)说:“余尝谓唐人之诗独尚乎风,宋人之诗则雅、颂为多。”[33]
他是把唐诗与宋诗分为“风”与“雅”“颂”两大类,均属“六义”之制,只是特点不同,体制不同而已。因此,以“风”而否定“雅”“颂”,显然没有道理;唐人“雅”“颂”之不足,宋人补足之,发展之,而“宋无诗”论者把它斥之为“以文为诗”,视为异端,自是无稽之谈。
宋诗虽不如唐,但唐、宋诗各有特点,“议论”的写作及内容,在一定的“度”内,亦可以表现为诗中的“理趣”,不可惟唐是取而不加分析地否定宋,这已为中、晚明诗人普遍接受的结论。
(二)关于“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
传统孔子儒家诗论,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也就是强调诗应明理,应有理据,要符合“礼”,《诗大序》更把它规范为“发乎情,止乎礼义”[34];对读诗者而言,重要的也是从诗中悟理、识理、懂得守“礼”。然而唐人讲究的是声律之美,情调之“真”,于是不知不觉中淡化着“教化”“说理”的传统,以至杜甫关心家国大事与百姓生活,写出不少有违唐声、唐律的感人之作,亦一时被认为是异调。于是,面对不少唐代杰出诗人所存在的“以议论为诗”的现象,北宋以后的一些学者,就提出了“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分野。
宋人李复(1093前后在世)提出:“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诗岂一端而已哉。”[35]在李复看来,“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只是诗人与学者在诗中各自不同的写作特点,并没有优劣之分,更没有以此而否定彼的必要。李复这个意见自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直接对侯谟有关杜甫与韩愈的诗与文既互相影响、又各有侧重的提问所作的答复。其所针对者,则是其时对“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不同风格的看法。宋代中、晚期,学者对“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有了更多的关注。例如,宋人何梦桂(1270前后在世)说:“尝与友人谭诗,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异。友曰:不然,诗患不到好处,诗到好处又奚文人、诗人之辨哉。此语真诗家阳秋也。”[36]“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此时已成为了亲友之间讨论的话题,对这个话题,何梦桂干脆认为没有必要划分“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直至元朝,刘将孙亦认为:“作诗者每不主议论,以为文人之诗,不知各有所当。”[37]他指出把“议论”事理的诗,视作“文人之诗”,而排斥于“诗”外的主张,是十分不妥的。
诗人往往会在诗中以散文的词句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宋人刘辰翁(1233—1297)有较详细的说明:
后村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满,而不知其所乏适在此也。吾尝谓诗至建安,五、七言始生;而长篇反复,终有所未达,则政以其不足为文耳。文人兼诗,诗不兼文也。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更胜彼一偏一曲自擅,诗人诗局局焉、靡靡焉,无所用其四体,而其施于文也亦复恐泥,则亦可以眷然而悯哉。[38]
刘辰翁指出建安之不足,正是过于诗人化,而缺少“文”的表达。杜甫诗之可贵,超出时人,正是在他的诗中时时运用了“文”的写作。韩愈、苏轼之完美,也主要是得益对“文”的运用。
四库馆臣在《濂洛风雅提要》中认为“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39]。也就是说,在诗坛上划分为“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两个不同风格的大类,并对其各自的优劣作出研究,是南宋、甚至是南宋末年才出现的。这个优、劣之分,入元以后就表现得比较突出了。
元人盛如梓有这样的说法:“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40]盛如梓此论是针对其时为写诗而写诗,脱离社会,凭空想象的诗人而发的。这些所谓诗人之诗,语出不实,只是“爱装”“斗好”,其实是在“欺”;不似文人之诗,质实无华,耐人“涵泳”。
刘祈(1203—1250)则直斥“诗人之诗”:“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41]刘祈对“后世诗人之诗”的批评,正是就其时诗坛不关心社会现实,只追求辞藻,卖弄学问的不正之风而发。他认为,这个时期的“诗人之诗”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可与动人以情、晓人以理的“文人之诗”同日而语。
诗中不可能没有文,也不必排斥议论与说理,这个认识,一直到明初仍为不少人所承认。洪武十四年张端为元人许恕《北郭集》撰《北郭集原序》:“今人之诗与古人之诗异,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异,然诗而不以文为法则又戾于古也。”[42]许恕虽未是明代诗坛的代表,但他的说法却是颇得到宋、元以来学者的心得,而又是针对明代诗坛偏颇之论而发的。
即使明代“宋无诗”论者以“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而否定宋诗最为盛行的成化至嘉靖年间,邵宝(1460—1527)亦明确地说:“世有诗人之诗,有非诗人之诗。非诗人之诗而才情、风致、音调、格律皆诗人也,则谓之诗人也亦宜,曷为而谓之非诗人之诗也。”[43]这里所说的“非诗人之诗”,指的主要就是“文人之诗”。邵宝认为把这些儒者的诗,排斥在诗人之外是没有道理的。
杨循吉(1456—1544)对其时所谓诗人之诗则作出了严肃的批评:“诗人之诗多以迫成,非必尽其胸次中语也。”[44]他认为其时所谓诗人多是为写诗而写诗,无病呻吟,脱离社会现实,无真情实感,但却自命为“诗人之诗”,这样的诗是不值得提倡的。
这个讨论自南宋开始,一直到晚明,复古诗派据“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而否认宋诗,唯汉、唐是宗,流而形成了缺乏真情,甚至是假情假意,脱离社会,为写诗而写诗,并美其名为“诗人之诗”的描摹风气,严重侵蚀着明代诗坛。其说时为有识之士所质疑与驳论。随着复古论的衰落与退出诗坛,在明代心学的背景下,人们的“心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直抒胸臆,表达“真情”,探求“真理”,重新成为了诗人的追求;诗中“文”的倾向,说理的内容,终于取得社会的普遍肯定。在明末,外患频仍,民族面临垂危之际,不少诗人直抒己见,写出了明辨是非、申张道义、忧国忧民、关心民间疾苦的优秀作品,充分显示了“文”与“议论”的感人力量。事实上,诗中恰当的“文”的表达,“议论”的运用,一直影响着明以后诗人的创作。
在中国古代诗坛上,宋诗是与唐诗并峙的又一座高峰。这座高峰的产生,是在于宋代诗人不愿坐享唐人成就而作的创新追求,是在于宋人坚持了前辈抒发真情、尚理、说理、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对宋诗的这一认识却是通过宋元,尤其是明代诗坛旷日持久的辩论,才得以重新审视,获得了社会的共识。因复古诗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引起诗人们的积极反思,其意义则是明人,尤其是复古诗人意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