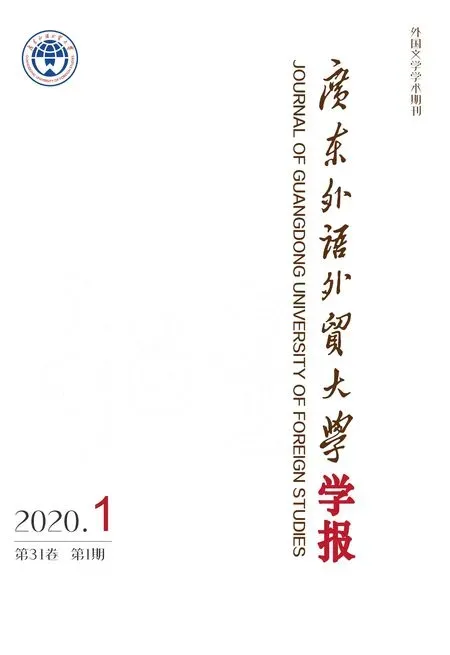坏女人、妓女与新女性:《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女主人公形象考辨
覃承华
引言
长期以来,海明威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形象一般都被视为“准则英雄”或者“硬汉”;他的女性人物形象则根据其与“准则英雄”或者“硬汉”们的利害关系被划分为“好女人”与“坏女人”①两种类型。比如,菲利普·杨(Philip Young,1952:81)指出海明威作品中的女人“要么是邪恶的、毁灭性的,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的妻子,要么是白日梦者,如凯瑟琳、玛利亚和热娜塔”;阿瑟·沃德荷恩(Arthur Waldhorn,1972:123)认为海明威的女人“要么是爱抚可人者,要么是阉割男人气概者”;杰克逊·本森(Jackson Benson,1969:39)声称海明威的女人可分为“坦率享受性生活、慷慨献身的女人与具有攻击性、没有女人味的‘十足坏女人’”。列斯莱·菲德勒(Leslie Fiedler,1960:304)对海明威刻画的女性人物形象持一种更为极端而尖锐的批判态度,认为“在早期作品中,海明威有意识地将女性遭遇描述的很残忍,而在后期作品中则无意识地将其喜剧化”。中国大陆学者基本沿用国外的批评范式。李加伦(1996:23)把海明威笔下的女性按头发长短分为两类,并认为“长发型女人属于温顺善良型;短发型女人属于独立破坏型”。张叔宁(2000)对《太阳照样升起》中勃莱特·阿什莉的“魔女”批评史进行了梳理,评述了七十年来勃莱特在美国的接受,最终站在以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为代表的学者一边,认为一个虽然迷惘有缺陷但深得海明威本人同情仍不失为新女性的勃莱特,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显然,他也没有跳出二分法的窠臼。台湾学者朱炎(2005:51)虽没有明确界定海明威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好坏,但将其分为两类,即“以写实的笔触所表现出来的女人和被浪漫化了的女人”。这种现象,正如罗格·惠特罗(Roger Whitlow,1984:11)所言,“最盛行的海明威女人范畴化的批评方式是将她们一分为二”。
实际上,著名的海明威批评家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1963:109)早就对这种一分为二的批评范式提出批判。“对海明威女性人物最常见的负面评论就在于他们倾向于表现两个极端,忽略中间立场。”但遗憾的是,不但批评家没有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甚至贝克本人的观点也被一些批评家误解,认为是他率先给勃莱特贴上了“魔女”的标签。通过文本细读并扼要梳理与考察勃莱特的学术批评史,发现其“坏女人”的标签值得重估,同时对其 “妓女”与“新女性”等“标签”做出辨析,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坏女人”,也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完全的“妓女”和“新女性”。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勃莱特只是一个介于妓女与新女性之间的过渡性人物。
勃莱特·阿什莉作为“坏女人”:一个莫须有的标签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是将海明威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一分为二的先驱。一九三六年,海明威相继发表以非洲狩猎为背景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 (TheShortHappyLifeofFrancisMacomber,1936)(以下简称《幸福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TheSnowsofKilimanjaro,1936)(以下简称《雪》)两篇重要短篇小说。由于《幸福生活》中的玛格丽特射杀了自己的丈夫麦康伯以及《雪》中的海伦用金钱毁掉哈里的写作才能,威尔逊据此声称,“这两个故事中的男人均娶了最具有毁灭性的美国坏女人”(Lewis,1965:103),体现出作者“与日俱增的厌女情结”(Meyers,1997:311),玛格丽特是“海明威对所有女性持敌视态度的一个佐证”(Kert,1983:275)。许多批评家紧随其后,纷纷对海明威的女性人物形象做出分类批评,具有代表性的有杨·菲利普、菲德勒以及多克托罗(E.L.Doctorow)等。总的来说,自威尔逊以后,学术界常见的做法就是将海明威的女性人物形象二分为“男性阉割者与爱的奴隶,坏女人与贤内助”(Donaldson,1996:171)。
(一)勃莱特因何成为“坏女人”?
威尔逊也是将勃莱特·阿什莉贴上“坏女人”标签的先驱批评家。自威尔逊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首次将勃莱特称为“唯一的破坏力”(Meyers,1997:311)以来,勃莱特便一直被当作“坏女人”加以批判。批评家将海明威部分女性人物形象贴上“坏女人”标签的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他们认为这些女性对男性主人公带来了毁灭性影响或者后果,“他们对与她们有关的男人们‘有害’”(Baker,1963:110)。显然,威尔逊称玛格丽特是“海明威对所有女性持敌视态度的一个佐证”的依据就是玛格丽特最终将其丈夫麦康伯置于死地。而哈里写作能力的丧失也正是因为他娶了海伦这个富有的女人,“这个善良的,这个有钱的娘们,这个他才能的体贴的守护人和破坏者”(海明威,2004a:74)。然而,这种推论是十分牵强的。这是因为,在《幸福生活》与《雪》中,根本过错均在男性身上。就《幸福生活》而论,麦康伯的错误在于他缺乏主见并错误地将职业猎手罗伯特·威尔逊的标准强加在自己身上,并在野牛来袭时仍冒死实践这一标准。麦康伯的妻子在一旁将正在到来的危险看的一清二楚,本想为他解围却在慌乱中将他打死。如果麦康伯不将自己置于危险中,玛格丽特便没有任何开枪的理由。就此而论,认为玛格丽特杀死丈夫是一个预谋的观点是不完全准确的。与麦康伯不同,哈里在谴责海伦的同时以及在临死前也进行了深刻反省。“这不是她的过错。如果不是她,也会有别的女人”(海明威,2004a:74)。但是,哈里接下来的自我剖析进一步否定了这是海伦的过错。他认为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的才能。因为其他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如果必须要从女人身上找过错,那么海伦唯一的过错就在于她是个“有钱的娘们”和她“好好地给养了”哈里。可见,哈里个人的主观原因才是使自己最终走向毁灭的根本原因。
就《太阳照样升起》而论,威尔逊称勃莱特是“唯一的破坏力”也是以她和男主人公的关系为依据的。然而,行为放荡的勃莱特并没有破坏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真正毁灭他的罪魁祸首是战争——摧毁了他的性能力。格雷·柏雷纳(Gerry Brenner,1983:28)认为,《永别了,武器》的主题“不是战争也不是爱情,而是伤痕”。我认为这一论断是十分贴切的,也同样适用于《太阳照样升起》。就整个小说来看,《太阳照样升起》讲述的正是一群具有各种战争伤痕的老兵在战后无序的世界中焦虑不安、苟且偷生的故事。在战后的精神荒原中,他们在价值追求和人生观念等方面也无所适从。作为小说的观察者与叙述者,巴恩斯的伤痕身心兼具,在所有的老兵中最为严重。这也是他无法与勃莱特真正结合的根本原因。
不难看出,尽管勃莱特被描绘成一个放荡成性的女人,但她对巴恩斯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她也深爱着巴恩斯。小说中的罗伯特·科恩、迈克·坎贝尔与佩德罗·罗梅罗均无法取代巴恩斯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但遗憾的是,巴恩斯无法满足她的身体需要,这是三十四岁的她所不能忍受的。“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人家做些什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海明威,2004c:82)。这是《永别了,武器》中牧师对弗雷德里克·亨利所做的精神劝导。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巴恩斯在爱情上的过错。虽然牧师指出亨利关于夜晚的事“那不是爱,那只是情欲罢了”,但情欲也毕竟包含在“爱”与“给予”之中。《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对话如“‘不谈了。空谈顶无聊’;‘你为什么要走?’‘对你好。对我也好’”等都鲜明地体现了巴恩斯的性无能和双方的极度无奈。就此而论,正是巴恩斯身体上的缺陷导致他无法为勃莱特提供“服务”;勃莱特爱上巴恩斯并没有错,问题的根源在于他无法给予。因此,真正阉割巴恩斯的是战争。
被称为“坏女人”的勃莱特与玛格丽特也具有本质区别。玛格丽特的“坏”主要体现在,她首先鄙视丈夫胆小,继而与威尔逊偷情,最后将丈夫置于死地。勃莱特则不同,她并未直接对巴恩斯等男人们造成任何伤害。虽然表面上科恩因为勃莱特而最终垮掉,但科恩被毁的根源在于他试图在战后的精神荒原中坚守早已过时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作为一个配角,其未婚夫迈克本来就是一个酒鬼和破产者。享乐主义者勃莱特与一个破产者订婚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罗梅罗则在与她短暂的艳遇后无情地将其抛弃。虽然她爱着巴恩斯,而她与罗梅罗的风流韵事也正是在他的牵线搭桥中实现的。因此,本质上勃莱特更像是一个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
其次,他们以勃莱特所言作为判断的依据。的确,勃莱特较早前曾提到自己是个“坏女人”(“bitch”)。在遇到罗梅罗时,勃莱特曾两次对巴恩斯说,“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海明威,2004b:202)。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她又说她不愿当一个糟蹋年轻人的坏女人。一些评论家据此认为勃莱特是一坏女人,并在小说结尾处有洗心革面的倾向。然而,她在说自己是“坏女人”之前说的一句“从来我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理解她是“坏女人”至关重要。贝克指出,“《太阳照样升起》的大量影响力源自于它坚定的道德支柱”(Baker,1963:92)。而勃莱特所说的“从来我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正好表明她根本不遵守道德准则。因此,她说的“坏女人”不足以成为她知道自己是“坏女人”的证据。
(二)被误解的卡洛斯·贝克
贝克真是将勃莱特视为“魔女”的批评家吗?这只是一些评论家对贝克观点的误解。张叔宁(2000)在《魔女还是新女性》一文中写道,“贝克的结论是:‘总而言之,她是该进地狱的致命的三十岁的女人’”。他进而认为,魔女一说从此确立,贝克也因此而成为“魔女说”的代表人物,“Circe” 一词成为勃莱特的代名词。然而,根据《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相关章节上下文的叙述,这种理解是不完全正确的。正如贝克这一小节的标题是“魔女与伴侣”(原章节的标题为“Circe and Company”),一些批评家只看到标题与结论的一半。
事实上,“Circe”这个词不是贝克而是科恩率先使用的,并且只在书中出现一次。在第十三章,迈克在转述科恩的话时提到这个词。“‘他(科恩)叫她迷人精(Circe),’迈克说。‘他硬说她会把男人变成猪。妙哉。可惜我不是个文人。”(海明威、赵静男,2004:158)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迈克等人对科恩这个说法是充满讽刺的,并不认同他给勃莱特贴上的这个标签。事实上,贝克也正是在竭力证明勃莱特不是魔女,或者说,他正试图从中间立场出发在她身上找到“魔女与伴侣”的属性。关于科恩的这个对比,贝克指出,“如果海明威一直是按照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铬黄》(CromeYellow,1921)风格刻画文学人物,他可能已发展科恩的比较”(Baker,1963:87)。但很显然,贝克做出这个表述时的语气是虚拟的。同时,贝克虽然强调海明威的第一部小说与“神话方法”(mythological method)相关,但他同时强调这种方法是“特别的”,并认为有必要将这一特别的方法与乔伊斯(James Joyce)和艾略特 (T.S.Eliot)等人的“写神话”(mythologizing)进行区分。在贝克看来,“神话方法”与“写神话”具有显著区别。海明威的“神话方法”是他自己的,“因为海明威早就设计并发展了自己的神话化倾向,这种倾向并不依赖于之前的文学作品、学术脚注或对段落的识别”(Baker,1963:87)。这就表明,海明威的“神话方法”与真正的神话有所不同,而“写神话”则是以固有的神话为范本的艺术创作。的确,贝克在区分“神话方法”与“写神话”后提出了一系列反问以说明海明威“神话方法”的魅力,有人认为这是贝克将勃莱特当作“魔女”的最强有力“诘问”。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海明威与乔伊斯的区别是显著的,“Circe”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最长的一个插曲,“Circe”采用“舞台剧的形式、以舞台说明和大写的人物姓名结束,这在《尤利西斯》(Ulysses,1922)中是独特的”(Flynn,2011),而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中只有一个词叫 “Circe”。
“如果他原本期望追随艾略特《荒原》(TheWasteLand,1922) 或者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神话方法,海明威显然就能这样做。但是他自己的美学观点使得他远离文学的神话改写并将他带入心理符号建构的深层区域”(Baker,1963:88)。贝克进而指出,“这是一个并不需要特别的文学手段加以解释的区域,只需要一个人的同情和一定程度的强化情感意识”。就此而论,贝克根本没有给勃莱特贴上“魔女”的标签。的确,贝克列举了种种可能适合勃莱特的标签,比如人首蛇身女怪、摩根·勒菲、女巫等,并进而指出她是该进地狱的致命的三十岁的女人。但这只是其论断的一部分。事实上,贝克接下来的语义发生了根本转变:“然而她就是她自己,总是引人注目。其他的名称都纯粹是任意的标签。只要这个关于女妖的名单没有尽头,其标签就可以成倍地增加”(Baker,1963:90)。显然,这才是贝克所言的重点。也是这个章节标题的意旨所在——勃莱特是一位“魔女”与“伴侣”两者兼具的人物形象。与这个结论相呼应,贝克进一步指出勃莱特对两个男人存有毫不含糊的敬畏:一个是真有男子气质的杰克;另一个是罗梅罗。而对于迈克,勃莱特曾成功地将他从男同性恋同伙中解救出来,“此后他在她活力四射的陪伴下过着社交聚会般的生活”(Baker,1969:153)。这表明,勃莱特并没有将所有的男人变成猪。贝克认为她不是个无情的妖女。这个论断表明,贝克的“Circe”与张叔宁的理解是有出入的。尤其是贝克接下来将勃莱特与巴恩斯的爱情比作“亚伯拉德-哀绿绮思式的关系”(The Heloisa-Abelard relationship)进一步表达了对勃莱特的同情。在亚伯拉德与哀绿绮思的爱情中,正是因为亚伯拉德被哀绿绮思的叔父粗暴阉割才使哀绿绮思成为修女的。因此,贝克写道:“作为第一个受害者,勃莱特是黑暗的维纳斯。如果她没有在在战争中失去‘真爱’;或者杰克没有丧失性能力以取代她的亡恋,勃莱特不断的自我毁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不可避免”(Baker,1963:92)。据此来看,贝克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战争和巴恩斯。同时,这个标题、论证过程与结论恰恰表明,贝克在批判勃莱特的过程中开辟了以折衷立场避免极端化的一条新路。
《太阳照样升起》出版后,海明威也被迅速贴上“迷惘的一代”的标签。海明威对这个标签做出了不遗余力的反驳。自威尔逊以降,勃莱特也被不断地贴上“坏女人”或具有类似含义的标签。大量海明威传记研究表明,科恩的原型人物是哈罗德·罗伯 (Harold Loeb)。“我要把那些杂种撕得粉碎”,海明威曾对好友凯蒂(Ketty)说,“我要将每个人都写进这本书,那个犹太佬罗伯是个恶棍。但你在书中是个好姑娘,我不会做任何惹你生气的事”(Baker,1969:154)。海明威将罗伯称为“恶棍”源于他对罗伯和朵芙(Duff)一段风流韵事的嫉妒。可见,海明威对科恩的态度是恶意的,对其原型罗伯也是极其不友好的。但他对勃莱特的原型朵芙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他也从未对此做出过任何解释。他到底想把勃莱特刻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最希望读者将其理解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勃莱特到底是个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海明威对勃莱特持的是褒奖态度还是贬损态度?这些都是海明威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勃莱特·阿什莉:一个介于妓女与新女性之间的人物形象
(一)勃莱特不是一名妓女
在《太阳照样升起》中,勃莱特不停地奔走于舞会、聚会与酒店之间,但按照常理都是男人们给她埋单。小说也没有交代她是否具有经济来源,但她绝不是一个以身体做交易的妓女。尽管她称谓自己的“bitch”也含有“妓女”的意思,但她不以肉体换金钱的滥交行为表明她并不是一名真正的妓女。
勃莱特与真正的妓女形成鲜明对照。为了强调她不是妓女,海明威早在第三章就以乔杰特·莱布伦做好铺垫。乔杰特是一个闭着嘴确是个相当漂亮的姑娘,但一开口笑就露出一口坏牙。她卖身是为了换取金钱和食物。虽然巴恩斯因为身体缺陷无法和她进行肉体交易,但他仍然委托老板娘给她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勃莱特则被描绘成一个十分美丽迷人的女人。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对她的美貌做出评价,比如,科恩说“这个女人很有魅力。她有某种气质,有某种优雅的风度。她看起来绝对优雅而且正直”;比尔·哥顿认为“多出色的女人啊”;老伯爵对她说,“你的醉态真迷人”,等等。关于二人的区别,富尔顿(Fulton,2004)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女人之间具有显著区别——乔杰特可以出价购买,勃莱特则不是用来销售的”。这也可从她与伯爵和与罗梅罗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证明。在与伯爵交往的过程中,除了伯爵支付消费费用外,勃莱特并未向他索要任何额外费用。此外,她还拒绝了伯爵的一项花费巨大的旅行请求。
勃莱特不是妓女的身份在与罗梅罗的交往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在见到巴恩斯后,勃莱特说:“我当时没有把握,能不能把他打发走,可我一个子儿也没有,没法撇下他自己走。你知道,他要给我一大笔钱。”(海明威,2004b:264)假如勃莱特说是她主动让斗牛士离开是个谎言,“可我一个子儿也没有”则是一句真话。这是因为,如果她有钱,她就有可能自己选择主动离开罗梅罗;同理,如果她有钱,她也不用请求巴恩斯在罗梅罗走后去将她从酒店接回。这些叙述均表明,勃莱特作为风流女人与妓女具有本质的区别。
(二)勃莱特距“新女性”仅一步之遥
与那些持“坏女人”论的传统批评家不同,女性主义批评家将勃莱特解读为“新女性”。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复兴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家纷纷从海明威女性人物中读出“新女性”的含义。这个时期,美国学界还先后出版了波尼斯·科特(Bernice Kert)的《海明威的女人:爱他的妻子们及其他》(TheHemingwayWoman:ThoseWhoLovedHim-theWivesandOthers,1983)和罗格·惠特罗的《卡珊德拉的女儿们:海明威作品中的女人们》(Cassandra’sDaughters:TheWomeninHemingway,1984)两部专著。这两部作品都是沐浴着女性主义批评的春风而问世并以女性视角来看待海明威的女人们的。尤其是惠特罗,他公开对勃莱特的“坏女人”标签进行驳斥:“勃莱特迷失而愧疚,她悲惨地自我毁灭,但将她解读为坏女人是绝对不合理的”(Whitlow,1984:52-58)。张叔宁在《魔女还是新女性》中扼要梳理了美国学界七十年来对勃莱特从魔女到新女性的历史变迁。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深入分析勃莱特的“新女性”特征。的确,勃莱特具有自己的主见和个性的外表,男孩子后梳式的头发也“反映了新的审美理念”(Wagner,1987:95)。她尤其具有新女性最为看重的特征——性自由。这种行为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勃莱特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新女性”。这是因为,新女性的崛起是以女性接受教育与进入职场为背景的。虽然读者无法得知勃莱特的受教育状况,但可以确信她没有职业。科恩与比尔都是作家,巴恩斯是一名记者,罗梅罗是一名斗牛士,勃莱特只是一位无业游民。她拥有的只是稍纵即逝的美貌和放荡成性的行为。“经济独立与心理独立是相关的,在《太阳照样升起》中金钱是由男人们操控的”(Martin,2007:73)。她每天游走于酒吧、酒店之间,完全依靠男人为她埋单,“在享有性自由的伦理时,没有确立自己的经济独立,并且对男人们为她付账单没有任何顾虑”(Donaldson,1996:178)。这些账单大多数是巴恩斯支付的,小说结尾处她也是被巴恩斯从旅馆接回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职业、没有收入的勃莱特不仅没有尊严,更注定她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新女性”。斯蒂芬·布朗(Stephen Brown,2018)指出,《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斗牛士罗梅罗是“在和公牛的‘相遇的凝视’(gaze of meeting)中恢复了男子气概”。不难看出,巴恩斯也是通过金钱在勃莱特面前赢得尊严、恢复男子气概的。在《永别了,武器》中,雷纳第对亨利说,“我得在巴克莱小姐面前装阔佬。你是我亲密的好朋友,我经济上的保护人”(海明威,2004c:16)。在《太阳照样升起》中,巴恩斯显然是勃莱特唯一的朋友和经济上的保护人,他也在不断的账单支付中获得一定尊严。“金钱是杰克丧失的男性气质的替代物,使他得以逃避战争现实并帮助他恢复身心缺陷”(Cannon,2012)。
海明威是一位对社会历史变迁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作家。因此,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二十年代女性的觉醒,女人欲从传统的父权社会中争取更多的权利。她们接受教育、从事职业;想要和男人一样抽烟、喝酒;留着男人一样的短发。最为重要的是,她们极力追求性自由权利。海明威在《太阳照样升起》与《永别了,武器》中都回应了这一时代特征。在《永别了,武器》第三十八章,凯瑟琳与亨利的一则对话鲜明地体现出凯瑟琳的性自由倾向:“‘我患过淋病。’……‘我倒希望也得。’…… ‘我讲真话。我希望和你一式一样。我希望你玩过的姐儿我都玩过,我可以拿她们来笑话你。’”(海明威,2004b:323)
长期以来,一些批评家错误地将这则对话理解为凯瑟琳没有个性,在爱河中沦为彻底的奴隶。但是,凯瑟琳此处关于患淋病的愿望与她早前希望与亨利合二为一的愿望具有本质区别。众所周知,淋病、梅毒都是性传播疾病,只有在拥有多个性伴侣的前提下才可能患上这些疾病。凯瑟琳说“我倒希望也得”,这实际上是在向亨利暗示她也渴望和亨利一样拥有性自主权、拥有多个性伴侣。亨利的“不,别胡说”,既是一种本能的回应,更是一种对凯瑟琳索要权利的担忧。这种忧虑在第三十九章关于剪发的对话中进一步体现出来。当凯瑟琳说“我要等到小凯瑟琳出生后再去剪发”,亨利一言不发,“我没说什么”。直到凯瑟琳紧接着追问:“你不会说我不可以剪发的吧?”亨利才被迫回答:“我现在爱你已经很够了,你要把我怎么样?毁坏我?”亨利故作镇定的发问清楚地表明他对凯瑟琳日益觉醒的女性意识的担忧。
不少批评家认为亨利具有强烈的恋物癖,尤其是对凯瑟琳的头发。的确,书中多次提及凯瑟琳的头发,被认为是亨利的精神慰藉。然而,凯瑟琳不仅威胁想要患上淋病,还打算剪掉头发。这意味着她极有可能变成一位勃莱特式的女人。这当然是亨利也是海明威所不愿看到的结局。因此,凯瑟琳必须在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前死去。海明威的目的就是要“葬送这个浪漫爱情,而不是褒奖它”(Whitlow,1984:20)。由此可见,虽然凯瑟琳之死对整个小说而言是个不圆满的结局,但这个不圆满的结局对于亨利和海明威而言却是极其圆满的。它主要服务于海明威艺术表达的需要,旨在突出现实主义者亨利与浪漫主义者凯瑟琳之间的冲突,并表明作者是在坚定地支持现实主义者亨利。因为,如果凯瑟琳最终还活着,她注定变成一个荡妇,这是海明威笔下的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女人的必然命运。
《太阳照样升起》与《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两部十分重要的作品,勃莱特与凯瑟琳也是海明威作品中两个最为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二人也具有许多共性。比如,都在战争中失去恋人,现任恋人都是老兵;都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女人;都很漂亮迷人;都是社交高手,等等。因此,有些批评家说“凯瑟琳是改良版的——事实上是更为现代版的勃莱特”(Donaldson,1996:180)。这种说法是欠妥的。对比发现,她们也有显著的不同:勃莱特很时尚、个性,凯瑟琳则不然,“是个很老派的老婆”(海明威,2004c:156);勃莱特是男人们的中心;凯瑟琳则以男人为中心;凯瑟琳有工作和收入,勃莱特则没有。因此,她们之间不存在改良关系,离真正的新女性都差一步之遥,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
勃莱特与凯瑟琳不能成为真正的新女性的缘由是海明威固有的对女性的不友好态度。尽管海明威对时代潮流具有高度敏感性,但他并不欢迎新女性的到来。“滥交没有出路”是海明威在《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核心观点。雷纳·桑德森(Rena Sanderson)指出,“海明威在宣布该书‘滥交没有出路’这一核心观点时就已经对勃莱特做出了间接评判”(Donaldson,1996:178)。也就是说,没有经济来源,仅凭滥交是不可能成为新女性的。因此,海明威压根就没有打算将勃莱特刻画成一名新女性,只是将其描绘成一名毫无希望的白日梦者。或许,海明威最早接触的新女性是他的母亲霍尔·格蕾丝(Hall Grace)。大量海明威传记批评表明,格蕾丝整日沉迷于音乐艺术,无心家事,导致其丈夫成为一个既主外又主内的双重角色。海明威很早就将同情心投射在父亲身上。因此,他对新女性怀有敌意,不可能为新女性的到来摇旗助威。梅耶说得好:“在他最出色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中,他最为漂亮迷人的女主人公勃莱特操控着一切男人。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他不再允许他的女性人物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除玛格丽特·麦康伯这个泼妇外,其他所有女性均屈从于其男性主人公”(Meyers,1985:445)。的确,除玛格丽特将丈夫置于死地外,强势的女主人公形象在海明威后期的长篇小说中不复出现。这个转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或许当初海明威在创作过程中并不清楚要将勃莱特塑造成何种人物形象;或许他已经意识到勃莱特式的新女性人物对女性的觉醒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威胁到男性的地位;或许他有意将这些具有新女性苗头的女性扼杀在他的作品中,凡此等等。就这些推测而论,勃莱特也可以被视为一个试验品、牺牲品和一个“失败”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海明威不小心塑造出了一个即将完全摆脱男权社会控制并对新女性运动具有一定引领作用的女性人物形象。因此,在吸取塑造勃莱特经验的基础上,海明威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中采取欲擒故纵的方式将一个正逐步从传统女性变成新女性的凯瑟琳成功地扼杀在摇篮中。就此而论,凯瑟琳之死是一个早就编制好的完美结局,是海明威对正在崛起的新女性当头一棒式的致命回击。
结语
《太阳照样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在其回忆录《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在多个场合回忆了他对《太阳照样升起》的修改和编校。这足以表明他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几本作品集和戏仿之作《春潮》,但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因此,海明威对如何创作《太阳照样升起》并无把握。与此相对应,对于将勃莱特塑造成何种女性人物形象,海明威也十之八九没有把握。的确,他对待人物原型罗伯和朵芙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在这种逻辑的指引下,小说的叙述者巴恩斯对科恩充满敌意、毫无同情之心;但他对勃莱特则怀着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既爱又恨的复杂态度。因此,一方面勃莱特在叙述者和创作者心目中并不总是“坏女人”,另一方面她又不是叙述者和作者要极力宣扬、歌颂的人物形象。在新女性盛行的特定历史时期,勃莱特具备新女性的绝大多数特征,但唯独经济上没有独立自主。这导致她无法成为一名完全的新女性,也注定她仍然要依附于男性。如果非要给勃莱特的尴尬处境做个定性,她充其量只算是一个介于妓女与新女性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这一定性,既可避免将其推向某个极端,也可解释她缘何兼具“妓女”与“新女性”的一些特征。或许,这一阐释更接近海明威刻画这个人物形象的初衷。
海明威的《杀手》和《永别了,武器》等作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被介绍到中国,中国的海明威研究也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即使从董衡巽的《海明威浅论》(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开始算起,至今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虽然中国的海明威批评成果丰富,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第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明威研究成果不多,大多数成果属于国外引介,缺少原创性,也具有一定滞后性。第二,一些批评家脱离原著,学术严谨性需要增强。有些批评家甚至把《永别了,武器》第一章死于霍乱的士兵人数 “七千人”都搞错了,也有人在其著作中搞错《老人与海》的出版时间和获奖时间,等等。这正如陆谷孙所言,有些拥有国家级课题的海明威批评家居然也将ForWhomtheBellTolls说成ForWhomtheBellRings。陆谷孙所言绝非危言耸听,这些不严谨现象是的确存在的。第三,重复研究过多,很多研究者不熟悉、不了解海明威研究的新动态,导致很多研究或直接或间接重复他人成果,甚至造成误解、曲解。总之,这些都是当前中国海明威研究中应该克服或者需要加强的问题。
注释:
①这一类女性的标签很多:如张叔宁的“魔女”;贝克在批判两个极端时,将其称为“致命的女人”(deadly females);赵静男在其所译的《太阳照样升起》中将勃莱特所说的“bitch”译为“坏女人”。为统一起见,本文采用“坏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