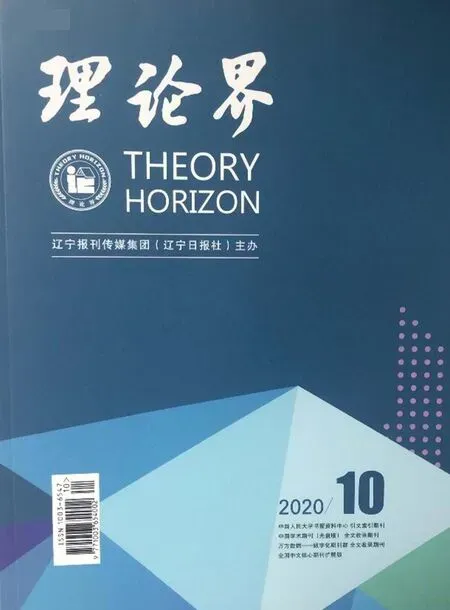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理论的语言学渊源探析
斯竹林
列维·斯特劳斯开创了神话研究的新纪元。正如韦尔南所说:“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后,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具体破译工作上,情况都不一样了,他的工作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和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他的对手、跟随者和那些同行来说,神话研究现在不仅面临着新的问题,而且即使用同样的术语也不可能提出旧的问题。”〔1〕
韦尔南的称赞并非夸大其词。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前,学者们的神话研究往往停留在外部,将对神话意义的分析引向共同的情感驱动力,或集体的梦,或宗教仪式,或社会文化背景,这会让神话的本质和特性淹没在文化遗留物、集体无意识、仪式或功能主义中。为了避免上述研究的弊端,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语言学的视角、原则、方法、理念扩展到神话研究中,将神话研究引向神话内部,并对结构语言学中的元语言、区分性特征、语言的不变性、能指与所指有具体运用。本文拟从神话学的研究视角,对其神话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对结构语言学的扩展加以描述和总结,以期为当代的神话研究提供些许有利的学术资源。
一、神话的“元语言”探寻
结构语言学对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研究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神话叙事层面和结构层面的划分上。列维·斯特劳斯将神话研究分为显性的叙事层面(在叙述中直接表达的故事意义)和流动的文本背后恒久的结构层面(隐藏和不自觉的非叙述意义)。神话的叙事是流动的,但背后的结构却是稳定的。
这种分层观念来自结构语言学中言语和语言的划分。索绪尔首先区分了语言与言语,提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确定对象,是社会的。而言语是个人的、流动的。结构语言学家要“站在语言的立场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2〕语言是词、惯例和语法的完整体系,它不是个人创造的,而是“已有的”。当个人发音时,会从语言系统中选择词汇、语法和语调音调,并按特定的秩序将它们排列起来以传递信息。言语是由音素组成的代码,结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解码,从流动性的言语中寻找稳定的语言结构,研究组织语言规则和构造方式,而不是个体说话方式。
在此基础上,雅各布逊并提出语言研究应区分两个层次——“谈论语言之外事物的‘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和谈论语言代码本身的……‘元语言’。”〔3〕结构语言学的任务是要把语言社团中客观的代码转化为元语言。
语言是神话由以开始的基础,因此,列维·斯特劳斯从结构语言学视角划分神话的结构。神话在讲述时,沿着不可逆的时间轴展开句法序列,所以它是言语。可神话又是一种超时间的存在,它的叙述模式不受时间限制,能说明现在、过去和将来。它由不同元素有序组织成一个共时性的结构系统,以构成人们自觉遵守的让故事产生的符号(语义)空间,因而它又是语言。
更进一步说,神话是更高层次的语言。神话的实质不在于文体、叙事方式或句法,而在于故事。神话由此脱离了它由以开始的语言基础。神话“‘超结构地’使用语言形式,可以说,它们形成一种‘元语言’,其中结构在一切层次上起作用”。〔4〕正是这种元语言的特性使神话与其他文体相区别。神话的规则与词所塑造的形象和描述的行动,不但是语言层面上的“常规能指”,还是另一个层次的意义系统的意义成分。于是,“国王”不仅仅是一个国王,“牧羊女”也不仅仅是一个牧羊女,而是词和其所蕴含的所指构造对立系统的手段,这个由理智形成的对立系统包括阳/阴(从自然方面看)和尊贵/低贱(从文化方面看)以及在这六个术语中间的一切可能的置换。
神话的结构研究是解码的过程,即要寻找这种“元语言”,即一种公开的意识背后隐藏和不自觉的深层思维结构。他相信,神话素组合关系的数量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人类凭空创造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从有限的思想库存中选取特定的组合。通过神话的结构分析,能够建立人类思想的“元素周期表”。
同时,“元语言”不在单个的神话之中,而在整个神话系统之中,个别的故事是系统中的单位语符列。神话对应着听众内部的“心理——生理”时间,对神话的理解,往往不是由发出者,而是由听众决定的。只有当听众的心智可以随着故事的展开审察全部故事时,才能领会神话的含义。“神话和音乐作品都像是管弦乐队的指挥,听众则成为沉默的演奏者。”〔5〕年长的社会成员,集体无意识地向年轻成员传达神话的音讯。当接受者领会了每一个音讯的意思,并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解读时,就会领会神话的含义。列维·斯特劳斯将单个神话比作一次演奏,将整个神话系统比作管弦乐队的乐谱。人类的祖先集体向后代无意识地传达了单个音讯,结构研究者通过了解神话中对立而又混合一处的人、动物、精灵、神的相对位置,解码原初乐谱的形式。
二、从“区分性特征”到神话二元结构
在对神话的结构关系的解码中,列维·斯特劳斯受到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基本原则的影响:语言符号“不是通过它们固有的价值,而是通过它们相对的位置”来起作用的。〔6〕语言是封闭、自足的结构系统,语言的意义要在语言系统中找寻,单个语言符号的价值在组合关系中得到确证,如果只是孤立地考察元素,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雅各布森在音位的“区分性特征”分析中将相对关系发展为二元对立关系。“对立项在数目上是两个……对立双方联系紧密,一方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引出另一方。”〔7〕在他看来,复杂的音位系统是对简单音位系统的多维度发展,这种简单音位系统——辅音和元音之间的对照——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幼儿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首先通过辨别音量的对立关系,认识基本元音和基本辅音的对立关系。再通过聚集与分散(Compact/Diffuse),锐音和钝音(Grave/Acute)的二元对立产生“元音三角”和“辅音三角”。
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二元对立观念直接运用到神话研究之中。在“结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分析”中,他首次用结构语言学的三角结构分析人类的婚姻模式,提出了以交换与不交换,接受与给予两个对立面产生的互惠(Reciprocity)、权利(Rights)和义务(Obligations)的三角。〔8〕
之后,他将此方法运用到神话的结构分析中。为了寻求神话文本背后永恒的结构,列维·斯特劳斯提炼出神话的基本情节,每个基本情节都是人物与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或是人物与众不同“状况”。他将情节浓缩成的简单关系(或状况),称作“神话素”(Mythemes,或大构成单元)。神话的意义并不在单个的神话素中,而在于神话素的组合关系中。
在神话学第一卷中,列维·斯特劳斯以自然与文化、常态(非人工商品)与变态(人工商品)的双重对立绘制出“烹饪三角”,研究对立的感官属性:生与熟、新鲜和腐烂、干与湿。在第二卷中,感官的对立被形式的对立取代:空与满、容器与内容、内与外。在第三卷中,他又引入水和火两个元素,将主要制作食物的方式(烤、熏、煮)组成与第一个形式相颠倒的结构形式。
在经典的“阿斯迪瓦尔的故事”分析中,列维·施特劳斯收集、分析和解释了大量关于神话的文化和人类学的背景数据(人口迁移、经济情况、社会结构、亲属关系),将植物、动物、事件和人群分类,确定了神话的结构框架。神话被分为地理的、宇宙学、社会的和技术经济四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有其符号意义,它们都被看作神话共有的逻辑结构的变化。地理图示显示出与玆姆申人捕鱼路线一致的季节性迁徙,宇宙哲学图示显示出人们观念中上下、天地、陆海的关系,社会学图示显示出随夫居和随妻居习俗的变换,技术经济图示显示出捕鱼的经济活动。最后将四个层级加以整合,揭示出神话的整体结构:母系倾向和父系倾向之间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接着,在对变体的研究中,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列举东与西的对立、海与陆的对立、素食与荤食的对立、限制和不限制的对立,把地理学范畴的词汇与食物范畴的词汇结合了起来。他将不同的神话素看作同一个结构成分的置换,把对立神话素看作是由地理、习惯或功能不同而引起的倒置,从而把表面上的不同变体纳入同一个结构体系之中。通过对神话进行结构层面的解读,列维·斯特劳斯运用二元对立的手法,建立起隐藏在神话后的包括地理、宇宙观、技术、社会经济情况在内的复杂结构。
三、从语言的“不变性”到神话系统的自我界定性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结构具有独立性,它甚至可以操纵个人。他想说明的“不是去表明人如何用神话进行思维,而是去表明神话如何用人进行思维却不为人所知”。〔9〕
神话的自我界定理念同样受到结构语言学的影响。索绪尔认为,语言具有不变性,语言系统一旦形成和被使用,就不受个人主观意志左右。“语言之所以具有稳固的性质,不仅是因为它被绑在集体的镇石上,而且因为它是处于时间之中。”〔10〕语言既是历史中形成的语言习惯,又对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又是特殊的社会契约,无法通过协商而更改。因此,语言系统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
列维·斯特劳斯借鉴结构语言学的观点,认为神话结构系统是封闭、自足的,具有自我界定的性质。首先,神话的元素取自于语言,受到语言系统的制约。列维·斯特劳斯将神话比作“理智的修补术”,神话思想借助结构性的语言,将个人和社会历史中所凝结的事件碎屑拼合,建立起有结构的组合。它利用旧的社会性话语(原材料)阐发出新的意义(家具)。而神话的创造者为修补匠,神话(修补匠)的创作受到语言(零件)的限制。首先,符合神话意指形象的词项本身是有限的。“神话思想的特征是,它借助一套参差不齐的元素表列来表达自己,这套元素表列即使包罗广泛也是有限的;然而不管面对着什么任务,它都必须使用这套元素(或成分),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可供支配的东西。”〔11〕其次,这些词项在语言中已经具有了一种意义——它们必定不是单纯的和单义的,却也可以作为语义的或审美秩序中的不变项而存在,这些意义使其调配的自由受到限制。
同时,决定把什么语言成分置于神话结构的何种位置,也受到神话结构的制约。修补匠对组成神话的元素加以推敲,以便发现其中每一项能够“意指”(Signifier)什么。元素可以放入不同的位置,但是所做的每种选择都将牵扯到该结构的全面重新组织,这一结构的改组将不同于人们所构想的东西。神话意义的改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其说是人创造神话,不如说神话创造自身。
神话被创作或是被感知时,都要与神话系统发生联系。个人和集体在创作神话时,总是受到神话系统在人们思维中的沉淀,即神话结构和规则的制约。换言之,神话系统的结构对具体的神话作品内容、语言、形式,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神话符合结构的规范,才能纳入神话系统中,人们才把它当作是神话。破坏系统的规范的创新只能是低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人们或是无法理解它,或是把它归入故事或传说而不归入神话的类别。因而是神话结构系统启迪人们说出了神话,而谁来说出神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话体系的完整性通过说话者得到了证实。
从这个角度说,不是人创造了神话,而是神话通过结构和规则发展转化并创造新的变体。但变体的产生与个人的创造相关。神话的创造者会在对有限的语言元素的选择中,叙述他的个性和生活。因此,神话被无限地产生出来,每一个都与其他的略有不同。神话螺旋式地发展,直到产生神话的智力冲动耗尽为止。从独立的神话结构出发,列维·斯特劳斯希望从结构意义上探寻人类的思维模式。
四、从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到神话对思维的浓缩
语言的转变与人类的思维活动密切相关。索绪尔认为:“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预先确定的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将是模糊不清的。”〔12〕语言不仅能让人们进行交流,更是思考过程的基本要素。在思考之前,我们先要对事物分门别类,然后再用语言描述它们。这种分门别类的过程就是对意义划分的过程。思想离开词语的表达就是混沌一片的,语言是思想的媒介,是它让声音和思想结合,才导致各单位之间划清界限。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这不仅指“能指”与“所指”之间任意结合,也是指人们以“能指”在混沌不清的意义连续体上任意地“划分”出不同的“片断”(所指)。
在此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提出,同语言一样,神话是思想在生成逻辑架构时的浓缩。神话是通过故事(意象和事件)推进的,而故事大于词和概念,所以它更明确地体现了人类思维活动的特征。当我们以神话去思考、整理和领悟周围的意义世界时,也会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统一体切割成段,以探寻事物的分类和次序,而这种切分和排列的方式同样会应用到对其他事物的思考中。
神话的创作者是思想的储存者,他们将现实中的一切翻来倒去,将社会的、物理的、心理的概念嵌于神话的感性形象之中。人们既不将概念直接显现,也不将之抽象化,而是将它们隐藏在具体物象背后。“我们在交易思想,他们则在储积思想。野性的思维在实行着一种有限事物的哲学。”〔13〕这种思维方式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野性的思维”,它是一种直观感性的思维,它借助知觉和想象,以持续不衰的好奇心改造自然、创作神话。
在索绪尔“能指”和“所指”互动关系的基础上,雅各布逊以隐喻和转喻描述了意义转换的过程。“话语段(Discourse)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一个主题(Topic)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毗连性关 系 引 导 出 下 一 个 主 题 的。”〔14〕隐 喻(Metaphoric) 在于对类似的认识,转喻(Metonymic)在于对邻近的认识。隐喻和转喻也体现在除语言之外的其他象征符号中,如弗洛伊德用转喻(位移)和隐喻(冷凝)分析梦的结构,弗雷泽将巫术分为基于相似定律的模仿巫术和基于连续性关联的传染巫术。
列维·斯特劳斯将雅各布逊的“隐喻”和“转喻”拓展到神话中。通过隐喻,神话中的超自然的世界——人、动物、精灵和神的关系组合得以被理解。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所有神话都隐喻了一个大主题:“从天性到教养的转变,代价是永远丧失与天空和大地交流的能力。”〔15〕通过转喻,我们可以通过神话阅读出某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气质,可以看到它缩影的世界的变化。神话是一面放大镜,突出了惯有的思维模式。神话提供了一个思维框架,借此,人们对斗转星移、昼夜交替、季节转换的思考方式同样可以运用到对社会组织、邻近群体的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去。
五、结构语言学的进展与神话研究的发展
早期结构语言学的缺失同样出现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中。雅各布逊分析“区别性特征”时的刻板二元形式(反映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中),已经受到了许多结构语言学家的抵制。现代结构语言学家已经认识到,人类发出语言和接受语言的机制比雅各布逊的机制更为复杂。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生成语法,认为人脑中存在先天的模块或结构,人生来具有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揭示人脑的思维机制。从此,语言研究的重点从外在的语言行为转到内在的语言能力。我国结构语言学者石毓智在解释这种生物机制的本质和它与语言能力的关系时提出“语言能力合成说”,认为人类认知是层级系统,“语言能力不是一个独立模块,也不是处于认知系统最基层的,它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16〕语言能力依赖天生的认知能力(符号表征能力、对数的认识能力、分类概括能力等),在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及非语言的技能和知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生成结构语言学和认知结构语言学更加关心的是人类取得语言模式的生成规律,而不是“元音三角”和“辅音三角”中的语音本身。雅各布逊的区别性特征,无法揭示获得语言模式的机制。同样的,列维·斯特劳斯通过神话的结构研究,虽然揭示了一部分无意识思维过程的表现,但却无法揭示人类思维的真正机制。
此外,雅各布认为“有一些简单的关系是所有语言都具有的”,〔17〕列维·斯特劳斯也将从特殊族群中的神话中探寻的无意识的思维结构,作为全人类的共通的思维规律。将个别的神话看作是神话系统的单位语符列的。那么,索绪尔意义上的“口头语言”——单个神话的特殊性和地方性在何处表现?它如何反映当地的文化?但列维·斯特劳斯不关心特定社会的集体意识,他追索的是人类思维的普遍结构,不仅适用于太平洋岛岸的土著,也适合于所有语言的表达者。但语言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它是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质是它的内在的特性之一。神话同语言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性的,是所有讲这种神话的人的集体意识的一部分。
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语言学对待音位的方式,将神话素从语境中抽离出来,无法对神话进行贴合语境和文化情境的结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将神话看作语言的一部分,而神话素是根据音素作为参照物,从神话叙事的核心要素中提炼出来的。这似乎表明,即使没有对产生神话的文明的深入了解,也可以解读一个神话,除了神话自身提供的上下文外,它不需要在任何其他背景下进行。正因如此,在俄狄浦斯王的神话研究中,列维·斯特劳斯根据主题的相似性而分离神话素的过程,以及在神话矩阵中对神话素进行分类的过程也同样武断。
正如韦尔南所说,结构分析必须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神话相关。他以希腊神话为依托,“分析万神殿的结构,展示不同的力量是如何组合在一起、联系在一起、相互对立和区别的。只有这样,每个神或每一群神的相关特征才能出现”。〔18〕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基础上,韦尔南以希腊神话为基础,将神话的结构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是叙事形式分析,即表层结构的分析。其中包含形式的分析——对故事组成方式的分析,句法关系,片段在文本叙事中的联系。也包含故事的语法——叙述背后的逻辑,建构在行动和反应之上的模型,情节变化背后的动力。第二个层次是语义内容分析。即通过建立对立或相似细节的情节网络(时空、物品、行动、地点),破译语义内容,定义按故事的语法建构的形式结构和在不同层面上的具体的语义内容。第三个层次是文化语境分析,即文化的特定形式产生和理解的符号空间。从神话中,可以获得思维的特性及其分类的框架,并将它放置在思维和社会历史的特定位置。〔19〕在神话的结构和情节中,每一个细节都具有精确的含义,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参照整个数据的其他部分来确认或反驳。希腊神话中体现的是希腊人的文化情境中会用到的元素:植物、动物、天象、饮食、社会、婚姻、性爱,神话的意义就存在于这当中,神话中所体现的思维模式与这些具体的元素相关。因此,在神话研究中,不应忽视具体的细节,这样才能赋予文化和思维模式的独特性。
六、结语
综观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他对神话研究的视角、原则、理念和方法都有开拓和创新。具体表现为:(1)将神话研究引向神话内部,探寻神话的“元语言”。(2)将语言元素的系统分析发展为神话的结构分析。(3)受“能指”与“所指”的互动关系的启发,探寻神话与人类的思维模式的深刻关联。这种对神话研究的创新,与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密不可分。
然而,通过以结构语言学作为探讨途径的神话结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最终关心的是“人类思维”的真理,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社会或社会组织。当他想深入探寻人类思维时,他以无意识思维的结构作为切入点,忽视了文化和思维模式的独特性。
列维·斯特劳斯与韦尔南探寻的同样是不同版本(或变体)的神话背后恒定的无意识思维模式,而不同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探究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最终是为了得出人类思维模式的普适性的结论,而韦尔南不是探寻人类的思维模式,而是古希腊人的特殊的思维模式。在韦尔南等一批结构主义学者的努力下,神话的结构研究逐渐摒弃对普适性的思维模式的寻求,而与特定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