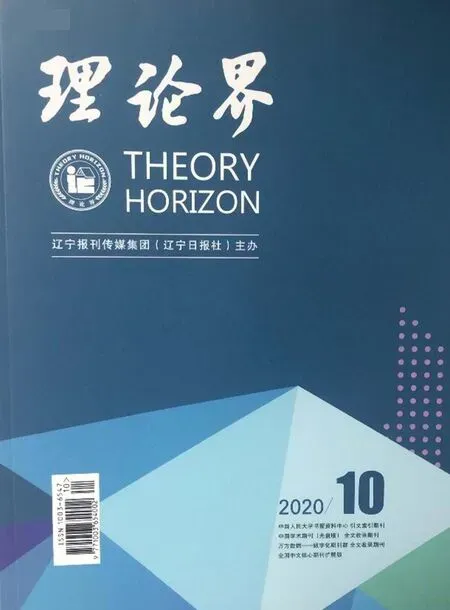谁动了莎菲的日记?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叙述人形象分析
陈 蕾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主人公莎菲曾引发不小的争论,尤其是人物体现出的“反叛”性格一直以来被视作一种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反映。〔1〕就像有学者所说,“莎菲”正是打开这部小说的一把关键性钥匙。〔2〕在某种后现代语境有赖于言说和叙事展开对主体想象的潮流中,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主人公借助“日记体”塑造“自我”的意义。〔3〕在这个意义上从形式出发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分析和比较是必要的,毕竟由于叙述人的存在使得谁书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个关乎谁是主人公、如何看待主人公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尝试通过探究“日记”中叙事人的形象重新理解构成“莎菲”这一形象的元素,以及“五四”时期女作家丁玲如何构想这一形象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莎菲身上隐现的现代性特征。
一、“日记”与叙述者莎菲
《莎菲女士的日记》采用“日记”的形式书写,这与近代以来“日记体”在中国的发展有关。首先,日记体的出现与小品文的日渐勃兴不无关联。彼时日记体引起人们关注的地方在于其本身作为一种文体的功能和作用。“日记体大半是小品文里的一种主要形式,而且是一切文体里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日记体的写作,是非常真朴而且自然的。不需要修饰,不会有破绽,只要随随便便写下来,就是真的,好的文章了。”〔4〕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对“日记体”的探索致力于构造一种独立之文体。比如1914年《雪鸿泪史》以“何梦霞日记”托名见刊于《小说丛报》,作者徐枕亚表明此书与《玉梨魂》相比“一为小说,一为日记,作法截然不同。”对“日记体”式抱有独立文类划定的态度。如此一来,使得既往文学中出现对“日记”形式的应用变得难解:在今天重新早期“日记体”作品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淹没在一般性的文学之中,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中使用“日记”的形式在这一时期尚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体文学。这与“日记”形式在当时的盛行形成反差。到了“五四”时期随着表现心理真实的潮流迎来“日记”文学创作的一次高潮。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代表推动了现代白话与日记形式的结合。1923年瞿秋白以“日记”形式创作散文《涴漫的狱中日记》,此后又有郁达夫的《荒城日记》等作品纷纷问世。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由三十四篇日记构成。正是由于“日记”机制的存在使主人公莎菲不仅是情节的参与者,更具有了能够抽身于事件之外的观察者视角。在《日记》中,写日记构成主人公的一个活动,它作为对过往经历的复述和总说,与其他情节不同步发生。作为日记的写作者,叙述人具有全知属性,它与被写进日记中的莎菲存在时空的差异。被写进日记的莎菲与叙述人相比缺少写日记这个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写日记行为保有叙述的相对独立性、单纯呈现内心自白的真实感。叙事在这里出现围绕写日记和其他情节的分层。
叙述行为与其他行为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叙述话语存在巨大张力。在叙述的维度中,叙述人能够同时具备不同的心理活动、叙事声音。比如对待爱情的态度,叙述人与莎菲呈现出鲜明的区别。莎菲对爱情充满幻想,她期待被爱;她在与凌吉士和苇弟的关系中显得软弱,处在被动的位置。这一切被日记外的叙述者莎菲清楚感知,她用日记记录下莎菲对被爱的渴望:大段的日记记录了关于凌吉士是否爱着自己的揣想。莎菲的疑惑和优柔寡断并未暴露在与其交往的男性面前。一定意义上这种在两性关系中对表达爱意的克制已然体现出了女性对自我主体性的追求。然而现实爱恋中的莎菲,其自我意志的表达仅仅停留在了对痛苦的感知层面。她在逐步收获来自凌吉士反馈的爱的信号,却并未因此感到快乐,反而对爱情更为困惑。于是她开始在痴迷爱情中有所警觉,直至最终与凌吉士爆发冲突。这却使得莎菲期望的美好爱情被推向极端反面,即“堕落”和“卑劣”,体现出现实中莎菲对爱情“罗网”进行抗争的不彻底性。她在痛苦境遇中的体悟依旧体现出爱欲作用下的“迷狂”。因此,尽管她在外人面前没有曝露出软弱的性格,但这些特征仍然在她身上鲜明地存在着,在叙事人的面前显露无遗。在这里反映出莎菲获得自我意识的路径与爱情信念的崩塌之间重要的关联,她身上呈现的自我意识实际来源于现实残酷环境、痛苦经历对个体的逼视下向内转的倾向。对于爱情失意的莎菲来说,写日记的叙述者也就开始逐渐成为她在爱情主导者缺失位置上的替代者。在质疑爱情的情况下,叙述人也即是写日记的自己成为了新的情感依赖对象。
叙述人显然呈现出了与莎菲不同的特性。与现实中的莎菲相比,叙述人显得更加理性,对感情有自觉的节制。在小说中叙事人不断通过“我想:……”“我想:……”“我想:……”的表述呈现对问题更全面的思考。一方面,这得益于日记形式造成的时空张力,使叙述人能够游荡在事件发生当时和后来的时空之中,既能够对情境感同身受,又能够全盘审视完整的事态,对此加以观察和反思。另一方面,作为叙述人的日记写作者莎菲恰恰由于这样的多重视角而得以与处在事件中的莎菲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在这里与其说这个人物是转变中的莎菲本人,毋宁说是作家创作中有意无意安排好的一个独立的形象。一个原因在于小说中对日记的写作不是单纯对事件和主观心理活动的记录,而是塑造了一个敞开的对话空间。在这里不仅隐藏着莎菲不为人知的心事,同时暗含着叙述人与莎菲的对话关系。
《日记》中的叙述者并不时时发声,它常常在这两种情况中显现:一是当莎菲陷入情感困境时与之对话,二是解构和嘲讽莎菲眼中的“希望”与“理想”,以领路者的姿态引导莎菲摆脱困境。在《日记》中叙述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能够外于情节,又与主人公的形象有所重叠。一方面,“日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具有自述和“私”的特征。叙述对于呈现和干预个体自我内心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叙述人毕竟不是主人公,在呈现的过程中,也就拉开了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形成某种特殊的语言。〔5〕因此,叙述人与日记体实际上构成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日记》中是围绕关于日记的写和读的关系才塑造了莎菲与叙述者不同的性格特征。现实中的莎菲所不具有的因素都在叙述者的身上得以灌注。在对日记的书写与阅读的两端连接着两种形象的莎菲,将性格迥异的形象集于一体。
所以,《日记》中的叙述人与作为自我内面的莎菲相生相伴。一方面,莎菲的形象便不再仅仅是积极投身于爱情,宣告自由恋爱精神的样貌,还需要看到“莎菲”的反叛。重要的是这不仅是莎菲名义上的反叛,同时是经由叙述人与日记的机制铺就的反叛。这其中不仅包含主人公向外的抗争,同时包含更为复杂的主体裂变和互动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叙述人的视角观察在写作日记和作为叙述者时候的莎菲,则会发现《日记》中关于“自我”的表达并不限于完成关于想象爱情和两性地位的需求,而是尝试构建某种自足的人格。叙述人对莎菲的某种劝导不止于将她从凌吉士等人的身边拉开,同时体现出使其从爱情中抽身的意味。从“我到底又为了什么呢”到“一种分析不清的意义”,再到“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的一个卑劣灵魂”,叙述人对“爱情”的认识已经从对现实困境的思考转向更深层哲学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日记》中的“自我”既包含莎菲在爱情态度转变中自我意识的确立,也包含叙述人跳脱于爱情命题之外使思想逐步深邃的过程。后一种“自我”的生成意味着对思考着“卑劣灵魂”的自己的认识,也就是对思想者本身的认识。这体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有关思想革新进程中尊崇知识的氛围,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日记》所要回应的不仅是关于要求自由爱情之精神的问题,也为“出走”的“莎菲”们提供了某种可供借鉴的进取路径,也即是通过“求知”以应对种种社会和人生的难题。在这里可以说丁玲对女性的理解已经不仅是意识到两性地位的悬殊和指认施压的一方为伦理上的“男性”,而且是意识到女性所要面对的是更广阔的社会命题,以及回应问题所需要的思辨性和处理困扰的自主性。
叙述人不仅了解莎菲,也了解作为另一个言说对象的凌吉士,也就是“他人”。比如她恰恰是通过莎菲与凌吉士的交往活动才得以发现莎菲在爱情中所处的不平等的地位,以及发现了莎菲“痴迷”于爱情所反映出的懦弱性格。在这种“全知”叙事的意义上叙述人的言说中闪现出作者的参与感。比如在写到凌吉士是“随便的坐着”的,“有时是握着我的手”时,叙述言语里的莎菲“手便不会很安静的被握在那大手中,慢慢的会发烧。并且一当他站起身预备走时,不由的我的心便慌张了”。〔6〕在这里叙述人的交谈对象既不是莎菲,也不是她自己,而是对无名无声的读者。可以说《日记》中的日记是一种预设公开性和社会性的文本,其“私语”的特性在叙述人的层面向小说文本外部敞开。在这个意义上是“日记”装置模糊了小说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如同沃霍尔把叙述人归纳为“有距离的叙述人”和“参与的叙述人”,叙述者由于“叙述”行为将自身放置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在这里“叙述”意味着营造了某种平等、松弛的话语空间。〔7〕一方面,这符合20、30 年代人们推崇在日记体形式的氛围中对其凝练语言的文体形式革新意义的认同:“这种文字上的训练,实在是作一切文章的基础。因为日记体是最便于写作,最富于趣味的缘故,日记的价值常超乎一切文体之上。”〔8〕另一方面,《日记》体现出了“私语”写作的公共性。将人物心理活动的内转倾向敞开。正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人的存在使得莎菲的言说没有走向封闭,而是在小说内部的主人公阅读、小说外部的读者阅读等多重维度中与世界对话。应该说,莎菲与叙述人的共同存在表现了《日记》叙述人的形式价值,这为日记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总的来说,在《日记》的叙述层面,作为叙述者的日记主人莎菲让我们走进她用话语编织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诸如凌吉士等其他人物所不能了解的。叙述人了解莎菲的全部内心活动,有着比情节活动中的莎菲更加稳定的理性思维。她同情莎菲遭到的情感打击,通过观察发生在莎菲身上的事件充当着她的倾听者和引路人,以清醒理智的分析与她进行对话,以自己对日记叙述的话语权来施加影响。这种叙述上的张力使日记成为一扇门,在既联结又延宕着叙事的过程中将作为叙述对象的莎菲和日记写作者莎菲联系在一起构成统一体主人公“莎菲女士”。
二、矛盾统一体“莎菲女士”
丁玲在《日记》中构建了第一人称叙述人的形象,如前所述它的独特之处是经由第一人称的形式将叙述人与莎菲集于一体,使它们实为一体两面。其中一面是莎菲在巨大的现实遭遇中身心俱疲,形成了一个受到压抑又无法自拔的受困者形象“莎菲”。另一方面,叙述人又体现出冷静和思辩的现代知识者的理性、自我精神。这则使得“莎菲女士”这个形象由于内部巨大反差的性格特性而充满矛盾和张力。这在小说中同时体现为一种叙事与情节的博弈:叙述人对莎菲在情节中的劝勉反映在叙事层面则也体现为一种“压抑”。这使得小说《日记》在同一的语言组合中同时容纳了不同的故事走向。这两个形象的关系随着行文的过程也不断发生转变,成为小说在推动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隐含的叙事脉络。
首先,如前所说莎菲与叙述人之间存在由于日记体叙述形式所造成的先天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实际上作为两个独立形象的情节主人公莎菲和叙述者莎菲之间的亲密关系亦是情节发展的结果。小说中出现两个让莎菲逐渐走近叙述者的理由:一是因为莎菲在其他人物身上难以获得抚慰的现实无奈。在小说“情节层”中莎菲与旒芳、剑如、云霖等友人保持书信来往。但是,这些写作活动并不能排解她内心的压抑情绪,反而加剧她内心的紧张感,只有在与叙述人对话的时候这种焦虑感才能够被消除。第二则是由于叙述人对这种情节现实以及对置身其中的莎菲的叙事性塑造。
可以看到叙述人对莎菲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情形不仅是一种“发现”,更是一种言说和塑造。莎菲的惶恐,以及她与其他人的隔阂是叙述人言说的产物。在叙述中则会隐含叙述人的主观意识。如此一来,日记所反映的莎菲的苦闷一方面与叙述人所要表现自己对莎菲的感知不无关联,她对莎菲“懦弱”的描述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莎菲“心口不一”两面性的显露。在描述莎菲与其他人的隔阂中,叙述人还表现出与其他人对莎菲的“争夺”。莎菲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站在日记背后的叙述人进行干预所产生的结果。比如当苇弟察觉到莎菲不爱自己时仅仅感觉到了莎菲对自己的疏远,但叙述人对此却有不同的表达。一方面,它比苇弟了解更多有关莎菲的信息,它知道莎菲在心底默默说他懦弱的情形。另一方面,叙述人显然发现了与世界的隔阂是造成莎菲痛苦的一个根源,并意识到了它的危害性。有意味的是它将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内容同时曝露在日记中。在这里叙述人将她了解的信息面向莎菲、读者以及她自身开放,却没有向其他人物开放。这显然无益于莎菲在情节世界中消除与其他人的隔膜,反而使她更脱离人群。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对莎菲的帮助存有某种“私心”,或者说叙述人对莎菲的成长道路有着过于主观的规划。这一点也成为激化两个形象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说对此有两处集中表现:
第一,小说中有一段藏在作者的叙述背后的叙述人言语。作者将日记叙事大致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十二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时段是一月一日至一月十八日;第三时段为三月四日至三月二十八日。中间省略了对二月的书写。将小说整体看作主人公莎菲一段时期中的完整历程来说,省略的部分也是莎菲日记的一部分。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叙述日记在二月出现停滞的原因是莎菲患病不能继续写作。而站在叙述人的角度来看,生病并不是导致莎菲停笔的最主要原因。她的患病早已是生活中的常态,病情恶化也早有征兆,从一月最末几篇日记中能看出莎菲痛苦的主因并不在病痛。她像是有准备似地迎接着住院时光的到来:
一月十六号,收到来信得知蕴姊婚后生活的不幸让莎菲显得十分难过,此时的她并未向任何人倾诉心中的惆怅,而是这样说:“为躲避一切的熟人,深夜我才独自从冷寂寂的公园转来,我不知怎样的度过那些时间,我只想:多无意义啊!倒不如早死了干净……”。〔9〕莎菲的“无意义”一方面来源于蕴姊爱情婚姻生活不幸的影响,触动她对自己爱情未来走向的孤独怀想。另一方面,叙述人显然希望她受到触动,希望借爱情的问题促使她重新思考人际交往,思考自身与他人那个没有言说又始终横在面前的隔阂。
一月十七日莎菲便开始“发狂”。“明明看到那吐出来的是比酒还红的血。但我的心却像有什么别的东西主宰一样,似乎这酒便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样,我是不愿再去细想那些纠纠葛葛的事……。”〔10〕对于重病之人,过量酗酒的行为显得反常。此刻的她“足足有半年胃病而禁绝了的酒,今天又开始痛饮了”。〔11〕莎菲此时的痛苦并不是像前几天的日记所诉说的病痛之苦。对于莎菲而言半年之久的生病已成常态,此时她真正感到的痛苦是精神的痛苦。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身患重病的莎菲此时甚至不惜健康也要饮酒。又是什么造成了她的精神之苦在此时甚至超越了病痛的折磨。如果我们看清叙述人在其中的作用,那么莎菲的酗酒行为就并不显得突兀:一直到讲述一月十八日的内容,叙述人才显露出自己的面貌,以及她对莎菲这几天的发狂造成的影响:她正是要让莎菲由于某些事情的刺激而激化她的痛苦,此时的痛苦已经不是对病痛的呻吟,而是反思,是叙述人为莎菲设计下引导并其走向光明未来的现实准备。也正因此才会有住院前夕一月十八日当朋友们“慌乱”地为莎菲准备住院大小事宜时如她所说的“于是我反而笑了”。〔12〕
这造成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可以追随情节得知莎菲的二月是在医院养病,故此暂时离开了交际圈,停止了写作行动。但是如果我们穿过语言的迷宫站在叙述人的角度就会发现这是叙述人有意为之的安排,也是她希望故事里的莎菲能够在“朋友”的牢笼中脱逃以获得一丝喘息的尝试。日记显示:听闻蕴姊的死讯时,莎菲尚且没有脱离原来的社交圈子,她保持着自己波澜不惊的心态。但按照叙述人的说法,莎菲已经对面前的老朋友们集体产生了抗拒。她已经开始在内心构建起围墙,阻隔自己与朋友们之间的情感沟通。回到众人面前的莎菲有了很大改变。一个原因正是因蕴姊的不再在场而使她失去了除叙述人以外的倾诉对象,她的心事彻底封闭在她与叙述人之间的日记里。她与外界彻底无法和鸣,她的心事也彻底成为了叙述人的内心自白。两个“莎菲”由此具有了除人物作为写作者与写作对象关系之外更深层的亲缘。
第二,如上文中所说莎菲对凌吉士的爱情经历了郁热、爆发直至最终冷寂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莎菲对凌吉士有过一次“灵魂肮脏”的控诉。这是她对这段爱情态度大转变的关键转折点,而这恰恰发生在她突然向叙述人的回归时期。如以往的日记一样,莎菲的“发狂”被叙述人用“理性”的方式抚平了,取代“发狂”的却是被叙述人点燃的另一种狂热的反抗激情。
在做好了现实准备、具有了反抗激情以后如何呢,莎菲的确像许多“新女性”形象一样准备出走。在先前的日记中叙述人已经给了莎菲足够的力量让她将凌吉士“用力推开”。可是这样的出走果真符合叙述人的期待吗?并不如此。在推开了凌吉士后“我哭了”。此处的哭泣不是脱去羁绊的喜悦,在小说中此刻的莎菲终于得到自己爱慕对象的青睐——“是把我的心融醉到发迷的状态里”的,那“骑士般的风度”男子仍具有无法抵御的魅力,得到凌吉士爱的回应仍能带给莎菲欢愉。这种欢愉恰恰证明着叙述人此刻的失语,她改造莎菲的行动真正遇到了阻碍。可以看到,如果凌吉士此刻给莎菲提供足够的欢乐,那么她的“伤心”则同样会被抚平。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她用力推开了凌吉士,并非决意为之。叙述人虽然成功地使莎菲摆脱“他”的罗网,但她和莎菲却因此发生对峙:“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13〕带着这样的对峙情绪,叙述人的日记写作收尾了,莎菲将要南下去向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二者看起来同步,实际已蕴藏危机。也恰恰是这样的危机反映着莎菲与叙述人共有的叛逆精神——虽然基于她对凌吉士所象征的“金钱”“地位”“家庭”的不认同,她能够在行动上摆脱凌吉士的牵绊,获得一定自由,但真正表明她要求自由的地方实际在于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被另一种驱力也即叙述人把控。后者怂恿着她极力去摆脱曾认为可靠的东西。小说在这里呈现出莎菲更为决绝的反抗:她意识到来自叙述人的驱力作为另一种形式的束缚,并对此采取抵抗。而对于叙述人来说,她对莎菲最终仍对凌吉士怀有执迷则表现出坚决的抗议。作为已经密不可拆、互为骨肉的叙述人和莎菲而言,她们通过对对方的质疑呈现着自我的特征。两者无法真正分裂,只能在矛盾纠葛中继续生存。所以她们共同说出了“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这样的话。这无疑表明以莎菲为代表的女性群体身上内在的统一和分裂并存。人物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类独特的形象。
最后,作品结尾处一句“莎菲,我真的可怜你”一方面反映着女性学会运用理性思维之后面对某种原始爱欲时的无奈,在新的认知中这种爱欲由于束缚在某种僵化的伦理道德价值中而带有“落后”的意味。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爱欲冲动拉住了莎菲匆忙奔向由现代理性意识构成的那未知世界的脚步。
三、结语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塑造了叙述人莎菲与被叙述人莎菲两个形象,她们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了“莎菲女士”。尤其是小说对叙述人的塑造不着痕迹。它潜藏在日记叙述背后,洞悉由日记构成的故事情节,既全知全解情节走向又参与其中与作为叙述对象的莎菲发生矛盾纠葛,使“莎菲”这个符号呈现复杂、奇异的效果。这体现出现代女性内在持存着的某种现代理性思维与原始欲望的激烈冲突。这个人物展现了“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女性现代理性自我意识的萌生,以及新的历史背景下女性对固有道德价值的叛逆。而这其中也反映着用现代理性的方式去解释一些心理层面模糊情感动态时的困难。小说在这里反映着已经出离于“旧途”又没有寻到确切出路时女性内心的徘徊。也正是这种在面临新道路选择时的犹疑使我们得以看到时代激变中某种真实的个体心境和对“启蒙”观念的复杂接受过程。
——重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解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