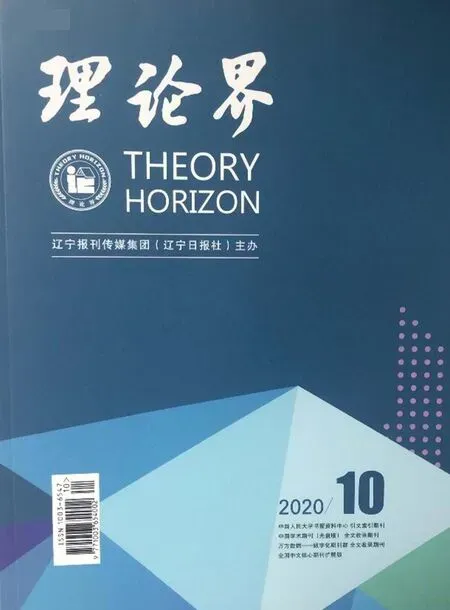从焦虑到平衡
——心理学视阈中莫里斯·桑达克绘本的幻想性叙事
彭应翃
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1928-2012)是美国儿童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绘本作家,他曾于1964 年凭借《野兽国》(又译《野兽出没的地方》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1963)获得美国绘本大奖凯 迪 克奖(The Caldecott Medal) 金奖,1970年更获得世界儿童文学领域最高荣誉国际安徒生奖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插画奖。与许多将爱、希望、欢乐作为主旋律的经典绘本相比较,桑达克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总是聚焦于儿童的负面情绪与沮丧经历,如愤怒、不安、嫉妒、困惑、出走、争吵等。被誉为桑达克绘本三部曲(以下简称三部曲)的《野兽国》《午夜厨房》(In the Night Kitchen,1971)《在那遥远的地方》(Outside over there,1981)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而这一特点显然与儿童文学对明朗、愉悦、积极等审美特征的强调背道而驰。那么,以儿童的负面心理为主要题材的桑达克绘本为何可以收获读者的认同与评论界的肯定、成为业界经典?其叙事的内容、方式、蕴涵等的特殊之处何在?若将桑达克绘本的幻想性叙事置于儿童心理学范畴之内进行考量,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这一问题某些层面的答案。
一、焦虑的发生:成人的缺席与儿童的情感失衡
许多研究者强调桑达克对心理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的许多绘本是对儿童心理的形象化诠释。这些绘本并不将儿童形象置于现实化情境、通过外部遭遇书写其成长路径,而更注重通过幻想性叙事展示儿童独特的心理状态及其变化过程。所以,桑达克绘本的重要主题都和儿童的某些心理症候有关,只是不同的论者对这些具有心理学蕴含的关键词的体认不尽相同。
例如,Richard M.Gottlieb 便认为,“愤怒”(rage)是桑达克绘本三部曲的重要主题,因为三部曲“确切地说,每本都以孩子的愤怒开头”并且“愤怒在孩子身上引发了诗意的效果,促使他们的意识进入梦境、幻想和其他艺术创造当中”〔1〕从而完成了绘本的叙事框架。这一观点固然合理,但是笔者认为,三部曲的核心关键词与其概括为“愤怒”,不如归纳为“焦虑”更为贴切。诚然,三部曲均表现了不同年龄、性别的主人公从怒气冲天到安静平和的情绪流程,但“愤怒”仅是其意识层面的心绪的外在显现,若追溯这显在情绪的缘由,其实都可归咎于儿童无意识层面深刻的焦虑感。
表面看来,受罚的麦克斯(Max)、被噪音吵醒的米奇(Mickey)、妹妹被绑架(想象中)的爱达(Ida),都以滔天怒火作为遭遇挫折后的情绪表达,但细加辨析,我们会发现,这些强烈而负面的情绪实际上都建立在儿童面对现实时深刻的无力感之上。这种无力感主要来源于绘本对儿童与成人关系模式的建构。麦克斯难以令母亲理解他孩子气的胡闹、孤枕难眠的米奇无法唤起父母更多的关注、被交托重任的爱达不能从母亲那里获得行动甚至情感的支持。不难发现,这些儿童共有的问题情境是其生命历程中成人的缺席。
此处的“缺席”并非物理意义上令儿童处于留守状态,而是指在精神层面,成人未能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首先,成人的缺席表现在图画层是其形象的缺失。例如,《野兽国》和《午夜厨房》中都不曾直接呈现父母的形象,他们尽管在叙述层面具有存在功能,但这种功能仅仅表现为无视儿童的诉求,所以他们的形象在画面中被刻意隐去从而凸显儿童的主体性地位。《在那遥远的地方》里虽然存在一个具象化的妈妈,但是她的有限出场均为侧影或背影、她与小妹妹同样色系的服装、她在悲欢场合中淡漠的神情、她始终垂在脚畔的帽子、远航的父亲竟然叮嘱爱达“一定要照看妹妹和妈妈(must watch the baby and her Mama)”〔2〕而非按照常理将照顾儿童的任务交托作为成人的妈妈,这些都暗示了这个妈妈的孩子气,暗示了她行动力的欠缺和成人性的不足。她在图画层的在场实际指向的是她真正意义的缺席。其次,成人的缺席表现在文字层则是其不能为儿童提供包含援助功能的有效话语。忧郁而沉默的妈妈对爱达的遭遇不闻不问,不论爸爸离家远行还是收到爸爸来信她都一言不发,这些构成了爱达心中几乎难以承受之重;面对麦克斯的胡闹,严厉的妈妈仅用武断的惩罚替代共情的理解和言语上的安抚,而她最终提供的“热 腾 腾 的(Hot) ”〔3〕而 非 温 热 的(Warm)晚饭也似乎无声地暗示情感的隔阂与冲突仍将延续;米奇被吵醒后虽然连声呼唤,爸爸妈妈却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因为他们“睡得很熟(Sleeping Tight)”。〔4〕
成人的缺席为儿童营造了一个“自我中心”式的情境,那么这一情境对儿童来说是否意味着主体性最大限度的发挥?在绘本中,这种情境所引起的首要心理反应显然并非以“自我中心”为起点的自我发展。成人的缺席更多指向的是儿童情感的落空。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前语言时期,婴儿的世界是没有客体的“自我中心”的世界,随着认识的发展,年幼的儿童逐渐建立了客体的观念,从“自我中心”主义中脱离出来,其认知系统逐渐向交往模式过渡。儿童开始认识到,“人们的行动不同于事物,人们是按照同儿童自己的活动图式具有一定关系的图式来进行活动的。从此儿童将迟早建立一种因果联系,这种因果的来源乃是别人,因为别人引起了儿童的愉快、舒适、镇静、安全等等”。〔5〕在儿童脱离“自我中心”的过程中,他逐渐“把别人作为情感的对象”,认识到不仅自己从属于“一个永久客体的世界”,而且“他的情感也要从属于那些定位的永久客体和来自别人的外部因果关系”。〔6〕也就是说,与他人建立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获得舒适感是儿童从婴幼时期开始便发展起来的情感与认知模式,这种认知为儿童建构了内心的平衡。此外,随着儿童能力与智力的发展,交往模式中的舒适感还来自于其语言与思维的特点。皮亚杰指出,儿童的语言和思维也具有“自我中心”的性质,由于身边的成人总是能够尽力去理解儿童的话语和情绪,所以在与成人的交流中,“儿童并不烦心使自己表达清楚,甚至并不烦心去与人交谈”,因为他们“总是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人们能够深知他的思想”,〔7〕这种想法令他们感到安心。可是,在桑达克绘本中,成人的缺席却打破了这种预先的平衡。当儿童遭遇困境、亟需通过成人这一“情感的对象”使其保持心理上的愉悦、安宁时,他们的交往图式中却缺失了成人这关键的一环。对麦克斯的愤怒熟视无睹的妈妈,对米奇的暴躁置若罔闻的爸爸妈妈,等待爱达施以援手的爸爸妈妈,他们的主体性缺席迫使儿童不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寻求指导、同情、安慰等情感的支持。情感的落空与失衡便使儿童面对现实困境产生无能为力、孤立无援的强烈焦虑感。当内心的焦虑难以及时化解时,儿童便将其外化为愤怒并加以一定程度的发泄。所以,儿童的焦虑感是三部曲叙事框架的核心起点,三部曲实际上探讨的其实都是儿童如何克服这种心理困境走向成长的问题。
从文本的层面来看,成人在儿童世界的缺席虽然并非绘本常见的题材,但是就现实层面而言,成人的缺席所导致的情感落空却是儿童在成长历程中或早或迟、或偶然或频繁必将遭逢的心理情境。当风雨来袭,熟悉的羽翼不能及时出现,舒适的安全区域不再触手可及时,如何凭借自身的勇气迎接风浪,这是儿童必会面临的难题;困窘、委屈、不安、暴躁,也是儿童在此境遇中必然产生的情绪。通过三部曲,桑达克绘出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儿童经验世界的心理学图景。同时,如何缓解成长的必然焦虑、走出心理困境便成为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关注的焦点。
二、焦虑的缓解:幻想与游戏
在成人缺席的情境中,儿童如何孤立无援地凭一己之力克服愤懑、苦恼、挫败感,重建内心的平衡从而达到精神上的成长?三部曲中的所有儿童都选择了相同的方式化解焦虑,这也是儿童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游戏”。同时,这些儿童也用相似的、与他们的思维特点最契合的载体呈现其独特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幻想”。这两种方式,均符合皮亚杰对儿童认知发展及认知特征的总结:“一定年龄的儿童对于某些问题,并不理解。这种问题就激起了儿童的幻想,所以就把这些问题当作一种游戏。”〔8〕
首先,在三部曲中,叙述者虽未言明,但读者不难猜到,情节的主线都建立在儿童的幻想之上。儿童具有不同于成人的思维模式与心理机制(如万物有灵、主客体不分等),“对他们来说,真实与虚幻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清晰的界限,他可以从这个世界跳到那个世界,好像从一个窗户前跑到另一个窗户前一样”,〔9〕所以将现实投射于幻想是儿童极其自然的心理选择。漂洋过海到达野兽国尽情胡闹,这显然是被罚“禁闭禁食”的麦克斯的最放肆的白日梦;跌进午夜厨房给制作糕点的厨师制造混乱,这是米奇在充满牛奶和面粉香气的、不安分的睡梦中的想象;闯进妖精洞用号角赶走小妖精解救被绑架的妹妹,这只是爱达编织的奇妙故事。在这些绘本中,当儿童面临真实可感的困境(被父母惩罚、被噪声吵醒、被交托重任)而求助无门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为其自身制造了一个虚拟场所,将现实问题移植其中,在想象中寻求应对方案。幻想的作用主要有二:其一,由于儿童的活动范围总是被限制在狭小的物理范畴之内(如一间卧室、一座院落、一栋房子等),其心理感受与情感能量便往往因此受到局限,而幻想则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令充沛的情绪找到宣泄的出口。所以,三部曲中幻想的发生地均与儿童的现实空间(狭小的卧室、封闭的花园)形成鲜明对照。大海中的野兽国、银河下的魔幻厨房、溪流环绕的妖精洞,这些被刻意强调的宽阔的、没有边界的时空背景正为儿童提供了舒张情绪、缓解压力的广阔通道。其二,由于儿童的行为总是因环境的单调以及经验和能力的单薄而缺乏实践意义上的自主性,幻想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令其可以无所顾忌地检验自身行动的能力,这种检验亦有利于儿童完成自我满足和自我肯定。
其次,儿童在幻想中走出困境与内心焦虑的方式都和游戏有关。麦克斯率领野兽尽情胡闹;米奇过家家式的玩耍;爱达对小妖精的追逐、挑战,这些都可视为儿童游戏的表现形式。游戏是儿童最为熟悉、最感亲切的活动,对游戏的亲近感可以有效抵消形单影只的孤独。与成人相较,各种游戏也是儿童最擅长的活动,儿童在游戏中往往能够游刃有余或者坚持不懈地处理一切麻烦,对游戏的痴迷更有助于缓解面对未知的恐惧、增强逆境中迎难而上的勇气。三部曲中的游戏虽然仅仅发生在想象中,却由于其共有的虚拟性、娱乐性、专属性而具备了儿童游戏的本质属性。所以,三部曲共同的叙事脉络,都是儿童以幻想为载体、以游戏为手段,对抗他在困境面前产生的暴躁、焦灼。
这种以幻想为载体的儿童游戏,亦可置于皮亚杰关于儿童游戏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解读。皮亚杰从儿童认知发展角度出发将儿童游戏分为三大类:练习性游戏、象征性游戏、带有规则的游戏。三部曲中的游戏形式与象征性游戏最为接近。在皮亚杰看来,儿童需要一种他能够自行掌控的工具进行自我表达,象征性游戏正是一种合适的工具。象征性游戏的主要表征是模仿,它通过对外界原型的模仿达到令儿童接受并适应外部现实的目的。在三部曲中,不论是麦克斯惩罚野兽,还是米奇在厨房胡闹,抑或是爱达解救妹妹,都可以认为是对现实的模仿行为。麦克斯模仿惩罚他的母亲,米奇模仿搅乱他睡眠的未知事物,爱达模仿她被期待成为的守护者。其实,儿童对其模仿的行为主体并不完全理解,因为这些行为主体执行的显然是成人的规约。循规蹈矩、奔忙劳碌、保卫家园等品质与行为,和儿童的天性及能力差距太远,都超出了他们能够胜任的范围。但是,若把这些行为以象征的方式进行重建,其所受到的接受阻力就会大大减弱。所以,皮亚杰认为通过象征性游戏,儿童可以接受他在现实中不能或没有接受的东西,也能用自己的方式对现实的困惑作出解释。因此,对儿童来说,“象征性游戏可以帮助解决情感上的冲突,也可以帮助对未满足的要求得到补偿,角色的颠倒和自我的解放与扩张等等”。〔10〕所以,在遭逢困境、成人缺席、难以获得情感慰藉而焦虑不安的情形下,三部曲中的象征性游戏为儿童提供了缓解心理压力的合适方式。
那么,象征性游戏是如何通过心理学意义上的运作帮助儿童缓解焦虑的呢?首先,游戏与梦具有相似的结构,正如皮亚杰所言,“游戏的象征主义和梦的象征主义相类似”。〔11〕三部曲中的游戏均在儿童的幻想中进行,而这些幻想均可被认为是儿童的梦。午夜时分厨房里的胡闹是米奇切实的梦,制服野兽和解救妹妹俨然是麦克斯和爱达的白日梦。“想象游戏,梦境和白日梦所共有的象征性思维”〔12〕令我们可以从释梦的角度解读儿童的游戏。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儿童的梦无疑地证明了由于白天的愿望未能得到满足,该愿望便促成了梦的产生”,〔13〕也就是说象征性游戏亦是儿童难以实现的愿望的变形的呈现。那么,在三部曲中,儿童的愿望是什么?惩罚野兽、大闹厨房、保护妹妹,都是儿童从现实的情境出发想要完成但受限于时空与个体经验难以完成的任务,但这些行动只能说属于儿童愿望的具体形式,却并非其精神内核。若要探索其内核,我们可以借用加斯东·巴什拉的观点并仍用释梦的方式解读幻想与游戏。“当梦想把梦想者带往另一个世界时,就使梦想者成为相异于他本身的另一个人。然而,这另一个人仍然是他自己,他自己的化身。”〔14〕同样,在三部曲的幻想世界中,对主人公而言,幻境中那个解决了难题的孩子虽以其自我的形象呈现,但实际上并非现实中孤独、无助、焦虑的他自己,而是“相异于他本身的另一个人”,是他期望成为的自己,是他人格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幻想中的主人公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任务(麦克斯打败野兽、米奇逃脱厨师的追赶、爱达解救妹妹)乃是因为他们被幻想主体赋予了其在现实中并不具备但是倾心向往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强悍、灵巧、坚韧),正好弥补了儿童因生理与心理的弱势(瘦小、笨拙、柔弱)而导致的行动力不足。也就是说,建构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这便是儿童的梦境、幻想与游戏的精神实质。这个理想形象的创设,其实也是幻想与游戏主体同自我的对话,其目的在于明确自身的缺憾与期许,为解决现实困境寻求合理的应对策略。因此,在三部曲中,一方面,通过幻想与游戏,儿童找到了缓解焦虑的合适路径;另一方面,通过理想人格的投射,儿童完成了自我审视,踏上了自我发现与发展的成长之旅。
三、平衡的完成:同化与顺化
幻想中的游戏为儿童提供了缓解焦虑的合理通道,那么儿童选择此方式解决现实难题、舒缓不良情绪的过程为何能够顺利完成?儿童是如何通过此种方式实现自我发展的?这些问题背后的内在心理机制借用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关于“同化”与“顺化”的概念便可找到答案。
在皮亚杰看来,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个体不断适应周围的物理与社会环境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文学文本中被描述为成长)“实际上是一种不断持续的建立平衡的过程,而这种平衡存在于两种伴随而行的机制之间:同化和顺化”。〔15〕所谓“同化”,指个体感受到物理与社会环境的刺激,并把这种刺激置于头脑中已有的思维框架里,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所谓“顺化”,指当已有的思维框架不能吸收外部刺激时,个体便修改或重建已有的框架,以适应这种刺激。同化与顺化相伴发生不断建立新的平衡,“当思维成功地将现实同化为自身的框架,同时这些框架又被现实呈现的新环境顺化时,思维就适应了这种现实”,〔16〕从而完成了认知的发展。不过,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在儿童心智发展的早期阶段,主客体不分是其显著特征。在主体与客体界限不甚清晰的阶段,如何才能成功地将作为客体的现实同化为自身(即主体)的框架?皮亚杰指出,“同化最纯粹的形式实际上就是游戏”。〔17〕作为儿童期最具特点的活动之一,游戏之所以被儿童看得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其对儿童发展具有心理学的意义。尤其当涉及符号与象征时,“游戏成为一种自现实到活动本身的同化,它为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原料,并将现实按照自我的多重需要进行转化”。〔18〕
从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出发观照桑达克绘本,可以发现三部曲为该理论提供了极相称的文学阐释样本。
三部曲的题材均与儿童适应环境、建立内心平衡的过程有关。成人的缺席将儿童推出了他熟悉的舒适区域,不得不面对新的物理与社会环境,被惩罚、被吵醒、被交托重任都可视为环境对儿童造成的刺激。对来自未知区域的新的刺激,儿童首要的反应是将其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从而寻求精神的平衡。这种同化的方式,就是皮亚杰所说的同化最纯粹的形式——游戏。这一共通的心理选择实际上亦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将陌生的刺激纳入其熟悉的思维框架。对儿童而言,其头脑中已有的最为熟悉的框架非游戏莫属。因此,三部曲中的游戏(即使发生在幻想中)实际上都是儿童以固有的思维方式对突然降临的现实困境作出的反应,其具体表现就是游戏的内容均与儿童受到的现实刺激密切相关。麦克斯因为胡闹受罚,他幻想中的游戏便是在野兽国尽情胡闹;米奇被厨房的噪音吵醒,他便神游午夜厨房制造混乱;爱达被寄望于保护家人,她便在想象中遭遇了专偷婴儿的小妖精。当儿童因环境的刺激感受到精神与情绪的焦灼,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是用游戏话语将这些压力进行重新表述。由于用以表述的话语类型存在于其最熟悉且热爱的领域之内,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焦虑。焦虑的缓解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是儿童从现实的情绪波动中挣脱出来,在想象的游戏里获得舒适感。成为野兽国国王的麦克斯、面团里的米奇、吹着号角的爱达,他们在文本的图画层中都用满足的表情诠释了这种用幻想性游戏同化外在刺激之后获得的舒适感。
游戏中的舒适感虽然是同化的结果,但与建立儿童真正的心理平衡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绘本中,儿童虽然从想象的游戏中获得了抗击焦虑的舒适感,但是这种感觉却并不持久,它很快便被不安所替代。从世界的另一头飘来的饭菜香味使麦克斯觉得孤单;钻进面团的米奇产生被厨师们塞进烤箱的恐惧;在想象中强悍的爱达却因找不到妖精洞口而慌张。当儿童用游戏思维将成长的困境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时发现,若要彻底消解焦虑,仅用头脑中已有的思维图式改造环境的刺激显然是不够的,若不能对已有的框架进行改写(即顺化),个体与环境便无法达成最终的和解。顺化的过程表现在文本中,是孩子们虽然都选择了游戏的形式以抗拒焦虑感、表达对现实压力的抗议,但是最终,他们在游戏里仍然认可了现实的合理性并对自身在游戏中的行为选择进行了调整。没吃晚饭便被送上床的麦克斯在野兽国胡闹一通之后如法炮制地“不准野兽吃东西,要它们去睡觉”;〔19〕“米奇在午夜厨房里大叫:‘喔喔喔’”,〔20〕这是游戏过后舒适心境的表达,也是对吵醒他的噪音的愉快回应。爱达最初只是心无旁骛地吹着神奇的号角以缓解父亲远行、母亲忧伤、妹妹哭闹所带给她的情感冲击,而她在想象中用激越的号角声驱赶小妖精、解救被绑架的妹妹的行动实际上体现了坦然应对现实变故的勇气。这些儿童一方面用游戏同化现实,将其遭逢的困境与陌生情绪纳入可理解与掌控的范畴之内进行审视;另一方面,他们在幻想的游戏中意识到,即使采用此种手段,现实与其固有的认知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遭遇的困境不可能改变其本质属性,只有调节自我的思维图式使其顺化于现实,才能解决问题、化解焦虑。
同化与顺化的相伴发生的结果,在文本中的体现便是儿童最终走出幻境,回归现实,与令其产生焦虑的人、事、物达成和解。麦克斯准备享用热腾腾的晚餐、米奇安然入睡、爱达平静地读着父亲的来信,这些岁月静好的场景与故事开篇的鸡飞狗跳形成鲜明对比,均是儿童经过同化与顺化的心理流程,接受现实、适应现实,最终重建内心平衡的体现。正是通过幻境中从被动接受现实到主动适应现实的过程,儿童完成了心理意义上的成长。
四、结语
桑达克绘本的经典性魅力固然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共同建构而成,但文本的幻想性叙事与现实儿童心理症候的呼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层面。首先,幻想性叙事聚焦于儿童的负面情绪,指出成人指导的缺失与儿童的焦虑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一显著的文本焦距来自桑达克对普遍存在的儿童心理问题独具慧眼的叙事视野。其次,用幻想与游戏处理不良情绪是绘本中的儿童形象共同的行为选择,这种极其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在幻想与现实间无缝穿梭的叙述方式是桑达克独具特色的叙事策略。再次,幻想性游戏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儿童如何通过同化与顺化适应环境,自我发展的心路历程,这是熟习心理学的作者独树一帜的叙事架构。总之,桑达克绘本以形象化的方式描绘了儿童遭遇现实困境时由焦虑到平衡的抽象心理过程,其叙事结构与儿童心理结构之间存在微妙的暗合之处。这种契合,催生了文本强有力的召唤结构,即使其题材与儿童文学的书写共识并不完全相容,却仍可唤起读者普遍而深刻的共鸣。
——《皮亚杰文集》不可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