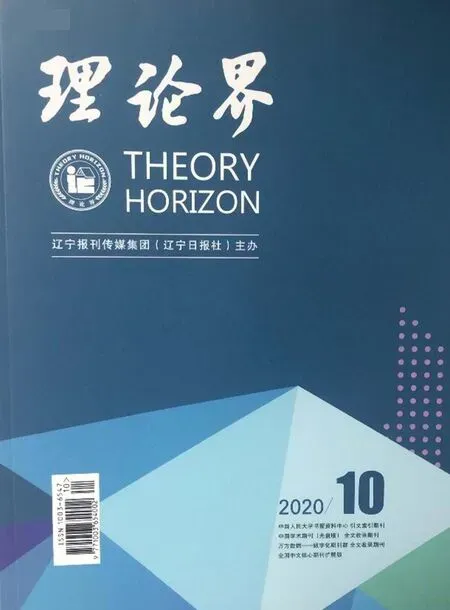话语与制作:海德格尔论亚里士多德灵魂问题的双重维度
赵 奇
海德格尔在1931年夏季学期的弗赖堡大学讲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Θ1-3:论潜能的本质和现实》) 中从潜能(Dunamis)问题着手,展开了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论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被述说:“存在一方面被述说为何者或类似于何者或多少,而另一方面则根据潜能和现实。”〔1〕就后者而言,单纯就其本身讨论“潜能—现实”概念不足以真正理解其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潜能的区分可以通过遵循存在范围的区分被完成”,〔2〕而这种存在范围的划分以是否具有话语(Logos)为标准。但话语作为存在范围的划分标准,理应在存在者的范围之内进行讨论才具有意义,而这就必然行进到以是否具有灵魂(Psuche)作为对存在者进行区分的标准之中。因此,澄清亚里士多德的灵魂问题,不仅为存在范围的话语问题提供了本质基础,也为阐明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概念提供了必要前提。
一、灵魂与话语的本质关联
亚里士多德将本原(Arche)分为两类,即有、无灵魂之物的本原。〔3〕类似地,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也将被赋予灵魂的活物与无灵魂者区分开。〔4〕具体而言,被赋予灵魂者即活物,而无灵魂者则是非活物。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在《形而上学》9.2 这一节详细讨论灵魂问题,就是因为它对“潜能—现实”概念至关重要。
海德格尔认为,被赋予灵魂者与无灵魂者的区分并不是任意的,灵魂作为区分标准,对于被区分的存在者而言是本质性的。如果这种区分处于传统二分法的视域下,那么必定从根本上误解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概念,而导致无终止的尴尬境地。〔5〕诚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灵魂是活物的原因和本原。”〔6〕灵魂与身体因此就处于互为奠基的关系之中:一方面灵魂作为身体的形式,另一方面身体作为灵魂的载体。亚里士多德断言:“灵魂是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形体之第一现实。”〔7〕因此,身体先在地被赋予灵魂,没有灵魂的身体就根本不是身体,灵魂使身体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示自身:“亚里士多德将‘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形体定义为有器官的自然身体,他的意思是器官能如它们应所是的那样起作用。”〔8〕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断言,灵魂应作为某种话语和形式而存在。〔9〕在我们澄清了有、无灵魂之物的本质区分之后,问题在于:存在范围内的有、无话语者的区分是否完全重合于有、无灵魂者的区分呢?若不是,两种类型的区分处于何种关系之中?澄清灵魂与话语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方面灵魂可以为话语提供本质性的存在者基础,另一方面话语可以对被赋予灵魂者的内在含混性进行澄清。所以,海德格尔将阐释话语本质作为理解灵魂与话语的关系首先要处理的问题。
在传统哲学中,话语被理解为“理性”或“判断”。但海德格尔认为,“话语”一词来自于言说(Legein),即“获得(Lesen)、收获(Zusammenlesen)、聚集(Sammeln),将一者加到他者之上,并因此将一者置于关乎他者的关系之中”。〔10〕言说的本质是聚集着的敞开(Aletheia),而直接来源于其中的话语必然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相比于言说,话语具有“规定着持立于自身的关系”(regelt die Beziehung der sich Verhaltenden)这种专属特征,在这种“持立于自身”的聚集性之敞开的状态之下,话语就“主题化”地呈现为一种“关系”。海德格尔否认这种关系可被理解为抽象的概念,而应是关系性意义上的次序和联系。〔11〕这种关系经过个别化,成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使某物呈现为自身之所是的方式。
澄清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语概念之后,海德格尔将其作为区分存在范围的标准,即可以将存在范围区分为元话语(Meta Logou)和无话语(Alogos)。海德格尔对元话语的“元”(Meta)做了深入解释:“元”不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单纯地伴随某物,而应该代表对话语的最本质理解,也即始终使话语处于聚集着的敞开状态之下,与话语具有密切关系。〔12〕那么,所谓元话语者,即始终被话语所引导;而所谓无话语者,则从未被话语所引导。进而,在存在范围内的区分标准是话语,而话语本质上就是最宽广意义上的“熟悉”(Kundschaft),熟悉本质上就是一种此在始终寓于世界之中,并处于对周围物已知的存在论状态,即一种“引起注意”的可能性。因此,元话语是一种“熟悉”,而“无话语”则被置于“不熟悉”(Kundschaftslos) 的视域之下。类似地,在存在者范围内以话语为区分标准,就可以分为元话语的存在者和无话语的存在者。〔13〕
跟随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者及存在范围进行阐释的路径,我们发现存在者可以被区分为被赋予灵魂的存在者和无灵魂的存在者,在存在范围以话语为区分标准可以分为元话语和无话语,继而又可进入到存在者范围,将存在者划分为元话语者和无话语者。海德格尔断言,亚里士多德以是否具有生命为区分标准并不能从根本上澄清被赋予灵魂者的内在层次,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生命”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也即人与非人的活物之间具有本质差异,决不可一概而论。〔14〕海德格尔首先排除了感知(Aisthesis)可作为区分人与非人的活物之可能性,因为人与动物都具有感知,即以感知的方式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当然这里所说的“感知”并非一种心理活动,而是在世存在的方式。斯拉凯(Thomas J.Slakey)对此也进行了严格区分:“感知仅仅是发生在感觉器官上的运动,而非在器官运动之外的某种心理进程。”〔15〕所以,感知功能本身就具有“作为”的方式。〔16〕但人对周围物感知的方式从根本上不同于动物对周围物感知的方式,而之所以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话语。所以,海德格尔的看法非常明显,即话语,而非感知,才能作为被赋予灵魂者的区分标准。但目前只是从话语一词的概念上说明了它作为一种区分标准而存在,海德格尔进一步解释话语何以作为被赋予灵魂者内部的区分标准:首先,话语作为一种主题化的呈现,那么就必然是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即“标明了人类的自我感觉”。〔17〕也就是说,拥有元话语的被赋予灵魂者持立于自身而进行实践活动,其他活物却不可如此。其次,由于话语作为广义上的熟悉,因此,人能在对周围物熟悉的存在方式下,对周围物进行统观(Umsicht)且定向(Ausrichten),从而“认识到其周围物”。〔18〕
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我们的结论是:首先,被赋予灵魂者未必是元话语者,因为话语只能是此在的本质特征,从通俗意义上来说,即人的本真呈现方式,而除人之外的其他活物虽然具有灵魂,但却没有话语。其次,无灵魂者也不等同于无话语者,两者的范围不同:无灵魂者包括失去灵魂之物,例如死尸,也包括根本就不拥有灵魂之物,如石头;而无话语者包含除人之外的其他一切存在者,不仅包含无灵魂者,也包含除人之外的被赋予灵魂者。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就非常清晰地阐释了灵魂与话语的本质关系。
二、灵魂视域下的元话语潜能:制作性知识
正如海德格尔在弗赖堡大学讲座第一章所论述的那样,不仅存在者可以被分为被赋予灵魂者和无灵魂者,而且被赋予灵魂者本身可以被分为拥有元话语的被赋予灵魂者和无话语的被赋予灵魂者。那么,作为在世存在的此在(Dasein),即对于通俗意义上的人而言,必定不同于其他一切活物,因为人拥有本真性(Eigentlichkeit)的话语,这恰恰是其他活物所缺少的。这种元话语的被赋予灵魂者,即人,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所具备的是一种“拥有”的能力,这种“拥有”具备熟悉性统观和定向的双重功能。这正是海德格尔在弗赖堡大学讲座第一章所说的“ 关于运动的潜能”(Dunamis Kata Kinesis),即本真的潜能,它只能为元话语者所拥有,因此,本质上就作为一种元话语潜能(Dunamis Meta Logou)而存在。而这种元话语潜能作为一种能力,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制作”(Poiesis)概念,因为制作必然是话语最基本的结构特征。因此,人的灵魂与制作潜能互相依赖、不可分割:一方面,作为拥有元话语的灵魂,必然具有制作这一性质,否则灵魂将无潜能,而无潜能的灵魂则不是拥有元话语的灵魂;另一方面,制作必然归属于拥有元话语的灵魂,因为其他的被赋予灵魂者决不能进行制作,而只能是出于其自然本性、结合某种目的,而造成某种“后果”。相反,只有拥有元话语的被赋予灵魂者才能进行制作。这是因为两者虽然都具有潜能,但所具有的潜能却存在根本差异。因为人所具有的潜能是在对周围物熟悉的基础上进行统观和定向,始终朝向其终点而存在;而其他被赋予灵魂者的潜能却仅仅是无定的(Apeiron),即作为一种无规定的力量而存在。因为海德格尔将人的潜能理解为就能力(Fähigkeiten)而言的潜能,而其他被赋予灵魂者的潜能只是就盲目力量(Kraft)而言的潜能。〔19〕
海德格尔接下来从正面论述制作的本质含义:“制作”属于此在的在世存在,使周围物始终向自身敞开,故而此在始终保持对周围物的熟悉,在这种熟悉状态之下,通过制作使不上手之物变得上手。然而,虽然制作必须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之上,但却不能持留于熟悉之中,因为熟悉仅仅是对周围世界的一种统观,使周围物处于敞开的已知状态之下,但其本身并非制作,而只是使它们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示自身。所以,熟悉性并非无中生有地制作某物,而是使某物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现自身。〔20〕因此,制作应该是“拥有元话语”意义上的“拥有”,即不仅可以对周围物进行统观,还可以进而在统观的基础上对周围物进行定向,从而进行制作。
在从制作与熟悉关系的视角对从属于灵魂的制作潜能进行初步阐明之后,海德格尔继而认为,若制作并非主体“无中生有”地制作出客体,而是在熟悉性的统观之下对周围物处于先在的审视状况之中,那么制作就不仅仅包含意向于制作出之物,也必然将其相反者(Enantia)寓于其中,而有灵魂之物所拥有的其他潜能只能是同名异义的。〔21〕正如所举的锯的例子,虽然在熟悉性的统观之下,拥有元话语的被赋予灵魂者选择了金属来制作锯,但必然始终已经将不合适的原材料寓于制作的考虑之中,否则就无所谓统观及定向。亚里士多德举例证明相反者对于灵魂制作的必要性:“有益于健康之物仅产生健康,能加热之物仅产生热,且能冷却之物仅产生冷。但有知识的人却能将两者都制作出来。”〔22〕海德格尔据此分析道,虽然如冷与热、健康与疾病互相都可以转向相反者,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与具有知识(医术)的人并无不同,因为都能造成相反者,但两种造成相反者的方式具有根源上的区别:诸如前者那种相反者,凭其自身并没有转化为相反者的潜能,而必须靠他物的推动作用,并且一旦转化为相反者,自身就不再存在;而对于后者,由于拥有医术的人作为以元话语方式存在着的被赋予灵魂者,那么就可以在对周围物先在的熟悉状态之下,进行对周围物的统观和定向,那么就拥有使冷与热、健康与疾病相互转化的潜能。而且,人自身并非如前者所说的那种相反者,而是在自身的持立中将相反者包含于自身之中,最终在熟悉周围物的基础上进行制作,从而医者在预先熟悉健康与疾病这对相反者的前提下制作出健康状态。〔23〕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制作必然从属于拥有元话语的被赋予灵魂者,即人。而其他的无话语者,无论是被赋予灵魂之物抑或是无灵魂之物,都不可能进行制作。并且正因为如此,人在制作中始终在对周围物熟悉的基础上将相反者包含于其自身之中。布罗甘(Walter A.Brogan)将其视为一种存在的双重性。〔24〕
虽然我们已经阐释了人必须在熟悉的状态下将相反者寓于自身之中,并进而定向,从而制作出所意向获得之物。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一对相反者之中何者才是真正被意向的呢?我们如何在熟悉的基础上进行定向并制作呢?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所谓制作性知识,就是“为了制作所计划之物,是作品(Ergon)”。〔25〕海德格尔之所以将作品称之为在计划之中被制作之物,是因为作品并非偶然地被拥有元话语的被赋予灵魂者所制作,而是始终在朝向(Zu)其结果(Telos)之中制作出作品,这里的结果并不是目的,而应该是作为界限(Peras)意义上的终点(Ende),即始终将自身寓于终点之中。这就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异,人始终朝向作为终点的结果而存在,而动物却始终以目的为导向,正如索拉布吉(Richard Sorabji)所说:“欲望具有目的,且在某种状态之中是对我们朝向目的行动的动力因。”〔26〕他在这里强调的正是动物始终朝向作为目的之欲望。人也是动物之一,当然也以目的为导向,但这并非人的全部。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即使某物尚未开始存在,也不能被随意制作,而是始终已经将终点寓于其自身之中,否则就不会是本真的作品。正是在这种朝向结果的过程中,外观从而呈现,因此,只有首先注视到存在者的外观(Eidos),才能在此基础上分析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只有始终朝向终点而存在者,才是应在熟悉的统观中被定向之物。〔27〕海德格尔继而认为,单纯凭借朝向终点存在,从而先在地审视外观这种特点并不足以得到本真的外观,而必须始终将相反者寓于其自身之中,并先在地将其排除,才能真正获得外观。因此,外观不仅仅通过向终点存在得到,也必须通过排除相反者的方式才能获得,因为人始终在熟悉的统观中将相反者寓于自身之中。相反者兼具无定与被限定的特质。〔28〕之所以是无定的,是因为它是除了朝向终点的外观之外的所有其他存在者;之所以是被限定的,是因为它被规定为用来相反于外观之物。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何在一对相反者之中定向本真的存在者之方式:首先朝向终点存在;其次寓相反者于自身之中。两者之间是相互奠基的关系:一方面,在我们定向于作为朝向终点存在的作品外观之状态下,始终已经先在地将相反者寓于我们自身;另一方面,在熟悉之统观中的一对相反者并不是通过我们作为主体进行选择而得到,而是朝向终点存在的作品之外观始终处于先在状态。
三、从制作性知识而来:灵魂的追求(Orekton)潜能
从上文对制作性知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制作必然仅仅作为元话语潜能而存在,无话语者不能进行制作活动。而元话语潜能不可为所有存在者所拥有,只能为被赋予灵魂的存在者所拥有,〔29〕而拥有元话语潜能的被赋予灵魂之存在者就是人,所以元话语潜能仅仅作为人的独特存在方式。因此,人的灵魂拥有一种追求能力,这是由于它拥有元话语,且被这种元话语的制作潜能赋予追求能力。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前述所探讨的元话语潜能及其制作都必须还原到作为有、无灵魂为区分标准的范围内,那么就必须阐明灵魂追求潜能的存在论结构,以及这种存在论结构以何种方式被构建。
亚里士多德说:“有知识的人能将两种互相相反者都制作出来,因为解释包含两者,尽管不相似,并且它是在具有变化的灵魂之物中。因此,它将从相同本原来变化它们两者,这已将它们联结到相同物之上。”〔30〕传统的翻译方法都将Logos 翻译为解释或者理性,但海德格尔却反对这种译法,认为这种翻译“忽视了源初和适当古老(的含义)”,〔31〕而应该译为“熟悉”,也即此在在世存在对周围物的“了如指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灵魂是运动的本原,即“在其自身中拥有运动和静止之本原的自然形体”。〔32〕康纳斯(Clare Connors)在此对变化本原与他者的关系进一步厘清:“海德格尔对潜能作为在他物中变化本原的再阅读,在这里本原是可变化的他者,并不仅是发生于他者中的变化本原。”〔33〕因此,这里点明灵魂与运动、变化的关系,是阐明灵魂的追求潜能之存在论结构的第一步,接下来海德格尔具体展开对灵魂与运动、变化本质性关联的讨论。
海德格尔将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视为阐明灵魂与运动、变化关系的最好文本,因为《论灵魂》从活物的视角来探讨灵魂问题,那么基于生命,就必然将灵魂与运动、变化置于关联之处。“在《论灵魂》这篇论文中,此问题自然被视为最恰当的主题,灵魂是构成有活物之特征的存在者之存在。《论灵魂》不是一篇关于心理学的论文,而是整体的生命存在论。”〔34〕灵魂进而也必须关涉于欲望,因为有感觉之处就会有欲望。〔35〕这就是说,动物作为有感觉者,具有作为感知欲望的追求。但它们的追求与人的追求具有根本上的不同:人必然朝向本质意义上作为外观的作品,而其他活物却是非本真的追求,即一种“猎取”,并不必然朝向本真的终点。因此,人所追求的结果不应该仅仅是目的,而更基本的是始终将其自身建立在完备性意义上的终点。〔36〕所以,灵魂虽然是运动的本原,但并非所有活物都可以在本真意义上运动,本真意义上的运动必然朝向作为外观的作品之终点:“灵魂也是运动由此得以起源之物,尽管这种潜能并不属于所有活物。”〔37〕对此,雅库布(Aladdin Yaqub)讨论得更加深入。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灵魂是运动的本原,但这并不代表灵魂作为一种动力因而存在,他从理智、想象和感知三个层次来论述动力因的不合理性。〔38〕进而,海德格尔将这种活物的运动潜能称之为一种努力追求。在他看来,这种努力追求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只有当某物已经现成在手(Vorhanden)时,我们才能进行追求,因此,努力追求处于某物之后;另一方面,追求始终先在地处于某物之前,因为追求是拥有元话语的被赋予灵魂者的先在生存情态。换句话说,我们始终寓于追求事物的关系之中,即使这个事物尚未存在,但追求本身却早已先在地存在。前者是我们日常意义上的追求,而后者则是本真的追求,前者必须在后者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海德格尔认为,若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我们也只能选择处于先在状态的本真追求,“然而这个行为能放弃设置于—之后(Nach-stellen),并且因此是设置于—之前(Vor-stellen)”。〔39〕但我们需注意的是,即使在本真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追求状态下,也必须先在地拥有被追求之物。这种被追求之物并非通俗意义上的实体,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而是与追求行为相互共属之物,也即这样的被追求之物与追求行为处于相互奠基的关系之中。
在阐明了灵魂的追求应作为一种先在状态之后,海德格尔进一步将灵魂的追求潜能明确地规定为在前述意义上的“制作”。〔40〕既然灵魂的追求潜能就是制作性知识,那么必然就作为一种元话语潜能而存在,因此,从追求潜能——元话语潜能——制作性知识三者之间的本质关联,就可以阐明灵魂的追求潜能之本质结构。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我们发现以追求与制作的本质性关联也可以阐明此问题:灵魂以何种标准才能恰当地追求应追求之物,而不错误地追求其相反者。正如制作必然是朝向具有本真终点意义上的外观之作品的制作一样,追求行为本身也必然朝向这种作为本真终点的外观之物。亚里士多德正是在《形而上学》第九卷中持有海德格尔所说的相同看法。〔41〕
四、结语
海德格尔在1931年夏季学期的弗赖堡大学讲座中(《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Θ 1-3:论潜能的本质和现实》)对于潜能与现实的论述始终未得到学术界的过多注意,然而这本著作不仅可以为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九卷提供一个全新的现象学视野,而且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前期海德格尔如何继承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对“潜能—现实”问题的阐述具有多种阐述视角,而最核心的就是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概念出发来理解“潜能—现实”问题,因为只有被赋予灵魂的生命体所具有的潜能才是真正的潜能,即元话语潜能,其他种类的潜能只是在其附属意义上存在。海德格尔首先阐明有无灵魂者与有无话语者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从而得出只有人才是拥有元话语的被赋予灵魂之物。进而,只有人才能在本真意义上、在熟悉的统观中,朝向相反物而制作,这种制作始终先在地朝向作为终点的外观。而这种元话语制作功能也正是灵魂本身的欲求潜能。由此,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关于运动的潜能”的区分,也从本质上真正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