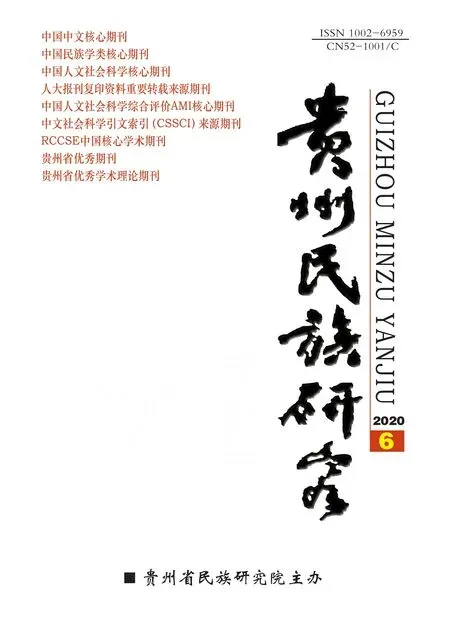“区域”的逻辑: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与农业转型探析
荀丽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9月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振兴的规划思路对于我国乡村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分类推进、分类施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思路涵盖于乡村振兴的各个层面。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乡村振兴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了依据区域差异划分引领区、重点区和攻坚区以实现对乡村振兴发展目标的“梯次推进”,即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口净流入城市的郊区、集体经济实力强以及其他具备条件的乡村,作为“引领区”到2022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周边以及广大平原、丘陵地区的乡村,涵盖了我国大部分村庄,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和主战场,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攻坚区,到2050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说,这一区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同时也反映了内嵌于区域发展格局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作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西部地区。由是观之,文章认为,对我国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特点与规律展开基于区域差异关切的深入科学研究应成为新时期乡村研究的重点。
西部大开发20年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多年超越东部地区。同时,西部地区内部新的区域不平衡开始凸显,主要表现为西北地区经济增速普遍慢于西南地区。在新的“南北不平衡”的格局下,西部地区内部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已经形成[1]。在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10年的历史节点,深入分析西部区域发展的短板,探索区域内部分异发展的机制、对于国家在新时期构建西部大开发高质量推进的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发展是西部地区发展中“短板的短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亟待落实。具体而言,农业的转型升级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意义,农业转型构成了乡村发展最核心的线索,也是是西部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基与先导。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的含义也超越了城乡二元对立视野下的地域概念,农业的转型更呈现出诸多跨越区域边界的“去地域化”特征。
由此,文章试图通过梳理地理学背景下的农业区划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区域”命题的探讨,来重建“区域”对于乡村发展的基础性和整体性的涵义。在经验层面上,结合笔者近年来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选取宁夏和贵州作为典型省区,通过不同的农业发展案例来呈现西部地区变迁中的农业形态,并对其所反映的政策干预路径和国家治理策略进行初步的讨论。
一、西部乡村发展中的“区域”命题
(一) “农业区划”: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命题
乡村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域系统。农业所涉及的土地利用和人地关系是乡村地域系统的根基和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区域”首先是农业区划意义上的地域分类。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是我国早期农业区划的集大成者,他于1935年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中提出了著名的“瑷珲-腾冲线”以呈现我国人口西北稀疏东南稠密的地理分布格局。“胡焕庸线”不仅反映了我国人口地理的分布特点,也通常被作为我国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的分界线,至今还对在多重层面上理解我国东西差异产生重要的影响。就农业区划而言,1936年,胡焕庸在《中国之农业区域》中依据气温、地形、降水、作物等要素将全国分为东北松辽区、黄河下游区、长江下游区、东南丘陵区、西南高地区、黄土高原区、漠南草地区、蒙新宁干燥区、青康藏高原区等九大农业区域[2]。1981年,我国第一部《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出版,将我国的农业地域区分为东北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黄淮海区,黄土高原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华南区,甘新区、青藏区及海洋水产区共十个区[3]。可以说,这一综合农业区划较多地承袭了胡焕庸等老一辈地理学家所呈现的农业地理格局。
从19世纪80年代初迄今4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加之气候变化等因素推动的自然地理格局的变动,我国的农业地域分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一,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全国≥0°C积温带北移西扩,北方地区增温明显,新增耕地集中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而东南地区的优质水田面积则显著减少;其二,随着国家农业科技的进步,农业技术推广的深入,农业生产的增长与效率的提高从依赖资源投入转变为依赖技术投入;国家在土地整治和生态修复上的投入也扩大了土地利用的空间和产能;其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由单一的粮食作物向追求营养全面的肉、蛋、奶、果蔬、水产等多元化取向转型,农、林、牧结合、农旅结合、农产品深加工等一二三产融合的新模式不断涌现,农业的多功能性日益彰显。伴随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业全产业链的劳动地域分工不断细化,特色农业分布地域相对集中。基于对这些重大变化的响应,刘彦随等[4]地理学家结合自然、经济、社会、技术发展等综合要素,提出了我国新时期现代农业区划方案,将我国的农业区域细化为:东北山地丘陵区、东北平原区、京津冀鲁平原及山地丘陵区,黄淮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区、东南沿海丘陵区、江南丘陵区、内蒙古高原区、四川盆地区、黄土高原区、云贵高原区、华南热作区、甘新沙漠高原区、青藏高原区、海洋农业区等15个一级农业区,西部地区涵盖了所有的高原农业区。
综合以上,西部地区农业转型的“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尽管西部地区不是传统的优势农业区,但是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将成为优势产业;第二,需要在新的城乡关系形态,新的农业劳动地域分工背景下理解西部农业转型的趋势及其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西部地区农业的就业保障功能值得重视;第三,西部地区是生态多样性丰富的区域,也是文化多样性丰富的区域,农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应是着眼于乡村全面振兴的产业发展。
(二) “城乡融合”:社会学研究传统中的“区域”命题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其一生的社区研究历程时,将其概括成为从农村调查开始,再进入小城镇研究,进而到区域发展的探索[5]。若加以梳理,费孝通先生的“区域”概念主要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区域”是一个超越行政区划的概念,是一种着眼于现实生活的经济区域发展的事实。费孝通在跨出江苏省界,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进入边区调查后才有感于东西发展的差距,更为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限制”,即是说“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区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有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5]。正是在这种经济协作的思路下,才有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区、黄河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东北亚开发、淮海经济协作区,中原经济协作区等一系列区域经济的概念,进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其二,“区域”是内嵌于城乡关系形态当中的,有其自身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农村中以亲属为基础聚居的农户,因各村各户互通有无的交易而发生“日中而市”的市场,进而形成作为农副产品集散和销售工业制造品中心的市镇。农村是市镇的“乡脚”,乡村是城市的“腹地”,而各级城市都有其自身的腹地,形成城乡相互依存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其三,“区域”都有其内部结构,是中心、腹地、口岸、道路的空间组合[5]。其四,“区域”是根植于乡村而又超越于乡村的,乡村工业带动的不仅是村庄,而是区域。这一点是费孝通在1948年《关于“城”“乡”问题》一文中谈到的。他因顾念于农民的生计而不主张“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乡村工业加以破坏”,认为“这样的手工业包括家庭手工业到五六百工人的工厂”。费达生设计的生丝代缫机构,利用电力发动,规模能以当地原料和劳力来决定,而“维持一个合作社的代缫厂,也不限于一个村,而应该是一个区域”[6],这是农民获得工业化利益的方案。
(三) “生活圈”:人类学研究视野中的“区域”命题
在人类学传统中,基于非洲、大洋州、南美洲,中国、南亚等地的区域研究是塑造历代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并贯穿了人类学理论的演进。尽管人类学是根植于这些跨文化“大区”的比较研究,但是在具体理论关切和问题意识上,人类学更为从微观的社会过程入手,更为关注某一区域中“人的活动”。 台湾人类学家黄应贵先生对于“区域研究”的省思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在黄应贵看来,在人类学视野中,“区域”的内涵更接近于吉登斯“区域化” (regionalization) 概念而衍生的“生活圈”概念,即“同一社会类别与个人,依其生命周期而来的日常例行生活上的活动与移动,所构成的实质或象征性边界或互动之地理空间。这种生活圈持续的时间越久,其性质和范围不仅会改变,其与其他生活圈的链接与权力关系也可能改变。尤其是交通工具和资讯传播工具的改变,使个人或群体移动的性质与范围改变而致使其生活圈的改变,甚至改变该生活圈与其他生活圈的权力关系,最后造成新生活圈的发展而导致区域的再结构”[7]。人类学亦可在全球化人、物、知识、资金等高度流动的背景下,透过“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的课题来研究一个区域内不同群体的人及其互动,从而超越传统族群研究的局限。在台湾人类学的语境中,即是可以将汉人及南岛民族的研究合而为一,关注不同人群与文化因互动而产生文化变迁的现象[8]。这一视角对于我们在面对多民族西部地区的研究议题时显得尤为重要。其实,上述对“区域”的理解也与1980 年以来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有关[9]。“区域”不再只被视为一个结果,而是一个经由社会关系和地方认同而不断建构的社会过程。
二、变迁中的农业形态:基于西北与西南的乡村调查
无论是在西北的黄土高原区还是在西南的云贵高原区,在传统的小农农业之外,都可以看到一些变迁中的农业形态。如果按照范德普勒格对世界农业趋势与模式的分类[10],这些农业形态包含了工业化的企业农业、也包含了“再小农化”的产业趋势,更有面向“农村发展”的多元化产业。这些农业形态既根植于“区域”,又在市场经济中充满“跨区域”的特点,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区域”。西部的乡村振兴也正是在这多样的农业转型推动下展现出丰富的未来空间。
(一) 企业农业:资本下乡与农业经营中的跨区域形态
在西部地区开展乡村调查,可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一个位于宁夏村庄的某农业企业经营的蔬菜基地生产的是专门供给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港澳地区的菜品;而蔬菜基地的投资者则包括了来自浙江或福建等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家,蔬菜基地的用工有宁夏当地的回汉农民也有来自贵州的农民工;工作效率更高且更受老板青睐的并不是宁夏本地人,而是来自贵州的农业劳工。这是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农业”的常态,它完全是跨区域的农业形态。在下文中,笔者将呈现一个来自宁夏的特色果品农业企业的案例,以此来讨论资本下乡背景下西部地区特色农业的发展逻辑。
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的月牙湖乡坐落着由RD农业科技公司开发的2500亩红树莓种植园区。红树莓,又名覆盆子,是营养价值极高的特色水果,是欧美国家的传统水果,市场价值极高。种植园所在的月牙湖乡地处黄河与毛乌素沙漠的交汇处,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独特的地理条件使这里树莓的果实甜度比其他产区高一倍,并且生产期病虫害很少,也是全国唯一获得有机种植认证的树莓产区。这些独特的优势使RD农业公司的树莓在欧美市场广受欢迎,种植园区一期工程的1250亩树莓主要用于海外市场的出口。
这片沙漠树莓基地的诞生是“资本下乡”的产物,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和农业现代化项目规划的产物。RD农业科技公司成立于2014年,企业前身在能源矿产领域积累了资本,转而投资农业领域。该企业于2010年开始便在中国林科院树莓种植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在宁夏驯化和引种树莓品种,最终选在月牙湖乡建立种植园区。2012年,月牙湖乡作为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建立了近2万人的移民村。在生态移民安置项目中,来自宁夏南部山区的生态移民搬入了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移民村,此外,基于与原迁出区土地置换的原则,移民在月牙湖乡拥有人均一亩的安置土地。移民安置土地原为国有沙荒地,经过政府的土地整理项目而作为移民安置用地。土地为各个移民村集体所有,但在移民搬迁时就统一流转给农业公司经营。RD农业公司即是通过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流转了5个移民村的2500亩地用于种植树莓,土地流转价格为每亩每年700元。企业还投资引进了以色列的微灌系统,建设了3000平方米的移动冷库,并选用在欧美销售市场上紧俏的树莓品种,主要供应欧美市场。鲜果采摘之后两小时内进入冷库,以零下35度速冻,零下18度储存,可以保鲜2年时间,销售也是全程冷链。在种植园区的长期雇工有120人,全部来自种植园毗邻的移民村。长期雇工主要在每年的3月至12月负责树莓基地的田间管理、园区管理和冷库运转。树莓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采摘期需要大量人工进行采摘。这样的季节性用工主要集中在7月下旬到10 月下旬的3 个月时间,每天园区都有500-600 人务工。采摘劳工领取计件制工资,每公斤树莓3元钱。手脚麻利的工人每天可以挣170-180 元,手脚稍慢的老年人或残疾人可每天挣80 元左右。种植园区的用工借了毗邻移民村的地利之便。事实上,由于土地的统一流转经营,移民村的移民处于“有地不见地”的状态,大型的移民聚居区成为打工者的聚居区,非常便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用工难的问题,劳动力价格也相对便宜。
在树莓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资本投入、种子技术、灌溉技术、冷链物流、出口制度、廉价劳力,租赁土地所构成的高度专门化的农业企业典范。农业企业全面面向市场、依赖市场,发达的交通物流支撑了这样的跨区域链接,主要目标集中于利润,与地方社会的关联仅限于廉价的计薪劳力。我们多少可以从这样的农业企业身上看到较为显著的“脱嵌”或“逃逸”特征。
2018 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困难。这一冲击,也使企业开始反思要开始面向国内市场的开发。经营树莓种植园的农业企业为我们描绘了他们未来转型发展的设想,而值得思考的正是这一转型的设想。RD农业公司计划将第二期1250亩的土地“反租倒包”给当地的移民,实施划片经营,每单元20亩地,5户人共同管理一个单元。每单元设有一个温棚,可以实现四季产果,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民收入。而RD公司则转向种苗繁育和技术指导,以及推动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户之间的合作及其与企业的合作。尽管不知能否实现,但我们看到了来自企业农业内部的反思以及现代农业中“再小农化”的趋势。
(二) 地方特色产业:区域再结构的城乡形态
贵州湄潭的茶产业可谓是西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代表。湄潭是典型的“高海拔、低纬度、寡日照、多云雾、无污染”地区,其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宜于茶树生长,不易发生病虫害,茶园农药使用少,质量安全可靠。1939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部的中央实验茶场即落户湄潭,而今日的湄潭已经成长为全国排名第二、贵州排名第一的产茶重点县。
回顾建国以来湄潭县茶产业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湄潭的茶产业是从小农经营起家的,在多年的产业升级发展中,对小农经营根基性作用的坚守,对茶农家户利益的保护,都构成了湄潭茶产业健康良性发展的基础。
核桃坝村是湄潭茶产业的发源地。可以说,湄潭的茶产业发展与核桃坝村的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1965年,长期贫困下的核桃坝村人在村支书何殿伦带领下用97天时间建造了一座能装12台水能坝的堤坝,引水上山、灌溉农田,一跃成为全国先进典型村。1981年,核桃坝村已经解决了温饱,开始探索致富之道。何书记带领村民充分利用荒山荒坡从贵州省茶科所引进良种茶苗,开无性系茶苗大面积种植之先河。19世纪80年代中期,核桃坝的几百亩茶园每逢春节采茶时节,茶农都要自己跑到德江等县去招工,采茶工的工资已达每月50元。核桃坝村还请茶科所的专家来教茶农如何用铁锅炒茶。随着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茶青采摘量的提高,核桃坝村的采茶用工量也大幅提高。同时,核桃坝的茶农中产生了新的分工,一些茶农由种植转向专门的茶叶加工和销售。1998 年,来自沿河的一位采茶工举家搬迁至核桃坝村租房采茶。这些外来户大多来自德江、思南、务川、沿河等县更为偏远的山区。2001年左右,因有核桃坝村民要转向茶叶加工和销售而将茶园出租,外来户们便开始承包茶园,专事种茶。而核桃坝村的村民无一人外出打工,从茶叶种植中分化出来从事茶叶加工和销售的茶农也逐步发展壮大。2006年,一些经济实力强的茶叶加工大户合作成立了湄潭县核桃坝村茶叶协会。
从2008年开始,核桃坝村着手利用各种政策项目开展村庄集镇化的建设。在贵州省城乡一体化试点的支持下统筹各项资金改造黔北民居600余幢,还建成了一座1500平米的茶青交易市场。核桃坝村形成了一个拥有四条街道,集村办公楼、茶叶加工销售和居民住宅区于一体的“小城镇”,水、电、路、学校、卫生等基础设施也一应俱有。而这个小城镇就是由原来的村庄脱胎而来。2015年,湄潭县作为全国农村土地改革实验县,核桃坝村成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试点。在核桃坝长期居住的外来户可以购买宅基地建房,并获得房屋产权,外来户便借着政策的东风在核桃坝落地生根。截至目前,核桃坝村茶产业面积达到12000亩, 有大型茶叶企业5家,茶叶加工大户62家,村集体收入累计420余万元。核桃坝的常住人口为1095户4932人,其中外来户236户,1325 人。除此之外,还有80户约400人在核桃坝租房,每天乘坐公交车到核桃坝打工的也有2000 多人。核桃坝的茶产业每年都可容纳3000多外来人口务工就业。用当地干部的话讲:“一般来说,只要你勤快的话,以目前鲜叶的价格,一天的采摘工资200-300元,手脚慢一点的老年人每天也有100多元。我们走在田间地头,随处都是我们的老百姓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在坡上干活。他自己会说我在坡上干就有钱赚,我坐在家里就没钱赚,谁愿意放弃白花花的银子不赚呢,这是老百姓的观念。这也是我们湄潭社会治安环境非常好的一个原因,自己有摇钱树,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也就没有闲心去做别的了。”[11]
徐宗阳、焦长权等研究者已经对茶产业与城镇化的内在契合性进行了讨论[12]。茶产业内部逐步分工分化的逻辑也构成了由村庄而集市,由集市而城镇的“就地城镇化”过程。核桃坝的村民本来都是从事“一产”的茶农,随着种茶规模的扩大分化出从事茶叶加工和销售的“二三产”村民,也产生了集中进行茶叶加工和交易的需求,适时的城镇化建设延伸了茶产业链条、稳定吸纳了外来劳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政策更巩固了这一成果。核桃坝村的案例体现了“就地城镇化”的“内生过程”,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索新型城乡关系形态的重要模式。
(三) 在地生活圈与“农村发展型”农业
农业的多功能化是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在传统的生产性种植业和养殖业之外,一些“非生产性”农业活动发展起来,比如景观管理、能源生产、农业旅游、康养照料服务等。这些是农业生产活动的附产品。农业是以一个多元农村发展活动有机构成的“共存体系”。与农业企业高度的专门化不同,这样的“农村发展型”农业更为多元化、地方化,将农业中的自然、社会和作为生产者和行动者的人的利益与愿景链接在一起[10]。可以说,“农村发展型”农业的发展过程也是“在地生活圈”的建构过程。
桐梓县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北部,北接西南地区的特大城市重庆市。桐梓县曾是煤炭大县,随着煤炭能源产业的关停并转和产能收缩,全县的产业发展集中到农业的转型升级上。桐梓县是典型的沟壑纵横的山区县,最低海拔310,最高海拔2227,一个村的海拔高差可以达到一千米。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为桐梓县的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机遇。由于靠近“火炉”重庆,每年都有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吸引上百万人次的重庆旅游者到桐梓避暑。全县25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乡村旅游点分布。全县共有1822家乡村旅馆。在比较集中的九坝镇,有乡村旅游共4个,乡村旅馆618 家,占了全县的1/3;高峰期有4万多外地人在那里居住。桐梓县因重庆人的避暑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活圈,并塑造了当地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是农民自发的过程,政府以乡村旅游为核心推动乡村农业转型也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在旅游业中享受到红利的农民不再固守苞谷等传统种植业,而是转向方竹、果蔬种植,牲畜养殖等特色农产品的生产。用当地干部的话来说:“我们要建设一百个乡村旅游示范点,乡村旅游这个产业目前得到我们老百姓的广泛接受。第一,把闲置的房产用好了;第二,种植养殖的东西在家门口就卖掉了。虽然农产品规模上并不大,但是就近卖就是最好的市场。”桐梓县还推动了康养小镇的建设。这些都与“桐梓-重庆”“新生活圈”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新的生活圈中,农民实现了农业经营的多功能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
湄潭县的“茶庄园”是茶产业向“茶旅一体”和“一二三产业融合”转型发展中的创新经营形式,集茶叶加工销售、茶文化体验、茶园订制、餐饮、住宿、度假为一体。以LX茶庄园为例,LX公司是一家民营的茶企业,2015年开始在湄潭县一次性流转1300亩土地发展“茶庄园”。所谓“茶庄园”并不是一个围墙封闭的结构,而是充分保持了原有村庄茶农的利益和能动性。茶庄园将流转的土地“反租倒包”给农户经营。这样,茶农首先可获得每亩800元土地流转费,每年递增20元;茶农还按照原来茶园种植经营,采茶时节的用工也是由家户自组织。作为“茶园管理者”的茶农每户可享受茶庄园免费的有机茶肥服务,在茶庄园统一管理下进行除草和病虫害防治,以保证有机茶园的品质。茶农种出的茶青由茶庄园以高于即日市场价1-2元的价格进行订单回购。LX公司主要投资度假民宿的建设,公共空间的美化,并联络都市旅游者和消费者中的中高端客户开展“茶园订制”,推动与电子商务公司合作,发展互联网上销售的订制茶叶。这些极大地提高了茶叶的附加值。“茶庄园”营造的是一个融合传统茶叶种植、茶园景观旅游、有机生活体验、茶文化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生活圈”,实现了茶园的多功能转化,在保障小农户利益的情况下,提升了在地生活的品质,推动在地产业的高质量升级。
三、余论
通过考察西北和西南地区乡村发展中一些变迁中的农业形态,我们对于当下乡村发展中的“区域”命题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这些乡村农业转型的案例,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在西部地区谈论乡村振兴的认知框架。一方面,不能再就“村落”而谈“乡村”,而是要在“区域”的多重内涵下讨论以乡村为根基的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另一方面,农业转型在乡村振兴中处于首要地位,而农业转型的方向则要依据西部地区特有的区域特点走生态化、有机化、多功能化的发展道路。在上文中企业农业,地方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带动的“农村发展型”产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再小农化”的趋势,小农经营可以在资本和政策规划的干预下保持充分的活力。在多元资本和多元主体融入乡村发展的大潮之下,“乡村振兴”不是“资本逻辑”对传统乡村的强势解构,而是在更丰富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建构城乡融合共进、和谐共生的“地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