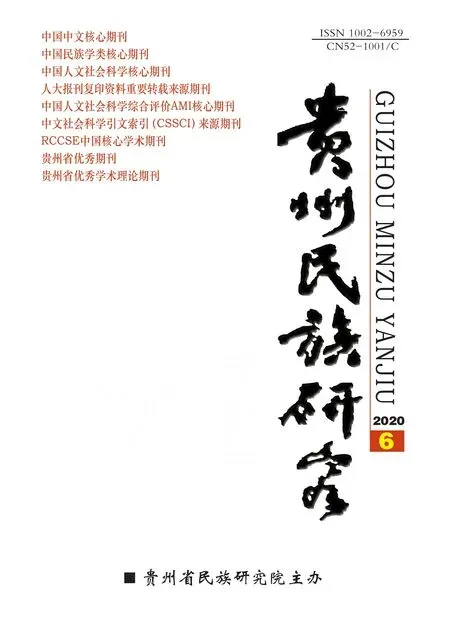吴泽霖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李金兰 周大鸣
(1.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2. 凯里学院,贵州·凯里 556000)
吴泽霖(1898-1990),江苏常熟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1927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执教于大夏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等高校。
回顾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大致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37年前),吴泽霖先生的学术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研究方面。自1928年起,他任职于上海大夏大学,除给学生讲授社会学课程以外,还撰写和翻译了《社会约制》 (1930年)、《社会学大纲》 (1934年)、《社会学及社会问题》 (1935年) 等著述。同时,他为中国社会学的初创做了许多工作,参与组织东南社会学社和中国社会学会,创办《社会学刊》与《中国社会学会报》等刊物[1](P13);第二阶段(1937年后),抗战爆发,大夏大学由上海迁到了贵阳。吴泽霖先生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都市社会转向了民族地区,开始致力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他运用在西方所学的社会科学理论,立足田野调查,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展开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先后整理和发表了几十篇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文章。尤其是其《炉山黑苗的生活》 《贵州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等文章,堪称我国民族志的代表作之一,为我国民族学、民族志调查研究提供了范例[2](P14)。
本文拟对吴泽霖先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开创民族博物馆事业、对西南少数民族现实问题的研究以及研究方法上的贡献进行分析和总结,借以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他在早期中国民族学史发展中的地位与贡献。
一、奔走于荒野僻壤,努力于田野工作
吴泽霖先生早年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对中国的民族情况并不了解。在《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的自序中,他提到自己读私塾时,根本不知道“民族”一词,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后才知道中国是由“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组成的,但对民族的内涵、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存在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3](P1)。而他后半生学术生涯却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37年4月,大夏大学邀请“西南夷族代表团”成员到校演讲[4],随后吴泽霖先生参加了京滇公路周览团到西南云、贵、川和湘西等地实地考察。吴泽霖后来回忆,当车队沿途穿越湘西、贵州和滇东各县时,他才第一次看到和接触到在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3](P1)。由此开始了他对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关注。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夏大学搬迁至贵州省贵阳市办学,当时的校长王伯群主张学校社会科学研究要“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务,西南各种问题中,尤以苗夷问题最为重要”,所以学校专门成立了“社会研究部”,聘请吴泽霖为主任,拟定研究计划,聘请专门人员组织大夏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到贵州省各县开展实地调查[5](P1-2)。从此以后,吴先生后半生的学术生涯转向了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在当时,贵州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是少数民族。关于他们的生活,很少有人进行精确的调查或客观的叙述。“苗夷二字,仍还是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观念,对于他们有种种荒诞无稽的传说,甚至有许多不近人情的污蔑”[6](P1)。吴泽霖先生认为,这些无谓的误会,会加深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隔膜,所以少数民族社会的调查是一件亟待进行的任务。讲课之余,他多次深入到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撰写了多篇有关贵州少数民族的学术著作[2](P14)。如《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 《水家的妇女生活》 《苗族中祖先来源的传说》 《贵阳苗族的跳花场》 《贵州苗夷婚姻的概况》 《贵阳青苗中的求婚》 《炉山黑苗的生活》等。这些调查客观地还原了贵州少数民族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1 年,吴泽霖先生辞去大夏大学教务长职务,执教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在这期间,他对云南省纳西族的社会组织、婚姻、宗教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著有《么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 《么些人的婚丧习俗》等文章。
1956 年,吴泽霖先生作为贵州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组织了在贵州的调查工作。虽已年届花甲,吴泽霖仍坚持到少数民族地区做实地调查,详细地记录了当时贵州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发展现状,所做的调查细致严谨,力求从大量确凿的资料中把握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共性和特性,以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科学研究服务[7](P122)。1958年,吴泽霖先生根据在贵州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写成《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该成果于1958年11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付印。
吴泽霖先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工作及其撰写的民族志,为后来的学者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民族学文化财富。
二、开拓西南少数民族博物馆事业
吴泽霖先生是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拓荒者。费孝通曾高度评价他对建设民族博物馆的贡献,认为“吴泽霖一生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专业是我国少数民族博物馆事业”“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他到哪儿,民博事业也就到那儿”[8](P91-92)。吴泽霖对收集民族文物的兴趣来源于他在欧美参观博物馆时受到的启发。“当年我在考虑如何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时,回忆起我在欧美时看到博物馆所起的作用,联想到民族博物馆在我国可能发挥一定的效能”[3](P7)。
1937 年4月,吴泽霖先生代表中国社会学社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主持的京滇公路周览团,沿途了解边疆民族的实际情况,同时在皖、赣、湘、黔、滇、川等省搜集各种文物,并拍摄风光风俗照片百余幅。回到上海后,举办了一个公开展览[9]。
大夏大学内迁到贵阳后,吴先生在校内建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他和同事在进行民族学调查的同时,也着力于各民族文物的搜集。到1942年,共征集了苗族等民族的文物2000余件。1941-1942年初,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览,展出的物品分为相片、服饰、用物、研究图表及著作等四大类,目的是使社会人士了解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10](P269-276)。民族文物在贵阳的成功展出,坚定了他建立民族博物馆的信心:“尽管在规模上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民族文物陈列,但对民族文化交流起过一点宣传作用。这点小小的效果却增强了我对民族博物馆在促进民族关系上能起积极作用的信念,并鼓励我在嗣后岁月里为促进建立各级民族博物馆而不断努力”[3](P7)。
1941 年,吴泽霖先生应清华大学的邀请来到西南联大执教。在云南的五年时间里,他利用课余时间,多次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征集了许多少数民族文物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公开展览。抗战胜利后,吴先生携带在西南搜集到的民族文物随清华大学迁校北京,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11](P1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吴泽霖先生于1950年7 月参加了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即贵州分团) 的工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还和大家一起搜集了一批贵州少数民族文物。在访问工作即将结束之际,于1951年2月19日,在贵阳市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省首次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一天之内参观者超过万人[12](P264-270)。
返回北京后,经政务院批准,在吴先生的主持下,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在北京故宫“三大殿”展出三个月,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这个展览。之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建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组,吴泽霖被聘任为主任[11](P129)。
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后,以原清华大学民族文物陈列室的藏品为基础组建了一个民族文物室。吴泽霖先生参加了组建工作,并被任命为主任。1952 年7月至12月,吴泽霖参加了中央西南民族工作视察组。仅仅半年,吴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川西藏族地区搜集的民族文物达数千件之多[12](P267)。1953 年,吴泽霖先生调到了西南民族学院工作。他又参与了西南民族学院民族文物馆的创建工作。为了充实这个馆的文物和照片,吴先生把抗战期间自己节衣省食所收集的少数民族服饰及照片资料全部无偿捐献了出来。在他的努力之下,两年之后,文物陈列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陈列方法、设备、展品等方面均面貌一新,被国内外专家誉为新型的博物馆[13](P136-137)。1982年,吴先生到中南民族学院任教,在该校文物室的基础上,创建了我国第一所民族学博物馆。
吴泽霖先生既是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拓荒者,又是民族博物馆学的一位理论家。他认为,收集少数民族文物并举办展览,目的是通过直观教育来增加民族间的了解,加强民族团结,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隔阂[14](P63)。在《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一文中,吴先生对民族博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的功能进行了区分。民族博物馆是“一种既属专业性而又为政治服务”的博物馆,它的任务是介绍兄弟民族的实情和广泛宣传民族政策。民族学博物馆“主要是为科学服务的,它是一种传播知识性的专业博物馆,是建立在民族学的基础上,同时也是依附于民族学而存在的”。田野调查和文物收集是民族学博物馆建馆的重要基础。民族学博物馆是民族学的一种间接的田野调查基础,双方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15](P81-82)。吴先生的真知灼见对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学以致用,学术为现实服务
人类学是一门以应用性而著称的学科。吴泽霖先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除学术旨趣以外,更有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在他看来,“民族学是一门既讲究理论,又注重实践的科学,而它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为现实服务”[16](P140)。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使他一直身体力行地关爱“他者”。
在上海大夏大学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期间,吴先生就率先提倡社会学应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以及理论应建立在社会实际调查之上。他选择了望亭镇和上海各种救济事业,分别作为乡村和城市的试点,组织学生调查[17](P9)。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免遭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与破坏,东部和中部城市的高校大规模西迁,大批知识分子云集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西南边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于当政者与学者们面前。1941年9月,中国边政学会成立,同年,《边政公论》创刊。学者们试图通过投身于边政研究,达到学以致用抗战救国的目的。吴泽霖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学者。
吴先生先后在《边政公论》 上发表了题为《边疆的社会建设》 (1943年)、《从么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 (1946年)、《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 (1947年) 等文章对边疆少数民族问题进行探讨。他认为,一般边民及一般处于地境偏远、物产缺乏区域内的人民,生活都在生存线下挣扎。政府对这些民众要有一种通盘施政的计划,绝不能因为地区遥远就对他们漠不关心。此外,政府施政时要采取适应地境及民情,权其轻重,不应四处全部划一。他主张,“我们需要的是民族间意识上的团结,而不是形式上划一的汉化,这是主持边政者应有的一种认识。”[18](P14)吴泽霖先生在对云南么些人(纳西族) 进行调查后,提出了许多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建议。如他主张用当地的语言开展实际工作,认为一切的政治设施、社会救济、教育宣传,最低限度在初期的时候,要使用边民的语言来做媒介,一方面可以深入,另一方面可以获得边民的信任。另外,他对从事边疆工作者提出了一些要求,认为从事边民福利事业者,必须备具相当耐心,使边民有比较、选择、欣赏的机会,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使用强迫手段。在原则上,“各种事业的推行,应由边民自己来承担”,同时尽量提携当地有力有志的人们,给他们以技术上、方法上的训练[18](P15-16)。吴先生提出的许多发展边疆的建议,至今仍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如他提出,要推进边民的福利,首先要改进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18](P15);其次要改善边疆的交通,发展以铁路为主及公路空运为辅的交通建设,促进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交流;另外还要改善边民卫生及教育设施[19](P3)。
此外,吴泽霖先生还参与指导过边胞服务站的工作。1942年7月,隶属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云南第一边胞服务站在丽江地区建立,吴先生当时兼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服务组的副组长,他推荐自己的学生张正东主持云南第一边胞服务站的工作。主要任务是为区内一些地方的纳西、傈僳、怒、藏等群众提供医药卫生和国民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并根据需要做些抗战宣传工作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据张正东回忆,服务站到1946年2月以后逐渐结束工作。在将近4年的时间内,该站各项工作都是在吴泽霖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平均每月给学生写一次信指导工作。1943 年夏天,吴先生亲自到丽江县了解边胞服务站的工作情况,并到当地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区进行社会调查[20](P107)。
四、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探求
研究方法的使用是否科学合理,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发展是否具有生命力。吴泽霖先生在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研究时,灵活运用了多种方法,如田野调查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心理分析法、残余分析法等。
第一,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方法与学科特色之所在。吴泽霖先生在3年贵州、5 年云南的生活中,经常深入到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同少数民族一起生活,获得了很多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积累了很多具有实际意义的田野调查方法。他强调,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和被调查者要有机地结合,多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调查的主持者最好由具有语言学知识,能掌握该种语言的人或本民族合适的人担任;调查的时间最好是1年,因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大都在一年一度的特定时间内举行。吴先生还特别重视女性报道人的作用。他认为,妇女的人生观往往带有特定条件留下的不同于男子的烙印,只有通过与妇女的密切接触,才可能更全面地、历史地了解当地的社会面貌[21](P35)。因此,“女学者参与民族调查非常必要,由男性学者来承担调查妇女的工作有种种不便,也不能深透彻底”[22](P29)。综观吴泽霖晚年结集出版的《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几乎都是从自身田野调查资料中提炼出来的结晶。他的弟子钟年先生曾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翻开这本文集,一股浓烈的田野气息扑面而来, 三十余万字的篇幅中, 将近百分之九十是作者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整理出的研究报告, 这在已出的社会科学家的文集中是罕见的, 就是在已出的民族学家的文集中也是罕见的。”[23](P82)
第二,历史分析法。吴泽霖先生从来不把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当作一个孤立的客体来研究,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纵向分析。他认为:“社会是立体的,有纵的一面,有横的一面。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现实。在田野调查时应结合历史进行研究,才能获得对一个民族的全面、深刻的了解。”[21](P35)他建议,研究者到非本民族地区进行与民族有关的调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学术问题,必须预先掌握该民族、该地区的一些历史和概况知识[22](P28)。在其相关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田野调查与历史的视野、方法的交叉与结合。在对炉山黑苗进行研究时,吴先生详细地梳理了炉山地区及苗族的历史,将有关黑苗的史籍记载与实地考察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考察黑苗的社会生活[24](P56-154)。此外,他通过史籍资料论证了么些人并不是滇西的土著,他们来自康藏一带,原有的文化是西藏文化,并依据实地调查么些人的宗教信仰、婚葬习俗来探询么些人的族源[25](P183-209)。这种将横向的田野调查与纵向的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于探讨西南某些史料记载较为匮乏的民族历史不啻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三,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吴泽霖先生在民族志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是一种极为细致的工作。表面的相同未必是实质上的一致;外表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同源嬗变的积累。深刻彻底地了解一个不同型态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既需要对其历史的追溯,又需要加以分析比较。”[22](P29)吴先生用“舍异求同”和“同中求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清水江各地域苗族婚俗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追溯苗族的历史和发现苗族社会发展与民族分化倾向的规律[26](P379-380)。此外,他还通过比较西南地区不同少数民族的婚俗习惯来探析群婚残余[27](P386-396)。
第四,心理分析法。吴泽霖先生使用了大量的心理分析来解释某一社会文化现象,尤其是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如苗族的坐家习俗,姑舅表婚,彝族婚礼中妇女对男家客人的戏弄等,均深刻挖掘了文化背后的心理因素。
在吴先生看来,维持“坐家”制度的因素之一是传统风俗的一种社会心理状态。大部分苗族地区婚后如新娘长坐夫家或新郎不许新娘回娘家,就会被人讥笑,他们在“游方场”上也会受到许多嘲笑。这种社会心理,使青年男女不愿意贸然突破而改变它,即使偶然有一方提出长住男家的要求,也会受到另一方的谢绝,这种因循的心理,是延长“坐家”寿命的一个因素[26](P349)。此外,苗族中部分地区流行早婚的情况,十四五岁或十三四岁就结婚,以这样的早龄像成人一样过两性生活,父母内心总会感到不安。“坐家”制就给这些父母们减轻了内心的谴责[26](P347-348)。苗族流行的“姑舅表婚习俗”同时满足了嫁出去女儿和母家的“心理慰藉”。因为“把女儿嫁回娘家后,更可多些走亲戚的机会,这样多少可以满足她留恋、怀恋娘家的心理。从母家来说,既嫁出了一个爱女,在随着年月的流逝而来往关系逐渐疏远的时候,又娶回了一个血肉相承的外孙女,在感情上也是一种安慰”[26](P271)。而彝族婚礼中妇女对男家客人的戏弄,则是“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妇女是受尽男子的欺侮的,平素郁抑下来的积忿,就无的放矢地借题发挥,把男子狠狠地整一下,痛快一阵”[28](P224)。
第五,残余分析法。对于残余分析法,吴泽霖先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社会制度嬗变的过程中常会有这种脱节现象,有时可能是暂时的,不久就会调适改变。但有时也会因积重难返,某些部分,始终不变,形成一种依常理看来似乎不协调不合理的安排。”[25](P209)对社会残余的分析,有助于追溯一个民族的历史。“从事对当今社会习俗中的一些与时代不相称的习俗残余痕迹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追溯那时与它们结合的社会制度的情况和背景”。“对残余的研讨不是一种猎奇,而是探讨社会发展的一种方法”[27](P386-387)。
吴泽霖先生使用残余分析法来追溯一个民族以前的社会状态。在他看来,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公房”是群婚制的残余;家族内婚和不同辈分的婚姻是原始群婚的另一种反映;夫随妻居的生活方式和姨表不婚的习俗是远古母系社会的残余;“坐家”或“不落夫家”制度体现了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后在婚姻制度上的一种逐渐过渡的过程。此外,我国许多民族中流行的“转房”习俗也是和社会文化的残余联系在一起的[27](P394)。
吴泽霖先生在民族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探求与他早年的学术背景密不可分。他不仅在中国接受过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教育,更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市政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训练[29](93-94)。因此,他在具体分析少数民族某一社会文化现象时,并不只是使用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方法交叉灵活运用。这使他常能透过纷繁庞杂的文化表象,做出深刻的解释。这种多学科的知识交叉融合的研究之路正是人类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由方向[30](P76)。
五、结语
吴泽霖先生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使人们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生活各方面都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大量研究成果和学术遗产。其严谨的学术研究,不但推动了我国新兴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更是有着“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综观吴泽霖先生的学术研究,他将国外社会科学理论融会贯通后再应用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其研究方法是从西南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拘泥学科领域,体现了他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