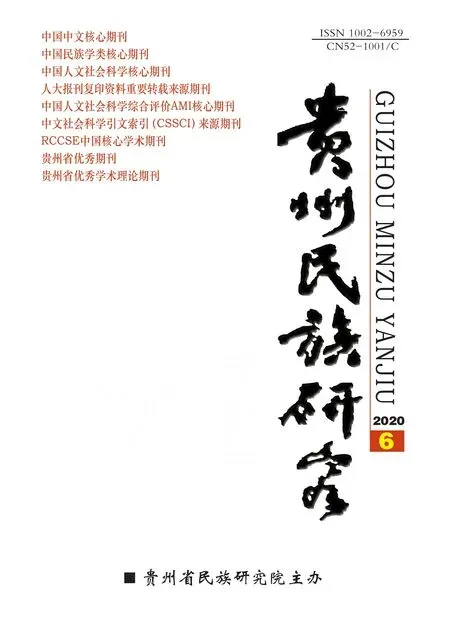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内源性资源当代价值研究
——以绿色犯罪学为视域
魏 红
(贵州大学 法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资源是建立在传统宗教信仰、民俗、习惯法上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传承久远的历史、坚固的群众基础和不可挑战的权威性,从遥远的先民时代至今,对少数民族群众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仍发挥着积极的调适作用,并与现代绿色犯罪学核心伦理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而绿色犯罪学兴起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传统间的思想、经验交流”[1],融合不同民族、文化的力量形成生态安全保障合力。同时,由于我国近现代环境法律规范乃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以西方环境法治理念为内核的环保法律制度要在我国“生根发芽”“落地开花”,只有立足国情吸纳本土性资源、结合内源性生态伦理理念,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因此,在不违背法治统一原则下吸纳少数民族内源性资源,在绿色犯罪学视域下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资源对国家生态法治的补充和辅助作用,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司法意义。
一、绿色犯罪学缘起及其价值基础: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之上的“生态正义观”
德国哲学家萨克塞认为,在人类与自然千万年相伴过程中,二者关系历经“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2]的曲折变化过程。于是,当环境问题愈加突出、社会开始认真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绿色犯罪学作为一种观点或方法应运而生。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 1990年首次提出“绿色犯罪学”概念,认为在对世界本源、自然关系以及人类自身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犯罪学研究范围必须容纳与生态环境、人类和动物之间依赖关系紧密的犯罪和危害。绿色犯罪学从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分析生态环境犯罪,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新的犯罪学立场,即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安全,还包括非人类物种的权利和安全以及生态系统平衡,体现了生态正义观念。
(一) 重新认识世界本源、自然以及人类自身
在世界本源认识问题上,几千年来,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始终围绕着“人为万物中心”思想而展开。从古希腊时代以人为衡量和认识万物的尺度和标准开始,经过亚里士多德对万物存在的理由是以供奉人类生存为目的的推演,到德国古典哲学代表康德对“人即为目的本身”的逻辑论证,一直延续至现代非理性主义代表在推翻一切传统文化上提出的“超人”“新世界观”(尼采) 中,仍然是以“最能体现生命意志力”的“人”为世界本源和中心。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由此而引发人类过度张扬的能动性,在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中已使得地球满目疮痍,给世界敲响了警钟,引发人类反思。环境主义者亨利·梭罗提出宇宙万物为统一体,彼此相互联系、和谐发展,主张所有物种一律平等的世界观[3]。著名生态中心论者利奥波德认为,“如果从生态学角度诠释历史,我们就能知道,人类只是生物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4], 《地球母亲权利世界宣言》起草人科马克·卡利南也提出:“我同时既是我的家庭的一员,也是我所栖居的流域生态系统共同体的一员。”[5]因此,现代环境保护学者将自然界视为一个联系的“生物共同体”,认为自然界、“生物共同体”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人类仅是“生物共同体”中一员而已,应遵循生态系统法则而不能凌驾其上。
在如何看待自然的问题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仅是人类生存的资源和索取的对象和服务的工具。正是近几十年来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愈发紧张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对待自然的态度,意识到人类必须降低自己的主体地位,需要并学会尊重和敬畏自然。因为自然并非只是人类认识与征服的客体和对象,而是有其固有内在价值。自然价值论代表人物罗尔斯顿教授认为,孕育生命万物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是宇宙的奇迹也是最为珍贵的现象,作为万物生命之源的自然必然具有内在价值也应受到与人类一样的尊重[6]。生物中心论代表泰勒教授相继指出,尊重自然的态度是指人类应秉持这样一种终极道德,即认为个体生物、种群以及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共同体具有天赋价值,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或意义不取决于它们对促进人类的目的(或其他任何物种的目的)的贡献的大小”[7]。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罗尔斯顿教授认为“没有人类大自然依然会鸟鸣花香、生机勃勃,而人类失去自然却无法生存繁衍,更不说发展昌盛了”[8]。因此,尽管人类在追求文明发展和价值实现的时候,不能避免对自然环境会造成某些破坏,但是人类要学会约束自己,争取给自然生态系统仅带去最小可能的干涉和影响[7](P195)。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与人类一样具有智慧、生命和内在价值,有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的权利。
人们在不断反思和争议之中,对世界本源、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逐渐向非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传统犯罪学领域中引入非人类中心主义促成绿色犯罪学采用开放性视角看待犯罪,在司法定义为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正式标签之外,绿色犯罪学将可能违反或不违反现有规则和环境法规的,且具有可识别的环境损害后果并源于人类的行为纳入研究框架之中。这些事件目前在司法规范中尚未被定义为犯罪,但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却是严重的。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无法关注并重视这些打破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并影响后果深远,目前却似乎对人类没有直接危害的行为,而只有从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出发,才能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
(二) 绿色犯罪学核心价值基础:生态正义
绿色犯罪学兴起是为了将人们注意力转向严重而广泛的生态环境危害。这类危害甚至比普通刑事犯罪更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命和生存环境安全。在此领域中人类与自然、非人类物种的关系和互动成为绿色犯罪学关注重心,生态正义则是其核心与基础。传统犯罪学将刑事司法作为唯一有效的正义途径,正义概念受到传统刑事理论对正义所作前提假设的限制:仅以人为正义的主体。因此,传统犯罪学中正义的形式较为狭隘,其所有形式的正义都是人类正义理论或观点的衍生或应用,而且仅仅只是人类的正义。传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也以人类利益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难以注意到或促进对非人类物种和环境的正义。而“正义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正义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运用与拓展,直接催生了生态正义”[9]。于是,以生态正义为判断基础的绿色犯罪学为解决上述局限性提出开放性解决方案,从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物种平等价值取向出发,认为生态正义内在于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之中,以自然内在价值论、敬畏生命和天赋权利论为主要依据,承认自然和人类以外的自然体和人类一样都拥有“善”和内在价值,赋予与人类享有同等生存权利和平等生存地位。因此,从生态整体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出发,生态正义不仅应建构于人类内部之间的自然资源分配和生态义务承担之上,更应将资源分配和种族存续的权利公正而平等地扩展至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这也就是绿色犯罪学的核心价值与基础。
二、我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资源价值体现:生态正义的意义关怀
从生态意义而言,伦理是对所有自然体争取生存行为的自由限度,而任何事物都可在趋向于相互依赖的个体或群体合作模式的进化过程中找到起源,生态学家们称之为“共生现象”。迄今为止,所有伦理进化都依赖于这一前提,即“个体是组分之间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一员。他的本能促使他争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但他的伦理意识也促使他(与其他成员) 合作”[5](P131)。“和谐”是维持人类价值与自然生态系统中所有自然体权利的平衡,即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和接受其文化生活方式的同时,允许各种生态系统自然体能不被干扰地展开自己的存在[7](P195)。因而,绿色犯罪学“生态正义”的提出不仅表现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认知,更体现了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应有合理性关系的接受,这也是其核心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同胞在迁徙、生产生活过程中历经无数的生态灾难,尊重、爱护自然和所有生灵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心理,也塑造了“万物平等”“敬畏生灵”和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这些生态理念千百年来不仅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心理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与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敬畏生命”“尊重自然”思想具有相通的伦理哲学基础。因此,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资源中天然地蕴含着“生态正义”的意义关怀。
(一) 少数民族原始自然观中绿色生态思想:万物平等
少数民族先民在原始生活早期更多地依赖渔猎和采摘活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尤为重要。长期以来,先民将人类与自然万物视为“共生”“同源同祖”关系,形成了万物同源平等的原始自然观。在我国纳西族、侗族、彝族等关于人与天地万物起源的传说以及苗族古歌《开天辟地》等文化资源中,都以神话形式表达了这一自然观。如纳西族传说中认为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并相信有一个代表自然万物的超自然神灵“署”,“署”就是草木鸟兽、山林川泽、风雨雷电整个自然界的总称。在上古时代,人类与“署”是相生相依、互无猜疑的好兄弟。但兄弟双方长大后却反目为仇、互相为敌,人类用弓箭、陷阱捕杀鸟兽动物,放火开荒破坏森林,使得自然遍体鳞伤。于是,“署”带领鸟兽、裹挟着风雨雷电开始向人类报复。在“署”强大的自然威力面前,人类软弱无助、难以生存,只有求助于天神帮助。最后在天神调解下,人类与自然和解并保证双方互不侵犯永远和谐相处[10]。在纳西族东巴教宇宙观中也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同体合一”的思想,认为开天辟地起就有自然万物和人类,不论是日月星辰、河泽山川、草木森林还是花鸟鱼虫、走兽人类,都源于同一个生命起源的蛋卵,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这也成为纳西族先民原始自然观和生态观最初的根源。在侗族古歌神话传说中也有类似说法,认为人类祖神松恩是从白蛋中孵出并生有七子:“第一个是蛇王,第二个是龙王,第三个是熊(虎),第四个是雷公,第五、第六个是姜良和姜妹,第七个则是猫郎”[11]。侗族祖先姜良、姜妹不仅与动物中的蛇、龙、熊(虎)、猫,甚至和自然现象雷都是兄弟姐妹。少数民族先民正是从“万物平等”原始自然观出发,不仅将动植物看成是自己生存、生活之源,而且将自然界中所有的物种都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自然万物和人类都是同一个大家庭中的孩子,形成了人类平等对待和维护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
(二) 少数民族自然崇拜中绿色生态思想:敬畏自然
人类社会早期,少数民族先民不理解自然现象和生命形成原因,认为存在着超自然力量并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不尊重自然万物就会受到神灵惩罚,因而敬畏和崇拜超自然力。这种认识尤其是普遍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之中。彝族是历史上图腾崇拜种类较多的民族,至今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有遗迹留存,如云南新平县鲁奎山地区,元江县三马头、大明庵附近村寨都不准捕杀食用獐子、崖羊、斑鸠、蛤蟆等动物,而哀牢山区彝族则供奉“涅罗摩”(母虎祖先),这些都与当地部族曾经的图腾崇拜有关。苗族先民不仅有崇拜图腾,而且由于支系繁多、地域分布广泛,崇拜图腾种类也丰富多样,有枫木、蝴蝶、神犬(盘瓠)、龙、鸟、鹰和竹等不同动植物。如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先民奉枫树为图腾,至今很多村寨将枫树视为保寨树,有的地区苗族同胞认为人祖姜央是“妹榜妹留”(“蝴蝶妈妈”) 的后代,将蝴蝶视为祖先崇拜[12]。
除图腾崇拜外,少数民族先民中还普遍存在着形式各异的自然崇拜。很多少数民族以茂林大树立社称为“龙山”“神树”或“鬼林”,如苗族、彝族、佤族、傣族、布朗族、纳西族、傈僳族、独龙族、白族和拉祜族等。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崇拜“岩山鬼婆”,民间俗语称“三十六个岩山鬼婆”,认为“岩山鬼婆”是以悬崖古树为家的岩山山神,如果人们进山打鸟射伤树皮或射落树叶都会触犯她们而招来祟害。因此,悬崖上的树林无人敢进更不敢随意砍伐树木,保护了岩山森林植被,客观上起到生态保护的作用。分布于云南西南部的佤族先民以“木依吉”神为崇拜对象,将其视为创造、主宰人间万物的最高神灵。在每个佤族村寨附近,都生长着一片参天大树的茂密林子,称为“龙梅吉”即“鬼林地”。而且佤族先民认为神林是“木依吉”,生存的地方,人们不能乱闯神林,不能动神林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土,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至今,许多佤族村寨神林保护较好,有的变为风景林,有的仍为村寨禁忌场所。神林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当地森林资源不受破坏的效果。
(三) 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中绿色生态思想:和谐共生
少数民族原始自然观和自然崇拜中,蕴含着人类与万物共生共荣思想,孕育并发展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并在民族习惯法和其他生态伦理资源中以各种形式要求保护动植物、爱惜环境、注重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如藏族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不仅对一切生命持平等、爱惜之心,而且对动植物更是怀有情感加以细心保护。藏族先民早在吐蕃时代就有了以佛教“十善法”为基础的民间规约,其中规定:“杜绝杀生;严禁猎取禽兽,保护草场水源;禁止乱挖药材,乱砍树木”等。傣族在为了祀奉勐神制定的勐规中规定:“龙山上的树木不能砍,寨子内其他地方的龙树也不能砍。”[13]在“石牌大过天”的瑶族传统社会中,石牌“料令”中很多内容是关于封山育林,禁止乱砍、乱猎、乱捕和保护水源、山林。如光绪年间(1871-1908年) 广西金秀大瑶山瑶族的《两瑶大团石牌》 规定:“瑶山香草、桂树、竹、木、山货、杂粮百件,不得乱取,重罚。”[14]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除了体现在宗教信仰和习惯法中,在少数民族漫长的渔猎和耕作史上还形成了众多的生产狩猎禁忌。如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都禁止春夏期间狩猎,因为这段时间是许多动物下崽和成长重要时期,不能打怀崽、产崽、孵卵和交配的动物,如果谁打了就会受到诅咒,以后再也打不到猎物。这些都体现了少数民族尊重动物、遵循动物的生长规律,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动物生态平衡的作用。
虽然这些生态伦理思想原始而质朴,甚至与现代科学精神有些格格不入,但其中所蕴含的万物平等、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智慧,却与绿色犯罪学核心价值思想相通,不仅体现了生态正义对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资源分配和生存权利上平等和公正的态度,也是少数民族先民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合理性关系的认知,千百年来指导着人们日常行为模式,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保护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三、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资源价值的现代体现:民众环境本体性安全保障
本体性安全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和物质环境的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15],吉登斯在其经典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就如此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资源由于内含顺万物生长而为的哲理和民族生存智慧,因而,生态保护传统和习惯不仅具有传承久远的外在仪式感与权威性,更具有其内在实质意义和核心价值;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民众对于自己民族传统的认同和发自内心的信服,也外化于神圣化仪式对生态保护传统的承载和强化。虽然宗教信仰和固化仪式对传统传承一方面具有强制性;另一方面,也为生态传统注入了带有圣典性质的实践持续。在以信仰和习俗禁忌为保障,维系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性,并连接民众信任和惯例的生态实践而言,少数民族生态保护传统(资源) 不仅为少数民族同胞提供了对未来社会的信心,也为民众提供生态环境本体性安全保障。因此,在构建我国绿色犯罪学生态环境犯罪治理体系时,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资源不仅提供生态理念导向支持,还有利于犯罪积极预防观的确立并能提供对司法实践的积极支持,充分展现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智慧的时代价值。
(一) 绿色犯罪学价值导向:与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相融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
绿色犯罪学体系建设中关键问题不在于规则的建立,而是核心价值理念的确立并为民众所信服。法律并不仅是规则和约束,更是活生生的社会过程。法律效力的完全获得并非仅取决于强制力,还有赖于得到大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促成这种应然状态实现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顺应人们对其人生目标的追求和神圣事物的崇敬,而最能表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信仰和传统。哲人坚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6],因为作为理性和意志高级体现的法律是建立于人类广泛而丰富的道德情感、信仰追求和价值判断之上,不仅是社会基本价值和核心信仰的理性体现方式,也是历经人类历史不断遴选、沉淀形成的传统。“一致的价值经验是认识正义的基础,认可这种主张并不困难,难处正在于实际获得一种广泛一致的价值经验”[17]。因此,绿色犯罪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只有立足于历史传统之上又具有现代伦理价值,才能具有凝聚力并内化为个人信念而为民众所信奉。
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少数民族同胞已经形成了人与万物同源共祖、共生共荣的生态伦理观。虽然是原始、朴素和非理性的自然观念,但其中所蕴含的“万物平等”“敬畏自然”价值理念却是现代生态正义的思想准备,也是生态危机面前促使人们对自然关系的认识回归到本真状态的基础。由于“任何民族的本土生态知识都具有传承功能,民族文化也具有抗击风险的能力,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巨变的再适应禀赋”[18],因此,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极为张扬时代,运用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念矫正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工具论的影响,与“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19]理念相融和成为民众个人信念,对我国绿色犯罪学核心价值形成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 绿色犯罪学应对策略:民族生态习惯法上积极预防观确立
各类生态环境犯罪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毁坏,更具有危害影响范围广、修复周期长、治理难度大以及危害链条化等随附效应,可能导致生物链、生态链断裂等严重后果,正是这些异于一般刑事犯罪的特性促发绿色犯罪学兴起并重新审视犯罪学关注的重心。近年来,我国学者已开始认识到此类犯罪的特殊性,如冯树梁教授认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是战略性犯罪或曰‘原罪’”[20],呼吁将社会生态安全作为犯罪学新的研究起点,提出“防患于未然,防患于将然,防患于已然”[21]的“三级预防”思路。因此,现代生态正义理念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犯罪事前积极预防,改变了以犯罪事后惩治为重心的传统认识。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伦理观念和社会实践连接的载体,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自发形成的生态规范和生态秩序,与国家制定法相比更贴近于一般民众生活,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更为深远和直接有效。习惯法中各种禁忌、禁条对于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就是源自于良心的命令,任何违禁行为后果带来的潜在压力既可能是出于心灵的恐惧,也可能是源于对神秘力量惩罚的担忧。因而,这种自我萌发的罪恶感表现出对破坏环境行为的外在约束和内在精神抑制。正是民族习惯法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生态保护机制,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生态、预防环境危害的积极效应。
(三) 绿色犯罪学施行:民族传统生态实践助益于司法实践
在倡导、组织人们参与生态保护、预防生态环境犯罪方面,少数民族传统生态实践为当代社会提供了积极实践范本。出于对自然敬畏、对万物生命尊重,实施动力源于形式多样的自然崇拜、宗教信仰、民俗禁忌以及乡规民约的少数民族生态实践,带有较强的自发性、自律性并具有参与的广泛性,不仅历史上对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起到了良好效果,即使在现代社会的今天,对于预防和惩治生态危害,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实践仍具有积极意义。
传统生态实践中,少数民族同胞在沿袭和尊崇传承下来的各类自然崇拜、宗教信仰和民俗禁忌之外,还自发形成多种多样的乡规民约约束和教育族群成员爱护动植物、尊重自然。如大瑶山瑶族20 世纪50年代订立的《大瑶山团结公约》规定:“经各乡各村划定界之水源、水坝、祖坟、牛场,不准垦植,防旱防水之林木,不准砍伐。”[22]20世纪90 年代,为保护云南泸沽湖生态环境,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制定村规,“严禁向湖中直接排放污水,严禁炸鱼、打野鸭,捕杀野生动物……严禁乱砍滥伐”[23]。除了乡规民约外,长期传承下来的很多民俗活动中也包含着生态保护内容。如贵州侗族每年有“三月约青”“九月讲黄”“讲款”的习俗。每年春天,侗族村寨成年男性就聚集在鼓楼,聆听寨老讲述保护秧苗、合理使用水源、约束各家各户鸡鸭放养等内容的侗款;秋天庄稼成熟时,村中寨老再次召集村民到侗家鼓楼重申相关“款约”[24]。
正是民族习惯法“对于规则遵从度最重要的规范化影响在于人们的认知”[25],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先民秉持万物平等、尊重自然内心信条形成的生态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实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犯罪执法具有导引和补充作用。导引作用是指在生态环境犯罪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尊重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并将其视为执行中的观念导引,执行工作就能得到被执法者的理解和认同取得良好执法效果;补充作用是指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可以适当考虑适用少数民族习惯法为相应补充。如在破坏环境资源案件中,刑法对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罪的处罚仅包括有期徒刑和罚金。但从现代生态修复理念而言,生态环境犯罪处罚的目的不仅在惩罚犯罪本身,更重要是在于促使生态系统得到修复,但在现有法律规定中却没有相关内容的明确规定。而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中对砍伐树木的行为不仅要惩罚还要求“补种包活”。因此,2018年贵阳市花溪区陈某明滥伐林木案件处罚中,当地法院不仅依据刑法规定判处相应刑罚,还要求被告人必须在当年8月以前,在当地黔陶布依族苗族乡半坡村补种树木115株,并要求保证成活率不得低于九成(注:陈明水滥伐林木一审刑事判决书,(2017) 黔0181刑初395号)。这种变通的刑罚执行方式不仅弥补了国家制定法的不足,而且符合少数民族生态保护传统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获得法律和社会效果的双重实现。因此,司法实践中运用民族习惯法和其他传统生态伦理资源,不仅可以考虑到各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伦理观的差异性和地方性,还可以展现法律实施的灵活性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促使国家环保法律在民族地区有效实施并取得良好社会效应。
四、结 语
传统文化因其蕴含和承载着人类世代积累和选择的经验知识而备受人们重视和尊崇。但传统资源传承并非自古至今静态不变的沿袭和保存,而是在人类每一代更迭中不断承继并创造着而永葆活力。我国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资源是少数民族先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宝贵生存智慧和经验,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不仅为探寻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指出了一条既原始却又崭新的路径,而且引导人类从超越自然转向回归自然、从外向征服世界转向内心省悟。
——许春金先生
——张荆先生
——张荆先生
——张黎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