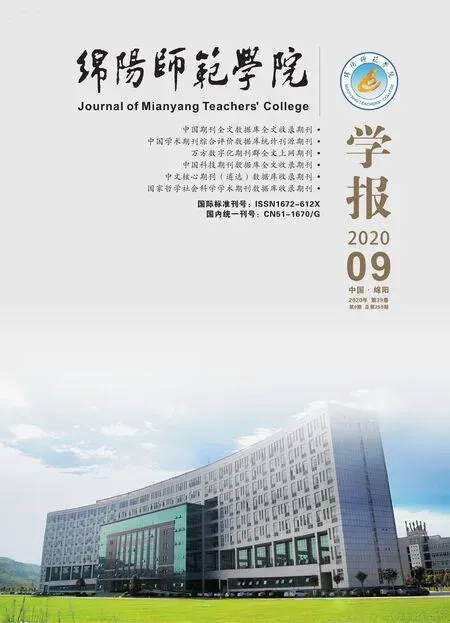黄人《〈小说林〉发刊词》理论探析
邓春霞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06)
摩西,即黄人,晚清作家、批评家,代表作有《摩西词》《中国文学史》等。《小说林》是1907年底以曾朴、黄人、徐念慈等为代表的小说林社为响应当时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而创办的小说期刊,而《〈小说林〉发刊词》正是黄人以其字摩西为名发表在《小说林》第一期的一篇陈辞,后又被收入《南社》中。“中国古代小说及其艺术理论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1小说也与社会学、美学以及文学等息息相关,黄人以《〈小说林〉发刊词》为载体的小说理论用半文言半白话的形式表达了对小说与社会的强烈关注。
一、小说的社会性
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繁荣发展,并在清中叶达到高峰,而当我国古代小说在1900至1911年间进入演进期时,小说理论也因此进入了转型期。刊登于1907年的《〈小说林〉发刊词》正是古典小说与近代小说、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之间的博弈,黄人针对时下狂热的小说场景叙述了自己的小说理论。
“今之时代,文明交通之时代也,抑亦小说交通之时代乎!”[2]171文章首句既是对发刊词中首段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初小说景况的概述。“独此所谓小说者,其兴也勃焉。”[2]171戊戌变法后的时代,既是文明“流行”的时代,更是小说“流行”的时代。“小说界革命”前后小说的繁荣是诗歌、散文、戏剧等都难以匹敌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黄人从“国民自治”“教育改良”“科学”和“实业”现状之不足入手,打开了对当时中国小说盛况的描述。“海内文豪,既各变其索缣乞米之方针……小说之风行于社会者如是。”[2]171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小说是蓬勃发展的,但它荣华兴盛的根本却是国内内因:当时社会生活出现了新的社会景象,商品经济繁荣,工商业发展,市民阶层扩大,这是与海外小说及其小说创造者们无关的繁荣形势。而戊戌变法后小说的繁荣不仅是中国本土小说的繁荣,同时也是近代翻译小说的繁荣。《〈小说林〉发刊词》叙述了当时繁盛的场景:海内外的文学大家们都摒弃了过去的依赖性,开始运用自己高超的谋略创作,有如《庄子·大宗师》中“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3]71,开始随心而化从域外的奇异传闻中获得思路;有如《元和郡县志》中“温峤至牛渚,燃犀照诸灵怪”[4]172,开始从社会总体出发暴露当时统治的黑暗现状。此外,近代小说不仅是内容上的创新,更是传播途径的更新。此前小说的传播途径“不外乎史家和目录家的著录、读者传抄、类书和丛书收录、戏剧改编”[5]4。而此时杂志期刊、报纸成为了小说输送的“异军”,小说也因而产生了四大流派和四大期刊。四大流派分别是以梁启超、夏曾佑等为首的“新小说派”,以徐念慈、黄摩西为首的“小说林派”,以林纾、周桂笙为代表的“翻译派”以及以王国维、周作人等为代表的五四“先驱派”[6];四大期刊分别是《新小说》《小说林》《繍像小说》和《月月小说》(四大小说流派与四大小说期刊并不对等)。“稿墨犹滋,囊金竟贸”,“竹罄南山,金高北斗”,“钞腕欲脱;操奇计赢”“虿发学僮……视沫一卷”[2]171。小说手稿的墨迹还未全干,人们就开始竞相购买;虽价格昂贵,印小说还是把纸张都用完了;商人也以囤积小说来谋取暴利;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不管是地位尊贵的人,还是卑下的人都不忍把小说放置一边,用手沾着唾沫来翻书。也许黄人的这一段文字描写过于夸张,但当时的小说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彼时小说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狭斜抛心缔约,……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又如是。”[2]171娼妓们开始学起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和《迦因小传》(均为林纾译)中马克和迦因的一套,逐渐与属意之人缔约;屠户和卖酒之人也学起了《福尔摩斯探案》和《马丁休脱探案》中柯南·道尔和马丁·休脱的侦查方式,开始细微观察,竞相表现其才能。婚姻上,人们开始崇尚恋爱自由,花圈雪服;政治上,人们也开始主张无政府主义,崇尚炸弹快枪以及暗杀的手段。小说盛行如是。然,一切都是对的吗?至此,黄人对古今小说境况发出了感慨:“虽然,有一蔽焉: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2]171过去人们把小说当成博弈的一种手段,乐舞谐戏的一类,毒药的一种;达官贵人也不屑于谈论小说;《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或虽附有“小说”,然此所谓“小说”,也非现今之小说,而宋代平语以及元明演义均未被收录史志中。酷爱小说之人也只能私下赏读,文章偶有引用则会被加以耻笑,小说仿佛对敌屈辱求和之人被判处诲淫诲盗之罪。
“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的社会功用又被无限夸大,被视为“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2]172,从而出现了众多荒诞虚妄、杂乱粗糙的劣质作品。“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2]172明末清初小说繁荣更多的是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是内在的、自发的;而近代小说的繁荣则受政治因素影响更多,且是外在的、被迫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7]165近代社会动荡,政治变革,使得作家们纷纷通过文学来抒发情感,鞭笞现实,以实现救亡图存。而小说通俗易懂的特性使得它能够从众多的文学形式中脱颖而出,因而有了戊戌变法后小说的兴盛。然我们就应该一味地宣扬小说吗?黄人是当时少有的理性主义者,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进行了响应,但他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学见解:他明确反对过度忽略小说和过度夸大小说作用的两种倾向。
二、小说的审美属性
正如苏州大学王永健教授在《“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中所言,摩西《〈小说林〉发刊词》中的小说观是“美学理论指导下的小说观”[8]165。黄人等人的《小说林》是“小说界革命”的“支持者”,但并不是吠声学步者。小说与美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针对戊戌变法后人们过度夸大小说作用的倾向,黄人对小说的文学实质进行了考究。他始终秉持自己的小说理念,认为小说的本质属性是文学的审美性,且其审美性是建立在审美情操和艺术性之上的,是强调小说的审美特质的。
“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2]172黄人在发刊词中提出了其核心内容。在他看来,文学家们所忌讳的莫不是心理不诚实及掩盖文学的本来面目等;但黄人本人所祈求和探究的,既不是小说能否使顽固之人的头脑变得灵活或使腐败的社会空气变得清新,也不是质询小说的主要创作者、评论者和品读者是谁,以及能否为大众谋取利益,是否与社会标榜的内容相符合等等,黄人所注重的是小说的本质——审美属性。
“微论小说,文学之有高格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2]172情操,在心理学上是指以某一种或某一类事物为中心的情感倾向,是思想与感情的综合。在黄人的文学理论中,他认为小说的审美属性首先表现在情操上。叙说男女情思,“宝钗罗带”作别,已不是高尚之士的言辞;一味表现个人的离愁别绪也已不是以国为重的有志之士的抱负。黄人的审美理想总体而言还是与当时社会主流一致的,符合小说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需求,但同时他也倡导时人在实现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时保持小说的审美情操。小说是具有审美属性的文学类别,因而我们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更应“极藻绘之工,尽缠绵之致”[2]172,竭力表达小说的审美情感,极力描绘其事物情态。小说的审美属性,可以丰富史学家的著作,也可以使人内在生机旺盛。如黄人所言,如果小说没有审美特质,那么有哲学、科学专书在,有法律、经训原文在,又何必需要小说呢?《黑奴吁天录》(林纾、魏易译)和《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林纾译)等或使我们感同身受,或使懦弱者有所建树,都能使我们从中获得美感,因而有其存在的价值。王嫱、西施美也,然终化为青冢一坯,昭君死于匈奴,坟头长满青苔,西施埋没于吴宫,成了亡国妖妃;而孟光、曹娥分别以贤妻和孝女之名留于《后汉书》中。正是因为其中蕴涵的高尚情操和格调使得黑奴汤姆、孝子汤麦司以及贤妻孟光等人得以扬名后世。可见,无限夸大小说的社会功用只会适得其反,更难以实现其社会价值,着眼于小说的审美情操方能更好地阐发其文学属性。
“吾不屑屑为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2]173小说的审美属性还体现在其艺术性上。倘若小说失去了其审美属性,就失去了其存在的艺术价值。同样,小说的艺术性也反作用于其审美属性。“且彼求诚止善者,未闻以玩华绣帧之不逮,而变诚与善之目的以迁就之。”[2]173寻求真实、追求善良的人,都能在哲学、科学、法律和经训上有所建树,或玩弄辞藻或专工文采,黄人谋求小说真、善、美的统一,强调小说的艺术审美性,这在他的其他文献中也得到了论证。“古来无真正完全之人格,小说虽属理想,亦自有分际,若过求完善,便属拙笔。”[2]180在《小说小话》中,黄人运用了真、善、美相统一的批评方法对《水浒》《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中的种种人物形象进行了品评。美是审美,需具有艺术真实性,或详略得当、虚实结合,或出奇制胜、合情合理,而不是过于追求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统一。在对《野叟曝言》的评论中,黄人也提出了“小说兼文学、美术两性质,更不宜尽”[9]313的主张,文学美和美术美都是小说艺术美的审美形态之一,他在文中重申了其对小说艺术性的审美追求。此外,在其散文《清文汇序》中,黄人也对文章的审美特质提出了要求:“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10]309黄人在面对中外文化碰撞之时,始终主张对传统文学批判继承、革新拓展,因而他对小说的美学话语进行了重构,反对文学的模式化,呼吁小说的艺术性和审美性。
小说的审美属性是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中的核心观点,也是黄人小说理论的理论重心,而审美性作为黄人审美理念的本质属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还与晚清著名翻译家徐念慈的小说理念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徐念慈是小说林书社的主要创建者,也是《小说林》杂志的主要创刊者,别号觉我。1903年起徐念慈开始其文学生涯,翌年10月他与张鸿、丁祖荫等人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任编辑主任;《小说林》创刊后他又任杂志译述编辑,且创有《〈小说林〉缘起》《余之小说观》等小说理论作品。1908年6月,徐念慈因误服猛剂去世,几个月后,《小说林》也因失去他这个主要创刊人以及其他因素停刊,可见《小说林》受其影响之大。而黄人作为《小说林》月刊的主编,他的美学观念也受到了徐念慈的影响。徐念慈认为小说艺术具体而言具有五种美学特征:一是使艺术具有大团圆性质,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望;二是使事物具有特色,人物具有具体理想;三是能够给人以美的快感,抒发人的种种情感;四是具有形象性,能够超越现实,展开幻想;五是科学理想化,超越自然。简言之,即“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2]398。徐念慈的美学观点是对中国小说理论的进一步深入,但也正如近代文论的编者们所言:“由于学习和运用西方美学观点毕竟在初级阶段,故徐念慈……对有些美学概念的理解并不是很清晰,批评起来也不很圆熟。”[2]402小说是具有审美特性的,那么其审美特性与其本质属性之间有何联系呢?小说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们“美的欲望”吗?徐念慈的美学理念是模糊的,而黄人的贡献恰恰在于他对此进行了更具体的描述——文学审美性是小说的本质属性,它是注重审美情操和文学艺术的。黄人破旧立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也许当初《小说林》的编者们正有此考量,黄人的《〈小说林〉发刊词》与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共同发表在《小说林》第一期中,除交代《小说林》发刊的原因外,其美学理念恰恰是对徐念慈的小说理论的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三、黄人小说理论的意义
“在晚清小说理论中,黄摩西可称是继梁启超之后最重要的一家,对小说性质的论述,在当时汗牛充栋的论述小说的理论文章中,堪称鹤立鸡群,历来受到人们的很高评价。”[11]不论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研究,还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或通史研究,到了清末都不得不提及黄人,提起黄人,就不得不涉及其小说理论著作《〈小说林〉发刊词》。可见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之重要。
“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2]171“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2]172针对以往过于轻视小说而今又过于重视小说的社会倾向,黄人提出了小说的本质是文学审美性的观点,正如四川大学教授陈应鸾先生所言:“黄人的理论在当时具有补偏弊的积极意义,是一种新的认识。”[12]270小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黄人的小说理论不但对社会生活现状进行了概况,还对“小说界革命”之失败提出了见解,对当下之不足提出了要求。1898年,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1902年又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13]247等观点;随后金松岑、王锺麒、陶佑曾等人又分别发表了《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等文章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言救亡图存之重要性。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过于侧重小说的政治意义,宣扬以实用功利为目的的小说观,而忽略了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历史会让过去的人、事、文都盖棺定论。黄人的小说理论能够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站住脚跟,正是因为他秉持了正确的文学基本观点:小说的本质属性是文学审美性。《〈小说林〉发刊词》中重视小说审美属性的小说观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全新主张。黄人力排众议,“将小说的价值由政治教育的基础转到了艺术审美的基础上来”[14]20,给了时人一种新的解析。
此外,黄人的小说理论也使得中国古典小说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人们开始改变对古典小说的看法。如《〈小说林〉发刊词》中所言:“虽如《水浒传》、《石头记》之创社会主义,……余可知矣!”[2]172人们如厌恶鸩毒一般厌恶古典小说,即使《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也阐释了作家们对时政的不满,也表达了作家们对改革社会政治的迫切理想,然而它们始终被列为禁书,创作者们也被诅咒应该下地狱受以极刑。古典小说被认为无任何可取之处。尽管戊戌变法后,社会中也涌现了大量的论述小说的文本,如梁启超的《论幼学第五:说部书》,严复、夏曾佑二人合作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以及康有为的诗歌《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等(这些文本中的“说部”均指小说),他们的文学作品都对过去固有的文学体系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冲击,都强调了拿起小说作为武器的重要性。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后,小说的地位也的确得到了量与质的提升,成为了文人手中必不可少的文字武器。但这些文本都仅是针对“新小说”而言的,是更强调“新”而非“旧”的、白话的而非古典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同等待遇。而黄人提倡新小说,同样也十分注重甚至更注重中国古典小说。除《〈小说林〉发刊词》外,他还另以“蛮”为笔名创作了《小说小话》中的众多随笔,如对《西游补》《五行志》《三侠五义》等明清历史小说的评论,并分别连载于1907至1908年《小说林》第一、二、三、四、六、八、九期中。也许有些评述并不十分准确,但对明清小说史料研究来说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中国古典小说也由此揭开“面纱”,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中国古典小说的地位也随之得到提升。
的确,黄人的小说理论在晚清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但也有其片面之处。“则从事小说者,亦何必椎髻饰劳,黥容示节,而唐捐其本质乎?”[2]173由于过度追求小说的审美性,追求小说真、善、美的统一,因而黄人提出反对作家们对小说的人工雕琢,需保持小说原本的自然属性,保持小说艺术本质美的主张。但如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所言,文学活动本就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文学四要素构成,作者本身就在其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小说必须通过作家自己的创作构思加以文字编撰才能得以组合成小说作品,因此不可能把作者的思想从小说中独立出来。小说不是植物本身,可以维持其纯粹美,它必须经过作者的加工改造,是作者笔下的产物。即使是计算机时代的今天,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是经过了作者自身的整合的。未经过人整理的文字只是一堆无用的代码,是计算机随机组合的结果,也许具有可读性,具有单纯的美感,但并不可称之为作品或小说。因而,黄人的小说理论带有唯美主义的倾向,是梦幻的,难以实现的。
当然,总体而言,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中的小说理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的不过度夸大小说社会性的真知灼见以及重视中国古典小说的主张使得他能站在更高的视野上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他的小说社会理论以及小说审美理念对西方文学的引进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他的小说的本质属性是文学审美性的观点也给中国近代小说界打开了美的新世界的大门,使得人们从此开始用艺术美的眼光欣赏和看待问题。“奇人奇书,在百年孤寂之后,它所积累的名声,我们真要‘连本带利’十倍百倍地奉献给他——他在地的后人,他在天的英灵。”[15]这是台湾学者黄维樑教授在其文《不能埋没的最早中国文学史》中对黄人的文学史的评价。此评价对黄人的《〈小说林〉发刊词》同样有效。尽管黄人的《〈小说林〉发刊词》仅有不到两千字,然其蕴涵的小说理论并不单薄,其社会影响也直至今日。黄人,其小说理论值得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