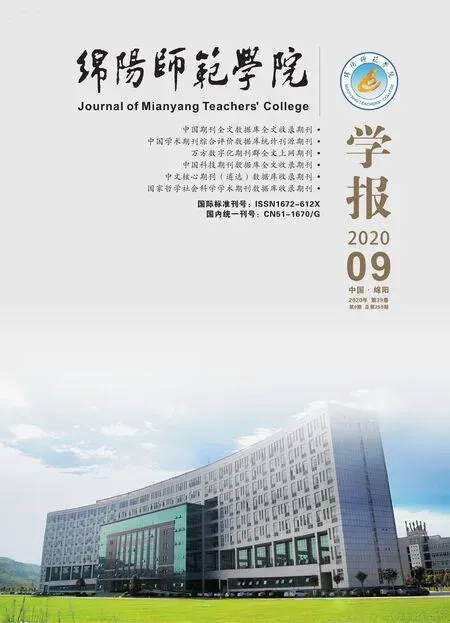次仁罗布小说的叙事道德观
陈明彬
(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叙事既是一个与美学关联密切的范畴,也是一个与道德关联密切的范畴。这里的“道德”不是指俗常伦理道德,而是指小说家的叙事道德,即小说家创作小说的观念、创作小说的理想和惯用视点。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小说观念,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小说。一个有追求且成熟的小说家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独特观察视点和叙事方式。恩格斯说:“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1]212从表现人物“做什么”到表现“怎么做”就决定了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视角、态度,也彰显着小说家的叙事道德,决定着小说家叙事的价值。说到这点,就不得不说到藏民族小说家次仁罗布。
在次仁罗布的小说里有一种对生命透切的理解和体悟,特别重视灵魂的吟咏,关注生命自我自在自由的运转。读他的小说在不经意之间会有一种深切的生命觉悟,甚或还会沉迷于他所创造的心灵世界里流连忘返,像余华说的那样: “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补充,我们的想象在逐渐膨胀。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与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且焕然一新。”[2] 133-134次仁罗布小说里那些直面自己民族生存现实的残酷写实在向我们诉说:人类生命固然是一个特别神圣的存在,但其所处的世界却是寥落的,于是一种对人之神性的期盼,对可能性生活的遐想,就这样在我们心底被唤醒。别人的人生经历也就是“我”的人生体验,正如钱穆所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3] 124故而,次仁罗布写的那些看似情节简单,语言未加多少锤炼的小说中对族人生存现状的描叙以及其舒展在族人生存现状里的生命触觉异常丰富,能触及人的灵魂深处,震撼人的心灵。就次仁罗布小说的整体审美而言,比中国当代一流作家或许有些差距,但他的小说所散发着的独特魅力甚或超过了许多一流作家,究其原因,当归功于次仁罗布小说特有的叙事道德,也就是说当归功于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观念,归功于他对小说属性独到而深刻的认知。
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不是因为作家能通过它对显在的人生、历史、宇宙作出某种审视、判断和把握,而是因为那些隐在、幽暗模糊、茫然不明的存在,被作家深耕和挖掘。米兰·昆德拉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4] 6-7显然,“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就是米兰·昆德拉眼中小说的叙事道德,小说的最高追求不是反映或再现世俗伦理道德,小说的内在规范是自己发现世界存在和本真秘密,自己解释世界。换句话说,小说就是要走出现有世界固有的伦理道德答案和现有世界固有的形象结论,去寻找那对于我们来说隐在神秘的、静默的、不被关注领域里的那些自由自在绽放的人性花朵,发现新的生活认知,这才是小说家创作小说的使命。次仁罗布的小说,犹如是对米兰·昆德拉观点的注脚。在他的小说里,感觉不到作家对现实伦理道德评判的流连和着力,走进他的小说世界,你不自觉就会站在一个超脱于俗世伦理道德的立场,在不经意间获得对生命、世界、存在的全新认知和发现。
小说走进的是存在、人性和灵魂本真深层,不是只关注小说社会学层面,在世俗道德意义上判审人心人事,它发现和守护的是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反对并超越的是简单的世俗伦理道德结论,揭示和展现的是世界无穷的可能性,这是次仁罗布小说叙事道德的一种追求。他所创作的所有小说都着意于从更高的精神视点来体察俗世、打量人生,去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因而,西藏的世俗世界,在他的笔下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通灵”的世界,是一个从俗世中来,却又沉入灵魂底层的世界。这也使他的小说走进一个浑圆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立于现世的伦理道德、得失是非、善恶穷达等问题之上,注目于深厚宽广和良善仁慈。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5]、《放生羊》[6]等就是在他的小说叙事道德支配下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
《杀手》入选“2006中国年度短篇小说”。它的故事情节简单:一个木讷、不苟言笑、有着冷峻面庞和迷离眼神的康巴汉子,历时十三载,风餐露宿,走遍整个西藏寻找杀死自己父亲的凶手玛扎,在历尽艰辛和苦难,找到那个仇人时,他却无法把这个男人和他心目中的杀父仇人画上等号。在感受到仇人温馨的家庭生活氛围,看到仇人儿子的稚嫩、可爱,仇人妻子的纯朴、善良,而仇人本身 “身子已经弯曲,头发有些花白,额头上深深浅浅地布满了皱纹”,康巴汉子内心的仇恨坚冰瞬间融化了,内心经过一番激烈挣扎后,他哭着离开了。康巴汉子的离开,不只是对仇恨的放弃,更是人性本真光辉的复归,一个真正的杀手在此得到确认。一个真正的杀手不是物质的杀手,而是精神的杀手,康巴汉子历经了长达十三年的时间才成为了一个可以杀死自己仇恨的真正杀手。这个不善言辞、沉默寡言的康巴汉子回归了他本性中的善良和宽容,并以他的善良宽容救赎了玛扎,也拯救了自己。作品的结尾,康巴汉子在梦里使得自我精神得到了救赎的原因就是他实现了自我的精神复仇。复仇曾是康巴汉子到处找寻仇人玛扎的原动力,也是他活下来的唯一理由,但最终以对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玛扎的原谅获得了自己心灵的释然。在这儿,一种源于生命深处的宽恕无不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康巴汉子的复仇行动转化为深层心灵仁慈与宽广灵魂的吟唱。次仁罗布说,他的作品描述的是藏族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情感,表现虔诚信奉佛教的藏族人在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的那种人类共有的喜怒哀乐情感和心态。藏族留存下来的文明对人类很有益处,因为那是历经千年大浪淘沙的藏族文化。作为一个藏族作家要用这种文化去照亮这个时代,就要在作品中去呈现这种文化。次仁罗布说,在他看来,文学的叙事要有勇气审视人们在无限膨胀的利字面前失去道德、牺牲、耐劳、勇气等精神,不是去躲避这些东西,而是去发现、尽力做到不流于表层,表现出藏族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去宣传藏族文化中那些修治人心、引人向善的普世价值,使人们明了除了物质之外,还有更高尚的精神。面对时代的冲击,次仁罗布基于这样的民族、人类情怀,坦然地走进藏民族心灵深处,超越俗常世界,在他的小说里进行着一种理想精神的建构。
任何世俗伦理道德的审问,任何趋同的固有结论都不是小说所要的,小说是一种发现。那么,小说创作得到的应在比世俗伦理道德更高的境界里,在通常之道德、人情、境遇的发现之中。
次仁罗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的《杀手》完全展示了俗世人间与天道的相通为一,为小说创作揭示了可能性精神空间,在描绘我们生活的世界,描绘我们生活世界的悲剧,描绘我们生活世界的“行路难”的同时,突破了那种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中国传统小说模式,又有一种特别的美学境界。他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诠释着一种属于他的叙事道德:根植于俗世人间,倾听灵魂的絮语,发现惟有小说能发现的东西。因而他的小说叙事,在注重延展个人生命触觉的同时,更注重传达次仁罗布自己或者说藏民们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感悟,既从现实取材,超脱现世人伦道德逻辑,又有现实层面的诉求且不拘泥于现实,比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认知要丰富得多,这也使得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具有非常复杂的面相。《杀手》中的杀手在“台上”举劾着玛扎杀人之恶的时候,玛扎在“躲藏”追杀的时间里无时不用对待生活的态度述说自己的善;杀手在心灵中细数玛扎污秽时,玛扎却在那细数的污秽中展示着那隐藏的美。这不仅是从更深层次上袒露灵魂的深刻,更在这深刻里,让读者看到了对慈悲的淡然,对“残酷”的无所谓,这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7]把这灵魂深刻呈现给我们的。次仁罗布的小说还达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但已是能写出“灵魂之深”的作家。其小说叙事里无所谓“残酷”,无所谓“慈悲”的境界,远离了一般善恶、一般的伦理道德,深入到灵魂底层,这就比一般小说的社会批判要深广沉厚得多。世事、人心在次仁罗布的笔下,自有一种苍凉、悲凉、凄凉和荒凉之感。但是,次仁罗布不是单纯地尖酸刻薄,他也有着藏民族文明里的那种超越美丑善恶之上的慈悲和宽容。读他的《杀手》的时候,你会和康巴汉子一起饶恕仇人玛扎,并抚爱康巴汉子那受了委屈的心灵;你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同时也有一种特别的欢喜。饶恕玛扎是因为罪恶与残酷都是悲惨的失败者,是害怕。作者以这种叙事方式给予人世间弱者以强大和愉悦,悲悯人世强者的弱小,而人世的良善和罪恶、委屈与残酷、害怕和软弱,一同被提升至高处,合而为一。这就是次仁罗布给自己确立的小说创作内在规范,他没有把他的小说叙事道德作为对固有伦理道德图式的陈述,没有被世俗伦理道德所左右,没有被俗常是非之心所牵绊,这也成就了其小说格局的深刻和宽广。然而,我们看到的一些小说却往往是一部伦理道德叙事小说、善恶叙事小说、是非叙事小说等。
当然,《杀手》这篇小说不仅是次仁罗布对小说精神的维护,更是他对自己叙事道德的诠释。这种叙事道德光线聚焦点落在“存在”上面。对于小说而言,它所发现的无不指向存在之谜,它要探究和追问的,无不是人类生活中那些悖论,人类精神中那些无解之题。在小说家创作的内在视点里,不应该有明白的、固有的结论,更没有预设结论的故事。作品精神的深广,文学能有自由挥洒的空间,都不是有预设答案的生活。小说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伟大小说探索发现的是那些过去、现在、未来可能永远也解答不了的问题。它们着力追寻的是存在本真,是时空,是生死等没有答案的命题。被是非、善恶的力量卷着走的小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真正的小说是被人物性格逻辑发展推着走的,是被人物命运卷着走的。是命运,就存在着无可奈何;是命运,就存在着两难,存在着无法抉择。故此,小说不是寻找答案的,而是发现小说惟一能发现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后的小说都开始向这个方向迈进,鲁迅一直在思考,绝望之后,人又如何在绝望里生活。伍尔芙在小说中不停地拷问,自己存在的价值在人眼里尤其是在女人眼里如何?怎样在无限的时空里去寻找。卡夫卡的小说,一直追问在现世里人的“异化”可否被解救;人性的复杂导致了人的善恶、是非的统一,难以区分,此善里有彼恶,彼恶里有此善,是与非亦如是。小说就是来探寻这些无法区分和抉择的两难问题的。
再看次仁罗布的小说《放生羊》。《放生羊》的故事情节简单清晰:年扎老人在梦中突然梦到了他那已经去世了十二年的老伴,在梦里,老伴憔悴不成人形,受尽磨难,她苦苦哀祈年扎帮她救赎罪孽,让她尽早摆脱地狱的煎熬。于是,为了让老伴快点脱离苦海,转世为人,天还没亮年扎老人就开始去转经祈祷,在庙里拜佛。在拜完佛回家路上,年扎老人看见一名肉贩子牵着四只绵羊,其中的一只绵羊咩咩咩地向老人叫着,叫声哀婉悲戚。一种怜悯之心陡然涌上年扎老人心头,于是老人买下这只绵羊放生。此后,这只放生羊在老人转经路上与老人相依相伴,人和羊之间由此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情感。绵羊陪伴着老人黎明时刻去转经,去庙里义务劳动、捐赠功德等,一起去救赎年扎老人老伴的罪孽。由于有了这只放生羊,年扎老人不再酗酒,不再有孤独寂寞之感。后来,年扎老人得了不治之症,他感觉到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但为了使这只放生羊下一世能有个好的一生,老人拖病带着放生羊去礼佛、去听活佛讲道、去买动物放生,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做慈善之事。为了能多有一些日子在人世陪陪放生羊,他带着这只放生羊一路叩拜,祷告神佛让他在人间多停留些日子……。这是一部缺乏跌宕起伏故事和扣人心弦情节的小说,但却是一部发现藏民族存在境遇和精神状态的优秀作品。小说里我们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同情、怜悯、尊重和敬畏,感受到了与存在的对话,对罪孽的反省,一种与天地同游的自由畅快,使我们这颗缺乏信仰的心灵有了一块美丽的栖息园地。简单质朴的故事就这样以别有的发现让小说有了一种对人心的振聋发聩。《放生羊》中追求的是对人物复杂灵魂世界的刻画和表现,以及对于藏民族文化性格的感悟、理解、把握和认同,因此对人的精神活动细节的深刻求取成为《放生羊》的常用手法。小说中神秘的梦兆抒写、细腻入微的心灵刻画、恬淡安详的精神面貌展示等,都在一定程度诠释着次仁罗布对精神活动方式的熟稔,对内在心灵颤动的敏感。正是这样,次仁罗布才能在简单的故事里将藏民族文化习性与宗教性格,藏民追求的坚韧与丰实,精神世界的丰蕴与多维融为一体。小说里,情节冲突被简化,而伦理、道德、人性、情感冲突则深刻化,力图以发现惟有小说发现的方式亮出藏民族的存在状态,正如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给予《放生羊》授奖词说的:“这是一个关于祈祷和救赎的故事。藏族老人在放生羊身上寄托了对亡妻的思念和回忆。他对羊的怜爱、牵挂和照顾,充实了每一天的日常作息。从此心变得温柔,梦变得香甜。小说中流淌着悲悯和温情,充盈着藏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8]
但为什么在《放生羊》中,要么是老年人,要么是上了年纪的僧侣或神殿的画师,才赞赏年扎老人的行为,却不见年轻人赞赏老人的行为呢?如果将次仁罗布的小说《放生羊》与他的小说《绿度母》[9]、《叹息灵魂》[10]进行对应性阅读,或许我们能获得答案。如年扎老人说的,“我离死亡是这么的近,每晚躺下,我都不知道翌日还能不能活着醒来。孑然一身,我没有任何的牵挂和顾虑,只等待着哪天突然死去”,“即使死亡突然降临,我也不会惧怕,在有限的生命里,我已经锻炼好了面对死亡时的心智。死亡并不能令我悲伤、恐惧,那只是一个生命流程的结束,它不是终点,魂灵还要不断地轮回投生,直到二障清净、智慧圆满”[6]。如果没有年扎老人在他饱经沧桑的人生遭际中实现了灵魂的澄澈, “想到活着该是何等的幸事,使我有机会为自己为你救赎罪孽”[6],就没有年扎老人轻松冷静对待死亡的态度。正是这样的生命感悟和理解,年扎老人才看见了放生羊所携带的生命密码,也因此在放生羊身上寄托了对生命、对老伴、对放生羊、对自己的无尽祈盼。老人对已亡老伴的思念、生命罪业的救赎等也由放生羊形象得到充分传达,放生羊无疑成了年扎老人生命觉悟的载体。年扎老人对生命的态度,又映照了生命的珍贵和可爱,也使次仁罗布的小说满溢着特别的温情,一种对现世生命的超脱,对死亡的无所谓,也凸显了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道德观。《放生羊》中那种对生命的觉悟和理解无疑是《叹息灵魂》和《绿度母》的继续。
次仁罗布凭借其敏锐的发现意识,通过对年扎生存处境与精神状态的关注,刻画出了藏民族群体的集体心理与社会性格,表现出一种温暖的、震撼人心的、强烈的存在力量。他把小说叙事建立在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精神高标上,以藏民族人性之美书写了自己对存在的体悟,激活了我们对于心灵生活的珍视情感,显示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他的小说《阿米日嘎》[11],也以这样的小说观念创作,以图对现代人类理想的心灵图式进行培植,修补现代文明悖论。小说《阿米日嘎》,讲述了然堆村有了一头美国种牛的故事:然堆村买了一头美国种牛,村里所有人都想拥有或者使用这头种牛,围绕这头种牛,村里人的各种欲望开始膨胀,贪婪、嫉妒等开始在村里蔓延。后来种牛死了,村民的内心世界又回归善和仁慈。
在次仁罗布的小说里,写了许多失败在尘埃里的小人物,但他们的卑微中都有一种倔强和庄严,其日常的欢乐和悲伤,都焕发着美丽和圣洁的光泽。如果不是次仁罗布有着超常的眼光和敏锐的生命直觉,他就看不出弱者的爱与生命的挣扎。这些小人物,他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没有严厉的批评,他们坚持以善良的心解读他们所处的世界,因而他们看到的世界是利他的、宽容的、仁慈的、纯朴的、温润的。他们以同中有异的方式成了藏民族的灵魂见证人,他们的命运年轮也铸就了次仁罗布小说的发现之旅。《放生羊》中的年扎老人,《杀手》中的康巴汉子就是这些小人物的代表。这又进一步说明次仁罗布小说叙事道德所及:包融一切的“同情心”,对世界无尽爱,将生死、悲喜合一的力量,如水般滋润万物、无所不达的善。次仁罗布小说创作观念、立场和视点都指向这些的平等和深刻,天地相通的境界。将美、善、爱合而为一的,没有恶意的生命景观,也成就了次仁罗布特别的小说世界。除了上述列举的次仁罗布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外,还有他的《雨季》[12]、《界》[13]等小说也是如此。由于人性世界的复杂,小说应重在呈现人类生活丰富的各样可能性;它不应在善恶里挣扎,而要反对单一的伦理道德结论。简言之,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打量一切人事是它的出发点,因而,它所发现的就是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