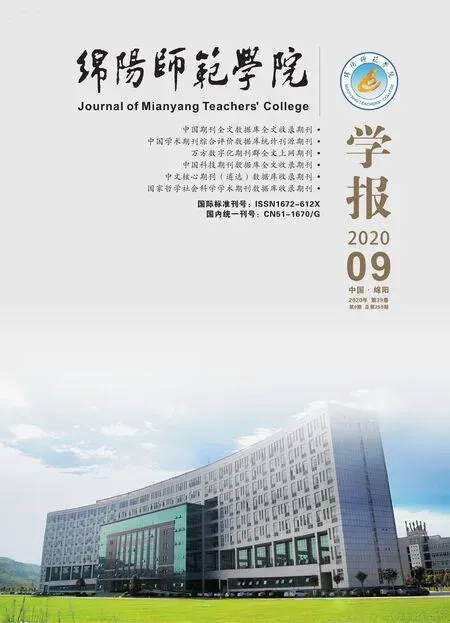旅游叙述何以成为可能:一个符号叙述学的分析
朱昊赟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
随着休闲经济时代的来临,人们对旅游休闲的需求日益高涨,旅游业态的发展、旅游形式的变化等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旅游现有的研究路径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构建视角,从自然地理层面探讨旅游目的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侧重个案分析;二是效果视角,通过引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营销学等概念,对旅游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作用进行研判。以上研究,其对象多是指旅游资源或者旅游影响,实则在某种程度上欠缺了对旅游体裁本身核心特征的思考。
旅游之所以鲜少被当作完整的叙述体裁进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旅游”叙述的文本边界存在疑虑。现如今常见的旅游叙述多是围绕具体文本体裁中的“旅游描写”展开,包括但不限于中英文导游词文本的翻译、旅游网站的宣传、文学作品的描写、影视体裁的展示、口碑分享、旅游摄影等。这些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都很明确地选择以风景作为一种叙事资源,或者描写中心”[1],承认“旅游目的地之所以能够被文学叙述所影响,主要便是由于游客自身、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作者三者之间存在情感联系,以此建构出旅游景观的意义”[2]。以上视角下的研究虽对旅游叙述价值作出肯定,但遗憾的是,其研究对象已是被再次媒介化的“旅游”衍生品,而不是对旅游对象自身。
旅游定义纷繁复杂,虽无权威定义,但也有学界共识。旅游不仅仅是指空间位置的暂时移动,而是“一种基于人自身的需要, 而产生的一种普适的人文现象”[3]。“在文学之外,叙述的范围远远广大得多”[4]3,“无论是国学热、旅游热、古迹热、奥运热、消费热、品牌热,都因叙述而获得意义关注”[4]16。旅游叙述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媒介化的文本再现,而应回归到旅游体裁自身的特征与本质上来,旅游叙述应当“透过‘内容’这一现象载体,直指‘叙事’这一问题本质”[5]。囿于传统叙事学的媒介边界问题,旅游叙述研究一度陷入僵局,直至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的出版,才让旅游摆脱“媒介化文本”的困扰,能够以独立的体裁形式纳入到叙述学的研究框架之中。
“广义的符号叙述学,即研究一切包含叙述的符号文本的叙述学”[4]416,“广义叙述学超越了门类叙事的阈限,试图为一切叙事,真实的/虚构的、不同媒介和不同时间轴的所有叙事提供一个更贴切的概念,一个有用的方法论,一套通行的术语,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广义叙述学的理论建构恰好体现了这种包容万象的能力”[6]。《广义叙述学》一书中对于媒介边界、叙述类型、主体冲突等问题展开的思考,不仅突破了以往旅游叙述研究的文本边界,树立了旅游叙述合法性的研究地位,更是对旅游作为一种独立叙述体裁核心问题的正视,是对其文本性和叙述性的升华。只是,该书尚未对旅游作为叙述文本的各环节进行详细讨论。本文通过剖析叙述底线的定义,探究旅游叙述作为独立叙述文本的体裁特征,并解答一直被学界所忽略的有关旅游叙述的特征问题。
一、旅游叙述的合法性
依据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提出的论述基础,任何叙述成立的前提条件,都需满足以下两个要求:“1.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2.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4]7判定旅游是否能够成为叙述,则需判断其是否扣合以上“叙述定义”规定的标准。因此,对旅游叙述文本性的探讨,也将从符号组合、人物参与及理解意向性的角度展开。
首先,旅游符号组合的定义要求。旅游文本与传统二维关系呈现的文本不同,它是一个立体三维的呈现。“在旅游活动中,功能单一的旅游者不能孤立地存在,他们只有进入到旅游符号的连续体中才能起作用。”[7]这个连续体被称之为区别于其他符号空间的“旅游符号空间”。郑哲为了突出旅游空间文化浸润的全面性,特意在“文化旅游的范畴中将‘环境’指代明确化,引入‘文化环境泡’概念,‘泡’是立体的、多角度的,在我们身上的映射是无死角的”[8]。如将旅游文本从多维度构建的话,则需囊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旅游的静态符号,即旅游目的地内供接收者直接面对和观赏的旅游对象。彭丹将旅游吸引力的建构翻译分为“神圣化景物的命名状态、框限和提升、奉祀秘藏、机械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9]五个步骤。前三个步骤以旅游资源的选取、旅游目的地空间范围进行框定的方式,实现旅游空间与惯常生活空间的区隔。任何旅游目的地都是“旅游规划师”设计出来的产物,只是“旅游规划师”并非指具体的个人,而是以发号施令的方式实现旅游目的地内符号组合的功能性总称。在符号叙述学视野下,“旅游规划师”实则是以区隔旅游世界和惯常生活世界为目的,以搭建起可供叙述的框架为手段的文本叙述者。通过“旅游规划师”(作为文本叙述者)的筹划,景观的布局、导览的线路、配套的设施、具体的表演活动等均以符号组合的方式落在了旅游文本之内。此时的静态旅游符号为游客的游览体验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且不以接收者的意志而出现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其二,旅游的动态符号,即游客“此时此地”的亲自参与。只有游客以投入自己的时间、体力、智力、金钱等方式,按照“旅游规划师”前期筹谋的路线、环节、导游的带队、活动等具体的游览规则进行线路游览,才可促进旅游静态符号产生意义价值。静态旅游符号是旅游的基础形式,动态旅游符号是对静态旅游符号体验过程的具体记录与结果呈现。旅游文本是静态符号与动态符号相组合的产物,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旅游文本”是以旅游规划为前提,通过旅游静态符号与动态符号相互交织而出的共同结果,单独从一个主体出发而对旅游文本进行解释与分析,必然不足以概括旅游全貌。
其次,人物参与是旅游文本概念中较为明显的一点。旅游目的地范围内的导游、游客、贩卖纪念品的商人、工作人员等,他们在旅游文本的动态化过程中以此时此地具象的“人物”方式现身,并在旅游文本中充当着不同的功能角色,共同为旅游这个文本的丰富提供着自己的力量。“文本的构成并不取决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接收方式。”[10]43叙述底线定义中对“接收者”进行强调,实则是明确了文本的“裁判人选”。此时的文本无需获得所有人的认可与接受,只要“接收者”能够接收信息并解释出意义便可使叙述成立。同样的北京之行,在爱好人文建筑的游客眼中,北京的故宫、长城、圆明园等古代建筑的风采成为北京旅游之行的意义;在爱好美食的游客眼中,全聚德的烤鸭、稻香村的点心、六必居的酱菜等传统小吃的美味则成为了北京旅游之行的意义。北京这座现代都市的客观存在没有丝毫变化,但是在不同的游客眼中却有不同解读。因此,文本完整意义的获得,实际上是文本存在的具体形态与接收者所拥有的主观感受相互“协调”的结果。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以上叙述条件的旅游才可以称得上是旅游叙述研究的范畴,旅游叙述的文本合法性问题已经界定清晰。“叙事不仅可以解释旅游的现实建构问题,同时也可以理解游客如何将旅游经验转变为有意义的经验故事。”[11]因此,对旅游叙述问题进行论证,不仅可从学理化角度厘清旅游文本的内在机理,而且也是对旅游行业发展进行的现实观照。
二、旅游叙述的演示性
当我们介入到旅游文本内部之后,对旅游文本叙述源头的讨论则接踵而来。在符号传达的过程中,叙述者是所有叙述文本产生的源头,叙述文本的接收者必须按照叙述者的所思所构进行接收。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将文本的叙述交流过程概括为“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叙者——隐含受众——真实受众”[12]14。此叙述理论多用于文学作品或电影的解释,而对于媒介类型较为丰富的旅游文本而言,解释性难免受限。
赵毅衡洞察到了媒介在当今信息传输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在《广义叙述学》中创造性地将媒介—时间向度指标纳入对叙述体裁的分类考量。通过媒介—时间向度与“再现的本体地位(纪实/虚构)”相结合,叙述体裁可概括为实在性叙述、拟实在性叙述、记录性虚构叙述、演示性虚构叙述、梦叙述、互动式叙述[13]六类。在这六类体裁中,叙述者以“人格—框架”的形式存在。“人格”“框架”分列线性两端,当文本体裁越靠近实在性叙述方向,叙述者越向“人格”一端滑动,且以显身的人格形式出现;当文本体裁越靠近互动式叙事方向,叙述者越向“框架”一端滑动,且以框架形式出现,人格化逐渐退场。
值得一说的是,叙述者不等同于真实作者,受述者不等同于真实受众,叙述者与受述者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功能性的指示符。“叙述者呈二象形态:有时候是具有人格性的个人或人物,有时候却呈现为框架,什么时候呈现何种形态取决于体裁,也取决于文本风格。”[13]因此,笔者认为旅游文本的叙述者是从做出各种旅游符号的安排、从旅游目的地的规划指令发出者的身上分化出的一个抽象人格,只是这个人格在“人格—框架”两端滑动,且更加偏向框架一端。前文所提及的“旅游规划师”其实便是此处叙述者“人格—框架”的功能显现,它为旅游文本的成立搭建了一个空间层面的框架,将旅游静态符号与日常符号做了物质层面的区隔。
演示类叙述与纪实性叙述相比,具有“展示性、即兴、观者参与以及媒介的‘非特有性’”[14]特征。“旅游与常态生活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首先一定表现为空间上距离的移动。”[15]依据上文中对旅游文本静态符号与动态符号两个层面的分析,旅游叙述文本是需要游客亲身前往旅游目的地进行“身体力行”的体验才可获取意义的文本类型。旅游文本需要游客前往、即刻获意的特征,恰好满足展示性叙述的要求。在旅游目的地内的游客,其行为言语均来源于现实生活,并非独创的新鲜事物,那么媒介的“非特有性”特征也由此展现。“游客总是在寻找或期待新鲜的、不同的事物。”[16]8游客之所以向往旅游很大程度上是对异地新鲜感的追求,这种意想不到的、充满新鲜感的事物才是游客希望体验到的。故而在媒介—时间向度下,旅游文本属于演示类叙述。
旅游文本亲自参与、现场获取的特征规约,促使游客需分化出一部分人格充当叙述者参与旅游文本的叙述,对叙述框架进行协同填充。因此,旅游文本在演示叙述的框架内,一方面可邀请游客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如扮演角色等)参与到叙述过程中,通过对旅游文本的各种静态、动态符号进行安排与设计,完成对旅游情节时间和意义向度的建构;另一方面又成功地实现被叙述的旅游世界和现实经验世界的区隔,突出旅游目的地之独特所在。
三、旅游叙述的二度区隔
“一度区隔是再现框架,把符号再现与经验世界区隔开来”[4]74,“二度区隔则是二度媒介化,与经验世界就隔开了双层距离”[4]76。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游客”是我们面对的客观实在的人:在一度区隔中,是一种身份区隔,游客成为一种需要以“体验”为媒介进行景观意义获取的特殊身份类型;在二度区隔中,他是叙述框架的协同参与者,需分裂出一部分人格对旅游文本进行填充。在此,笔者需要着重强调一点,纪实类叙述属于一度区隔,而虚构叙述必然是以二度区隔的方式与经验世界进行的分离,但并不是只要进行了二度区隔就是虚构,这一因果关系不能够混淆。
“旅游世界不是客观科学或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它是作为旅游主体从其特殊观点体验到的世界,显然是一个主观和相对的世界。旅游者对旅游世界的建构可以通过叙事或实地旅游体验的方式进行。”[17]就再现的本体地位类型而言,旅游叙述与戏剧、演出、游戏、比赛等形式同属于二度框架区隔的叙述类型,但与他们有明显不同之处。
在一度框架下,旅游文本在组合的过程中通过筛选,对静态、动态符号的呈现状态已经是被挑选出来用于展示的符号结果。旅游与戏剧、演出、游戏、比赛等形式相比,其一度框架是相似的,都是符号化的选取与再现,均与现实的经验世界进行了空间的区隔。但是在二度框架的区隔下,它们则有明显差异。在戏剧、演出的二度框架内,演员表演的人物是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并非演员个人自身;在游戏的二度框架内,游戏者充当的是游戏中的玩家角色,这个角色是游戏规则制定下的“人物”,也非游戏者自身。但是在旅游设置的二度框架之下,游客却不是虚构的角色人物,而是主体自身。
“人一旦面对他人表达意义,或对他人表达的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种相对应的身份。”[10]1游客在现实生活中和普通人一样,具有一个现实人格。“游客”被作为研究对象从人类群体中抽取出来,产生了一度区隔。只有在游客面对旅游文本、进入到旅游体验过程之后,才算进行了二度区隔。这时游客才可以分裂出一个人格,他以线路行进、观看景色、聆听讲解、拍照留念等行为推动着叙述文本的进行,协同叙述者进行框架叙述。我们当然不能说此时游客的体验是虚构的,因为游客还是自己本人,而不是扮演框架要求下的其他角色人物。因此旅游二度框架的设定并非将其指向了虚构叙述的类型,而是对其叙述框架的再次丰富。
游客才会有“虚构”的感觉呢?那便是进入到旅游文本内部以“扮演非本人的角色”之时。“当我们看到了区隔框架时,我们才知道它是虚构。虚构的意义正是为主体提供了聚合轴上的可能,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具有的其他本质和存在形态,从而丰富对自我的认知。”[18]最为典型的是迪士尼乐园、侏罗纪公园这类旅游项目,游客在其范围内可以扮演怪兽、恐龙、公主、海盗等与日常生活差异极大的角色,他们期待与体验的便是这种虚拟世界带来的新奇感。不得不说的是,游客虽然是在二度框架之内进行了各种体验,但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世界,或者说必须是回归的。当我们作为区隔框架世界内的人物状态出现时,是无法看到区隔内的这个世界是符号再现的世界,因为区隔的作用便是把框架内符号再现的世界与框架外的世界隔绝开来,此时虚构以事实的方式呈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这个道理。
四、结语
旅游叙述何以成立,是研究旅游叙述问题的起点。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符号叙述学论域内旅游与其他一般的叙述类型一样,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叙述文本对象进行分析探讨,这一结论是具有开创性的。本文正是通过符号组合、人格—框架二象以及二度区隔的讨论,尝试完成对旅游叙述合法性与特征性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