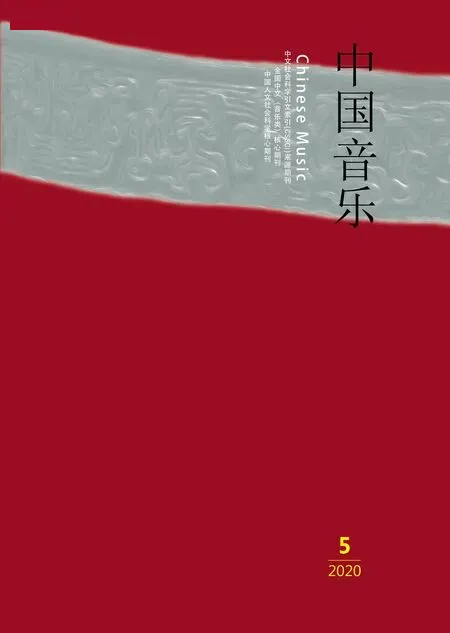“音乐作为实践”的内涵、教育方式与价值
——埃利奥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述评
○ 喻 意
20世纪末,美国音乐教育家戴维·埃利奥特(David J.Elliott,1948-)创建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对以贝内特·雷默(Bennett Reimer,1932-2013)为代表的“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进行了批判,他提出的“音乐是一种多样化的人类实践”(music as a diverse human practice)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也引发诸多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聚焦于三方面议题:“音乐作为实践”的内涵、音乐教育的方式,以及音乐教育的价值。本文就此进行详细阐述。
一、“音乐作为实践”的内涵
“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是以雷默为代表的审美哲学的重要理念,埃利奥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把音乐与音乐教育都当作一种“实践”,认为“音乐是人做的事情”,音乐教育应在实践中展开。为什么把“音乐当作实践”(music as practice/praxis)①埃利奥特早期提出“music as practice”,后期更强调“music as praxis”。,其内涵是什么,下面就此进行分析。
(一)“音乐作为实践”与技术的区别
埃利奥特对于“实践”的认识基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又有所区别。他汲取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对“实践”(praxis)与“技术”(poiesis)进行了区分。“实践”比“技术”包含的内容更多,它不仅仅是为了制作出某种结果和产品的技术或工艺,而是一种有目的性和意图性的行动。这种行动需要人们执行理性的选择。
劳力安妮·道勒夫(Lori-Anne Dolloff)认为,埃利奥特在音乐教育中对实践与技术的区分很有意义。他指出,进行这样的区分对音乐教育非常重要,否则艺术仅仅变成一门技术则失去了它的意义。他举例说道,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下,经常会听到“音乐跨域课程”(music across the curriculum)这样的字眼——就是把音乐作为一种类似教授数学、语法以及历史信息的工具,音乐变成一种发展记忆力和学习能力的方法。道勒夫认为这种方法并没有代表真正的音乐的综合性,而仅仅是一种运用音乐手段来教授数学与语言的技能,这并不能成为音乐教育。②Lori-Anne Dolloff.Elementary Music Education:Building Cultures and Practices.Edited by David J.Elliot.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92.
埃利奥特对于实践与技术的区分,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这样的界定,使得“音乐”这一概念具有了动词的属性。这为他将“音乐”与名词性质的“音乐作品”的区分打下了基础。因为在他的理论建构中,“音乐”与“音乐作品”(product)大相径庭。
(二)“音乐作为实践”不同于作品
埃利奥特的实践教育思想认为,审美音乐教育把“音乐”等同于音乐作品(product)。而他认为,“音乐”与“音乐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音乐”具有相关的四个维度,实施者(musicers)、正在做的事(musicing)、完成的事(music)及创造者做事时的完整语境(context)。
对于音乐与音乐作品的区分,维夫瑞德·格鲁恩(Wilfried Gruhn)指出,埃利奥特对音乐实践的定位充分解释了什么不能称之为“音乐教育”,音乐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对象或客体,音乐理解与语言习得的方式很接近,都是在音乐交流和活动的过程中展开。③Wilfried Gruhn.Understanding Musical Understanding.Edited by David J.Elliot.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04.麦卡锡(Marie McCarthy)对此也持赞同态度。他站在实践哲学的立场对审美音乐教育提出批评:审美音乐教育的“音乐”概念仅仅关注了音乐作品,它忽视了音乐的社会语境;它根植于西方的艺术音乐的审美,而忽视了音乐中除审美之外的其他维度;它不能适应音乐的其他功能与价值;它抹杀了音乐实践活动的本体重要性;它的理念反映出男权主义倾向。总之,他认为审美音乐哲学把“音乐作为客体”(music as object)的观点不适合研究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下的音乐意义。④Marie McCarthy.The Praxial Philosoph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Edited by David J.Elliot.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7.
埃利奥特将音乐作为行动的根本特质归结为过程性和实践性,而不是“作为结果的音乐作品”。这一主张遭到了雷默的反对。雷默认为这种“音乐”认识仅关注了行动与过程,是对音乐作品的忽略——“过程虽自始至终,结束却落在作品”,他认为埃利奥特不应该“把过程作为音乐的全部要义加以关注的立场,和(设定)关乎产品的立场针锋相对”。⑤Reimer,B.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Advancing the Vision.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3,p.48.瑞德尔(Randles)也反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这一看法。他指出,“实践”哲学对“音乐”的定位,是把音乐“作品”(works)概念消解为仅仅是“用来听的”,音乐作品的价值被严重贬低。⑥Randles,C.,Hagen,J.,Gottlied,B.A.,& Salvador,K.Eminence in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as measured in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Bulletin of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2010,pp.65-76.
将“音乐”概念等同为“音乐作品”的教育认识消解了音乐及音乐之外的更多功能与意义,埃利奥特的音乐实践观则凸显出“音乐”及其教育中包含的更广泛的内涵与维度。这样的主张着实为我们揭示出“音乐”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必然联系,以及我们不可忽视的音乐的诸多社会功能。那么雷默对埃利奥特的批评作何理解?我们在埃利奥特后期的著作中能看到更多端倪。对于音乐与音乐作品的描述,自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创建之时,就为埃利奥特理论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二者关系究竟如何树立,从起初的分开与对立,到后期的融合与包含,可想而知实践哲学思想在发展中经历的艰难历程。
(三)“音乐作为实践”的文化多样性
实践哲学提出,每一种音乐都是一种实践(Music as a human practice),许多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风格的音乐实践就构成多样化的人类实践。音乐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置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伯纳德就此认为,个体身处于一个变化的生活与音乐文化中,必须承认世界音乐的多样性与不同音乐世界的同时并存。⑦Pamela Burnard.What Matters in General Music?Edited by David J.Elliot.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70.实践哲学的另一位倡导者鲍曼也强调音乐具有文化多样性。他指出,当前的音乐教育已经脱离了音乐教育学科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以及作为人类实践的本质。⑧〔加拿大〕韦恩·鲍曼:《没有绝对正确的路径:音乐教育无法拯救真理》,《变化世界中的音乐教育》,黄琼瑶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4页。
然而,埃利奥特把音乐实践的文化属性界定为“多样性”的做法,在鲍曼看来,会导致音乐教育体验的广度和参与具体音乐的深度之间的矛盾。并且,当“指定”成为不容商量的结局和手段,严格的训练的努力就导致了严格训练的终结。实践哲学理论自身无法回答在教育中应该教诸如谁的音乐、哪一首作品及多少类音乐的问题,换句话说,“音乐作为实践”的潜在优势并不意味着它能为音乐教育工作提供所有问题的明确答案,音乐教育在本质上也许并不是多元文化的。⑨Wayne D Bowman.The limits and Grounds of Musical Praxialism.Edited by David J.Elliot.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74.
从鲍曼的批评可以看出,他不赞成埃利奥特对实践音乐教育作出的“多样性”界定,但对于实践教育应该怎样,他没有给予明确界定。对于埃利奥特的实践观,我们再看看其他学者做出的分析。
(四)“音乐作为实践”的多重含义
有关“音乐作为实践”的含义,我国学者也展开了一些讨论。覃江梅用诸多词语来描述“实践”的特点:社会性、情境性、政治性、多元性、开放性、文化性、过程性和反思性。⑩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审美与实践之维》,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李莉研究了埃利奥特的后期哲学思想,认为实践教育的内涵体现于“伦理性”和“育人性”,它与美德和“善行”(Good work)紧密相连。⑪李莉:《埃利奥特新版〈音乐教育哲学〉实践观的解读与启示》,《中国音乐》,2015年,第4期,第64-65页。管建华的研究强调了实践音乐教育的伦理性,说其是对亚里士多德道德伦理学的返本开新,并且这种伦理性是“智”和“爱智”伦理,与中国古代的“仁”和“爱人”伦理不同。不过,关于实践与技术的区分,他不给予认可。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活动区分为实践智慧与技术理论制作为后世实践哲学的二元分裂埋下了伏笔。⑫管建华:《生态社会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归复——礼乐文明实践哲学与希腊文明实践哲学的返本开新》,《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1期,第31页。除此之外,韩中岭认为,从“实践”的字面意义上看,应理解为是一种行动中的哲学,强调音乐教育在于操作实践的哲学诉求,强调动手、操作、行动中学、做中学,带有杜威时代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实践哲学,不如说是方法论。⑬韩中岭:《实践论音乐教育哲学诉求探析》,《艺术研究》,2014年,第11期,第117页。
总而言之,对于“实践”内涵的探讨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对实践特性的剖析各有深意。有些批评意见耐人寻味,这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实践哲学开阔了视角。
(五)“音乐作为实践”的复杂意蕴
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作为实践音乐哲学的理论来源,并将音乐区别于技术的论述,帕乃奥梯迪(Elvira Panaiotidi)存有不同看法:他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关于“praxis”与“poiesis”的概念溯源发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最初思想中,艺术实际上是归属于“poiesis”的范畴,艺术更像是技术(制作),而非实践。他认为,埃利奥特仅仅是借用了实践概念重新定义他的“音乐教育实践哲学”,并把“制作”等同为音乐作品的教育,把“实践”阐述为带有行动性质的音乐表演的教育。⑭Elvira Panaiotidi.The Nature of Paradigms and Paradigm Shifts in Music Education.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Review,2005,13,1,p.60.
帕乃奥梯迪的研究提醒我们,“实践”概念有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并非像当下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从表面上浮现的那样简单。在笔者看来,将“实践”定位成一种行动与活动,绝不只是教育方法转变的问题,它更是一种将“人”作为教育最终目的、将“人”作为教育主体的教育价值观的转变。埃利奥特所说的“音乐是人做的事情”旨在表达不能将“音乐”仅仅当作是“音乐作品”,或者说是一种物化的客体,而应将其看作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处于特定语境中的、人们亲身参与的生活实践。我们的音乐与我们的文化、政治、情感密不可分。之所以强调“行动”,其价值就在于此。
事实上,对于实践的多元性与文化性定位,以及实践与技术的区分,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赞同意见的。只不过,埃利奥特将“音乐”归属为亚里士多德实践知识的做法,并没有完全自圆其说。尽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音乐作为一种制作知识与技术不同,它是一种更具有目的性的行动,这一点被埃利奥特充分采纳。但是,埃利奥特创建的“实践”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终究不是一回事,二者有很大区别。⑮喻意:《埃利奥特音乐教育哲学的“实践”内涵——从“借用”亚里士多德概念谈起》,《中国音乐》,2019年,第3期,第137页。这也成为埃利奥特后期修订“实践”概念的重要缘由之一。
之所以鲍曼对“实践多样性”提出质疑,是由于鲍曼本人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反本质主义者。他持有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他认为实践性的音乐教育应具有偶然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规定音乐教学就是这样或者那样。在他那里,任务给予“实践”的规定性涵义都不被认可。这也是他与埃利奥特实践理念的根本差异。事实上,在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内部,对实践的认识就存在差异,鲍曼、里吉尔斯基和埃利奥特各有侧重。即使是埃利奥特本人,对于“实践”的诠释在后期也发生了改变。但不管怎样,不可否认的是,“音乐作为实践”给我们的音乐教育带来了重要启示:我们的教育应关注学生的主体体验,促使他们运用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在教育活动中发展潜能。
埃利奥特将音乐定位成“多样性实践”的立意,是为了提倡对不同类型音乐文化的教学和不同音乐功能的认可。将音乐理解为“人类行动”,并与“音乐作品”进行区分,充分凸显了“人”在音乐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显而易见,“音乐”不仅仅是一段物理声响声音或符号性的乐谱,那些蕴藏在创作者、聆听者或表演者个体的音乐认识与理解,也是“音乐”重要的存在方式之一。当然,一部音乐能够感染人,最终仍需要以作品的形式得以实施,音乐的“过程”与“结果”作为音乐的组成部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被孤立出来单独具有意义。雷默和瑞德尔的批评也提醒了我们,在转换不同的哲学视角看问题时,切忌非此即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行动中的音乐教育
埃利奥特所说的“音乐是一种实践”,这里的“实践”意指一种行动。正如他所说,音乐是一种“人类有目的的行动”(a particular form of intentional human action)。一直以来,审美音乐教育都非常重视音乐聆听教学,主张通过对音乐作品的欣赏与审美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力,而埃利奥特认为以音乐表演为主要形式的“做音乐”(musicing,music making的缩写)是教学中心。
(一)“做音乐”中的行与思
“做音乐”是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核心概念。埃利奥特认为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实践,应该在做音乐中进行教学。做音乐最能体现“音乐不是作品而是一种人类行动”的理念。那么,做音乐行为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埃利奥特在他的音乐实践哲学中,强调“行为中认识”(knowing-in-action)、“行为中思维”(thinking-in-action)以及“过程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的重要性。他认为音乐与其他活动一样,其中思维与行为不可分,思维与行为在音乐行为中的发生时间不是一前一后的关系,而是同时进行。
鲍曼认为在行动中思考,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本质,从这个层次上讲,埃利奥特对于审美的批评很公正,值得理解,且很有意义。⑯同注⑨,pp.69-70;66-69.马丁(Jeffrey Martin)也认为,在“审美教育”的观念里,作曲与即兴这类音乐行为仅仅是主观的“右脑”加工过程,缺乏批判性反思或批判性话语。这种旧思想(审美教育)并不能成为艺术进课堂的理由,相反,它消除了学习艺术的可能性。感觉和概念的极性分离也站不住脚,情感的对象不能被独立的定性为个体对现象的回应。这就好比“用脚去思考”,它是那种并非在行动之后而是与行动同时发生的思维。他举例,在比赛中一个足球运动员不能(或没有)停下来去思考他怎样踢球或者是否应该踢这个球;相反,这种思维和决策的做出与正在进行的行动同时进行。它与音乐实践行动中思维决定创作一样,作曲与即兴就是很好的反思性实践形式。在他看来,埃利奥特的行动与思维的联系就解决了这个问题。⑰Jeffrey Martin.Composing and Improvising.Edited by David J.Elliot.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66.
库普曼(Constantijn Koopman)研究了埃利奥特设定的音乐知识类型(过程性知识、正式知识、非正式知识、印象知识)。他认为,教育哲学始终致力于为学校提供一套形式的知识系统,并在技术学习上为学生带来收获。但在这些形式的知识诉求与有限的技术学习之间,很难分清源流。而埃利奥特的行动素养包含复杂的音乐知识形式,其“行动中思维”的理念取代了狭隘的技术训练式的教学观,为音乐教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然而,他认为埃利奥特把“行动中思考”“行为中认识”以及“过程性知识”这些概念放置于中心位置,其“音乐”被界定为一种本质性的认知活动,并没有为我们建立起反思音乐的根基与方式。⑱Constantijn Koopman.The Nature of Music and Musical Works.Edited by David J.Elliot.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81-82.
处理行动与思维关系的统一性,是实践音乐教育的核心议题,也以此成为其批评审美音乐教育的重要支撑。鲍曼、马丁和库普曼的论述从不同角度都对埃利奥特的立论给予了支持。马丁用足球运动员的生动实例说明了人的思维与行动的不可分性,库普曼认为埃利奥特提出的音乐行动素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拓宽了音乐教育的视野。只不过,他批评埃利奥特的“音乐”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活动”,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并不合理。埃利奥特哲学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念,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汲取了亚氏实践的行动性。其“音乐作为实践”的出发点恰恰是将音乐理解为一种行动,其主张“行动中思维”的目的是为了强调思维与行动的同时发生,并非落脚于“思维”,所以并非像库普曼所说的“本质是一种认知活动”。
(二)“做音乐”与听音乐
埃利奥特认为音乐是一个多维的人类现象,包括两种有目的的相互交织的人类活动:“做音乐”与听音乐。其早期思想中“做音乐”主要包括即兴、作曲、改编、表演和指挥五种音乐活动。由于音乐表演被认为是最具典型性的“做音乐”,埃利奥特不惜笔墨论述音乐表演的优越性。埃利奥特对音乐表演的特别重视及其对音乐聆听的“轻视”遭到一些批评。
鲍曼指出,“理想主义”哲学(审美哲学)与音乐商品化的过程使得人们忽视了音乐表演。但是,实践哲学理论意味着音乐实践活动的思维性本质,但它并没有表明某一种实践活动本身优于其他活动。因此,他认为埃利奥特把音乐表演凌驾于其他音乐教学之上的定位与实践主义哲学本身并没有必然关联。⑲同注⑨,pp.69-70;66-69.。当然,他也认可重视音乐表演对于理解音乐实践是至关重要的。
库普曼不赞同埃利奥特把聆听音乐,尤其是唱片音乐,仅仅归结为一种被动的音乐体验。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忽略了音乐发烧友的实践,发烧友听音乐并非像埃利奥特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全身心投入到音乐之中。关于音乐聆听与音乐表演实践活动在音乐教育中谁更具有优势的问题上,他反倒认为聆听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作为听众更容易掌握各种音乐风格,也会更加全神贯注。而表演者常常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了技巧上,影响了他们的全身心的音乐体验。⑳同注⑱,p.87.
里基尔斯基认为埃利奥特将聆听能力依托于表演能力,但许多有才智、有辨别能力的人具有优秀的鉴赏与品味,甚至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生产/创作音乐的人的数量。例如,99%的芭蕾热爱者,他们自己都从未上过芭蕾课,更不要说让他们精通全部芭蕾剧目。他们几乎没有直接的“知道过程”(know how)或对芭蕾有技术性的知识,却拥有实践训练的经验,这些经验来源于专注的听赏行为。
埃利奥特对于音乐聆听的“冷落”引起我国学者王玲的不满。她认为,埃里奥特之所以如此强调做乐和表演,暗示了聆听是消极、疏离、冷漠、没有完全参与的活动。她认为,所谓的“客体”并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我们参与构造出来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我们参与构造出来的。聆听的活动也是一种践行活动,其参与感并不会比实际操作者更低。
显然,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将“做音乐”放置于教学中心的理念,引来的批评最多也比较强烈。那么,埃利奥特为什么会持有这样的认识?这源于他对实践特性的认识。他之所以给予“做音乐”突出地位,是因为他强调语言知识(verbal knowledge)与过程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的区别。在音乐学习中,过程知识是主导知识,而“做音乐”(musicing)的本质是过程性的,做乐者(musicer)的艺术行为最能体现实践者的姿态。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富有智慧、称职的聆听音乐的能力,取决于通过智慧的或称职的音乐表演才能发展出的认知能力和洞察能力。㉑David J.Elliott.Music Matters: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03-104.从埃利奥特将聆听能力与“做音乐”进行的这一关联中可以看出,他早期的思想确实呈现出“做音乐”优于听音乐的倾向。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实践理论可否支持不需“做音乐”活动而是通过反复听音乐来提高音乐聆听能力的观点?不带有表演性质的聆听有没有意义?事实上,埃利奥特后期的思想已对此做出了解答。他后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对做音乐与听音乐进行了重新思考,调整了对音乐聆听的态度,“聆听”(listening)也成为“音乐活动”㉒在对埃利奥特第二版《新音乐教育哲学》的翻译中,刘沛将“musicing”译为“音乐活动”,体现出埃利奥特后期对“musicing”概念进行扩展后的内涵。(musicing)的一个部分。
三、音乐教育的价值
我们对音乐教育哲学问题的探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我们学习音乐、教授音乐寻找意义与根据。那么,在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中,音乐教育的目的与价值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埃利奥特哲学思想的重中之重,“自我发展”“音乐素养”等概念均被着重阐述,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一)自我发展、自我认知与自尊
对于音乐教育价值的阐释,埃利奥特引用了心理学家奇特森科米哈伊的“最佳体验”(optimal experience)理论。他认为,在音乐活动中设置与一定音乐挑战相适应的音乐任务,伴随这样的音乐活动,学生感受到的是“音乐享乐”(enjoyment)和“福流”(flow),并获得最佳体验,这能够促进他们的“自我发展”(self-growth)和“自我认知”(selfknowing),这也是音乐教育的目的所在。㉓同注㉑,p.129.
沃尔德(Sheila C.Woodward)就此指出,早期儿童音乐体验发生的语境至关重要,教师的干预、平衡挑战与技能,可促使儿童获得音乐关注与自我发展。对于这点,他与埃利奥特的理念是一致的。教师应该为孩子们创造出合适的学习环境,远离那些无创造性的记忆与重复,为了孩子们从出生开始获得最佳音乐体验,获得情感、身体、自我认识能力的发展提供需求。㉔Sheila C.Woodward.Critical Matters in Early Childhood Music Education.Edited by David J.Elliot.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53.然而,持反对意见的托尔(Patricia O’Toole)认为,埃利奥特的“最佳体验”价值论,把音乐价值缩减为一种单一的“认知体验”(cognition experience),仅关注个体的“脑认知”(brain-cognition),这样的结果将是,教育一位地追求技术至上。㉕O’Toole,P.Why don’t I feel included in these Musics,or,Matters? Edited by David J.Elliot.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97-307.
库普曼提出以下质疑:(1)“自我发展”与“自我认知”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逻辑关联。自我发展可能是人们参与实践后,进行自我意识反思的结果,而不是行动期间就自动发生。进一步来说,“自我发展”既可以从不成功的行动,也可以从成功的行动中获得。因此,这与奇克森特米哈伊的“挑战”之间的关联不大。(2)埃利奥特的价值理论只适用于限制性的实践,有些音乐实践并不具有明显的挑战性质。例如聆听音乐、合唱表演、器乐表演——这些活动并不都伴随显著的音乐能力评估。不过,库普曼也说道,埃利奥特的实践哲学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包括音乐的概念、价值、行动等哲学概念,为西方音乐教育实践哲学创设了良好的开端。㉖同注⑱,pp.83-84.
王玲认为,虽然埃利奥特并没有把音乐用作功利目的,但他的自我发展和内在之益体现的是一种征服感:“我是能做好这件事的人。”音乐本身并不是令学习者体会满足和愉悦之物,而是征服一段音乐的“成功”让学习者有一种证明自我的快感。埃里奥特的这种自我成就式的音乐教学观念,不仅未能体现出艺术于人的真正益处,还会将人导向类似于功利追求的错误价值之中。她还指出,在埃里奥特看来,音乐素养是由知识构建起来的,提高音乐素养和品味即是为了学习音乐知识及其文化背景。但是,虽然音乐鉴赏需要一定的知识学习,但知识并不等同于品味。品味体现了一个人综合的心灵世界。如果艺术落到一种知识和技艺的层面,随之而生的一个推论就是:不同艺术素养之间难以相通。㉗王玲:《试评埃里奥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黄钟》,2013年,第3期,第126-129页。
从上可知,沃尔德主张在音乐教育中关注自我发展,教师应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以促使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埃利奥特的“最佳体验”正是借鉴了奇克森特米哈伊的创造力系统观——在教师、学生与创造力行为中,达成“福流”体验(埃利奥特所说的最佳体验)从而促进创造力发展。“最佳体验”确实对学生的创造力培养非常有利。至于托尔将这种体验界定为仅仅是“认知体验”,认为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技术至上,笔者看来,强调认知发展与导致教育的技术至上,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关联。
在库普曼对埃利奥特的批评中,笔者认为有些批评是合理的,比如对于“自我发展”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必然关联的否定。但有些批评言过其实,比如说聆听、合唱、表演等活动中不存在挑战性质,所以无法包括在埃利奥特所说的实践之中,这显然有失公允。事实上,聆听、合唱及器乐表演这些音乐活动,都需要复合型音乐能力,演出作品难度的增加都必须具备与之相应更高的音乐能力。
王玲对埃利奥特的批评集中于两点:(1)自我发展的价值设定不是有益的价值;(2)音乐素养的构建不过是技能与知识。对于第一点批评,王玲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埃利奥特早期的价值观确实比较关注成功感和享乐感;但她的第二点批评并不完全合理。她对音乐素养的认识并不充分,仅从字面上将音乐素养等同于“knowledge”,从而将音乐素养判断为仅仅是知识与技能,这并不符合埃利奥特音乐素养的真实构成与内涵。㉘喻意:《“福流”体验中发展自我——论埃利奥特早期实践音乐教育目的观》,《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152-154页。事实上,埃利奥特的“音乐素养”概念远远大于字面意义上的“知识”,它包括经验的、直觉的、过程的等多种音乐认识与思维。
(二)音乐教育为了“音乐素养”
埃利奥特的教学旨在音乐挑战的情境下,运用音乐问题解决能力一步步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musicianship)。这使学生得以从初学者、入门者变为精通者、熟练者及专家,而埃利奥特非常看重这种专业性质的音乐学习与实践。对此里基尔斯基认为,这种从新手一步步到达专业的演奏级别(新手、进阶学习者、能够掌握一定技巧的学习者,最后到专业级别),是为“专业艺术家表演者”(music expert or artist)培养模式设定的,其结果是,音乐实践作为外行、业余、娱乐业中的普遍性及其社会性都无法得到与它丰富性相匹配的关注度。一个广泛被接受的音乐实践课程,一般至少能令学生以业余的身份投入到音乐行动中去。如果埃利奥特将课程只作用于专业受训者的实践,而不是服务一般听众、业余表演者和创作者的活动,那么就音乐和音乐教育而言,其价值非常有限。他认为不同的实践造就不同的音乐,关键要考虑其中不同的意向、情景、期待和观众的参与度。㉙Thomas A.Regelski.Accounting for All Praxis: An Essay Critique of David Elliott’s Music Matters.Bulletin of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2000,111,pp.72-74.
里基尔斯基与埃利奥特的分歧体现在对音乐教育的音乐性价值与生活性价值的取舍中,埃利奥特比较注重前者,而里基尔斯基更看重后者。我们知道,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正是由于注重音乐内在价值而遭到了实践哲学的反对,这就不难解释埃利奥特对“音乐素养”的强调被有些学者称作是审美理念的变种。但笔者认为,对音乐素养卓越性的追求,并不与实践音乐教育的其他价值相矛盾,这取决于两点:一方面在于其强调的音乐素养的构成成分;另一方面在于实践音乐教育价值的主要诉求。事实上,里基尔斯基与埃利奥特的冲突背后有着更深层次哲学根源的差异。二者虽然都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但里基尔斯基尤为信奉实用主义哲学观,因此他衡量音乐及音乐教育好坏的标准更加关注于实用性和效用性。从这种层面上讲,他的实践教育观非常看重教育的外在功能,不免呈现出教育的工具主义倾向。尽管如此,他将目光放置于普通大众的音乐教育,这为改变当下部分地区局限于精英教育的现状提供了良好契机。
综上所述,已有对埃利奥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实践音乐教育中“音乐作为实践”的内涵、“做音乐”行动理念,以及音乐教育的“自我发展”价值等内容。这其中,有的对他的实践思想给予支持与肯定,有的对他的部分观点提出质疑或反对。支持的声音大多聚焦于其“音乐作为实践”的复合型概念、“实践”与“技术”的区分、“行动中思维”的音乐活动观、音乐与文化的联系、教育的多元价值等内容;遭到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其赋予音乐表演的核心地位、对音乐作品的忽略、精英主义的音乐教育理念、音乐教育的价值设定。在这些质疑声中,有些具有合理性,有些值得商榷。事实上,埃利奥特的实践教育思想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后期关于实践、音乐实践、音乐教育的方式和价值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鲍曼、库普曼、里基尔斯基等人对埃利奥特的影响,以及他逐渐扩展与丰富的“大实践”概念。
实践音乐哲学在音乐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反思当下音乐教育问题的浪潮。这对反思我国当前音乐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具有警示意义。由于20世纪西方教育模式的渗透及影响,“技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现象在我国音乐教育中普遍存在,传统教育中的多维“音乐”概念需要被重拾与唤醒,音乐的灵魂和精神价值应给予重塑与重视,音乐教育的目的与价值该如何定位,亟待我国音乐教育工作者进行深入思考。埃利奥特实践哲学关于“音乐”概念、音乐教育的方式方法和音乐教育的价值很多特定的实践内涵,有助于我们认清审美教育哲学的局限性,也促使我国音乐教育深入理解音乐与审美、与实践、与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及音乐教育与人们社会生活的联系,这些都为我们的音乐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