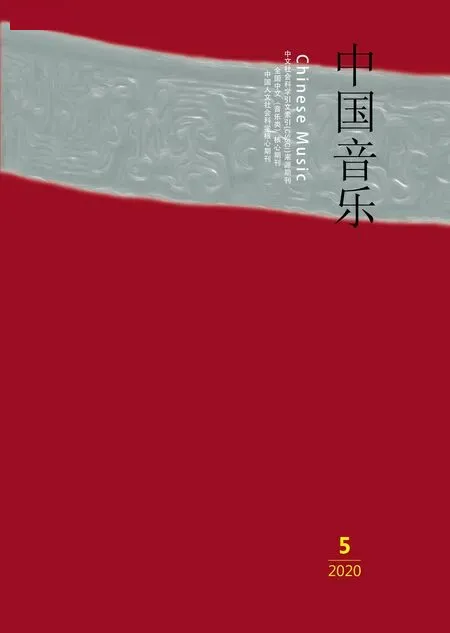仪式语境中的凉山彝族毕摩音乐概念及其内涵
○ 李自强
引论:基于研究现状的思考
凉山彝族毕摩音乐是毕摩在民间信仰仪式中操持的一种仪式音乐。笔者通过中国知网、超星、独秀等学术网站,对彝族毕摩音乐、彝族尼木措毕祭祖仪式音乐①隶属于毕摩音乐分类之一,下文详述。的研究成果进行检索。得出以下检索结果:从时间上来看,对凉山州彝族毕摩音乐的研究肇始于2008年;从文献篇目来看,有关凉山州彝族毕摩音乐、尼木措毕仪式音乐研究的论文仅有十余篇,如《凉山彝族巫术乐舞考察与研究》②杨曦帆:《凉山彝族巫术乐舞考察与研究》,《中国音乐》,2009年,第1期,第102-106页。《凉山彝族毕摩仪式音乐形态研究》③杜梦甦:《凉山彝族毕摩仪式音乐形态研究》,《歌海》,2012年,第5期,第11-15;11-15页。《论凉山彝族原生态音乐“毕摩”的音乐文化特性》④黄志勇、魏玉梅:《论凉山彝族原生态音乐“毕摩”的音乐文化特性》,《音乐时空》,2013年,第3期,第53-54;53-54页。《四川彝族原始宗教音乐研究》⑤杜梦甦:《四川彝族原始宗教音乐研究》,《音乐探索》,2015年,第3期,第17-30页。《凉山彝族毕摩祭祀仪式音乐研究》⑥袁艳:《凉山彝族毕摩祭祀仪式音乐研究》,《艺术评鉴》,2017年,第21期,第33-35页。等。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其一,对毕摩音乐的介绍性文章具有概述性特征。如《论凉山彝族原生态音乐“毕摩”的音乐文化特性》一文,对凉山彝族民间信仰仪式操作者——毕摩及苏尼进行论述,探讨两者主持仪式的差别,阐述了毕摩主持仪式的核心——尼木措毕仪式经文及音乐。该文以社会学的视角切入,详述毕摩与苏尼的分工及其社会地位,对尼木措毕仪式音乐进行了总体概述。其二,对其进行音乐形态学的研究。在《凉山彝族毕摩仪式音乐形态研究》一文中,作者从音乐形态的角度将凉山彝族毕摩音乐分为咏唱式、吟唱式、诵唱式、综合式四大类,同时,基于尊重“异文化”的理念,在记谱时采用了彝语和国际音标并用的方式。《四川彝族原始宗教音乐研究》一文,作者采用语言学学科方法对彝族宗教音乐进行研究,从彝语调值、发音等方面看彝族语音“元音”“辅音”如何与音乐紧密结合,同时用具体的案例进行佐证。
以凉山州尼木措毕祭祖仪式音乐为论点进行研究的论文有:《四川小凉山彝族“列目丛毕”的毕摩经诵研究——以马边彝族自治县仪式为例》⑦周翔:《四川小凉山彝族“列目丛毕”的毕摩经诵研究——以马边彝族自治县仪式为例》,《大音》,2012年,第1期,第143-167页。《四川越西彝族“尼姆撮毕”信仰、仪式和音声三重关系之探析》⑧路菊芳:《四川越西彝族“尼姆撮毕”信仰、仪式和音声三重关系之探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136-144页。《马边彝族尼姆撮毕仪式音乐的多声形态》⑨路菊芳:《马边彝族尼姆撮毕仪式音乐的多声形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75-90页。《小凉山彝族传统丧葬仪式及音乐探究》⑩路菊芳:《小凉山彝族传统丧葬仪式及音乐探究》,《艺术评鉴》,2017年,第9期,第30-33页。等。其中,文章《四川小凉山彝族“列目丛毕”的毕摩经诵研究——以马边彝族自治县仪式为例》是第一篇以“尼木措毕音乐”为论题的研究成果⑪音乐学界对于“尼木措毕”的彝语音译有:列目从毕、尼姆撮毕等,笔者在写作时统一使用“尼木措毕”。,作者以民族音乐学的方法、理念对马边县列目从毕仪式音乐进行研究,从“近语言——远音乐”经诵音声的说唱形态、“近音乐——远语言”经诵音声的音乐形态来解析尼木措毕仪式的音声行为。在《四川越西彝族“尼姆撮毕”信仰、仪式和音声三重关系之探析》一文中,作者对尼木措毕仪式的考察内容进行描述,同时,借鉴杨明康在《中国民歌及乡土社会》一书中将宗教文化产品分为“基础层次”和“外围层次”的理念,将尼木措毕仪式音声分为“核心层次”与“外围层次”。“核心层次”部分主要论述仪式的音乐分类及音乐形态特征,“外围层次”部分将“器乐声音”与“非乐音形态的声音”纳入其中并作出相关解析。最后,作者根据薛艺兵在《神圣的娱乐》⑫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将仪式音乐放入“三重认知”的理念,对信仰、仪式、音乐进行探讨,通过对越西县彝族祭祖仪式音声的研究来探讨“三重认知”理念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文章《马边彝族尼姆撮毕仪式音乐的多声形态》,作者将尼木措毕仪式音乐分为“节奏性诵读类”和“旋律性诵唱类”两种,这种“二分法”是继上文《凉山彝族毕摩仪式音乐形态研究》后出现的另一种分类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研究者们所采用的视域、理念、方法各异,但主要切入点均为对音乐本体形态的分析与分类。对于毕摩音乐或尼木措毕音乐的局内概念、术语并未引申讨论,然而这些局内的概念、术语表达却体现出局内人对其音乐的认知、观念及深层内涵的把握。因此,笔者希望以以上研究成果为基础来反思局内的音乐概念、术语表述与局外的观察及书写,从而对仪式语境中毕摩音乐的概念、术语进行局内关怀,让局内人发声,进而为局外者对这一音乐事象进行表述、书写、研究提供再思考。
一、初入田野:局内与局外的表述
“现代学术界不断把传统音乐的‘自表述’,通过‘他转述’来转换成共享概念。民间术语、地方性概念由此亦获得了公共知识的意义和功能,参与到将其把它的所指不断展示给公众领域的认知活动中。然而,传统口传世界与现代书写的世界的根本不同,使原生性‘自表述’与现代‘他转述’之间形成了思维方式的很大区别。而要真正理解原生性‘自表述’,必须回归到它的使用群体和使用语境当中,把这种表述放置在与它勾连的表演当中,把表演放置在它赖以生存的语境当中,通过术语与概念、行为与语境的观察,理解传统音乐术语对持有者的意义。”⑬博特乐图:《“灵动”的术语——蒙古族传统音乐中的概念表述及其转述问题》,《音乐艺术》,2018年,第2期,第86-93页。所以当研究者在面对局内者所持的音乐事象时,需要思考以何种方式、视角去面对自己研究的音乐事象,以何种方式进行田野观察的文本性表述、转述及阐释。针对上述问题,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学科呈现了诸多学者的经验与成果。如沈洽的《论“双视角”研究法及其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践和意义》⑭沈洽:《论“双视角”研究法及其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践和意义》,《中国音乐学》,1998年,第2期,第65-85页。和萧梅的文章《仪式中的制度性音声属性》⑮参见萧梅:《仪式中的制度性音声属性》,《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第32-43页。,作者指出制度性音声属性是继制度性展演探讨外的另一个“听”见并理解仪式的途径。曹本冶在《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的研究》⑯参见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音乐艺术》,2006年,第3期,第83-102页。作者在文中指出:三个“两级变量”即:近——远、内——外、定——活。一文中,从思想——行为的研究角度出发,给予传统音乐的研究以新的见解,并提出三个“两级变量”的方法来理解仪式音乐。这些理论与方法是前辈学者基于毕生田野经验所总结出的经典范式。
诚然,研究者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音乐事象时,无法第一时间身处音乐事象的语境中,参与其表演,观察其行为,也就不能更好地感知、理解音乐事象背后的意义所在。兴趣使然,笔者于2016年12月只身来到四川省凉山州的腹心地区美姑县,该县也被称为“毕摩之乡”⑰彝族一代毕摩宗师阿苏拉则出生于此,并建立起“阿苏拉则藏经阁”。。在美姑县佐戈依达乡依曲古村,笔者找到了毕摩音乐国家级传承人曲比拉火⑱曲比拉火(1977- ),男,彝族,系杨古苏布毕摩流派传人,毕摩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了其操作的一场平安仪式。基于对毕摩音乐现有研究文献的研读,笔者在整场仪式过程中将所有精力集中在曲比拉火的演唱上,关注毕摩音乐的旋律音高、旋律走向、曲体结构、节奏等音乐形态方面的内容,却忽略了仪式中的太多细节及与其相关的因素。
田野中,笔者带着毕摩音乐相关研究成果,在仪式中聆听曲比拉火的表述,很少听到现有研究中所提及的“毕摩音乐”“嘎基毕”“嘎哈毕”“尼木措毕音乐”等一系列被学者们“表述”“转述”的概念。同时,笔者在后续十余次田野考察中对毕摩音乐获得了更多的体验与感知,从其演唱音乐的形态学(西方式的分析法则)方面去试图印证已有成果的总结,当然也获得诸多的体会,如音乐学界对于毕摩音乐形态学的分析及以旋律与演唱方式为切入点的分类法,“四分法”与“两分法”的分类可以清晰明辨。诚然,以西方音乐分析的角度去研究毕摩音乐的分类也是一种视角,毕竟这种视角有其重要的影响与价值所在。至少在笔者的田野中关于毕摩音乐的分类,若以音乐形态学为视角,是可以得出上述分类法则和观点的。
然而真正让笔者对主位(毕摩)表述感兴趣并进一步在田野中追问曲比拉火所持的音乐概念、分类及表述方式,是基于一场大型的尼木措毕祭祖仪式活动。随着与曲比拉火、曲比尔日等杨古苏布流派毕摩传人不断地交流,参与他们所主持的各类仪式,笔者对毕摩音乐的个人体会、感知逐渐加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客位表述概念也逐渐显露出“真身”。这引发了笔者一系列的思考:局内的概念表述背后有何种意义?是否能体现他们的音乐观念?局内的分类依据何在?通过局内人的概念表述与分类是否能对客位的转述或者表达、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这种视角方法是否能够更好地符合“文化价值相对论”的理念与规约?
以上是笔者初入田野据局内表述而引发的思考。接下来笔者将对毕摩音乐的概念、术语、分类进行一次局内的观照,看局内人的音乐观念。
二、仪式语境中的表述:毕摩音乐概念及分类
当今学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毕摩以及毕摩音乐的概念解析,都有着其独到的见解。对于毕摩的定义,曲比阿果在文章《凉山彝族毕摩卡巴调查研究》⑲曲比阿果:《凉山彝族毕摩卡巴调查研究》,《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87-192页。中指出:“毕摩是凉山彝族社会中的神职人员,是凉山彝族宗教仪式的主持者,承担了日常中与祈福、消灾、除晦、度亡、祭祖有关的仪式。”而在《浅谈彝族毕摩的由来及其地位》⑳曲木尔足:《浅谈彝族毕摩的由来及其地位》,《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91-93页。一文中,作者指出:“彝族彝师毕摩具有多重身份,从宗教职能来看他是祭司,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巴莫阿依则在文章《中国凉山彝族社会中的毕摩》中指出:“毕摩是以念诵经文的形式调解人与神鬼关系的宗教职业者。”㉑巴莫阿依:《中国凉山彝族社会中的毕摩》,《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第1-10;1-10页。
“从毕摩一词的词义入手,‘毕摩’(bimox)的‘毕’意味念诵,得名于毕摩做仪式的方式——‘毕’,即念诵经文。‘毕’也引申为念经为特点的仪式活动……,‘毕摩’就是指从事念诵经文之仪式活动的人。”㉒巴莫阿依:《中国凉山彝族社会中的毕摩》,《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第1-10;1-10页。基于彝族学者对毕摩的“自表述”,我们可以得知,“神职人员”“人神之间的中介”“宗教职业者”等不同的称谓,都来自于彝族学者对毕摩文化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这基于研究者现场作业(field work)时的仪式场域,这种解读当然不能脱离毕摩所持的仪式,若脱离仪式语境,对于毕摩的解读或多或少会有所缺失。
对于毕摩音乐概念的定义,音乐学界大多以毕摩主持仪式时所使用(念诵、唱诵等方式)音乐的形态来定义。以下笔者将以曲比拉火等毕摩的“自表述”为视角,对毕摩音乐的概念、术语及其分类进行梳理,看其在仪式语境中如何表述该音乐及其分类法则。
彝语“毕抚”,我们所熟知的“毕摩音乐”就是通过该词汇翻译而来,但是“毕摩音乐”这一局外转述概念并不能完全表达局内人(毕摩)在仪式中所表述的“毕抚”的含义。彝语“毕”,意味念诵,也是毕摩做仪式的方式之一,而“抚”一词,却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嗓子;其二,音调。笔者通过三年田野调查发现,当曲比拉火等毕摩在仪式场域中进行交流时,他们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毕摩音乐”一词,转而使用“毕抚”,这与他在接受媒体、政府、研究者等采访时所使用的称谓不同。笔者之所以认为不同,是由于“毕抚”一词的“抚”有音调之意。众所周知,音调只是音乐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具有差别。阿萨菲耶夫曾指出:“要使音调化过程称为音乐而不是语言,须经历什么样的途径呢?要么与语言音调融合,成为一体,成为富有表现力的有声词语的有节奏的音调,而且长期以来以稳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固定在数千年的实践之中,这是一种具有新的素质的东西。要么不通过词语,采用工具主义方式去感受人的姿势与动作组成的‘默音调’(包括手语),使其成为‘音乐化语言’或‘音乐化音调’。然而,这些都远远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所谓音乐。”㉓〔苏联〕阿萨菲耶夫:《音调论——〈音乐形式即过程〉第二部》,曾祥华译,《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9年,第4期,第59-61页。当然用阿萨菲耶夫所谓的“我们概念中的所谓音乐”来概括我们今天在仪式中所观察到的仪式声响或声音显然是不够的。曹本冶先生在其文《思想~行为:仪式中的音声研究》中提及:“80年代在香港的道教仪式中意识到‘音乐’一词来概括仪式中所听见的声音是不够的。”㉔同注⑯。曹本冶在其文《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一文指出:“笔者在80年代研究香港的道教科仪活动之时就开始体会到,用‘音乐’来概括道教科仪展现时所有的声音是不够的,因此萌发用‘音声’的概念来弥补‘音乐’的局限。”如果从今天的研究来看,毕摩仪式所展现的音乐或者音声置于仪式境域中,阿萨菲耶夫所说的“默音调”则容易被理解。
随着音乐边界的扩大,在文化自省、审视与思考的今天,“毕抚”一词显然已被学者们认为是音乐或者音声去研究。笔者在田野中询问曲比拉火等毕摩,“毕抚”是否是音乐这一问题,曲比拉火的表述是:“我们毕摩做仪式会用很多音调,以前我们都说‘毕抚’,至于是不是音乐,我没有去想过,在申报非遗时就用毕摩音乐这个说法了,现在我们在接受采访时大家都说‘毕摩音乐’这个词,我们也就用了。”㉕根据曲比拉火口述整理而来,时间为2018年3月。可以看出,毕摩对于他们所操持的音乐有其自身的观念、理解及意义,因为“毕抚”一词可直译为:嗓子念诵,念诵者当然是毕摩,所以应该对他们予以局内观照,去理解他们在仪式语境中的“毕抚”与今天“毕摩音乐”的内涵与外延。
仪式音乐依附仪式活动。“毕抚”是毕摩对毕摩仪式所用音乐的统称。凉山州彝族毕摩举行的仪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嘎基毕(路下方)仪式;一种是“嘎哈毕”(路上方)仪式,两类仪式所用的音乐构成毕摩音乐。兹下将对这两类不同仪式类别的音乐及其分类做如下讨论。
(一)嘎哈抚
“嘎哈抚”依附于嘎哈毕仪式,在嘎哈毕仪式中使用。彝语“嘎哈毕”,意为“路上方”,嘎哈毕仪式在凉山州地区特指“尼木措毕仪式”。“尼木措毕祭祖仪式作为彝族宗教仪式‘嘎哈毕’(路上方)仪式的核心内容,对其研究须先从‘尼木措毕’一词说起。‘尼木措毕’(nip mu cobi)意为:由彝族的神职人员毕摩为亡灵念诵经文,表达追思,慰藉亡灵,教导亡灵,驱鬼除邪。‘尼木’是彝语(nip mu)的音译,‘尼’指‘尼杜’(nip ddu),意为‘灵牌’,‘木’意味‘做’,‘措’意为亡人,‘毕’意为‘诵经文’。”㉖吉尔体日、曲木铁西、吉尔拉格、巴莫阿依:《祖灵的祭礼:彝族“尼木措毕”大型祭祖仪式及其经籍考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3-4页。故“嘎哈抚”就是在嘎哈毕仪式中所使用的音乐。
笔者于2017年11月跟随曲比拉火、曲比尔日、曲比拉哈等毕摩前往美姑县拉马阿觉乡参加了一场大型的嘎哈毕仪式(尼木措毕祭祖仪式)。在仪式中曲比拉火向笔者介绍了嘎哈毕(尼木措毕祭祖仪式)中所使用的“尼抚”。“尼抚”用曲比拉火的表述就是:“在尼木措毕仪式中使用的音调。这些音调只能在嘎哈毕中使用,且每项仪式所使用的音调都有规定,不能混用。”
由此可见,在局内分类观念中“嘎哈毕”特指尼木措毕仪式,尼木措毕祭祖仪式音乐属于“嘎哈抚”。
(二)嘎基抚
“嘎基抚”依附于“嘎基毕”仪式。彝语“嘎基毕”意为“路下方”,其主要是彝族人民治病、取名、招魂、除晦、婚嫁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仪式。“嘎基抚”在“嘎基毕”仪式中的运用也是一一对应的,并且毕摩对他们使用的“嘎基抚”有着清晰的分类:
1.日抚。“日”在彝语中有“驱鬼”之意,“日抚”是“嘎基毕”仪式中常用的一个音调,主要用于仪式中的驱鬼环节。这一类音调能够使人清晰地听到旋律起伏,用毕摩的话来讲,这一类就是“唱”的,所以这一类从主流观念来讲属于音乐。
2.犁抚。“犁”在彝语中有“赶出去、推出去”之意,“犁抚”主要用于“嘎基毕”仪式中。主人家(主祭方)有此类仪式需求时,毕摩演唱该音调将主人家中的“坏东西”“脏东西”“鬼”等赶出去。该仪式同样也有驱鬼之意,但是音调却与“日抚”不同。
3.拉抚。“拉”在彝语中有“劝解、劝说”之意,“拉抚”在嘎基毕仪式中主要用于治病仪式。毕摩在给人治病时用草编成“草鬼”,一般八至十个不等,毕摩念诵“拉抚”与鬼进行交流、劝解,意在让鬼远离病者。用毕摩的表述该音调主要采用说的形式,也可以认为是念诵形式。
4.日邪。在毕摩仪式中该音调主要用于嘎基毕仪式中的招魂仪式。笔者在2018年彝族年间跟随曲比拉火做过两场此类仪式,毕摩在主人家(主祭方)的屋后檐下进行仪式,将去世人的灵魂召回。该音调采用唱的形式。
5.活抚。“活”在彝语中有“好的”之意。“活抚”主要用于除晦仪式中,一般主人家的房屋、装饰品(耳环、银饰)等受到“不干净”的东西侵扰时,需要毕摩来除晦,毕摩在仪式时就演唱该音调。
6.莫挪抚。彝语“莫”在嘎基毕仪式中是猪、鸡、羊、牛等在仪式中牺牲后的统称,有着符号化的象征,象征祭品。“挪”意为“赶”,在仪式中意为“赶往西天”之意。该音调主要用于平安仪式,一般在彝族年前后,每家都会做这样的仪式。在仪式中只要需要祭品都会念诵这一段音调。意思是:毕摩念诵该音调与主人家的祖先们进行沟通、交流,保佑子孙平安、多福,并将猪、鸡、羊等作为祭品献祭。
7.索默。该音调在毕摩仪式中都会用及,无论是嘎基毕仪式中的驱鬼、招魂、治病等仪式,还是嘎哈毕仪式的尼木措毕祭祖仪式,都会在仪式前使用该音调㉗索默音调在嘎基毕、嘎哈毕当中都会使用,因为嘎基毕仪式种类较多,而嘎哈毕主要指尼木措毕祭祖仪式,故曲比拉火将其归于嘎基毕音调之中。。正如曲比拉火所述:“索默就像自我介绍一样,仪式前就会说唱,主要有两段。第一段主要内容就是说唱给自己家族毕摩神㉘彝族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毕摩死后就会成为家族的神来守护、协助家族的毕摩完成毕摩仪式。,第二段主要内容就是保佑主人家(主祭方)、财产等平安。”
8.拉昔。彝语“拉昔”,在仪式中意为“献茶”。毕摩在仪式中演唱此音调给毕摩家神、山神、水神、火神等,邀请其帮助毕摩做仪式,将主人家(主祭方)家中的“脏东西”等驱赶出去,“好的”东西留在家里。
综上可知,毕摩音乐依附于毕摩仪式,在仪式中被称为“毕抚”,它包含了彝族毕摩仪式所布的全部音乐,应当属于第一层级。毕摩仪式主要分为嘎基毕与嘎哈毕两种,嘎基毕仪式对应“嘎基抚”,嘎哈毕仪式对应“嘎哈抚”,二者可视作第二层级。在嘎基毕中由于仪式的不同,如治病、祛邪、平安等仪式,所布音乐亦不同。嘎哈毕仪式所布的音乐“嘎哈抚”或者说“尼抚”不在嘎基毕仪式中使用。故嘎基毕中所用的“日抚”“犁抚”“拉抚”“日邪”“莫挪抚”等音调与嘎哈毕仪式中的“尼抚”应当属于第三层级。
如上文所述,从仪式语境中去看待仪式中所使用的这些概念、分类、称谓及其表述,站在一个局外人(研究者)的立场与视角不由地思考其到底有何内涵?对其意味着什么?
三、田野中的感知:概念背后的内涵与观念
上文提及了毕摩在仪式语境中对毕摩音乐(毕抚)的概念、分类,如果研究者不将局内(毕摩)陈述概念置于仪式语境之中去思考,这些局内表述概念有何种意义,那么可能对毕摩音乐这一音乐事象的研究会有所缺乏或者说不能理解其音乐思维,进而就很难理解毕摩在仪式场域中所呈现出来的表演行为(声响、动作等)。以下笔者将对毕摩音乐概念背后的音乐观念与内涵,结合田野中的访谈进行讨论、论述。
(一)对音乐的认知——基于“抚”的感知
上文所述对于“抚”的局内定义之一,即是音调。正是“抚”的局内自表述存在,出现了当今学术界对毕摩音乐他表述的“各种调”,如“除晦调”“硕默调”等。笔者将“抚”置于其表现形式,这种形式源自于毕摩的自述——“唱”和“说”,也可以理解为当今民族音乐学对于音声中听得到的“音声”(所谓音乐)的音乐性(远语言/近音乐)与语言性(远音乐/近语言)㉙同注⑯。的研究。“唱”,源于毕摩演唱时的旋律——节奏——节拍等,旋律性较强,这种音调的音乐性较强。“说”,在笔者看来,这种音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说”,而是伴随语言音调有节奏的念诵,其音乐性(旋律性)较弱,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念诵”。
也许“毕摩”对于音乐的概念没有界定,更确切地说是认知,但是从“抚”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来看,当今局内(毕摩)在面对局外者的研究时,都会将两种形式(说与唱)纳入“音乐”的表述范畴之中。这种“音乐”指代的是研究者对“音乐”的感知,属于研究者所感知的“音乐”。局外者在书写、研究中也从未忽略过“说”的那一类。在《毕谱》经文中有关于尼木措毕音乐的来源:“刚开始时做毕摩仪式,只念不唱,后来毕摩模仿大自然的声音,鸟叫、牲畜的叫声、水流声、风声等,将其纳入毕摩经文说唱之中。”㉚此部分来源于曲比拉火对其经卷《毕谱》的翻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尼木措毕仪式音乐的来源之一是“模仿说”,这种有意识地模仿促成了局内所谓的“抚”(音调)的来源,局内者并不在乎毕摩音乐是否是音乐,因为这种音乐事象存在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娱人,而是所具有的极强的实用性与功能性,更是一种依附于民俗活动的族群认同。
所以,无论是采用音调、音乐还是音声表述,研究者应当去关注局内的称谓,对这些局内表述关注,才能更好地认知我们所感知的“音乐”与局内感知的“音乐”的差异,以及这种音乐事象对于局内的意义与内涵。
(二)审美意识——基于对“抚”的追问
“抚”的另一层局内定义,即是“嗓子”。嗓子作为他们音乐呈现的方式在仪式中演绎,笔者将讨论的是通过“抚”的局内定义、曲比拉火成为毕摩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问题的追问,来解析“抚”所透露的局内审美意识及毕摩音乐呈现的音乐形态的缘由所在。
对于“抚”的追问,源自笔者所经历的一场大型尼木措毕祭祖仪式。笔者认为,既然“抚”有嗓子之意,那么毕摩音乐的演唱需要一副什么样子的嗓子呢?因为尼木措毕祭祖仪式就是毕摩通过念诵、诵唱等方式用经文与祖灵、自然神、鬼怪等进行交流、沟通的仪式,以求和谐与共,将祖灵平安送回祖地。那么尼木措毕祭祖仪式音乐对于毕摩嗓音的要求是必然存在的。毕摩演唱主要依靠喉音,笔者在田野期间曾询问曲比拉火何种毕摩音乐的演唱是最美的,是最受大家认可的?曲比拉火给予我的回复即是:“毕摩的声音必须如大黄牛叫一般的低沉而绵长,绝对不是跟小黄牛叫一般的奶声奶气。”因此“大黄牛叫”“小黄牛叫”这两个词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对毕摩演唱好坏的衡量标准之一,我们可以视其为音乐审美认知的“自表述”。同样的问题我也曾问过曲比尔日,他的回复是:“我们几兄弟操作仪式的能力大家都是认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被邀请去做尼木措毕仪式,前几年我的声望还是很大的,所以也被受聘到美姑县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工作。随着这几年‘非遗工作’的进行,毕摩音乐去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在选定传承人的时候,毕摩们聚在一起演唱毕摩音乐,大家投票选出一位作为传承人,最后大家选出来的就是曲比拉火,因为毕摩们认为他的声音是非常有磁性的,深邃、厚重,所以他就作为毕摩音乐传承人去申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这些年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当然这对于我们杨古苏布流派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可以得到其他流派毕摩的认可,这就是很好的了。”从笔者与曲比尔日的聊天中可以看出,不同流派的毕摩对于毕摩的嗓音有衡量标准,何为好?他们非常清楚!
当然,无论是曲比拉火对于嗓音好坏与否的自表述为“大黄牛叫”还是“小黄牛叫”,或是毕摩同行所谓的“深邃”“厚重”“有磁性”,透过这样的衡量标准,可以看出毕摩音乐的演唱对于嗓音的要求有其自身的评判机制,这种机制或标准的背后其实是毕摩音乐审美观念、认知的体现。
对“抚”的追问,思其审美意识,就不难理解毕摩音乐呈现的音乐特征。旋律多在一个八度以内,以级进为主,深沉而深邃。毕摩通过演唱、念诵等方式进行仪式,音乐呈现的形态通过声音传递出来使得仪式场的人获得感知。这种形态却是局内(毕摩)意识的外延。此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点,即是生理要求所致。尼木措毕这类大型的仪式,仪式程序相当繁复,每一项仪式音乐的布局皆不同,一部经文耗时较久,长时间地演唱,嗓子是难以承受的,故毕摩音乐的形态会呈现出这样的形态。
(三)音声制度——源自分类的启示
“嘎基毕”与“嘎哈毕”仪式在同一层级具有不同的音调布局,举行仪式的人能够在仪式场域中配合毕摩作出相应的仪式行为,这种音调传递的信息被局内所感知,亦知道音调所包含的内涵与指令并作出相关的行为。同时,“嘎基抚”只在“嘎基毕”仪式中使用,“嘎哈抚”也只在“嘎哈毕”仪式中使用,两者之间具有严格的界限与规约。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笔者,能够感受到上述音调、行为等在仪式场域中对局内者所发出的信号。正如《仪式中的制度性音声属性》一文指出:“仪式内涵之所以能够通过音声‘进行可感知的系统’表述,并‘固定于可感知形式的经验抽象’,再得以体现(embodiment),是因为其‘规律性和可预知方式中的重复行为’在展演结构和音声属性上形成了特有的制度,并被其文化群体所感知和共享。”㉛同注⑮。毕摩音调在仪式场域中被文化群体所感知,逐渐形成其特有的仪式和音声制度,使得文化群体在仪式中作出相应的行为。
此外,从毕摩音乐的分类来看,第二层级的两类音乐不能混用,不同的仪式所布音调也不尽相同,通过音调的展演,局内者、参与仪式的人能够清晰地辨别出仪式的类型及其所属类别。2017年11月笔者在凉山州美姑县随曲比拉火参与了一场为期四天的大型尼木措毕祭祖仪式,共记录三十余道仪式程序及其音乐布局。而在尼木措毕祭祖仪式第一天,笔者共记录了四道仪式及其音乐。晚间笔者询问主祭方:今天白天所举行的仪式,毕摩唱的嘎哈抚你们以前听的多吗?主祭方回答:“听过,但是毕摩们今天唱的不是嘎哈抚,是嘎基抚。”笔者的疑惑在于,毕摩所唱的音调不是在嘎哈毕仪式中使用的吗?为何不是“嘎哈抚”?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向曲比拉火谈及此事。曲比拉火说:“是的,今天所唱的并不是‘嘎哈抚’,只有在祖灵扫尘仪式后,我们唱的才是‘嘎哈抚’。尼木措毕仪式在祖灵扫尘仪式后,我们唱的经文大部分都是唱给祖灵的,与祖灵进行沟通,将其送回‘祖地’并保佑主祭方平安,多福,所以‘嘎哈抚’唱的都是好的。但是嘎基毕中的‘嘎基抚’就不一样,很多音调都是用来驱鬼、除晦、赶脏东西的,所以‘嘎基抚’唱的基本都是坏的,不好的。”㉜在笔者所经历的该场尼木措毕仪式中,Ku si(祖灵扫尘)仪式在第二天,该仪式是在Nie hei nie die(制作灵牌)仪式后进行,Nie hei nie die(制作灵牌)仪式是将火葬地的祖魂物化成“灵牌”,具有符号化象征意义,只有“灵牌”制作完成,尼木措毕祭祖仪式才算真正的开始。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通过音声局内者能够辨别仪式的类型,并能辨别出其属于“嘎基抚”还是“嘎哈抚”。虽然尼木措毕祭祖仪式被研究者所熟知,将一场尼木措毕祭祖仪式从头到尾进行,被认定为就是尼木措毕仪式,但是通过音声的布局与展演我们却能够得知,在制作灵牌及祖灵扫尘仪式之前的仪式中所布的音乐,毕摩所演唱的音乐在局内意识中属于“嘎基抚”并非“嘎哈抚”,结合上文局内者自述的“好的”“坏的”可知,因为仪式对象、所指不同,虽然“嘎基抚”在尼木措毕祭祖仪式(嘎哈毕)中使用,但是其类别属性却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音声所透露的制度体现。
这种音乐所依附的仪式长时间地存在于该文化群体信仰中,毕摩在长期的信仰仪式实践中使其为群体所熟知,故通过音乐局内人即能辨别仪式类别的不同。同时正如曲比拉火所述的“好的”“不好的或坏的”,笔者以为这是面临不同仪式对象时,经文内容通过音乐在仪式场域中展演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符号。局内人能够通过音乐辨别出仪式的类别,局内操持者(毕摩)在面临不同的仪式对象使用他们所谓的“好的”“坏的”的音调,这些音调置于仪式场域中时本身就具备了制度性。
结 语
文章通过现有对毕摩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和仪式语境中毕摩音乐的自表述,两者结合形成反思,进一步引申到局内的概念及其分类,是由于其在仪式场域之中的表述透露出该音乐事象操作者的音乐观念与思维,这种观念包括局内人(毕摩)对其所持音乐事象的概念认知、分类等,而这些认知、分类背后体现着其自身的内涵及属性。当研究者在面对这些自表述并对其进行转述时,或多或少赋予了对这些局内表述、概念的期待,在进行转述时就会存在缺失。如果将毕摩音乐置于仪式语境中来阐释毕摩在仪式场域中的表述,我们能够更好地感知其概念所具的多义性、仪式所包含的类目(分类)及其背后的内涵所在。
附言:本文为笔者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美姑县尼木措毕祭祖仪式音乐研究》绪论及第二章节选,在节选时作出调整与修改。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导师甘绍成教授及曲比拉火的指导,特此感谢!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