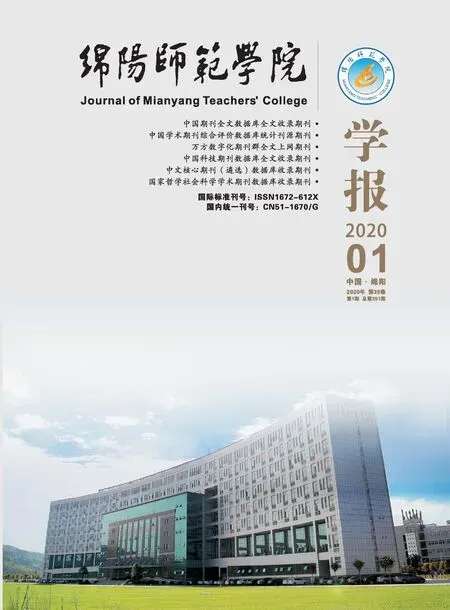符号学视域下电影《罗马》中的女性形象
赵 林
(成都大学影视与动画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罗马》是由墨西哥籍导演阿方索·卡隆执导的剧情片,荣获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名年轻的墨西哥土著女性克里奥,为丈夫长期不在家的索菲亚一家做女佣,当面对克里奥的突然怀孕,索菲亚被丈夫离弃的生活窘境时,影片中三个主要的女性角色相互扶持走出困境、迎向新生活的故事。本文以符号学为工具,通过对墨西哥影片《罗马》中克里奥、索菲亚、奶奶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的解读,揭示墨西哥电影中父权制对女性的压抑和身份设定的刻板桎梏,展示出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爱与信仰、独立与坚韧等复合性形象特质,以及对传统刻板印象的新变、对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对父权制的抗争。
罗马独立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由于长期饱受父权制的压迫,女性现实生活的窘境和悲剧还在持续不断地上演。社会的阶级分化、性别导致的种种不平等问题,使得墨西哥女性要么陷入现实的泥淖,沉沦麻木,无法自拔,要么不再忍受现状而勇敢追求新生。因此在墨西哥的电影本文中,并非所有的女性都具备女性意识的觉醒,仍然有大量在父权制影响下沉沦麻木、不抱幻想的女性形象存在。在这种语境下,引用符号学和女性主义相关理论作为研究工具对电影《罗马》进行深度解码,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作为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支,借助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学三种思维模式,采用不同的审视角度和解读方法,以详尽的文本分析破译好莱坞电影的影像符码,揭露其深层意识形态中反女性本质,使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和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1]与其他墨西哥电影不同,《罗马》是一部导演回忆幼年时期的私人电影,是一部纯粹的女性题材影片,以导演小时候生活的墨西哥城罗马区命名,以此献给曾经陪伴自己成长的家里佣人。但也正是这样一部私人电影,却拥有着跨越国别、时代、个体、经验差异的普世价值:影片中对女性遭遇的认同感,对女性身份地位的体认与尊重,和塑造女性在绝境中拥有的温柔与力量都使得影片中的女性形象生动而又真实。克里奥作为墨西哥土著的底层女性代表,最后选择不再麻木地生活,而是对未来的生活抱持希冀;索菲亚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代表,在经过了一系列蜕变成长之后,选择坚强独立地扛起生活重压,终于勇敢地脱离了对男性的依赖,摆脱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压抑。
一、社会底层女性的困囿:克里奥
(一)麻木盲从的刻板形象
克里奥作为墨西哥土著与社会底层女性的代表,一直在索菲亚家中做女佣。她来自农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对生活没有特别的憧憬、向往,没有远大的理想和人生抱负,麻木地接受着生活固有的安排。导演对于克里奥形象的建构就是还原真实。作为社会底层人物的代表,克里奥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不断重复的、盲目接受的。但这一“普罗大众”式的刻板印象也为后面克里奥的形象转变埋下了伏笔。
影片开篇就是刷地的情景,简单、冗长,克里奥刷地时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这个时期的她还是一个本分隐忍、默默干着自己分内工作的女佣,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随着一声声的洗刷和冲地声,一次次的水波纹出现在镜头中,导演既用这样的长镜头将观众带入到他想要讲述的那个时期,也从侧面反应克里奥生活的一成不变和麻木重复,表现出在墨西哥作为土著的社会底层女性麻木盲从的刻板形象。
在墨西哥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态度极为专横跋扈,身处社会底层的墨西哥女性对此却是默许的,以至于克里奥在意外怀孕并被无故抛弃后,她对男友的态度仍然是保持平静的,甚至在男友的大声嘶吼和谩骂中也一脸淡然,没有较大的情绪起伏,反而像是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挣扎无用的感觉。作为父权制社会中底层女性的代表,她既没有发怒,也没有反抗。这便是导演刻画墨西哥社会底层女性普遍存在的刻板形象的典型代表。
(二)经历巨变后试图新变
作为墨西哥底层女性的代表,克里奥有着刻板的思想和作风,但是历经生活一次又一次的巨变后,也为她打开了突围困顿、试图新变的窗户。
克里奥原本的女佣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她将自己藏在了这个冷血的社会角落里。而意外的怀孕,让她第一次有了对生命的迷茫;在地震中带着孙女跪地祈求的老奶奶和保温箱中瘦弱但顽强的婴儿给了她第一次心灵上关于“生命”认知的冲击;在男友的抛弃和谩骂中,她依然平静,此时影片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一群人做双手高举过头顶、单脚站立的动作时,只有克里奥成功了——但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男人才是主导,这时的克里奥对于“生命”有了第二次的压抑和困顿;在医生告知孩子没有生命体征的时候,克里奥紧紧搂抱住已经夭折的孩子时,克里奥对“生命”有了第三次的困惑和苦恼;站在圣诞夜晚被大火烧过的山脊上,面对和故乡相似的风景,看着孩子们在焦土上依旧嬉闹时,克里奥对“生命”有了第四次的接受;并不会游泳的克里奥从海里救回索菲亚的两个孩子后,“一家人”瘫坐在沙滩上,在夕阳中围抱在一起,克里奥对“生命”有了第五次劫后余生的释然;在克里奥与索菲亚一家结束旅行后回到家,对另外一名女佣说着“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时,索菲亚对“生命”有了第六次的渴望和热情。如此这般的情绪累积和层层叠加,使得作为社会底层女性代表的克里奥不再是麻木的,而是对生活和生命有了新的认知体悟和憧憬向往,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不再是一味的忍耐与默许,而是有了冲破父权制控制的思想在逐渐萌芽。
“按照法国学者麦茨、意大利学者温别尔托·艾柯等人创立的电影符号学观点,电影的本质不是对现实为人们提供的感知整体的摹写,而是由一系列符码所组成的约定性的符号系统。”[2]“大海”在《罗马》中是克里奥生命里重要的符号意象,两次与大海的会面是克里奥从生活的麻木刻板到突围困顿、试图新变的见证。克里奥在失去孩子后跟随索菲亚和她的孩子们进行了一次旧车告别旅行。她们第一次遇见大海是在去旅行的途中,孩子们抑制不住看见大海的兴奋,吵闹着要去这个计划之外的海边玩耍,一行人暂时放下生活连日来给予的束缚与压抑,向着大海奔跑而去。此时的大海在孩子们眼中是玩乐的天堂,但是在刚经历了被男朋友抛弃又失去孩子的克里奥眼中,此时的大海却是无情并且残酷的,它仿佛能够吞噬下世间一切。克里奥拒绝了孩子们热情的邀请,大海给她的压抑感让她望而生畏,生活已经没有空隙让她暂时喘口气了,就像这终日翻腾的大海,表面风平浪静,内里却暗藏玄机。第二次遇见大海是在告别旅行的回程中,再次见到了这片大海,仿佛她们告别过去的生活时也要连同这片海一起告别,依然翻腾的波涛,但这次却把克里奥的压抑和害怕照进了现实。两个小孩嬉戏打闹着走到了海水深处,大海似乎穷尽全力地“拥抱”他们,不会游泳的克里奥一步一步走进大海,走进生活际遇给于她的困顿和绝望,但大海此时也成就了她,她带着两个孩子一步一步走出了大海,也即是走出了自己内心封闭的“海域”,走出了自我意识的困囿之局。在夕阳映射的海滩上,劫后余生的“一家人”围抱在一起,爱串联起她们对生的所有渴望。“大海”让克里奥从之前的人生困境中释怀,此时海浪拍打的是生活的希望,带来的是美丽的乐章。
二、新时代女性的觉醒:索菲亚
(一)男权话语下的依附者
索菲亚是生活在墨西哥城的中产阶级知识型女性的代表。20世纪70年代的墨西哥城罗马区动荡不安,正处于女性觉醒进行时阶段,罗马区男权主义的桎梏还普遍存在。“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作为本体性、自主性存在的女性一直是缺席的,或者说女性始终是作为在场的他者而存在的。”[3]3索菲亚前期的全部关注点都落在丈夫身上,而她最初则是以一个男性依附者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
她会在门口迎接丈夫回家,会在大家一起看电视时让女佣煮热饮给丈夫,会注意到丈夫踩到狗屎后的厌恶情绪而责骂女佣,会在丈夫弃家后想方设法地寻找并且感到惊慌、茫然、崩溃。索菲亚的丈夫以男权中心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家,满地的狗屎,杂乱的冰箱都是他作为男性想要逃离这个家的借口,但索菲亚不会怀疑这些借口,甚至会怪罪于女佣没有尽职尽责地完成工作。索菲亚的丈夫在离开家的时候开车穿过正在游街的乐队,她失落地站在原地,目光一直追随着丈夫离开的方向,任凭自己淹没在全是男性的游街乐队中。而全是男性的游街乐队就是那个时代下墨西哥的典型症候:索菲亚丈夫置身其中包裹着华丽刚硬的外壳从容离开,而索菲亚置身其中却只能用肉身凡体任其压迫。在当时的墨西哥城,男性有社会大坏境的庇护,女性却只能靠自己的斗争顽强地活下去。女性的觉醒意识在这里还是沉寂的,对男性的遵从与依附还是统领着索菲亚的身心。索菲亚的丈夫弃家后,她想了很多办法想要挽回,要求孩子们给爸爸写信,企图让丈夫看在孩子的份上能回家;在陪克里奥去医院时找到丈夫的同事,企图通过丈夫的同事得到丈夫的具体消息等等。这种生活的突变使得平时一直依赖丈夫的索菲亚处于惊慌失措甚至是无助崩溃的边缘。此时的索菲亚作为丧失了主体性的客体而存在,成为了被丈夫所支配的对象,没有自己独立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凡此种种均体现了一个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一个社会对女性造成的压迫。
(二)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纵观全片,索菲亚其实是影片设置的唯一一个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角色。她与克里奥不同,在丈夫出轨弃家时,她没有像克里奥一样冷漠隐忍,她极力地挽救这段感情,在一切办法都无效时,她开始改变:她重新找了份能养活全家的工作,换了那辆尺寸不合适的车,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的希望。影片中以前那个完全意义上的男权社会正在土崩瓦解,“女性不再盲目的把男性当成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4]。索菲亚也不再受制于父权制的压迫,她用女性的温柔与刚强成为全家的支柱。
影片中一共出现过三次开车进家门的画面。第一次是索菲亚的丈夫开车回家,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场。导演给这个男性角色的镜头都是烟、音响、方向盘等男性色彩浓烈的符号意象。全家在门口迎接男主人回家,男主人开了三次才勉强把车开进家门,最后一次还压在了狗屎上。第二次是索菲亚开车进门,人换了,车还是那辆不合大门尺寸的车,这次索菲亚并没有再小心翼翼地开进门,而是以一种横冲直撞的蛮横姿态开进家门。这时索菲亚的情绪已经彻底崩溃,丈夫出轨,生活开支骤减,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她的身上。她对克里奥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做女人的都是孤身一人。”女性潜意识里就把自己当成了男人的依附品,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思想和能力。第三次开车进门是索菲亚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标志,她卖了尺寸不合适的大车,换了一辆能轻松开进门的小车,不管是经济上的原因还是对过去的告别,索菲亚已经接受改变并且选择主动积极做出改变。所谓的告别大车旅行,也正是索菲亚告别过去生活的象征。她选择直面生活,直面未知的未来。她告诉孩子们自己为了继续支撑家里的生活而换了工作的真相,告诉了孩子们父亲的离开,在孩子们担忧父亲不再爱自己时,她并没有趁机抹黑这个父亲的形象,而是极力地美化,并安抚着孩子们的情绪……这些转变令人惊讶与赞赏,此时索菲亚的女性独立意识已然觉醒。她不再是一个依附于男性的从属角色,而是一个依靠自己并且成为家人们依靠的独立自强的女性,她用温柔和刚强撑起这个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里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5]309通过这三次开车进家门的转变,一个曾经依赖于男性的女性在蜕变着、觉醒着。女性的独立意识不再被父权制压抑,开始在绝境中生长出温柔又坚韧的力量,开始勇敢地与男权社会抗衡。
三、家庭精神的隐性支柱:奶奶
(一)“为母则刚”诠释女性的坚韧、温暖与爱
“奶奶”是生活在摩西哥城中,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普通老人的缩影。虽然一如常人的温和,但其实,奶奶的刚强、坚毅才是墨西哥城罗马区21号这个家长久和谐生活下去的隐性支柱。
“爱”是奶奶能给予这个家最直接的温暖与支撑。一个从小在较为优越的环境里成长的单纯善良的老人,一生的执着大抵不过是家人的平安喜乐。在这个被父权制所牵制的社会中,奶奶是老一辈奋力自持的女性的代表,岁月流逝,已然老去的奶奶依然为家庭操劳奔波,默默甘当付出者和引航员。
对于孩子们关于食物的争吵,她会说:够吃,都有得吃;对于孩子们关于谁去看电影的争论,她会带上大部队一起去等等。奶奶的“爱”不只是对自家小孩子的爱,还有作为成熟女性对于对索菲亚和克里奥的爱。她的爱没有阶级之分,没有亲疏远近。对于索菲亚来说,失去丈夫的无措和痛苦时刻揪着她的心。当被迫成为一家之主时,她需要在孩子和佣人面前极力隐忍,但在奶奶面前,索菲亚也只是个孩子。奶奶给予了她一个能暂时逃避成人世界回到孩童的港湾。她能肆无忌惮地埋怨,痛哭失声地倾诉自己内心的惶恐。对于克里奥来说,一个单身还怀着身孕的底层女人,不被雇主辞退已经是万幸了,更别说雇主能反过来照顾自己。所以克里奥遇见奶奶是异常幸运的,奶奶对她没有来自上层阶级的高傲和歧视,而是像对待家人一样地平等对待她——奶奶会带克里奥买婴儿床,会说家里孩子之前用的也是这个床;会在克里奥羊水破了去往医院的车上,抱着克里奥不断地为她祈祷,丝毫没有任何嫌弃鄙夷;甚至对于街上遇见的暴乱,奶奶也会祈祷一句“希望这些警察不要杀了他们”。奶奶用爱连接起了这个家,竭尽一己之力帮家里人阻挡了一次次来自男权社会对柔弱女性的侵袭与冲击,建构起了这三个女性关于爱与信仰、独立与坚韧的复合形象。
影片中有三次飞机飞过天空的镜头,这些符号意象预示着这一家的命运走向,也暗含着奶奶作为这个家“精神内核”般刚强坚毅的存在。影片刚开场,有人匆匆地取桶、接水、刷地,声音由远及近,终于一地的肥皂泡沫带着水纹进入了观众的视线,泡沫散去,清亮的水面映着一架小小的飞机倒影,这是克里奥再日常不过的工作场景,也是这个家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场景;影片中第二次出现飞机的时候,克里奥的生活开始变了,生活和命运都对她施以重压;到第三次飞机飞过时,影片也接近尾声,克里奥走出了自己内心的挣扎。这三次飞机飞过的画面,不仅是克里奥的生活、心境转变的暗喻,也是奶奶一直支撑着这个家的隐喻。自始至终,奶奶操持着这个家的日常生活:克里奥被抛弃,发现自己怀孕后,奶奶没有放弃反而带她去买婴儿床;到克里奥走出困境,奶奶也还在为这个家的琐碎杂事继续操心。不管发生什么,生活总要继续。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经历着什么样的伤痛,生活仍将也必将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无奈中的无惧无畏。每当这个家在经历波折和困苦时,奶奶就会像天空划过的飞机一般,鼓励并且带领大家继续前行。飞机既已起飞,在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没有理由半途而废。这正寓意着女人们的生活也一样,即使已经痛苦不堪,也要有努力撑下去的无畏和坚毅。奶奶就像已经起飞的飞机,飞了快一辈子了,饱经风霜,历经磨难,但仍然承载和庇护着这个家,教会其他两个女性勇敢地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用爱和温暖为这个家撑起一片蓝天。
(二)精神“避风港”对新女性的感召与唤醒
在父权制主导的社会中,精神慰藉是女性的隐性支柱。社会给予的压迫和桎梏使得女性沉沦并窒息,女性饱受现实生活的困窘和压抑,精神上更是欠缺和空虚。奶奶作为饱经风霜的女性个体,也是老一辈稳固家庭的女性群体的代表,为女性摆脱传统的刻板印象,引导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家庭的“避风港”,也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性别地位开始摆脱父权制压迫的精神支柱。
女性要突破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和性别地位,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羁绊和困难,这个时候呼唤和支撑女性继续下去的所有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凭着一腔信念。这份信念,就是电影中奶奶所撑起的叫做家的“铜墙铁壁”。纵使历经风霜并且饱受苦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感召与唤醒,一种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不妥协和呐喊。奶奶在精神上给予的慰藉,是促使这个家里另外两个女性改变和觉醒的良药。
影片中那面被打碎的“玻璃”也是典型的“有意味的形式”。坚硬的玻璃为这个家遮风挡雨,但终究因为孩子的争吵打碎了它。生活的窘迫使得大家来不及顾及这面破碎的玻璃,但走出困境之后直面新生,这面碎掉的玻璃也为生活打开了一扇能够透气的窗口。奶奶就像这面窗户,竭尽全力地为这个家遮风挡雨,但是人总要自己学会成长。破掉的玻璃更像是奶奶放手的成长,只有自己经历了生活的磨炼,才会真正品尝到生活带来的甘甜。一扇破碎的玻璃,何尝不是压抑的生活中奶奶为这个家打开的一个通风口,迎风而生,坚强生活。这在当时墨西哥浓重的男权主义氛围下,女性为了自身的独立和权利在不断地与父权制社会做抗争,奶奶作为坚强的代表,带领着索菲亚和克里奥走向新生。奶奶的从容淡定,是克里奥在遇到危险时的盾牌和镇定剂,也是索菲亚勇敢面对生活的有力推动者。奶奶作为这个家隐性的精神支柱,使得克里奥有了社会底层女性的思想新变,索菲亚有了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底气。
四、结语
墨西哥电影《罗马》塑造了处于不同阶级的三位女性形象。她们在面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压迫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和觉醒:克里奥作为社会底层女性在经历过生活的巨变后产生了思想新变,不再是曾经面对男性肆意压迫只能麻木接受的女性形象,而是拥有了接纳生命、期待生活的新思想;索菲亚作为新时代女性的代表,在面对生活的困窘时,从最开始没有男性可依附的惊慌、崩溃到最后换掉工作,选择独立,不再自怨自艾,不再依附于男性;奶奶在面对这一系列的家庭变化时,用她刚毅的精神内核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最内里的温柔与坚强。
而正是由于这三位女性相互之间的改变、成就和支撑着彼此,才使得这部纯粹的女性主义题材影片《罗马》有了跨越国别和种族、超越时代局限的普世价值和认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