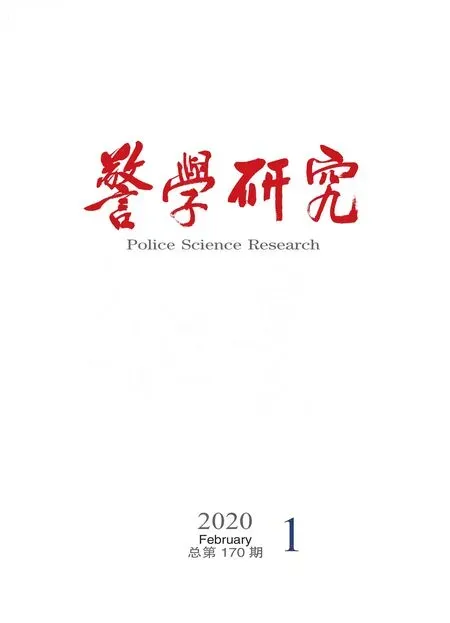选择性取证用证之考量
——以冤错疑刑案为镜鉴
(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在证据裁判制度下,案侦司法过程都需围绕证据材料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刑事证据的收集,俗称“取证”;刑事证据的运用,俗称“用证”。取证和用证之目的,都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为司法裁判服务。而案侦司法是否公正,其选择性取证用证,就会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选择性取证用证的必然性
在现实案侦中,有些侦查员为了尽快破案,往往是只注意收集嫌疑人的有罪证据,而不收集其无罪证据。这就难免会出现有罪推定的问题,增大出现冤错案件的风险。反过来,如果只收集无罪证据,那又如何呢?要是嫌疑人(或其辩护人)为证明自己的无辜,他们只选择收集其无罪的证据,那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侦查机关却不行,侦查是有追究犯罪之目的性的行动。只收集无罪证据,这显然有违侦查规律。国家需要侦查机关,往往是因有犯罪案件存在。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需要侦查人员破获案件,去抓获犯罪嫌疑人。这就需要有指向性地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行为的证据,而不可能泛泛而查地浪费侦查资源。因此,侦查活动不可能不收集嫌疑人的犯罪证据,而只收集其无罪证据。既然案侦是针对犯罪行为进行的,它就应该围绕犯罪事实进行。其取证和用证,当然也应该围绕该事实取舍。因此,侦查过程中要选择案件材料是必然的。从逻辑上讲,既然是一些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它们就和刑事犯罪有关系,就应该全部都收集在案。但侦查初始,案情往往不甚明了,收集案件材料就时常一时难以判明其真实的证据价值。这时候选择材料,决定其取舍,也就往往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风险。
为求司法公正,侦查活动应该尽可能地收集案件材料,判明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关系及其性质,以便能够进一步地核查证据,寻求案件事实真相。取证和用证之目的,就在查清案件事实,以证据材料锁定犯罪嫌疑人,在破获案件的基础上,用证据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而在取证与用证过程中,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追求证据效率的影响,案侦人员都难免要追寻犯罪事实,对证据材料进行一定的取舍。而辩方,为摆脱嫌疑或减轻处罚,也会对证据材料进行相反的取舍。总之在案侦司法过程中,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他们的取证用证都有其目的性、方向性和逻辑性。有目标、有方向、有逻辑,也就难以避免有对证据材料的选择。因此,双方对证据材料的选择都是难以回避的,具有相当的必然性。而在选择证据的过程中,它们也就体现着案侦司法人员和被告人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观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中的正与误,又事关案侦活动和辩护结果的成败与司法正义的伸张,因此有必要深入地进行探讨。
二、选择性取证用证之利弊
(一)选择性取证的弊与利
1.选择性取证中的违法性与违理性。在犯罪案件的侦查中,警方是否有只收集有罪证据,不收集无罪证据,或者只收集哪些犯罪证据,不收集哪些无罪证据的选择性自由呢?答案一般是否定的。针对具体的犯罪嫌疑人,警方是否可以有罪的证据就收集,无罪的就不收集呢?这也是否定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1]这说明,案侦司法人员不收集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是有违程序法的。程序中的这种规定,体现了案侦司法的公正性。公正性,是案侦司法不同于个人取证用证的地方。并且,在全面收集案件材料之前,就做单方面的选择,就涉嫌“有罪推定”,容易失去公正性。这些先入为主的单方面选择,有可能将案侦引入歧途,极易造成冤案、错案、疑罪案件。罪案之所以需要进一步侦查取证,收集各种证据,还在于案件事实不完全清楚,证据还不够确实、足够和充分,需要公安司法人员收集各方面的材料去甄别之,证明之。这是司法理性的必然要求。如果在充分收集各方面案件材料之前,就选择性地收集哪些证据,不收集哪些证据,在缺少司法理性的同时,也就缺乏客观公正性,那么危及公正司法,出现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2.选择性取证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侦查活动一般没有只收集涉嫌人有罪或无罪证据的可选择性,但这不等于说案侦司法人员完全没有选择收集证据的自由度。侦查取证有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案侦人员要提高取证效率,就需根据主客观条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这就不可能不加选择地乱收集证据材料。首先,有些证据虽然很重要,但是一时没有取证条件而无法进行收集工作,只能暂时放弃优先收集。一些证据虽然并非关键,但是其比较容易获得,案侦人员就会随机取得,以便此后进一步收集和补强。也有些证据初看并不重要,但随着取证的深入,关联材料增多后,逐渐表现出了其重要性。而有些时候,警方又存在同时收集若干证据的可能性,但基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又不能平均使用侦查力量展开同步收集,必须有所选择地分步实施,等等。这些,都是合理的。其次,具体到每一个侦查员,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有选择地收集各种证据材料。而且,在选择之中,他们的认识能力和业务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准确无误地找到真正的证据或最佳证据,而需不断地在材料选择中试错、纠错、查证和求证。在此过程中,在同等的条件下,他们就会优先选择收集对案件重要的证据,或者根据难易程度,优先选择容易收集的证据,先易后难地收集证据,等等。这些,也是合理的。最后,对一些社会影响面广、冲击力大的犯罪案件,其关键证据哪怕比较难取得,侦查机关也会千方百计地做出巨大努力,不惜千辛万苦地获取之。这种选择,是基于对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及其恶劣影响等的考量。评价侦查效益,不能只盯在效率上,还得照顾社会效果。犯罪毕竟是社会问题,衡量控制犯罪的成效,还少不了社会性的评价指标。这也是合乎常理的。
这些根据主客观条件的选择性取证,符合有限的侦查资源的现实状况,符合最大化地发挥取证效力的规律,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同时,这里的选择,是根据取证条件的选择,是先后分步实施中的选择,而不是做出只收集哪些证据,不收集哪些证据的选择。这种选择性取证,在一定的时空条件限制内,同样达到了全面取证的目的,因此具有相当的合法性。
(二)选择性用证的利与弊
运用证据材料,首先要正确接收和解释其蕴含的事实信息,并按照客观事实的发展逻辑去组织在案材料,以还原案情的事实真相。在这过程中,要按照法律要求,对案件材料进行选择,对证据事实进行理性构建,以形成法庭认可的法律事实。
1.选择性用证中的合理性。在侦查工作中,不仅有合理的选择性取证,更有合理的选择性用证。如果说侦查取证应该全面,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各种证据材料,不能有所偏好的话,在组织证据体系的阶段,对案件材料则应该有所选择,有所取舍,从而有序地构建证据材料,去突出事实重点,而不能一股脑地堆砌材料。警方组建证据体系之目的,主要是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要求法庭惩罚犯罪。而国家的公诉活动是控告被告人犯有罪行的活动,一切要用控诉有罪的证据说话,证据体系不能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因此,有所选择地用证是必然的。但这种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遵循全案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唯一性四个逻辑规则的要求。[2]它们是选择性用证的限制性条件。有了这些条件,选择性用证才具有合理性。在选择案件材料的过程中,真实性规则要求:每一份证据材料都要查证属实,能反映案件的实体和程序事实,而不是推论,更不是妄测。完整性规则要求:待证法律事实要件全面完整。案件的实体构成要件事实、取证和诉讼程序,需要证明的每一个环节都不缺少证据;而且,每一个案件事实之点,都不能是孤证,而需有起码的证据量。遵守了完全归纳法,形成了能够闭合所有证据的逻辑锁链。一致性规则要求:全案的证据本身、证据之间、证据与证明对象、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都能相互印证,并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若有疑点和矛盾,它们必须得到合理解释,从而排除其合理怀疑,遵守了不矛盾律。唯一性规则要求:在案证据之间有本质的必然联系,证据体系的结论具有排他性、唯一性,没有第二种可能,遵守了排中律。这四个逻辑规则,都要建立在全面收集案件材料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选择性地片面收集证据材料。有了材料的全面性,才谈得上完整性和一致性。如果在收集证据材料阶段,就选择性地只收集有罪和罪重的证据,组证阶段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就是虚假的人为现象,并不反映案件事实的客观真相。这种弄虚作假的选择性用证,也就并非合理。因为逻辑还有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之别。客观逻辑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主观逻辑是思维反映事物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人对事物规律的勾勒和描摹。如以上真实性的逻辑真假值、完整性的完全归纳法、一致性的不矛盾律、唯一性的排中律,这四个形式逻辑规则都是思维反映案件事实的主观逻辑。这种逻辑规则,往往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如果弄虚作假,可能表面上吻合“不矛盾律”,事实上是与客观事实本身的发展逻辑相背的。因此,在组织证据体系中,不能孤立地只看一两个规则,而必须四个规则联系起来,共同判断整个证据体系反映案件事实的情况。
客观事物是运动变化着的,其发展变化本身就包含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是要用辨证思维去反映的客观对象。而形式逻辑反映的不矛盾律,只是事物相对静止的局部现象。它有一定的限制性条件,证据体系的四条逻辑规则,都是这种情况。四条规则彼此联系和限制,它们以真实性为保障,以完整性为基础,以一致性为条件,以唯一性为限制,缺一不可。但真实性是对证据材料的起码要求。所收集的材料没有真实性,就不能保障其能反映案件客观事实的真相。
2.选择性用证中的违规性。在案侦活动中,不仅需要全面取证,更需要恰当用证。取证收集的在案材料,常常杂乱无章。在刑事诉讼中,不可能一股脑地将之全抛在法庭上。这就需要侦查员仔细甄别它们的真伪以及与案件的关联性及其刑事法律关系,运用它们去组成证据体系,从而证明整个刑事案件的事实真相。组织证据体系不是随意而为,必须按照案件事实发生发展的逻辑规律,将混乱无序的案件材料按照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归类组织。在组织过程中,必须遵循以上全案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唯一性四个逻辑规则,对证据材料进行精心选用、组装与拼接,使之成为有序的事实结构,以消除证据信息的不确定性,减少其熵值。在选用证据材料的过程中,如果违反了犯罪构成的法律要件和证据体系的四个逻辑规则,就会不同程度地造成案件质量下滑。严重的,就会形成冤错案件。在组证阶段发现疑点,有的侦查员不去分析疑点和查证疑点,只是为了消极地完成诉讼任务而回避矛盾。他们将有疑点和有矛盾的材料剔除掉,从而使在案材料人为地显得一致。这种选择性用证的结果,用表面的“一致性”,掩盖了事实上的不一致,就是一种虚假的一致。这与前述吻合“不矛盾律”的本质一样,也是一种弄虚作假。区别在前述“吻合”,可能在取证阶段就进行了不恰当的选择,这里则是在用证阶段才出现了不恰当的选择。许多人可能会辩解说,其所用材料都经过了查证,分别来看都是真实可靠的。可是,哪怕局部证据材料是真实可靠的,但其违反了全面性和完整性,也就在整体上违反了真实性。这种虚假的一致,建立在局部用证的基础上,其逻辑错误是以偏概全。在违反完整性、真实性的同时,实际上,仍然违反了一致性规则。这里要紧的是不回避矛盾,有疑点就要认真分析,查证疑点,排除合理怀疑。因而,遵守组织证据体系的规则,必须建立在公正全面地收集证据之上,选用证据必须是实质性地遵守四个规则,而不是自欺欺人地掩盖问题。掩盖证据中的漏洞和矛盾,常常是出现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
三、应如何选取证据和选用证据
(一)选取证据与选用证据相互渗透
在案件侦查中,取证和用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时常相互渗透。证据材料本身,首先需要得到证明,这就要接收和解释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信息,用证也就渗透在取证之中。这种渗透,尤其表现在组织证据体系、接近终结侦查的后期。有些关键证据缺失,需要补充收集;有些证据有误,需要重新辨识和鉴定;有些证据还是孤证,需要进一步收集和补证;有些证据仅有口供,还需收集物证佐证之;而有些人证的证明力不足,还需进一步补强,等等。在这些情况中,都是在组织证据的用证之时,才发现有进一步取证的必要。而在进一步取证之中,也有必要将之放在证据体系中去考量其证明力。当然,还有些证据是到了诉讼阶段,才发现有缺失、有毛病,需重新收集,或哪些证据还需进一步查证。这时,往往已经错失取证良机,或进一步查证的可能,就形成了疑难案件。这些自主性选择,都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当然,也凸显出了侦查员取证用证的基本功力。
在案侦司法活动中,由于侦办人员的能力存在差异,其选择性取证用证的自由裁量权,也常有种种偏差和出格的可能,甚至出现不合规、不合理、不合法等情况。这些情况就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侦办质量。比较极端的情况,就会造成冤案、错案、疑罪案件。案侦实践中,侦办人员应该如何选证用证?要懂得该怎样做,首先要知道不应该怎样做。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些选择性取证用证中的冤、错、疑刑事案件。它们像明镜一样,可以通过观察他人,审视自己,鉴别正误。冤错疑刑案的价值就在可从中吸取教训,悟出取证用证的正确方法。所以,有必要不怕露丑,认真总结。正视它们,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二)选择性取证用证与冤错案件
1.选择性取证中的错误。证据选择造成的错案,比较典型的,如黄家光围殴致死人命案。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城西管区,新岭冲村村民与哩敢村村民因琐事结怨。1994年7月5日下午,一村霸黄恒勇被人围殴而死。警察赶来时,村里年轻人都跑了,从外地打工回家探父的黄家光,恰巧从边上路过,被警察逮着要其带路去抓捕涉案人员。于是,涉案人都对黄怀恨在心,他们串通口供,诬陷黄家光也参与了围殴。[3]在这起群殴致死案中,光天化日之下,人证众多。警方只要摆正侦查公正的位置,黄家光有没有作案时间,本来不难查清,非常不应发生错案。可惜,侦查人员却偏信同案犯们的供述,而不听不信黄在外地打工、无作案时间的辩解。同时,在调查取证中,他们只收集对黄家光不利的证言,而不收集对他有利的证言。最后,法庭认定黄家光犯了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在监狱服刑期间,黄家光天天喊冤,坚决否认自己杀人,不断地申诉。2002年5月,当年诬陷他的人也有所悔悟。在三亚监狱中,他出具了《悔过信》,这才揭开了造成错案的真相。
黄案是选择性收集嫌疑人有罪证据,而有意忽视其无罪证据的典型案件。其实,这种选择性取证的动机,在许多案件中都普遍地存在着。由于侦查人员要迅速破案,完成打击犯罪的工作任务,追踪犯罪就成了他们的职业需要。带着这种职业压力侦查取证,就容易为完成任务而应付差事,只收集嫌疑人的有罪证据,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无罪证据。哪怕搞刑讯逼供,只要嫌疑人招认,对上、对外都能交账。因此,“公正”取证,对侦查人员是个极大的考验。
2.选择性用证中的错误。在组织证据体系过程中,案侦人员如果通过选择性用证,处心积虑地掩盖证据矛盾,即使一时掩饰成功,也难免最后要暴露事实真相。案件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总会从一些细微之处暴露出证据矛盾。还是以“黄家光围殴致死人命案”为例,指证黄家光参与围殴的同案犯供述和证人证言,与说案发当天黄家光在跟着他们一起搞装修的工友的证言之间,就明显地存在矛盾。而且,此案还有活着的被害人王文童和现场目击证人黄玉兰,[3]虽然他们不一定都叫得出案犯的姓名,但是他们既然是案件的亲历者,就可通过辨认等来甄别参与围殴的嫌疑人。他们的证言,比同案犯的口供更能从不同侧面去甄别案件疑点。可是,案侦人员为什么就不收集他们的证言呢?或者是虽然收集了,但却在组织证据体系之时,舍弃了、剔除了它们?这种选择性用证,说轻一点,就是为了图省事、偷查证之懒,而掩盖证据之间的矛盾,自欺欺人地组成了证据材料的“一致性”。说中性一点,有可能是急功近利,邀功领赏。说重一点,可能是办人情案,甚至可能是受人钱财,徇私枉法,等等。这种种不良动机,都掺杂了个人私利。其形成的证据“一致性”,就是人为选择的一致,掩盖了实质性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最终与“同案犯”的《悔过信》等相互印证,证明这种选择性用证铸就了冤错案件。这种人为选择的一致决不限于这一起错案,在一般的疑难案件中也非常多见,尤其是在疑罪案件之中。最后,它们都在证据材料中暴露了案侦人员当初不当取舍证据中的诸多问题。在取证用证之中,如果有种种私心私利掺杂其中,有选择性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选择取证的时机与用证的条件
收集证据是有时机的,许多刑事案件失去了取证良机,就失去了案情的真相。很多疑难案件,都是侦查人员没有抓住取证时机,其主客观原因错综复杂。一些侦查员不能正确处理个人私利与工作时机的关系,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消极怠工,而到后期用证组证时,不得不去补充取证,才发现为时已晚。错失取证良机后,他们却不从自身找原因,而归咎于客观原因。这种选择,体现出案侦人员的工作动机和态度,同侦查业务能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黄家光案中的人证,时间长久了,有些人就记不清案发当时的情境,有些证言与案情细节就难免有出入。这既需要侦查人员积极主动地及时取证,也需要他们有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常识,更需要他们有用客观物证去佐证主观人证的能力。如果态度消极,只图应付差事,而不多方面取证,尤其是不重视物证的收集与印证,就可能像黄案一样,仅凭单方面的供述和证言,就铸成了错案。当然,在这里,侦查员还有习惯性推定嫌疑人有罪的心理,这也有碍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这种心理,在案侦过程中也非常普遍,需要侦查员自我警惕。
用证组织证据体系,直至得出全案的唯一性结论,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要有客观方面的证据认定,也要有主观方面的逻辑把控。侦查员不能任性而为,更不能凭空捏造。以上组织证据的四个逻辑规则,缺一不可。有了这种底线,才有减少选取和使用证据出错的可能,降低出现冤错疑案件的风险。
四、排除与认定中的选择性取证和用证
在侦查过程中,排除嫌疑人或认定嫌疑人,都需要有相应的事实材料,这就难免要选择性用证。但在这里,排除与认定的证据标准,却是大不相同的。排除犯罪嫌疑,一般并不要求组织严密的证据体系,而只要有一两个关键证据就行了。但是,认定犯罪嫌疑,却需要按照四个逻辑规则,组织逻辑严密的证据体系。在实际案侦司法中,应该怎样正确地取证用证?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一些耳熟能详的冤错疑案件。
(一)本应用证排除嫌疑的,却选择了认定嫌疑
在2003年杭州“5·19”二张叔侄强奸致死案中,死者王冬8个指甲缝中,DNA鉴定并非是二张叔侄的,而另有其人。本来,就此可以排除二张的嫌疑。但侦查人员却不愿这样去做有利于二张的排除,而一门心思地要去认定他们的嫌疑。侦查员认为,死者手暴露于外,接触物多,其DNA鉴定很可能与案件无关,仍然不能排除二张的嫌疑。这里的有罪推定,并非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而是建立在“可能”和“仍然”的推论之上。这就违反了组织证据中的真实性规则。
侦查员认定,奸杀是二张所为,理由就是死者与朋友最后通话的手机是二张的。但手机,是非常间接的孤证。认定罪行,每一事实点都要有起码的证据量,而且需组织逻辑严密的证据体系。二张辩解说,案发当晚,他们的车到达杭州西站后,王冬借他们的手机打电话,要朋友过来接她,但是朋友要她乘出租车到钱江三桥后再联系。叔侄俩便把她送到离钱江三桥更近的艮秋立交桥。王冬下车后,他们便把手机留给了她,好让她联系朋友。然后,他们从二桥上高速,开往上海。但侦查员不相信他们的辩解,认定手机和奸杀有关,王被奸杀一定是他们所为。在这里,“手机”只是一个非常间接的物证,它并不能单独认定奸杀这个犯罪事实。相反,王冬8个指甲缝中同一男人的DNA谱带,足以说明不是她偶然触摸进入指甲缝的,而在搏斗抓扯中进入的概率非常之高。在一审二审期间,这份DNA鉴定曾引起激烈争议。辩护人认为,它足以排除二张作案的可能。但是二审法院最终视之为“与本案犯罪事实无关联”。[4]这里,面对两个物证,司法机关却认定了最不可能的手机,而排除了最有可能的DNA鉴定。直到2013年,再审公开宣判后,公众才看清该案漏掉了DNA鉴定指向的真凶勾海峰,而冤判了借手机的二张。
在这里,取证阶段的问题不大,两方面的证据都收集了。但在用证阶段,却选择了真正“与本案犯罪事实无关联”的手机,作为认定二张有罪的证据。其背后,显然是绝对地不相信嫌疑人的辩解,而偏执地将臆测作为确凿的证据使用。本来,认定犯罪嫌疑,应该有查证属实的确凿证据,并要进行一系列严密的逻辑推理。但这种建立在妄测之上的“可能”,对证据材料的选择运用却没有排除合理怀疑。整个证据材料所形成的体系,不具有真实性,缺乏系统的完整性,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没有一致性,其结论也就不具有唯一性。
(二)本应用证指向另一嫌疑的,却选择了伪装现场等说辞
再看“于英生杀妻案”。1996年12月2日上午,于英生之妻韩露在家被害。司法机关认定,案发当天,于英生因琐事与妻子发生争执,在厮打中致韩死亡。为逃避法律制裁,于伪造了强奸杀人的现场,试图制造液化气爆炸来掩盖犯罪行为。起诉书中,列举了现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于的供述长达50多页。但于英生说:警察对我不间断讯问、折磨,连续7天7夜。下雪了,他们让死刑犯舀凉水给我洗澡,洗了3个小时,让你要死要活都不行。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写,写你的认罪状。那没有的事,怎么写呢?他就叫你编,你就编吧。最终,经6次审理,2000年,法院改判于英生的死缓为无期徒刑。
同司法机关选择的有罪证据相反,在于家梳妆台抽屉边缘的2枚外来的陌生指纹,本来可将侦查线索引向真凶。但侦查员却弃之不用,而千方百计地将犯罪嫌疑往于英生身上引。而且,侦查员为了排除证据矛盾,他们还在移诉中隐匿了该嫌疑指纹。他们说,现场除了于英生一家3口的指纹,再没有外来的指纹信息。后来,省检察院复查该案,到蚌埠收集证据时,才发现了这2枚陌生的指纹。这2枚指纹,6次法庭审理都未提及,说明它们并未被移交法院。这也说明,警方虽然取证之初收集了它们,但是后来组织诉讼材料时,却舍弃了它们。而且,警方在于妻内裤残留物中还检出了精子;DNA比对分析表明,该精子不是于英生的。辩护人将之提交法庭,替于英生作无罪辩护。但控方认为,于妻内裤上的精子源于他人用过丢弃的避孕套,被于英生捡拾,用来伪装犯罪现场。这种说辞,只是一种推测,不是确凿的证据。但法庭和检方对此都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却对于英生的辩解置之不理。
判决之后,于家人开始了12年的申诉。17年后,在无法合理排除该案证据之间矛盾的情况下,安徽法院首次执行了“疑罪从无”的判决。此后,警方才启动再侦程序,通过从被害人内裤上的精子DNA比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武钦元。武为蚌埠市一名交警。他供述,案发当日早晨,他进入于英生家中,见韩露身着睡衣独自在家,遂心生歹意,对其实施强奸。作案过程中,武用枕头捂住韩面部,致其死亡。此后,他伪造现场后逃离。[5]令人费解的是,当初,侦查员为什么就忽略了DNA鉴定这样重要的证据?为什么要隐匿现场他人指纹这样关键的证据?而司法举证用证的过程中,检方和法院又为什么对被告人的辩解不听不查,不去排除合理怀疑?在案侦司法的取证用证过程中,这一系列的错误选择,最终导致了这起冤错案件,令人唏嘘不已。
五、选择性取证用证造成的疑罪案件
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疑罪从无”的理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千呼万唤,终于付诸实施。它使一些陈年旧案暴露出了证据矛盾和疑点。但此时,案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取证时机,甚至根本就无法再补充取证了。这使当初选择性取证和用证的弊端最终显现,暴露无遗。这种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补救性取证的案件,其证据疑点,最后只能存疑。这就导致疑罪从无的司法判决。下面,再看看两类典型案件。
(一)福建念斌投毒案中的选择性取证用证
福建平潭念斌投毒案,是“疑罪从无”的典型案例。2006年7月27日,房东陈炎娇母女和丁云虾的3个孩子共进晚餐,4人出现中毒症状。次日凌晨,丁家10岁的儿子俞攀和8岁的女儿俞悦抢救无效身亡。公安机关侦查认为,邻近摊位的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因两家平日有矛盾,警方监听了念斌和其妻的通话。听闻孩子死去,念妻两次质问是否他下毒。念斌默然。念斌到案后供认,因他对丁抢走其顾客不满而将鼠药投入丁家厨房的烧水铝壶中,致丁、陈两家人食用壶水煮的饭菜后中毒。[6]经8年诉讼,念斌4次被判死刑,又3次因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该案选择性取证问题异常突出,警方向法庭提交的讯问光盘,在10分55秒处存在明显的断点。而断点处,恰好就在念斌从不招供到招供的节点。公安部的鉴定意见,却是没有断点。原来,侦查员用无断点的录像光盘,贴上与交法院光盘同样的标签,送公安部鉴定。得到无断点的鉴定书后,才将之交给法院。[7]再审质证中,侦办人不得不出庭承认,音像断点处有2小时中断。但这2小时,不是在搞刑讯逼供,而是在“说服教育”念斌。双方交易,不抓其老婆,念斌就按公安说的做。接着公安教他怎么说,被掐掉的就是这个交易过程。所以,音像里才会出现念斌开头一直不说,后来突然开始交代的情境。[6]这种偷梁换柱的掉包行为,涉嫌伪造证据,掩盖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
这里的选择性取证用证,是侦查员在按照自己的推测制造和使用证据。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监听认定,其后的取证用证,都是在围绕这种认定做功课。询问证人时,在做鱿鱼和稀饭的水这一关键问题上,陈炎娇称“用的是红塑料桶里的水”,丁云虾说是“水壶里的水”。二人的证言存在矛盾。侦查员应当深入查证,但他们却将陈的3份证言隐匿起来。而在后来再次询问陈的笔录中,就将做鱿鱼和稀饭的水直接改写成“用水壶里的水制作的”,以便消除证言矛盾。警方没在吃剩的食物、呕吐物和死者的肝、胃和胃内容物里检出鼠药氟乙酸盐,但是为了形成认定氟乙酸盐中毒的结论,他们隐匿了剩鱿鱼汁、胃内容物等关键证据,却从死者的心血、尿液和呕吐物中检出了氟乙酸盐。这种检出,是将氟乙酸盐标准质谱图复制成两份,一份写上俞攀呕吐物对照标样,一份写上“俞悦尿液”。然后,又用一份来历不明的含氟乙酸盐的物品,制作两张质谱图,一张写上“俞攀呕吐物”,一张写上“俞攀心血”。[6]这种取证中的隐匿和造假,也是一种选择。这种作伪的选择,没有合理的解释,导致了一系列矛盾和混乱。如水壶没有检出毒物,水壶里的水却检出毒物;用高压锅煮的稀饭没有毒,高压锅却检出毒物。这使检验报告大受律师质疑。由于检材的提取和送检程序都存在着操作不规范和违法等问题,该证据最后被法庭排除。2014年8月,终审宣告“被害人死于氟乙酸盐鼠药中毒的依据不足,投毒方式依据不确实,毒物来源依据不充分”,念斌无罪。宣判之后,平潭警方很不甘心,又重新对念斌立案侦查,念仍然没有摆脱犯罪嫌疑。
(二)吉林刘忠林杀人案中的选择性取证用证
吉林省东辽县凌云乡会民村,1989年,该村少女郑殿荣失踪。1990年,村民修河,挖出她的尸体,发现其已怀孕20~21周。再审该案时,已经事隔28年,被埋葬的郑殿荣尸骨已经丢失。原审判决生效10年后,先前的取样也被全部销毁。再审法院原来准备做亲子鉴定,以甄别犯罪嫌疑人刘忠林与胎儿有无亲子关系,但已经没有可能。那么,当初警方为什么没有做鉴定,或者是做了,为什么在案材料中没有显示?这就是个很大的疑点。而且,造成这种疑点的责任,在侦办一方。若实施责任倒查,就得有人担责。况且,就是胎儿和刘有亲子关系,刘忠林存在作案动机,但这并不能就推定他实施了杀害郑的作案行为。在这里,证据材料应该查证落实,而不应该是推论。同时,此案的关键证人江久英说,在种土豆的某一天,刘忠林对她说:“小荣子怀孕了,我得领她把孩子做掉。”还叮嘱她:“别跟人说,说出去我就没命了。”这是警方锁定刘的关键证据。可是,刘的律师对此提出质疑:东北种土豆的时间,大概为3、4月份。郑死时怀孕4个月左右,她只能在5月份才知道自己有孕的情况。刘忠林提前就告诉江这一情况,非常不现实。而且,郑殿荣失踪时,是有其侄女郑春梅相伴的。郑春梅虽是聋哑人,但她比划着描述,绑架郑殿荣的2~3人中没有刘忠林。[8]可见,一般证人与目击证人之间的证言存在矛盾,这就使当初对刘忠林的有罪判决存在很大问题。而再审时,证人江久英等已亡故,无法进行法庭质证,使此案物证和人证的疑点都无法理清,只能存疑。这就反映了侦办案件取证与用证中的不严谨问题。它们使此案,也形成了典型的疑罪案件。这大概是法院决定再审此案后,拖了4年后才开庭,而开庭后,又拖了2年的一大原因。2018年,吉林省高院再审,才认定刘忠林无罪。这最后的无罪判决,也是典型的“疑罪从无”的判决。这暴露了当初选择性取证和用证中的不合理、不合法等问题。
(三)疑罪案件并没有使当事人获得正义
在念斌投毒案中,当无罪判决一锤定音后,伸冤者瞬间转变成了被害人丁家。对他们来说,案子再次成为悬案,真凶依然无着,正义仍然缺席。宣判当天,当地综治办反复叮嘱念家人:如果判决无罪,不要放鞭炮庆祝,以免丁家亲属受到刺激。受害人家属则要求法庭对念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2个中毒死亡孩子的爷爷,一提起念斌就激动得挥舞双手。他说:“8年了,来来回回地判,凶手居然逍遥法外!2个孩子没了,谁给我们一个说法?”[9]而害怕被害人报复他的念斌,仍借住在朋友家,东躲西藏。尤其在平潭警方又对他立案侦查后,他更感到自己还是个嫌疑犯。
在于英生杀妻案中,刚开始警察上门告诉于的岳母,说于英生无罪释放了。其岳母不接受,认为于还是凶手:“你们拿张判决书,说他杀人就杀人,说他没杀就没杀了?”直到真凶落网,岳母才认他。老人哭了,说女婿怎么受了这么多年委屈,代别人坐了这么多年牢。[5]可见,“疑罪从无”的判决,并不能使当事人获得真正的正义。对社会公众而言,更是这样。选择性取证用证的失误,使案件的真相缺位,就缺乏实现正义的起码基础。
六、选择性取证用证与案侦司法人员素质
司法活动都要通过证据材料去反映案件事实,证明案情真相。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追求公平正义。否则,案件事实真相缺位,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在追踪犯罪活动中,需要侦办人员识别案件材料,接收证据信息,判断和选择证据材料。而选用证据材料组织证据体系,则是还原案件事实的必然途径。在这些活动中,都极难避免要选择性取证用证。而其证据信息的正确判断和确定本身,则需要案侦司法人员具有相应的能力。在选用案件材料证明案件事实过程中,他们选择得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时常鱼龙混杂,全凭案侦人员的素质加以把控。
在刑事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既然难免要在案件材料中进行选择性取证和用证,那么,关键就在如何选、如何用,需要遵循怎样的司法原则,是在全面收集证据的前提下选用,还是在有限收集证据时就选用;是根据客观条件进行选用,还是根据主观意愿进行选用;是有罪推定后才进行证据选用,还是在选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推定有罪的结论;是为完善证据体系结构和加强其证明力地选用,还是只顾突出局部之点而不顾及其余地选用,等等。那些典型不典型的冤错疑案件,无不因选错用错了证据材料使然;而那些典型不典型的成功案件,也无不因选对用对了证据材料使然。因而,怎样选证、如何用证,其具体的选用办法,很值得案侦司法人员认真对待,慎重考量。用什么样的法律理念进行选择,以什么样的证据标准进行取舍,用什么样的司法原则进行使用,以什么样的诉讼目的进行组证,在这些考量中,案侦司法人员不枉不纵的敬业精神,及其公正执法的素质至关重要。它们足以照见其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而冤错疑刑案,都无一例外地同选择性取证用证的能力差相关,都同不恰当地处理个人利益,敷衍塞责,追求表面破案率,甚至徇私舞弊相关。
提升案侦人员取证用证的能力,不仅仅是业务素质的问题。可以说,在所有的疑难案件中,都有取证失误的问题;在所有的冤错疑案件中,都有用证错误的教训。但是,不能孤立地看待取证用证的业务素质。在这里面,除了错失取证良机等问题,许多案件像二张叔侄案和于英生案那样,从在案证据就能锁定案犯,却在用证中出了大差错,办成了冤错疑案件。从中可以看出,案侦业务素质还错综复杂地与人品联系在一起。从冤错疑案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起码的人品等综合素质,是案侦司法人员相当重要的素质。同不能想当然地推定嫌疑人都是有罪的一样,也不能想当然地推定案侦司法人员都是公正的。在这里,需要职业能力的磨砺,更需要职业制度的约束。就职业操守而言,不能要求人人都大公无私,只讲奉献不讲报酬。在侦查效益的激励机制中,个人利益应该兼顾。关键在要通过恰当的奖惩激励机制,引导人追求高质量的侦破效益。而一旦出现冤假错案,则要进行责任倒查,终身追究。这些措施,在司法改革的责任制中已经明确,关键在落到实处的问题。有些案件,当初取证条件不好,有可能出现差错,但案侦人员对此要有足够的警惕性,随时准备纠正失误和差错,而不能为了自身利益有意回避,将错就错。如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当初地方公安局不能对堰塘女尸做DNA鉴定,他们是通过佘妻娘家的辨认,确定女尸为佘妻张在玉的。而主观辨认出错的可能性极高,用证时就需多方查证。但当别地有人作证说,出现堰塘女尸后,他们还见到了张在玉时,侦办人员竟然堵塞言路,不让村民作证。这就是职业操守问题。侦办负责人吊打佘,佘说某局长:“你要对今天的行为负责。”这局长居然冲佘喊:“老子知道不是你。但你不坐牢,老子就得坐牢。”佘母上访、佘兄申冤、村民作证,都被关押,[10]其目的,是为了隐匿对自己立功受奖、升官发财不利的证据。这种将错就错,相当恶劣。考量证据,首先在考量取证用证之人。要把住选择证据之关,首先要把住选择案侦司法人员之关。取人先于取证,用人重于用证。对害群之马,就应该清除出公安队伍。流水不腐,吐故纳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才能促进案侦司法队伍的活力。这里,除了需要人的自觉性等个人品格,更需要用制度去管理人,督促人。
七、结语
选择性取证用证虽然相互渗透和补充,但它们在案前案后仍有所侧重和不同。一般来说,案侦的初始阶段,证据材料较少,侦查活动多以广泛取证为主。从许多典型案件可以看出,这时的侦查方向和证据情况不太明确,只要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侦查员多能较为客观地筛选案件材料,相对公正地收集在案证据。而案侦的后期阶段,证据材料较多,侦查便慢慢偏向以用证组织证据体系为主。在证据材料的逻辑指向性中,侦查员也就容易形成一些定式思维。这些定式思维若指向正确,可以较为迅速地锁定嫌疑人,而破获案件;但若指向有误,则很容易为假象迷惑,从而干扰侦查员的正确判断。这时,如果侦查员存有应付差事等私心,就可能让侦查行为走入歧途;如有急功近利等杂念,就可能失去取证用证的公正性,甚至明知有错而将错就错,造成冤错疑案件。因此,在考量取证用证的选择性中,不能不考量案侦司法人员的人品等综合素质。我们要充分利用冤错疑刑案的价值,使其照亮选择性取证用证的公正之法。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让坏事转变为好事。
——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