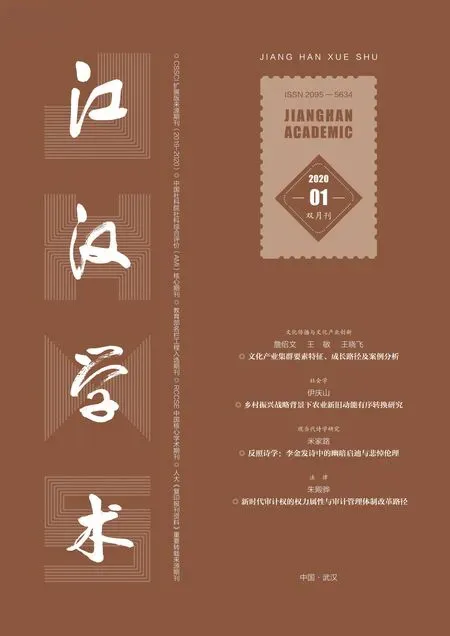反照诗学:李金发诗中的幽暗启迪与悲悼伦理
[美]米家路(文),赵 凡(译)
(1.美国新泽西学院 英文及世界语言文化系,新泽西 幽茵 08628;2.云南艺术学院 文华学院,昆明 650102)
一、反照叙述:一种亵渎性启迪
反射光或折射光是贯穿李金发诗歌的母题,我称其为“反照性诗学”(poetics of reflexivity)。反照性/自反性诗学是对李金发的整个主题学进行有效性解释的一个考验,与此同时,反照性诗学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叙述里涵盖身份与自我构成的诸多话题。用卡林内斯库的话来说,美学的个人主义是界定颓废的关键[1];颓废美学真正的主角应是“自我的崇拜”[2]20;颓废的主要特征在于“事后考虑……反思……沉思生命的美德,及其情绪与突发事件;在于过度精细与造作的恶习”[2]15。阿多诺在讨论现代忧郁与无聊中的内部(intérieur)意象时,同样将反思解释为忧郁意识的本质性隐喻[3]。克尔凯郭尔亦将现代概括为“反省的时代”(reflecting age),其特征在于,削平与抽象化令人生畏的清晰,本质上同一的诸意象的某种粗表流动,以及内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无法弥补的裂痕②。因此,反照的母题明白无误地捕捉到了现代性状况中自我的某些本质。于是我们在波德莱尔中读到:
明晃晃的巨大镜面,
被所映的万象惑迷![4]312
换言之,作为返回黑暗、困倦、寒冷、潮湿、泥泞洞穴的结果,由于背对启迪的阳光,人类所能感受到的唯一光源便是从背后传来的折射光,这光显得幽暗、模糊且扭曲。与郭沫若的强健身体转向作为自我之基本能量的太阳、光亮与火焰不同(“太阳哟!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你。/太阳哟!你不把我照得个通明,我不回去!”)[5],李金发诗中的形象被太阳所眩至盲,因而转离了太阳,对自我的启迪由此被拒斥。随后,黑暗洞穴中的自我转向镜子、玻璃、水晶、大理石、花岗岩、宝石、钻石、月亮、水、雪、冰、雾、泡沫与苔藓,除了源自元素本身的光之外,它们自身中未包含一丝“原初的自然光”。太阳、星辰与行星在它们内部折射,并通过它们传递③。因此自生光与折射光之间的剧烈差别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化叙述中与自我塑造有关的另一种话语转向。随着这一质变性转向的发生,中国现代性叙述中自我的反照意识便随之崛现。
(一)自生光与反射光对自我塑造产生的基本差别
在“我”或观看者与自生光的源头——太阳之间,存在一种生物关系(bio-relationship),因此,眼睛/“我”(eye/I)接收径直传递的光。对于“我”来说,自生的太阳完全自足、透明,且是向心式的;“我”与光源的距离纯而无杂,因为“我”即太阳,太阳即“我”,因此,向着启示的太阳流动的“我”可以被视作对自我的绝对赞颂,中心的“我”之自主性在郭沫若《天狗》——“我便是我呀!”——的吞噬行为中得以阐明,尽管这种自主—自我(auto-self)被兴起的民族主义所背叛。郭沫若自生光的唯我论创造出一种永远进步,永远凯旋的“我”,向着自身返射的自我,诸如此类的反思空间却不会相应地出现,在中国现代性的话语中,自我与身份的叙述因此被镌刻上某种匮乏。
就后者来说,则内存着一种三角关系:“我”经过镜像的中介,抵达光的源头——太阳。因为光芒并不直接传至眼睛/“我”——“眼角膜、黏性体液、眼球晶体、视网壁”——而是通过镜像的反照,因此,对“我”来说,光源是间接的、离心的、他者指向的。“我”与光源间的距离遥远而破碎。伴随着光对眼睛/“我”视作反照的镜面物的照亮,“我”由此经历了镜面物反照中的光/生命。此处的分裂将这反照重复为间接的双重迂回:光源与镜面物的反照;眼睛/“我”又再次反照镜面物中的反射光。对重复本身的再重复并未创造出同一性或相似性,却创造了破坏其统一性的差异、剩余与他者性。
就此意义看来,德里达的论述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此种双重反照:“不再存在单纯的起源,因为被反映的东西本质上被一分为二,并且不仅仅是它的影像的自我补充。反映、影像、摹写将其复制的东西一分为二。思辨的起源变成了差别。能反观自身的东西并不是一;起源与其再现、事物与其影像的相加律是,一加一至少等于三。”[6]在这种双重反照中,“我”的直接对应物同自生光源一起被阻隔了;最初的光源被永久地拒斥。所以,“我”不得不生活在镜面物中,或立于镜面物前,或依靠着镜面物。正当“我”眺望镜面物的反射光时,一场危机突现;在镜面物中,对“我”自身的反映显得空洞、匮乏和虚妄,“我”显现为非我与分裂的自我,这些皆来源于一个隐形而模糊的深渊处。经过此种反照的启示,自我危机的觉醒时刻如约而至——折回镜中自身的瞬间④。
正如被照亮的并非真实,而是自我的虚妄,“我”并不在场,也没有“我便是我”,却有“我是一个他者”(“Je est un autre”),一个非我。因此对启迪的亵渎乃是经由一个自我反照的异度空间才得以进行⑤。中国现代性的状况,应归因于根本不同的光源图景:要么作为自生光转向太阳,要么作为反射光转离太阳。力比多能量经济学的不同形式也由此建立:通过将身体与光源相认同,郭沫若创造了饱含生命冲动的自我;而李金发则通过眺望镜面物中的反射光,使自我发散为一个个分裂的自我⑥:
曙光反照出每个人的
有死的恐怖的脸颜
(《无依的灵魂》)⑦
(二)李金发诗中反照的三种交错形式均能被分辨
1.反照光中的他者性
正如上文所述,“我”在镜面物中映射出自身,而镜面物则依次反射源于太阳、星辰、行星与天空的光。这些镜面物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矿石、镜子、玻璃、水晶、大理石、花岗岩、宝石与钻石;另一类是自然意象、月亮、水、雪、冰、雾、泡沫、浪与露。所有的这些物体本身并不释放任何光,但它们内部都共同具备反射或折射的能力,它们可以反射/折射太阳光。换言之,如果太阳系不再把光洒向这些物体,那么它们也就变得黑暗无光;或者说,如果这些物体的表面被污染、破坏与遮蔽,那么它们都将失去反射的能力。⑧
除了具备反射的能力外,它们还拥有相同的触点,亦即都用表面来反射外来光,它们所反射的亮光从不进入其内部与深处。因此,反射光无法穿透,只在表面流动。从质量上看,除了大理石、钻石和花岗岩外,第一类的镜面物性质脆弱;除了月亮外,第二类的镜面物性质短暂。就此看来,当“我”眺望镜子时,镜子反映出的自我显得遥远而虚幻,也就是说,镜子反映出的并非是“我”,相反却是“非我”:“不足信之夜色,/亦在镜屏里反照,/直到月儿半升,/园庭始现庄重之气息”(《乐土之人们》);“我”一闪而过的一瞥显得古老:
无定的鳞波下,
杈桠的枝儿
揽镜照着,
如怨老之歌人。
(《柏林Tiergarten》)
镜中反映的“我”本身乃是一个空虚、无限的深渊,这深渊逃避对自我的把握。反映在镜中的部分作为一种分裂,将自身腾空为他者,因此,反映在镜子内部的部分作为他者,与处于外部(extérieur)观看的“我”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
无底底深穴,
印我之小照
与心灵之魂。
永是肉与酒,
黄金,白芍,
岩前之垂柳。
无须幻想,
期望终永逃遁,
如战士落伍。
饥渴待着
罪恶之忏悔,
痛哭在首尾。
(《无底底深穴》)
反照叙述的主体呈现在这些自然意象中:月、浪、雪、冰、雾、泡、露。与镜面物的坚硬易碎不同,自然物显得瞬息与易逝,易于腐朽,比镜子激发更多的冷感。李金发在一首诗中描述了他生活在黑夜中的恐惧,站立于愁惨的景象里,倾听活物们痛苦的抽泣。他希求上帝的光芒能替代他深深的悲伤,但是:
反照之湖光,
何以如芬香般片时消散;
我们之心得到点:
“Qu’est ce que je fais en ce monde?”
(《夜归凭栏二首》)
水之反照中的青春易逝性同样表达于另一首诗中:
你当信呵!假如我说:
池边绿水的反照,
如容颜一样消散,
随流的落花,还不能一刻勾留!
(《温柔》)
间接反射光中的“我”不仅仅缺乏深度、转瞬即逝,且由于光源——太阳的分隔,而显得无力。在诗歌《不相识之神》中,李金发将虚弱无力的“我”比作雪后无法走出残道的爬虫,陷于困境,心力憔悴:“我们蹲踞着,/听夜行之鹿道与肃杀之秋,/星光在水里作无力的反照,/伸你半冷之手来/抚额使我深睡,/呵,此是fonction-dernier!”(《不相识之神》)。有时,反照唤起了诗人的恐惧:“夜潮追赶着微风,/接近到凄清的浅堵,/稍微的反照之光,/又使他退后了。”(《十七夜》)
除了令生命凝固的雪的形象外,“举目一望,/更可见昆仑积雪的反照。”(《给Z.W.P》),另一个反照形象是水上的泡沫,它展示出“我”漂浮无根的衰颓状况。泡沫准确地显示“我”漂浮于水面的经验,它尽可能地寄生在无深度的表面。泡沫代表着缩减至最浅显的琐屑与无意义外表的生活或自我。将自我搅得六神无主的漩涡不过是在间发性的单调与平庸中空虚地重复自己。在无效旋转的反照中,“我”感知到了行将就木的恐惧:“夜来之潮声的啁啾,/不是问你伤感么?/愿其沫边的反照,/回映到我灰色之瞳里”(《断句》),还有:
浪儿与浪儿欲拥着远去,
但冲着岸儿便消散了;
一片浮沫的隐现
便千古伤心之记号。
(《à Gerty》)
2.在反照叙述中,双重反照是自然意象中最特别的
双重反照发生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当超验物渐趋平稳,镜子的后面除了反照在镜中的“我”,以及从镜内(例如从反照中)看出的“我”以外,什么都没有。最终,“我”成了镜中的“内部”的复制品——被当作现实来把握[7],与此同时,亦被当作外表来把握。在复制的过程中,“我”的双重反照或双重的间接性便由此生成:
吁,这等可怕之闹声
与我内心之沉寂,
如海波漾了旋停,
但终因浮沫铺盖了反照,
我无能去认识外体
之优美与奇丑。
(《柏林之傍晚》)
另一方面,反射光中对“我”的反照并非毫无间隙地复制,亦非毫无瑕疵的运转。在“我”的景象与反射光之间张开了一条裂缝,这条裂缝劈开了反射光自身的反照,在充足的反照中产生出剩余与差别。这种剩余或分隔使反射光再次反照,从而组成了一个最终延宕反射光之返回的第三者,并进一步拒斥了来自自生光源(自然之光)太阳之启示。因此,这种双重反照中的剩余所提供的双重扭曲不仅仅出现在“我”所是之上,也出现在“我”所非是之上,亦即出现在自我之上的反照,也出现在他者之上。[8]
李金发在一首诗中描绘了一个饥饿、干渴的受伤诗人,他激情如火,但创作时,笔中却无墨;奏乐时,琴弦却崩断:
松软了四肢,
惟有心儿能依旧跳荡。
欲在静的海水里,
眺望蓝天的反照,
奈风来又起了微沫。
(《诗人凝视……》)
双重反照中的第一次反照即为海水对蓝天的映照,但覆满白云的蓝天本身,除了对太阳这一自然光源的反照外,并不释放任何自然光,这便是第二次反照。当蓝天的反射光(蓝色本身就是阳光的七种基色之一)遇到海水表面的反照,而映入“我”的眼睛时,这便构成了第三次反照。然而,反射着上空被反照的蓝天的海上浮沫,也反射着被反照的海水,这些泡沫依次反射蓝天下被反照的事物,从而形成双重反照,而泡沫却阻断了蓝天与海水之间反照的平缓流动,也阻断了“眼/我”与海水以及海水中蓝天的反照。
在此情况下,任何与光源的直接接触皆不可能;空间的界限被切开了两次或被散布了两次。正是这双重循环与双重分隔产生出一种反照剩余,在“我”/眼之上两次重叠,一次在“我”所是之上,一次在“我”所非是之上。换言之,这一双重切割的剩余物召唤某些介乎于镜子中间的东西,将某种反照性构想视野安嵌在其内部与外部。这种双重的反照意识与自我的形塑相关,其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化叙述来说,乃是李金发在其诗中所创造的最有意义的范式。它有别于郭沫若在力比多能量组成的叙述中永不回头的突破进取。
激发自我之物质性空虚的另一类事物则是植物花草,比如苔藓、莲花与芦苇。莲茎与芦苇的内部中空。利用莲花和芦苇作为自我的修辞能有效地描绘出“我”的状况。因此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诗句:“老大的日头/在窗棂上僵死,/流泉暗枯在荷根下,/荷叶还临镜在反照里”(《秋老》)。荷叶在反照的平面中看着它的根,这种看取消了二者间的距离,并将它们带入水平的无深度表面。此时,叶子向着自身弯曲:向着自己所长出来的根弯曲;向着自己生长的生命源头弯曲。
双重反照又一次在这修辞中出现了。荷叶向着它生命开始的根部上返射,这是第一次反照;接着,它们不得不从自己开始弯曲的根部转身,这是第二次反照。第一次反照暗示了“我”之所非是的自我意识之觉醒(叶子对其根的质疑,所以叶子的返射只是为了看);第二次反照则承载着“我”之所是的自我反照意识——一个由第二次反照所补偿的“非我”(“not-I”)或一个经过了异己(non-self)之原初反照的成熟自我。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反照之间生出了本质上的差别。然而,它们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紧密地相互关联。任何文化生长或自我塑造都必须经过这种双重反照性而进行。从这一角度来看,李金发在诗中所揭示的双重反照得以构成中国现代性与启蒙话语中自我反照叙述的辩证法。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已经讨论了三类事物中显现的反照叙述:矿物意象、自然意象与植物意象。我们的细致探求开始于两个光源:自生光源与反照光源。我们已经涵盖了至少四种基于李金发所呈现的力比多能量经济的理念,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化的一般叙述中的理念。通过这一反照修辞,我们已经发现了“我”或自我,起初在镜子的空处及无深度的内部,紧接着的分裂使“非我”诞生,之后对表面的复制被当作现实,最后借助反照中分裂的剩余物而产生双重反照。就此而言,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双重反照乃是李金发诗歌中反照叙述的根本,同时也是重塑中国现代性启蒙大业内中国现代身份的根本。
另一种反照叙述的形式主要显现于矿物世界。让我们回想一下,矿物世界即是一个人造天堂。如上所示,反照的产生乃是光从自生光源(自然之光)中转离的结果;反射光与自然光相比并不自然。如此一来,所有从矿物质释放的光——镜子、水晶、钻石、宝石、大理石、花岗岩、玉石、陶瓷——经过反照后显得并不自然。在矿物质形式中非自然光与自然光的比较,即为反照叙述的第一层含义,它与我在此处讨论的颓废美学有关。在《巴黎的忧郁》中有一首题为《邀游》的散文诗,波德莱尔在此诗中创造了一个理想之地,充满了奇妙与精致事物的奇妙乐土:镜子、金属、布帘、奇香、光亮的涂金家具。他重新探索了花朵与绚烂的宝藏:“那是奇异之国,胜似任何其他国家,就像艺术胜过自然,在那里,自然被梦想改造,在那里,自然被修改、美化、重铸。”[4]4-19在《恶之花》中有一首题为《巴黎的梦》的诗,波德莱尔在诗中将大理石宫殿、钢铁、石板、黄金、铅、结晶、金属、玉、镜子、水瓮、金刚石、宝石称作“奇妙的风景”:
一切,甚至黑的色调,
都被擦亮,明净如虹,
而液体将它的荣耀
嵌入结晶的光线中。
对于波德莱尔来说,这些被擦亮的、如虹的矿物质能激起无限的梦,与现代之美的愉悦。因此,人工的美优于自然的、真实的美。这便是我想阐述的反照叙述的第二层含义。
在波德莱尔的诗学中,未经人类改造的自然完全是一片蛮荒,它培育邪恶的土地,因此与罪恶相联系。一切自然之物于美学意义上的美丽无涉,而理应遭到唾弃。波德莱尔的浪荡子在于他是一个崇拜人造物,以及反常古怪性的美学英雄,遭受彻底羞辱的自然被迫偏离常轨,进入不正常之美的领域:“浪荡作风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9]尼采也将颓废描述为:“疲惫者的三大兴奋点:残忍、做作、无辜(白痴)。”⑨对于有机自然的极度贬低,以及对作为人造物的现代性的赞美致使自然处于堕落的状态:一个死了的自然(a nature morte)[10]159-201。从这一角度来看,矿物世界中的反照叙述(并非自然矿物本身,也非未遭污染的原矿,而是被磨亮抛光的反照矿物)表达了从有机生命向无机生命,从充满活力的身体向死气沉沉的矿物,即从自然向非自然的美学质变。李金发诗中的美学质变的特征则在于,从人类状态向下复归到动物状态,然后又从植物状态最后复归到矿物状态。
先前在对黑暗母题的讨论中,我们提到诗人想将自己变成一只黑乌鸦,去捕抓所有的心肺,以此作为对世纪之废墟的报复。然而,就人类状态的特征与动物状态的特征来说,它们之间存在的关键区别便在于,从吃熟食的习惯转变为吃作为动物饲料的植物的习惯:“我初流徙到一荒岛里,/见了一根草儿便吃,/幸未食自己儿子之肉”(《小诗》),或是:
神奇之年岁,
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
(《夜之歌》)
在诗人的动物状态中,他对自己的食物相当不满,因为植物淡而无味。因此,他想从动物状态变成植物状态,去拥有植物世界中那种死气沉沉的经验:
我厌烦了大街的行人,
与园里的棕榈之叶,
深望有一次倒悬
在枝头,看一切生动:
那时我的心将狂叫,
记忆与联想将沸腾:
……
(《悲》)
枝头上幻影似的“倒悬”意味着离开人类状态而进入了无生命的植物状态,并从人类状态的痛苦中去设法寻找遗忘。在一棵树上像叶子或果实那样倒悬,这种去人性化形式将不会获得任何拯救的希望,只会收获更多的痛苦,去人性化形式导致了完全的自我毁灭与腐烂,因为所有的自然形式更倾向于腐烂、分解、转瞬即逝与坏死。自然世界中植物的脆弱性意味着时间的庞然大物能将其轻易毁灭。自然遗迹不经过美学化的提炼,自然之中就没有什么能保持永恒。
因此,死亡或自然的腐败成为了永恒之美的条件,亦成为人造美学化的结果。自然毁灭后的结晶形式,源于时间的秘密转化而成为矿物世界。因此,矿物世界便是从自然状态转化为非自然状态这一过程的反照形式。这并非自然最原初的形式,却是其最精巧、最刻意、最反常与最人工的形式。这使得李金发沉潜于一个物化的矿物状态,并以此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人造天堂:“但我们之躯体,/既遍染硝磺”(《夜之歌》),或更进一步:
我筑了一水晶的斗室
把自己关住了,
冥想是我的消遣,
bien aimée 给我所需的饮料。
(《我欲到人群中》)
在这首诗中,诗人想在人群中展露自己,但他感觉自己缺少神性,所以他先建造了一座水晶屋,接着计划重建一座水晶宫。在这人造天堂或人造宫殿的幻景中,诗人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国王或骑士。他唯一的劳动便是思考,沉思他所创造的欢愉之内部。根据“非我”(人群)所提炼的“我”的细节,即是通过时间来抵达神性:
在我慵惰的年岁上,“时间”建一大
理石的宫室在河岸,多么明媚清晰!
(《忠告》)
大理石宫室的光明,并非由创造“我”之凡庸的残酷时间所释放,而是源于宫室自身在河中的反照,这暗示着正是时间摧毁并改善了宫室的光明。在此诗中,时间的破坏性与不育并不指向生命—经验的空虚,却指向了美之极乐的灵光。对于李金发来说,身处矿物状态中,一方面可以完全忘记由残酷时间引起的痛苦,另一方面在矿物的反照中经验了美闪现的瞬间。正是在从人到动物到植物最后到矿物的向下质变中,李金发或许从遗迹残片中提取了一种向上的美的净化(catharsis),将瞬间性升华为永恒性。矿物在现代颓废中产生出带有亵渎性的人造之美,他对矿物的沉迷在其另一首诗中显而易见:
我爱一切水晶,香花,
和草里的罂粟,
她的颜色与服装,
我将用什么比喻?
(《憾》)
在矿物的透明中,在自然散发的芳香中以及飘忽不定的鸦片梦中,美的人造天堂被非自然的亵渎方式所照亮,而非自然的神圣方式;通过抛光、磨亮以及旋转矿物的反照,而非原矿本身的辐射。
3.反照的溢出,其被视作冥想的隐喻空间
(1)由于力比多能量的缺失,使得整个身体随即陷于无力与麻痹,世界中的一切物事因而满溢,变得无用:“短墙的延长与低哑,/围绕着愁思/在天空下的园地/自己开放花儿了。”(《短墙的……》)物事的溢出被供予某个沉思的空间,本雅明如是说:“把闲置在地上的日常器皿,当作沉思的对象。”[10]170
(2)时间的庞然大物将自然僵化、抑制与腐坏为完全的废墟:大地荒疏、井水干枯、景致空虚,还有枯枝败叶、动物尸体、白骨累累与鬼火磷光遍布整个自然:“我发现半开之玫瑰已复萎靡”(《诗神》),或是“新秋的/花残了,盛夏的池沼干了”(《忠告》)。这一荒原或废墟的境况不仅见于李金发的诗中,而且还使自身带上了沉思这种人类情感的讽喻意味。
(3)反照叙述中的双重反照里,出现了一次分裂或剩余,这种剩余构成了用以沉思的第三空间。简而言之,沉思的反照空间出现于颓废世界中的稳定之物;也就是说,当在力比多能量的无力中感受开始外部化与对象化的身体痛苦,这痛苦本身变成了沉思之时⑩——李金发写到“金椅上痛苦之王子”(《你还记得否……》),那么一种疼痛、痛苦、毁灭与颓废的沉思话语便随之被建构。这一阵痛的沉思叙述将提供自我塑造的生命活力,亦将在民族文化叙述中,提供重塑美学情感与时间意识的辩证法机制。在李金发的诗歌中,我们已经经历了阵痛,特别是其颓废身体中的力比多能量危机,但我们也更频繁地目睹了李金发颓废美学情感的意识,以及最意味深长的是,身处现代性与启蒙的大业中的李金发对自我反照的辩证理解。
二、颓废身体:走向一种悲悼的否定伦理学
离《微雨》出版大概还有三年的1922 年,李金发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同年朱自清发表了长诗《毁灭》。在诗中,朱自清回想起一次不大寻常的梦,在杭州旅行时,他忽然“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这首长诗最特别的部分在于,它极饱满地呈现了一种颓废氛围:病态、漂浮的灵魂、世界的疲惫感、冷风景、疏离、干枯的荒漠、空处、死亡的欲望,以及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具筋疲力尽的身体,四肢“衰颓”。一种强烈的悲悼感弥漫全诗。这是一首自我表达之诗,或是“我”徘徊于黑暗与光明、怀疑与信仰,以及向前进步与向后颓废之维谷的诗。朱自清在诗中将自己立于“不知取怎样的道路,/却尽徘徊于迷悟之纠纷的时候”[11]。
1923 年3 月,徐志摩发表了一首题为《青年杂咏》的名作,在诗中他三问青年,为何沉湎伤感、迟徊梦中、醉心革命?在第一个诘问中,徐志摩将青年的沉湎伤感描述为:在忧郁河边筑起一座水晶宫殿,河中惟有忧郁流淌,残枝断梗不过映照出伤感、徘徊、倦怠的灰色生命。青年冠上的黄金终被霉朽。诗中最重要的是,徐志摩将“忧郁”(melancholy)一词音译为汉语“眸冷骨累”,这准确地抓住了显现于身体中的忧郁症状[12]。另一个象征主义诗人穆木天,将法语词“颓废”(decadence)译为“腐水朽城”[13]。激进的情色诗人邵洵美将这个词译为“颓加荡”[14]。1922 年左右,一同与李金发留学法国的诗人王独清写了一首题为《我从café 中出来……》的诗,此诗描绘了他的颓废境况:喝完混了酒的咖啡后,四下满是寂寥的伤感,徘徊不知向哪一处去,他悲叹道:“啊,冷静的街衢,/黄昏,细雨。”
正如我们所见,在李金发出现之前,中国文学大体上便已见证了力比多经济的危机或浪荡的颓废(une turbulente décadence)。这一态势的持续增长,最终在1925 年李金发的诗集中达到顶点。从1922—1930 年以及之后的一些年里,中国现代诗歌沉湎于感伤、痛苦、恸哭、悲悼之中,一言蔽之,沉湎于身体痛苦的深深颓废与忧郁状态之中。可以将此一现代性负面理解为对非本土文化资源的翻译,或理解为在中国处于努力重铸其文化身份的新纪元时,西方文化叙述的影响,这确实要求一种新的诠释理论结构⑪。负面的翻译现代性在重铸自我与文化身份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遭到了简单地拒斥与责难,与这种负面翻译现代性的常规诠释或意识形态诠释相反,我打算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即通过各式理论资源来诠释这种现代情感的特别形式。我打算主要以辩证的角度观照此问题,李金发对缘于力比多能量危机的颓废的极度称颂,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自我的负面塑造,通过“镜像—悲悼—纪念碑”的叙述范式进行。
让我们先从现代性话语构成里的颓废与进步的辩证法开始。卡林内斯库认为进步与颓废的概念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深刻地暗示。“进步即颓废,反之,颓废即进步。”⑪这一概念构成了现代性的双重辩证法。莫兹利(Maudsley)在其《身体与意志》(Body and Will)中讨论社会与进化时,他认为退化普遍地反作用于进化,而颓废几近于进步;社会即是由上升与下降的双重流动所构成。因此,“存在者,从高级下降到低级的退化过程,乃是自然经济中必不可少的活力所在”[15]。黑格尔同样讨论过进步与颓废的辩证概念,他强调通过差异与混乱而重获和谐一致:“进化是生命的必经过程,要素之一,其发展源于对立:生命的总体性在其最强烈的时刻,只可能作为一种原出于最绝对之分裂的新的综合而存在。”[16]122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李金发总是从生命—世界的对立面与反面来感知生命—世界,这是为了表达他与进步的启蒙现代性相反的颓废之美学。李金发的辩证性感知可从如下二例略见:
我生存的神秘,
惟你能管领,
不然则一刻是永远,
明媚即是肮脏。
(《你在夜间》)
另一例:
如残叶溅
血在我们
脚上,
生命便是
死神唇边
的笑。
(《有感》)
由此看来,现代性的颓废与进步在这一层面并不相互对立,而是在一种双重陈述中共存。李金发的“现代性否定伦理学”从这一角度而言,不仅终究是必要的,而且成为了构建人类身份及其主体性的必经过程。
其次是视镜与悲悼:如上所述,拒斥光明的后果便是返回仅留存反射光的黑暗洞穴,返回到由镜子反射的现实之内部。正如阿多诺所言:“然而,窥入反射之镜的他是个闲人,一个已经退出经济生产程序的个体。反射之镜印证了对象的缺乏(镜子不过是把事物的表面带入一个空间),以及个人的隐匿。因此,镜子与悲悼彼此勾连。”[16]42就阿多诺此论来看,尽管镜子将外部现实的表面完全反射(这让人悲悼失落的真实世界),但镜子也能记录世界的损失,人在镜中对自己的观看可以将内部反映为现实。
正是通过视镜与悲悼的结合,失落的世界才得以弥补。颓废是力比多能量中向下的衰退,这种力比多能量生成了灰烬中的身体与废墟中的自然。一方面,正如李金发诗中写道:“但我们所根据的潜力,火焰与真理,/恐亦随时代而溃败”(《心期》);然而另一方面,在腐烂的过程中,人类主体对灰烬与废墟的反射,出自被创造、被合法化的新秩序,这一新秩序通过伴随着悲悼情绪的镜中之自省性而来。因此,视镜成为了一个居间要素,为了抓住自我的新知识,它为悲悼主体提供了一个特定空间来返射自身。因此我们在李金发的诗里看见:“月儿半升时,/我们便流泪创造未来”(《à Gerty》),如此便:
有了缺憾才有真善美的希求,
从平凡中显出伟大庄严。
(《生之谜》)
再次是悲悼与纪念碑:在李金发的纪念碑诗歌中,《弃妇》这一悲悼母题与坟/墓的形象联系起来(“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徜徉在丘墓之侧”),使得整首诗可以被读作一首挽歌,一座女人的墓碑。事实上,死亡主题与坟墓修辞整体性的弥漫于李金发的诗歌之中。因此他有时被视作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死亡诗人”[17]。对坟墓与死亡如此大量的呈现,建立了李金发诗歌的纪念碑身体,以及将自身构建为纪念碑石的修辞⑫。例如:“希望得一魔师,/切大理石如棉絮,偶得空闲时/便造自己细腻之坟座”(《多少疾苦的呻吟……》),或是:
在时代的名胜上,
残墓衬点风光。
(《晚钟》)
以及:
快选一安顿之坟藏,
我将颓死在情爱里,
垂杨之阴遮掩这不幸。
(《Elégie》)
在《悲悼与忧郁症》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将忧郁症的本质与悲悼的常规情感进行比较。弗洛伊德认为,哀悼是一种丧失客体的经验,一种丧失社会及文化之象征的复杂反应,最终社群中的成员必须面对悲悼的责任。弗洛伊德写道:“悲悼通常是对爱人之丧失的反应,或是对某种被取代的抽象物,诸如国家、自由、理想等事物之丧失的反应。”[18]243-260在悲悼状态下,世界变得贫困空乏,痛苦的经验支配着悲悼情绪。悲悼与集体记忆的象征,亦即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的五个讲座》一书中提出的“纪念碑”(the monuments)概念紧密相关。悲悼与纪念碑均遭遇了对象的丧失,一方面是个体与个人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则是集体与社会的丧失。悲悼将目下卷入过去;纪念碑则将过去带至目前。不过,它们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职责:寻找新物替代丧失之物的欲望。[18]9-55彼得·霍曼斯(Peter Homans)把弗洛伊德的悲悼与纪念碑理论、韦伯的祛魅理论、科胡特(Kohut)去理想化(de-idealization)概念、温尼科特(Winnicott)的幻灭(disillusionment)概念、克莱因的憔悴(pining)概念以及涂尔干的失范加以综合,发展出一套他所称之为悲悼、个性化及意义创造的修正理论。⑬
霍曼斯认为,个性化乃是悲悼的结果;通过从已然消逝的过往中采撷而来的丧失经验,可以激发“变成某人”的欲望,与此同时,为自我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意义。现代性的典型世俗化呈现出一种为了消逝的象征与社群的整体而不断增长的悲悼。因此,在消逝的社会文化理想之面孔中,悲悼将反照的心理机制建立在冲突与创伤的痛苦经验之上,最终提升为“成为某人之自我”,而纪念碑则搭建了一种集体记忆,亦即通过物质仪式的中介,一种联合的象征将一切个体的消逝与过去的历史结合一处。由此观之,悲悼成为了创造性的别样形式,这形式最终构建出一个成熟、独一的自我,而纪念碑则构建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社会成员总是返回于此,并将这种丧失经验内在化为“内存纪念碑”(“monument within”)。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由丧失客体所致的创伤痛苦才得以被治愈,正面的复原力才得以再生。所以,当文化面临灾难时,痛苦的能力与悲悼的能力才显得必不可少,这两种能力产生出支撑自我之内在与外在的容量,也就是说,在个体化的语境与集体化的现实中产生出来。正如李金发写到:“在décadent 里无颓唐自己”(《“Musicien de Rues”之歌》)。在《悼》这首诗中,通过悲悼的痛苦经验,李金发将现代性的负面伦理转换成一种现代性的正面伦理。全诗如下:
闲散的凄怆排闼闯进,
每个漫掩护的心扉之低,
惜死如铅块的情绪,无勇地
锁住阴雨里新茁的柳芽。
该不是牺牲在痼疾之年,
生的精力,未炼成无敌的钢刃,
罪恶之火热的眼,
正围绕真理之祭坛而狂笑。
铁的意志,摧毁了脆弱的心灵,
严肃的典型,无畏的坚忍,
已组成新社会的一环,
给人振奋像海天无垠。
此诗中涌现出了一个新形象,这形象将自己贡献于生命能量的提炼,将其铸造为强韧的钢刀来抗击罪恶、揭示真理,并最终建立起一个新社会:它包含了李金发眼中的新自我与优雅之美。启蒙运动的失落理想正处于恢复、修养与重构的过程中;经过反照的悲悼,中国现代性中的脆弱个性与新生自我正变得愈发强壮与成熟。颓废身体的叙述也由此诞生出一种崭新的自我伦理,其塑造并非经由正面进行,却是通过黑暗与负面完成。
在中国现代性一般的话语构造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比李金发更多地引介了三种意义重大的话语元素:颓废感性、时间的飞逝感;自反意识。第一种元素承载的观念为:进步即颓废,颓废即进步;第二种元素显示了永恒中的短暂存在,以及飞逝时间中的永恒存在;第三种元素则暗示自我总是需要向其本身反射,由此辨认对于现代身份叙述而言的自我本质的真实性。正是通过李金发这种特有的感情,中国现代性的叙事性才见证了这种新话语的发生,而此后关于自我的塑造亦焕然一新。
至此,在郭沫若和李金发之间——在力比多能量经济的膨胀与力比多能量经济的危机之间;热烈、光明、激情、进步的自我与寒冷、黑暗、无力、颓废的自我之间;在太阳、光亮、火焰、黎明的叙述与冬天、夜晚、潮湿、反照的叙述之间,一种话语张力得以在中国现代性启蒙大业的力比多能量经济中构建起来。
注释:
① 本文来自作者的长篇英文论文“The Decadent Body:Toward A Negative Ethics of Mourning in Li Jinfa’s Poetry”,承蒙赵凡翻译成中文,特此致谢。
② 克尔凯郭尔的反省概念,亦可参看哈维·弗格森(Harvie Ferguson):《忧郁和现代性批判: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心理学》,1995 年版,第60-80 页。
③ 就光明与黑暗的详尽讨论,参看安娜-特丽莎·泰门妮卡(Anna-Teresa Tymieniecka):《光明与黑暗的基本辩证法:生命之本体创造中的灵魂激情》,The Elemental Dialectic of Light and Darkness:The Passions of the soul in the Onto-Poiesis of Life,1992。亦可参看马丁·杰伊:《垂目》,Downcast Eyes,1993;大卫·迈克·列文编(David Micheal Levin):《现代性与视像霸权》,Modernity and the Hegemony of Vision,1993。
④ 就人类自我与身份构成中的自反性功能的进一步讨论,可参看罗伯特·斯格尔(Robert Siegle):《自反性政治:叙述与文化的本质诗学》,The Politics of Reflexivity:Narrative and the Constitutive Poetics of Culture,1986。
⑤ 对于亵渎启迪(profane illumination)的概念,我在此使用与瓦尔特·本雅明的涉及主体差异的“启迪”(Erleuchtung)不同。当然,我对本雅明的启迪论述进行了清楚阐明。就本雅明的亵渎启迪概念的讨论,可参看玛格丽特·科恩:《亵渎启迪:瓦尔特本雅明与超现实主义革命的巴黎》,Profane Illumination:Walter Benjamin and the Paris of Surrealist Revolution,1993。
⑥ 对分裂自我这一主题的研究,可参看《现代主义自我》,见于克里斯托弗·巴特勒(Christopher Butler):《现代主义:欧洲的文学、音乐、绘画(1900-1916)》,Early Modernism:Literature,Music,and Painting in Europe,1900-1916,1994 年,89-106 页;丹尼斯·布朗(Dennis Brown):《二十世纪英语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自我:自我分裂研究》,The Modernist Self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A Study in Self-Fragmentation,1989。
⑦ 本文中李金发的诗作均引自于周良沛编:《李金发诗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不另加注。
⑧ 关于身份的反射/反思话语的一本有趣著作,可参阅鲁道夫·加谢(Rodolphe Gasche):《镜子的锡箔:德里达及其反思哲学》,The Tain of the Mirror:Derrida and the Philosophy of Reflection,1986。
⑨ 尼采:《瓦格纳事件》,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 年,第38 页。有关颓废中的人造概念,亦可参看斯沃特:《19 世纪法国的颓废意识》,The Sense of Decade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第 169 页。
⑩ 关于信仰塑造中的痛苦身体及其功能的详尽讨论,参看伊莱恩·思凯瑞(Elaine Scarry):《痛苦身体:世界的生成与毁坏》,The Body in Pain: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1985 年。
⑪ 就“被译介的现代性”对中国文化叙述之构成的影响的广泛讨论,参看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中国(189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890-1937,1995。
⑫ 就诗歌中作为悼文出现的墓碑功能的研究,请参看J·道格拉斯、尼尔(J.Douglas Kneale):《纪念碑书写: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修辞》,Monumental Writing:Aspects of Rhetoric in Wordsworth’s Poetry,1988 年。
⑬ 对三位一体理论的详尽讨论,参看皮特·霍曼斯(Peter Homans):《悲悼的能力:幻灭与精神分析的社会起源》,The Ability to Mourn:Disillusionment and the Social 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1989。尤其是最后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