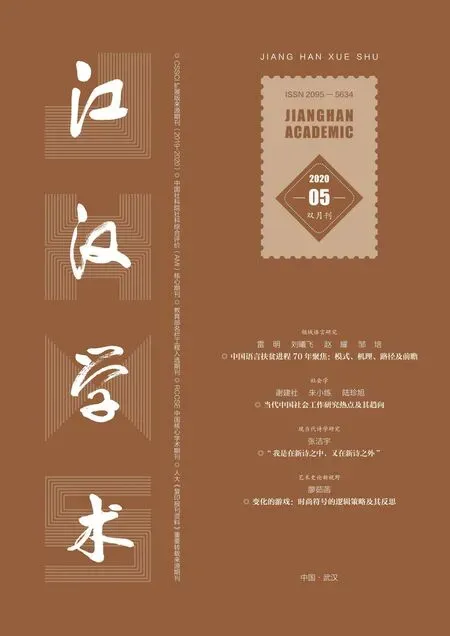从资本逻辑之思到生命政治之思
——市民社会批判范式的更新与发展
郝志昌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在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一再强调要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对其解剖,这无疑是重要的。但是面对当下的现实,不难发现,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越来越以生命政治的面相大行其道,否则它就不能更好地实现增殖的目的。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在对市民社会的既有解释上,资本逻辑是理解它的核心要义。但是随着资本逻辑越来越以生命政治的面相表征自身,对市民社会本身的理解角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我们看到,生命政治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获全胜,这种治理术将生命作为关注的核心,生命开始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主题。在这种背景中,较之于以往市民社会的既有形态,当代市民社会开始力图在生命中取得居留之所,并围绕生命本身进行逻辑架构。而作为被架构的结果,生命本身开始遭受了权力的算计与殖民。要言之,市民社会在今天以生命政治的形态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因此,想要坐实市民社会的生命政治新形态,我们必须追问这种新生形态产生的逻辑基础是什么?这种新生形态转向的根本力量是什么?以及这种新生形态如何被架构出来的?当然,资本逻辑以生命政治的面相表征自身,并不意味着资本逻辑的断裂抑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失效,而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以新生的面相——生命政治延续自身。因此更为准确地说,生命政治并非逃遁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从当下的现实出发来说,以生命政治视角能够更为清晰地透视今天的市民社会。
一、资本逻辑与市民社会的既有形态甄定
市民社会在获得生命政治的新形态之前,已经清晰地以其既有的形态进行自我运作。或者准确地讲,正是市民社会本身已经具备既有形态作为支援性背景,才使得市民社会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新生形态。为了更好地说明市民社会在当代获得的生命政治新形态,必须首先甄定作为这一新形态的支援性背景——市民社会的既有形态。在这种意义上,市民社会的既有形态构成了市民社会新形态的逻辑起点。有鉴于此,对市民社会的既有形态进行条分缕析的考辨,就成为必须首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就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而言,甄定市民社会的既有形态,并非仅仅简单地罗列出市民社会的既有解释,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澄明这些既有的解释和市民社会新形态之间的内在性关联,否则对市民社会新形态的言说就难以为继。
首先,市民社会在自身的具体展开和现实运作过程中,最初表现为与政治社会的无分状态,这一状态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中的“Politike Koinonia”概念,在英文中表述为“civil society”,即“市民社会”的概念。并且,亚里士多德在此提出的“Politike Koinonia”,在《政治学》的语境中直接针对的是政治共同体抑或城邦国家。据此,市民社会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际就是政治社会的代名词,或者说二者处于统一的状态中。此外,从词源学上考虑,还可以发现与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概念相联系的“公民权”一词的词根是polis,意指城邦。这说明了公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身携带政治属性,对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1]113。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古希腊公民享有的首要权利就是在城邦中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可见,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统一,关键点是理解公民的含义。城邦所代表的政治社会,是公民成其为公民的必要条件,倘若政治社会消失,公民也就失去了他自身所享有的“公民权”,那么市民社会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市民社会在古典时期可以说具有政治属性,因为与市民社会勾连的城邦和公民都完全体现了政治属性:城邦是作为政治性质的领域,以及公民是作为天生携带政治属性的主体。
古典市民社会初创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统一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讨论市民社会的论域。虽说后来的西塞罗,近代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继续发展了市民社会理论,但仍没有跳出古典意义的这种原初范式,以至于泰勒指认道:“洛克仍然是在传统的意义上——亦即‘政治社会’的同义语——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的。”[2]15
其次,资本逻辑的到来,结束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体的双子状态,并且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开始呈现出一种博弈状态。黑格尔在这一点上,首次明确进行了区分,开辟了之后讨论市民社会的论题域。在此,从黑格尔、马克思到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人,无论对市民社会的主导属性给予了怎样的界定,都遵循了这一前提。从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无分的状态到分离的状态,马克思认为主要源于两种力量,分别是商品经济的需要以及政治革命的完成。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求摆脱政治社会的束缚,而这一要求的实现是在政治革命中完成的。质言之,这两种力量其实是资本逻辑的体现,资本逻辑的出现要求市民社会成为政治社会之外的一个独立领域。
在这种意义上,由资本逻辑开辟的市民社会,不仅与政治社会分离开来,也因而附带着资本逻辑的经济属性,这是市民社会经济属性的获得。针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属性,黑格尔与马克思是保持一致的。资本逻辑的出现,促进了现代世界的发展以及现代理性的诞生,这是现代世界向传统世界告别的重要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3]197。在现代世界中,黑格尔用“需要的体系”来规定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把市民社会看作“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3]309。马克思用“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来揭示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他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4]532。
当然,除了从经济内涵上理解市民社会之外,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在对待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博弈关系立场上,黑格尔认为国家具有普遍性以及最高的伦理性,而市民社会自身因经济属性的束缚而携带着特殊性、偶然性等因素。因此,黑格尔把国家看作是市民社会的最终目的和必要的依赖条件。同样,马克思承认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因素,马克思认为这表现在市民社会中的人的利己性和孤立性上。并且,孤立性不过是对利己性后果的一个表现罢了,正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利己性,市民社会的自由就表现为“人作为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5]183。这虽然是市民社会中的人所表现出的消极的特殊性,但是,市民社会中的人却是直接存在和感性存在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理解,认为普遍性只有通过特殊性才能实现自身,如果普遍性不是通过每一个个体作为中介来实现,就是抽象的普遍性。因此,国家反倒不是市民社会的必要依赖条件,市民社会才是政治国家的依赖条件,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
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处于分离的二元模式,并表现为一种博弈状态,不仅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说明,同样在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等人那里也有新的呈现。20世纪初,福特制生产方式的盛行引领着社会结构的转型,自由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此时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不是表现为以往明确分野的状态,而是表现为政治社会越来越干涉市民社会。质言之,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开始交叉影响,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这种垄断的资本主义为了保证自身合理性、合法性的维护,非常重视在政治、文化领域中对市民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组织加以控制,这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因为这种垄断的资本主义迫切需要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在其实质上,经济理性的获得在此时更多是诉诸意识形态理性的认同。在这种背景下,葛兰西认为,“我们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层面: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6]12。明显地,市民社会在葛氏这里,以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定位在上层建筑行列。市民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软性的文化领导权成为保障国家的帮手。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在他前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他把社会结构划分为两个领域,一是市场领域以及私人自主的领域;二是政治社会代表的公共权力领域。其中后者可视作政治社会领域,前者可视作市民社会领域,它指的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私人自主领域。在此,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语境中进行的。在后期著作中,哈贝马斯把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子体系,分别为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其中,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谓的“系统”,而社会文化体系指的是生活世界,也即市民社会部分。在后期思想中,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受到了系统的殖民,即交往行为受到工具理性的支配,以此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在此,哈贝马斯从文化意义上来规定市民社会,完全是循着葛兰西的路径进行的。
综上,我们可以理清的是,市民社会的既有形态是在两个谱系中演变而来的:一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无分的模式;一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离的模式。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市民社会,前者是传统社会笼罩下的具有政治属性的市民社会。并且对于后者来说,随着资本逻辑自身发展的变化,市民社会又依次表现为具有经济属性的市民社会和具有文化属性的市民社会。显然,资本逻辑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它的诞生促使了其政治属性过渡到经济属性,它的发展促使了其经济属性过渡到文化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既有形态的每一次转变,都离不开它之前的旧形态作为支援性背景推动、促进每一次新的形态的产生。
二、资本逻辑如何获得生命政治的新面相
资本逻辑的诞生,要求原初的市民社会摆脱政治属性的束缚,成为独立的私人自主领域,这是政治属性向经济属性的过渡。资本逻辑诞生之后,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又促使了经济属性过渡到文化属性。具体而言,资本逻辑包括两个维度的内涵:首先它表现为具有实体性意义的“物”的一面,这构成了资本逻辑的客观逻辑;其次表现为具有观念性意义的“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的一面,这构成了资本逻辑的主观逻辑。资本逻辑中的客观逻辑具有实体性的意义,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实体形态。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7]743。并且,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了能够尽快地、最大限度地进行积累,在其最初是以血腥和赤裸的方式进行的,马克思对此指出,资本乍来到人间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871。照此而论,资本逻辑的客观逻辑实属我们提到的经济属性,表现为实体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我们也相应地注意到,资本逻辑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以文明的外衣代替赤裸裸的剥削方式,在理论上就体现为资本逻辑的主观逻辑。我们提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属性,在晚期资本主义中,资本逻辑为了能够更进一步增殖自身,必须通过文化理性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我们看到,市民社会的既有形态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三种形态。
实质上,资本逻辑充当了这三种形态演变的根本力量。从原初的政治属性过渡到现代社会的经济属性,肇源于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政治革命的完成。不难发现,商品经济和政治革命此二者宣告了资本逻辑的诞生,它们的核心实乃资本逻辑的最终归宿。继而,从现代社会之初的经济属性再过渡到晚期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属性,归因于资本逻辑自身的内在变化,即福特制引领的社会结构转变要求晚期的资本主义要想得到自身合法性、合理性的维护,首先应该诉诸于文化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把国家称为“披上甲胄的领导权”,即要想巩固政治社会的稳定,必须率先从具有文化领导权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答案。质言之,市民社会的既有形态的每次转变,资本逻辑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然而,资本逻辑在当今的资本社会中,自身形态再一次得到了更新和发展。资本逻辑越来越关注生命自身的建构,在这种新的转变背景下,对市民社会的考量就必须再次启航。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逻辑在当下,为何以及如何以生命政治学的构境表征和延续自身?这成为我们言说市民社会生命政治形态的关键点。
在此,我们必须引入劳动力概念,才能更清楚地揭示以上的问题。需要指出,“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8]201。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开始聚焦于生命主体本身上,关键在于劳动力本身中的“力”表征着一种生产的潜力、可能性。因此,作为这种潜力和可能性的总和的基质——生命,才能成为资本逻辑在传统政治哲学范畴被掏空的困境之下,将新的关注对象置换成为生命(身体)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并完成交易,才能满足资本逻辑最终目的。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就此指出,“劳动实际上所付出的不仅仅偿还了资本家先前为保证获得他人的工作潜力而花费的金钱;劳动还得这样再持续一段额外的时间”[9]105。这也就是说,劳动力在成为商品并完成交易之后,在生产自身的基础上同时能够继续生产比自身更大的价值。因此,在劳动力概念当中,昭示着资本积累的奥秘以及剩余价值的起源。而这个劳动力概念就意味着生命(身体)必须受到资本逻辑的重点扶植、投资、管控等,只有这样才能利于资本更好地进行增殖,因为生命(身体)本身是劳动力能够实现其无穷潜力的基质所在。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不论是面向个体的规训权力,还是面向整体人口的生命权力,都是在规训和扶植的基础上使生命的潜力、可能性发挥出来。因此,良好的人口数量越大,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就越发具有自主性,资本才能够以更强的掠夺性继续“昂首前行”。
毫无疑问,在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的重要关注对象已经开始围绕生命本身进行架构。这一转向的原因在于生命本身所形成的劳动力具有生产的潜力和可能性。这一转向的目的在于资本要再次创造新时期的“美好”和“奇迹”,必须重视生命本身所携带的这种潜力,从而使这种劳动力较之于以往能够被同质化为更大的劳动量。因此,资本逻辑中囊括的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为了能够继续合理地促进资本增殖自身,必须展开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在今天的理论表现形态就呈现为生命政治学。
进一步地,资本逻辑开始把生命囊括进自身的双重逻辑中,呈现出生命政治学的转向,在其实质上是权力支配域的置换,认识到这一点极其关键。展开分析,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具有的购买力,从而形成了支配力,最终膨胀为一个权力场。就购买力来说,这是资本逻辑所形成的第一个权力——经济权力。马克思就此指认道:“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10]21货币所具有的这种购买力是资本进行权力支配的起点。在此基础之上,资本具有了对劳动以及产品的支配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为了能够实现自身的增殖,就得通过货币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从而获得对这一特殊商品的支配权力,并最终实现这种特殊商品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表明,资本在膨胀为社会的一切权力,诸如政治权力、社会权力、文化权力等之前,资本所具备的经济权力是这些庞大的权力场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当下的资本逻辑在构建其庞大的权力场时,出发点已经开始置换为政治权力。换言之,如果把购买和支配劳动力的经济权力作为构建整个权力场的起点从而来实现资本的剥削,那么现在已经置换为把扶植和投资生命的政治权力作为构建整个权力场的起点。哈特和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一书中,将这种置换称其为“生命政治的剥削”。所谓“生命政治的剥削”,指的是现代社会通过对生命本身的投资和扶植,使得生命政治建构下的劳动力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劳动力更具有潜力和可能性,这样就使得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更具有自主性。因此,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本逻辑必须把文化、教育、医疗、出生率、死亡率等关乎人口健康的因素包含其内,因为资本逻辑已经认识到只有对生命的投资和扶植,才能够使生命政治建构下的劳动力具有自主的生产力。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资本逻辑在今天最美妙的地方。然而我们不应该忘了,资本逻辑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直接干涉生产,反而它让生产变得更为自主,但是资本逻辑最终的目的仍是剥削——一种在外部的更具侵略的剥削。哈特和奈格里就此指认,“资本与生产性的社会生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谓的有机的了,因为资本日益外在化,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生命政治的劳动力不再是资本主义机体内一个起作用的器官,而是变得更具自主性,而资本通过其规训性政权占有装置以及剥削机制等,寄生在劳动力之上”[11]105。
据此,在对劳动力概念进行考察后,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资本逻辑统治下,资本逻辑为了能够把劳动力同质化为更大的劳动量,必须关心劳动力的基质——生命(身体),因为劳动力这种具有潜力、可能性的力量蕴藏在生命(身体)当中。此外还能得出另一个结论,资本逻辑在置换了其对象之后转换为生命政治的剥削,这应该是让它感到最“美妙”的地方。因为当资本逻辑展开对生命(身体)进行投资、扶植之后,生命政治的生产会变得更具自主性,此时的资本逻辑更少地直接介入到生命政治生产中去,或者准确地说,此时的资本逻辑对于生命政治生产而言具有外在性,但是它却能够更多地对其生命政治生产的产品进行剥削,变得更具掠夺性。
由于资本逻辑的本性使然,我们看到,资本逻辑为了持续获得自身的自足性,逐渐表现为生命政治学。这意味着资本逻辑所代表的传统政治学的范畴和对象逐渐被掏空,转而寻找新的关照对象——生命(身体)。如果说以往资本逻辑只是从资本本身生产的客观逻辑和现代理性的主观逻辑出发,把其关照对象描述为阶级主体和法权主体,并围绕阶级主体和法权主体构筑法、民主、普遍意志等范畴域的话,那么现在资本逻辑开始将上述对象瞄准为生命主体,并围绕生命构筑关于人口、医疗、卫生、教育等范畴域。因此,当资本逻辑所关注的对象无法更为合理地应对新的现实时,它出于本性必然要寻找新的目标,这构成了资本逻辑关照对象的置换和转向。同时,生命(身体)在成为资本逻辑的关照对象之际,其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阿甘本认为,“‘生命’不再是一个医学和科学的观念,而是一个哲学的、政治的和神学的概念,我们必须对我们哲学传统的许多范畴进行相应的重新思考”[12]434,这揭示了生命(身体)开始从一个私人性的、“属我”的领域走向了被政治算计和操控、被权力侵入和殖民的领域。是故,阿甘本指出,“作为福柯和德勒兹思想遗产的‘生命’,必然构成来临中的哲学的主题”[12]433。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来临中的市民社会新形态的主题。
由是观之,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关注对象已然开始发生转变,生命正在成为资本逻辑的靶子,这意味着资本逻辑越来越以生命政治的面相表征和延续自身。当然,生命政治在实质上仍旧保持资本逻辑的本性,它并非逃遁出资本逻辑的贪婪本性之外,只不过生命政治是资本逻辑在当今的更新和发展。但是,若想更为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的当代形态,必须在更为细致入微的生命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市民社会。
三、赤裸生命的当代回响——市民社会的生命政治新形态
我们看到,从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古典意义的市民社会以降,市民社会的形态依次委诸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这构成了市民社会在每一个时代的既有形态主题。在此基础上,随着资本逻辑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以生命政治的手段展开自身的进程中,生命开始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主题。同样,市民社会在今天的既有形态,也随之开始变革,并以生命政治的形态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要言之,当代市民社会开始力图在生命中取得居留之所,并围绕生命本身进行逻辑架构。作为被架构的结果,生命本身开始遭受了权力的算计与殖民。着眼于此,如果我们可以把以往各个时代由市民社会而产生的矛盾,分别归因于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的话,那么迨至今天,市民社会所引发的不安甚或危险的因素,几乎都是来自于生命本身。
具体来说,生命政治关涉的对象并非是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个体的人抑或部分群体的人,而是整体的人口,否则我们说市民社会在当代呈现出生命政治的形态是有所偏颇的。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强调生命政治学的“最终目标是人口。人口是适合作为目标的,而个人,一系列的个人,成群的个人,是不适合作为目标的。而仅仅作为用来在人口层面获得的某种东西的工具、替代或者条件来说才是适合的”[13]33。但是,将整体的人口作为生命政治的关注对象,并不意味着生命政治不关注个体的生命。准确地讲,福柯区分了个体的性质:一类是无区别的普通个体,他们构成了整体人口,他们似乎处于安全之中;另一类则是特殊的个体,他们不仅不属于整体人口的行列,并且他们的“特殊”意味着会对整体人口构成威胁,而生命政治关注的个体就是后者——一种异常的、例外的、被排斥在整体人口之外的特殊存在。关注这类特殊个体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整体人口的安全而做出的相应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生命政治关注的对象最终定位在整体的人口上,据此,市民社会才全面呈现出一种生命政治的形态。在这里,遭到排斥和驱逐的特殊存在的生命,以维护全体人口健康的名义被权力操控,这构成了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的形象。但是,问题还不单单仅限于此,因为“现代政治政府,不管使用哪种论调,都建立在其公民们的‘赤裸生命’之上,并全神贯注于此中”[14]205,这就造成权力很容易会突破界限,成为极权主义。作为后果,每个生命包括原先属于整体人口的无区别的普通个体,都随时可能成为赤裸生命。
那么何谓赤裸生命?为了说明权力对赤裸生命的架构手段,以及赤裸生命在现代社会中起到的作用,阿甘本同时引入了“神圣人”的概念。阿甘本强调,“本书的主角,就是赤裸生命,即神圣人(homo sacer/sacred man)的生命,这些人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15]13。也就是说,为了保障生命政治生产的整体人口的健康,被排除在神性和法律双重保障之外的就是赤裸生命的真实内涵。他们既不是属神的,也不是属人的;既不能被祭祀,并且可以被合法杀死。赤裸生命因此被双重排除在这两个领域,而二者中间的模糊地带——例外状态的领域才是他的栖居地。这种的例外状态是悬置法律统治,它的本质是在法律之外的,那它就是违法的,但是可笑的是这又是合法的,这是例外状态即在法外又在法内的深刻悖论,而主权者正是通过这个完美的、隐秘的悖论对生命进行操控的。换言之,例外状态被宣布以后,法律被暂时悬置,主权者就成为真正的又随意的法,这是很恐怖的事件。
赤裸生命的这种现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反观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人口安全的名义从而宣布一个又一个例外状态的各种法令难道还少吗?那些历历可见的紧急状态、难民营以及收容所还少吗?这种例外状态的常态化现象,无疑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中对具有特殊存在的个体人口的一种生命政治操控。并且,在主权者眼中,任何人而不单单是那种特殊存在的个体人口,都随时有可能成为赤裸生命。
眼下,即便是在当代市民社会中被生命政治所架构的“正常人”没有立即被宣布为赤裸生命,他们也同样遭受生命政治的不断殖民。其实,这种现象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得到了隐性的揭示,马克思指出资本逻辑造成了“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二分的局面。其中,“现役劳动军”正是生命政治视野之下的那种符合资本逻辑本性的“正常人”,他们本身也不断遭受资本逻辑的规训。虽说马克思指认的“产业后备军”并没有明显地沦落到例外状态下的赤裸生命,但是他们都是主权者眼中的特殊存在,是需要被权力驯服的目标。如果“产业后备军”中的一些生命,不能在资本逻辑的规训下成为“现役劳动军”的正常补位者,那么他们将被现代性所废弃,成为真正的赤裸生命。这样看来,在今天资本逻辑越来越以生命政治的面相大行其道了。并且,“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的二分情况,如果仅仅体现为生产环节中机器对生命的划分,那么今天生命政治架构下的生命,绝非仅仅出现在生产环节之中,而是遍布在市民社会的各个环节和角落,诸如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等等领域中。乔纳森·克拉里在他的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以生命政治的形态操控生命的现实。克拉里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着眼于造就一种“新人”:他们的睡眠时间通过生物科学的帮助可以被缩短,这种操控生命的方式在克拉里那里被称之为24/7,即一天24小时和一周7天的缩写,从而满足资本的更好发展。并且,“24/7式的市场与支撑持续工作和消费的全球简直已然运转多时,然而现在,一种新的人类主体正在形成,与24/7体制更加紧密地配合起来”[16]7。对此,上文我们提到,原本的正常人似乎处于安全之中,但是这里我们有待思索的是:原本的正常人还是否能够保持安全,这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我们毋宁说,原本的正常人,其实终究还是赤裸生命的体现而已。
市民社会中的生命成为今天生命政治治理术关注的核心,这种治理术通过对生命进行事无巨细的架构,使得今天的市民社会完全以生命政治的新形态呈现出来。并且我们发现,无论是生命政治架构下的特殊存在的例外个体,还是被生命政治视之为符合其标准的正常人,都随时有可能成为赤裸生命而被曝光。当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生命政治绝不是与资本逻辑断裂之后的新型治理术,而是资本逻辑改头换面的新生。在实质上,生命政治是资本逻辑在当代的再一次更新与发展,并且也只有这样,资本社会才能继续“昂首前行”。有鉴于此,市民社会在今天所体现出来的矛盾,归根结底应该从生命政治入手找到芝麻开门的解密钥匙,这是时代给我们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