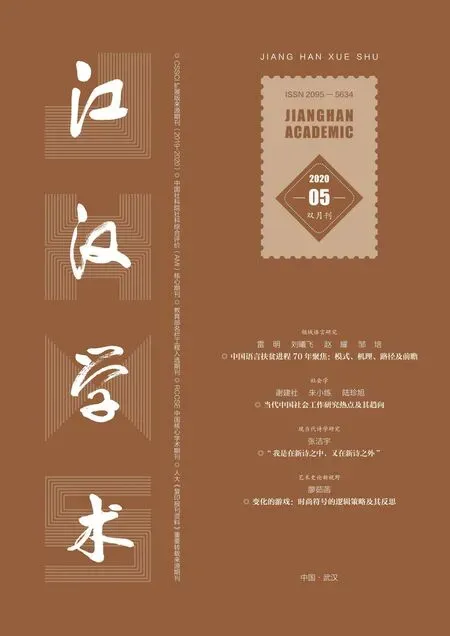变化的游戏:时尚符号的逻辑策略及其反思
廖茹菡
(四川美术学院 公共艺术学院,重庆 400053)
时尚既是一种现代文化体系,也是一个文化符号系统,它的表意功能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学界也有不少关于此话题的学理探讨。但是,时尚符号的基本运作逻辑还没有得到清晰全面的阐释。这不仅会让时尚符号的相关研究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会让大众对时尚的理解流于表面,从而迷失在虚幻的时尚世界中。澄清时尚符号的运作逻辑不仅有利于时尚研究的系统化,也有助于引导大众以正确的心态对待时尚,进而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时尚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语言的表意是较为清晰的陈述,而时尚的表意只是模糊的暗示。时尚也不同于时装。时装是物质层面的存在者,而时尚是意义层面的存在者。它是一种逻辑体系,可以运作于各种物质性载体当中。时尚符号比具象事物更抽象、更具动态性,比语言符号更丰富、更具复杂性。特殊的时尚符号需要特定的研究方法,只有合理的方法才能切中时尚符号的运作逻辑。
一、如何研究时尚符号:整体统筹与内部深化
现有关于时尚符号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大类。微观视角的研究分析特定时尚符号的表意方式和具体含义。例如男女同款的新款T恤如何彰显性别平等,破洞牛仔裤和穿孔装饰如何表达叛逆思维,各类时尚杂志中的“时尚”一词发生了怎样的意义变化等。宏观视角的研究则关注时尚符号的整体性特点。例如时尚符号的基本属性是什么,它如何实现群体间的区分与凝聚,如何促进消费社会的扩张等。然而,这两类研究都没有准确地抓住时尚符号的本质,没有彻底地澄清时尚符号的运作逻辑。
微观视角的研究忽视了时尚文化的本质属性。时尚是以变化为核心特点的文化系统,而仅仅关注某些具体时尚符号的研究方式并不能体现时尚的变化性。这类研究只是在分析某种符号形式与意义之间的意指关系,而没有考虑单个时尚符号本身的暂存性,以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继承关系。因此,与其说这类研究在讨论时尚符号,不如说它们在探讨商品符号。商品符号可以独立存在,它可以是一个猫爪杯、一双老爹鞋、一件灯芯绒西装、一包坚果、一本图画书……但独立的商品符号无法构成时尚系统,只有商品符号的变化过程才可能产生时尚现象。猫爪杯只是一个爆红的商品,网红杯子的形态变化过程才是时尚。老爹鞋也只是一件时髦的商品,鞋子外形的年年更新才是时尚。时尚是所有最新事物的集合,它见证着新奇事物的生死更替。可见,微观视角的时尚符号分析只抓住了时尚文化中的点,而没有将点连接成线与面。因而,它无法厘清时尚符号的运作逻辑,因为逻辑存在于关系当中,而不存在于零散的点之中。
虽然宏观层面的时尚符号研究把握住了作为一种变化过程的时尚体系,但它仍然不够详细和全面。现有的宏观研究大多采用外在性视角,谈论时尚符号在社会中的价值。它们基本都以西美尔的时尚理论为基础,强调时尚符号具有确认社会身份的功能。这种观点本身非常合理,同时也兼顾到了时尚的变化性,并将这种变化界定为追求更高社会地位或个性化身份的结果。然而,这种变化性会对时尚符号本身带来什么影响,却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探讨。这便使得宏观研究只能从外观望时尚符号的作用,而不能从内解析时尚符号的逻辑。
可见,要全面阐明时尚符号的逻辑和特点,就必须将所有时尚符号统筹在一起,排除差异性,总结共同性;同时,还需要步入时尚符号系统的边界之内,探究众多符号之间的关系。在此,鲍德里亚关于时尚符号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他深入时尚符号系统的内部,概述了时尚文化的运作逻辑。不过,鲍德里亚的分析过于宏观,他更重视作为一个整体的消费社会,而非专门关注其中的时尚体系。同时,他也没有剖析时尚符号本身的结构特点。因此,其理论只能作为解析时尚符号的起点和参考,而不能成为时尚符号研究的绝对律令和终点。
二、时尚符号的基本逻辑:变化、差异与新奇
鲍德里亚曾总结出四种不同的逻辑: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操持运作的逻辑)、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等价逻辑)、象征性交换逻辑(不定性的逻辑)、符号/价值逻辑(差异性逻辑)。而时尚的逻辑就是差异性逻辑[1]47,49。时尚文化之所以属于差异性逻辑,是因为时尚的不变之处在于其变化。这是一种自主的、持续的、制度化的变化。正如史文德森所言:“只有当这种变化是为了自身的动机而发生,并且经常发生时才成为时尚。”[2]18鲍曼也明确指出,在时尚中,“不可想象的不是永远不停地运动的可能性,而是中断一系列已然开始的自我感应的变化”[3]。时尚是一个“自我推动”的体系,它“能在没有任何出自或产自系统自身之外的原因的情况下自发地不断运动”[4],它在社会学层面中实现了在物理学意义上难以真正达成的永动机梦想。
而变化就是制造差异的过程。由此,时尚符号的运转逻辑就是变化和差异的逻辑。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时尚形式的逻辑将一种持续的变动加诸所有的区分性社会符号之上。”[1]28但是,这种变动不是所指的无限游移,而是能指的无穷更替。它不是符号的内涵变化,而是符号的形式变化。时尚符号的逻辑不是让一条裙子的象征意义发生持续的转变,而是让表征时尚的裙子本身发生变化。因为形式的变化是直观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识别的。意义的变化却是隐含的,且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大幅度干扰,它难以在人群之中达成绝对的共识。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长裙与短裙之间的长度差异,却较难确认长裙的“温柔”不同于短裙的“干练”。因此,长裙与短裙之所以能在不同的时期成为时尚,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长度层面的形式差异。同理,珊瑚橙之所以能成为2019年的潘通(Pantone)年度流行色,正是因为它和2018年的外光紫具有色相层面的形式差异;而PVC材料制成的透明包袋之所以能在近两年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它和皮质包袋具有材质层面的形式差异。
时尚符号用形式的变化保障着差异的存在,差异的存在则维持着新奇感。时尚的变化没有规律可循,即便其变化过程可能呈现出循环的趋势,人们也永远不可能根据这种趋势准确预测时尚的未来走势。如果时尚的下一步被人们精准地猜测到了,这将会为时尚带来最致命的打击。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处于时尚中的“人们知道时间正在对之作快速的选择。但他们不知道——他们都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能经受时间的检验,什么不能”[5]。而在马拉美编纂的时尚杂志中,一篇写于八月份的文章也曾以这样一句话开篇:“现在谈论夏天的时尚已经太晚,但谈论冬天的时尚又太早,甚至可以说,现在谈论秋天的时尚也太早。”[6]可见,即便是像时尚编辑这样的时尚引领者也不可能详细预知下一种时尚。这种不可预知性的结果就是新奇性的产生。稳定的不变是持续性的重复,严密的循环是规律性的变化,它们的未来都清晰可见,遥远的每一天似乎都近在眼前。时尚却通过体制性的不规律变化摆脱了规律和重复。由此,它成功地登上了新奇代言人的位置。而新奇也成为了时尚符号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它正是时尚“惹人喜爱的地方”[7]。
新奇的事物就是时髦的事物。在时尚符号的世界中,所指只有“时髦”与“不时髦”。新的就是时髦的、时尚的。旧的则是不时髦的、过时的。不过,“不时髦”并不意味着退出时尚的舞台,它并不是塔尔德式的“非模仿”[8]10的“非时髦”,而是以对照组的身份凸显差异、反衬“时髦”的“反时尚”。反时尚也是一种时尚,它“不是对时尚的反动,而是时尚生命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9],它把拒绝时尚当作了一种新的时尚。由此,能够指涉“时髦”的能指是无尽的。一方面,所有非时尚的事物都可能被时尚符号所征用,它们会被冠以时尚之名,从而卷入时尚的逻辑体系。澡堂拖鞋、热水袋、黑色塑料袋、格纹编织袋……这些生活用品原本只是实用之物,却在近几年间以奢侈品的姿态陆续登上时尚秀场。另一方面,曾经被使用的时尚符号也可能被再次征用,进而将不时髦翻转为时髦。踩脚裤、运动装、喇叭裤等过时单品的再度流行就是例证。时尚的所指总是在寻找新的能指。时尚符号就像一群参加接力赛的选手,它们一边轮番上场,一边不停地吸纳新的队员。每一年的流行趋势就是当年最新的队员名单。通过在不同形式的能指之间自由游走,时尚符号践行了自己的逻辑,它在变化中制造差异,在差异中创造新奇。不过,时尚符号的形式变化不仅是替换作为一个整体的自己,它还会采用解构的方式,对自我进行局部的颠覆和替换。
三、时尚符号的形式变化:自我解构与局部替换
对于时尚符号的差异性逻辑来说,最彻底的变化方式必然是将某个符号作为一个整体而完全舍弃。这不仅能最大程度地制造差异性,还能营造最令人惊异的新奇感。但是,在现实的时尚世界中,这样的更新方式很少出现。首先,时尚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其逻辑总是运作于某种具体的文化领域或文明形式当中,这便将时尚符号的变化范围限制在了一定的界限之内,还为时尚符号设立了基本的形式结构。以最常见的服饰领域为例,时装文化中的时尚符号总是游走在各种服饰符号当中,它们永远不可能放弃自己作为一种服饰款式的身份。因此,从广义层面来看,时装符号永远无法完全舍弃自己的形式,它们只能作为一件可穿戴的事物,始终徘徊在各种服装与饰品的形式当中,除非它们从一种文化领域跳脱进另一种文化领域。但是,这种跨界的转移往往会打破时尚逻辑的连续性,因为我们通常不会将不同领域中的时尚符号并置在一起。我们只会在长裙和短裙之间寻找形式差异,而不会在长裙和短篇小说之间进行形式对比。
而从狭义层面来看,服饰的基本结构也限制了时尚符号的变化程度。巴特曾在《流行体系》中将时尚服饰的各种流行元素总结为属项的清单和变项的清单。前者包含饰品、袖笼、领子、颜色、边、鞋、质料、裤子、褶裥等六十个属项,后者则包含同一性、构型、材质、量度、连续性、位置、分布和连接这八组变项。巴特指出,属项的清单与变项的清单可以涵盖所有母体的实体,它们组合成了流行特征的完整清单。[10]104这一清单是巴特分析时尚体系的逻辑基础。所有的时装符号都是这些属项和变项的搭配,它们无法逃离这个形式的集合。虽然时装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制造出新的属项,但与时尚文化的变化节奏相比,这一层面的创新会显得力不从心。同理,服饰体系的这种结构限制现象也存在于其他领域。众多网红零食的味道虽然各有特点,但它们都由基础的酸甜苦咸辣组合而成。护肤产品虽然年年出新,但其基本功效都围绕着保湿、美白、抗皱等。由此,各个文化领域中的时尚符号的更新总是不够彻底。
其次,抛开特定文化领域对时尚符号的形式限制,在时尚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符号的整体更新也是一项成本很高的任务。正如西美尔指出那样,所有的现象都有节省能量的倾向,它们会用最经济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目的。时尚也是如此,它会通过不断重复过去而高效地完成“变化”这一基本任务。[11]由此,时尚设计师会借用曾经的时尚,并引导人们将被遗忘的事物当作全新的事物,从而用符号的重复利用代替符号的创造。这也是人们常常将时尚与轮回相联系的原因所在。重复过去就意味着放弃彻底地更新自我,它只是既有事物的重新出现,并非全新事物的初次登场。这只是再现,并非创造。复古时尚就是重复过去的最佳例子,虽然历史给时尚设计师们提供了丰富的灵感资源,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框定了时尚变化的边界,降低了时尚运转所需的能量。
当然,时尚对过去的重复不是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而是以新的形式重塑历史,例如用新型面料制成的喇叭裤,印有抽象现代图案的旗袍等。这是时尚符号对自我的解构和再造,是循环和局部替换的结合。正如雷曼所言,“时尚的引用没有一定的规则。它聪明地借用过去的风格,创造全新设计或是符合现代的风格”[12]。相同廓形的裙子从长变短,相同面料的西服从两颗扣变三颗扣,相同图案的T恤从浅灰变深灰,相同颜色的衬衣从有口袋变无口袋……各种细节变化不仅维持了时尚文化所需的差异性,还降低了制造差异的成本,提升了创造新奇的效率。同时,时尚品牌也可以通过这种局部替换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品牌标签。例如迪奥(Dior)始终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新风貌(New Look)的沙漏型结构,以凸显柔美风情;香奈儿(Chanel)会坚持硬朗的直线剪裁,以彰显女性的现代意识;川久保玲则持续推出夸张的廓形设计,以反思身体与衣物的关系。这种更新模式也正是史文德森所说的“补充的逻辑”,即“新时尚基本上不再着眼于取代所有过去的时尚,而只满足于对它们作些增补”[2]28。这便是时尚符号从内部解构自我,局部性地替换自我,进而从细节之处更新自我的过程。
而时尚符号之所以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内部的解构和局部替换,是因为其能指通常具有持续的可分性,它们能够自我分裂和自我繁衍。时尚符号一般依附于具体的存在物:服装、饰品、化妆品、食物、电子产品,甚至还包括学术研究话题①。这些存在物几乎都具有多层次的可拆分性和高度的自由组合性,时尚符号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这些特征,从而保障解构和重组的可行性。以一件时髦的外套为例:这件外套本身是一个能指,但是,扣上扣子和不扣扣子的穿法又能将这个能指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能指。同理,扣一半的扣子、卷起袖子、立起领子、磨破内衬等方式都可以将原有的能指加以拆分。同时,这种拆分往往不会停留在第二层的能指之上,它还可以被继续拆解直至无穷。同一个棒球帽正戴、反戴和斜戴都可以成为不同的能指,而反戴的棒球帽又可以分为遮住额头或露出额头。同一个背包用单肩背、用双肩背或直接用手拎都是不同的符号,而用手拎的背包又可以分为左手拎或是右手拎,拎单根背带或是双根背带。同一条围巾如果被打成法式结、套舌结或是简单的蝴蝶结就会成为不同的时尚能指,而每一种套结的围法又可以再分为单圈或是双圈。可见,时尚符号可以在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空间中展开自我解构和局部替换,这为时尚符号的形式变化带来了极为丰富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时尚符号的可拆解性的存在,巴特所说的“次级服装客体(secondary dress object)”才能够实现。巴特指出,由服装降级而来的着装可以进一步将自己转变为更次一级的服装。例如外套是服装,外套在某个情境中被穿着时会成为着装,而具体的穿着方式——例如少扣两颗扣子——又可能成为新的服装[13],就像言语会沉淀为新的语言那样。如果时尚符号不能对自我进行拆分,而只能整体性地重复出现,那么,次级服装系统就不可能存在,自我解构和局部替换也不可能实现,这将为时尚的快速运转带来极大的障碍。
不过,符号的形式变化并不足以长期维持时尚逻辑的变化性。我们对新奇形式的判断取决于这个形式是否能给我们带来陌生感。时尚符号的更新、循环和局部替换必然能够带来新奇感。更新创造全新的符号,循环利用已被忘却的事物,局部替换则通过补充的逻辑来增加陌生感。但是,当时尚的变化速度持续提升时,这些变化方式都可能逐步失效。首先,整体更新原本就难以实现。其次,快节奏的循环很难制造新奇感,因为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忘记曾经的时尚事物。第三,局部替换具有程度的限制,仅仅增加一颗扣子并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陌生感。同时,我们对新奇的标准也会随着时尚的加速而不断提升。由此,为了维持自身的运作,时尚符号的变化还需要意义层面的补充。
四、时尚符号的意义变化:形式差异的强化
虽然在时尚的语境中,符号的基本所指只是“时髦”或“不时髦”,但这些符号却可以利用自己在其他层面的意指含义来制造差异性和新奇感。这些意指含义将成为时尚符号能指的一部分,从而融入时尚符号的形式层面。由此,意义成为了形式的补充。这意味着时尚符号形式的局部替换不仅是形式本身的替换,还可以是符号含义的替换。例如象征热情的红色与象征危险的红色就是两个不同的时尚符号,表现青春感的短裙与表现运动感的短裙也是两个不同的时尚符号,指涉现代工业感的透明玻璃杯和指涉清新自然风的透明玻璃杯更是两个不同的时尚符号。它们虽然没有形式层面的明显差异,却具有意义层面的显著不同。这些意义差异足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将它们区分为时髦和不时髦。只不过,时尚符号通常不会单独利用意义层面的差异,而是会将其与形式差异相结合,因为意义层面的差异是非直观的,人们很难在没有任何引导的情况下准确地将其识别出来。
这些能够制造意义差异、补充形式差异的意指含义就是凡勃伦所说的时尚“托辞(pretense)”。凡勃伦在分析时装的变化原因时曾经指出,时装有很多不切实际的作用,它们往往会令时尚追随者感到不安和难以忍受,因此,时装总是会把某种以实用性为指向的目的作为革新的托辞。可是,这些托辞又很容易被识破,因为它们不能被设置得过于真实和严肃,不能完全掩盖了时装显示有闲的重要功能,否则,时装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而当托辞被揭穿时,人们会再次因为时装的奢侈浪费而产生罪恶感。由此,人们只能从一种新的带有托辞的时装中寻求安慰。这便促成了时尚的变化性。[14]不过,凡勃伦只指出了实用层面的托辞,当代时尚的托辞要更为丰富。美观、彰显个性、凸显地位、情感慰藉等都是时尚为了变化会使用的托辞。设计师们擅长用直击心灵的故事讲述自己的灵感,以表现其独特意义;喜欢用震撼人心的舞台展示自己的设计,以增强其文化氛围;更沉迷于用妙趣横生的广告推广自己的产品,以呈现其深刻内涵。这些行为都是在制造时尚托辞,它们旨在述说作品的新奇之处。时尚发布会就是灵感、舞台和广告的最佳聚集地,海滩、邮轮、森林、手术室、超市等故事场景都曾被搬上时尚秀场。灯光、音乐、模特、道具、标语等元素的巧妙搭配不仅能为时尚产品的形式增色添彩,还能增加其意义层面的丰富程度,它们构成了时尚托辞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托辞具有明显的放大和强调作用。当人们无法明确判断符号的形式差异时,托辞能够引导人们识别出时尚符号在意义层面的差异,从而强化其形式层面的新颖之处。这是消费主义中的常见技法,大众媒介用不同的话语让单纯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及膝半身裙比过膝半身裙更显腿长,桃粉色比水粉色更显肤白,A型裙比H型裙更显年轻,拉链式的外套比纽扣式的外套更方便,魔术贴的鞋子比系鞋带的鞋子更易穿脱……这些托辞用“纤瘦”放大了2厘米的长度差异,用“好气色”突出了微弱的色彩区别,用“实用”强化了几秒钟的穿脱时间。它们用丰满华丽的外表实践着简明有力的差异性逻辑,甚至可以将几乎完全相同的形式阐释为不同的时尚符号。近几年流行的宽松牛仔裤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抛开时装大片中的模特、背景、色调等附加托辞元素,前几年流行的男友风牛仔裤与近两年流行的老爸风牛仔裤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它们都是将宽松款的男士牛仔裤翻转为了女士牛仔裤,只不过前者被诠释为了强调性别平等的时尚潮流,后者被阐释为了跨越代际的复古风格。
同时,时尚托辞的阐释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去价值功能,它只以制造差异为目标,而不涉及价值高低的判断。就像鲍德里亚指出的那样,“从迷你裙到长裙,其中所包含的差异性以及选择性的时尚价值与从长裙到迷你裙的价值是一样的”。虽然时尚变化似乎总是以“美”为目标,但这种“美丽”只是被阐释出来的,它是对无尽变化的时尚的一种合理化论说,它能将“最为怪异的、功能性障碍的、滑稽可笑的特性视为凸显自身的差异性”,它们能将“叛逆”“慵懒”“不羁”的形象诠释为“美”的形象。[1]63曾经,铅超标的美白化妆品被大为追捧,影响自由行动的超高假发也被人们争相佩戴,可能引发多种疾病的紧身胸衣更是长时期地占据女性的衣橱。现在,极度不舒适的“恨天高”被奉为时髦单品,威胁健康的消瘦身材则被称为超模比例。这些在理性上几乎没有任何优势的时尚单品都受到了时尚之“美”的眷顾,它们超越了塔尔德所说的逻辑规则,而遵循着超逻辑规则。它们让各种“很蹩脚”的托辞显得理所当然[8]102。可见,在时尚符号的逻辑中,几乎所有的意义都是制造差异的媒介,一切看似有意义、有价值的概念都只是时尚变化的托辞。它们与符号的形式层面共同构成了时尚扩张自身领地的有效工具。这是时尚逻辑的权力,也是时尚符号的本性。然而,这种去价值的能力却为时尚文化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五、时尚符号的变化边界:价值底线的守护
正是由于时尚逻辑对价值标准的忽视,即便时尚文化具有不少正面意义,它也一直承受着道德层面的各种谴责。时尚无视礼仪、规则和风俗,它挑战传统,颠覆秩序。它用无尽的更新助长了奢侈,用蹩脚的托辞激发了欲望,用制度化的模仿压制了反思能力,用无意义的差异替换了真正的审美。它用强有力的差异性逻辑将人们束缚在求新的世界中,又用多样化的符号伪装自己的单调所指。时尚符号用永恒的变化激活了意识用于阻挡震惊感的防备功能,进而削弱了现代人对新奇的感知能力。这不仅会导致审美能力的持续弱化,还可能引发价值观念的坍塌,进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时尚在利用各种文化形式及意义制造差异时,不应该忽视这些形式及意义本身的价值,而将它们抽离为纯粹的工具。巴特在分析时尚符号的组合方式时就曾指出三种不可能性:物质规则层面的不可能性,道德或审美层面上的不可能性,习俗层面上的不可能性[10]165。第一种不可能性属于存在层面,例如裙子不会有两个裤腿,杯子的结构一定包括杯底,背包肯定有开口等。而后两种不可能性属于价值层面,例如内衣一般不会外露,袜子通常都穿在鞋子里面。这些不可能性都是高于时尚逻辑的物理和文化规则,它们应该受到时尚符号的尊重。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时尚极度扩张的时代,时尚逻辑虽然很难颠覆存在层面的不可能性,却可以弱化价值层面的不可能性。这不仅是时尚托辞的潜在功能,也是时尚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助力。如今,裙子可以是透明的,内衣可以外穿,严肃的西服可以搭配网球衫和运动鞋,袜靴翻转了袜子和鞋子的叠加顺序。就连一些原本严格遵从宗教规则的头巾也开始紧跟时尚的步伐,“适度时尚(modest fashion)”在习俗与时尚审美之间寻找到了最佳契合点。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时尚符号具有去政治化、去宗教化、去习俗化的功能,它可以将遵循象征性逻辑的各种文化符号转化为遵循差异性逻辑的时尚符号。在时尚的语境中,裤子上的补丁不再代表艰苦朴素和勤俭持家,而仅仅是一种时髦的装饰;连衣裙上的宗教人物也不再是被朝拜的对象,而是新颖的印花图案;印有“DHL”的T恤也不再是快递员的工作服,而是一款与职业无关的时装。无疑,借用文化符号已成为时尚逻辑的常用手法之一,它与重复过去的时尚符号一样,既能为人们带来新奇感和陌生感,又能降低创新的成本,只不过前者利用的是空间差异,而后者利用的是时间距离。文化符号既可以用于增补其他时尚形式,也可以被解构和重组,进而形成新的时尚符号,并为时尚的变化提供更多可能性。这是时尚对文化平等与自由的表征,更是当下跨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可是,这并不能成为时尚滥用文化符号的理由。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联都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它涉及我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这种厚重的积淀不可能被轻易忘却或忽视。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那样,“虽然我们对各种美的情感会受到风俗和时尚的重大影响”,但由于道德上的赞同与不赞同立足于人类天性中最强烈和最充沛的情感,它们只可能在时尚的影响中“发生一些偏差,却不可能完全被歪曲”[15]。虽然鲍德里亚认为,在时尚中,世界终将丧失一切参照,并进入最终的消解[16],但这种观点却略显悲观。无论时尚如何发展,它总是位于一种更高层面的社会文化之中,无论时尚逻辑如何扩张,它总是处于一个更大的符号系统之内。文化符号的时尚化只能暂时性地掩盖其象征意义,而不能彻底切断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否则,社会文化就会失去其历史深度,并走向虚无,社会价值标准就会逐步坍塌,并走向混乱。
近年来,多起时尚品牌涉及文化歧视的事件就是由于时尚逻辑超越了价值规则,从而让文化挪用成为了文化冒犯,并引发了大众的谴责,例如杜嘉班纳(Dolce&Gabbana)“筷子”事件,古驰(Gucci)的“黑脸”毛衣事件等。伴随着时尚文化的持续扩张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化挪用已经成为时尚界的热门话题。借助网络,人们能够轻易获知各个时尚符号的形式来源和原初意义。在文化交流逐步深入的同时,人们对各类文化的敏感度也明显提升,文化挪用现象也越来越容易引发争议。虽然绝大部分时尚引领者在借用他者文化符号时,并非怀有刻意冒犯的意图,但由于时尚变化的速度太快,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深入了解这些陌生文化,也没有恰当的机会去反思自己的借用方式是否合理。这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时尚的加速助长了不恰当的文化挪用,快餐式的符号借用则为时尚提供了高速更新的渠道。在这样的趋势下,时尚逻辑更应该重视价值标准,以免陷入这一不良循环,并为文化的和谐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时尚符号的运转就像是一场以变化为规则的特殊游戏,它建构了一个轻盈的流动世界。但是,游戏具有隔离性,它不应该将自己的规则随意延伸至其他领域。虽然从逻辑层面来说,时尚符号具有征服一切的可能性,它能利用形式层面的替换与意义层面的强化来践行变化、差异与新奇的运作模式,但时尚符号的组合并非绝对的自由,它必须遵循一定的物理规则和价值准则。时尚必须坚守基本的价值底线,将自己的变化控制在一定的边界之内,以保护既有文化体系的基本结构。时尚符号在征服其物质载体时必须了解历史、尊重文化,不能一味地求新求变、标新立异。即使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时尚也不能忽视理性的思考。时尚符号只有将自己的逻辑放置在社会价值体系之内,才能保持时尚文化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注释:
① 关于学术领域的时尚现象的研究可参见:王晓升:《论学术“时尚”——从鲍德里亚对时尚的分析说起》,载《哲学动态》,2013年第7期,第20-25页;Crane D.“Fashion in Science:Does it Exist?”,载 Social Problem,1969年第 16卷第 4期,第433-441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