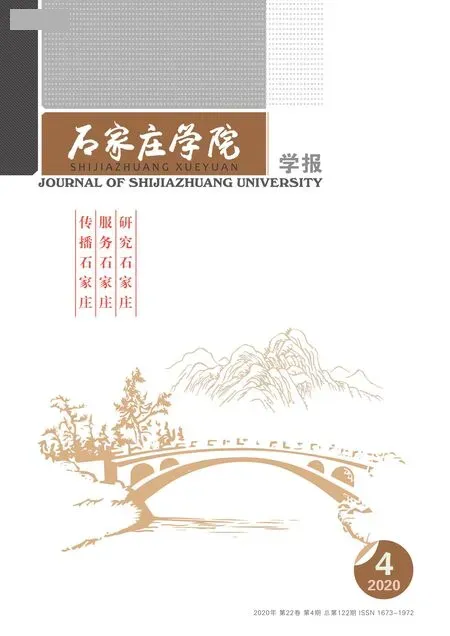论孙犁“新笔记小说”的创作
刘佳慧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图书馆,天津 300250)
有评论家认为,孙犁是解放区作家中受时代局限最小的一位作家。这是因为作家常常会根据自己的个性主张和审美追求,对题材在艺术上进行特殊处理,使得一部分作品既顺应时势,又具有时代之外的特殊价值,其创作也由此而获得了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很多时候还颇有预见性地探索出主流文学的可开辟领域。李瑞山认为:“作家忠诚于时代,忠诚于人民,作家的思想感情与时代和人民神貌俱合,无不相通,作家的创作与时代的大潮息息相关,完全契合,‘生活的实践和写作的实践完全统一’,作家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进而反映出时代的脉搏,表现和讴歌时代的进步精神,并在作品中融进作者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真诚地表现自己”,从而使作品“反过来作用于时代”。[1]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孙犁题材开拓和表现领域的自觉性、先觉性。孙犁晚年创作不仅暗含“寻根文学”萌芽,与各类风俗风情小说和新文化小说遥相呼应,最重要的是开启了新笔记小说的先河。
孙犁晚年创作《乡里旧闻》和《芸斋小说》,目的是记录历史,虽然仍以“真人真事”为写作素材,但不只是隔开时空,还具有明显的思辨和评说色彩;旨在通过小人物来表现大时代,是笔记体和史传体的结合。《乡里旧闻》通过“听说”形式为农民写史和作传,《芸斋小说》则以“笔记小说”的形式来记录自己亲眼所见的文革众生相和自我感悟,人名为虚,经历为实,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对国民性进行深刻挖掘,成为兼具传统史传笔法和现代主义色彩的佳作。
一、界限不明:孙犁“新笔记小说”的创作特色
孙犁晚年的小说与散文创作间界限甚微,作家跨文体的成功却给学界带来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孙犁晚年的叙事类作品都是笔记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新笔记小说的开先河之人;也有学者认为,“孙犁晚年只创作过散文,没有创作过小说”[2]6。孙犁晚年文体的含混,既是出于避免麻烦、多渠道尝试书写形式的主观用意;又是在跨文体领域“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基于“文体不但是指一种形式,更首先是指一种内容、一种思想体的外化:一个小说家能够用别人尚未试过的方式来讲故事,总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别人从没听过的故事”[3]42的概念,从叙事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孙犁晚年的写作,除去诗歌、杂文、副文本写作和回忆、寓言、悼亡等纯散文,包括《乡里旧闻》中的绝大部分和《芸斋小说》中的全部作品在内的叙事类作品几乎都可以算作新笔记小说的创作范畴。
《新笔记小说选》的编者张日凯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说:“新时期率先从事新笔记小说创作的是几位老作家,继之,中青年作家也涉足其间。孙犁的《芸斋小说》,可谓开新笔记小说之先河。1982年春,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纷繁的来稿中发现了孙犁的墨迹,这便是《亡人逸事》。全篇两千余字,读后顿感笔记小说美学意味十分浓郁。”[4]432汪曾祺则认为:“相当多的笔记小说的感情是平静的,如秋天,如秋水,叙事雍容温雅,渊渊汩汩,孙犁同志可为代表。孙犁同志有些小说几乎淡到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语简而情深,比如《亡人逸事》。这样的小说是不会使人痛哭的,但是你的眼睛会有点潮湿。”[4]2孙犁开启新笔记小说创作之滥觞,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新笔记小说》选了孙犁的11篇作品,只选了汪曾祺的5篇,足见孙犁在“新笔记小说”创作领域的分量之重。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笔记小说”的概念并不明晰。“笔记,文体名,异名有随笔、笔谈、杂记、札记等。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作品可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但亦可专门记叙、论述某一方面。”[5]2112笔记因为记录史实和一朝一代的文献故事、人物言行而带有纪实性,久而久之,甚至肩负起“补正史不足”的作用。但有时因为记录者的主观渲染和延伸想象而具有“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色彩,在文体范式上向小说接近,渐渐也因此具有了“小说”之名。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笔记和小说都驳杂不纯,难免会发生交叉。
孙犁本人并未承认笔记小说的概念①孙犁在《论笔记小说》一文中认为笔记和小说不同,有小说式的笔记,也有笔记式的小说。,但却撰文梳理了笔记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还为笔记小说分别释义、辨名。他认为,笔记小说秦时已以断片形式出现,汉晋初兴,唐宋大兴,明清已浩若烟海,但杂列并陈,概念渐偏重于小说,笔记注重记史、军国大事、重要人物言行等,与今天的小说定义大不同。他喜爱的正是这种文体不明的混淆体,如王林所说:“他(孙犁)经常购读中国士大夫的‘笔记小说’、‘随笔文学’,更加重了他那种超阶级、非阶级斗争的士大夫封建思想。”[6]125笔记小说在孙犁的藏书中占有1/3,孙犁有唐人笔记十几种,宋人笔记十几种,明清笔记还处于糠米不分的状态。
学界对于“新笔记小说”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定义,钟本康从三个阶段梳理了新笔记小说的发展脉络:“80年代初,孙犁、汪曾祺等老作家揭开新笔记小说创作的帷幕。林斤谰、贾平凹、何立伟的一部分作品也具有了笔记体的特征。80年代中期,阿城、韩少功、李庆西、高晓声等人的新笔记小说的创作,进一步扩大了新笔记小说的影响。80年代末,除老作家们新作不断外,还有田中禾、陈军、张曰凯不断充实其队伍。”[7]1李庆西于1987年将这些作家的创作定名为“新笔记小说”,新笔记小说都是具有传统文人气质的作家的作品。张舟子认为:“新笔记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新笔记小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直接继承了中国文学史上笔记小说的艺术传统,但是又不拘泥于这一传统。几乎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各个门类。”[8]7
孙犁新笔记小说的创作,主要来自于《世说新语》《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孙犁买过多册《世说新语》,他说:“我读这部书,是既把它当作小说,又把它当作历史的。以之为史,则事件可信,具体而微,可发幽思,可作鉴照。以之为文,则情节动人,铺叙有致;寒泉晨露,使人清醒。尤其是刘孝标的注,单读是史无疑,和正文一配合,则又是文学作品。这就使鲁迅说的‘映带’,高似孙说的‘有不言之妙’。这部书所记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记言为主。事出于人,言出于事,情景交融,语言生色,是这部书的特色。这真是一部文学高妙之作,语言艺术之宝藏。”[9]329由此可见,孙犁对《世说新语》小说成分的看重仍然要大于笔记成分。他晚年《芸斋小说》和一些怀人之作,都向《世说新语》学习,侧重于书写人物品藻。如《杨墨》开端就直接做了《世说新语》式的人物介绍:“老友杨墨,山东人。高大如杨,状其身体;粗黑如墨,形其皮肤。非本名也。长相虽然如此,性格却是很温和,很随便的”[10]399,显然是模仿《世说新语》容止篇的写法。
《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本身都是小说,但是有笔记的形式和成分,《阅微草堂笔记》继承了笔记传统,《聊斋志异》是笔记、传奇兼而有之。这两部名著都对孙犁晚年的创作有深刻影响。孙犁对《聊斋志异》的感情,绝非一般古典文学名著所能比拟。在他心中,《聊斋志异》的成就几乎仅次于《红楼梦》。他读这部书,断断续续读了若干年,而且是苦闷的时候读,寂寞的时候也读,用一生细细咀嚼品味。同时他又非常喜欢《阅微草堂笔记》,认为“《阅微草堂笔记》的成就,并不能就说比《聊斋志异》低下”,是与《聊斋志异》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孙犁认为《聊斋志异》是一部奇书,让人百看不厌。他最爱《聊斋志异》的万物有情,认为《聊斋志异》直承了唐小说和唐以前小说的传统。孙犁非常喜欢《聊斋志异》的写人状物,常常在自己的创作中学习《聊斋志异》的叙事干预、偷笔法和弄引法,欣赏《婴宁》《黄英》等文的人物塑造。蒲松龄一直从农村下层的视角看待政治和世情,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孙犁。他的《石猴》《幻觉》《地震》都采用《聊斋志异》写法,不仅模仿得惟妙惟肖,还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
由此可见,孙犁认为《世说新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均为小说,并将《世说新语》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小说形态与笔记体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笔记小说形态。通过大量阅读笔记小说,孙犁在一些作品中逐渐使用笔记小说观察、理解生活的方式来进行写作。他靠自己的摸索,赋予了笔记小说现代性和生命力,创造出比较成功的笔记体小说。虽然都是记叙真人真事,但因为“我”的介入,使得以一二细节刻画人物的笔记形式变为小说模式。
孙犁晚年的两大系列创作《乡里旧闻》与《芸斋小说》都介乎散文与笔记小说之间,而《芸斋小说》直接被作家定义为小说,《乡里旧闻》却用“旧闻”二字含糊文体,表明作家自己也无意为其界定文体。但是,孙犁自己又在文章中强调过《乡里旧闻》系列作品中的《玉华婶》为小说:“《玉华婶》,此篇亦系小说,投寄《文汇月刊》。”[9]192由此可见,《乡里旧闻》不完全是散文,也融含小说成分。从创作风格来看,《芸斋小说》和《乡里旧闻》分别显示出倾向于《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不同文风。孙犁的《芸斋小说》,延续了从《左传》就开启的“君子曰”评论模式。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和虚构文学都受到《左传》中“君子曰”模式的影响,如《史记》的“太史公曰”、刘伯温的“郁离子曰”、《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此类既是评论模式又是补充模式的插入文本与正文形成“镜子—本文的关系”[11]171。作家通过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文言部分来评论人的命运、物的命运,人和物相互映照,散发出古朴的魅力。《乡里旧闻》则有一说一、照实叙述,作家自己不再做任何议论感叹,走的是纪晓岚采用限制视角进行叙述的路线,读起来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貌和味道。
二、殊途同归:论孙犁与汪曾祺“新笔记小说”的异同
虽然也有研究者将孙犁与汪曾祺进行对比研究,但存在研究不足、对比不够的问题。他们二人虽然知识结构、创作经历迥异,但同是晚年发力的作家,都于20世纪80年代初尝试新笔记小说的创作,是什么样的内因和外延促成了二人在晚年创作道路上的相遇,非常值得深思。
孙犁与汪曾祺虽然早年没有交集,但在创作方面心有灵犀、异曲同工,彼此互相欣赏。孙犁与汪曾祺的惺惺相惜来源于二人创作理念的一致。汪曾祺对美的追求是和谐[12]11,是健康、优美、富有诗意,他在创作中极力表现优美健康的人性,将乡土生活理想化。如:20世纪40年代的《邂逅》,书写了贫苦女孩庄严自尊的生活态度;50年代的《受戒》记述的是43年前的梦,书写了一段明净无邪的少年之恋。孙犁的美学观念也正是如此,其战争小说如《吴召儿》《麦收》《浇园》,都充满对乡土田园的浪漫描写。
二者都是晚年发力,汪曾祺有4/5的作品写于新时期,孙犁晚年的创作量大约占他平生创作的一半。二人晚年的创作都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怀恋,致力于修复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断层。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重续京派传统,书写系列怀旧乡土小说,如《故人往事(二题)》等。而孙犁也进行了相同的文学活动,书写了《乡里旧闻》等系列乡土小说。从对文体的认识上看,二者都是80年代新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家,都是文备众体的尝试者,在对固定文体的突围中,二人不谋而合。汪曾祺有意尝试,企图打破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界限,他自己也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我的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可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展开一些,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点的情节。”[13]165孙犁与汪曾祺的做法相似,说自己晚年的作品是纪事而并非小说,冠小说之名是为了解决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然而,与汪曾祺无论怎么打破文体,创作出的仍是小说相比,孙犁倒是拓宽了文体的类别,《芸斋小说》和《乡里旧闻》都很难说是单纯的小说或散文、笔记小说或纪传文学,文体的奇妙组合,暗藏作家意味深长的用意。
新笔记小说如同纽带,将孙犁和汪曾祺这两位大作家联系在了一起。孙犁认为,汪曾祺小说中“既有传统的东西,又向外国作家学习。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结尾之处,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赞扬汪曾祺的《故里三陈》,“读起来省时省力,而得到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少”;并发出“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的肺腑心声。[14]140
汪曾祺对孙犁也非常尊敬,他曾说过:“孙犁的小说清新淡雅,在表现农村和战争题材的小说里别具一格(他嗜书如命)。他晚年写的小说越发趋于平淡,用完全白描的手法勾画一点平常的人事,有时简直分不清这是小说还是散文,显然受到了中国的”笔记“很大的影响,被评论家称之为‘笔记体小说’。”[15]360并且赞扬“孙犁是少数几个懂得文学‘艺术性’的作家中的一个”,他最为佩服孙犁的地方在于:“孙犁抗战时写小说,不像别人就是摸岗哨,端炮楼;也不能说仅仅‘反映抗日’,他写的是‘人’。同样是对‘革命’、‘战争’的观察,在别人看到大风大浪的时候,他更容易关注到卷入其中的人情、人性”。[16]他选取各个时期的将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成功结合的几位典型性作家进行论述,解放区的代表作家就是孙犁,直接与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沈从文并列,还排在自己之前,足见汪曾祺对孙犁非常高看。
从汪曾祺三位子女书写的回忆录中,也可略见一斑:“他80年代初对我们说,中国让他服气的小说家只有三人,鲁(迅),沈(从文),孙(犁)……孙犁则是把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写成了真正的小说,语言也好。”[17]173汪曾祺曾经开过一个影响自己创作的作家名单,“在这个单子里,爸爸没有提到孙犁,可能是因为他开始读孙犁的作品时,风格已经基本形成了。可能是‘老头儿’当时也算有了一些名气,孙犁的年龄和他相差不多,当众宣称孙犁对他影响很大,觉得有些‘跌份儿’。这都是我们的小人之心。不过,爸爸当初确实把孙犁列入中国三个会写小说的作家之一”[17]226,儿女们的猜测对于又“好胜”、又好奇的汪曾祺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1995年,汪曾祺还将孙犁的作品改编过电影剧本,叫《炮火中的荷花》[17]226,足见两人渊源之深。
二者都把结构看成是文章的内在节奏,小说中都没有复杂情节,都爱书写人物传,也常常将人物传写成传神的人物志;都爱书写情感片段,常常使用空白结构。汪曾祺的《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孙犁的“旧闻系列”“旧事系列”“故事系列”都是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讲究,又不夸张、不刻意,靠感情真实和内在节奏取胜。从文字笔墨来看,二者的语言都因为清新流畅、雅俗结合的“文士”化口语而成为现代汉语写作的典范。二者都爱用唯美的五四白话语言、生动的北方口语、凝练的写意笔墨记人记事,文字兼有文言文的简洁和白话文的精致,是对现代汉语的完善。汪曾祺用墨,有时是略铺张的;孙犁用墨,则极为俭省。如同是写芦花荡景色,孙犁写道:“在那里,鲜嫩的芦花,一片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10]119汪曾祺则写道:“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当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薄棒,通红的,像一支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12]343虽然都书写了紫色芦花盛开时的荷塘景象,孙犁仅用一笔带出,汪曾祺则从多个角度描摹渲染。
同样是写能言善辩的美丽女孩儿,汪曾祺这样描绘小英子的外貌:“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12]333孙犁《麦收》中的二梅:“风吹过来,乌黑的头发往后面飘,孩子的脸多么丰满好看呀,这是奶奶从小一口水一口饭喂养大的啊!”[10]107汪曾祺从容貌、衣饰等多个角度书写了小英子的伶俐和精神,孙犁则充满感情地写出二梅的健康和质朴。
孙犁和汪曾祺都喜欢用白描和比喻状物写人,如孙犁的《言戒》,通过运用两段服装描写来比较传达室的中年工人发迹前后的不同,先前的无闻和发迹后之的奢豪形成鲜明对比,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政治暴发户的嚣张举止和丑恶心理。汪曾祺也通过人的服装写性格,如《瞎鸟》中的“大裤裆”:“他夏天总穿一条齐膝的大裤裆,裤裆特大。‘大裤裆’独来独往,很少和人过话”[18]302,用非常闲散简易的借代和描写就生动刻画出“大裤裆”闲散简单的性格。
孙犁与汪曾祺的笔记小说虽形似却有一些实质上的区别。从作品的主体性来看,孙犁每篇笔记小说中都有“我”,“我”不仅是叙述者,还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元,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如:《言戒》中的主人公虽然是传达室的中年人,但是却以“我的为人”为开篇,“我”的戏份很多;《三马》中“我”虽然仅为讲述者,但是却插入了大段关于“我”和老伴儿的故事。汪曾祺的小说中却几乎没有作者的影子,不仅“我”很少作为第一人称出现,就算以“我”的口吻来叙述,“我”也仅仅是个记述人,故事本身和“我”没有太大关系;《闹市闲民》中的“我”,仅有叙事功能。
孙犁缺乏汪曾祺的趣味,其作品中虽然不乏幽默之处,但不如汪曾祺那样随处可见文字的趣味,也没有汪曾祺小说中的讽喻内核,这可能与其正统的解放区作家身份相关。同时,孙犁又缺乏汪曾祺的悲剧精神。汪曾祺虽然不赞成感伤主义,但并不是消除悲剧精神,他文章的结尾常常是意蕴深长的悲剧,孙犁则很少用悲剧结尾。如汪曾祺写于“文革”后的《钓鱼的医生》,塑造了急功好义、一生总做“傻事”的王淡人这个人物形象。小说以这样一句结尾:“你好,王淡人先生!”[12]516《岁寒三友》等悲剧作品,仅结尾一句“外面,正下着大雪”[12]363,就让人惊心动魄,泪流满面。孙犁因为《芸斋小说》的结尾大部分附有议论部分的“芸斋主人曰”,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悲剧的力量。一些没有议论的,如《鱼苇之事》写旧时家乡的变化,作家虽然充满失落之情,但是仅用淡之又淡的“我听到的,也好像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10]394来收束全文,将感情隐忍克制到了极限。孙犁和汪曾祺的结尾都具有非常震撼的点睛功效,难分高下,都是高手风范,言有尽而意无穷。
文风的差异直接来源于性格和创作使命感的不同。汪曾祺以玩味的态度看待“新笔记小说”,孙犁写作新笔记小说还是出于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其晚年的叙事类作品以”回忆“为创作主线,已从讴歌时代的写实性、记录时代的史诗性向反思历史转向,作家不再倾向于为时代英雄做素描,更倾向于以小人物写大时代,以书写心灵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深刻挖掘国民性。汪曾祺刻画世情人性,总是向民间靠拢,多写闲散的民间形象,如《笔记小说两篇》中的老秦、老葛和捡烂纸的老头儿。《闹市闲民》中的“他”,一切政治运动都没在他的生活留下痕迹,是位“活庄子”。而孙犁却将政治人心结合,多写老战友和亲戚朋友的变与不变。汪曾祺把美好人情归于儒家文化,背后的实质是其对传统的依恋,这种依恋来自京派血脉。孙犁则把美好人情归于战争,孙犁晚年的创作总是充溢着革命情结和劝世情怀,背后的实质是孙犁对革命的皈依,这种皈依来自20世纪30年代末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交汇。
有学者认为:“……汪曾祺作品并非没有可质疑之处……对底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对民间的价值标准,汪曾祺往往无条件地认同、称颂。”[19]449尤其是其晚年的作品,更是完全采取赞赏的态度来书写民间。孙犁则不同,他晚年从文化批判角度审视传统农村社会,书写旧人旧事,重提“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切肤之痛,正面面对改造农民性问题,剖析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与鲁迅强调国民性的愚和病相比,孙犁在《乡里旧闻》中着重刻画了中国农民的又一“原罪”——“私”,直接地承续了“五四”传统。
已有学者指出:“只是到了汪曾祺的出现,新时期的文学才真正接通与40年代文学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20]243如果说汪曾祺承接的是20世纪40年代写生活的传统,那么孙犁也是从意识形态中努力突围而出,用生活来写政治的成功作家之一,同样也连接起40年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桥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若只见汪曾祺而不见孙犁,多少是有些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