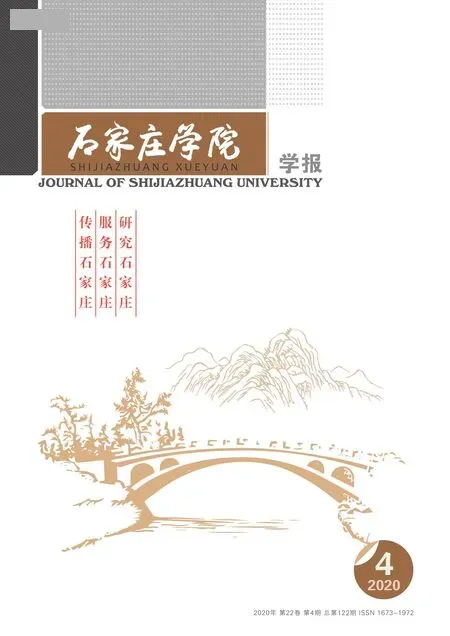唐慧琴小说论
默 崎,陈学通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石家庄新乐籍作家唐慧琴,先后发表小说《日头日头照着我》《牵牛花》和《拴马草》。这三部小说其语言形式是从知识分子的雅化书面语体到乡土小说的口语语体,再到口语、书面语混杂的语体。小说语言方式和叙述方式的不断变化体现着唐慧琴创作的逐步深入。同时,在这三部小说中,她的女性意识从不自觉甚至自我压抑的状态逐渐走向对女性意识的张扬。文革后,正定籍作家贾大山开拓了石家庄乡土小说写作,由他而起,周喜俊、康志刚等作家紧随其后,70后、80后作家脱颖而出,石家庄的文学创作队伍日渐繁盛。唐慧琴的小说创作,是当代石家庄作家谱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本文就唐慧琴小说的叙述方式和作者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对上述三部小说做历时性研究,从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作者在写作中思考的不断深化以及其女性主义意识的不断强化。
一、小说叙述方式
构思一部小说,语言风格和叙述策略的选择是其成败的关键。因此,对这几方面的分析研究就很有必要。
《日头日头照着我》(以下简称《日头》)的语言流畅自然,但又不失细腻文雅。小说以知识分子视角、现实主义笔法表现乡土中国的社会生活。《日头》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乡政府干部文秀在包村工作中发生的故事。因为小说是农村题材,故事围绕主人公文秀在几个村子的生活工作展开。作者把这部小说中的语言分为三类:人物以农民身份说话时,她多运用最能显示地方特色的方言、俚语进行再现式叙述;在叙述文秀等乡政府干部说话时,就在口语方言的基础上进行提升,使其带有一些书面语体的特点;小说叙述者讲述故事时,其话语偏向文秀式的风格,因为小说所聚焦的中心人物就是乡文化站站长文秀。
由题材而言,《日头》属乡土文学范畴,口语化的通俗性表达就成为此小说的必然选择。口语化写作自现代文学以来形成以赵树理和老舍为代表的两种表达方式。老舍的口语写作建立在北京文化基础之上,其话语风格典型地代表了北京人的文化特点和精神气质,成为京味儿小说的鼻祖。赵树理的小说面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而聚到解放区的读者,所以为了贯彻小说政治教化的功能,他的小说是以广大的北方口语为基础,舍弃纯方言表达的、地方文化意味强烈的创作风格。唐慧琴的小说语言显然是效仿老舍。她要以地方方言来进一步表现家乡的风土人情、民心民性。乡土文学的写作,是展现众多亚文化区域中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情,在不同的地方文化中寻找和发掘它的独特个性。她把方言融入到人物言行之中,以形成人与其居住地风土文化的完美相谐。它表达的不仅是人物与事件,同时要表现语言、性格、心理等综合在一处的地方文化。唐慧琴有着非常敏锐的语感和很强的语言掌控能力。她将活泼生动、充满原生态的日常口语和习语、俚语等各种话语素材充实到小说中,能凸显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形象。在写作中,方言土语的词汇表达能充分表现乡间自由自在、原生态而泥沙俱下的鲜活特点,但很多土语不能与文字对应,这是自有了口语化写作以来就存在的难解甚至无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转而采用书面化的词语来表达,虽然这样做部分失去了人物和话语的鲜活之感。总体而言,唐慧琴对方言的把握和运用在石家庄作家当中是出类拔萃的。
在《日头》的写作中,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平等而融洽,作者没有过多干涉人物的行动。人物在小说的虚拟世界中由一次次的矛盾冲突而凸显性格气质,成为比较丰满立体的“自由人”。人物活了起来,以自己的性格逻辑向前“独立”发展、行走。作者给予人物相对的自由空间,作者与小说人物之间形成一定的平等关系。这是中国文学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另一种小说写作模式。它是陈独秀之“德先生”“赛先生”等观念的产物。唐慧琴的《日头》的写作与巴金创作《家》的情况就有些相似。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后,小说中的人物便全部活了起来,由此而自足地成长、丰富充盈。作家的任务就是“忠实”地“记录”而已。这使作品成为一定程度的“自足”式写作。比如,文秀由起始对包村事务的手足无措到后来的游刃有余,甚至一些无关大局的“小伎俩”的使用。她与乡政府大院里同事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分化组合,在家庭内部夫妻、婆媳之间,与自己娘家弟妹和母亲之间,这些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共同作用力的形式推动着文秀在一点点改变。人物在事件矛盾的积累中而逐渐形成以既有性格气质为基础的发展变化。小说并没有俗套地以“大团圆”结尾,而是尊重其人物与事件的内在发展逻辑,形成了开放式结尾。
从《日头》到《牵牛花》,唐慧琴以不同的笔墨来完成对故乡的发现与刻写。其语言由较为文雅细腻向俗白粗粝发展,这不仅是作者个人文字驾驭能力的表现,更是一种跨越性别与文体风格的变化。这让我们又一次体会到语言写作的规律是“由简到繁易,由繁入简难”。口语化写作中讲求的“俗白中求精工”,一般人很难达到。我们的语言文学教育一般都是以文字的典雅精致为最终指向。在这样的文学写作和审美教育下,无病呻吟的所谓雅辞丽句充斥文坛,俗白、简洁有力的口语化表达却凤毛麟角。
小说《牵牛花》的语言,带着新乐乡土气息,生动传神。在讲述珍珍原来是跟何长山私奔了时,一句“怪不得二十六岁了还不嫁人,原来是草帽底下扣着人呢”[3]8。叙述村里的“小广播”台乱这个粗俗的人时,说他“有气无力的,像割了蛋的驴”[3]130。小能人台乱的顺口溜,“何长山就是沾(石家庄一带方言,行的意思),小麦种到大河滩。就是天公不作美,二亩小麦全旱干”[3]122。“给脸子看,给话头吃。”[3]122“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3]130这样富于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语言,使唐慧琴的小说更富表现力。
叙述语言变得粗粝,使《牵牛花》的小说风格也为之一变。作者女性身份向后台隐退,传统话本中的说书人(男性)身份凸显。这乍看是作者写作的“大踏步后退”:由知识者的审视甚至俯视变为说书人的旁观。视角的下移,颇有作者与笔下人物尽情狂欢的意味。当然,作者并没有让其进一步发展为“狂欢体”的写作,她使小说时刻保持在叙述人的控制之下。这种乡土小说的写作,唐慧琴笔下所呈现出来的虚拟世界,既和她保持着近距离亲密接触,又在心理上产生了一些距离。近是因为作者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乡土,她一直生活在城与乡的接合部,对农民和农村生活有着近距离的直接体认;远则是因为作者的文化心理、精神气质已经远高于这些笔下的乡邻,对家乡人的生活做派、精神气质能作理性的判断分析。上述一切恰好促成了作者对自己的故乡的深刻认知,又使她能够以远距离的视角完成对故乡精神回望的审视性写作。
随语言而一起粗粝的,是小说所表现出的审美气质。唐慧琴的这种写作,使《牵牛花》向传统话本体叙事“回归”,唐慧琴的小说美学风格也由之而变:由知识者对故乡大地的悲情式观照向大气混莽、泥沙俱下、不着更多评判的道路发展。同时,叙述节奏加快,全篇情节点环环相扣,写景抒情的“空镜头”使用越发减少。人物性格甚至行动更多地被作者掌控。作者与其笔下的人物不再和平共处、互相尊重。人物形象也随之由丰满立体向略带扁平的状态发展。我们知道,人物形象的丰满与扁平没有高下之分。扁平型人物塑造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惯用手法。在回归乡土的小说创作中,这样的人物塑造更能与小说整体形式相匹配。回归传统与乡土的写作使唐慧琴的小说语言更加汪洋恣肆,土语、俚语联袂而出,人物形象在单薄之外其性格却更加凸显。工笔细描向大红大绿的年画式写作挺进。
这种作者成为主导的传统写作,其产生、发展是以乡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的存在方式为文化依托的,在对人物甚至读者能动性的限制前提下而展开。笔者认为,每一种写作的模式和方法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能简单区分其优劣。作家只是在寻找更为“合脚的鞋子”。小说创作观念的改变,间接性地表现出写作者与其当下生活之间的联系。同样,它也反映着作者全部的内在意识形态样貌。
贴近现实,不矫饰做作,不对人物进行刻意地拔高,以事无巨细的微观再现、近乎呈现性的工笔描画出今日石家庄乃至河北人的乡土生活。然而,也正是这样对农村、农民近距离的摹写,时代发展变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以氤氲之气为之衬托,以点带面的写作才得以完成。那些刻意迎合时代主旋律、以一时的政治概念为得失,貌似紧跟时代大潮、敷以假面的虚伪写作,最终将被历史抛弃。
《拴马草》为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的语言风格以混杂的方式呈现。总体而言,它们既有对唐慧琴之前写作的承袭,又有新的变化。
《拴马草》中前面几篇小说的语言沿袭了《牵牛花》的状态,以口语化、方言味浓郁的乡土小说的叙述形式展开。作者长期生活于此,她对农村人事的高度熟稔,使其作品中的人物形神毕肖。家长里短的世故人情,被她叙述得绵密有致。女性的细腻观察与深刻思索,又让她看到传统乡村伦理与市场化的碰撞。小说集后半部分的几篇作品,其语言风格又向着知识分子化的书面语挺进。在《青花小袄》《好大一棵树》《桃花红,梨花白》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面貌的小说叙述者。这些小说语言细腻温婉,故事也随之聚焦到城市中年知识女性身上。典雅精致的叙述语言,表现独立不倚却能随物赋形的女性形象。她们能穿透事物的外表而抵达其本质,深谙世故之道却依然保持内心的单纯。到此处,唐慧琴的小说语言成为具有某些“小资气”(追求独立人格)和大家闺秀风范(传统、婉约,对男性既有期望又不主动行动)的合体。
从语言风格来看,唐慧琴的三部小说给读者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貌,并且这些语言形式对小说内容起到了很好的辅助功能,为其小说的整体思想价值提供了有力支持。她对语言的把握精准到位。她的小说语言有时泼墨如雨,滔滔不绝,宛如大江东去;有时却惜墨如金,点到即止,三言两语就把一个人物写得丰满生动。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唐慧琴小说的缺憾是她的语言有时过于汪洋恣肆,该收的时候由于其叙述的惯性很难刹住;叙述与评论过多,就会干扰读者的兴致与思考,读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作者的思想而成为一种“不平等”的交流。她的小说中高密度的事件(情节)连缀,也会使她的写作过于追求生活的真实、原生状态而忽略了小说毕竟是一种艺术性再现的有意味的形式。就如同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集体化境遇:在只重再现生活而刻意隐藏情感与理性评价的形而下写作中,对人的精神追求、对生命存在的揭示缺少了一种追问的力度。唐慧琴的写作也应该对此高度关注。
这种以实写虚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未见得是唐慧琴有意识的自觉行为,但她这种写作方向值得肯定。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发展了70年,这期间既有失败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建国初的革命现实主义由于其只顾意识形态的张扬而忽略了文学本应首先是人学的特点,成为高大全实则假大空的写作;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又使文学成为一种过于追求现代主义形式的游戏而曲高和寡;之后的新写实小说取其两端,既没有了意识形态的虚假宣传,又丢掉了先锋文学的形式追求而变得空心化严重,没有了对历史本质和人的生存意义的寻找。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度写实并抒写人的精神追寻的小说就更受到各界读者的青睐。小说以实写虚的风格,以精雕细刻来表现社会生活的苍莽之气,也能达到对人生之追问的高度。所以唐慧琴的高度写实的小说,自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二、女性意识的萌动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唐慧琴小说的主角绝大多数是女性,她笔下最为出彩的人物也多为女性。持续对女性自身的观照、审视,使她的小说表现女性话语身份、女性意识越来越频繁而深入。
《日头》是农村题材小说,但其叙述人的形象、小说的语言风格具有女性知识者的话语特点和思想意识。它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写作上相对缺乏经验,因此作者选取叙事聚焦的人物更靠近作者本人。小说以一个农村“文化人”(乡文化站站长)视角展开叙述。这使小说更能在虚拟性与真实性织就的文本中驰骋。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可以不经过更多变形,以“我手写我口”的方式流泻而出,使小说在情绪情感的抒发上更为真实且气势饱满。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会以更高的真实性打动读者,它具有强烈的代入感。作者的职业身份与人物高度重叠,文秀这一乡镇女干部形象就更加真实可信。她既能看到乡政府大院里各种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又能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心理去感受、分析这多维的社会生活。这样,小说的人物就更加立体鲜活,事件与情节更富内在的逻辑性。
从唐慧琴的角度而言,越贴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女性心理状态的写作,就越容易以真情实感引起读者的共鸣。写作者在起步阶段,对以自身为中心的周边性社会生活的开发更容易上手并取得良好效果。纵观中国新文学以来百多年的时间,从鲁迅、茅盾、老舍到今天的严歌苓、莫言、贾平凹,由自身写起几乎成了小说创作的通例。这也符合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心理认知规律,小说创作以自身为起点而逐渐扩大。
在创作《日头》时,唐慧琴的女性意识尚在未被真正触发的状态。她以更为多见、“流行”的现实主义小说为模本进行创作。她隐藏在男性构成的强大话语背后,以混杂了男人与女人的眼光来观察这丰富多姿的社会生活。故文秀虽身为女性,却没有更多地基于女性性别之上的话语表达。
唐慧琴的《牵牛花》是向传统乡土叙事回归的创作。传统乡土小说题材的写作,其创作架构与情感、美学表达以民间化、地方化和通俗化为主要特点,以底层民间文化为载体。传统文化便在这样的乡土题材形式中发扬光大,持续流传。由性别而言,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是充分男性化的。主人公珍珍冒犯传统日常伦理的行为,是公然与男权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的对抗。表面沉寂的传统文化被撕开一角,珍珍与何长山的“不轨”行为必然招致村民的不满。
小说通过珍珍把女性意识的话题表现出来。为了爱情,这个未谙世事的女孩可以忍受一切:村人的嘲笑非议,亲人的冷眼甚至打骂,自己在地窨子苦等何长山三年时光的磨难。越是偏僻落后的地方,男权思想越根深蒂固。对一名女性而言,其以卵击石的反抗何其艰难。珍珍对传统世俗伦理的挑战,也是作者唐慧琴内心深处对女性自由与平等的呼唤,对传统男权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小说采用的珍珍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抗争的叙述模式,自现代以来的小说文本中比较多见。女性因爱情婚姻而采取的行动,在乡土伦理的文化范畴里并不突兀。因此,小说以珍珍的逃婚与私奔展开故事情节,不会使读者感到生硬突兀的女性主义呐喊,因为它是以追求人性自由的大旗为掩盖的、对女性意识的间接性表达。作者故意弱化了珍珍反抗、颠覆乡土传统男权伦理的女性主义呼喊。这种策略性叙述,客观上降低了女性主义思想与传统伦理之间的直接剧烈冲突。因为这种传统的乡土伦理叙述本身就是充分男性化的文化之体现。一定的叙述形式就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显现。也可以说,作者唐慧琴在一个传统的题材叙事之中注入了现代的因素:抗婚与私奔不仅作为传统的争取自由来看待,而且成为女性为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抗争方式。
相较于珍珍颇具反抗韧性的闪光形象,男主人公何长山要暗淡许多。他本是村里说一不二的支书,但在与珍珍相携一生的故事中,何长山在小说中最为精彩的华章也就是与珍珍越出伦理的“私奔”行为。小说对珍珍浓墨重彩的描摹,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何长山的形象表达,从这个角度而言,何长山成为珍珍追求自己爱情的一个“道具”。显然,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珍珍在与何长山的婚前交往以及之后的夫妻生活中,她一直保持着主动而不是柔弱地任人摆布。女性虽是弱者,她们却要在男性的世界里,闯出自己的天地。①这个为女性解放而抗争的大旗在小说的下半部移交到珍珍的侄女花儿的手里。作者潜在的女性意识的外化,才有了小说中珍珍们的行动。她要让女人在“白日梦”般的文本世界中去行动,去摆脱附属的地位。
唐慧琴在塑造珍珍这一形象时,其女性意识介于表现与隐藏之间。珍珍对爱情坚贞执着,宁可与世俗传统决裂,也要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这样的人物并不突兀,新的时代背景赋予了珍珍这种反抗的思想和意识的行动力,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我们所见到的郎才女貌的俗烂的教堂抢婚式的故事。所以在珍珍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女性意识的萌动。但这种女性意识的萌动又是含蓄的,她没有把珍珍塑造成觉悟了的女英雄,与何长山结婚后,她的女性意识又恢复到与常人无异的状态。乡土中国的一隅,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文化的传承与封闭保守是社会的常态。因此,小说的后半部珍珍就逐渐退出前台,她向传统文化反抗的行动终告结束。下一代女性花儿开始走到历史发展的前台。一代代女性的成长就是以她们生命中偶然的“冲动”而使历史的发展缓慢地改变其既有的轨迹。花儿没有更多的以情爱为起因的反抗性行动,但是她依然在向着女性觉醒的更高远处行走。所以综合地看,作者的女性意识既有强烈的爆发式地对传统的直接冲击,又有在历史长河中的长时间沉默。唐慧琴这样处理其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恰恰高度符合了社会生活的本然样貌。其女性意识也就体现在表现与隐藏之间。我们可以视之为作者女性意识在其作品文本中的萌芽。但这种萌芽如同浮出地表的冰山,那巨大的水下部分被黑暗所掩盖。
小说集《拴马草》中的几篇小说,女性化意识变得更加明显。它们以知识女性的眼光视角来观察与审视复杂的社会生活。《青花小袄》中,“奶奶”是贯穿全文的线索,是千百年来女性在男性世界里柔弱并坚忍生存之象征——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强调,对女性的自我体认,不愿(讨厌)男人对自己猥琐地审视与冒犯。主人公与拍马屁的领导、铜臭味的商人,甚至那位庸俗的“农民诗人”,都是那样格格不入,而对“农民诗人”的母亲、“我的奶奶”式的女人则充满了体认之爱。而“我”与“大领导”之间的既疏远又贴近的关系,是由真正的理解或曰心心相通而形成的。所以小说所表现出的女性“我”的形象,虽貌似软弱且面容渐老(主人公一直提及自己四十多岁的年纪),但越是这样的女性,对自身、对男性则有着更深刻的体认。她与“大领导”之间,属于纯粹的形而上的精神之交。女性渴望被认同但又拘囿于男权场域对自身的“塑形”而不敢越雷池的内在心理,通过“我”与大领导的交往而曲折地表达出来。“什么事你不要找,你要等。”“奶奶”的这句话成为唐慧琴小说世界女性生存状态的隐喻。
唐慧琴的这种女性意识的逐渐显现,在她很多小说中都有表现。《拴马草》这部小说集里,《好大一棵树》《青花小袄》《桃花红,梨花白》都有相似的叙述结构①这种叙述结构介于独立与非独立之间的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它们进一步确证了唐慧琴对女性意识的自觉思考——一位中年女性,既婉约于男性构成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这样的写作,在以乡土文学为主业的作家写作中是极为难得的。具有了这样的女性意识,唐慧琴的写作就具有了另一种思考问题的维度和深度。同时,唐慧琴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不同于那些我们熟知的女权意识极为鲜明的作家的作品,比如一直进行女性主义呐喊的张洁那种《方舟》式的写作。这又形成了唐慧琴写作的另一风格,她不会像自由女神一样走上街头,去控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承受。她以独立而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追寻。她在文本中,树立自己作为女性的旗帜:她可以承受不公与偏见,但她已洞悉一切。她以隐忍的方式展开对男权社会的抗衡——这一点,再往前走一步,就可成为严歌苓《扶桑》式的对中国东方女性的精魂的讴歌与赞美。她地母般地面对苦难与伤害,对所有人持一种深沉博大的宽容与谅解。
唐慧琴的小说,擅长刻画的女性形象有两类:一是农村中的老年女性,二是自我色彩浓厚的中年女性形象。
她笔下的老年女性,有《拴马草》中的银平娘、《牵牛花》中的长山娘、《青花小袄》中的“奶奶”等。这些女性被赋予了比一般男性更有能力、更具魄力的性格特点。她们胸怀宽广、心地善良,在矛盾冲突时能当机立断。由于年长,她们的女性性别特征渐少,她们的“征战杀伐”依然是在浓厚的几千年男权壁垒之内闪转腾挪。她们恪守的依然是传统伦理与“妇道”,但是历史地看,她们在男性文化包围的战场中浴血奋战。这样的人物塑造,一方面是作者对女性自身的热切观照,当然更是她对男权有意无意的抗衡,对女性“英雄”的呼唤与寻找。
第二类女性形象的出现,让我们窥见了作者女性意识的自觉。这些女性形象更多地出现在《拴马草》小说集里。《好大一棵树》中的苏芸、《青花小袄》里的“我”、《桃花红,梨花白》中的“我”,这些人物都是人到中年的知识女性。她们承袭了上述老年女性历经沧桑而形成的老练与洞明,但是这些特点悄然隐于幕后,由直接与男性的对抗变化为试图一个人的精神独舞。无论面对俗不可耐的商人、同事还是面目模糊的不争气的丈夫,她们似乎成为方外之物。这样自得的女性自处方式,与男性保持着一定距离,却更吸引了男性的“围猎”。《好大一棵树》中的苏芸,就是这样女性的写照。她与男性的关系,尴尴尬尬,像极了《日出》里的陈白露。这就是唐慧琴女性意识萌动之后对女性、对自己的呈现式表达。在男性的世界里,女性走向真正的独立,何其艰难。于是,女性与男性的周旋依然存在,隐忍与承受伴随着的是她们对自由天空的想象。然而,天空高远,殊难抵达,就算真的有一天触摸到天际,可能依然不是她们想象中的样子。
唐慧琴的三部小说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来看,题目的拟定很有意味:《日头日头照着我》——《牵牛花》——《拴马草》。《日头》中,作者还没有清晰的女性意识表达,其女性话语是暗含在庞大的男权文化之后的。就如同题目之意,太阳(男性)对大地万物(包括女性)的普照(保护甚至拯救)。第二部小说中,牵牛花“生性强健……对土壤适应性强,较耐干旱盐碱,不怕高温酷暑”[3]封底。小说以草本植物牵牛花不炫人眼目甚至有些单调土气来象征珍珍这一人物形象。其百折不挠的韧性精神,身在底层不甘被埋没而勇于抗争的行动,处处散发着貌似柔弱实则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牵牛花一样的柔中带刚的坚韧气质。这种柔弱又顽强的植物,就是对以珍珍为代表的女性本质的表现。第三部小说集命名为“拴马草”,以之喻指农村妇女银平娘。拴马草“生长于路旁道边,根部发达,很难拔除,耐踩踏,生命力极强”[2]1。这就是银平娘的写照。她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与岁月洗礼,为人善良而大气,遇到大事更能冷静面对。这也是石家庄本土,甚至河北燕赵大地上受尽历史苦难的女性形象。作者正是以草更为朴实无华的样貌,抒写乡土中国的老一代女性形象。这三部小说相连缀的题目,能隐约表现出唐慧琴在小说创作中女性意识从隐在到逐渐在历史前台显影的历时性变化。文秀——珍珍——银平娘这样的女性人物谱系,成为作者逐步深入到久远年代对中国女性命运逐渐开掘的形象代表。同时我们也看到作者唐慧琴的女性意识的逐渐深化:从下意识的隐藏到逐渐一点点发生萌动,进而走向有意识的提倡。
总的来说,唐慧琴的小说创作,结合了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双重特点。她既有对农村、农民细致入微的刻写,又有对身居城市的知识女性内在灵魂的发掘。她因文而设的语言方式、由表及里的对女性意识的发掘和表现,在石家庄、河北乃至中国的小说作家的行列中,也有属于她的一席之地。从石家庄作家而言,她是继贾大山、周喜俊之后,比康志刚略晚出现的70后作家。文革后,贾大山开拓形成了石家庄乡土文学创作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唐慧琴在继承了前辈作家对方言土语、民间风习深刻表现的基础上,她以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丰富的社会生活为背景,书写着石家庄、河北儿女随中国在时代大潮下的发展而不断向前的故事。虽然唐慧琴的小说创作还远不够完美,但她以小说形式的精巧多姿、思想意识的深刻而卓然挺立。越是写实性地对一个具体地点之上人物、风习的深入刻写,反倒能映衬出大时代背景下国家社会之大江大河的缓缓流淌。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历史的参与者和记录者,她的现实主义作品也会成为历史发展变化的活化石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