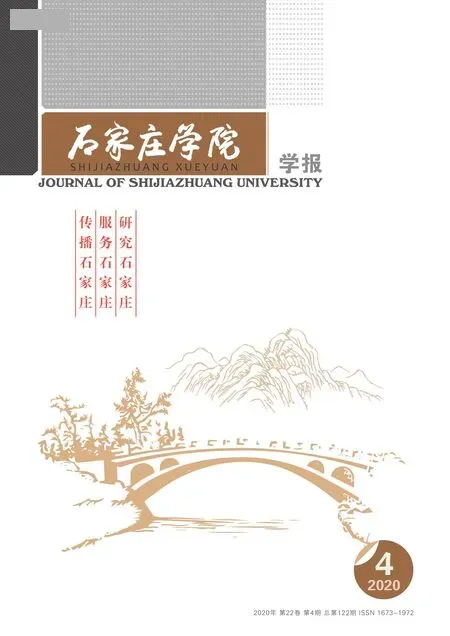元朝官方域外交流考
赫学佳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版图面积最大的朝代,占地面积1 372万平方千米。其疆域东至日本海、南至南海、西至天山、北至贝加尔湖。《元史》称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1]1071元朝是我国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需要统摄繁多的民族以及辽阔的地域,因此成就了一个极其开放的蒙元帝国。中国古代的域外交流在元朝不断发展和壮大,官方交流与民间贸易在范围和规模上不逊色于其他朝代。元大都(今北京)成为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2]
元朝的丝绸之路在汉唐丝绸之路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与域外国家交流的两条主要路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张亚光、毕悦提到,元代陆上丝绸之路大致可分为“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两部分。[3]Nichols J将蒙元时期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4]可见中国古代的元朝社会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目前国内学界对元朝的域外交流研究主要集中在域外贸易、丝绸之路发展等方面,对元朝域外交流以及朝贡体系的研究远远少于汉唐时期。针对这一问题,学者武晓丽对元朝的贡象现象进行了略述,[5]学者喜雷对贡女制度进行了评述等。[6]本文在梳理元朝域外国家朝贡方物的基础上,从官方域外交流的视角探析元朝在世界交通史上的贡献及价值,借助较为前沿的研究成果,重新评价元朝与域外国家的交流体系。
一、元朝域外交流体系述说
中国的域外交流从汉代伊始。《后汉书·乌桓传》中记载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率众向化,诣闕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7]2017由此可见,我国的域外交流史非常悠久。元朝的对外交流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1。

表1 元朝不同类型的中外交流
(一)中欧之间的交流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传入欧洲。李约瑟在其文集中对中国的发明进行了高度评价与赞扬,并提到世界受惠于东亚,特别是受惠于中国的整个情况正在非常清楚的显现出来。[8]263
元朝初期,欧洲的使者经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原之地。这期间,丝绸之路主干道受到昆仑山、阿尔泰山、天山、等东西山脉阻断,且途经之地大多是高山、沙漠与戈壁,驿站主要依托山脚零星绿洲或水草丰茂之地而设。[3]著名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提到,在西欧可以购买到中国的一些产品,比如丝绸、瓷器等。元代的著名来华商人马可波罗更是用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更了解中国,其中对中国多个城市进行了详细描绘,比如杭州、扬州等。除了来华的使者,元代统治者派往欧洲的使者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畏兀儿人列班·扫马出使罗马教廷和西欧诸国,他是最早到达西欧的中国人之一。
蒙古西征后,在亚欧大陆建立了四大汗国,分别是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尔汗国,四大汗国在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之间血脉相连,同时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驿路相通。汗国之间的来往畅通无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欧之间的贸易发展。元朝与欧洲诸国的交流主要以商业贸易为主,由此出现大量的民间商业团体与组织,属于非官方的外交方式。
(二)东亚与中国的交流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开始与东南亚建立联系,不断发展海上贸易。《元史列传·外夷篇》中介绍了元廷与高丽、日本、耽罗、安南、缅甸、琉球等国家的交往,其中与沟通最频繁的是高丽国,高丽国的世子多次被送到元朝大都为人质。相比于元朝与欧洲的交流,东亚诸国大多是元朝出兵进行武力征服之后,进行域外朝贡。元朝对东亚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战则屠城,降则封贡”。元廷与东亚域外诸国的交流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南方丝路,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元廷与东南亚诸多国家建立了官方朝贡体系。在派遣使者的同时,进行商业贸易。
随着元廷与东亚国家的交流,逐渐形成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封贡体制”。“封贡体制”又名“册封体制”,其是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分封天下的延续,为后世明代形成全国范围的“封贡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据统计,各种文献中记录与元朝有联系的国家和地区达200个以上,远达非洲东北部沿海地区。[9]
二、域外各国朝贡方物分析
域外各国使者携带的朝贡方物和礼品由于国别与地区而不同。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欧洲所到使者携带的物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宗教用品。马克兄弟因教皇大使的允许,依照大汗的指示,取得圣墓灯中的油少许。[10]92这里的圣墓灯是进行宗教活动的用品。欧洲使者曾多次来到中国,其主要目的除了商业交往之外,就是传教,因此欧洲使者的贡物之中必有宗教用品。第二种是欧洲贵族社会使用的精美生活用品。教皇给予他们许多有价值的礼物比如精致的水晶花瓶,以教皇的名义送给大汗。第三种是商业贸易物品。1260年,欧洲使节来到中国,朝见元代皇室之后,将自己所带的商业贸易产品进行交换。[10]93东南亚国家使者携带的供物大抵也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珍贵土产。据《元史·外夷篇》记载,安南国选择质量最好的土产如金、银、珍珠等物品,派遣使者进贡元朝。第二种是动物。元朝皇帝很喜欢象,经常向东亚国家索要象。[5]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中,有各种不同的奇珍异兽,朝贡动物成为中外使者携带之物中很常见贡品。第三种是人,其中包括女人、太监以及各类技人百官。朝贡来的人,主要进入皇家贵族社会,有的进入皇室,也有的会被赏赐给功臣诸侯。
结合以上6种情况,笔者对5种比较特殊的朝贡方物进行详细阐明。
(一)代身金人
元朝,安南国向元廷朝贡一种比较特殊的物品“代身金人”,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至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这300多年中,安南国共计向元廷朝贡“代身金人”8次。[11]
“代身金人”之事始于元世祖至元年间,《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一月,留其使郑国瓒于会同馆。复遣柴椿等4人与杜国计持诏再次下谕命令陈日烜来朝,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安南国进贡“代身金人”由此开始。元廷与东亚国家的外交是建立在战争之上的官方政治交往。代身金人的作用是政治代表,其作用是维护中国与安南国的政治关系。
(二)花驴
元朝曹伯启的《汉泉曹文贞公诗集》中有这样一组诗,题目是《海夷贡花驴过兰溪书所见》,这一组诗中的两联如下:“天地精英及海隅,兽毛文彩号花驴。同来使者如乌鬼,还责中原礼法疏。”元朝末年王冕有一首诗题为《花驴儿》,其在序中提到:“杭州有回回人,牧花驴儿,能解人意,能识回回人语。”这两首诗对“花驴”的描写不尽相同,第一首诗可以看出“花驴”是朝贡方物,第二首诗中“花驴”是回回人用于杂耍的“工具”。由此可见,元代朝贡方物中“花驴”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同时扮演着不同的身份作用。
这里提到的花驴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斑马,由于斑马形似驴,又身带花纹,所以元朝人成为“花驴”,也曾被称为奇兽。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十二月,是岁,马八儿国进花驴二。[1]271《元史·外夷篇》记载,海外诸藩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1]3783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二月,达鲁花赤杨庭璧曾出使其国。其国今天的位置大致在印度半岛的东南面。马儿八国出现在《元史》中,说明斑马从元朝开始已经进入中国,并且受到元朝百姓的喜爱。
元朝曹伯启与王冕之“花驴”,前者是使者朝贡方物,后者是回回人进行杂耍的民间花驴。由于斑马的原产地是非洲,而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才到达非洲,因此元朝的“花驴”并非由非洲大陆直接朝贡而来的。所以“花驴”进入中国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由回回人从陆上丝绸之路带进中国,成为民间杂耍之物,发展到明朝成为“福禄”的象征;另外一条是由海上丝绸之路带进中国,由马八儿等国朝贡带入中国。
(三)象
元代儒生宋褧写过这样一首诗《过海子观浴象》:“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可见在元代“象”已经成为一种和谐的符号。元代历史上不仅有“贡象制度”,还有“帝王御用象舆”这种独特的交通工具。据《蒙古史纲要》记载,在元代的宫廷中,车舆是必备之物,除了架在四头大象背上的轿子(即象辇)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车舆。[12]76在陕西咸阳长武县博物馆收藏的《元末明初象舆人物图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象舆的原貌,为贡象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
向元廷进贡大象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其中包括占城、马八儿国、安南、缅国等。《元史》中提到,元初,既定占城、交趾、真辣,岁贡象。[1]1553在元朝鼎盛时期,进贡大象的数目有上百头。在大型的仪式场合,象舆的出现也成了一定的规制。
元朝对象的热衷是从忽必烈开始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乘象舆征乃颜。帝王选择“象舆”出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第一,象的体积庞大,可以展示帝王的威严。第二,忽必烈有足疾,不便骑马,此后形成了采用“象舆”出行的定制。[5]
元朝贡品中出现“象”这一庞大的动物,与当朝统治者的喜爱有很大的关系。“象”主要由域外国家朝贡而来,由于路途遥远,需要长途跋涉,因此跟随“象”一同进入皇家的是“驯象师”。随着元朝从兴盛到衰败的百年历史中,朝贡“象”的国家多次以“驯象师”不舍家乡为由拒绝元廷的象贡。象贡成为元朝兴衰的标志,象贡的数目随着元朝的衰亡而不断减少。
(四)玳瑁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蒙元帝国朝贡方物也是不同的,一般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朝贡,挑选当地最好的土产进行纳贡,朝贡方物中最多的就是珍贵饰品,其中包括不同种类的玛瑙、翡翠、珍珠等。这里选择珠宝中特殊的一种“玳瑁”进行介绍。
“玳瑁”俗称“海龟”,生活在海里,所以有此贡品的一般是东南亚临海的国家。玳瑁的龟板由13块组成,用硬物敲击龟背,使淤血充满龟板,再将其制成玳瑁制品。古人认为玳瑁制品戴在身上可以辟邪。玳瑁作为一种珠宝首饰在民间和宫廷都很受欢迎。据《元史·外夷篇》记载,元朝要求安南国从中统四年(1263年)开始,每3年进贡一次,可以挑选儒士、医生及通晓会占卜的人、各种工匠各3人,以及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绵、白瓷等物品。[1]3735
(五)贡女
元外交流史中,高丽的贡女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封贡礼制。其伴随着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双方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元朝与高丽国有130年的外交历史,在这段历史中,贡女制度对两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本质上来看,贡女制度是蒙元帝国强权外交的一种政治体现,同时也体现出高丽王国追求和平、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6]
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蒙古帝国同东真军联合出兵高丽,高丽与元朝的朝贡交往由此开始。在最初阶段,元廷向高丽索要岁贡主要是水獭皮、绸布、细苎、棉子、龙团墨、毛笔、紫草、荭花、蓝笋、朱红、雌黄、光漆、桐油等方物特产,并没有涉及到贡女。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元太宗遣兵大举进攻高丽,这是高丽第一次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入侵。元廷提出让高丽进贡童男童女的要求。这次入侵持续了28年,两个国家之间上演了侵略与反侵略惨烈的一幕。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贡女制度。[13]373
贡女制度的发展随着元朝的兴起而兴起,也随着元朝的衰落而衰落,200多年的贡女制度体现了民族压迫与反抗的精神,贡女制度的特点如下:第一,蒙元帝国把这一政策作为主要的政治手段,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贡女制度逐渐向和亲制度发展。第二,高丽向元廷进贡的贡女,不仅针对皇家政府,同时还有宗室藩王和贵族官僚。在元朝宫廷可以找到高丽女子的记载,在上层贵族家庭也有相关的记载。第三,贡女制度制度化的说法是由于元廷出现了专门管理贡女的一些机构比如“结婚都监”等。随着宫女制度的制度化,贡女的数量和规模与日攀升。第四,据《高丽史》和《高丽节史》记载,元朝时期贡女活动高达50次以上。由此可以看出贡女在元朝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高丽王国与蒙元帝国的后期,各个阶层的社会人士强烈要求废除贡女制度,所以在至元元年(1335年),高丽递交《请罢求童女疏》。同年,元廷同意禁止征选高丽女子进贡。随着蒙元帝国退出历史舞台,贡女制度也逐渐消失在历史中,但是贡女制度产生的影响在历史长河中不可磨灭。
三、元朝促进中外交流的基础条件
元朝的域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状态,这种前所未有的开放,与下面这几种因素有直接关系。
(一)元代朝廷的对外政策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朝代之一,元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域外交流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元朝的贸易发展,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设置相关官僚制度
元朝的官吏制度大体仿效宋朝的官吏制度体系,但是与宋朝明显不同的是元廷更加重视与域外国家交流官职的设置,比如中央机构中,户部设宝钞都提举司、礼部设侍仪司、会同馆,工部设诸色人匠总管府、织染提举司等。[3]元廷还在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州设立官吏,进行监管和督查,这也就形成了元朝独特的域外交流官僚服务系统。这样的官僚体系为元朝与域外诸国交流提供了诸多方便,官方的政策支持推动各个行业的往来。元朝的“域外政治政策”是元朝成为古代中国最开放朝代的一个典型证明。
2.减免相关税务政策
元朝为了鼓励商务贸易,在一些大都市降低税务标准。元廷开国以来,实行的是“百中取三”的税务政策。《元史》记载,商旅往来艰辛,特免其课。[1]1887元朝在宋朝贸易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重商”的政策,这些税务政策,刺激了更多国家的使者来到中国,与中国发展贸易。这使得“丝绸之路”的长途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巅峰状态。与此同时,元廷对待外来商人实行“减免赋役”的政策,因此欧洲很多商人远道而来,同时贸易的发展也推进了官方使者的相互往来。
3.货币制度
元朝出现的纸币是中国货币史上的重要发明。元朝的纸币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流通,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向前发展,也为域外交流提供了便利。元朝地域辽阔,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金属货币不能满足运输需要。因此,元廷开始印纸币。纸币的出现说明元朝的贸易相比其他朝代更加繁荣,其是元朝域外贸易全球化的催化剂。
在元代历史上,前后出现过5种不同的纸币,在缓解旧纸币贬值的过程中,新的纸币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是纸币的发行对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不容置疑的积极效果。元代纸钞基本具备了现代货币的一切职能。[3]元廷对域外来使的回赠中也出现了纸币,这说明域外诸国对元朝的纸币政策有极大的兴趣。并且承认“纸币”相当于“货币”,可以等价使用。货币制度的完善,也为域外国家出台相关“货币制度”提供了范本。
(二)陆上驿站制度
蒙古军队的铁蹄踏遍了亚欧大陆,不论是西征还是东征,其所到之地开路架桥,最大程度上改善了交通状况。据《蒙古秘史》《史集》等史料佐证,窝阔台时期驿站已经贯通欧亚大陆,远达波斯。[14]忽必烈时期,元朝就建立起从蒙古本部通往四大汗国的驿道,从山西忻州雁门关到别失,8里设置了几十个驿站。到元代中后期,全国的驿站数量已经达到1 500处。驿站附近每隔一段距离会打出水井,提供水源,为来往的商人、使者提供休息的场所。《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提到每个驿站都提供马匹、牲畜、粮食等物资。在长途跋涉过程中,驿站的出现为行人和使者提供了便利,由此衍生出于驿站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范,这也成为元朝域外交往的特点。
还有一些驿站还提供储蓄业务,商人可以将物品或者钱财储存在驿站,需要时再来取回。“储蓄业务”需要储蓄双方的信任,可见随着贸易业的发展,商业行业规范也在元朝得到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元朝政府还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商业贸易的发展,比如《市舶则法》等。
(三)海上“驿站”
元朝与海外诸国建立了朝贡体系,遥远的海上路途,元朝运用了海上“驿站”的办法。元朝政府把距离比较近的国家作为海上“驿站”。通过这些驿站,与更遥远的国家交流。据《元史》记载,高丽国就是日本等国家的交流传播中心。除此之外,印度也是中西海上交通线的中继站,从俱兰到伊利汗国的航线为元朝人所用。这样的“海上驿站”在减少了人力物力的同时,还可以联系到更多的国家,但是由于出现了作为中间传话筒身份的第三国家,也加大了中途断交的风险。
这一时期,中国海船的造船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马可波罗游记》这样记载,“各有船房五六十所,商人皆处其中,颇觉宽舒”,“有二厚板叠加其上,然后用麻及树油渗合涂壁,使之绝不透水”“海船舶上至少应有水手二百人,盖船甚广大,足载胡椒五六千担”[10]113。这说明当时造船舶的技术已经相当先进,这也为海上的商业和对外交流提供了便利。发达的造船技术和“海上驿站”为元朝和海外国家交往提供了技术支持。
(四)商事法律制度
元朝针对商业、贸易、手工业等不同的行业制定了不同的法律法规,不但保障了各行业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同时规范了市场秩序,刺激了外来商人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元代的法律比较完善和细致,其法律法规主要是《元典章》《通制条格》等。
元朝对商品的质量、大小、规格以及数量进行统一规定,出台相关的政策。一些质量优良、设计精美的手工艺品和商业产品会经过丝绸之路进入域外各国的皇家贵族上层社会,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用品。元朝忽必烈规定,民间所卖布帛有狭短者,禁止。[1]51元朝出台一系列政策保护由“丝绸之路”而来的使者与商人,不仅使得其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同时也保护了使者和商人的财产。在关口和渡口以及驿站驻兵把守,设置专门的官吏来管辖外来人员等。
(五)护照制度
元代朝廷在“海上驿站”和“陆上驿站”设立了一种特殊的“护照制度”,称之为“牌符制度”。方便官吏的管理和加强安全检查。“护照制度”的制定为元朝的域外交流提供了人身和财务安全保障。根据不同“牌符”的材质判断域外使者的身份等级。如果外国使者想要使用驿站,需要拿出相应的“牌符”,其作用与护照类似。这些“牌符”的材质有金、银、玉、木等,代表不同的国别和身份。护照制度有利于保障驿站地区的安全,对官方外交和商人贸易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四、结语
元朝的国际交流开放程度达到了历史空前水平,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面积最大的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范围和程度都超越了前朝,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杉山正明指出,蒙元时期的重商传统和自由贸易政策是欧亚统一市场形成的重要条件。[15]248
元朝的开放是在战争的基础上的开放,其开放的方式相对不平等。元朝的开放是蒙昧的开放,元廷采用了强有力的外交手段,所以元朝的朝贡体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中官方的朝贡体系并不弱于商业贸易体系。因此,元朝的域外交流的影响也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从元朝自身的角度来看,继往开来,承接唐代以来对外开放的制度和贸易,又为明代域外交流提供了可靠的蓝本。其将古代的对外开放规模推向了高潮。另一方面是从国际角度来看,元朝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交流提供了制度、技术的支持,在制度上,规范了对外交流的法律意识。驿站提供的便利条件,为来往的行人提供了粮草补给和保障。在技术上,制造船舶技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为后代的造船业提供技术支持。
与元廷有过联系的国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北欧国家,这些国家大都比较遥远,没有与元朝进行过直接战争,所以元廷与其的交流大多数是宗教和商业贸易。《马可波罗纪行》《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伊本白图泰游记》等游记,大量的篇幅都在记载商业贸易。由此可见北欧国家与元廷的外交大多以商业为目的。第二类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大多与元廷进行过直接战争,这也促进东南亚国家与元廷形成一种朝贡体系,《安南纪行》《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等游记,记载了对元廷的朝贡方物。尽管两类交流的方式不相同,但是就全球范围的国际交流而言,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外交方式都是不同程度的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互鉴。
总之,从文明互融的角度看待元朝的朝贡制度,其不仅为当前全球化的经济文化等提供了蓝本,同时将对当今世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合作提供可借鉴的宝贵依据。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