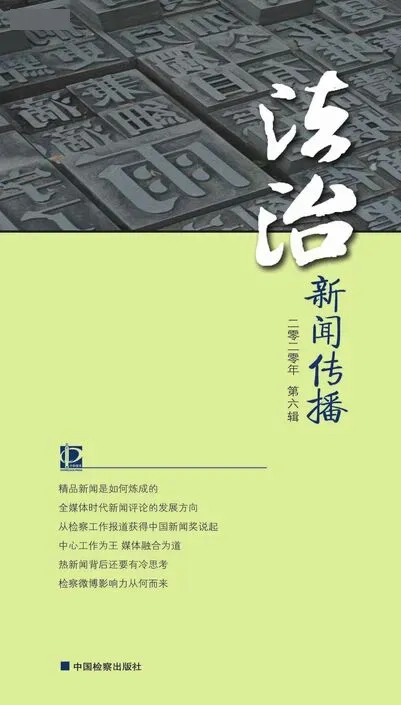刑事案件报道十大风险点
■张 羽
2020 年8月,广西一女子被前夫杀害后埋尸化粪池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不少媒体对案情细节进行报道,有的刻意渲染凶杀案细节,并配有大量图片,一些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转发时把血腥、凶残的作案细节作为卖点吸引眼球。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今年7 月“杭州女子失踪案”中,被某些媒体大肆渲染的细节正是“丈夫将妻子杀害并分尸扔在化粪池中”这一细节,甚至有不良媒体使用“化粪池警告”这种标签化词汇,造成恶劣影响。
刑事案件通常情节曲折离奇,相关新闻报道关注度较高,然而亦是一片雷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引发网络舆情。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2019 年11 月7 日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明确要求,要“维护司法尊严,依法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不渲染凶杀、暴力、色情等”。
这种原则性的要求如何落实?对于一起刑事案件,哪些该报、哪些不报,哪些详报、哪些略报,哪些不仅要报而且报后还需解读?笔者在此梳理了刑事案件报道中的十个风险点。
1.过度详细描述犯罪手段,渲染血腥、色情等犯罪场面
风险点:引起读者心理不适,制造社会恐慌,极易引发犯罪模仿效应。
提示:广西女子失联案件①报道中,涉及凶手藏尸衣柜、抛尸化粪池的具体犯罪过程的详细描述;陕西幼童遭父亲抱摔死亡的案件②报道,亦有现场视频流出,清晰还原犯罪嫌疑人残暴摔死幼童全过程,尽管一些媒体发布时已将画面进行打码处理,但仍令人觉得恐怖。
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曾多次拒绝媒体对刑事个案的采访,原因是“不想从客观上扩大他希望达到的恐怖效果”。她指出,犯罪目的、作案手法都是“可学”的,因此,这种案件的报道不应细化,作案动机、作案手段等都不要深挖细说,否则,不但客观上帮罪犯扩大了影响,还会在社会上造成恐慌。
2.报道正在侦查中的案件细节
风险点:暴露侦查手段,泄露缉捕策略。
提示: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一书中记叙了一个典型案例——2000 年湖南常德发生张君特大系列杀人案,杀死28 人,重伤20 人。警方抓捕时,数十家媒体聚集,报道了大量案件抓捕细节。到案后,据张君交代,他外逃时就带两件东西,一是手枪,二是报纸,发现追捕者就杀人,通过看新闻确定逃向,从而顺利跳出包围圈。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报道正在侦破中的刑事案件风险极大。如不加选择地披露案件细节,会给犯罪分子逃跑、藏匿造成可乘之机。如今,媒体行业对处于不同刑事诉讼阶段的案件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原则,即正在侦查中的案件一般不报;影响较大、必须报道的,经案件侦查部门及其上级机关审核同意后可先发程序性消息,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待案件审理终结后,再作详细报道。
3.负面报道过度集中,给刑事案件贴标签
风险点:引发读者恐慌情绪,甚至引发犯罪模仿。
提示:虽然还没有证据证明“杭州女子失踪案”③和“广西女子失踪案”存在关联,但两者相似的犯罪手法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个别媒体为追求点击率,喜欢使用“贴标签”的手法,诸如“化粪池警告”“最危险的枕边人”等标签化行为,加剧社会焦虑情绪,甚至可能引发犯罪模仿,需要引起媒体行业的警惕。
4.报道自杀事件,要注意正面导向
风险点:容易引发更多的自杀事件。
提示:早在1974 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平均每一桩成为头条新闻的自杀事件都与其他至少58 宗自杀事件相关。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上著名的“维特效应”(得名于《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致的自杀模仿)。有资料统计,1 例自杀死亡可使6 个人受到严重影响,1 例自杀未遂可使2 个人受到严重影响,自杀死亡给他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持续10年,自杀未遂持续6个月。
那么,在现代媒体广泛传播的情况下,自杀案件是不是不能报道了?关键在于解读角度。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安内堡公共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心理治疗中心等几家组织牵头,给出了一套自杀报道原则,一方面,如果媒体报道里详细描述了自杀方式,或者使用戏剧性的标题或者图片,或者反复广泛报道自杀事件并将死亡描绘成壮烈或轰动的事件,都会引发更多的自杀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媒体谨慎报道自杀,哪怕是很简短的报道,都有助于改变公众偏见和认识误区,能够鼓励有自杀风险的人群寻求正面帮助。
5.描写办案人“反常识”“反人情”
风险点:把司法办案简单化、庸俗化,造成“低级红”“高级黑”。
提示:“低级红”“高级黑”是近年来新闻界努力批判的现象,但依然屡有发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党建》杂志曾列举例子,比如黑龙江省某法院在网上发文称“默然姐姐,28 天连续加班,没换过衣服,没洗过头,在执行局干警的心中,她就是女神、女超人”,看似颂扬敬业精神,却是违背人情常理的“低级红”。
刑事案件报道中,为了突出办案检察官,也会出现个别类似用力过猛、适得其反的现象。应注意办案细节不能靠“想象”,为了凸显“高大上”而编造细节;编辑也应在后期把好关,看到人物描写,多想想细节是否合情合理。
6.过度披露案件以及相关涉案人员的个人信息
风险点:泄露个人隐私,引发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纠纷。
提示:新闻报道是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行为,而隐私权、名誉权则是归属于个人或者法人的权利。在案件报道中,二者很容易发生冲突。例如曾有一篇题为《沈阳一强奸猥亵女生的教师一审被判死刑》的报道,就因详细披露了被告人作案的具体单位和具体时间而引发争议,原因是读者很容易从中猜测被害女生的范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我们在刑事案件报道中,采编人员通常会因为同情心理更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但特别容易忽视对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利保护。例如在很多案件中,媒体将加工丑化的嫌疑人头像大幅刊登。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公布过名誉权纠纷裁判规则22条与22个典型案例,④其中不乏媒体侵权的身影。
7.在法庭判决前,做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
风险点:容易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程序。
提示:无罪推定、罪刑法定,是刑事诉讼法确定的重要现代司法原则,任何人非经法定程序被法院判决前,都是无罪的人,要避免报道中“提前审判”。譬如在未经审判终结的案件中要使用“犯罪嫌疑人”,不能使用“罪犯”或者“嫌犯”。在具体的案件报道中,一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如“罪大恶极”“穷凶极恶”或者恶意丑化嫌疑人、被告人的词语,建议少用或者不用;对于定性定罪有争议的案件,建议不报或者做正反双方的客观平衡性报道。
8.涉及少数民族、未成年人、残障人士、孕妇、进城务工人员等特殊群体,要谨慎报道
风险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提示:刑事案件报道之所以受众多、有“卖点”,是因为其具备一定的猎奇性,如果案件当事人是少数民族、未成年人、残障人士、孕妇、进城务工人员等特殊群体,就更加容易博人眼球。然而,如果把握不好报道的尺度,易招来社会舆论反感,甚至进一步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
9.乱用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照片、视频
风险点:极易引发青少年犯罪模仿效应。
提示:近年来社交媒体迅猛发展,表达方式更多样化,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都得到飞跃。新媒体案件报道为了吸引流量,经常大量使用现场图片、监控视频、庭审直播以及个人社交网络信息,就很容易走入泄露隐私的“雷区”。前文提到的“广西女子失踪案”和“陕西幼童遭父亲抱摔死亡”都有“无码”图片视频流出,不仅渲染了暴力,还极容易对喜欢看社交媒体但缺乏足够判断能力的青少年产生诱导作用。
10.重细节描写,轻司法解读
风险点:疏于对社会讨论进行正面引导,引发法治误读。
提示:部分媒体对于某一类型案件的过度关注,大尺度地挖掘犯罪过程,但缺乏释法说理,缺乏从法理上对案件进行深入剖析,易引发受众的猜测与遐想,形成“拟态环境”,不利于法治社会理念的引领与治理。
刑事案件报道归根结底就是写案(案情)和写人。案件细节是引发读者兴趣、让检察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手段,要以生动、鲜活的笔法用好这个手段,但不能“不择手段”,导致读者只把目光过度聚焦在那些江湖恩怨、百姓情仇上,而是要让读者感受司法的温暖和公平正义的阳光。写案,重在说法释理,正面引导社会公众行为,体现法治意义;写人,重在体现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为推动社会法治进步所付出的努力。所以,我们采编的每一篇刑事案件报道都要“一看二想三思考”,想一想是否有利于案件顺利侦破、是否有利于社会治安稳定,避开雷区,规范行文。
注释:
①《细节曝光!玉林男子杀害前妻后埋尸化粪池,还转走她15 万元去旅游》,https://society.huanqiu.com/article/3zcF7qgt246。
②《心碎!遭父亲抱摔2 岁半男童,没救过来……》,https://kuaibao.qq.com/s/20200821A0M85D00?refer=spider_push。
③《警方通报:杭州失踪女子被丈夫杀害分尸并扔至化粪池内》,http://news.haiwainet.cn/n/2020/0725/c3541083-31842658.html?baike。
④《最高法院:名誉权纠纷裁判规则22 条》,https://www.sohu.com/a/330030047_12002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