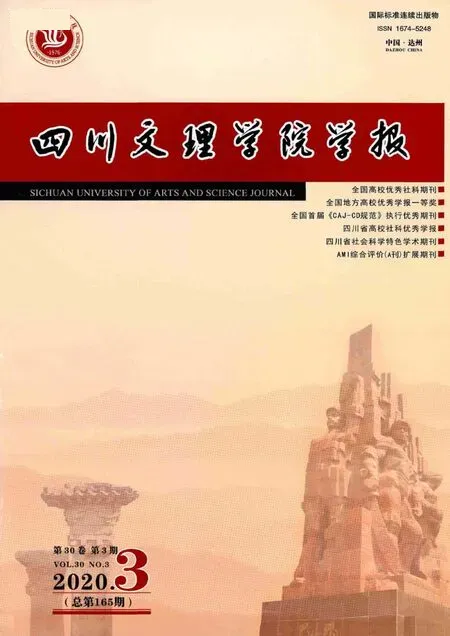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对李白的考辨
郑 慧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 成都610031)
胡应麟,字元瑞,号少室山人,明代著名学者、批评家,有诗论专著《诗薮》,诗文集《少室山房集》,论学专著《少室山房笔丛》。其《少室山房笔丛》包括《经籍会通》《丹铅新录》《九流绪论》等十二种,是胡应麟学术笔记之合集,也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其中,关于李白的条目有十六条,集中在《丹铅新录》及《艺林学山》,主要是针对杨慎对李白考据的辨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对李白的考辨,涉及李白身世、李白诗歌用事、李杜关系评价、李白词辨伪等几个方面,可以窥见胡应麟对李白的相关评论。
一、对李白身世的考证
关于李白的身世,历来有许多争议,主要有蜀郡说、山东说、陇西说、碎叶说等。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关于李白的评论中,就有“李白出处”“东山李白”“李白题词”“李姓非一”这四条专论李白的身世。
首先,胡应麟对李白出处做了详细的考辨,并对各种说法进行了梳理,感叹关于李白身世的说法错综复杂,颇多争议:
“古今诗人出处未有如太白之难定者,以为山东者,《南部新书》也,《旧唐书》传也,元微之杜诗序也,晁氏《读书志》也;以为蜀郡人者,范传正碑也,《新唐书》也,刘全白墓碣也,魏万、李阳冰、曾子固太白集序也,《唐诗纪事》也,《彰明逸事》也。然余考之魏颢序,言白本陇西,父家于绵,身既生蜀,继以授篆于齐,育子于鲁云。阳冰序则言白本陇西成纪人,中叶非罪谪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遂指李树生伯阳,继亦言授篆于齐紫极宫云云。《新书》传则言白系武昭王孙,神龙初潜还广汉,遂为郡人,长客任城,与孔巢父等居徂徕山,号竹溪六逸云云。曾子固序则言白蜀郡人,出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游梁最久,复入齐鲁云云。”[1]89
胡应麟对诸多说法作了梳理、归纳与总结,包含了山东、蜀郡、陇西、碎叶说。在这几种说法中,持“蜀郡说”的代表就有杨慎。杨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明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杨慎对李白这位家乡先贤十分景仰,因此对李白的身世作了详尽的考辨,力证李白为蜀人。其主张“太白生于蜀之昌明县青莲乡”,[1]88即今天的四川江油县,并多次驳斥了“山东说”,认为“山东说”源于世人对杜诗的误解。他说“杜子美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东李白’。案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引杜诗为证,近于郢书燕说矣。”[1]89-90
胡应麟针对杨慎的说法和论据一一做了辨析。在“东山李白”条中,胡应麟引用陈晦伯《正杨》之考,首先就推翻了杨慎的论据“乐史序无此文,用修盖误忆不考”,[1]90说明杨慎记忆错误,疏略失考,此论据站不住脚,并由陈晦伯的考证进一步深入。陈晦伯认为“杜田注”关于山东李白事是伪作,胡应麟按此条线索考证到“杜田注”引自《彰明逸事》,又陈晦伯提到的《南部新书》源自魏万碑记载。胡应麟对魏万《序》及《彰明逸事》相关记载做了深入分析,最后认为《彰明逸事》记载来源于《唐诗纪事》,而《唐诗纪事》仅为资料汇编,并不严谨,其说法有穿凿附会之意,不可信之。因此胡应麟说:
“《彰明逸事》与杜田注中所引亡一不合,田盖援《逸事》以注杜诗,非本传正碣也。景庐、用修、晦伯三君俱似未考此。此文载计氏《唐诗纪事》,其传会之迹灼然,因父尉任城,白有词题厅事,遂传彰明令等诗;因杜‘匡山读书’之句,遂传大匡山;因白自序陇西,遂传以陇西院;因白自号青莲,遂传以清廉乡。考魏万、李华、李阳冰传,传正诸文无一合者,大抵白既生其地则流传付会,自应亡所不至,亡足讶也。”[1]91-92
在“李白题词”条中,胡应麟又辨析了杨慎批评《新唐书》关于“白为山东人”记载之误:
“《新书》白传首言白为凉武昭王孙,其先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巴西,白生于此,长隐岷山,苏颋为益州守异之,非以白为蜀人而何?李阳冰、范传正俱以白本陇西,生于蜀,《新书》盖博参之,杨不略考下文,谬哉。”[1]92
胡应麟认为,杨慎对《新唐书》的批评过于武断,并没有联系下文。而《新唐书》只是参考了诸多说法,与李阳冰、范传正以白本陇西,生于蜀的说法差不多。
总的来说,杨慎对于李白身世的基本看法是,李白生于蜀之彰明(今四川绵阳江油县),读书于匡山,并极力驳斥了“山东说”。
在“李白出处”条中,胡应麟也参考各种说法,对李白的身世作了一个总结概括:
“合诸说而订之,则《卮言》所谓白本陇西人,产于蜀,流寓山东,其说最完。而《纪事》末所谓或曰蜀、或曰齐、或曰陇,俱不为无据也。况白但生于蜀,一出后未常返其故居,陇西以其本宗,山东以其流寓,志白奚不宜者?用修欲专太白于其乡,凡诸方有据者一概没之,非通论也。”[1]89
胡应麟认为“白本陇西人,产于蜀,流寓山东”的说法最为妥当,并且认为杨慎带着个人好恶,“欲专太白于其乡”,对于其他说法的证据则不予采纳,有矫枉过正之嫌。笔者认为,胡应麟关于李白身世的看法较为完善和公允。一个“专”字,表达了胡应麟认为杨慎的评价带有个人情感,并不理性。又在“李姓非一”条中,胡应麟说“用修断以太白为蜀人,此乃据《自序书》而信其家室金陵之语”。[1]94一个“断”字,再一次强调了杨慎的武断。
有论者在评论杨慎对人物的考证疏漏时,说杨慎是“爱之过甚,辨之弥坚,难免有失偏颇。”[2]14笔者较为同意这一观点。杨慎对李白充满景仰,并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因此不遗余力地证明李白是家乡人,是蜀人。其情之切,而考证有所疏漏。胡应麟则客观地爬梳各种记载,条分缕析,证据充分,公允公正,可以看出胡应麟治学的严谨态度。
目前对李白身世的考证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根据魏颢《李翰林集序》、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以及李白自己的诗歌,认为李白的籍贯在陇西,但出生地在四川。四川是李白实际上的故乡。李白在蜀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在蜀中生活的二十几年,李白在故乡的大匡山读书,在蜀中游仙学道,并漫游了蜀中的名山大川,如“东游梓潼、盐亭一带”“南游成都”“北游剑门”“西游峨眉”,最后“由夔州离蜀出峡”。[2]25-27李白在蜀中也留下了许多诗文创作,并且其人其诗都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离开故乡后,无论走到哪里,李白都在怀念故乡,怀念巴蜀。可见,从心灵归属上,李白的故乡也在巴蜀。
二、对李白诗歌用事的考证
胡应麟对杨慎关于李白的考据辨析,还有考释李白诗中名物,对其用事及字词的校勘,如“素足女”“浣纱女”“禺山戏语”“弓足”“屏风牒”等。
“屏风牒”条,杨慎云“梁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十二牒,李白诗‘屏风九叠云锦张’,牒即‘叠’也”。胡应麟按曰“牒即案牒之‘牒’,子云所书意如今围屏十二扇者,以文翰故借牒为言耳。太白‘屏风九叠’自咏庐山,杨曲引以证。”[1]193
杨慎认为李白诗“屏风九叠云锦张”来源于梁萧子云“屏风牒”事。其事语出《南史·王远如传》,是指南北朝时期轻便灵巧的折叠屏风。“牒”也就是折叠的“叠”。但胡应麟却认为,萧子云所用的“牒”是案牒之“牒”,是借案牒来代指,而李白诗“屏风九叠云锦张”是咏庐山山峦重叠。胡应麟认为,萧子云之“牒”与李白之“叠”意思并不一样,是杨慎对于李白用事引证的曲解,是胡应麟对李白诗歌用事之来源的进一步辨析。
又如“素足女”条,杨慎认为李白诗“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来源于谢灵运《东阳道中》诗“可怜谁家妇,渌流洗素足。……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说李白“全祖之而注不知引”。[1]113
胡应麟案曰:
“谢、李之题素足又皆本陶“原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也。即此知晋、唐妇人不缠足无疑。夫足素则不纤,纤则不素,未有既缠之足灌诸渌流者也。昔题妇人足,不曰素洁则曰丰妍,(“丰趺皓春锦,足趺如春妍”是也。)夫今妇人缠足,美观则可,其体质干枯,腥秽特甚,使谢、李辈舍其弓纤而诬以洁素,一何舛哉。”[1]113
对于李白诗歌用事,胡应麟认为,李白“素足”之用事来源于陶渊明《闲情赋》,并不是来源于谢灵运,晋朝、唐初妇女是没有缠足的,这一习俗始于唐末、五代,并对妇女缠足这件事提出了看法,说妇女缠足“体质干枯,腥秽特甚”,可见胡应麟并不认同妇女缠足这一做法。
另有“浣纱女”“禺山戏语”条,同样是讨论李白诗“素足”之用事。这几则材料既是对李白诗歌用事的考证,也是对于缠足起源的考证。在“双行缠”条中,杨慎举六朝乐府诗《双行缠》“新罗绣行缠,足跌如春研。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以及杜牧诗、《花间集》等诗词,认为缠足这一习俗起源于六朝。
胡应麟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一是对杨慎的证据“行缠”作了不同的解释“乐府‘双行缠’,盖妇人以衬袜中者,即今俗谈裹脚也。唐以前妇人未知札足,势必用此,与男子同。”“唐以前妇人足与男子无异,则足之服制可见”[1]111胡应麟认为“行缠”当时指衬袜,并非专指妇女缠足,在当时是男女通用的,没有什么区别;二是对《太平御览》等诸多记载和证据进行了考证;三是在“浣纱女”条中,引用李白“一双金履齿,两足白如霜”“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等诗,表现李白对素足的审美,以此质疑杨慎关于缠足起源于“六朝”之说。在“禺山戏语”条中,胡应麟认为杨慎对李白素足女的引用存在误解,就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考察唐初妇女并没有缠足的社会背景。“杨两引太白素足女诗而讶其回盼,张又有野花邨酒、金莲玉弓之说,盖皆未悉唐初女子不缠足故也。”[1]114
因此,胡应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书籍之雕版,妇人之缠足,皆唐末五代始之,盛于宋,极于元,而又极盛于今。”[1]114后世对于缠足的起源大多采用五代之说。胡应麟认为,杨慎对于李白诗歌用事存在误解,正是由于没有弄清楚缠足起源这一历史背景。
杨慎评论李白诗歌,注重讨论其源流与发展。由这几则材料可以看出,杨慎认为李白诗歌很多用事是对六朝诗歌的承继。将李白诗放在诗歌发展的源流中,这是杨慎对于六朝唐诗观很有见地的观点。不过杨慎的引证有时候存在“疏略失考,论断轻率”[3]120的情况,因此胡应麟根据杨慎的评论,进一步探讨了李白诗歌的源流,指出了杨慎考据的疏漏。
三、评李杜关系
李杜比较,也是颇具争议的问题。胡应麟在诗论著作《诗薮》中,对李白与杜甫颇多评论,并探讨了李杜诗歌的比较,总体态度是李杜并尊,不相伯仲,不可以优劣论。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胡应麟针对杨慎的考辨同样涉及李杜比较,可作为其《诗薮》关于李杜评价的补充,主要有“太白子厚”“江陵”“评李杜”“锦城丝管”等几条材料。
在“太白子厚”条中,杨慎说“杜诗语及太白处无虑十数篇,而太白未尝假借子美一二语,以此知子美倾倒太白至难。”[1]192胡应麟驳斥说 :“考子美不但虚心太白,即高、岑辈无所不倾倒,然二子诗推毂杜者亦无几,遂谓子美出高、岑下,可乎?文人相轻,尚矣。子美揖让诸公,正其卓尔难及处,后世鹜奇之士遂为口实,奈何!”[1]192
胡应麟认为杨慎此说有失偏颇,有文人相轻之嫌,并举杜甫同样欣赏高适、岑参为例,反驳了杨慎以此论李杜优劣的逻辑。并且胡应麟进一步说杜甫敬重同时代的名家,正是杜甫难得的胸襟与坦荡,却被猎奇的人曲解了。
在“江陵”条中,杨慎云:
“杜子美诗‘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扁舟已过万重山’,雕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前,此语太愦愦。”[1]194
胡应麟驳斥云:
“太白《岳阳楼》诗云:‘楼观岳阳尽,川回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右李作亦五言律,视杜吴楚东南、乾坤日夜等句何如?无论二公敌国,即李之凤凰何如崔颢、杜之五夜何如王维耶?二公制作,他不必多论,止据自相酬和之篇。杜赠李二十部,真可惊风雨、泣鬼神,而李‘饭颗山头’四语殊近鄙猥,岂止两岸猿声、江陵白帝之相去哉。然以此定李、杜优劣、诚坐井窥天也。”[1]194
杨慎此说有扬李抑杜倾向。胡应麟认为这两句根本不可比,并用杨慎同样的方法,举了李白、杜甫《岳阳楼》诗,用来质疑杨慎。又举二者相互酬唱之诗为例,说明杨慎用这样的方法定优劣的做法是“坐井观天”。同样的评论,在胡应麟《诗薮》中叙述得更为详细:
“古大家有齐名合德者,必欲究竟,当熟读二家全集,洞悉根源,彻见底里,然后虚心易气,各举所长,乃可定其优劣。若偏重一隅,便非论笃。况以甲所独工,形乙所不经意,何异寸木岑楼、钩金舆羽哉。正如‘朝辞白帝’,乃太白绝句中之绝出者,而杨用修举杜歌行中语以当之。然则《秋兴》八篇,求之李集,可尽得乎?他日又举薛涛绝句,谓李白亦当叩首,则杜在李下,李又在薛下矣。甚矣可笑也。”[4]
胡应麟认为,对于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不能“偏重一隅”,而应“各举所长”,并举《秋兴》八首等诗为例,用逻辑关系驳斥了像杨慎那样用杜甫歌行与李白绝句定优劣的做法是很可笑的。所以这也可以看出胡应麟对李杜评价的基本态度,认为李杜各有擅长,不可以优劣论。
在“评李杜”条中,杨慎认为“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大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1]195杨慎认识到李白、杜甫诗歌风格不同,但仍然对李白更为偏袒。胡应麟评价说“二杨语皆为李左袒者也”[1]195。又在“锦城丝管”条中,胡应麟评论了杨慎引用高廷礼《唐诗品汇》评杜甫七言绝之事,认为二者扬李抑杜,但“二君书必皆传于后世,读者当自有公论也。”[1]192
总之,杨慎在部分诗论中,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不够客观理性,有扬李抑杜的倾向。这与他考证李白身世时的态度有相同之处,都存在“评论太过,有失公允”[3]122的情况。因此有论者在评论杨慎对人物的评论中说“在评论人物时,杨慎有时夹杂着个人感情和好恶,这就导致他的某些评论缺乏公允,甚至失之偏颇。”[3]108胡应麟李杜并尊,在其诗歌理论著作《诗薮》中,从李杜整体成就、李杜诗歌风格等方面探讨了李白、杜甫有各自擅长的领域,不能够评价优劣,反映了胡应麟李杜并尊的观点及公正客观的诗论态度。
四、对李白词的辨伪
胡应麟对李白的考辨,还表现在对李白词的辨伪,集中在《艺林学山》及《庄岳委谈》中,重点对李白词《菩萨蛮》《清平乐》进行了考证分析。他是较早对李白词的真伪提出质疑的学者。
首先,在《艺林学山》“草堂”条中,胡应麟对杨慎《词品》中关于《草堂诗余》之命名的解释提出质疑。《草堂诗余》是南宋人编纂的一部词选,明清两代,非常流行但褒贬不一。杨慎《词品》认为其名称来源于李白。“昔宋人选填词曰《草堂诗余》。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见郑樵书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余’者,《忆秦娥》《菩萨蛮》二首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1]210胡应麟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此用修《词品》中第一误处。蜀草堂始自子美,李于杜年行俱先,讵肯以其草堂名集?盖杨以李为蜀人,故传会其说,靡所不至。夫《草堂》所选太白止二首,余尝疑非其作,余率宋人之制,安得尽系于李之草堂哉?”[1]210
胡应麟认为,将《草堂诗余》之名和李白相联系,显得有些牵强。一是“草堂”与其说与李白有关,不如说与杜甫有关,与杜甫草堂有关;二是《草堂诗余》只选了李白两首词,这两首还被认为是伪作。因此,杨慎将二者相联系,同他考证李白的出身地和评价李白的态度是一样的。杨慎对李白的景仰“靡所不至”,因此带有个人感情,不够客观。
胡应麟继续在《艺林学山》“草堂”“词名多取诗句”以及《庄岳委谈下》中,详细考证了李白《菩萨蛮》为伪作:
“今诗余名《望江南》外,《菩萨蛮》《忆秦娥》最称古,以草堂二词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学士,或以实然。余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即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衰飒,于太白飘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评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若怀素草书、李赤姑熟耳。原二词嫁名太白有故。《草堂词》宋末人编,青莲诗集亦称《草堂集》,后世以二词出唐人而无名氏,故伪题太白以冠斯编也。”
“《菩萨蛮》之名,当起于晚唐世。案《杜阳杂编》云:‘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娼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亦载此事。则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题,何得预制其曲耶?”[1]423-424
胡应麟从不同方面详细辨析了李白《菩萨蛮》为伪作。一是从风格上来说,这首词“虽工丽而气衰飒”,与李白飘逸的风格并不符合,且胡应麟认为李白以风雅自任,不屑于作这样的词;二是从词的意境上,胡应麟认为更像是晚唐风气;三是后世误将《草堂词》和李白《草堂集》混淆,而伪题李白;四是考证《菩萨蛮》这一词牌,应起源于晚唐。李白的时代还没有这一曲牌。在《艺林学山》中,胡应麟对这一证据有多次表达。总之,胡应麟从内容、意境、以及词牌的考证几个方面辨析了李白《菩萨蛮》为伪作。
最后,在《艺林学山》“上江虹”条以及《庄岳委谈》中,胡应麟还对李白《清平乐》提出了质疑:
“古今乐府多有同名曲异者,如唐人《清平调》与宋人《清平乐》,迥不同,太白《清平乐》,盖五代人伪作。因李有《清平调》,故赝作此词传之。”[1]211
“杨用修《词品》又有《清平乐》词二阙,尤浅俚,俱赝作也。”[1]424
胡应麟同样从词牌及内容上认为《清平乐》为伪作。从词牌上看,后人误将唐人《清平调》与宋人《清平乐》混淆,才“赝作此词”;从内容上看,胡应麟认为这两首词“尤浅俚”,不像李白的风格。
当代学者王辉斌等对李白这几首词还从版本学、文献学方面进行了考证,得出《菩萨蛮》《清平乐》等词非李白所作的结论。且王辉斌也提到“最早辨‘李白《菩萨蛮》’之伪且又甚力者,乃首推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5]
五、“正杨”与“正正杨”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虽然对杨慎的考据进行了辨析,指出了杨慎考据的失误,但其本人对杨慎其实是非常敬仰的。他在《丹铅新录引》中说“杨子用修拮据坟典,摘抉隐微,白首丹铅,厥功伟矣!”[1]53肯定了杨慎考据的贡献及作用,又在《艺林学山引》中说“余少癖用修书,求之未尽获,己稍稍获,又病未能悉窥。”[1]190表达了对杨慎的崇拜之情。可见胡应麟对杨慎的学问和人品甚是推重。因此,胡应麟辨析杨慎考据的疏漏错误,并非是文人相轻,这与当时文坛“正杨”与“正正杨”的学术讨论有关。
杨慎作为明代文坛大家,其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丹铅诸录”,由于考证驳杂,不免有所疏漏,于是学界掀起了一股针对杨慎考据再考证的辩论之风。从陈晦伯《正杨》开始,又有胡应麟《笔丛》继之,还有王世贞等诸多学界名人,都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是为“正杨”与“正正杨”。这场争论,并不是简单的文人相轻,而是对学术的求真求实,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也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很多具体的问题在讨论中越辩越明,比如本文提到的关于李白身世的考证、关于李白词的辨伪等问题。胡应麟对于李白的考据逻辑严密,证据充分,客观公正。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针对杨慎对李白考据的讨论,我们可以窥见胡应麟扎实的考据对当时学界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以从“正杨”与“正正杨”的讨论看出明代学术思想的活跃,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李杜优劣之争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