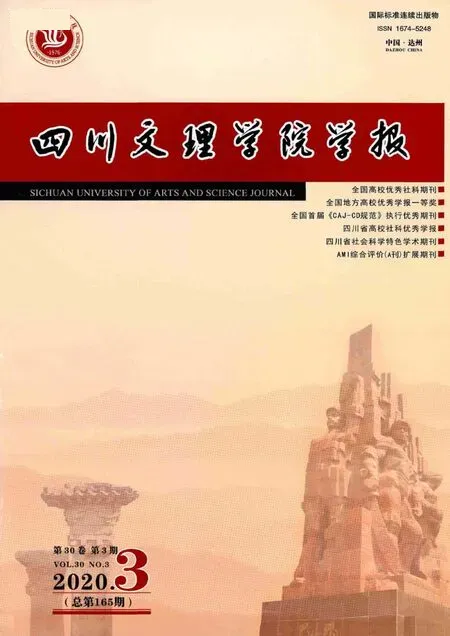中华文明第二期与禅宗美学的生命智慧
——关于中国美学精神的札记一则
潘知常
(南京大学 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00)
一、中国“无宗教而有信仰”的思考
信仰的建构,在古老的中国,既引人瞩目又道路坎坷。尤其是禅宗的思考,更是与众不同。也因此,在研究禅宗与美学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时候,由于事关对于禅宗的思考的特定语境的准确把握,无疑,也就尤其重要。
当然,十分引人瞩目的是,最初的中国,信仰建构就已经与西方世界殊异,不是“因宗教而有信仰”,而是“无宗教而有信仰”,成为古老中国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曾以“天”为宗。
众所周知,在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唯有中华文明始终没有灭绝,也因此,我们一般都把中华文明称之为:“连续性的文明”,并且因此而区别于其它的“断裂性的文明”,可是,为什么会如此?无可置疑,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巨大的向心力。或者,置身其中的中华民族一定默认着某种价值、某一安身立命之处,这就类似于西方的绝对价值、终极关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西方民族必须回答,中华民族也必须回答。也因此,不难想象,在历经沧桑的古老中国的背后,也一定还存在着一个价值的“中国”,一个“中国的中国”。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中国之所以始终屹立于世界东方,一定也是有其道理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所谈论的中国,其实并不是完整的中国,而只是真实的中国的二分之一——此外还有四个地区,却很少涉及,它们是:西藏(含青海的部分)、新疆(含甘肃的部分)、内蒙古、东北。必须提示的是,在这四个地方,都是很少见到孔庙的。而且,我们过去所谈论的中国的统治者,也不是全部的中国的统治者,而且也只是真实的中国的统治者的二分之一。须知,在中国,起码有一半以上的统治者都是来自北方族群(包括隋唐的统治者)。换言之,中国之为中国,地点并不限于内地,统治者也还有一半以上来自北方族群。何况,在中国的朝代中还有着元朝与清朝的客观存在。那么,它们是怎么凝聚起来的?又是怎样集中在了中华文明的大旗之下的呢?
例如,在中国,人们最为熟悉的,莫过于“逐鹿中原”。“中原”,似乎就是中国的麦加、中国的圣地。而所谓“中原”,我们知道,最早应该是从洛阳开始,当时,洛阳就被称之为天下之中。著名的何尊上有一句铭文:“宅兹中国”。其中的“中国”,就是指的洛阳。最早的中国,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显然,这里的“中”,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神圣范畴,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神性建构。正是因此,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也使得中国的诸多民族都没有例外地、也都孜孜以求地渴望融入中原。
显然,融入中原,也就是融入中国故事、中国叙事,这“融入”,会使得执政成本大大降低,也使得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强。这意味着,正是在中原,才蕴藏着极为优质的精神资源,也才存在着一双神奇的“看不见的手”。它是中华民族最为内在的向心力、最为强大的凝聚力,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无穷复制的文化基因,更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得以世世代代连绵不绝的核心秘密。
换言之,“中原”之所以值得“逐鹿”,是因为它有着自己的牢不可破的信仰。不过,与西方不同,它不是通过“上帝”来呈现的,而是通过“天”来呈现的。或者说,在西方,是以“上帝”为宗;而在中国,则是以“天”为宗。“天“,就是中国人的信仰。
然而,严格而论,中国的“以天为宗”却又很难被称之为宗教。因此,对于“天”的敬仰,确实很难被称之为宗教,但是,必须强调的却是,与众多的因此而导致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否定性评价不同的是,我仍旧坚持认为:“天”,却毕竟是一种信仰。正是它的存在,才导致了“德‘的向前向上,导致了”德“的不断提升。而且,”天“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无宗教而有信仰“的特色的形成。
托克维尔特别注重于去考察不同民族的“摇篮时期”,他认为:“摇篮时期”昭示着“一些民族何以被一种似乎不可知的力量推向他们本身也未曾料到的结局。”[1]在我看来,中国也如此,与世界其它几大文明不同,中国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有宗教地进入文明社会,而是君权“天”授,也就是没有宗教地进入文明社会。
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在信仰建构路径上的另辟蹊径,以儒家为例,一般认为,在孔子之后,儒学的拓展可以分为两大不同的取向。一个是走向理性,以《大学》和荀子为代表,一直到宋代的程朱理学,最终被推向了极致,另一个是走向宗教,以《中庸》《易传》为代表。或者认为,倘若以孔孟儒学为第一期,则第二期的儒学应该是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秦汉儒学,突出的是儒教的“外王”,关涉的也是公德层面,可以以子贡、子张、子夏、荀子、董仲舒、陈亮、叶适、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陈寅恪先生曾云:“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2]就是对第二期儒学的肯定。第三期的儒学,是以心性为本体框架的宋明儒学,突出的是“内圣”,关涉的则是私德层面,可以以颜回、曾参、程朱陆王为代表。然而,无论如何,在这当中,在信仰建构的层面,儒家所做的探索,都无非是在以情感为纽带的社群意识基础上(这是出之于孔孟儒学的原创)的外向拓展,也就是走向了以“敬仰”为纽带的宇宙意识,这当然属于汉唐儒学的创新。人,生而不能离开社群,但是,同样的是,人,也生而不能离开自然。人在一出生就置身社群生活的同时,也在一出生就置身天地宇宙,不难想象,正是因此,顺理成章地,从秦汉开始,儒家的探索,在“社群”的基础上,又注意到了“天地宇宙”。对于置身自然生命并且在自然生命中生生不已、共同精进的期望,以及在敬畏与感恩中挺立主体价值,从天道以论人道,确实是在孔子、孟子那里都不曾思考和探索过的,也确实是儒学思考的新收获。然而,在不论是“社群意识”,还是“宇宙意识”,却都是出“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思考——“无宗教”,是其中的主旋律。
至于宗教,在古老的中国当然也不是没有,但是,却大多与信仰的建构毫无关系,而只是建立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的自然迷信。在其中,人的精神被自然奴役,人是不自由的,无意志无精神,被泯灭于自然,只知道自己是自然的,没有价值,更没有自由,以此,至多也只能被称之为初始阶段的多神教。土地爷、山神、河神、菩萨、狐仙、太上老君、关公,都可以请进神龛,只要能够带来好处,就都无可无不可。可是,也正是因为多神,诸神之间的权能也就都十分有限,而且彼此矛盾,以至于甚至诸神资深都自顾不暇,又怎么给人类以强大的鼓舞?原则的相对和功能的有限必然使得这类的宗教成为功利的宗教。而且,有的时候,是“信”或有之,“仰”却没有,有的时候,则是“仰”或有之,“信”却没有,还有的时候,则是既没有“信”也没有“仰”。无疑,这其实不能被称作“信仰”,而只能被称作“崇拜”。与此相应的是,既然如此灵活,那么,原则的力量、至高的力量自然也就荡然无存。
在此意义上,在中国,儒家又被称之为“儒教”,也就顺理成章了。显然,它区别于西方的“因宗教而有信仰”,它或许应该被称作“无宗教而有信仰”。
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无宗教而有信仰”的思考中,也存在着不足。
就以中国文化中的“天“为例,作为宗教,无疑并不成熟。因为“天”其实只是一种低于自由意识的自然意识。借助于黑格尔对于文艺复兴的批评,则是:在其中“单纯的主观性、单纯的人的自由,即他具有一个驱使他去做这件事或那件事的意志这件事,还没有构成正当的理由……即令意志具有了……符合理性的目的……这当中也依然只有那种可容许的因素”,而且,也“只是按照它的内容限于应用在特殊的对象范围之内。只有当这个原则被置于与那绝对地存在着的对象中,亦即置于对上帝的关系中来加以认识和承认……它才获得对它的最高认可。”[3]例如,当年天主教进入中国,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礼仪”之争。为什么会如此?就正是因为中国的祭天(还有祭祖、祭孔)。因为祭天(还有祭祖、祭孔),所以中国的儒教已经超出了(道德)哲学的范围,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性,但是,这里的祭天(还有祭祖、祭孔)又只能被称之为低级而又低级的宗教性。显然,这里的“天”毫无人格神的意思,只禀赋着道德性,不过,它的不足显然不在“宗教”程度不够,而在“信仰”程度不够。换言之,“天”的不足恰恰是因为:在其中精神始终都并没有意识到唯独自己才是主体,因此却转而将自己隶属于自然,误以为自己是被自然所规定、所决定的,一方面已经有所超越,也已经禀赋一定的精神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毕竟是此岸的,因此即便有意义,也仅仅是现世的意义。何况,加之自身的抽象程度毕竟还是不够高,因此也就只能凝结为一种道德伦理,例如“民本”“国家”“公天下”等等。可是,也因此,在其中,信仰的积极意义也就仍然是有限的。精神性质匮乏,自然意识凸出,导致了精神沉沦于自然,而且反而视自己为自然(如自然之天)。而在其中,精神却不是自由的,精神对于自然的自由态度更是不可能出现,而只有宿命态度。
至于在信仰中本应充盈着的“神性”和“精神性因素”,也因此而没有能够在关于“天”的思考中被成功地剥离而出。对此,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曾反复予以讨论。例如,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他指出:“中国的宗教可以称之为一种道德的宗教(在此意义上,人们可以把无神论归之于中国人)”[4]240“他自身中没有立足点”,“人自身没有内在的、一定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因此对他来说,一切外在者都是内在者;一切外在者对他来说都有意义”,“与他有关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力量。”[4]244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也指出:在中国,“主观性精神的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4]126在《历史哲学》中,他又指出:在中国,没有像西方的关于信仰的思考那样,“‘精神’退回到自身之内”的情况,中国“的宗旨只是简单的德性和行善”,在其中,“我们无从发见‘主观性’的因素”,“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很远。”[5]这也就是说,尽管它也被称之为信仰建构,但是却并不具备信仰之为信仰的根本内涵。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精神因素的不够突出。这就正如孟德斯鸠所观察到的:“礼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6]313“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6]279总之,在其中充盈着的,也还仅仅是自然性、实体性的内容。
我们知道,信仰之为信仰之所以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都不可或缺,完全就是因为,在其中,存在着的是人与理想、人与无限、人与未来的直接对应,也就是自由者与自由者的直接对应,它借助追问自由问题,殊死维护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无上权利、至尊责任这一唯一前提,个人的存在,在信仰维度而言,其实就应该是自由的存在。然而,这一切,在中国的“无宗教而有信仰”的思考中都还暂时并不成熟。它更多地强调的,还是人与动物的不同。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因此,人之为人,其实并不高于人,而只是高于常人。因此,只是“人圣”,而不是“神圣”,于是,也就不必去向绝对至善的理想、未来、无限敞开自己,更不必去以绝对至善的理想、未来、无限为标准来审判自己、忏悔自己,所谓“为仁由己”。而这也就必然遁入费正清等人提出的“既成事实就是合法性”。总之,既然具有某种超自然超现世的纯粹精神生活——独立和超越于自然意识和现世生活的精神生活在中国尚未出现,既然对超感性的、精神意义的东西尚且知之不多,既然对主观自由也尚且知之不多,那也就只好把“必须”当做“应当”。于是,种种与现实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功名利禄之类,还仍旧被作为了性命攸关的判断标准。人之为人,也不是马丁·路德所谓“内在的人”,而仍旧是“外在的人”,仅仅是“因行称义”“因言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于是,人之为人也仍旧是角色中、关系中的自己,而不是自由的自己、无角色、无关系的自己——哪怕是社群中的自己,也哪怕是宇宙中的自己。
二、“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于佛中”
幸而,中国的“无宗教而有信仰”的思考还并没有结束,而是在上述基础上继续地艰难展开。
在2005 年出版的《王国维:独上高楼》一书中,我曾经从“大文明观”的角度,中华文明的沧桑历程,在2132 年的古老中国,可以具体划分为两期。其中,中华文明第一期围绕着儒家思想展开。儒家思想初步解决了中华文明的根本困惑,以至于后人会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而道家思想则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但是,它的“天问”与“天对”毕竟只是围绕着中国本土思想展开的,也毕竟没有直面过中国文化以外的挑战。
而中国文化的与西天的佛教的对话,则是本土思想与非本土思想的第一次的对话,是中华文明第二期。
毋庸置疑,佛教进入中国,堪称中国文化的一大姻缘,不但成功地使得非宗教的中国思想有史以来第一次中断,而且成功地连接起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智慧。而作为对话的结晶,禅宗也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然而,尽管相对于儒家的“有”与道家的“无”,禅宗走向的是“空”,但是,“无宗教而有信仰”,却仍旧是它的共同特色。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第一期,已经成功地开启了“无宗教而有信仰”的中国特色的“到信仰之路”、“到自由之路”。但是,其中也确实困难重重。例如,因为不存在彼岸,因此就很难高扬某种超自然超现世的“精神性因素”,为信仰建构所必需的那种对于自由的固守与呵护,以及以超越本性、以无限、以未来为天命,乃至借助追问自由问题而殊死维护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无上权利、至尊责任这一唯一前提,也很难得以实现。人的存在更很难成为永远高出于自己的存在,永远是自己所是而不是自己之所不是的存在。
例如,所谓“灵魂”,亦即自由存在的精神世界,就很难被切实加以关注。这是因为,在中国,所有的真善美都没有完全放在彼岸的一边,所有的假恶丑也都没有完全放在此岸的一边,因此也就并没有被赋予一种绝对的、神圣的价值,于是,作为与彼岸相对的人也就没有被赋予一种不可让渡的绝对的、神圣的价值,而是仅仅往往被赋予了现实的“三不朽”而已,“灵魂不朽”与“灵魂救赎”,自然也就还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与此相应的,则是“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无疑,它们也绝对并非一无是处,尤其是在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它们的维护社会正义、凝聚社会正能量的历史贡献更是不容否定。然而,究其实质,却也不能不说,“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毕竟还没有完全进入信仰的语境,因此存在的只是“信念”,而不是“信仰”。而且,也不是对于自我意识的体验,而是对于外在世界的体验。在“他自身中就没有立足点”。[4]244“人自身就没有内在的、一定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因此对他来说,一切外在者都是内在者;一切外在者对他来说都有意义,都与他有关”。[4]245由此,作为统摄一切的终极价值的精神关怀、灵魂关怀也就迟迟未能到位。这样一来,既然人的自然本性可以“自然而然”或者“顺其自然”地生长为超越本性,那么,自然也就“人间即天堂”“人人皆尧舜”了。于是,精神的世界、灵魂的世界自然也就不会成为赎罪的炼狱、灵魂净化所、未来灵性生活的预修学堂乃至涤罪所,精神的自由和灵魂的得救更自然也就并不重要,最终,当然也就不是“灵魂救赎”而是“现实忧患”才会成为孜孜以求的目标。
然而,“无宗教而有信仰”毕竟只是“无宗教”,但是却绝对不是“无信仰”,因此,也就绝对不是对于精神的、灵魂的到信仰之路、到自由之路的否定。既然如此,那么“终极关怀”与“救赎意识”也就必然会成为必须。它意味着对于精神世界、灵魂世界的被污染、被玷污的孜孜以求,意味着从绝对至善的理想、未来、无限的高度(因此才被象征地称之为“彼岸”)地对于自身的重新发现。
在我看来,禅宗之为禅宗,其重大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相当长时间以来,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尽管已经意识到了儒家的立足于“有”乃至道家的立足于“无”,尽管都希望“物物而不物于物”,但是却毕竟始终粘滞于“物”,即便是继之的魏晋玄学,转而用人格理想取代道家的天之自然,堪称十分可喜的进步,却仍然未能彻底解决,仍然是无法做到“应物而不累”。到那时,我们也确实并没有说清楚其中的根本差异,也就是:从“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到“终极关怀”与“救赎意识”的转换,换言之,从现实世界向精神世界、灵魂世界的转换。
然而,一旦意识到了上述根本差异,问题无疑也就显而易见了。
简单而言,庄子无疑已经注意到了“有”与“无”的区分以及“无无”的问题(后来的玄学,例如郭象,则干脆取消了“有”“无”问题),但无论如何,两者毕竟都是“即有即无”,或者偏重“无”,或者偏重“有”。与佛教的对话之后所产生的禅宗,明快之处则是:“非有非无”。例如庄子的“齐物”是在有差别的基础上的,因而并不否定万物的存在,禅宗却否定万物的存在,结果就从道家的“同一”走向禅宗美学的“空”。又如庄子只是天人之学,最高范畴为道,即自然(本性、本然、无为),而禅宗则是心性之学,最高范畴为心,即空。这无疑也使得思想的发展更为深刻、深入。再如,僧肇、道信就发现庄子“犹滞于一也”。庄子提出的“游道”“入天”“见独”“无待”“忘适”“无物”“无情”,都并非无懈可击。“游道”是由于有“道”的存在,“入天”是由于有“天”的存在,“见独”是由于有“独”的存在。“无待”是因为有“待”的存在,“忘适”是因为有“适”的存在。“无物”是因为有“物”的存在,“无情”也是因为有“情”的存在。而禅宗的出现,则使得这一思考从“无物”走向“无相”,从“无情”走向“无念”,从“无待”走向“无住”。还有,庄子对于“分别”的批判和对“无分别”的推崇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但却毕竟还有缺陷。禅宗进而从批判“无分别”又在更高的意义上回到了“分别”。所谓别即是别,同即是同(这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例如巴什勒提出的“本体上的平等”,“接受和接收一切差异”相近),显然就更为深刻。
事实上,禅宗所讨论的,其实已经不是现实世界的问题,而是精神世界、灵魂世界的问题了。从儒家的“有”、道家的“无”转向禅宗的“空”,对于禅宗而言,无疑也正是针对儒家、道家的对于精神世界、灵魂世界的关注不够彻底、不够深刻而引发的反省。
三、发乎情,止乎觉
禅宗的产生,在中华民族的信仰建构方面,无疑应该是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个重大转折。
在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当然是惠能。最初,印度人普提达摩经海上丝路从印度到达广州,在广州建宝林寺,被称为“西来初地”。不久就从广州到南京,会见南朝的梁武帝,孰料话不投机,于是他又“折苇渡江”,到了河南的洛阳,此后的二祖慧可、三祖僧灿,再从河南的洛阳转至安徽的潜山,继而,四祖道信再转到江西的庐山,再转到湖北的黄梅,其间,从黄河文化区域到长江文化区域的转换清晰可见。然而,中华文明第二期的关键的一幕是惠能揭开的。因此,尽管他本人并不在乎历史,但是,拥有他,却毕竟是历史的骄傲。正是因为他的出现,后期的中国文化才再一次隆重上路,再一次整装出发。从此,不再是“佛教在中国”,“中国化的佛教”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且,惠能之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也不再是流转于黄河长江之间了,从此,代表黄河的孔子、代表长江的老子、代表珠江的惠能并肩而立,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圣哲。通过惠能,禅的一瓣心香最终花落珠江。
首先,众所周知,印度的佛教对于生命的看法是负面的,这与中国的思想传统儒家和道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毕竟仍旧是宗教的,也是有神论的。马克思.韦伯指出:“印度所有源之于知识阶层的救赎技术,不论其为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有这么一层不只从日常生活、甚而要从一般生命与世界,包括从天国与神界当中解脱出去的意涵。”[7]然而,经过禅宗的转换,印度佛教的苦难意识被转变为乐观的“禅悦意识”,印度佛教的以“无明”开场也被转化为以“明觉”开场。总之,是从“有神的唯心主义”到“无神的唯心主义”。这意味着:在中国,即便是宗教,在本土也会被润物细无声地改造为非宗教,也会仍旧是走在“无宗教而有信仰”的道路之上,意味着中国的信仰建构与宗教无涉。禅宗自称“教外别传”,并且以“别传”来区别于传统佛教乃至传统宗教,正是对此的慨然宣告。
转变的关键是:从“是心是佛”到“非心非佛”再到“不是心,不是佛”。从禅宗开始,先验的“觉”竟然下降为经验的“觉知”。其中的奥秘是以“心”为“性”。本来,在佛祖那里,“心”与“性”判然有别,但是惠能却蓄意使之统一。如是,则成佛不再是走向彼岸,而是自我觉悟。性,不但是佛,而且还是主体的本觉与所觉,是一体的。结果,“佛性论”在中国转变“佛心论”。于是,“空”成为“真空”,“有”成为“妙有”。最终,“平常心是道”就是必然趋势,于是,佛教信仰进在中国得以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然而,这一次的进入又与魏晋玄学不同,不但是从贵族、知识分子扩大到了市井百姓,而且,尽管禅宗与玄学都是通过“无”把外在束缚统统予以化解,从而回归个体的生命愉悦,但是,魏晋玄学的目标是紧紧抓住偶然的机遇,成就一个我,但是禅宗却无此追求,只是当下承受而已。
总之,禅宗所带来的根本智慧,无疑就正是生命的超越的智慧。它从不引导人们离开具体而又单纯的我——世界——佛,而是倾尽身心去啜饮生命之泉,这就必然超越有无、是非、生灭、得失,“用智慧观照,用一切法,不取不舍”(《坛经》)。并且,认定时间即空间、瞬间即永恒、感性即超越、实即虚、色即空、动即停、生即死、有是有同时又是非有、无是无同时又是非无,“在不住中又常住”同时又无所谓“住不住”。主张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迷时为生死烦恼、悟时即菩提涅槃,现实与理想、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无明”与开悟,也如此。因此,妙悟是现象透处即本体、本体显处即现象。从现象看,是不离有无;就本体看,是不落有无;从整体看,则是不离有无,不落有无。所谓“行住坐卧皆道场”“平常心是道”。
精神世界、灵魂世界的“觉”,当然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过去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儒)、“发乎情,止乎逍遥”(道),现在却成为了“发乎情,止乎觉”(禅)。精神,开始超越了精神与自然的直接统一,开始返回到它自身,一种以精神自身为根据的自由精神,第一次得以在朝宗的温床上加以孕育。尽管,这只是起点,也还并没有达到绝对无限的内在,但是,毕竟已经开始不再作为自然的东西来加以对待,毕竟已经开始把精神当作精神,作为精神的精神自身也毕竟开始变成了精神的对象。超自然超社会的精神生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舞台。
在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成就了“妙悟”与“境界”。
关于“妙悟”,目前已经有众多的讨论,我在《中国美学精神》中也已经专门论及。然而,迄今大部分的讨论却仍然还是云里雾里,就“妙悟”谈“妙悟”,往往被忽视了的,却是“妙悟”的根本内涵。事实上,“妙悟”之为“妙悟”,关键是从过去“神思”与“象”、与经验世界的直接关联,转向了今天的与“境”、与心灵世界的内在相通。它意味着:历经千年沧桑,中国文化终于寻觅到了进入精神世界、灵魂世界的途径。因为精神世界、灵魂世界不是一个可以把握的对象、一个可以经验的对象(否则事实上也就放逐了精神世界、灵魂世界),那么,怎样去对之加以把握呢?“妙悟”正是因此而应运诞生。这,就是禅宗所谓的“于念而离念”。
境界,是中西(印度)思想融会贯通的产物,没有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中由“空”而引发孕育的“境”,中国人也许还一直都在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意象”,也还一直都会停留在从庄子开始的心物关系之中,但是,因为本土思想与境外思想的结合,为信仰建构提供了本体存在的根据。境界之为境界,已经不是昔日中国人所喜欢说的什么“情景交融”,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的诞生。由此,精神世界的无限之维就被敞开了,人之为人的终极根据也被敞开了。我们知道,人是动物与文化的相乘,也是“原生命”与“超生命”的统一。其中的“超生命”其实就是人之为人的文化生命,亦即“灵魂”。境界的出现,尽管首先是在禅宗领域,但是透过宗教的外衣,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它体现的正是人的被文化化,是文化的从附属层面一跃而成为本体层面。人的超生物性——也就是文化性占据了本体的地位。犹如有形存在的人置身的只是世界,无形存在的人所置身的,正是境界。世界,转瞬之间全然成为了对人有所意谓的客体。当此之时,作为人的精神无疑就亟待去自我表达,境界,就正是人的精神的最高的自我表达。这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在理解”[8]8就是世界,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就是境界。从生命“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是世界,从生命的“形式方面研究了前提”,是境界。[9]从“任何物种的尺度”出发的,是世界;从“内在固有的尺度”出发的,则是境界。当然,它并非“真理”,但却是“真在”;它不同于“在”的“理”,是对应于认识,作为“在”的“真”,它对应的是“生命”。而且,相对于“在”的“理”的“真理”,作为“在”的“真”的“真在”,也就是境界,才是“真实”的表达,也是人的终极、人的精神、人的自由、人的超越的最高表达。
四、“有宗教而无信仰”
当然,禅宗的探索也有其历史的局限。这也就是说,迄至宋代,当信仰形态的宗教最终被仪式形态的宗教取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思想引进,却又毕竟仍旧是喜忧掺半的。
中国的引进佛教,究其实质,是有意无意中意识到了信仰的匮乏的必然结果,然而,信仰的建构又谈何容易,它意味着必须毅然跨越毫无精神性的自然意识,趋近超自然的精神世界,可是,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宛如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的跃升,这犹如凤凰涅槃,也犹如脱胎换骨,无异一次精神的万里长征。可是,来自西天的佛教无疑并不胜任,因为它自身也仍旧是自然宗教,在这方面,与中国文化并不存在质的差异。其结果是,佛教进入中国,历经“三武一宗”的四次劫难,而且大致跋涉了三个三百年:第一个三百年,是佛教进入,第二个三百年,是禅宗兴起;第三个三百年,是禅宗逐渐衰落。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菩萨道思想逐渐离开了中国人的视线,佛教逐渐被儒家化。这就是禅宗的出现。所谓“教外别传”,其实就是暗示着禅宗已经脱离了印度佛教。由此我们想到,百年中,胡适、钱穆、柳田圣山都不约而同地用“革命”一词来描述禅宗的出现,钱穆甚至说,真正辟佛的不是韩愈,而是禅宗。其中的真正内涵,正是佛教的逐渐淡出。
在这个意义上,玄奘去世与慧能出家的同时出现,似乎就是一个历史的征兆。从此玄奘就只活在《西游记》里,玄奘历经艰难取回的“西天”智慧、西天的信仰,也从此被束之高阁。有文化的玄奘从此输给了不识字的慧能。
就以慧能与神秀的对比来看:神秀的偈句把“明镜”与“尘埃”对立起来,慧能却认为,其实它们并非彼此对立,而是“心”之两面。“明镜”是心,“尘埃”也是心。万事万物,无论好坏、善恶、智愚,都是我们的心,因此,惠能第一次提出:关键在我们去如何用“心”。这样,首先,惠能开创了“无神论的唯心主义”。全世界的宗教都是“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但是,惠能却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宗教道路——“无神的唯心”。其次,慧能提示说:既然无“神”,这个“心”也就不在“神”,而在每个人的自身。这就是所谓“众生是佛”, 每个人都原本就是“佛”,无需“成”也。只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跟“佛”分开了,所以才要去“成佛”,但是,只要意识到自己就是“佛”,也就不需要去“成”了。最后,因此,所谓“佛”,就只是一个觉悟者。当你意识到原来的所有人生问题都不需要去解答,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问题,于是,你就成为了一个觉悟者。无疑,这样的看法,即便是在全世界,也是开天辟地的全新思想。中国人的思想由此而焕然一新。
然而,被禅宗改变的却不仅仅是佛教,还有佛教的信仰。本来,佛教还是孜孜以求于现实的人心向绝对的佛性的趋近的,但是,禅宗却把绝对的佛与现实的人心混同起来,例如,吕瀓就睿智地发现,禅宗的真正奠基者道信所提倡的安心法门,所谓“道信的禅法”“与当时倡导的‘他力信仰’是对立的”,“道信则强调以心为源,应该凭借自力去做,因而有反对他力的性质。”[10]而且,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尊称为“经”的《坛经》也刻意地强调自性自度、自性自修。马祖干脆说:“平常心是道”,这意味着:连慧能的“迷”、“悟”之间的区别也不复存在,蕴含在西天佛教之中的信仰萌芽被有意淡忘。甚至,因为信仰的被消解,禅宗本身事实上就也被消解了。在基督教那里作为信仰的宗教,在禅宗这里变成了生活。佛教之中的“心”也被具体化为了“心性”。“佛”的宗教被改变为慧能的“心的宗教”,“佛”的信仰转换为“心”的敬仰。虚无缥缈的“佛心”变成触手可及的“人心”。于是,不再是尽从彼岸送来,而是“尽从这里出去”。成圣与成佛、修身与修行、仁爱与慈悲,科举和成佛……都混同起来,事实上,从此,与儒家也就混同起来。无疑,转而从“信仰”的建构又回到了儒家的“道德”建构的老路,这恰恰也正是禅宗的缺憾。
换言之,佛教的引入,倘若是意在中华文明的信仰建构,那么,则应该是两种可能。其一,从“无宗教而有信仰”进入“因宗教而有信仰”,转而借助于“宗教”的衣钵“来完成中华文明的信仰建构。其二,进一步固守”无宗教而有信仰“,那么,则应该是摆脱宗教的衣钵,进而在信仰建构的层面做出全新的努力。然而,禅宗的出现却恰恰未能令人满意。它接过了宗教的衣钵,但是却没有进而以之作为信仰的温床,走的却恰恰是”有例如王阳明哲学的诞生,例如《红楼梦》美学的诞生,但是,倘若仅就禅宗本身而言,却毕竟有所不足。
我们知道,就信仰的建构而言,“精神”内涵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众所周知,人之为人,仅仅只是一个未成品,生而有之的,只是与动物一样的自然本性,所直面的,也只是与动物所直面的一样的自然世界。幸而,这对于动物来说已经是全部,对于人来说,却只是局部,或者说,只是一半,而且是相对来说并不起决定作用的一半(尽管也很重要),另外的更为重要的一半,则是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亟待人类自己去创造的世界,也是真正拼尽全力去争取。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示: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而且能够“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8]30意味着直接的外在自然世界的被主动剥离,每每把现实世界混同精神世界,把人的自觉意识混同动物的自觉意识,遗憾的是,外在对象作为他物,却始终都是异己的,也始终都是每个人都须臾不可离开的,因而就也始终都在制约着自身,不但当然毫无自由,而且更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自己在其中借以实现自身的对象来看待。而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则意味着:即便是不再凭借直接的外在自然世界,精神世界、灵魂世界却依旧存在。何况,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根本区别本来就在于必须能够自由地对待对象,并且能够在外部对象身上直观自我,并且,还因此而穿越了直接性、个别性而进入普遍性。
然而,在禅宗,却尽管意识到了人类唯有借助精神生活才有可能真正生活于自然世界,意识到了必须从精神本身来理解精神世界,但是却也毕竟未能完全从自然意识中超拔而出,也未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因为,所谓自由包括对于必然性以及客观性、物质性的抗争,以及对于超越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性、理想性的超越两个方面。禅宗敏捷地把握住了其中的超越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性、理想性的超越,由此,中华文明第一次不再关注脱离了自由的必然(例如儒家),而是直接把自由本身作为关注的对象(这无疑又是从道家“接着讲”)。由此,自由本身成功地进入了一种极致状态(中华文明的思想本身也因此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广阔领域),但也正是因此,自由一旦发展到极致,反而就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自由。恰成对照的是,西方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采取的态度是:自由地选择(荒诞)。它勇敢地逼近这一危机,承认生存的荒诞性,并且坦然地置身之中,在其中体验着自身的本质。然而,禅宗的态度却是:自由地解脱(从“逍遥”到“觉”,即“解脱”)。结果,从庄子的“游”发展为禅宗的“证”(世界都成为象征,成为一个隐喻,于是才有所谓“看破红尘”),这当然十分深刻。然而,面对“生死怖人”的烦恼,它却仅仅以“解脱”就取代了“烦恼”,“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爱心也同时被取代了。其结果,就是滑向“无可无不可”的掩耳盗铃,这,又是我们亟待予以高度警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