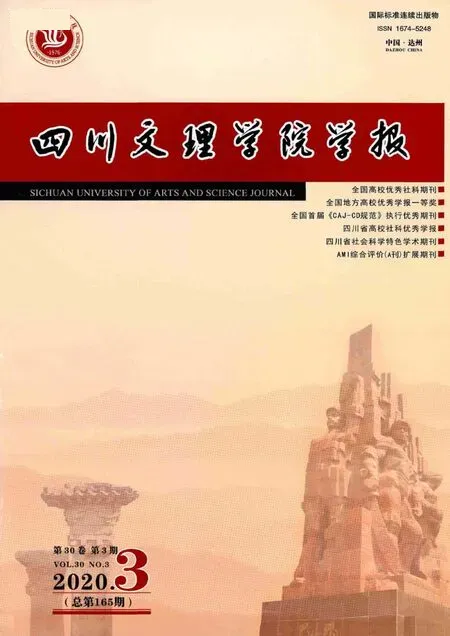审美救赎:赎回信仰,赎回爱
——有感于潘知常教授新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
刘 燕
(浙江传媒学院 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凡有灵魂的,都等待着一场救赎。
爱、生命、美看起来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但作为学术研究,依然需要充足的佐证。21 世纪前20 年,生物工程、仿生工程、无生命工程三大智慧设计工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的趋势似乎正在上演,关于超人类的话题不断地见诸报端,关于未来的人类是什么的、人的存在形式也不断地在艺术家、脑科学研究者的创作和发现中被重新定义和思考。
与人类身体一同走进超人类世界的还有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的痛苦,是当今时代最大的痛苦,从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萨特,在从生存走向存在的途中,虚空的存在问题一直拷问着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如果人类仍然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未来,人类的精神痛苦并不会因为身体寿命的延长而快乐,反而还将进一步加深。
在过去,人类依靠宗教来回答灵魂最终的归宿,把精神寄托在天堂或轮回里,以此来麻痹心灵的空虚,然而在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之后,祛魅之后的宗教,早已不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精神依靠,而仅仅只是变成了少部分人的个体精神规范,其存在的合法性规范也不复在世俗生活之外。那么,对于无神论者,在没有神的世界,我们该怎样才能活得有意义呢?寻求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是人存在世界的必要条件。面对精神追寻意义的痛苦,哲学家必须给人类一个答案。不过,现代的哲学家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强调否定虚无而“解脱”这痛苦的无意义的人生。尼采则为生命意志获得了一个强力,即生命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扩张,他认为艺术是强力最生动最直观的体现,主张用艺术肯定人生,提出了“审美救赎”的概念。海德格尔认为要真正地阐明人生的哲学问题,就要“为死而在”“向死而生”,因为死亡和无有才是人生的本相。
在阅读《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之时,仍不免要将潘知常教授所提的“审美救赎”与现当代影响最大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相关照来思考“审美救赎”如何成为唯一的可能性拯救。尼采的“审美救赎”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支持和传承,但常被其他哲学家抨击是靠艺术幻觉和艺术陶醉来忘却个体生命的痛苦和虚无罢了,关于艺术如何在审美中产生救赎,马尔库塞、本雅明等都所言甚少,论据确实有限。
在新著中,潘知常教授延续了审美救赎的哲学概念,但真正让人信服的是,他不把审美救赎放置在空洞的艺术幻觉中,而是将审美救赎放在信仰的维度上,回归到生命意志的本身来看生命,就像生命进化的动力来自生命的冲动,能够产生审美救赎的艺术,也必然带有生命本身的力量,随之就引出了信仰的核心是爱,审美救赎是赎回信仰的路径,审美救赎最终赎回的是爱,是对生命的爱,这也是潘知常教授一以贯之的生命美学的核心。
一、“以美育代宗教”百年后的审美教育与审美救赎
在尼采提出“审美救赎”之后,在中国上个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先生也对于宗教“祛魅”后的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救赎方案。王国维先生和尼采的观点相似,他强调要以审美艺术的超越性来取代宗教的作用,发挥审美与艺术的宗教性质与功能。1904 年在《红楼梦评论》中,他就发表了对于艺术价值的看法。他认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次一切美术之目的也。”[1]王国维并没有否定审美艺术中存在的宗教的神性、超越性和形而上学的属性,他从审美与艺术的信仰维度来回答中国信仰缺失之后艺术的使命。
1917 年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他的登高一呼掀起了一股声势浩荡的全新的对中国人灵魂重建的美育热潮。在宗教衰微传统崩解,国人价值困境和信仰迷茫之时,审美教育的实施确实为虚空中的中国人找到了精神的安慰。不过,“美育代宗教”是将美育与宗教对立起来的,它将一个灵魂救赎的哲学命题,变成了一个现实的课题,否定了审美与宗教在终极关怀上的一致性,“美育代宗教”发展到后来美育与信仰完全独立开来,艺术被当作疏解逃避灵魂存在焦虑的工具,艺术教育成了提升个人修养、享受幸福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灵魂的救赎,虚空无意义的痛苦仍然存在,艺术异化严重。
在书中,潘知常教授借助五十五万字的篇幅与蔡元培先生对话,尖锐地指出“以美育代宗教”的问题在于:它全面否定了宗教,而没有肯定宗教精神中信仰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可以拒绝信教,但不能拒绝宗教精神,在当代世界,信仰不是万能的,但是,假如没有信仰,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当美育失去了信仰的支撑,审美的过程就只是技能的培训,人们关注的是现实的满足,而不是终极关怀的彼岸世界,因此也就不再具有救赎的功效。
在此意义上,所谓审美救赎其实也就是审美教育的别名,只是,与审美教育不同,它更加强调的是要拯救人被剥夺了的虚空的非真正存在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是隐匿不彰的,它就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日常生活的存在,是一种异化的状态。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所接受的无信仰的审美教育,则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是在帮助人们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快乐地“沉沦”,但这并不是作为人的真正存在,而仍旧是异化的非真正的存在,依然无法解决人类虚空的痛苦。审美救赎,却正是把人从非真正地存在向真正地此在的赎回。
二、从“信念”到“信仰”,审美救赎要回归神圣与生命
要从异化的非真正的存在回到真正的存在、此在,潘知常教授认为,必须要深入地分析审美教育中的认知是如何偏离救赎的,并且要回到信仰和终极关怀的维度来探讨审美救赎的核心。
关于以什么来代宗教,在百年前不仅有“以美育代宗教”,还有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梁簌溟的“以伦理代宗教”、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孙中山的“以主义代宗教”。这些对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都有助益,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百年中国发展的瓶颈——梁漱溟先生称之为“中国问题”之外的“人心问题”,潘知常教授认为,在此中,只有审美与艺术、哲学能够触及“人心问题”,盖因它们与宗教都是奠基于“灵魂结构”,同属终极关怀。
审美与艺术与哲学和宗教不同的是,后两者是将意义抽象化、人格化,对二者而言,意义都凝结在世界中,是一种先“生产”后“享受”的救赎方式,但审美却完全不同,它是创造性的生产过程,是边“生产”边“满足”的救赎。正如每个人都具有创造性,每个人都有审美权利,每个人都有救赎自己的可能性,人类创造宗教的原始目的就在于为自己创造一个彼岸,创造的过程就是充满希望的救赎过程。像萨特在一次演讲后的采访中谈到,“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2]
回到“以美育代宗教”激起的扫“美盲”的社会热潮和创造力的开发,潘知常教授认为,我们美育对应更多的是审美的“信念”教育,是世俗审美,而非深入深层“信仰”的神圣审美。“信念”和“信仰”的区别在于,“信念”作用在“人的目的”上,以人为工具,而“信仰”是以“人为目的”的。“信念”是一种可觉察的、可控的意识,“信仰”则是与生命的本源有关系,藏在不可觉察不可控的潜意识中,能够取代宗教的美育,不应当是世俗之美,而应是神圣之美。
现代兴起的附庸风雅的生活方式、花样繁多的艺术培训,越演越烈的身体美学、生活美学,毫无疑问都是美育兴盛的产物,他们唤醒了人们对美的认识和追求,某种程度也满足着人们对彼岸的幻想。不过,这种审美体验是享乐需要,是“信念”的美育,是为达到“人的目的”而产生的,而并不是以“人为目的”的,充其量只是在“信念”层面达到了一种马斯洛称谓的“优心态文化”的审美满足,而与审美救赎产生的超越性、形而上学的神圣体验相距甚远。
要让美育能够取代宗教,就必须要回归到“信仰”的本质来建立美育的信仰。信仰本质上是一种爱的共同体、生命的共同体,卡希尔指出,人类“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这个“共同纽带”就是终极意义,也就是信仰。[3]蒂利希认为,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4]人类精神最深层次的本能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与对生命的渴望,由此,信仰也必须要回归到生命的本质,才能真正地将人从精神世界的被剥夺感中赎回,并得享平安。
三、宗教“祛魅”后的虚无主义与审美救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把当今时代称为“第四大觉醒”(Fourth Great Awakening)的时代,人类“精神的发展或非物质上的不平等同物质不平等一样严重,甚至更甚。”[5]宗教时代,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自从宗教被“祛魅”之后,精神上的虚无主义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从财富鸿沟到数字鸿沟再到精神鸿沟,人与人的差距越拉越大。虚无主义,这个“灵魂丧失”的现代之幽灵就以各种方式潜伏进了我们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之中。
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失去了最高价值的现代人比任何时代都倍感无聊,这种情况和古罗马时期追求享乐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不确定的未来让享乐主义又重新占到了世界的中央,世界以自由、价值多元、虚空为名充满了放纵、醉生梦死、奸淫和邪恶。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精神救赎的时代。
太阳底下没有新事。回顾欧洲历史,潘知常教授认为,让西方社会两次崛起的虽有航海大发现、科技、资本主义精神,但根本动力却是基督教产生的信仰精神。人类作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冥冥中却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着人类前进的方向,昭示找一个重要的信息:人类可以拒绝神,但不可以拒绝神性,人类可以拒绝宗教,但却不能拒绝宗教精神。这一观点,也屡次出现在潘知常教授的著作中。
这种对于神性的关注,与积极心理学的先锋派领袖乔纳森·海特的研究不谋而合。乔纳森·海特认为,人们群体生活的社会空间,不仅仅满足于以亲密或喜爱度表示的水平维度、以阶级和社会地位表达的垂直维度的二维空间,人的内心感受上还有第三个维度——神性的道德维度。必须强调,神性的道德维度,并不意味着就是宗教。[6]因为它虔信的并不是宗教,而是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隐藏在背后的信仰。人类是无法抗拒神圣的,在《神圣与世俗》中,伊利亚德指出人类有感受神圣的能力,神圣不断以“隐蔽的宗教形式”出现在现代俗世的世界里。[7]因此,即便在虚无主义的人生中,一半是野兽一半是神明的人类仍然渴望神性。对神性的渴望,让我们渴望从虚无中摆脱个人工具性的存在,摆脱世界是它——他的他者的存在,而成为“你”的存在、自由的存在。潘知常教授关于“神圣”的研究,虽然没有采用积极心理学作为佐证,但却从世界所走的历史道路,从不同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的关系中,发现了这一深藏在人类灵魂中对神圣的无法抗拒的追求,不能不说是这一睿智的发现是对中国美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四、没有爱是万万不能的,爱是信仰的核心
人类对神圣的渴望和追求,在今天也超过了任何时代。灵修、朝拜、瑜伽、旅行等灵性体验活动风靡全球,心理学家发现朝拜的提升感让人得到了爱的满足。著名心理学家哈洛的恒河猴实验,用剥夺小猴与母亲之间亲密关系的实验,证明了爱之于灵长类动物的重要意义。爱,正是隐藏在人类生命里的核心,是人生的原体验。
人类不能没有爱,柏拉图说,“谁若不从爱开始,也将无法理解哲学”,费尔巴哈说“只有爱给你解开不死之谜”。《哪吒》、《头号玩家》、《阿塔丽:战斗天使》,现代大量的影视剧中,那些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最终都选择了降服于爱。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体验。
无论是西方基督教的博爱,还是佛教的慈悲、儒家的仁爱,爱都是深藏在人格结构里的信仰,宗教的道德规范说到底就是爱的道德规范,宗教精神其实就是爱的精神。过去人类的历史,是不同民族与神灵对话的历史,其核心是神,而不是人。而当宗教祛魅之后,人才真正地从自在的奴性的人成长为自觉的人,宗教精神开始抽象为人性的存在,人完成了成为神性的人的转身。人不再走向神,而是走向了神性背后的爱,走向了以爱为中心的存在。人与彼岸的关系,就变成了人与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走向了爱与爱的关系。总之,宗教精神走向了爱,人走向了“我爱故我在”。
潘知常教授认为,人类总需要一种“非如此不可”的东西,无论是“沉重”还是“轻松”,人类文化的历程中都不可缺少,而这种非如此不可的东西,就是神圣文化的信仰,它对生活永远说“不”,对理想永远说“是”,从大量艺术家、文艺作品和现代社会中都能找到这一需要的存在。例如,人们喜爱梵高的向日葵,被毛姆以高更为原型的《月亮和七便士》感动、伤心,宝玉出家、为高尔基主人公的燃心为炬而打动,幻想在别处的诗和远方,其根本上都是在呼唤神圣文化的信仰。
神圣文化的信仰就是爱的信仰,是对人类破碎存在重建的信仰。人生活在三个存在于自然世界、人际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与任何一个世界的割裂,都会让人类产生深深的孤独破碎感,爱就是一种与世界、人类、自我一切重新建立积极关系的信仰。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说过,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得到全面知识的唯一途径是爱:爱超越了思想,超越了语言,爱是一种灵魂的力量,唯有通过爱才能真正的达到与世界、宇宙、天地、人融合。[8]在无宗教的时代,对抗虚无主义,人们不应再孜孜以求成为信仰“知识的人”,而应是信仰“爱的人”。人类存在的意义,只有从人性存在的根本价值出发,才能找到存在的价值,这才能从根本上赎回人的信仰的尊严。
五、审美救赎与艺术的信仰之路
审美救赎并不是一个新命题,尼采早已以艺术来肯定人生,认为审美是可以救赎的,马尔库塞也说过“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9]但他们并没有说明审美救赎发生作用的原理。在新著中,潘知常教授解开了审美救赎运作的奥秘。
他认为,哲学以及审美与艺术都可以到达信仰,但哲学只关注现实的此岸,并不关心彼岸,审美与艺术却可以到达此在的彼岸。审美救赎之所以产生,在于审美体验中存在着内在的自由生命借助于外在形象所进行的自我建构,这种被称为意象呈现的方式,正是审美与艺术的特殊本性。[10]475意象呈现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力量,吉尔伯特、库恩在《美学史》中认为“它体现了人们创造象征和符号的独特而神奇的力量。”[11]审美与艺术和宗教、哲学一样是奠基于“灵魂结构”的象征性活动,透过隐喻地看世界,通过“超能指”,审美使存在着的东西都成为象征,从而与形而上的、终极的东西联系起来。在审美体验中,透过艺术符号的意象呈现,终极关怀被带入审美的体验中,人类的精神世界重新投向了彼岸,人生的意义重新显现出来,人的信仰就显露出来。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与审美都能够实现救赎的功能,只有关注“真在”的艺术,意象呈现才真正地产生救赎的功能。只有在每一次的审美的瞬间,人超越了自己的动物性、自私的本性,达到与他人共同、共享,灵魂在身体中被唤醒的瞬间,我们才是真正地体验到审美救赎。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唯有现代艺术才能担当此任,审美救赎就是坚定不移地以艺术去否定异化和物化社会。真正的艺术必须必须保持独立,禀赋一种面对现存社会的否定、颠覆的能力,才能“赎回最虔诚、最善良的人来”。[12]因此,艺术必须是那些能自由独立地对“真在”关注的艺术才能够胜任审美救赎。
艺术的审美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趋向,海德格尔称之为“真理之发生”的审美与“趣味之满足”的审美。对“真在”关注的艺术,是审美的“真理之发生”,它将艺术还原为认识价值、伦理价值,通过审美带来真理的领悟。而趣味之满足,主要是审美的享受,它满足的是人的感官需要,对外物感性形式的趣味性需要。艺术和工匠作品的区别就在这里。因此,艺术要产生审美救赎,就必须让艺术成为建立新世界的载体,在美育中,不仅要诉诸在审美技巧实践上的培育,更重要的是对艺术家信仰架构的培育,也即爱的信仰在艺术创作中的培育。
六、从“无神的信仰”到“审美救赎”:中华文明的自我救赎之路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潘知常教授认为“无宗教而有信仰”是中国特色,这恰恰与审美救赎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语境相吻合,有助于中华文明走向审美的自我救赎之路。不过,要完成中华文明的自我救赎之路,就要正本清源,把中国美学传统中充满活力的“活东西”精粹释放出来,并且找到审美救赎与中华文明的交汇点。
在中国的美学传统中,存在着忧世的美学传统和以文学为生活的美学传统,这两种美学传统又可以分为言志载道的传统和吟咏情性的传统,前者的代表是《诗品》《文心雕龙》,后者的代表是《山海经》和《红楼梦》。相比而言,前者更多的是审美逍遥,后者所代表的美学传统才更接近于审美救赎。潘知常教授认为,尤其是《红楼梦》的出现,中华文明才第一次走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怨恨之书的老套,作为中国第一本还泪之书、赎罪之书,第一本爱之书,从现实关怀走向了终极关怀。
他认为《红楼梦》对于情的提倡是中国美学在漫长经历中最为趋近于“爱”的一次努力。《红楼梦》虽是在讲贾宝玉和众多女孩“情-情”的故事,却指向了中华民族人性结构中自由和尊严的缺失,只有当人的自由意志觉醒时,人的自由和尊严被捍卫的时候,爱、忏悔、悲悯才会发生,人才会醒悟到人要造就人自己,这时真正的审美救赎才会发生。为此,潘知常教授认为,中国美学要接着明清《红楼梦》的“情本美学”继续往下讲,要在中国美学精神中加入爱、忏悔、悲悯与悲剧的主题,以自由为经,以爱为维,以守护“自由存在”并追问“自由存在”,完成从审美逍遥向审美救赎的华丽转身。在爱的信仰之维上重新建构中国美学,是中国美学的神圣使命。
中国美学传统要兼收基督教博爱、佛教慈悲、儒家的仁爱,从有缘有故的爱转向无缘无故的爱,破除它的负面指向(例如天下为家、孝亲至上)以遥遥指向它的肯定指向(例如“天下为公”“仁者爱人”)来建构审美救赎。把爱是对于无限性、人是目的、人是终极价值、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责任、“成为人”“人样”“人味”作为坚定不移的信。[10]369
而在当前,中国面临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个矛盾的主题,全球问题、人的物化问题表现得很突出。潘知常教授认为,中国的审美救赎,需要在“以美育代宗教”百年之后的再启蒙,自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绝对不应该被看做是西方文化的专利,而应该被看作中西文化的共同追求。中国特色的审美救赎是要让自由意志与自由权利成长,通过审美教育将信仰赎回,将爱赎回。
结 语
作为富有盛名的美学家,潘知常教授的《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将中国美学提升到了哲学境界。以生命来见证爱,以爱来救赎生命,“我爱故我在”不但是生命美学,更是一种生命哲学,在它背后意味着人类的人格结构、信仰结构、社会价值结构都出现一次全新的提升和转型。当人类真的在未来超越了自己而成了新人类存在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回答我们的生命为何而需要永恒地存在?爱,给予了人们最好的回答。
我相信,未来潘知常教授所掀起的“爱的革命”一定会赢得这个时代乃至下个时代更多的爱的追随者,也必将中国美学引入生命的纵深研究,跨越生命的边缘情境,让中国美学精神从有缘有故的爱转向无缘无故的爱,最终将美的尊严、爱的尊严、精神的尊严、信仰的尊严完整地赎回,并且,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在信仰中、在爱中,完成自我的生命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