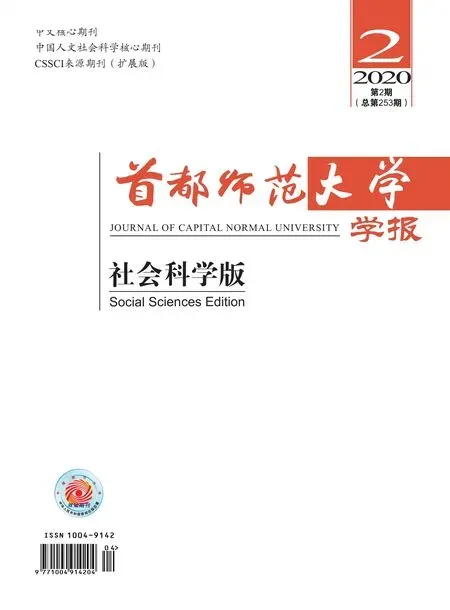威权体制下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湛中乐 康 骁
西南联大因其辉煌成就而备受关注。据统计,中国期刊网1978—2008年收录的直接相关论文高达334篇。①伊继东、冯用军:《中国西南联大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一种词频计量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从2009年至2018年,又增加了70多篇相关论文。②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笔者以西南联大为主题和关键词检索到2009年以来的文献达70多篇。最后检索时间:2018-02-03,14:14。在既有的研究中,西南联大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为民主、自由、自治和包容的氛围,这使得西南联大几乎成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象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教育史研究中的“西南联大神话”,并批评既有研究忽视了西南联大的自由和民主的复杂性与多维性;③田正平、潘文鸳:《教育史研究中的“神话”现象——以蔡元培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个案的考察》,《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研究者往往根据现实需求对历史进行“预制似的解读”,片面提取历史事实以论证当下决策的正当性。“当大学纷纷要求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科学理念、自治传统、兼容并包原则、学术自由的思想、教授治校的制度等被不断强调。”①伊继东、冯用军:《中国西南联大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一种词频计量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事实上,传统观点和批判观点的分歧在于是否将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理想化和神圣化。批判者并未否认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只是要求研究者不能忽视其复杂性。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此问题,并尝试通过还原西南联大所处的历史情境的复杂性来研究其自治和学术自由,进而将西南联大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实现归结为如下因素:第一,知识分子犬儒主义尚未形成;第二,政府无力干预,自治传统得以延续;第三,开明的地方政治。②阳荣威、梁建芬:《西南联大教育成就的历史情境分析》,《大学教育科学》2016年第3期。第二个和第三个理由都可以归入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基本问题,③周光礼:《学术与政治——高等教育治理的政治学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研究者经常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分析西南联大自治和学术自由,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孱弱是西南联大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一个重要理由。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实属孱弱。1927年以后,威权体制逐渐确立,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也随之强化。④1928年北伐以后,蒋介石建立起党国一体的权威政治,即“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威权体制。参见萧功秦:《从百年变革看中国新权威主义改革模式》,《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4期。此时仍以中央政府控制力孱弱解释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恐怕有失妥当。蒋介石建立的威权体制与西南联大之间的关系或许更为复杂。申言之,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威权体制的背景下如何实践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一、威权体制向高等教育领域扩张
中世纪的大学是指一群有志于研究学术的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团体。⑤林杰:《西方知识论传统与学术自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这种团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学术共同体,亦被学者称为信任网络,⑥周光礼:《学术与政治——高等教育治理的政治学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直到今天,大学作为一种信任网络的性质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小的共同体始终存在于一个大的共同体之中。这个大的共同体在13—15世纪是封建国家,在16—17世纪变成了王朝国家,18世纪以后又变成了领土国家。⑦Randall Lesaffer,European Legal History: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translated by Jan Arrie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382.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必需处理其与国家这个大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政教分离的原则确立以前,大学还受到来自宗教的压力。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与国家、宗教之间的矛盾不断演变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宗教并不足以影响或控制整个社会。因此,分析西南联大与大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分析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西南联大的自治与学术自由深受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传统的影响。从191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蔡元培、张伯苓和梅贻琦分别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这三所大学在抗战以前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典范,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逐渐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在当时能够实现,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碎片化状态使得大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成为社会思潮。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南北分裂,各派军阀纷争不断。军阀们为了笼络人心,对大学的态度往往也较为宽容,例如贿选总统曹锟和奉系军阀张作霖都有过尊师重教的轶事。⑧曹锟常对手下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就得靠教授”。张作霖曾下令,政府经费的40%投入教育,并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教师。李克、沈燕:《蔡元培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第90-91页。当然,军阀们也有过很多伤害大学的行为,例如张作霖曾强行将北京九所国立大学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1925年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亦是军阀争斗的结果。①李娟:《党化教育、大学自治与人事纠葛——1925年东南大学易长风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总而言之,军阀混战减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这使得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成为社会思潮,社会精英投身于教育事业,致力于推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教育救国”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应该首先或者主要通过教育才能实现。②张天宝、姚辉:《我国近现代“教育救国思想”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3期。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战争的不断失败,使得社会精英开始探索救亡之路。社会精英在探索救亡之路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教育的作用。“教育救国”的思想萌生于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洋务运动中开始进入实践领域。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形势日益艰难,各种西方理论涌入。在此背景下,众多杰出人物认为新型教育是救国救民的至上法宝,并亲自推动新型教育。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教育救国论”思潮才开始消退。③吴玉伦:《教育救国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教育事业,例如,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验等。④张天宝、姚辉:《我国近现代“教育救国思想”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3期。除了农村教育改造运动外,高等教育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高等教育,例如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等等。他们不仅投身于国立大学的建设,而且支持私立大学的发展,例如,蔡元培不仅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而且还参与了私立东南大学的建立。这些人不仅受“教育救国论”思潮的影响,也受到了“教育独立论”思潮的影响。“教育救国论”针对的是教育的目的和重要性,而“教育独立论”则回答了如何办好教育。1920年代,在学术自由观念和办学经费短缺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教育独立的思潮,要求效仿西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摆脱政治对大学的掣肘。⑤张晓唯:《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思潮评析》,《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5期。在“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的影响下,现代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1920年代和1930年代,政府新设了20所国立大学。⑥李木洲、刘海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设立与分布》,《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4期。1925年,全国国立大学数量达到一个小顶峰,共有21所国立大学。⑦李涛:《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数量及区域分布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2期。1924年全国共有私立高等学校47所,1927—1937年全国新增私立高等学校11所。⑧周楠、李永芳:《民国时期私立高等学校述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这些学校大多效仿西方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模式”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私立高等学校大多建立了董事会、校长和评议会并立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⑨刘根东、何洪艳:《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及其借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国立大学则建立了校长和评议会并立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中央政府控制力孱弱、“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成为社会思潮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背景。在此背景下,这三所高校得以建立自治、民主和保障学术自由的内部治理结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基本上继承了这三所高校的传统。但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时代背景与前三者稍有不同,一方面蒋介石逐步建立起威权体制,另一方面随着抗战的爆发,威权体制强化。威权体制的建立和强化使得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与前述三校有所区别。
1927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次年国民党颁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政权被托付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得以建立。其基本特征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实际上就是以党治国。其组织聚合力、意识形态聚合力、政党动员力和政府执行力远远强于北洋时期的军事强人体制。⑩萧功秦:《从百年变革看中国新权威主义改革模式》,《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4期。威权体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逐渐增强,中央政府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监督者。从1927年到抗战前夕,中央政府从意识形态、组织、经费等方面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控制。
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的中央政府通过党化教育政策和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实现了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控制。1928年8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统一革命理论案》,要求“定一个言论标准来,令全体党员遵照标准发表”。①《统一革命理论案》,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页。此项法案之目的是在党内统一意识形态。在《统一革命理论案》通过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在两广推行“党化教育”政策,以实现对教育领域意识形态的控制。所谓“党化教育”,实际上就是以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1927年,“党化教育”在全国铺开,各地纷纷出台“党化教育”政策。②具有代表性的是蒋梦麟起草的《党化教育大纲》:一、以本党(中国国民党)训练党员之方法训练学生。二、以本党的纪律为学校规约。三、根据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及民族主义第六讲,建设新道德应从求知入手。四、依训政时期国家的组织为学生自治的组织。五、以三民主义之中心思想确定学生的人生观。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0卷)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23页。“党化教育”政策将培养学生与培养党员等同起来,混淆了政治系统与学术系统。如果将知识的传授和发现作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任务,那么“党化教育”政策显然会妨害这一任务的实现。“党化教育”政策全面铺开之后,受到了教育家们的诸多批评。例如,陈独秀就公开声称,将来是否要搞党化妓院。1928年5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废止党化教育名称,代之以三民主义的教育。”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7期。转引自骆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立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将“三民主义”确立为中华民国教育的宗旨:“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计民生,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④《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2页。转引自骆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立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104页。在实施方针上,该法案要求各级教育将三民主义贯穿到课程和课外作业之中,实际上是要求教育发挥民主胜任的功能,即增强公民个人认知能力,培养现代公民,建设现代国家。与“党化教育”政策相比,“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有所放松,不再坚持以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
在组织上,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改革行政组织和大学的组织结构,基本上实现了对高等学校的组织控制。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重新组织了教育行政体制。北洋政府时期实行三级管理模式,中央设教育部,各省区设教育厅,地方设教育局。教育部直接管理教育厅,教育厅直接管理教育局。由于军阀混战,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处于一种应然状态,并不具有实际效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等人建议效仿法国设立大学院和大学区,以确保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改掉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化习气,推行教育行政学术化。⑤秦凌:《民国时期教育立法研究(1912—1949年)》,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9-41页。然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与“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威权体制根本上是不相容的。⑥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失败的理由可参见杨卫明、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非凡尝试——民国时期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撤销了大学院和大学区,恢复了教育部和教育厅制。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教育行政组织逐渐完善,并实现了对全国高等教育的控制。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制定《大学组织法》,改革高等学校内部权力结构。北洋政府时期,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建立在“教授治校”的基础上,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建立在“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基础上。在“教授治校”的体制下,教师控制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教授治学、校长治校”体制下,教师对校内权力的影响退缩到学术领域,行政权力在校内管理体制中获得主导地位。
在经费上,南京国民政府逐渐规范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分配。北洋政府时期,教育经费经常被军阀侵占和挪用。为扭转此种积弊,蔡元培在大学院改革过程中提出《教育经费独立案》,主张实行教育会计独立制度,但是各地方政府仍然阳奉阴违,教育经费独立制度无法推行。实践证明,教育经费只有依赖中央权威才能获得保障。随着教育部的重新设立,教育部于1930年颁布《确定教育经费计划及全方案经费概算》,规范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分配。从高等教育经费保障这个角度来看,威权体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扩张符合高等教育当时的发展需要。
从1927年到1937年,一方面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建立并向高等教育领域扩张。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天平逐渐向威权体制倾斜。卢沟桥事变以后,整个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所有的文化教育“围绕着抗战这个主题生动活泼地呈现出来,并且准备着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①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换言之,抗战和建国成为时代的主题,并辐射到高等教育领域。193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了抗战时期基本的教育政策。此时的教育政策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基本上背道而驰。《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二条规定了战争期间的教育政策,核心主张是教育服务于抗战。②《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收录于荣梦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488页。193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了九项方针和十七项要点。③《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收录于罗廷光:《教育行政》(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283页。该纲要认为教育的缺点在战争中彻底暴露出来,需谋求根本之挽救。在方针上,该纲要提出“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否定了教育独立论。相关措施包括:每一学校之设立及每一科系之设置,均应规定其明确目标与研究对象,务求学以致用;从速制定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办法;实行导师制,导师负责学生的品格修养与公民道德训练;中等以上学校一律采取军事管理办法;设立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提高学术标准。这样一些措施实际上是将教育当成了实现政治的工具,必然会危害到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抗战的到来使得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国民党对教育的控制。“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威权体制在教育领域的扩张加速。
总之,威权体制建立以后逐渐向高等教育领域扩张,高等教育中习以为常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观念开始受到挑战。抗战开始以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受到的冲击愈发严重。但令人惊奇的是,西南联大仍然被人们视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象征。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威权体制的冲击?威权体制中的哪些因素为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留下了生存空间?
二、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
政治体制的威权化伴随着全面抗战的到来而加深,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控制日益强化,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组织和教师资格三个方面。
首先,意识形态教育组织化和常规化。尽管抗战以前,三民主义教育就已经在高等学校推行,但是高等学校在三民主义教育的实施方面尚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够依本校实际情况开展。胡适在1937年庐山谈话上再次重申大学教育避免政治干预的基本观点,反对国民党现任官吏担任大学校长或董事长,反对国民党干预大学教师聘任、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④柳轶:《1919—1949年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但是胡适的发言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国民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教育。国民政府决定在高等学校统一设立训导处,推行训导制度。所谓训导制实际上包括“训育制”和“导师制”,训育制将德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导师制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配备一位导师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学业和生活。1938年3月,教育部设立“训育研究委员会”,1942年3月改为“训育委员会”,专门推进各级学校的训育工作。1938年2月,教育部制定了《青年训练大纲》,规定了训育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向学生灌输国民党的党义,使得学生自觉践行国民党党义。1938年3月,教育部制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正式实施导师制。
其次,组织控制更加严密。大学院和大学区改革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2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部组织法》,重新组织教育部。新成立的教育部负责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内设高等教育司执掌有关高等教育的各类事项:关于大学教育及专门教育事项,关于各种学术机关之指导事项,关于学位授予事项,关于其他高等教育事项。①广少奎:《重振与衰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此后,国民政府虽然修正《教育部组织法》多达十次,但是教育部的职权基本保持不变。尽管如此,教育部的职员总数和部设委员会的数量却在抗战期间不断增加。1931年,教育部部属人数大约130余人,到1940年时教育部部属人数已经激增至200余人。②广少奎:《重振与衰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抗战期间,教育部设立的有关高等教育的委员会包括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1939)和学术审议委员会(1940)。③尤其要注意学术审议委员会。该会有助于改革高等教育和促进学术研究,但是该会也开政府组织学术审议制度之先河,是学术集权化的表现。参见张瑾:《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论述》,《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除了教育部的扩张,组织控制强化还表现为政府对大学内部组织设置的控制。尽管1929年《大学组织法》已规定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但是各校内设机构仍由各校自行拟定,名称分歧亦多,如数学系与算学系的分歧。为统一各高等学校内设机构,教育部于1939年制定了《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统一各高校内设机构的设置。④《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699-700页。
再次,严肃教师资格。北洋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薪俸、晋升与抚恤等逐渐规范化,但是高等学校教师的聘用标准仍由各校自行设定。1929年《大学组织法》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级。1940年,教育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明确各级教员的资格。高等学校在任职条件上放宽标准必须经过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该规程设置的资格主要是学历、职业经历和学术成果方面的条件,对于提高学术标准是有益的。⑤该规程的具体内容参见骆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立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126页。然而,一旦教员资格由教育部统一规定,高等学校在教师聘用上的自主空间就大大缩小了。
政府控制强化对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总体而言西南联大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介绍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著作不胜枚举,毋庸赘言。本文仅从校内体制的民主化和西南联大抵制政治干预的角度简要介绍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
在校内体制上,西南联大的校内治理体制民主化程度虽然降低,但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民主传统一直保存下来。西南联大虽然也设立了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但是校务会议和教授会并不经常召开,学校的日常事务和部分重要事务实际上由常务委员会处理,而常务委员会由教育部任命。尽管校内治理体制的民主化程度降低了,但是西南联大在很多事务的处理上深受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民主传统的影响。《校务会议组织大纲》和《教授会组织大纲》虽然由常务委员会制定,但是这两份组织大纲仍然规定一些重要事务须提交校务会议或教授会审议。例如,校务会议审议如下事项:“(一)本大学预算及决算;(二)大学学院学习之设立及废止;(三)大学各种规程;(四)建筑及他项重要设备;(五)校务改进事项;(六)常务委员会交议事项。”⑥总览卷,第105页。教授会审议如下事项:“(一)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二)学生导育之方案;(三)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予;(四)建议于常务委员会或校务会议事项;(五)常务委员会或校务会议交议事项。”⑦总览卷,第111页。此外,1938年10月18日,常务委员会还议决:“本校常务委员会开会时,请本校各院、处长列席。”⑧第九十一次会议,第70页。在一些重大事务的处理上,民主传统的作用尤其重要。例如,在“一二·一”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过程中,从1945年11月29日到1945年12月26日短短一个月,教授会先后召开9次会议研究当时局势,采取应对之策,而此前教授会一个学期开会次数通常不超过两次。
在学术问题上,西南联大坚持学术标准,自觉抵制教育部的干涉。联大的抵制行动集中表现在学系设置和课程设置上。1939年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统一学系的名称与设置,原则上禁止两个以上的学门合成一个系,如确有必要须报经教育部核定。①《教育部关于大学及独立学院院系名称设置的训令》,王学珍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38页。西南联大当时的学系设置与教育部的规定尚存在距离,尤其是哲学心理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都是由两个以上的学门合并组成。但是,西南联大并未一味迎合教育部的要求,反而以三校的历史和设备为由决定暂时维持原状。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于院系名称的呈文》(1939年9月23日),王学珍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37页。直到1940年,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再加上历史学和社会学确实相差甚远,校务会议才将历史社会学系分成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系。③《关于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学及社会学两系的呈文》(1940年6月10日),王学珍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在课程设置问题上,西南联大的抵制行动更为明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教育部多次谋求统一高等教育课程,但是直到抗战爆发前,教育部仍未完成这一任务。④广少奎:《重振与衰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272页。1938年,教育部又启动统一大学课程的工作。当年9月,教育部出台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课目表》。教育部此举遭到了西南联大的强烈反对。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将《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略加删改抄送教育部。该函从大学多元发展、教育部权能不分、教材的稳定性、教授地位与教学自由、教育部官员的德行等五个方面质疑了教育部统一大学课程设置的举措。⑤《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1940年6月10日),王学珍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在西南联大的抵制和呼吁之下,教育部最终默许了高校变通执行有关教学工作的各项训令,实际上就是放弃统一高校课程。此外,西南联大能够将政治与学术区分开来,分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教师和学生往往能够统一到学术自由的旗帜之下。
三、威权体制下如何实践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尽管威权体制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相冲突,但是西南联大的历史表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可以在威权体制的夹缝中生存。事实上,德国的历史早已证明这一点。德国统一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德国的学术自由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德国的政体实为开明君主专制。质言之,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完全可以在威权体制的缝隙中生存。那么,西南联大为何能够生存下来?有学者将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氛围归结为特殊历史情境的产物。例如,知识分子犬儒主义尚未形成;政府无力干预,自治传统得以延续;开明的地方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作用。⑥西南联大的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实现可以归结为如下因素:知识分子犬儒主义尚未形成;政府无力干预,自治传统得以延续;开明的地方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作用。参见阳荣威、梁建芬:《西南联大教育成就的历史情境分析》,《大学教育科学》2016年第3期。这样一种归纳不无道理。但是,仅仅把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归结于外部因素,忽视威权体制本身存在容纳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妥当。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威权体制的哪些内部因素使得其能够允许一定限度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存在。
首先,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存在取决于其在政治目的上与威权体制的一致性。政治生活就是不断地进行价值选择,而价值选择的最终依规就是形成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目的一旦形成就会对政治生活的性质、政治手段的选择、政治的根本任务和政治秩序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⑦彭定光:《论政治目的的道德定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具有公共属性和公共价值,难免卷入政治生活之中。无论在德国还是美国,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实际上都承担着一定的政治功能。1806年,普鲁士在战争中败给了法国,民族危机迫使普鲁士进行改革。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主张通过举办新大学来振兴国家,反对国家干预大学。①冒荣:《远去的彼岸星空——德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在德国,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承担着复兴大学、复兴民族的政治任务。即便在美国,传统观点将学术自由视为一种特殊的言论自由,其政治目的在于促进民主自治。也有学者将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区分开来,认为言论自由服务于民主正当,而学术自由服务于民主胜任。②罗伯特·波斯特:《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左亦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60页。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承认学术自由存在政治功能。只不过在威权体制下,这种目的上的一致性尤其重要。质言之,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政治目的符合威权体制确立的政治目的时,它们才会有机会在威权体制下生存下来。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之所以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政治目的上与威权体制一致。
事实上,执掌西南联大的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都承认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具有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政治目的。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一文将中西方大学的目的归于“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所遂生之道”③《大学一解》,王学珍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具体说来包括“明明德”和“新民”二者,“明明德”指认识自我的功能,“新民”指大学的政治功能。大学的“新民”目的的实现离不开“自由探讨之风气”,即学术自由。在梅贻琦那里,学术自由是大学实现“新民”这一政治目的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新文化和进步的泉源。④李硕豪:《梅贻琦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蒋梦麟也认为教育是一门利群的科学,即儒家的“明德新民”“己欲立而立”。社会和国家的进步依赖于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而教育的准则是学术。⑤张翼星:《蒋梦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现代大学教育》2011年第6期。蒋梦麟一方面强调学术具有高于政治的永恒价值,学术不应涉足政治,保持一定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承认教育和学术承担着政治功能,教育和学术在政治是非和正义标准问题上责无旁贷。张伯苓似乎并未论述过学术自由的理念,但是其办学实践坚持着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⑥高建国、晏祥辉、李杰:《西南联大“三常委”办学理念差异与契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张伯苓在办学的过程中亦坚持了公共精神,即以培养现代公民作为办学的目标。⑦宋秋蓉:《私立时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公共精神的研究》,《江苏高教》2012年第4期。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的观念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救国论和教育独立论思潮,教育独立是手段,教育救国是目的。通过教育培养新民、改造国家和社会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主张本质上都是“救亡”,所以威权体制能够容忍西南联大的自治与学术自由。
其次,西南联大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存在取决于威权体制本身所必不可少的执行弹性。自秦汉以来,“中央权威一统而治”是中国国家政权组织的基本特点。1840年以后,这种政体在内忧外患背景之下逐渐瓦解。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国家四分五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采取战争和政治等多种手段基本上恢复了“中央权威一统而治”的局面。受庞大的治理规模的拖累,“中央权威一统而治”的政体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央统辖权和地方治理权之间的紧张关系。⑧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8-20页。权力和资源越往中央集中,各地区和各部门有效治理的能力越低;各地区和各部门的治理权限越大,对中央权威的威胁也越大。为解决此种张力,中央权威一方面强调决策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明确授予或默许各地方和各部门具有执行的灵活性。此种执行灵活性以中央权威和决策统一性为前提。如果我们把高等院校视作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基层权力组织,那么前述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分析威权体制下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事实上,西南联大作为国立大学当然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基层权力组织。一旦我们运用决策统一性和执行灵活性这对概念分析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我们就会发现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法令,内容涉及教育宗旨、大学组织、教员资格、学分制、课程设置等多方面,⑨相关法案参见骆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立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198页。所谓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实质上不过是中央政府授予或默许的西南联大执行前述法令的灵活性。例如上文提到的学系设立问题和课程设置问题,教育部或通过立法明确授予西南联大等高校自主决定的空间,或默许西南联大等高校灵活变通教育部出台的统一课程。除了颁布一套严密的法律,中央政府还经常发布许多行政命令,要求西南联大等高校执行。对于这些行政命令,西南联大有时也会主动灵活地执行。例如,1935年,教育部发文要求各级学校将蒋介石所言的“礼义廉耻”定为校训,但是1938年11月26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仍然将校训定为“刚毅坚卓”①第九十五次会议,第74-75页。,只不过西南联大表面上不行文张扬“刚毅坚卓”之校训。②高建国、晏祥辉、李杰:《西南联大“三常委”办学理念差异与契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再次,中央政府的自我克制(权力的自我克制)是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能够在威权体制的夹缝中生存的另一个内部因素。在威权体制之下,尽管各地方或各部门在执行上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中央政府有权随时限缩或取消执行上的灵活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会任性妄为,在许多争议的处理上中央政府通常会自我克制。原因是,权力天然具有界限,就像大炮和望远镜一样。③“在一定的限度内,你把它(大炮)造得越长,它的威力就越大,一旦你超过这个限度,它的威力就会下降。”“在一定的限度内,你把它(望远镜)造得越大,它就越有力;超过了这个界限,不可抗拒的自然就会使你希望他完美的一切努力违背你的初衷。”梅斯特:《主权之研究》,《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冯克利、杨日鹏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页。“为了保存自己,它(权力)必须自我克制,必须永远使自己与那个界限保持距离,它最极端的努力一旦达到这个界限,就会导致自身的毁灭。”④梅斯特:《主权之研究》,《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冯克利、杨日鹏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页。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中央政府有时会自我克制,避免过度干涉各地方和各部门。中央政府的这种自我克制在西南联大的校歌审定案和课程设置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1939年7月11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校歌,并呈报教育部。令人吃惊的是1939年12月2日,教育部突然发出训令,认为西南联大校歌“系西洋成曲,似未能表现校歌特具之精神,令即行作曲配词……”⑤黄恩德主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内迁院校在云南》(第5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此训令受到梅贻琦的批评。后来,教育部似乎意识到训令的荒唐之处,遂不再坚持执行此项训令。事实上,权力的自我克制这个因素很难说是威权体制所特有的。自我克制在所有的权力现象中都可以找到足迹,民主政体中的权力也会存在自我克制的现象。本文之所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加以讨论,是因为权力的自我克制对于威权体制以及威权体制之下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尤其重要。在威权体制之下,如果权力一旦脱缰,不再自我克制,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坍塌。
四、结论
通过讨论西南联大的自治、学术自由与威权体制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与威权体制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仍然可以在威权体制的夹缝中生存。第二,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存在复杂性和多维性,我们不能将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作为想象的异邦。第三,从威权体制的内部视角来看,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要在威权体制下生存,依赖于如下三个因素:大学的政治目的与威权体制的政治目的一致、威权体制明确授予或者默许的执行弹性、威权体制的自我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