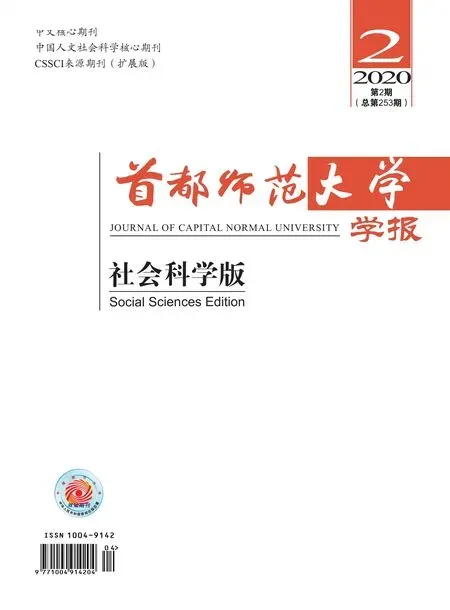“梅兰芳现象”与20世纪中国戏曲新美学
施旭升 徐 晨
一、从“梅兰芳现象”谈起
毋庸置疑,称梅兰芳(1894—1961)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应该并不为过。梅兰芳不仅以其杰出的舞台艺术创造而成为20世纪中国戏曲的一个表征符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的“梅兰芳现象”,其意义与影响甚至已明显超越了戏曲艺术本身,而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性且有着世界意义的美学与文化现象。可以说,梅兰芳不仅代表了一个戏曲时代,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学风范、一种艺术精神。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实践,正是以其典雅蕴藉的古典风味以及对于“古典”的传承与守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
确实,自20世纪20年代“四大名旦”声名鹊起以来,梅兰芳就成为话题式人物,成为人们不断谈论的中心。即使在梅兰芳去世之后(“文革”时期除外),“梅兰芳现象”的影响热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提升,更是成为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换言之,对于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来说,“梅兰芳现象”肯定是绕不过去的。虽然,历史上的梅兰芳曾经被太多的媒体以及各色人等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言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梅兰芳研究始于五四时期乃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是梅迷及梅党乃至梨园内外广泛的热捧,另一方面是新文化人士言辞的激烈批判以及随后几代戏剧学者的不断反思。特别是随着访日访美访苏的进程的展开,梅兰芳的世界性影响逐渐形成,在东西方戏剧的全球视野中来审视梅兰芳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向。
问题是:作为一个“世纪现象”的梅兰芳,不仅曾经因为其杰出的艺术成就而声名远扬,同时也因为其身份和反响而被贴上了太多的标签,引起了国内外学界持久的热议甚至带来诸多的误解和曲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随着梅兰芳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关于“梅兰芳现象”不仅曾被广泛地加以讨论,而且形成了某些似是而非的陈说,如所谓“梅兰芳表演体系”①关于“梅兰芳表演体系”,又被称为“梅兰芳(戏剧)体系”,而与斯坦尼体系、布莱希特体系相提并论,被称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此一说法流传甚广,且似是而非。之类,既影响广泛,更以讹传讹。所以,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关于梅兰芳的陈说,究竟被遮蔽了什么以及放大了什么?“梅兰芳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梅兰芳舞台艺术的美学意义究竟何在?如何在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的坐标系上来定位梅兰芳?诸如此类,也就成为理解和把握梅兰芳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21世纪的今天,邹元江教授更是以一部《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对于梅兰芳的表演美学体系及其相关界域进行了具体全面的理论阐释。该书以23章篇幅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最后得出了23项结论。这些结论中的大部分都显示出邹元江教授对于梅兰芳研究中的诸多陈见的积极反思,但也有些结论却显得有些勉强,值得商榷。譬如,邹元江对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精神”的批评,认为“实际上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美学思想泛西方化、泛斯坦尼化的产物”②邹元江:《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84页。。其实,细究起来,此一结论本身就大有偏颇。因为这不仅关乎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美学特质的理解,更关乎对于梅兰芳所身处的“特定历史时代”的美学精神的把握,所以也就有必要对其加以进一步讨论。而这种讨论如果离开了梅兰芳及其被言说的时代背景与其文化语境,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回答清楚的。恰如邓晓芒在评述邹元江的结论时所指出的:“梅兰芳的成功与其说是受到了西方艺术理论的影响,不如说是实现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现象学还原’。”③邓晓芒:《中西戏剧理论的“错位”与“化用”——读邹元江〈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5期。窃以为,这种“还原”并非只是观念上的,只有努力“还原”20世纪上半叶梅兰芳舞台实践的艺术现场,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给予梅兰芳以准确的历史定位,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精神实质,进而才能准确理解梅兰芳在20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的美学价值。
二、如何理解“梅兰芳表演体系”?
邹元江教授的梅兰芳研究是从对于“梅兰芳表演体系”④邹元江将其转述为“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进行美学阐释。其实,无论“梅兰芳戏剧体系”还是“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都是以梅兰芳“表演”艺术实践为中心,当属无疑。的质疑开始的。确实,从梅兰芳半个多世纪的舞台表演艺术实践来看,究竟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梅兰芳表演体系”?人们又是如何理解“梅兰芳表演体系”?诸如此类,也就成为人们首先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确实,提起“梅兰芳表演体系”,人们一般都首先想到黄佐临。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黄佐临做了一个“漫谈‘戏剧观’”的发言,指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兰芳和布莱希特代表着各不相同的“戏剧观”。其发言后经整理在1962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才在国内出现了所谓“梅兰芳戏剧观”的说法;此后黄佐临为英文版《京剧与梅兰芳》一书作《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一文①黄佐临:《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梅绍武译,《人民日报》1981年8月12日。,明确将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布莱希特的戏剧观相比较,但黄佐临本人似乎一直并未明确却也未曾否认“梅兰芳表演体系”一说;到了1982年,“梅兰芳戏剧观”经上海戏剧学院青年学者孙惠柱改造而成为“梅兰芳表演体系”,并将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相并列而提出了所谓“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说。而此说一出,竟然不胫而走,且引发了诸多争议。然而,事实上,因为对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研究来说,此一“梅兰芳表演体系”说虽流传甚广,却颇多附会。②参见傅谨:《“三大戏剧体系”的政治与文化隐喻》,《京剧学前沿(续篇)》,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195页。
这里,问题的实质也许不在于梅兰芳有没有“体系”以及对于所谓的“梅兰芳表演体系”有着怎样的理解与曲解。因为不管贴上什么标签,都无损于梅兰芳舞台艺术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因而,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如何给予梅兰芳以准确的历史定位?究竟怎样理解和评价梅兰芳舞台艺术的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以及如何看待梅兰芳的艺术实践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梅兰芳的戏剧美学观念是如何在梅兰芳的舞台实践中得以具体体现的?是否真的如邹元江所言完全是为了“迎合斯坦尼体系”而变得“混杂”且“不清晰”的呢?如果说,理解这一切,离不开对于梅兰芳的戏剧观念与实践进行历史还原的话,那么,对于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实践本身进行正本清源的梳理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邹元江对于所谓的“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的系统研究确实是有历史还原与理论澄清的价值的。但是,将梅兰芳所代表的表演艺术视为一个“已成”的实体,而不是一个在具体历史语境当中不断变化且不断完善的艺术经验体系;在看到了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外源性影响的同时,却又把这种影响仅仅视之为“西方的”理论“误导”所致,则成为邹元江的一个明显的思维误区。
与邹元江过分强调“西方的”理论对于梅兰芳的“误导”不一样,理解“梅兰芳表演体系”其实还有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传统/现代”的维度。它与“东方/西方”的维度一起,正好构成了一个理解和定位梅兰芳舞台表演艺术的一个直角坐标系。如果说,“东方/西方”是坐标系的一条横轴,那么,“传统/现代”就是该坐标系的一条纵轴;而这个坐标系的原点就是作为梅兰芳艺术起点的20世纪初。
晚清时代,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③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1872),转引自秦晖:《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确实,在一个新旧尖锐对立的时代,作为梅兰芳艺术起点的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出现巨大转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随之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20世纪更是中国的一个“不断革命”的世纪。随着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的开展,古老的中国戏剧也经历了一个急速的以革命化、功利化为导向的现代化的历程。受此影响,京剧在民国初期以最快速度掀起大规模“改良”热潮,及时跳出清末京剧藩篱,实现了从艺术审美、剧本创作、表演形式到剧团管理、观众组织、媒体宣传等方面的全面更新,形成了民国京剧的新传统,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从而,原本属于市民娱乐层面的戏曲也就难免被裹挟进入这一历史进程当中。创作历程几乎贯穿半个多世纪的梅兰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的更新和立场的选择,也便成为我们理解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及其美学精神的重要前提。
梅兰芳舞台艺术实践的自觉应该是始于1913年的上海丹桂第一台的演出,他自己就认为是其“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①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何以言之?因为,梅兰芳1913年的上海演出不止是一次简单地走码头,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他看到上海观众喜欢“唱做并重,新颖生动”,立即新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加演。他深深意识到“上海舞台上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新的舞台、新的观众、新的戏剧观念和新式的灯光装置,等等,无不刺激着年轻的梅兰芳。特别是梅兰芳在1914年11月至1915年1月的第二次赴沪演出,更加坚定了他要“改良”京剧的决心。如果说,此前梅兰芳更多的是接受严格的古典的训练,那么,此后的梅兰芳则更主要的当是开启了自己真正的艺术探索。于是,在继续习演昆曲的同时,先是《孽海波澜》《一缕麻》《邓霞姑》《宦海潮》等“时装戏”的编演,然而接着则是《洛神》《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千金一笑》等“古装戏”的新编。
关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体系的定性,把它归于“旧文化”的一端似乎无可置疑,然而从“传统/现代”的维度上来看,梅兰芳以其不断的趋新求变,表现出对于传统戏曲的改造;如果至此还把梅兰芳视为“‘旧文化’的范本”②傅谨:《梅兰芳与新文化》,《京剧学前沿(续篇)》,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第286页。,显然又是十分不妥当的。因为,事实上,梅兰芳不仅受欧阳予倩等编演“红楼戏”的影响,自己也早就明确意识到,只有跟上时代的变化,才能获得自身生存与艺术发展的空间。为此,他率先排演了大量的时装新戏、古装新戏,并对传统剧目做出大幅度加工改造。梅兰芳的“改良”迅速得到观众的热烈拥护,每出新戏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即使是激烈批判“旧戏”的傅斯年也曾在文中记述其亲眼目睹的场景说:“我有一天在三庆园听梅兰芳的《一缕麻》,几乎挤坏了,出来见大栅栏一带,人山人海,交通断绝,便高兴得了不得。”③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新青年》杂志五卷四期“戏剧改良专号”,1918年5月。
当然,作为“改良”先驱的梅兰芳,并不满足于为“新”而“新”。梅兰芳与他的智囊团(所谓“梅党”)尤其注重将新思想、新审美以及新的戏剧理论与其编演的新戏剧目相结合。如果说,他最初排演的时装新戏还是囿于某种“写实”的范畴,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以京剧面目出现的“社会问题剧”,那么,最晚到20世纪20年代初,梅兰芳就已经注意到了西方“非写实”的唯美主义戏剧,并且有意识地通过其一系列古装新戏的编演做出探索,旨在创造出一种抽象与理想的、超越现实生活的东方唯美主义戏剧。从而,随着其“时装新戏”的息演,梅兰芳转而完全专注于“古装新戏”的编演,直至他生命中最后编演的《穆桂英挂帅》。梅兰芳“从传统到现代”的表演艺术实践终于止步于激进的“现代”思潮的门槛之前。
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之后,梅兰芳几乎成为一个特例,他除了被允许继续担纲私营性质的“梅兰芳剧团”的主演,同时还成为主持新中国“戏改”运动的主要官员之一。这也使得梅兰芳难免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能积极投身其中。所以,“戏改”之后,除了那部重新编演的《穆桂英挂帅》,梅兰芳可选择的剧目却越来越少。事实上,自“三并举”的提出,与“传统戏”渐趋萎缩相一致,加大“现代戏”及“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力度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特别是在梅兰芳去世之后,1963年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④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界新年联欢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以至文革中江青主导的“样板戏”的推出,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戏曲的古典美学精神就已被彻底荡涤,或者也可以说,“现代戏”的一枝独秀已然促成了中国戏曲古典美学的终结。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虽然戏曲舞台上很快有了传统戏的恢复,但是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所代表的古典美学精神却与新的时代已渐行渐远。
故而,就20世纪中国戏曲而言,所谓“梅兰芳表演体系”,并非只是一个指代中国传统戏曲体系的泛泛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有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具体的美学内涵的表演艺术体系。它不仅关乎中国戏曲的一般性原理,更体现出梅兰芳和他的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精神和美学内涵,包括其中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将“梅兰芳表演体系”和差不多同时代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简单地相提并论,还不如将梅兰芳置于20世纪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来审视其独特的文化与审美的内涵,以及其时代的变迁,由此可以揭示出“梅兰芳表演体系”与斯氏及布氏的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戏剧体系的本质上的差异。
三、梅兰芳:“新古典”的生成
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所体现的文化姿态和审美立场来看,梅兰芳既是东方的、现实的、伦理的、民间的,同时也是超越的、灵性的、雅化的。其经典雅致的艺术追求,从激进的现代化的立场来看,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在“东方/西方”的维度上,梅兰芳所坚守的仍是一种与西方现代艺术趣味相对应的中国戏曲的“古典”美学风范。
然而,在趋新求变的“现代”思潮的鼓荡之下,梅兰芳的坚守确实不再是那份纯粹的“古典”,而是一种基于传统之上的创新,使它成为一种新的“古典”。这也就是梅党所谓“有声必歌、无动不舞”①齐如山:《国剧的原则》,《齐如山全集》第三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464页。的中国“理想优美之剧”。这也与其后梅兰芳“移步不换形”的戏曲改革观的形成是一脉相承的。
从梅兰芳的艺术血统及家族渊源来看,他无疑属于传统的、民间的;然而,梅兰芳的艺术又绝非传统与民间所能界定。缀玉轩的“梅党”确实不同于具有启蒙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而是一帮有着古旧气息的文人雅士,以及实业家、银行家。虽然他们已不再着长袍马褂,但是“品梅”成为他们共同的趣味与爱好。可以说,他们当中虽有像齐如山等那样受到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但是他们总体上的趣味还是相当守旧的。梅兰芳虽然有访美访苏演出且大获成功,但是梅兰芳的主体观众却仍然是中国大众。梅兰芳终其一生所坚守的还是其民间的姿态和传统的立场。即使是1949年之后,梅兰芳虽被新中国的体制所吸纳,但是他最终并没有全部融入体制,仍有其一种民间的身份和一份传统的血脉。即使在激进的革新思潮鼓荡之下,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创造当中,依然有着像《三娘教子》里所宣扬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人情伦理,也依然有着《宇宙锋》《生死恨》当中所呈现的现代悲剧美感的渗透。所以,与其强调梅兰芳的民间性,不如正视梅兰芳的古典性;与其强调梅兰芳“对于西方戏剧观念的迎合”,不如揭示梅兰芳对于传统的坚守。
梅兰芳“新古典”的创构究竟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有论者指出:“古典”乃是“指以经典作品为典范、强调审美理想的继承性和艺术价值的恒定性的艺术观念。古典艺术精神是一个民族文艺传统的精髓,对于理解传统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②高小康:《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也就是说,“古典”显然不是自封的,而是源自于传统。或者说,“古典”的精神必然是与某种深厚的传统结合在一起,而体现出“审美理想的继承性和艺术价值的恒定性”。这种“新古典”无疑主要体现在梅兰芳的新编戏的创作当中。他曾在介绍自己的新编戏创作过程时说:
我排新戏的步骤,向来先由几位爱好戏剧的外界朋友,随时留意把比较有点意义,可以编制剧本的材料,收集好了;再由一位担任起草,分场打提纲,先大略地写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共同商讨。有的对于掌握剧本的内容意识是素有心得的,有的对于音韵方面是擅长的,有的熟悉戏里的关子和穿插,能在新戏里善于采择运用老戏的优点的,有的对于服装的设计、颜色的配合、道具的式样这几方面,都能够推陈出新,长于变化的;我们是用集体编制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个试探性的工作的。我们那时在一个新剧本起草以后,讨论的情形,倒有点像现在的座谈会。在座的都可以发表意见,而且常常会很不客气地激辩起来,有时还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他们没有丝毫成见,都是为了想要找出一个最后的真理来搞好这出新的剧本。经过这样几次的修改,应该加的也添上了,应该减的也勾掉了。这才算是在我初次演出以前的一个暂时的定本。演出以后,陆续还要修改。同时我们也约请多位本界有经验的老前辈来参加讨论,得到他们不少宝贵的意见。①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梅兰芳全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278页。
虽然是新编,却既能“善于采择运用老戏的优点”,又“能够推陈出新,长于变化”,定本演出之后,还要不断地进行“修改”。新编创作依然遵循的是传统的体制,推崇的却是全新的风貌,古典的韵味也就自然蕴含其中。正如许姬传所言,梅兰芳一系列新编创作,从《西施》《洛神》到《生死恨》《凤还巢》,它们“在唱腔、音乐、表演、服装、舞台美术各个方面,都给人以清新瑰丽的感觉,就证实了他的创作方法是步步升华,光景常新的”②许姬传:《许姬传艺坛漫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3页。。
所以,梅兰芳的“新古典”更意味着一种典范性的品位、风貌、格调和境界的创造。这也合乎王国维之所谓“古雅”:古典的韵味当中,必然包含着风情和雅致,既意味深长,又常品常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一种“新古典”的美学精神,既不是一个既定的对象实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和教条。从梅兰芳所传承的经典剧目到诸多的梅派新编剧目,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新古典”的传承与重构。它既是传统的延续,更是一种“新”的创建。可以说,以1913年梅兰芳的上海演出为起点,自此以往,梅兰芳舞台艺术无不显示出一种传统的自觉与再发现。
确实,“古典”之于“现代”,不是一种简单的隔空“对话”,也不是纯然以“现代”取代“古典”,而是以“古典”的神韵为现代人提供一种血脉、一种审美范式,甚至具有某种精神“原型”的意味;或者说,这种“古典”之于现实的审美体验,犹如提供一种“格式塔质”,它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从而,与其说这种“古典”是与现代化或时尚化相对立的,还不如说是在现代性追求的时代背景下一种古典情怀的回味与模式的重构。它既是梅兰芳自我选择的结果,同时又是一种不断“他者化”的过程。换言之,是由一个与梅兰芳的自我相对应的“他者”来推动的。这种“再发现”当然不止一次,而是数次;不是纯然被动呈现的产物,而是梅兰芳主动选择的结果。这与邹元江所谓梅兰芳“对于西方戏剧观念的迎合”显然并不是一回事。
从一种“新古典”的生成建构来看“梅兰芳现象”,制约着梅兰芳艺术表现的社会性因素,无非两个方面:市场的和政府的。在时间的区隔上,以1949年为界,构成了梅兰芳艺术表现的两个阶段。如果说,1949年之前,梅兰芳主要还是受制于市场,那么,1949年之后的梅兰芳,则主要倾向于新政府新社会的感召而更明显地热衷于政治立场和思想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梅兰芳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存在,甚至也不免有其矛盾之处。也许,梅兰芳本人并不自觉,甚至常常不由自主或者言不由衷;其艺术表现也呈现出多重话语的特性:不仅常常言其所非言,而且难免是其所非是。事实上,梅兰芳的访美之后所获得的“博士帽”乃至晚年的“体制化”,显然都不属于梅的真正的身份认同。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都是一种“他者”立场上对于梅兰芳的身份型构。因而大体上可以认定这些基本上都是外在的,而不是自发的;是社会政治赋予其光环,而不尽然属于梅兰芳的自觉的艺术旨趣和精神追求。故而,梅兰芳的艺术表现,从“移步不换形”的戏改观念的被批评,到《穆桂英挂帅》中的“中规”与“合辙”,也都可以说是梅兰芳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回归“新古典”的结果。
四、20世纪中国戏曲“新美学”的建构
再回到邹元江所讨论的议题上来,如果就像邹元江所言:“梅兰芳走向世界的历程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戏曲魅力的历程。”①邹元江:《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那么,梅兰芳的意义,就仅仅是一种博物馆式的存在么?如果我们承认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那么,事实上它就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且改造了中国戏曲的古典美学精神,而且更创造出了20世纪中国戏曲的新美学。
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何以能够代表20世纪中国戏曲的新美学?固然,无论是欧阳予倩称梅兰芳是“美的创造者”②欧阳予倩:《梅兰芳——美的创造者》,《梅兰芳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还是叶秀山所言,梅派艺术是一种“典型的美”③叶秀山:《古中国的歌:叶秀山论京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对于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美学特质的概括显然都还是语焉未详,只能属于概而论之。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将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置于“传统/现代”与“东方/西方”所构成的二维坐标系中来加以审视。
在“传统/现代”的维度上,可以说,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所体现的“新古典”精神特质,既具有典范性,又具有时代性。换言之,它固然属于过去的那个时代,然而却只有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急遽的现代化进程的“镜像”当中才得以显现。而在“东方/西方”的维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在“现代”及“西方”的镜像之中,梅兰芳在其艺术实践中才逐渐显示出中国戏曲的古典美学的品性与特质。离开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离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语境,其实是很难理解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品格及其意义的。
梅兰芳的艺术实践究竟体现出怎样的20世纪中国戏曲“新美学”的建构?如前所述,梅兰芳舞台艺术实践,不仅意味着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终结,而且也体现出一种“新古典”的生成。虽然,梅兰芳的著述未必建构起一个严密的美学理论体系,但是,梅兰芳的舞台表演艺术实践则无疑代表了在中国戏曲古典美学传承的基础上,伴随着西方戏剧美学观念的传入,创造出一种以“新古典”舞台样式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的新美学。
具体说来,这种20世纪中国戏曲“新美学”的实践,大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20世纪戏曲审美形态的嬗递,戏曲审美逐渐实现了从“听戏”到“看戏”的演进。对于戏曲的观赏,传统习称“听戏”;20世纪以来,人们则逐渐习惯于称为“看戏”。所以者何?原因就在于20世纪的中国戏曲审美,经历了一个从“听戏”到“看戏”的历史转变,而且这不止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方式上的转变,它更代表着20世纪戏曲表演与观赏的美学精神的转变。
所谓“听戏”,就是观众以听为中心。“听戏”是和“唱戏”相关的。戏曲“四功”(唱念做打)当中,尤以唱念为主,做打次之。戏谚有所谓“千斤念白四两唱”,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戏曲讲究载歌载舞,追求歌舞化,突出“以歌舞演故事”。戏曲表演当中,好的唱段,往往绕梁三日、余音不绝。而热衷于“听戏”的戏迷,泡在戏园子里,自然而然耳濡目染。可以说,直到20世纪初,“唱戏”/“听戏”成为中国戏曲审美的基本风貌。
但是,20世纪初以来,随着戏曲改良的兴起,逐渐实现了从“听戏”到“看戏”的转向。所谓“看戏”,注重的是戏曲艺术的剧场整体的呈现。看戏的人(观众),已然将注意力从“听戏”只专注于唱腔转移到观看舞台整体表现。从剧情戏理到身段场面,从服饰化妆到灯光布景,无疑较之“听戏”阶段,引起观众更多的关注。
促成戏曲审美这一转向的,无疑是与清末以来的“西风东渐”有关。20世纪的中国戏曲,从舞台到表演,历经了太多的变化。特别是海派京剧的出现,和相对恪守传统的京朝派京剧相比,不仅有着新的更为靓丽的舞台样式,有了更多的灯光布景、服饰化妆,而且也促成了戏曲美轮美奂的视听一体的审美效果。
梅兰芳艺术实践历经了戏曲从“听戏”到“看戏”转变。梅兰芳一改以唱为主的传统青衣的表演方式,融汇了花旦、武旦等戏曲行当的特色而独创“花衫”行当,使得青衣的表演既好听又好看。特别是梅兰芳的戏曲新编创作,不仅提升了剧中歌舞的表现力,更是在剧情构造、剧中人物的表情动作、具体情境中的个性表达等方面都大大提升了戏曲舞台的美听美视的效果。
其二是20世纪戏曲美学精神的演变,实现了从“古典”到“新古典”的转变。确实,20世纪以来的中国戏曲,已远非只是一副“古典”的面孔。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戏曲的“古典的,传统的”美学风貌,似乎戏曲舞台美学都是“虚拟性、程式性、写意性”的;戏曲就是“歌舞演故事”,戏曲表演总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长期以来,秉持这种“古典”式的戏曲观念,人们的认知已然形成了关于戏曲的诸多刻板印象。
其实,20世纪初以来,以京剧及各地方戏的兴盛为代表,中国戏曲的古典形态及其美学原则似乎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终结”状态;而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相一致,戏曲新的美学原则也势必随之兴起。在不断趋新求变的艺术实践面前,关于“古典”戏曲的一些刻板印象就难免被打破。一方面,戏曲传统的审美惯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20世纪的戏曲“革新”却又总是占有着主导地位。一方面,“京朝派”的京剧历来被视为正宗;而另一方面,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却又造就出被称为“海派京剧”的“新京剧”的繁荣。
正是在这一历史趋势之下,20世纪中国戏曲新美学得以乘势而起。归结起来,这种戏曲新美学的兴起大体不外乎两种路径:一种是“弃旧从新”,是断裂式的;一种是“整旧如旧”,是延续式的。前者与激进的戏曲“现代化”的实践相伴随,后者则是基于一种渐进式的戏曲改良之路。如果说,“弃旧从新”最终导致“样板戏”的出笼,那么,“整旧如旧”就成为梅兰芳舞台艺术实践原则的重要体现。
可以说,正是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实践为传统戏曲在20世纪的趋新应变带来了一种“新古典”戏曲的生机,并伴之以戏曲新美学的兴起。它根植于古典戏曲美学的土壤,却又在中国20世纪的求新求变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土壤中艰难求生;它深受欧风美雨的侵袭,而又无意中得其滋养,形成其特殊的“新古典”的艺术特质。
与梅兰芳“新古典”的美学原则截然相反,“样板戏”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数:它以现代意识相号召,其中充斥着革命精神;不破不立,破字当头;与艺术表现中个体人格的消隐相一致,舞台的阶级属性得以强化。特别是使得其中“三突出”“高大全”之类的创作理念,成为文革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典型的美学原则和表现符号。
新世纪以来,戏曲(特别是昆曲和京剧)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危机。一方面,戏曲需要理论上的美学自觉,在恪守传统的同时,需要走出一条“新古典”的创造之路;另一方面,激进的功利化的价值诉求则又难免使得戏曲在不断的趋新求变当中走向消亡。如今,梅兰芳的艺术实践和美学追求是否还能给我们提供一副拯救的良方,我们确实需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