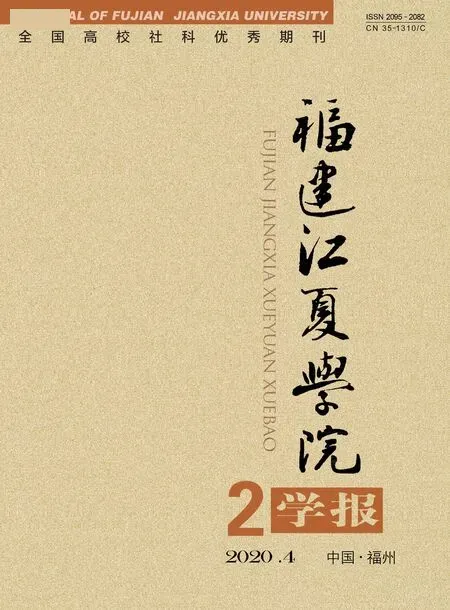论物权内容法定
郑永宽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我国学者多将物权法定原则解析为类型法定与内容法定两方面。①也有学者将物权法定原则解析为包含类型强制与类型固定两方面,参见[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但很显然,该规定过于简略,在类型法定外,物权的内容不可能完全由法律规定。②我国的规定与日本、韩国的相关规定在措辞上略有不同,如《日本民法典》第175条规定:“物权,除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者外,不得创设。”该规定只是宽泛地要求不得由当事人任意创设物权。地役权的内容、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抵押权担保的范围等,均属于当事人可得约定的物权内容,不胜枚举。内容法定事实上只是一个框架,只是在轮廓上须由法律强制性地予以确定。③[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德国有学者认为,所谓不得创设,原来仅指物权的种类,即所谓类型强制,后来又有学者认为,物权内容原则上也不得与法律规定相抵触,而产生另一个类型固定的要求。但实际上,类型即决定内容,类型强制应即包含类型固定,此一区分相当勉强。转引自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再思考——从民事财产法的发展与经济观点分析》,载于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而在德国学界,人们通常将该原则表述为“物权类型法定原则”。参见[德]沃尔夫冈·维甘德:《物权类型法定原则——关于一个重要民法原理的产生及其意义》,迟颖译,王洪亮校,载于张双根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2006年第2卷。由此,在对每一种物权的本质性的主要内容强制规定之外,事实上为当事人的内容合意仍保留了一定的自治通道。[1]问题是,当事人创设物权内容的自治空间有多大,即哪些内容允许当事人任意约定,哪些内容须遵循法律的强制规定。该问题可细分为二:其一,“法定”的物权内容是否一律不得变更;其二,物权内容的约定是否有界限。为使物权法定原则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并保持法律制度本身的稳定性,笔者认为,对于物权内容法定的要求,应采用从宽解释的方法,赋予当事人更大的创设空间。
二、物权法定内容变更或约定的基本前提:可得公示
在德国法上,物权类型法定原则的发展形成涉及到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以便进一步划清物权法与债权法的界限以及强调它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物权债权划分的论述中,物权类型的封闭性当然被作为前提条件,而且进一步迫切地警告预防“债权法融合到物权法中”,因为这将“极大地损害轮廓的清晰,概念的精确,以及破坏已经确定的并且条理清晰的体系”[2]。时至今日,对于物权法定原则的阐述理解,仍须以物权债权二元划分的背景为前提。
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理据,笔者曾撰文指出,从物权的对世权属性及物权交易中对于交易安全与便捷价值的追求,均可推知物权的公示要求。然公示的技术与能力有限,在坚持物权债权二元划分仍不可废弃的语境中,物权的自由创设因物权公示之不可能而不可能。所以说,为使物权的公示简单易行,不可在物权自由之下因当事人的任意而肆意扩张物权的类型:反之,物权惟有法定,使其单纯化,始可达致公示的目的。[3]物权既已法定,且得公示,人人可得周知,乃得要求他人不得侵犯,物权之保护绝对性始可获得确保。而于交易中,则易于得知交易对象的内容,有助交易之迅速;复得避免不自知而取得有物权负担之标的物,故能确保交易之安全。④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关于物权法定主义的确立根据,论者还提出诸多主张,具体可参照[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6页;段匡:《德国、法国及日本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综上,物权的存在,均须公示;物权法定而非自由,亦因公示之所限。公示实乃物权之所以具有对世效力的技术前提。因此,在物权类型法定的限制下,探讨物权内容变更或约定的界限或范围,可得公示也就成为须满足的基本前提。
三、物权法定内容是否得变更
学理上,关于物权法定原则,一般认为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物权,既不能创设法律没有规定的物权,也不能创设与法定内容相异的物权。[4]19-20但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物权法定内容一律不得变更。除了明显允许当事人作“除外约定”的内容外⑤《物权法》中包含不少此类条文,其中部分可能构成物权内容,而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债权性约定。如第115条规定:“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16条第1款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192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其他内容是否均须强制遵循,仍值探究。
一般认为,较之于合同法,物权法更具强制色彩,但物权法作为私人间物权关系形成的基本规范,整体而言仍应属于自治法的定位。依苏永钦先生的见解,物权法规范多属于权限规范,而非行为规范。权限规范和行为规范最大的不同在于,还有没有自治的空间。物权立法规定的只是物权的内容,尤其是物权间的分际,而无意规范当事人的行为决定,立法者没有禁止当事人间依物权分际作进一步交易的必要。[5]86-92如《物权法》第89条规定建筑房屋不得妨碍相邻方房屋的通风、采光和日照,考虑到该规范无涉公益,如果相邻双方订立“出卖采光权”的契约或设定“不行使采光请求”的邻地利用权,应可生效。[5]89
物权法的自治法定位值得肯定。物权法定原则的确立,绝非旨在取代当事人物权意思的具体形成,立法者只是有意识地防范双方达成的协议随意转化为对第三人有效力的法律地位,所以立法者框定了物权的种类及各种物权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各种物权的客体、设立条件及公示要件等,以示物权之分际及功能目标之发挥要件。而除了涉及基本物权秩序构成及各种物权基本架构的内容外,《物权法》所规定的大量具体条款,除非涉及公益与基本人权,否则,不宜简单地认定属于强制性条款而一律不得变更。例如,《物权法》第158条规定:“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地役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若约定地役权的设立须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如此变更应该可以,因为法律规定登记为地役权设立的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当事人的约定并未突破该法定最低限度要求;相反,其提高了地役权的公示要求。再比如,当事人设立不动产抵押权时,约定转移抵押物的占有。尽管《物权法》第179条关于抵押权的界定揭示了“不转移抵押财产的占有”,但对于不动产抵押权而言,不动产客体、登记生效、担保功能等要素,才是其区别于其他物权的基本要素,不转移占有则只是满足抵押人就抵押物继续用益的价值需求。因此,若抵押权人为更好控制抵押物以免抵押物价值减损,约定转移抵押物占有似乎不能简单以突破常规或不利于物的利用而否认该约定的效力。⑥申卫星先生的观点与此不同,其认为转移标的物占有的抵押权,不受认可与保护。参见申卫星:“物权法定与私法自治——解读我国《物权法》的两把钥匙”,载于龙卫球、王文杰主编:《两岸民商法前沿——当前民商事理论创新与立法前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页。当然,此约定事实上并未涉及第三人,仅具有当事人间的相对效力,但该例子至少再次说明,物权内容“法定”,应尽可能作限缩解释。
司法实务中,可以以《物权法》第202条关于抵押权存续期间的规定为例。该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实践中,当事人可能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具体的抵押权存续期间,且在抵押权登记时一并将该期间登记公示。那么,法定内容的如此变更是否有效呢?我国司法裁判常常给出否定回答。⑦例如,重庆彭水支行与同人公司担保物权纠纷上诉案,参见朱凡主编:《案例导读:物权法及配套规定适用与解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405页;陆晓伟:《从物权法定主义看抵押期限约定的法律效力》,载http://china.findlaw.cn/fangdichan/fangdichanlunwen/fdclw/73128.html(访问日期:2016年10月4日)。但事实上,我国《物权法》只是在第5条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并未涉及违反该原则之法效。实践中,任何与法定内容不一致的约定,显然不应简单武断地基于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为由,一律认定为无效,否则,整部《物权法》将基本实同公法。就《物权法》第202条而言,该规定很难说涉及公益或基本物权秩序,其只是为一般性地避免抵押人所有物上之物权负担过于长久存在,或也为防范抵押权人利用其强势地位,迫使抵押人接受长期施加于其物之上的抵押权限制,如此而言,该规范应旨在保护抵押人,则至少在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间短于法定期间之情形,该约定是否仍简单基于违反法定内容而无效,不无商榷之余地。
此外,即使之前较一致认为属于法律强制性规范的“禁止流押、流质”规定,近来学理上质疑反思者也颇多。[6-8]比较法上,我国台湾地区就“禁止流押、流质”的规定也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⑧具体分析可参照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4-677页。所以说,即使不包含“允为除外约定”的措辞,物权“法定”条款也不尽然属于强制性规范,是否不得变更,须结合规范属性、所涉利益等因素具体把握,而不是想当然地认定为无效。
四、物权内容自由约定的界限
“物权法想要对每一种物权的‘内容’作出封闭规定,断无可能,它所能做的,充其量是对‘内容’进行轮廓式的规定。”[1]很显然,对于法无规定的很多方面内容,当事人当可形成物权合意。问题在于,当事人的物权内容约定,须遵循什么样的界限?
笔者认为,在法定内容之外,当事人的物权合意除须满足可公示的技术要求外,内容方面的限制在于不得违反具体物权的基本构造与功能。物权的基本构造决定了物权的性质、种类与功能发挥,当事人不得借物权内容的任意约定,突破物权的类型法定,并影响物权的功能发挥。例如,当事人之间的不动产赠与,并约定受赠人永远不得再处分该不动产,该约定内容能否经登记公示而具有物权效力呢?笔者认为,理解所有权的本质规定性,除了其自由属性外,也在于其永久性。尽管所有权人不必随时支配其物,但处分权能的永久限制,却使得受赠人取得的不再是所有权。因此,该约定已经突破所有权的基本构造,无法归属于任一法定物权类型,从而该物权内容约定无效。相反,若当事人约定且登记的只是受赠人在有限时间内不得处分不动产,则如同法律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处分抵押物,该约定应属有效。
五、结语:物权内容法定从宽解释适用的成本考量
前文已经说明,若欲使物权内容的变更或约定具有对世效力,而非仅仅在当事人间具有效力,内容的约定或法定内容的变更须经公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物权公示仍主要依赖动产占有与不动产登记。占有的公示方法虽简便易行,然其形式单一,不足以表征多样化与个别性的物权种类与内容,故其公示能力极其有限。⑨郑永宽:《物权法定主义再反思》,载于龙卫球、王文杰主编:《两岸民商法前沿——当前民商事理论创新与立法前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页。占有是一种产值极低的公示方法,占有能够公示的功能不仅有限,而且常常误导。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载于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张永健:《再访物权法定与自由之争议》,载于《交大法学》2014年第2期,第127页。相形之下,登记的公示方法则可具体表达与区别不同的物权种类与内容,具有较高的产能。因此,如果拟在物权类型法定的限制下,尽可能地挖掘物权内容合意的自治空间,公示要件的满足将只能依赖于登记来完成。这就意味着,物权内容的合意的适用范围基本仅局限于不动产物权,即如倡导物权自由最积极的苏永钦先生,也不得不妥协认为,不可登记物仍采物权法定。[9]
不动产物权内容的具体形成,在不违反社会基本物权秩序、物权基本结构功能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与基本人权的限度内,应当尽可能赋予当事人合意的自由。但此一般性的结论仍须应对如此的怀疑:不动产物权内容合意空间的扩大,是否将导致物权任意约定的泛滥,并因此极大增加非使用者成本与系统成本?
首先,必须明确,物权内容合意自由只是在物权类型法定背景下的有限自由,其须遵循的更多限制已如前文所述。以用益物权为例,我国当前用益物权共有四种,均存在于土地之上。用益物权的具体种类决定物权的基本内容与功能,无非是在土地上建造建筑物、从事农业耕作或为他人土地供作便宜使用。其中,以地役权的规定最具抽象性,留下最大的合意想象空间;至于其他用益物权,尽管当事人在物权内容具体化上享有适度的自治空间,但受物权具体类型及其功能的限制,且基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世俗化、理性化,当事人的物权内容任意约定不会泛滥化。如果法律适用中肯认物权内容自治空间的扩大化,只会导致物权内容任意约定的适量增加。
物权内容合意空间的扩大,可能确实会增加相应的外部化成本,包括非用户成本与系统成本。非用户成本主要有:为避免侵害他人物权所支出的估量成本以及为确认交易对象之物权内容而支出的估量成本。[10]由于物权内容约定受物权类型法定的限制,且约定内容限于不动产物权范围而须登记公示,所以,由此基本不会增加非用户的估量成本。至于系统成本,包括物权登载成本和其他相关法律机制成本[11],其中主要涉及登记机关“实质审查”物权约定内容是否“合法”,以及检视各种已登记内容间是否有冲突的成本,而当涉诉时,裁判者同样面临须检视物权内容约定是否“合法”而有效的工作。不可否认,物权内容法定从宽解释适用以支持自治空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增加系统成本,但只要当事人的任意约定不泛滥,这种成本增加就是有限的、可控的。相反,若以增加工作负担或裁判难度为由,主张在包含除外约定或指引性概括条款外,法定内容一律不得变更,当事人亦不得为内容约定,这无疑是不现实的,将使物权法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极大抑制物权合理秩序生成的有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