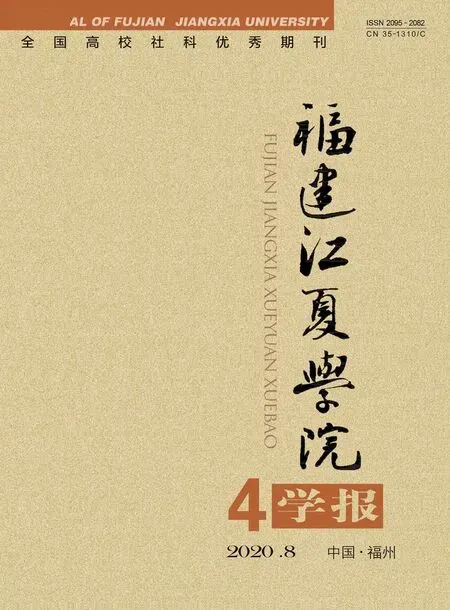《好了歌》前景化语言特征研究
李美芹,郑然丹
(1.2.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引言
随着清代白话长篇小说的流行,《红楼梦》横空出世。《好了歌》在《红楼梦》第一回出现,被称为神仙一流人物的甄士隐经历了丧女、家中失火等境况,最后走投无路不得安身。晚年落魄的甄士隐拄着拐杖,到街前来听得跛足道人吟诵这首七言诗: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1]
作者称《红楼梦》不过是“毫不干涉时世”的满纸荒唐言。但学者朱彤则认为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和甄士隐的《好了歌解》两篇通俗韵文,成了再现典型历史环境的点睛之笔。[2]《好了歌》是否指涉现实,它在文本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首诗与当时历史环境的关系、与作者自身的情感态度又有何种关系等,至今没有定论。
西方文体学的分析方法为《好了歌》提供一种有理有据的理解,对中国的诗歌鉴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补充。田星认为中国的诗学研究尚存着“失之简略”或“失之繁复”的现象。[3]而现代文体学,以作品为本体,能够“以语言事实为出发点,把语言描述和文本阐释结合起来”。[4]对语言形式特征的感受和把握可以避免可能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促使读者感悟作品整体意义的时候以一种相对科学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中,诗歌语言形式特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从绘画方面引进的概念——前景化。根据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理论家穆卡罗夫斯基(Jan Mukarovsky)的观点,诗歌语言中,标准语言构成诗歌语言的背景(background),对标准语言规则的系统违反则构成了诗歌语言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而这一前景化语言特征是实现诗歌语言诗意(化)的手段之一。[5]
笔者尝试用文体学的分析方法阐释《好了歌》,分析前景化在语言层面的两种主要的实现手段——偏离和并置产生的语言特征,结合雅各布森的对等原则分析前景化在结构方面的两种表现方式横组合前景化与纵聚合前景化在《好了歌》中的体现,进而分析这首诗如何通过诗歌语言和结构的前景化实现诗歌的诗意化并表现诗歌的主题,即从男性视角揭露世俗妄念,指出世人对功名、钱财、美色和后裔的念想让他们无法洒脱地生活。
一、违反规则的偏离
将偏离文体观充分发展并高度理论化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将偏离的概念首先运用在文学(主要是诗歌)的分析中。雅各布森指出,“当语言用于诗歌之中时,其诗性功能(poetic function)占主导地位,而诗性功能使语言最大限度地偏离实用目的,由此而形成极度规整而又奇特反常的诗歌文体。他们的这些看法与中国古典文论中对‘诗家语’与常语的区分似乎不谋而合。无论古今中西,诗歌语言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于日常语言。”[6]60《好了歌》中,既有语域偏离、句法偏离、词汇偏离、语义偏离等语言层面的偏离,又有图式偏离、题材偏离等超语言层面的偏离。诗人运用“诗歌特许权力”(poetic license),通过在语言层面和超语言层面违反常规的偏离,使诗歌语言偏离语言常规,明显不同于日常语言。
(一)语言层面的偏离
偏离能够打破正常的交流过程,“为了得到合理的解释,就尽可能地运用想象和深层次地联系,填补思维空档,这使得表面的反常往往能比正常的言语促发产生更多的、更丰富而深刻的含义”[7]从全诗来看,《好了歌》虽然存在语义上的不合逻辑,但经过读者的思考,其中的深意最终能够被更好的理解。诗人形象地表现了世间存在的这一种驳论: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金银、娇妻、儿孙忘不了。如果人人真心向往逍遥自在、了无牵挂的神仙,又为什么会放弃不了这些世俗的东西呢?前后诗句中表现出的反差,可以理解为世人的执念太深,即使向往成为神仙,也没办法放弃世俗;又或者神仙指的就是凡人甄士隐,所以才放不下这些东西。两种解释不相互冲突,而互相补充、互相丰富,形成复义。同时“世人都晓神仙好”的对句在形成了质的偏离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量的偏离,拓宽了思维发展的维度。“高度概括地把封建‘天理’赖以建立的四大伦理支柱——忠孝节义作了全面的否定。”[2]“孝顺儿孙谁见了”违背了社会常规,在以孝为德的封建社会怎么可能见不到一个孝顺的子嗣,这是一种“失协”(incongruity)的“明确性偏离”(determinate deviation)。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里的句法和用词显然是脱胎于文言。这句话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缺少了主语和衔接词,表现了句法偏离。但缺少的句子成分对诗意的表达来说可有可无。这种情况下,保留在诗中的词语更能凸显出诗人情感;突出这是世人而不仅仅是个人有着聚敛财富的执念。同样的“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中也存在着句法偏离,语序不同,表达的意思可能基本相同,但文体风格则往往不大一样。如果按照常规的语序应该是:古来多痴心父母,谁见了孝顺儿孙。“痴心父母”和“孝顺儿孙”被前置,变得更为突出,儿孙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得以“前景化”。这种故意打乱词序的移位不是一般的倒装,而是诗人有意的呈现。
所有的语言形式特征都具有某种语义上的作用。“忘不了”这种口头的大白话和“终朝”“日日”这种书面语混用,原本适用于叙述的大白话被用在了诗歌文体中,这是一种语域偏离的现象。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但《好了歌》口头语和本应以文言文为主的书面语的混用模糊了日常用语和诗歌语言的界限,偏离了诗歌语言的基本常规。清代脂砚斋曾评论道:此等歌谣,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通俗,故只此便妙极。于是,“孔圣人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个古老命题,被换成了“好了歌”的打油诗形式。”[8]该诗歌以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语言表现了“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豁达,“其说得痛切处,又非一味俗语可道”。[9]
词汇偏离可以表现在词语的用法上,即在特定的语境下违背词语的常规用法使一个常用词获得偶有语义(nonce meaning)。“世人都晓神仙好”中的“神仙”这个词被用来指看破红尘的仙人道士,实际上也可能指的是“神仙一流人物”的甄士隐。《红楼梦》中的谶诗通常以人物的诗词来预示其自身的命运,这种模糊、含蓄且隐蔽的暗示人物命运的诗通常是立言于前,有征于后。但《好了歌》则是通过道士之口点出了甄士隐的过去。世人都晓神仙好,但无人能放弃功名、钱财、美色和儿孙,即使有着神仙一流人品的甄士隐也不例外,以此来以小见大。甄士隐表面上“神仙般”的散淡是命中无子的沉沦,因为“唯有儿孙忘不了”,他才祈求一僧一道为他指点一二。当赖头和尚的谶语貌似唬住了甄士隐,为了“烟消火灭”,他有意让“有命无运,累计爹娘”的英莲在元宵节外出,第二天才假意派人寻找,向其他人作伤心状。道人看似脱口而出的谶谣,或者正好言中了“神仙”甄士隐过去对功名的追逐和对儿孙的渴盼,甄士隐才能根据宿慧解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利用了僧道传谣的疯癫样子,加深了其作品的神秘性和宿命性的同时,一语双关,造成指此言彼、声东击西的效果。
(二)超越语言层面的偏离
语言的形式对文体风格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的文体学研究或许是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大多只注重对语言形式的分析,把孤立文本中的语言现象和常规相对照。但库克认为文本分析应该把文本和语言的结构形式之外的因素,即读者对世界的心理反映也考虑进去。[10]
偏离不仅可以表现在语言形式、文本结构的层面,还能在心理感知的层面上产生图式偏离(schema deviation)。这首七言律诗的体裁就打破了同时期读者对清代世情小说的心理预期。宋元以后,由于言文长期分离,“文体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俗人’的方面人们干脆抛开文言,因而话本戏曲等俗文学得到了大大的发展。而注重形式的方面则把骈散结合起来,进一步程式化、规则化,出现了八股文这样严格规范的考试文体。”[11]这种倾向发展到清代,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与现代白话已经比较接近,但小说中的《好了歌》还是采用了律诗的形式避免了枝蔓芜杂,冗言废话。“如果完全用叙述体来交代,易于失之直露‘伤时骂世之旨’触及贾祸”[2];另外律诗以及其他形式体裁的文体在小说中的多处出现,让《红楼梦》成了小说中所未曾见的“文备众体”。
同时,这麻屣鹑衣的跛足道人吟诵出来的假语村言,除妄醒梦的同时,又非常符合道士出场时的疯癫形象,因此《好了歌》不同于其他世情小说中会出现的散文闲赋、诗歌与人物以及情节塑造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也造成了一种打破心理预期的图式偏离。曹雪芹在立意撰写小说的同时,按头制帽,诗即其人,把“在小说情节中确有必要写到的诗词,根据要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文化修养,模拟得十分逼真……小说中诗词曲赋是从属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描述的需要的。”[12]跛脚道士勘破了这个泥浊世界,却又“隐去真言”,他是小说中真正的神仙,却又以邋遢跣脚的形象出现,即使言语触犯时忌,作者也可以以人物的疯癫,以及道士神神叨叨的假言村语为自己开脱。
《好了歌》中也出现了题材偏离。何类题材为常规,何类题材为偏离,不同时期的定义是不同的。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符合题材常规的诗“言志”、词“言情”。这首诗歌处处散发着一种厌弃仕途的情结。与作者同时期的清初学人,“以振兴儒家正统思想来抑制异端的横行”,在文学领域,他们“以《诗经》的雅正传统为核心,回到儒家诗学的基本理念,显示出一种重整儒家诗学传统,以树立新的诗歌观念的共同意识。”[13]但和当时盛行的儒家积极入世的主张不同,这首由跛脚道人吟唱的诗歌流露出的则是道家寻求解脱的厌世倾向。全诗用语极为浅俗,对仗、用韵均不讲究,但大俗之中可见大雅。这首谶谣不但贴合了跛脚道士逍遥不羁的人物形象,其朗朗上口的诗歌节奏、情感色彩鲜明的文体形式风格与诗歌的整体意图紧密关联。跛脚道士的大白话似乎毫无诗意可言,然而正是这种安排凸显了该诗的风格特征,引导读者去深思其中寓意。
二、过度规则的并置
诗歌的所有技巧都可归结为并置的原则。通过分析出现在实现层、形式层和语义层的并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诗人如何使用诗歌语言实现陌生化效果的。在《好了歌》中,过度规则的并置主要体现在实现层的书写并置和语音并置,以及形式层的词汇并置和句法并置。
(一)实现层:书写并置和语音并置
七言诗的书写规则首先从外形上就区别于其他文体,每句七个字,每两句为一联,形成了书写并置。从前述《好了歌》中图式偏离的分析可知,采用诗歌的形式是为了避免冗言废话,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抒发对时事的愤恨无奈。诗歌体裁促使读者对文本有一种雅的期待和阅读体验。但符合常规的七言律诗太雅,不符合道士疯癫落脱的形象,于是曹雪芹通过语域混用,用俗字口语使诗歌读起来更加贴切,让“眼闭了”“随人去了”这种极为生活化的语言在七言律诗中出现。利奇曾指出,规则性的前景化(并置)和不规则性的前景化(偏离)在不同的话语层次中出现的频率是不同的,因此二者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6]73语域混用和书写并置的同时出现打破了读者的心理图式,让读者生出一种因过于熟悉而产生的陌生感,激发他们用崭新的眼光去深入文本体会个中滋味。
与书写并置同时出现在实现层的规则性前景化手段还有语音并置,整首诗每一联都以“了”结尾,虽然没有违反语法规则,但多次重复在句尾使用“了”,形成量的偏离(qualitative deviation)。前面分析句法偏离的时候提到“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这两句子的语序被倒置。也因为作者有意更改了语序,这句话才能和其他句子一样用“了”收尾。虽然写诗押韵是常规,是区别诗歌与散文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作者放弃所允许的选择自由,在原本可以多样化的地方引入了规则性的形式,在每一联都用“了”收尾,造成过度的规律化。在每一联都以“了”作结尾,似乎象征着只有凡尘妄念的最终消散,才能“好”得“了”,只有放下空念,才能“了”结。这种有意形成的语音上的过度规律化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失衡”(deflection)现象,它增加了诗歌的乐感和回环感,增强诗歌的连贯性。
“好”和“了”都是开口呼音,且以开口度大的ao作韵母,形成上下句的语音对等,又因为“好”“了”都位于句子的尾部,形成位置上的对等。两种等价关系强调了“好”“了”之间的联系,突出了一种辩证关系,“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对于作者来说“好”和“了”在语义上就是对等的,“好”“了”在语音上的对等正是映照并前景化了这种对等关系。建功立业、发财致富、贪恋妻妾、顾念儿孙都是被欲望蒙蔽、尚不“觉悟”的缘故。而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只有当贪嗔痴的念想都“了”结,人才“好”获得修行。
(二)形式层:词汇并置和句法并置
形式层上的词汇并置也是规则性前景化手段的一种,词汇并置“在语言表达与所表达的内容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使语言不仅能传达意义,而且模拟意义的结构,让读者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好像能直接看到所表达内容的‘形态’(shape)”[6]119只看《好了歌》每一章的后一联,便可以很清晰地发现每一联中都有着相对应的词汇并置。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第一章第二联中的“古今将相”和“荒冢一堆”相呼应,成等价关系。第二章第二联中的“无多”和“多”语义相反,也有词汇并置的情况。
词语并置在很多情况下都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句法并置。第三章第二联中,“君生”和“君死”,语义上等价(相对),并且在句中所处的位置相同,因此这两个词有着耦合关系。因为出句和对句都是主谓+系表结构,所以这一联词汇和句法双重并置,有着语义和位置都等价的结构。同理,“痴心”与“孝顺”有着耦合关系,“父母”与“儿孙”以及“古来多”与“谁见了”也有着耦合关系,第四章第二联也是词汇和句法的双重并置,并且这一句中位置的相同更加严格。因为并置结构中,位置上的相同越严格,语义相对、相反的效果越明显、越强烈。所以全诗最后一联比“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表现出的情感更强烈。不过“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的前景化效果要高于“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并不只是前景化方法的垂直方向的紧密度更高,而在于整首诗系统地、连贯地突出自身的特性。
三、纵聚合与横组合
从雅各布森的选择(聚合关系)和组合(结构)关系的区别入手,利奇(1966)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前景化”,纵聚合前景化(paradigmatic foregrounding)和横组合前景化(syntagmatic foregrounding)。纵聚合前景化和横组合前景化也分别被称为偏离和平行结构。[14]形成横组合前景化的平行结构可以使文章更具有凝聚力,成为一个整体;纵聚合前景化则让前景化的成分系统地联系起来。这两种前景化手段在《好了歌》中都有所体现,二者相映成趣,相辅相成,增强了文本语义之间的联系效果。
(一)横组合前景化
雅各布森曾提出诗歌文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将聚合体赖以建立的对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推行到组合段上[15],使得言语序列的构成中出现了原本只与选择有关的等价现象。《好了歌》中每一联都有出现的对偶修辞,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以对等原则为基础的并置。对等原则可以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所有语言层面,将诗歌结成一个统一体,保证诗歌文本分析的整体性和概括性。比如第一章: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功名”“将相”和“荒冢”这几个在词义上分别有着相近和相反的等价关系,且这两句对偶句是以“了”结尾,形成了尾韵。《好了歌》中的第一章出现的多重的并置现象,不仅使两句话在形式上对称,而且表达的内容在语义层面上也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功名”和“将相”是意义相近的对等关系,功名在封建社会中指科举称号或官职名称,将相在这里泛指当官的人,本位于选择轴上的要素,现在却在诗歌中横向结合,组成了诗句。“将相”和“荒冢”这两个意象则是存在着一种相反意义的对等关系:因为生前风光显赫的将相,死后也只会化为无人问津的墓冢。诗歌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尾韵,排比等语言在词汇层和语音层的等价现象,且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言语信息表层的毗临原则,使诗歌的行文与其他文体迥异其趣[16],产生了独特的风格。
这两句诗歌里言语的特定组合方式和对等原则的使用,让语篇中变异的成分之间产生了衔接,前景化成分产生横向的连贯。这一章中,“忘不了”和“没了”这种口头语和“古今”这种书面语混用,在语言层面产生了语域混用的偏离现象,如果它们就是彼此孤立的,这种偏离现象对语篇的总体理解起不到很大的作用,然而,作者使用了“功名”“将相”“荒冢”具有等价关系的词汇,通过词义联系,让这第一章里的各个句子产生了衔接。诗歌语言把语言学中用于描述聚合轴的等价原则,应用于组合轴,从而使用等价关系来增强诗歌之间的关联,产生文学文本中的连贯性。
语言形式上的连贯性,通过联想可以服务于语义逻辑上的连贯性。《好了歌》中对偶句让诗歌在形式上具有了一种连贯性。《好了歌》中每一层分别以“功名”“金银”“姣妻”“儿孙”为中心词展开论述,相似或对立的语言要素间展开的联想可以构成诗歌具有连贯性的深层结构。“篇章的结构性”[17]149就表现在语言形式上连贯性、语义逻辑上连贯性两个方面的实现。这种横向的衔接(cohesion)是一种语言形式上的篇章的粘连,“篇章在形式上的粘连为语义逻辑上的连贯性服务,是内在语义连贯性的表层形式标志。”[17]153通过研究文本《好了歌》的平行结构可以发现,诗歌在语言形式和语义逻辑上都具有连贯性,并且各处语言选择之间的照应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
(二)纵聚合前景化
“‘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还意味着时空的关系,因为对等原则将具有时空特征的一组词语,用语言序列历时性地呈现了出来”。[3]《好了歌》中共时的选择轴上对等的4个表示世间妄念的词语“功名”“金银”“姣妻”“儿孙”被投射到了组合轴,依次出现在诗的上下句中,从而具有了一种历时性的特征。每一章的第一联,复迭的诗句结构相同,每句仅更换2个词语。同一中又有变化,具有一种历时性的动感。使诗歌因为结构的回环往复,吟诵起来朗朗上口,也正好符合步斗踏罡的道士形象。
纵向来看,在句式上形成等价关系的每一章节的第一联,在“世人都晓神仙好,唯/只有……忘不了”这样的句子同样位置上放置4个不同的词语“功名”“金银”“姣妻”“儿孙”,但这4个词都位于相同的选择轴上,指向世间痴念,相互之间存在着词义上的等价关系,2种等价关系纵向相互对应和加强,不但增强了整首诗歌语义上的关联,也从各个维度表现出截然不同、倏枯倏荣的世态,从而成为了“满纸荒唐言”的例证。
《好了歌》中各个成分之间的等级关系,即相互的上下级关系体现着文章的系统性。每一章诗歌的第一联的出句句法相同,以“惟有”“只有”开始,“忘不了”结束,但“功名”“金银”“姣妻”“儿孙”事异义同,它们之间具有自然的联系,这时的对等被提升为系统的构造手法。这种对立统一形成了诗歌中对等要素间的张力,让前景化的成分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重要性上按递进顺序排列。这些词组明显和世人(特别是男性)的社会生活有关,语义上有一定的阶层性差异,从最普遍追求的社会认同到个人最难以割舍的父子情,根据当时社会中男性的价值体系的序列,按照重要性层层递进形成高潮(climax)。前景化的成分也因为这种递进关系系统地联系在一起。
四、结语
这首七言诗在通过偏离和并置形成其独有风格的同时,前景化的语言特征对其主题内容和情感的表现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好了歌》这首诗为本体,对前景化的语言特征进行分析,能够找出产生某种文体效果的语言上的原因。自《红楼梦》问世起,其中的诗词曲赋已存在多种理解。虽然文体分析也不能够精确完整地说明这首诗的意义,因为它从来都不是确定无疑的,但可以通过对超出常规的文本语言特征进行考察,为特定解读提供文本语言证据。首先,从语言层面和超语言层面出现的偏离现象而言,曹雪芹是有意打破常规,对封建社会的四大伦理支柱进行否定,又令诗歌的语言特征符合道士的疯癫形象,这增加了整首诗歌的神秘性的同时,使作者避免了伤时骂世的贾祸之灾。其次,《好了歌》的并置现象同样能产生陌生化的效果,语音并置增加了诗歌的连贯性,“好”和“了”在语音上的对等关系照应着语义上的联系:只有当贪嗔痴的念想都“了”结,才“好”获得修行。横组合前景化和纵聚合前景化又使《好了歌》形成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
利用文体学的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修正中国传统的诗词鉴赏中出现的“失之简略”或“失之繁复”的现象。对于文学文本的文体分析,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运用语言学的理论来进行文学鉴赏,比如借鉴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和对等原则,可以让我们在语言层面发现诗歌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能够增加看问题的一个新角度,深化认识。通过描写和分析作者选择的语言成分及其产生的特定文体(修辞)效果,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避免对诗歌有失偏颇的解读。
任何语言形式特征都可能与文体风格和诗歌的整体意图有关。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到,“艺术在本质是向他人传达感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表现为一定的感受(内容)寻找适当的形式,‘形式’的东西可以被感受为内容、为本质”[18]。文体学通过描述和分析诗歌语言上的形式特征来显示诗歌的文学性和“诗意”之所在,能够以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方式解释作品的意义或文体风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