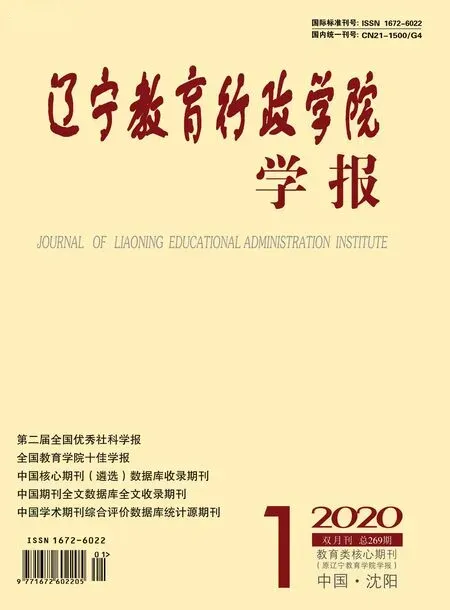马致远散曲的用典类型、特征与意义探析
张 华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541004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1](P155)在隋树森主编的《全元散曲》[2]中,马致远今存小令115首,套数16 首,残套7 首。在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中,最常见的艺术特点之一就是用典。据薛美霞在《马致远散曲的用典内容、形式及特点探析》中不完全统计,马致远的130 多篇散曲作品中有将近200 多个典故。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对用典下的定义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3]简言之就是借古论今,援古证今。用典既要效法前人的文意,又要推陈出新,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典故进行适当改造,糅合情感,妥帖表达,不露痕迹,如此方为上乘之作。马致远散曲作品中的用典恰是如此。在元代统治者废除科举和民族歧视的政策下,许多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才高运蹇,因此有“十儒九丐”的说法,这些落魄文人将自己的愤懑失望、怀才不遇写进诗词,而用典则成为他们不露痕迹地寄托情感的最佳选择。东篱先生很多作品的创作动机就是如此,他的散曲用典颇多,意蕴深刻,类型多样,笔者简单地将其进行了一个分类,按内容分为“稽古”“引经”;按形式分为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化用。[4](P6)除了对马致远散曲用典的类型进行举例分析外,笔者还会主要从审美特征入手,分析其用典的特征。
用典的益处毋庸置疑,然而近来学术界却有了截然不同的声音:“用典适用于所有文类吗?”“怎样用典才能恰到好处?文章的用典究竟起什么作用?”[5](P29)因此,笔者将借此深入,全面客观地探析用典背后深层的意义。
一、马致远散曲用典的类型
学术界对用典类型的研究比较细致也相对统一。吴琳在《析用典》中将典故按内容分为“稽古”“引经”两类,按形式分为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化用,[4](P6)笔者认为这是比较全面的分类。薛美霞的《马致远散曲的用典内容、形式及特点探析》也承袭和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张晓静在《<文心雕龙>用典探析》中认为用典的表现形式分为“事典”和“言典”两种,这两者表达的含义与吴琳的“稽古”与“引经”大同小异。梁秋生在《浅谈诗词用典的类型和方法》中介绍了三种用典方法:直用、隐用、正用,其中的直用和隐用分别对应吴琳在《析用典》中的明用和暗用,两者的含义基本上也是如出一辙。综上,笔者借助前人研究典故时的类型,将马致远的散曲作品按内容分为“稽古”“引经”两种,按形式分为明用典故、暗用典故、正用典故、反用典故、化用典故五种。
(一)按内容分
稽古,“也叫‘用事’,就是引用历史故事、运用前人事迹,从中借某种特定含义来表达作者情怀”。[4](P6)简言之,就是指“援引古人的事迹来证实自己的论点”。[6](P1370)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有引用古人故事或含蓄或直接的表达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这是一种借古论今、援古证今的手法。借古,援古是手段,喻今,证今是目的。马致远多采用这种手法也与当时的时局有关,元朝统治者废科举,轻汉人,饱受孔孟之道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拳拳治世之心得不到重视,社会地位更是不堪一提。文人们对时政的不满只能隐约含蓄地通过诗文、借用典故来折射和表现,一腔愤懑与抑郁之情只能深深地埋藏在这些相似的典故里,马致远稽“古”抒己怀正是这一方面的体现。马致远一生饱经沧桑,早年热衷功名,渴望大展宏图,晚年却选择远离官场,归隐山林。因此,马致远散曲中“稽古”中的“古”分为两类:一是斗志昂扬、力争上游之类的典故。[南吕·四块玉]《临邛市》中的“汉相如便做文章士”,[双调·拨不断]《叹寒儒》中的“读书须索题桥柱”等都为意气风发之人、建功立业之事;二是遁世遗荣、餐松饮涧的典故。[双调·拨不断]《菊花开》中“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双调·拨不断]《浙江亭》中“子陵一钓多高兴,闹中取静”皆为隐士归隐山野之事。
引经,“主要是指引用前人典籍中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观点,所引之言往往为人们所熟知”。[4](P6)简单的来说,就是指“援引古代圣贤的言辞”。[6](P1371)当然,引经并不仅仅拘泥于圣贤之言,而是一般著作皆可引用。马致远深谙此道,善于借用前人优美的词句篇章,吸取精华,再加上其已臻化境的文学功底和深切独特的感悟体会,所以引经据典往往是得心应手,浑然天成。[仙吕·青哥儿]《正月》“照星桥火树银花”就是化用唐朝著名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南吕·四块玉]《恬退》中“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化用陶渊明与污浊官场毅然决裂的宣言《归去来兮辞》中的“归去来兮”,手法高超,巧用词句,韵味自然。
(二)按形式分
明用典故,指“借其意而明用之。即对典故作出较为明显的概括或引述,使读者一看就知道”。[4](P6)如[仁双调·庆东原]《叹世》中,“阴陵道北,乌江岸西,休了衣锦东归。”明用项羽阴陵迷道、垓下之围的典故,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观和英雄观,成败兴衰不过是南柯一梦,英雄豪杰不过是过眼云烟。[双调·夜行船]《秋思》中“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中引用唐代名臣裴度在洛阳修建绿野堂和曾做过彭泽县令的陶潜参加慧远高僧组织的白莲社的故事。[般涉调·耍孩儿]《借马》中则借用三国名马关云长坐骑赤兔马和张飞坐骑乌骓马的典故,马主人将自己的马与历史上名马相比肩,侧面烘托出马主人对自己的马珍之爱之。
暗用典故,是指“假定读者通晓古籍,用不着说明是谁的事迹”。[4](P7)[双调·夜行船]《秋思》中“看钱奴更做道你心似铁,争辜负了锦堂风月”的“看钱奴”和“锦堂”就是暗用典故的范例之一。“看钱奴”出自于元代戏曲作家郑廷玉的杂剧《看钱奴》中所创作的一个为富不仁、刻薄贪婪的人物形象,“锦堂”暗用的是宋韩琦在相州故乡筑昼锦堂的典故,后用来泛指富贵人家的第宅。这类典故不如明用典故清晰明显,而是隐藏在文章之中,往往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知识量辅助理解。
正用典故,是指“所运用的典故与其作品的题旨相符合”。[4](P7)[双调·拨不断]中“菊花开,正归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起首两句,就运用了陶渊明归隐的典故,紧接着写自己所交之人都是慧远高僧、鹤林殷天祥、名士孟嘉之辈,就像杜工部、陶渊明、李白这些杰出的诗人一样,在大好河山,在山林田野,饮酒赋诗,纵情高歌。如此美妙的田园生活,身处其中,好不快活!作者正用典故,以隐士风流人物自比,道出自己辞官归隐的缘由,表达了归隐田园的志向乐趣。类似的还有[南吕·四块玉]《恬退》中“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典故,“归去来”也俨然成为隐士远离官场醉心田园的代名词,与作者“恬退”的美好意愿相一致。
反用典故,即指“不用典故本身或为人们所公认的普遍含义,而用其相反的意义,即所谓‘翻前人作’,或‘反其意而用之’,借以抒发一种与原典相反的思想感情和见解,得出一个与通常评价完全相反的判断”。[4](P7)学者马丽梅在其论文《苏轼诗用典研究》中将反用称作翻案,“指对历史上同一件史实,作出与前人或大多数人不同的判断”。[7]马致远为了表达功名利禄恰如电光石火,瞬息即逝,经常引用锐意进取之典故表达相反的意思。[双调·蟾宫曲]《叹世》中的“项废东吴,刘兴西蜀”,却转眼变成了“梦说南柯”,反用其意,功名成就、鲜衣美食不过是南柯一梦、过眼烟云。[双调·清江引]《野兴》“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两句也大有深意,这里的“山中相”指的是南朝梁代的陶弘景,梁帝数次欲聘弘景入朝为官,陶不应,然梁帝每有军国大事常传信咨询,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马致远在此并不像大部分人一样羡慕陶弘景的“归隐”,反而却带那么点讥讽之意。正面说自己要做一名山中宰相,再也不管世间纷扰。话里话外的潜台词就是陶弘景并不会做山中宰相,因为他仍然心在朝堂,在“管人间事”,所以就称不上是真正的恬淡无欲、超然物外。这人貌似山间隐士,实则红尘未断,仍受世俗困扰。作者将原典之意完全推翻,呈现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表达出对红尘的毫不留恋和彻底的隐退思想。因此,恰切地反用典故,不仅可以表达自己新颖的观点,不落俗套,还能启发读者进行别样的思考。
化用典故,是指“以前人语句为基础,对其加以变化翻新,与自己的作品融为一体,借以表情达意”。[4](P7)[双调·拨不断]《布衣中》的“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两句则是化用晚唐诗人许浑《金陵怀古》中的颔联“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马致远前后颠倒一下位置,但是韵味却迥然不同。史良昭在《元曲三百首全解》中对两者的一个对比赏析非常恰当准确,他评价道:“许诗的‘楸梧’一联是针对‘金陵’一地而描绘的专景,借此写景含蓄地表现‘英雄一去豪华尽’的主题,而马曲借用则情急语破,用以展示对古今历史中一切‘英雄’‘王图霸业’的否定。下句紧接的‘一场恶梦’,更是势如破竹地为这一否定再添一个惊叹号。‘六代宫’‘千官冢’,无不体现着‘王图霸业’的影子。所以虽是借用成句,却直有‘语若己出’的效果。”[8]化用前人诗句并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稍加改造焕发新意,马致远的用典手法已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综上,马致远散曲用典颇密,种类齐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几种类型的用典之间并不是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引经”和化用典故这两种用典之间就有相通之处,前者援引的同时也会适当化用,不露痕迹,而化用典故本身就具有化用生新之意。还有马致远明用的一些典故在具体语境中又具有相反的含义,明用和反用两种用典同时存在于一句话中。所以,由此可见,典故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独立、泾渭分明,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也有延伸交互之处,其目的是共同为主题和情感服务。
二、马致远散曲用典的特征
自古以来,用典是诗词中备受作者青睐的一种修辞手段,这不仅因为诗词本身具有含蓄深远、篇幅短小的特征,更是因为用典带来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效果。诗词用典适当,则能使作品言简意深,词华典赡、耐人寻味。马致远的散曲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更是兼备以上三种审美特征。
(一)言简意深
言简意深的审美特征,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诗词的结构形式决定的,诗词篇幅短小有限,这就要求文辞必须高度凝练、简洁,用极少的语言去呈现丰富的内容、表达深远的含义。而用典则成了诗词家的最佳选择,因为它不仅可以简练地概括发生的事情,更能够恰如其分地抒情达意,使其变得意味深长。
[双调·拨不断]《叹寒儒》中云:“题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短短两句,包含了两个历史著名人物的典故,司马相如题桥柱、作《长门赋》,才能卓绝,受到帝王宠幸;孟郊寒窗苦读,进士及第,春风满面,意气风发,然而作者紧接着感叹的是,很多寒士并没有司马相如和孟郊那样的好运气,即使如历史名人一样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也无法施展,不能得到朝廷的赏识和重用,含蓄地体现了元朝文人沉沦下僚、不为世用的普遍遭遇,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轻视贤才的深沉控诉和怨忿之情。
[双调·夜行船]《秋思》中第五支曲云“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时光短暂,转瞬即逝,这里借用一个羲和驾日车的典故作比喻,形象生动,准确妥帖。“不争镜里添白雪”反用李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意思,引出“上床与鞋履相别”这句玩笑,很容易使读者联想起那句民间俗语“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作者把这句俗语的意境化繁为简,便塑造成为耐人咀嚼寻味的哲理名言,表面上看是真正的大彻大悟,看淡生死,其实我们不难读出这句玩笑背后隐藏着的作者的心酸和伤感、不甘与无奈。紧接着马致远在明白这一切道理后,表明自己难得糊涂的处世智慧——“鸠巢计拙”,这一切的铺垫,引出了下曲作者对人生深刻的思考与领悟,功名利禄、是非成败皆为身外之物,与其羁绊于名缰利锁,不如寄情山水、自在行乐。第五支曲单单化用两个典故,就清晰地表达了马致远晚年时期平淡朴素的人生追求,起到了辞简意足的效果。
(二)词华典赡
马致远的散曲作品颇多用典,这些典故的运用使原本比较直白浅俗的散曲变得文雅富丽,词华典赡,增加了语言的色彩度,丰富了作品的文学性。
[南吕·四块玉]《浔阳江》中“送客时,秋江冷。商女琵琶断肠声。可知道司马和愁听。”月色清冷,深秋江畔,送别友人,歌女弹着忧伤的乐曲,时间仿佛倒流,好像见到了当年唐朝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时,浔阳江头夜送客,写下一曲《琵琶行》的情景。白居易的《琵琶行》文辞优美,以情动人,成为传世名篇后,凡路经浔阳江的文人骚客都会情不自禁的缅怀起白居易这位一度被贬的诗人。马致远仕途偃蹇,命运不济,如今身临其境,郁郁不得志的遭遇,使他与古人间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典故的运用,使这首小令言辞典雅,情深意切,丰盈了作品的意境。
[双调·湘妃怨]《和卢疏斋西湖》中“雨中楼阁烟中寺,笑王维作画师。”王维是唐朝赫赫有名的妙手丹青,西湖画桥烟柳,美不胜收,连王维笔下的山山水水竟也无法与之相比,足以侧面衬托出作者对西湖景色由衷的喜爱与赞美。历代歌颂咏赞西湖的作品数不胜数,然而马致远另辟蹊径,引用人物典故,让人眼前一亮,不禁联想起连王维笔下的山水都无法比拟的景色该有多美?这处用典实在绝妙,使整首小令增色不少,清新典丽。
[双调·夜行船]《秋思》中首句“百岁光阴一梦蝶”,用了《庄子·齐物论》的典故,“百岁”与“一梦”相对应,在突出石火光阴,百年一梦的恍惚之感的同时,又增加了词藻的妍丽之色,还与此曲其他各句构成押韵。王世贞称赞曰:“马致远‘百岁光阴’,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押韵犹妙。”[9]沈德符更是高度推崇:“若散套,虽诸人皆有之,惟马东篱‘百岁光阴’、张小山‘长天落彩霞’为一时绝唱,其余俱不及也。”[10]笔者认为这句意境空灵,雍容典雅,堪称一绝。
(三)耐人寻味
除了结构、语言等基本审美特征以外,相对更高层次的审美特征而言,典故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有时很难被迅速精准地把握。它需要读者去反复揣摩,体察深意。显而易见的是,用典这种修辞手法学习和模仿起来难度并不大,但是要想做到将典故变得别具深意、耐人寻味却并非简单之事。马致远在这上面却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南吕·四块玉]《凤凰坡》云:“弄玉吹箫送箫郎,送箫郎到青宵上。到如今国已亡,想当初事可伤,再几时有凤凰。”此曲运用“萧史弄玉”的典故,这个典故本用于男欢女悦,夫妻恩爱之题,可是在这里我们却读出了一种黍离之悲。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马致远并不是真正地表现亡国之思,而是对蒙古军统治中原,民族矛盾激化,汉文化传统逝去的怅惘哀痛,是对重武轻文、重蒙轻汉的时代背景下,汉人时乖运舛、数奇不遇的深沉叹息。“再几时有凤凰”,更是表现人生理想失落、可望不可求的一种悲哀心理,是理想中“九天雕鹗飞”与现实里“困煞中原一布衣”的鲜明而又无奈的深刻对照。用典加深了此曲的悲剧氛围,吸引读者去探索和想象东篱先生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
三、马致远散曲用典的意义
(一)解构信息 剖析情感
典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浓缩和沉淀,用典是对民族文化的别样传承和诠释。一个典故的生成,总是寄托着人们特殊的道德认知和情感经验,这就决定了当人们互相对一件事物产生相同的认知,抑或是情感在某一时刻达到高度的共鸣,选择用典则是传达信息、宣泄情感的最佳方式之一。读者通过作者引用典故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进行解构推导,探寻文本背后的深层意蕴和情感维度。
[南吕·四块玉]《天台路》中“采药童,乘鸾客”,引用了刘阮入天台山采药遇到两位美丽仙女并一起生活的故事。南北朝时代,狼烟四起,烽鼓不息,百姓对平静安宁、安居乐业的生活心怀向往,于是一批描写避世绝俗、追求美好生活的作品便应时而生。紧接着“怨感刘郎下天台”这句是转折之笔,“怨”字清晰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态度——不理解刘阮两人还乡恋世的选择,最后一句“谁叫你回去来”,化用晋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句子,通过两者一入世一出世的对比再次强调作者的观点,寄托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即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和对现实俗世的不满。典故在语境中的解构意义诸如此类,可见一斑。
(二)适度用典 精准传情
毫无疑问,用典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无数文学大家都青睐于此种表达技巧。例如马致远、苏东坡、辛弃疾等都长于用典,推敲典故,寄存情感,无形中推动了典故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是它的积极影响;然而,它的负面效果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文坛用典堆砌、雕章琢句、弥见约束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有些典故过于晦涩,造成理解的难度,设置了阅读障碍,将一部分读者无形中“拒之门外”,从而缩小了受众面。例如李商隐的某些无题诗,南朝刘宋时的颜延之、南宋吴文英的某些诗作。因此,用典不是文章的万能圣药,像马致远[黄钟·女冠子]套曲这样用典密集并能准确传达出思想情感的佳作毕竟是凤毛麟角。
[黄钟·女冠子]套曲作于马致远思想未成熟时期,欲归隐田园又流连功名,欲遗世独立又“尘根未断”,纠结、矛盾、挣扎,万千思绪,复杂难言。所以我们看到马致远在这首曲子里所用的典故比他其他的散曲都要多,他仿佛是在这些历史典故里寻找答案,寻找放弃的勇气,寻找隐退的理由。最终,他豁然大悟,不论是半生寒微终遇明主的姜子牙,还是才华横溢却一生未达的孔仲尼,都是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所以不要计较得失,一切都会如南柯一梦,过眼云烟。密集却又适度的用典,将马致远在感悟生死,看淡名利的过程中的一番矛盾心情精准地传达了出来。
恰到好处的用典,可以精准地传达作者欲表达的思想情感。但是,如果滥用典故或一味求新,则会适得其反。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滥用典故来代替原字十分反感,他在《人间词话》里推崇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认为其词自然本真,情感真挚,相反却觉得吴文英的词平平淡淡,甚至颇为不屑,“梦窗以下则用代词更多”,笔者认为这与吴过分追求典故,造成意境晦涩难解离不开关系。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实用角度还是审美角度来说,用典能使作品言简意深,词华典赡,耐人寻味,大大增加文学性和趣味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万事都是过犹不及,用典也是同理。典故的运用必须恰切适度,否则全然靠典故堆砌,不仅读来拗口生涩,失去原有的美学价值,而且会造成读者阅读受阻,无形中降低作品的吸引力,削弱作品的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