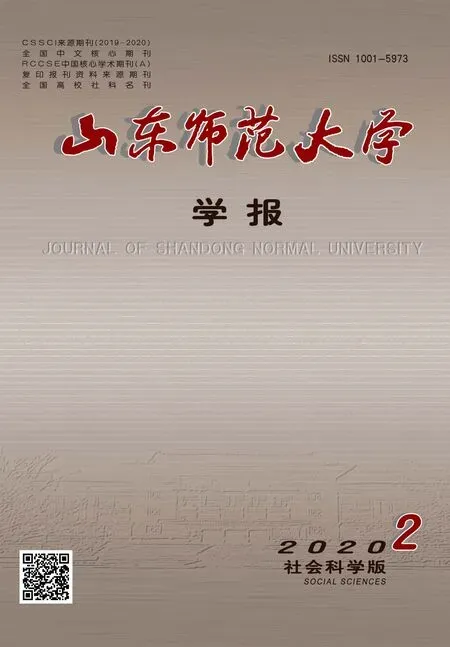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内化”
——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理论为考察对象*①
周新民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新中国成立至1970年代末期,小说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小说的倾向性、真实性、题材、主题等问题,而到了1980年代初期,小说理论最为关切的是小说形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小说形式的独立价值也得到充分肯定。有论者认为,相对于政治观、哲学观、艺术观,小说形式“一旦出世,便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为后世持全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见解的作家使用”(1)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小说形式具有独立性的理论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冯骥才也认为,“单就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说,是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欣赏价值的。即在我们确认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同时,形式美有其相对的独立性”(2)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对小说形式的重视,为中国接受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是20世纪西方崛起的重要理论潮流,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理论、叙事学、语言本体论、符号本体论等理论流派。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一向注重文学作品、文学形式的独立价值,拒绝讨论文学作品和作者、社会现实的联系,也不注重文学作品的外在意义,与中国文学传统、“十七年”时期的文学观完全不同。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不是被动地全盘接受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而是以着眼解决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过程之中的问题为立足点,来理解、接受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正如卢卡契所言:“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3)[匈牙利]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52页。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接受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过程中,是以“内化”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为基本方式,建立起了独有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一点在小说理论上的表现最为典型。本文将以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理论为考察对象来讨论这一问题。
一、作为小说技巧的叙事学
叙事学只关心叙事文体的叙事方式、叙述,不看重叙事文与外在社会生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也不关心叙事文和作者之间的联系。因此,叙事学是一个封闭的纯粹形式系统。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比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只数和纺织方法。”(4)[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4页。叙事学认为,叙事就是它的一切,其他的诸如题材、主题、创作主体、现实生活等,都和它无关。叙事学文学理论被国人关注是在1979年。这一年,袁可嘉于《文学世界》发表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一文。(5)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从1970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播。1975年《哲学社会科学动态》第4期刊出《近年来欧洲结构主义思潮》,这是中国最早接触结构主义的文字。1982年,乐黛云出国参加“批评方法与中国现代小说研讨会”,接触到叙事学,成为中国把叙事学作为小说理论来看待的第一人。她把叙事学作为提升小说魅力的形式要素:“叙事学主要研究故事的表述方法,同一个故事,表述方法不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完全不同。有的很动人,有的则枯燥无味。”(6)乐黛云:《“批评方法与中国现代小说研讨会”述评》,《读书》1983年第4期。乐黛云把叙述看作是小说质的规定,认为叙述决定了小说艺术魅力的关键之所在:“如何造就一个小说世界并将读者引入呢?小说家不能依靠线条、色彩、音符、节奏;也不能依靠激情、韵律、表演、冲突(或者说主要不能),他的根本手段就是‘叙述’。同样题材、同样主题的小说,往往在审美价值的创造上相距甚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叙述技巧的高下。”因此,乐黛云认为,要提高小说的艺术魅力,就要从小说的形式着手,而叙事学正好“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在小说分析中,它是揭露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7)乐黛云:《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五)——第六章叙述学与小说分析》,《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
把叙事学作为小说形式技巧来看待,是1980年代初期的小说理论的普遍现象。作为1980年代初期卓有影响的批评家,南帆也把叙事学看作是小说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帆注意到叙事视角的重要价值,也注意到由于视角的变化,小说叙述的面貌焕然一新。叙述视角是叙事学的主要内容,它被看成小说叙述的关键之所在。南帆认为,叙事视角由全知全能视角转为从一个独特的、特定视角来叙事,是小说艺术发展的重要进步。“对于叙述观点的重新探索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么一种发现: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观察世界有时比无所不知更为意味深长。”(8)南帆:《小说技巧十年——1976—1986年中、短篇小说的一个侧面》,《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在南帆看来,与全知全能视角相比较,限制视角是强化小说主观性的重要技巧。他说:“小说更为注重的显然是人物对于世界的个人化感受与理解。在湛容的《人到中年》、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叫红唇儿》、韦君宜的《洗礼》、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一批小说中,作家在同一小说中设置了两个以上的叙述观点。于是,小说中的完整事件被种种不同的色彩析解了。作家舍弃了事件本身的节奏和统一性而换取了众多人物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现。”(9)南帆:《小说技巧十年——1976—1986年中、短篇小说的一个侧面》,《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南帆把叙事视角看作是强化小说叙述主观性的一个重要技巧。如此理解,显然是窄化了小说叙事视点的功能。不过,把限制视角局限于体现人物的主观感受,的确顺应了反思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桎梏的潮流。张德林也把叙事视角看作一种重要的艺术技巧:“视角的选择和转换,与作家艺术构思的密切关系,另一个特点还表现在,这种艺术设计往往寓有深意,可以起到深化主题的重要作用。”(10)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
与叙述视角相联系的是叙述人称,也是叙事学的重要概念。在布斯看来,叙述人称缺乏单独的价值和意义:“可能夸大得最过火的就是人称的区别,说一篇小说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写的,或者把小说归入第一人称类或第三人称类,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东西,除非我们更恰切地描绘出叙述者的特定属性是如何与我们希望取得的叙事效果相联系着的。”(11)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转引自霍夫曼、墨菲:《小说理论基础》,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5页。不过,叙述人称决定了叙述者和所虚构的艺术世界之间的距离。这也是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相互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1980年代叙述人称仅仅被看作是叙述语言上的技巧。对此,高行健有过明确的说法:“在第三人称‘他’的叙述语言背后,总有个不在作品中直接出现的‘我’,即叙述者。换句话说,当叙述者‘我’直接见诸文字的时候,人们便称之为第一人称的写法,而从叙述语言中把‘我’省略掉,便成为第三人称了。第三人称可以说是叙述者‘我’对被叙述者‘他’的耳闻目睹,以及对‘他’的分析和理解,在研究第三人称的叙述语言的时候,不能不同时研究叙述者本身。”(12)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2页。在高行健的眼中,叙述人称这一重要概念,只是叙述语言变化上有所差异而已。基于此,高行健宣称:“把第二人称运用到叙述语言中去,这是一种新技术”。(13)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14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读”,是因为把叙事学仅仅看作是一种小说技巧,仍然把小说看作是作者的产物。其实,在叙事学理论看来,小说是叙述者的产物,叙述者和作者也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1980年代初期的批评家对于叙述者和作家之间关系的误读,是把叙述学理论看作是传统小说理论的丰富和补充,看作一种现代小说技巧而已。
从总体上看,叙事学在1980年代前后,只是作为一种表现技巧来看待的。叙述视角、叙述人称、叙述者等,还只是能够丰富小说语言的表现力、有利于表现小说的主体精神、小说主题的重要方式。如此理解叙事学,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范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到1980年代,走上了反思和革新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道路。戴厚英认为:“现实主义的方法——按照生活的原来样子去反映生活,当然是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的一种方法。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方法,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方法。”(14)戴厚英:《人啊,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6页。作为在那个时段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李陀更为激进地主张要超越现实主义固有写作模式。他说:“小说固然‘有一定的写法’,但写法却不必定于一,不一定非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15)李陀:《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十月》1982年第6期。正是这样的历史语境,叙事学在中国1980年代初期作为小说技巧被接受,成为打破既有现实主义小说理论陈规的重要方式。
二、“有意味”的文体形式
1980年代中期,由于持续受到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小说理论出现了形式本体理论建构的潮流,形成了与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相类似的本体理论。此现象已为众多研究者注意到。但是,中国形成的形式本体理论,同西方形式本体理论绝非完全一样,而是打上了中国小说理论自身发展的烙印。到1980年代中期,小说理论发展进入小说文体理论创建的关键期。何为文体?“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16)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导言》,昆明:云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页。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17)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导言》,昆明:云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页。。正因为文体具有沟通小说形式和内容之间关系的突出特点,文体理论的建构在反思只注重小说内容而忽视小说形式的理论主张时,显得尤为重要。因而,有批评家呼吁:“作家创作的程序是内容到形式,而理解、分析、评论一部作品的程序应当相反,从形式到内容。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即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18)杨周翰:《新批评派的启示》,《国外文学》1981年第1期。因此,小说文体理论建设的路径普遍被看作是从形式到内容。这也是1980年代中期建构小说文体理论的基本思路。西方语言本体理论和符号学,恰逢其时地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1980年代,西方思想家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哲学家的学说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他们的语言哲学思想也开始影响中国的思想界。维特根斯坦“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9)[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5页。、海德格尔倡导语言乃是“存在的家园”(20)[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伽达默尔认为“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以及特别是诠释学经验都是从语言这个中心(Mitte der Sprache)出发展开的”(21)[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62页。等观点,被中国哲学界所认同和接受。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为小说理论观念的变革提供了理论资源。
其实,语言本体理论具有先天的缺陷。对此,王岳川有过概括:“1.表征危机,即将表征差异和个体自由极端化,使交流不可能;2.批评语言的狂欢,即概念堆积、语词过剩;3.语言成了碎片,再也不能整合人的形象,导致后乌托邦话语。”(22)南文:《思·语·诗——“语言学转向与文学批评”研讨会综述》,思想文综编委会、暨南大学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主编:《思想文综(第一辑):语言与思想文化专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在接受语言本体理论时,中国小说理论从建立小说文体理论的角度上,有意规避了语言本体理论的一些弊端。尤其在小说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上,并非全盘接受西方语言本体理论观点,没有把语言看作独立自足的本体,而是把语言看作“第二现实”:“文学乃是人类借语言符号所进行的对自身把握、超越和创造的方式。所以,相对现实世界来说,文学的语言符号是一种全新的本体结构。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创造出一个获得独特的生命意义的‘虚构的世界’,它是人类的本质通过想象性延伸的方式所获得的一种存在。”(23)罗强烈:《罗强烈文学评论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页。语言虽然被看作是本体,但它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建立一个和现实世界相联系的本体,是“第二现实”。基于这一点,对于意义的追求仍然是中国文学批评家接受语言本体理论的基本视野。茵加登曾区分了文学语言的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声音的组合层面,它是小说的最基本的层面,它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第二个层面——意义层面。在这个层面,有意义的句子和句子系列展现出在具体生活情景中的人、物等。第三个层面是观点层面,它是第二个层面发展出的一个有机的、有意义的综合体,一个特定的世界,在此基础上生成观点。第四个层面是“形而上性质”的层面。在第三个层面上,由于读者的“意向性经验”的介入,就产生了“哲学意义”。黄子平在《得意莫忘言》一文中,就借鉴茵加登的理论来分析小说语言的本体意义。黄子平引入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象”“意”“道”等概念,把茵加登的语言本体理论置于中国文学传统视野中来理解。黄子平以“言”对应音韵学、格律学,从审美的角度考察“节奏性冲动”如何影响了文字、句型的选择;以“象”来对应隐喻、意象、象征等修辞手段,探讨作品的意义和功能;在“意”的层面,情绪、态度,观点和感染力,紧张性、强弱、流动或跳跃的状态都将得到准确的描述,并指出它们如何呈现在语言的张力之中;而由此的阐发就是“道”的层面了。黄子平的分析把茵加登关于语言组成的文学作品本体理论,置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视野中加以阐发,其最终结论是:“文学作品是一种‘意义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里,客观世界被自觉地加以重构和改动,产生了一个奇异的、独立的‘世界’。”(24)黄子平:《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显然,在黄子平眼里,文学作品这个独立的世界,非纯粹的语言自足体,仍然指向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符号学介入小说理论之后,产生了小说符号诗学。这也是形式主义本体论的一种重要形式。符号本体论强调,小说创作主体对于小说价值的投射,包括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等,都是虚幻的。“社会文化具有多少种符号系统,主体就有多少种异化的方式和可能性,直到你发现,所谓内在统一的、完整独立的、具有绝对纯粹的本质、在宇宙及社会中占有不可替代的稳固位置的‘主体观’恐怕是个幻觉。如果这种主体观不复可信,那么与‘何为主体’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势必重新解释。”(25)孟悦:《语言缝隙造就的叙事——〈致爱丽丝〉、〈来劲〉试析》,《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2期。南帆也认为:“主体仅仅是语言结构之中的一个成份,而不是语言结构的主宰。将人视为支配语言系统的权力中心,这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26)南帆:《主体与符号》,《文艺争鸣》 1991年第2期。但是,当符号体系、符号结构成为中国小说理论的核心时,它便有意识地偏移了符号本体理论原本的逻辑,给小说理论带来了崭新的内容。在中国符号诗学视域里,小说普遍被认为是“‘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的一种,而且应该是以语言来叙述人物事件与心理为主要内容和主要表现手段的一种审美符号系统”(27)徐剑艺:《人物形象的审美符号化》,《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但是,小说也没有被看成是纯粹的“叙述语法”的集合,还是指向了意义:“小说作为一个非实指再现性的具有诗学意义的人类表现性模式——象征符号体系来阅读和批评。”(28)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页。徐剑艺曾建立系统的小说符号诗学。他认为,小说所构筑的符号包含能指层和所指层。能指层是小说的物质形式,也是小说符号超语言性活动的出发地。而小说的所指层,“才是小说符号的所指意义,但可惜的是,这种思想或观念形态的主题尽管可以指称非现实的另外一个世界——象征世界的审(神)话内容”,甚至“不是一种明确的思想或意义”(29)徐剑艺:《小说符号诗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页。。指向象征意义,是1990年代前后中国小说符号诗学的根本性特征。孟悦借鉴小说符号诗学的观点来介入具体小说文本的分析与解读。她认为:“《来劲》、《致爱丽丝》确乎代表了某种‘社会象征行为’。它们实际上可以说是以颠覆某些语言规则的方式,象喻着曾占主宰地位的某一意识形态慨念体系的崩溃瘫塌。更确切地说,这两篇小说与其说颠覆了语言关系,不如说(象征性地)破坏了那一形而上学地看待主体、看待主体间、主客体、主体与文化关系的观念体系,象征性地破坏了与其相伴生的小说观(人物观、情节观、叙述观)、审美感知力和艺术惯例,象征性地破坏了某种久已稳固的、秩序化了的文化心理结构。”(30)孟悦:《语言缝隙造就的叙事——〈致爱丽丝〉、〈来劲〉试析》,《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2期。总之,通过小说符号,指向或者象征一定的意义,这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重要收获。其意义在于,它把小说和现实之间的直接反映关系,把小说和主体之间的直接表现关系,都转换为符号的象征意义,从根本上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小说文体理论的建构。
总体上看,语言本体理论、符号本体论等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从根本上启发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重视文体建设的新思路。但是,被纳入文体理论建设视野的“形式”,和西方形式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形式”有不同的含义,具有沟通现实、建立起意义关系的内涵。
三、叙事学的民族文化转向
1980年代末期,寻根小说家韩少功、阿城等倡导小说创作要深入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这是当代小说理论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1990年代初期,曹顺庆提出了“文论失语”的话题,直指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中国被边缘化的窘境。曹顺庆的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共鸣。“文论失语”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叙事学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深化了叙事学的文化转向路径。于是,着眼于民族文化来探究叙事形式,成为小说理论不得不面对的时代命题。
其实,叙事学的文化转向在1980年代就埋下了伏笔。1980年代中期,托多洛夫出版了一部反思性的论著《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他检讨了叙事学的理论前提:“二百年以来,浪漫派以及他们不可胜数的继承者都争先恐后地重复说:文学就是在自身找到目的的语言。现在是回到(重新回到)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忘记的明显事实上的时候了,文学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通向真理与道德的话语。”(31)[法]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78页。托多洛夫要求文学不再局限于形式本身,要重新回到意义的关切上来。该著于1987年出版,对批评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随后,越来越多的叙述学研究者意识到,叙事学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形式分析问题。叙述形式中有深刻的文化内容,甚至可以说,叙述形式比内容更深刻地反映了控制叙述的社会文化形态。因此,叙述学日益朝文学文化学方向发展”(32)微周:《叙述学概述》,《外国文学评论》 1990年第4期。。这里所谈的叙事形式与文化的关系,是指宏大的社会生产、社会制度包括社会活动对形式的生成、制约与规范作用。虽然叙事形式仍然是探究小说文体特征最有效的途径,但这种探究再也不是局限于文本自身,它从文本出发而溢出文本,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赵毅衡认为叙事形式研究根本不能脱离文化,形式与文化互为表里:“叙事学的形式分析就可以进行到文化形态分析的深度。”(33)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66页。
叙事学的自我反思,为中国小说理论经由叙事学转向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理论前提。1989年来北京大学讲学的浦安迪认为,中西叙事学理论由于文化差异,体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东西方文化自有其各自独立的特殊形态,中国文学中的‘叙事’的涵义也与西方文学中的‘narrative’的涵义,在许多方面大异其趣。”(34)[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浦安迪认为,西方文学发展路径是荷马史诗——罗曼史——长篇小说,形成了叙事文学的主流。而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三百篇——骚——赋——乐府——律诗——词曲——小说”的传统。西方文学的传统是叙事,而中国文学传统是抒情诗。浦安迪对于中国叙事学的深刻认识,为中国学者建构叙事形式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系统地建构小说形式与民族文化关联的是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它以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形式为研究对象,全面地探讨了小说形式系统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杨义认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为中国叙事学的根基:“中国人是这样看待叙事:叙事学就是头绪学,就是顺序学。中国叙事学以史为源头,以史为重点,它是从史学里发展起来的,然后波及到小说、戏剧,它是把空间的分隔换成时间的分隔,然后按顺序重新排列这样一个过程。”(35)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杨义立足于返回到中国文化的原点,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观念、哲学观念和美学观念入手,来探讨和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具体言之,《中国叙事学》从中国民族文化观念入手,全面地分析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等形式要素,系统地建构了叙事形式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
进入新世纪后,注重形式与文化、意义的关联的思想,赋予了中国小说理论建设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使中国小说理论关注中国现实情境,“寻找叙述形式和意义的关联”也被赋予现实的考量。(36)祖国颂:《叙事的诗学·序》,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中国社会难免受到追求经济效益的功利主义诱惑。那么,如何规避现实?从中国传统伦理中寻找到出路,是中国学者开出的药方之一。李建军即是沿着此路径建立起叙事形式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他的《小说修辞学》呼吁在形式构建之中体现鲜明的伦理意义。李建军认为:“技巧的实验和变化并没有带来小说艺术的进步和发展,反而造成了小说的危机”(37)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93页。。相反,小说形式、技巧应该与伦理道德相联系,因为“小说也许是与伦理道德问题联系最紧密、最广泛的文学样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一种叙事性文体,小说叙述的核心内容是人的复杂的内心体验和人格发展,关注的是人在情理冲突、善恶冲突、利害冲突中的精神危机和道德痛苦,也就是说,小说所叙之事,往往是处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情境之中的人的‘事’,而这些‘事’里不仅包含着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反应,也反映着作家的道德态度和道德立场”(38)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2页。。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传统和现代至1980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都偏重文学的教化功能,文学的形式要素并没有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当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重要价值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我们要看到,40年来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于中国小说理论影响走的是一条内化的道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被中国小说理论吸收,成为中国小说理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被内化的接受路径,是外来文学理论在中国生根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