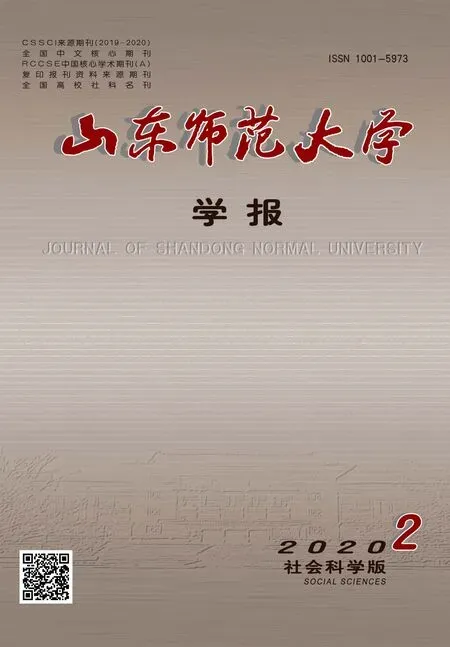经典教育与大众文化融合的解释学路向*①
史 洁 张曙光
(1.山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250014;2.山东女子学院 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250300)
经典作品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超越时空、跨越民族文化、具有恒久意义而又历久弥新的典范之作,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但在今天,经典作品遭遇了大众文化,经典阅读与经典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大众文化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界定,但相对于高雅文化、精英文化而言,它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市场运作为手段、以满足大众精神愉悦为目的的特征是明显的。随着大众传媒从报刊、杂志、书籍等传统印刷传媒转向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手机等电子传媒,以电子传媒为载体、以大众娱乐为目的的大众文化形态对传统的经典教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一、冲突与弱化:经典教育遭遇大众文化
经典教育,是引导学生阅读和理解经典作品,从中领悟其精神意蕴、把握其艺术价值,从而启迪思想、激发智慧、陶冶精神,促进自我发展与生命成长的过程。经典作品是发生教育影响的基础和根本,但由于电子传媒的普及和流行,越来越多的经典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甚至被拍成了“抖音”,成为了某种形式的“网红”。因而,经典作品教育影响的根基地位受到了冲击。学生已经习惯于从电影、电视、手机的屏幕中获得审美体验,习惯于在网络上浏览短、平、快的文章,越来越多地被屏幕和音响所包围。“一书在手,乐而忘忧”的文字阅读方式已渐渐转变为“读屏”“读图”的视听方式。对于有些学生来说,他们所感受的经典的内涵和意义,就是电影、电视剧上的画面和形象,就是穿插在剧情中的歌曲,就是网络上的流行语。当学生说他读过了《三国演义》,很可能是说,他看过某一版本的电视剧,或者能够哼唱几句“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插曲。学生眼中的哪吒,也很可能不再是《封神演义》《西游记》中的那个哪吒,而是影视、网络上的哪吒。即便是影视、网络中的哪吒,也已经从当初“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上天他比天要高,下海他比海更大”的电视剧中的小英雄,变为今天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烟熏妆、蒜头鼻,说话阴阳怪气,“生而为魔”但能“逆天改命”的“小魔童”。
“悟空,我饿了,给我找些吃的来。”唐僧往石头上大模大样一坐,命令道。
“我正忙着,你不会自己去找……又不是没有脚。”孙悟空拄着棒子说。
“你忙?忙什么?”
“你不觉得这晚霞很美吗?”孙悟空说,眼睛还望着天边,“我只有看看这个,才能每天坚持向西走下去。”(1)今何在:《悟空传》,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4页。
这就是《西游记》的“大话改编”。《西游记》的网络化、影视化、“大话”改编,各种版本不下几十种。孙悟空、猪八戒,各有一个系列的影视形象改编。其他的经典名著同样是这样一种情形,有大话,有戏仿,有演义,有“重写”。
至于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经典解读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流行态。央视《百家讲坛》,从易中天讲《三国志》、于丹讲《论语》《庄子》、王立群讲《史记》,到蒙曼讲《长恨歌》、李菁讲《诗词红楼》,等等,经典作品借助电子传媒走进了万户千家。
经典教学的课堂里,与过去师生朗朗读书声相比,增加了更多的花样。如在《林黛玉进贾府》教学中,教师让学生经历了不同电视剧版本的比较,欣赏让人荡气回肠的《葬花吟》,经典作品的教学更多地成为一种影视艺术的欣赏。如果说多媒体的使用,激发了学生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兴趣的话,课堂上的“戏说”就显得有点滑稽和可笑。鲁迅的《孔乙己》,在课堂上成为了“孔乙己告状”的剧情展示,他要状告丁举人,将丁举人的罪状一一数出。《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一改“移山”的“迂腐之举”,“明智”地选择了“搬家”。经典作品的教学如同网络文化的“戏说”一样,在极为严肃的课堂上成为“戏谑”的对象。
对于二胡初学者而言,如果不能及时疏导这样的状态,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而阻碍演奏者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有的演奏者本身是科班出身,在二胡演奏练习过程中,很多演奏者显得较为浮躁,缺乏足够的耐心,一些自己不理解的知识和技能也不虚心请教。一旦在正式场合表演就会很容易紧张,紧张就容易出错,导致整个演奏效果大打折扣,杂乱无章。
经典在这样的时代,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学生还需要不需要经典名著的滋养?如果说需要,又该以哪种方式来接受这种滋养?这是经典教育应当回答的现实问题。有专家认为,网络时代、新媒体时代、电影电视时代、流行歌曲时代、“网红”时代,不要再执着于那些经典作品,而是要关心现实、关注当下,创造和参与流行的大众文化。“过去我们常想,在没有经典的日子里,我们是否能够活下去?不过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勇敢地试一试。让我们伸开双臂,热烈欢迎去经典化时代的来临。让那些视经典为‘命根儿’的人士,迎着西风,向着落日,像宫里的太监那样,一遍遍地哭喊:‘把根儿留住!’”(2)季广茂:《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今天的经典教育必须“回归经典阅读的传统”,比如“韦编三绝”“悬梁刺股”“囊萤映雪”之类的发愤苦读精神;比如朱熹所说的“只管看来看去, 认来认去, 今日看了, 明日又看, 早上看了, 晚间又看, 饭前看了, 饭后又看”这种似乎最笨、但其实最科学、最有效的读书方法等。(3)许总:《经典阅读与人文精神重建》,《江淮论坛》2011年第4期。大众文化时代,经典教育的路径在哪里?应当如何发挥经典对青少年学生持久有效的影响力呢?
二、真理之光:经典作品的持久影响力
经典不会因为大众文化的冲击而失去其生命力,这是由经典自身内在的“真理性要求”所决定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它有着内在的“真理性要求”,而且这种“真理性要求”会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作用于人,产生一种影响力和冲击力。在海德格尔看来,经典作品具有一股外冲的力量,它召唤读者,要求得到理解和解释。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说:“在作品中发生着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蔽(Entbergen),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4)[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页。内在于经典作品的“真理”是存在者之真理,它开启和建立了一个世界,揭开了一个敞亮之域,在“真理之光”的烛照下那些隐蔽的、不在场的东西渐渐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说,经典作品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存在,它主动地走向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对着每一个当下的读者说话。它把我们“卷入”它的世界,而我们在受到它强烈吸引的同时也发现,它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经典作品的“真理性要求”。就此来说,并不是有人说“去经典化”经典作品便不再具有经典的意义了。
经典作品的“真理性要求”,在阅读活动中,表现为对读者影响的持久有效性。海德格尔说,作品的创作是作为一个事件而发生的,“作品作为这样一件作品而存在,这一事件把作品在自身面前投射出来,并且已经不断地在自身周围投射了作品”(5)[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8页。。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是说,作品不只是一种自立性的存在,它必须将自己“投射”向周围世界,对周围世界产生影响、发挥作用才能成为它自己,实现它自己,才能“让作品成为作品”。伽达默尔说:“不管古典型概念怎样强烈地表现距离和不可企及性并属于文化的意识形态,‘古典的文化’(Klassische Bildung)依然还总是保留着某种典型的持久有效性。甚至文化的意识形态也还证明着与古典作品所表现的世界有某种终极的共同性和归属性。”(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10页。经典作品,作为历经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不朽之作,超越了“时间限制”,总是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说些什么。所以,经典作品并不是与我们相对峙的自为存在的对象,它始终与我们处于互动的关系之中,在经典作品向我们提出真理性要求的同时,也将我们移入它所开启的世界之中——它向我们发出了邀请,要我们参与其中、与它一起建构或生成经典作品的当下意义。这也是经典作品得以流行、传播并不断扩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经典作品的真理性要求,可以在读者那里得到强烈的反应,让读者产生一种意义的领悟、情感的体验、境界的提升、审美的反应。明清时期的评点家金圣叹说,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这种读书之乐,就是对经典作品的情感反应。比如他在评点《西厢记》时说到,这种读书之乐,是“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以至不知“是死是活、是迷是悟”,“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7)王实甫:《西厢记》,金圣叹评点,李保民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2-33页。之所以具有这样的“高峰体验”,就是因为来自经典作品的力量会触及读者的心灵,让读者“感到自己窥见了终极的真理、事物的本质、生活的奥秘,仿佛遮掩知识的帷幕一下子给拉开了”(8)[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唐译编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189页。。
应当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无论阅读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经典自身所具有的“真理之光”总是存在的。它照耀我们,将我们移入它特有的“光晕”之中,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文化基因,让我们感受到经典作品的伟大力量,就像卡尔维诺所说:“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9)[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页。
三、大众文化:理解经典作品的另一种方式
当然,经典作品具有超时间、跨地域的永恒价值,但并不是说,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经典作品的创作,是作为一个事件而发生的,它并不是一个自为性的存在,而是在不断地对读者产生影响、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实现自己,从而“让作品成为作品”的。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我们既不能以“去经典化”的态度消解经典作品的价值,否定经典教育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固守传统意义上经典的“权威地位”,企图以经典的权威性去对抗大众文化。我们应当清楚,经典作品的“真理性要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持久有效性”就在于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性、空间上的开放性,在它影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读者的同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也以其当下视域和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解释经典作品,实现经典作品新意义的再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多层次的“视域融合”:作品意义在时间上的延伸、在空间上的拓展,读者视域在作品阅读中所实现的更新与升华,以及作品所代表的传统视域与读者的现实视域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经融合产生了新的意义。
在哲学解释学看来,经典作品“不是关于某个过去东西的陈述,不是某种单纯的、本身仍需要解释证明的东西,而是那种对某个现代这样说的东西,好像它是特别说给它的东西”(10)[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10页。。经典作品,面对发生变化了的时代,并不固守它原有的意义,而是向这个时代讲话,就好像是特定为这个时代而讲的一样。对于理解者来说,我们阅读、理解经典作品,无论产生这一作品的时代多么久远,我们并没有搁置据以理解的当下视域和既有经验。在我们的理解中,“总是涉及到比单纯历史地构造作品所属的过去‘世界’更多的东西。我们的理解总是同时包含某种我们一起归属这世界的意识。但是与此相应,作品也一起归属于我们的世界。”(1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10页。就此来说,经典作品不属于某段特定的时间,它是没有“时间距离”的存在,具有“无时间性”,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我们的理解中实现了过去与现在的融合。
今天,经典作品遇到了大众文化,但是它并没有停止对我们的影响,只是影响我们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有“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经典阅读方式,而且也有图像、音频视听等方式。经典作品的图像化、视听化、网络化,乃至漫画、大话、戏仿,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潮流而不可阻挡。依据哲学解释学的观点看,这也是经典作品走向大众、影响大众、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一种方式。经典作品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朱自清评论文体演变过程中雅俗转化时说的一段话: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12)朱自清:《 经典常谈》,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第146页。
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时代,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同样遇到了“大众文化”。词、传奇、平话、章回小说之类的“俗玩艺”,就是那个时代在民间大众中流传、以满足消闲娱乐为旨趣的“大众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新文体,尽管一开始处于“卑微”的地位,但终究由于读者的接受和欣赏向着“雅化”的方向发展:“雅”迁就了“俗”的趣味,“俗”也随之摆脱、蜕变,渐渐适应了“雅化”的传统,于是“雅俗共识”也就成为“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可见,“雅”文化与“俗”文化并非是界线分明的,“雅士”与“俗人”也存在相互转化的过程,用“雅文化”提升“俗文化”,以至不少的“俗玩艺”上升到经典的地位。
在黑格尔的时代,像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会根据观众理解的需要加以生动性改编。对于评论家批评听众趣味低劣的现象,黑格尔评论说:“艺术作品以及对艺术作品的直接欣赏并不是为专家学者们,而是为了广大的听众,批评家们就用不着那样趾高气扬。”(13)[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51页。今天,当一部部的经典作品被搬上屏幕,被“拷贝”到网络,被进行数字化改编的时候,不是经典作品的边缘化,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命力的再次萌发。在这里,经典作品内在的意义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传播经典作品的媒介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让经典作品吸引和影响了更多的大众,而大众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热爱和享受经典作品的感情。黑格尔说:“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里感觉到—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14)[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8页。经由数字化、图像化改编的经典正是以“属于目前生活”的亲近性和生动性走进了现代人的生活,表现了现代人的情绪。经典作品植根于现实的沃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就我们当代流行的电子传媒而言,它绝不会取代经典作品,而经典作品则会通过电子媒介的传播影响更为广泛,生命力也更加鲜活而持久。
四、视域融合:经典教育走向大众文化的解释学路向
在电子传媒时代,经典作品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大众文化。对于青少年的经典教育来说,经典作品以影视改编、歌词传唱、网络传播等方式走进了他们,在提升他们“雅俗共赏”趣味的同时,也实现了经典教育与大众文化的视域融合。经由电子媒介传播的经典作品,同样具有其“真理性要求”和“持久影响力”。我们读纸质媒介的《论语》《史记·孔子世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那是文字激发起的我们对圣人伟大德行的崇敬、向往之情。同样,我们在欣赏电影《孔子》时,依然会产生这种强烈的情感或心灵的震撼。电影以其镜头的时空转换和视听的冲击力,将我们带入一种高峰体验。“鲁国,我的父母之邦,我终于回来了”,周游列国、历经磨难的孔子,回到鲁国,颤抖地跪拜在城门前,这样满含热泪地呼喊,“衰老了, 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礼乐仁和的梦想只能托付给未来了”,临终的孔子这样无奈地发出感叹。这种具有艺术表现力的电影以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触动了我们的心灵,甚至让我们满含热泪。可见,无论经典作品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种来自《论语》《史记》的精神力量,在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敏感神经的同时,总会引发我们的情感共鸣,给予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启迪。
当然,在电子媒介时代,具有“视觉吸引力和感官冲击力”的图像艺术会不会“以虚拟的直观真实性替代了思考的深刻性 ,以肤浅的趣味性消解了理性与意义的深度 ,以直觉快感取代了精神美感”(15)赖大仁:《当代文学及其文化——何往与何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实际上,无论印刷的纸质媒体,还是电子、数字的媒体,不过都是一种媒介、工具和手段。传播什么样的文化、怎样传播文化全在于我们如何运用。今天的经典教育,不应当也不可能回避电子媒介,而是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致力于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让经典作品以新的生命活力激发我们的生活热情,点燃我们的理想信念,提升我们的生命质量。以大众文化促进经典作品的传播,以经典的传播提升大众文化的品味,这是新时代经典教育的文化使命。
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庄子》、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鲍鹏山“新说”《水浒》、姚淦铭解读“老子的智慧”……都是借助于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让一部部经典作品以亲切的面孔走进普通大众的心灵,实现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读图”与“读文”并非二元对立,文字的作品与图像的作品在经典教育中可以相互融合。借助于鲜明生动的屏幕形象、优美动听的音乐曲调,拉开罩在我们面前的那些“遮掩生活奧秘的帷幕”。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经历经典作品所展示的“形象世界”,感受经典作品“投射”来的“真理之光”。《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等电视节目,就这样以“属于目前生活”的亲近性和生动性,让经典作品走进了我们的现实生活,让民族的文化基因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在屏幕上,经典可以以乐曲的形式演奏、传唱,以朗读的方式传播、弘扬,以书画的形式阐发、诠释,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分享。经典走进生活,成为生活化的经典;生活融入经典,会因经典的渗透而充实、雅致。作为鉴赏团的一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说起电视节目《经典咏流传》的现场:“观众全都沉浸在诗词音乐的强大感染中”“随着歌手的欢乐而欢乐,随着歌声的惆怅而惆怅,也随着非常富有文化意蕴的歌词而心有触动”“曲终之时情不了、意不散、神不灭,它们所延绵的精神和风骨,和今天的我们紧密握手,浸润着我们,指引着我们”。(16)康震:《经典咏流传:唤醒经典的生长力》,《文艺报》2018年3月28日。来自经典作品的力量借助于大众文化途径直抵我们的心灵。
作为青少年的经典教育,更需要大众文化的融入,这是由青少年的心理特点所决定的。从“知之”到“好之”,从“好之”到“乐之”,青少年阅读经典作品的兴趣需要电子传媒的激发。事实也正是这样,当多媒体走进课堂、走向学生,以电子媒体播放的多彩画面和立体声音响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也在引导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内在的精神意蕴和不朽的艺术价值。《论语》的教学,可以穿插电影《孔子》片断;《庄子》的教学,可以引导学生观看专家解读《庄子》的电视片断;《空城记》《失街亭》《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经典作品的章节,都可以与电视剧的相关片断对照看……这样的经典教育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让经典作品回归生活,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随着“互联网+”和“融媒体”时代的到来,经典作品呈现方式的多样化要求经典教育的多样化。这就需要经典教育的新理念、新方式。比如,基于互联网的“文字+视频+图像+音频”的呈现方式,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读文字、看视频、听声音、写评论,让静态的文字作品变成实时互动的“立体世界”。
今天的经典教育,应当保持开放的视野,顺应这一趋势,探索“互联网+经典阅读”的方式,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微信、微博等自媒体手段,将学生带入立体、交互式的阅读中。这样,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距离以令人亲近的方式与学生对话,学生在自觉不自觉间便被“移入”经典作品所开启的意义世界。当然,作为学校的经典教育,图像、视频、语音不能代替文字的、能启发深思与想象的经典。“读图”“读屏”,也并非意味着学生思维与趣味的肤浅,其同样可以引导学生在“图像”与“文字”的交互作用中更加深刻、透彻地理解作品。费斯克借鉴罗兰·巴特“可写的文本”概念,提出了“生产者式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在他看来,“生产者式文本”,比如电视文本,同样具有开放性,它“为大众生产提供可能,且暴露了不论是多不情愿,它原本偏向的意义所具有的种种脆弱性、限制性和弱点”“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17)[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事实正是如此,以大众文化形式呈现出的视频文本、图像文本、音频文本,尽管具有其自身的意图,但作为读者的学生并非是单向的接受,他们同样立足于文本的开放性,发展自己的思维和智慧。一位语文教师,在导读《西游记》时,将电影《大圣归来》引入课堂,让学生比较原著中的唐僧与经过改编电影中的唐僧,并提出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开放性问题:你更喜欢哪一个唐僧。(18)熊芳芳:《生命语文课堂观察》,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116-134页。这样的比较,不只是有趣,而且也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和想象空间,让学生进入深度的阅读和理解,从而参与文本意义的再创造。
五、开放与限定:经典教育与大众文化融合的辩证结构
经典作品的图像化、网络化、音频化,甚至“大话”,可以理解为我们基于现实情境的另一种理解方式。但是,所有的理解都应当遵循经典作品自身内在的意义要求。就此来说,视域融合不只是今天的理解者与传统的经典作品的视域融合,而且也是作品自身自其诞生之日起其意义的不断丰富,及其在今天凭借大众文化所实现的新的意义。一方面,经典作品的意义是开放的,它指向今天的生活,允许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它、理解它,赋予它新的意义;另一方面,经典作品意义的源头仍在作品本身,脱离了作品意义的架空分析、任意改编都是对经典作品价值的消解。这就是作品意义开放性与限定性的辩证统一。
事实上,经典阅读与教育所遇到的既可能是那种为了大众、引导大众、促进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也可能是迎合大众、不经鉴别、鱼目混珠的“大众文化”。本来,“大众文化”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诸多不同因素的组合,前者是作为“popular culture”的大众文化,后者则是作为“mass culture”的大众文化。因此,在经典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大众文化有一个分析、辨别的过程,以便提升受众“雅俗共赏”的趣味和审美水平。比如,有些经典作品的“大话”改编系列,不过是以经典作品为引子“另起炉灶”,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大圣归来》等,仅仅是 “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而有的则是以戏说、颠覆为目的的滑稽与恶搞,自然缺少了经典内在的精神意蕴。对于“另起炉灶”的经典改编,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比如,用于经典教育中的比较阅读与分析,让学生在深度阅读和理解中发展智慧、促进成长。对于那些不经鉴别的低俗“大话”、畸形“恶搞”,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低俗、畸形的经典“大话”,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变为批判与颠覆的反面,即一种类似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19)陶东风:《大话文学与文学经典的命运》,《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但搞笑版、滑稽版的经典改编往往因为好玩、搞笑、有趣而在校园迅速流行,如果不加以引导鉴别,学生们就会驱逐经典的厚重、追求颠覆的快感,就会造成思维的钝化、思想的浅薄、审美的庸俗。钱理群说,这种“随手拈来,大口吞下”式的“快餐文化”,对孩子心灵可能会造成毒害,他引用鲁迅的话说:“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其结果不只是倒胃口而已——吃‘烂肉’、喝‘酸酒’长大,是可能成为畸人的。”(20)刘正伟主编:《名家解读:语文教育意蕴篇》,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页。面对这样的文化现象,经典教育必须让学生学会鉴别,“提高理解、辨析、评判媒介传播内容的水平,以正确的价值观审视信息的思想内涵,培养求真求实的态度”(2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4页。。因此,教给学生跨媒介阅读的方法,首先要让他们学会鉴别媒介信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2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作为mass culture的大众文化,有可能就是这样摧毁精神的“满面笑容的人”。因此,我们要让学生在深度阅读与比较中明白,经典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大众文化”需要鉴别的眼光。青少年学生应当自觉培养起理解、辨析、评判、提升各类“大众文化”的能力和水平。
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对于经典教育来说,具有两面性。黑格尔在《美学》中曾经谈到,对于经典作品的舞台表演不能拘泥于原著所表现的历史客观性,而要“注意到当代现存的文化、语言等等”。他认为,根据当代生活进行合理的改编,可以给人亲切感、熟悉感,但是也不要让希腊神话中的奥甫斯“手执小提琴”,因为“小提琴与神话时代的矛盾就太刺眼了”(23)[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52页。。如何在经典教育中把握经典作品与大众文化融合的度?最根本的就是,经过大众文化改编或阐释的经典有没有表现出“心灵和意志的较高远的旨趣”“心灵中人类所共有的东西”“真正长存而且有力量的东西”。(24)[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54页。既来源于经典内在的真理性要求,又体现当代人的新的生活方式,揭示出“心灵与意志”的高远旨趣,应当是判断经典教育与大众文化融合的价值尺度。
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只有把握好经典阅读与大众文化融合的辩证结构,才能提升经典教育的价值,发挥经典滋养生命、发展智慧、促进成长的作用。对于经典来说,保持其开放性,而不至于使其成为一种文化桎梏;对大众文化而言,坚持其对大众阅读的引领性,而不至于使其陷入一种无厘头的空虚和无聊。这就是经典教育的辩证结构。“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25)[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85页。作为经典教育,当然不能让经典作品成为“文化监狱”,束缚学生想象和思考的自由,但也决不能让经典作品走向“娱乐至死”的滑稽和搞笑,导致心灵的扭曲、审美的庸俗、思维的弱化,这是经典教育所应坚持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