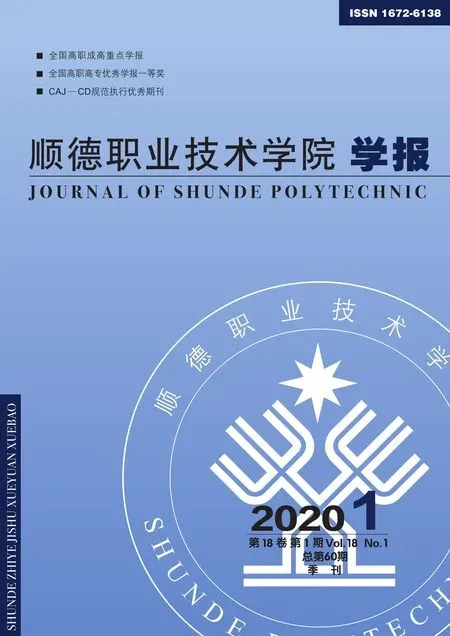虹影作品中的上海想象
——以“重写海上花”三部曲为例
苏安娜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上海因为其独特的形象和特殊的地位受到无数作家的青睐,他们在原有的城市形象基础上进行集体想象,建构了一座文学中的上海。虹影也在这股上海文学浪潮写就了“重写海上花”系列三部曲(《上海王》[1]《上海之死》[2]《上海魔术师》[3]),为这座文学中的城市再添一片砖瓦。然而,作品在引起赞许、肯定的同时,也招致不少质疑和否定,主要的疑虑是非沪籍作家可能无法写出上海的精气神。那么,不同于新感觉派、张爱玲、王安忆等拥有本土生活经验、记忆和感受的海派作家,土生土长于重庆的虹影如何突破书写困境来描绘上海?是否写出了真正的上海精神?又借上海来表达什么?
1 想象方式:建构上海与书写女性
上海想象,指的是创作者对上海——这座兼具历史与现代性的城市发起的集体想象,呈现出的上海既有共通的面貌,又有各自的不同。可见,文学中的上海并非完全是经验叙述的产物,而是一个不断被赋予意义的开放空间。因此,虹影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本土作家在上海文学话语权争夺上的地域优势,而是以何种想象的方式重写上海旧事,突出其文化精神。
1.1 时空构形:小说中的上海想象
小说里的时间和空间,是感知文本世界的重要维度。虹影对城市的时空构形有着大胆的想象和创造,她重塑了晚清到民国的上海历史,呈现了开阔多元的城市空间。
1)时间构形:晚清到民国上海历史的重塑。
虹影的“重写海上花”颠覆了传统古典小说的线性时间模式,重新切割、调整、组合时间,实现了从晚清到民国的上海历史重塑。
首先,文本历史时间跨度巨大,主要以晚清到民国为大背景。《上海王》的时间线是1906—1927 年,《上海魔术师》为1945—1948 年末。《上海之死》虽然着力描写1941 年11 月25 日—12 月5 日的事,但文末的时间表详细交代了远东战争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主角们跨越几十年的回忆也扩大了时间的断裂跨域。
但仅有特定时间坐标仍然不够,上海的历史依旧是模糊的。因此,虹影一方面自如地驱遣历史人物,如于堇的晚宴有周佛海、胡兰成等人的参与。另一方面,择取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如1948 年的通货膨胀、1935 年的大饥荒和洪门、青帮之争。晚清到民国的上海历史也在叙述中逐渐有了较清晰的轮廓。
其次,文本中融入了虹影对历史的见解。《上海王》采用的是“我”和筱月桂的双向视角,“我”和她不时在过去和现实中来回穿梭。当筱月桂看到“我”带来的相关传记时,十分不屑地将黄金荣、杜月笙称之为“青帮小瘪三”,嘲讽历史传记给予他们的所谓“面子”。其实,这是虹影在借筱月桂发表自己的历史观。如今人们推崇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给历史人物给予的评价也不一定恰如其分。她对历史人物隐形的颠覆,也间接表露了她要用自己的方式重读上海的历史。
总之,虹影在固有的史实基础上再塑了历史,注入了其独到的历史观。然而,也暴露出了些许不足,譬如上海历史传奇的蓄意夸大。虹影的后期创作偏商业化,她择取了黑帮、欲念、谍战等西式的东方主义元素,同时运用了与《英国情人》相似的创作手法,即用名人的私生活做噱头引子。“我”写这本小说是因为刘骥先生珍藏的筱月桂剪报,但我却找不到她的任何资料。这一差异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向读者抛出了疑问。筱月桂是否真实存在?二人之间是否真有过一段未曾说破的情缘?作者当然要强调筱月桂确有其人,强调《上海王》事事有典,这更引起了读者的探究兴趣。笔者认为,虹影的小说之所以没有得到主流的评论界和学者的肯定,与她蓄意夸大历史外在的传奇性密不可分。
2)空间构形:开阔、多元的城市空间。
小说空间不仅是人物的现实空间,还是“文学以话语作为形态,对各种社会空间寄其中的结构做情感体验和话语表达。”[4]虹影笔下的上海大气开放,充满着现代气息。
在三部曲中,虽有弄堂、打浦桥、南京路等代表上海的文本符号时而在文中闪现,但主要的活动场所是开阔、中西交融的公共空间。筱月桂成长于华洋交接处的高级妓所一品楼,有着代表古典审美取向的深红大门和厚重石墙,内里却是现代的套间,分属各位姑娘。新与旧、情与爱就在此纠缠。于堇住在“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的顶楼,饭店是西化建筑的集中体现,外墙是花哨的花岗岩,内里是低调的乳白大理石,象征着财富和地位。三人中生活质量最差的兰胡儿也时常出入上海滩大老板黄金荣的“大世界”,外观仿造西洋,里头则有着传统设计的百米天桥。
不仅如此,这三个空间无论是物化还是精神空间都足以容纳各色各样的人物故事,呈现多元的形态。在一品楼,筱月桂结识三任上海王,也亲眼目睹凶险的帮派斗争,塑造了她爱恨分明、敢拼敢闯的性格和强大的身体、精神欲念。于堇与各方人物在国际饭店周旋,它见证了她的挣扎,消解了她的爱恨,最终目睹了她决绝的坠落和整个上海的沦陷。兰胡儿则是一步步站在南音北腔的大世界舞台,展示惊险刺激的东方杂耍,表演神秘惊艳的西洋魔术,在暗潮涌动中成长为勇敢独立的女子。而大世界比起前两者也更加多元,各种声音、文化在此对抗、糅合,呈现出狂欢式的空间构形,也显示出作者开阔的情怀。
1.2 阴性书写:小说中的上海女性
虹影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上海人,群像虽不乏英勇的男性,但最突出的是上海女性。她通过阴性书写,向传统的男性叙事进行挑战。“阴性书写”最早来源于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微笑》,是与男性话语中心相悖的女性话语书写,创作多以女性为题材,关注女性自身的语境。虹影也从多个方面进行描写,颠覆女性的次生地位,张扬新型的女性主义。
1)从被动到主动:女性历史主体身份的确立。
在虹影看来,“现代上海的开拓者,无论华人洋人,女人男人,都有点气魄。”[1]2这鲜明地表达了她对所谓上海书写的看法,一是“小”的特点并不能充分展现上海品格,“大”才是她的追求;二是现代上海的开拓者不分国籍、性别,尤其女性也应是城市现代性的参与主体。
基于此,虹影没有像左翼文学、新感觉派小说一样让女性在作品中缺席,而是让处于边缘的女性成为主人公,从封闭、私人的空间中走出来。但她们不是张爱玲文中的曹七巧、葛薇龙,也不是王安忆书中的王琦瑶、富萍,算计着生活的柴米油盐,被动顺着时代和命运,而是抛头露面地参与原本只属于男性的权力、政治角逐,成为上海的冒险家。
像筱月桂本是书寓底层最卑贱不过的妓女,发达后,给自己封王而非封后,成为了新一代隐形的上海王和第一位女实业家,连男性都为之一震,甚至产生畏惧。当筱月桂向余其扬求婚,余其扬说“家里不能有悍妻,你作为女人太厉害,本领太大,家里有个我服的人,我在外就无法威服别人。”[1]262他的躲闪,间接流露出对筱月桂女性历史主体身份的肯定。相似的细节在其他两部文本中也有描绘。于堇返沪不是为演出的声誉,也不是报纸宣扬的“孟姜女救夫”,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兰胡儿也辗转在青帮斗争中,巧妙地帮助加里从大老板手里逃脱,隐喻着女性也有能力对男性进行救赎。
值得注意的是,虹影是“把女性的个体命运置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不是历史、民族的道义改变了她们的情感和命运,相反,改变历史的却是她们的情感。”[5]女性在历史中拥有自主权,并能为自己的行动和选择负责。于堇身为美方远东情报机构人员,本应帮助美国和养父休伯特。她不是没有过挣扎,但骨子里的爱国大义让她最终在亲情和国家中选择了后者,改动了从日本军官处得到的情报信息,致使珍珠港被袭击,加快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度。她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一场著名的世界战争的走向,证明了一个女人也可以改变世界。
2)双重解放:女性灵与肉的欲望解放。
性的突破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少现当代作家都对“性”这一命题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虹影更进一步地阐释,女性应有性的自觉,应关注自己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
虹影从不避讳性,其笔下的性流露出大胆形象、迷离浪漫的美感。享受性爱时的她们宛如置身于极乐之地,“觉得自己的灵魂从未如此自在,翱翔在一个空旷之中。”[1]36她极力描绘美妙的生理体验,唯美的文字和奇妙的修辞一同带来感官的巨大冲击,也间接表露出女性对身体的把握其实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性的开放与享受只是她们身心解放的一种体现。
不仅如此,虹影还突破了性的禁地,将笔触伸向同性恋领域。最突出的是于堇与白云裳。她们对抗的竞争关系中掺杂了微妙又复杂的情愫,二人在彼此的互相试探中,竟对彼此产生了种令人不安的感觉,发生性关系也是“迷迷糊糊之中,没有任何快乐,不过好像也没有非常严重的反感。”[2]149深入她们性心理的隐秘区,不难发现这种女性间突破禁忌的情感交流,不仅是女性生理性取向上的转变,也无声传达了性心理上对传统男性叙事的挑战和性爱欲望叙事的抵抗。
性在虹影的文字间狂欢,狂欢在极致点达到吊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不以性为耻,在性中取得真正的欢乐,寻求稳定的依靠和安慰,甚至获得重生的希望。筱月桂讨好男人却没有真正的性快乐,导致阴阳失和,偶然通过窥视仆人秀芳和男友做爱而结束了病状。甚至她在垂死之际做梦,和早已归西的常爷上演一场“幽媾”,奇迹般地重生。性窥视和性幻想等奇异的体验,流露出女性对性的自觉意识。她们需要性,渴望爱,但不乞求性。真正达到此种完满的是被作者称为“暖爱小说”的《上海魔术师》。它摆脱了《女子有行》中阉割男性生殖器的男女冲突,《上海王》和《上海之死》中极端的克夫、弑夫模式。兰胡儿和加里王子两人互相依存,互不干涉,真正达到了灵与肉的温情和解。
但在张扬的灵肉解放中,仍能窥到激烈斗争中妥协性的存在。突出的一点即女性在斗争中要将身体出卖给男性取得成功。筱月桂辗转于三个男人之间,利用自己西化的身体成就一场上海黑帮政治的革命。为何女性要依靠这一方式才能成功?显然暴露了女性自身的认知缺陷。可见,哪怕是英勇如筱月桂,即便有着自觉意识,但骨子里仍有一部分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的影响,在行事中难免不自觉地流露出几分妥协。
2 想象意义:上海想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2.1 城市文化:异质多元的上海精神和上海文化
1843 年,上海正式开埠,现代性慢慢成为城市精神特质之一,具化为作家们创作中的上海,无论展现的是上海的哪个时期哪一方面,都难以避免地触及到它的现代性。茅盾的《子夜》批判现代性,他写资本家和上流社会的丑恶交易、奢靡生活,带有“左”的倾向。新感觉派则在光怪陆离的上海城市生活和纵情声色的现代性描写中暴露精神的虚无。王安忆的上海呈现未完成的现代性,既不止步不前,又不激进向前。但不管如何,这些作品都一致反映出上海的“现代性特征”。
虹影延续了这一特点。她说,“上海,是中国现代性的象征,我对中国现代性的认识,具体化为上海这个城市的女人成长的故事。”[6]筱月桂的成长就追寻着上海的现代性,她创立申曲,成立电影公司、创办实业,上海的现代文明在她的一言一行中体现。但这种延续同中有异。《上海之死》反复出现“上海,你这建造在地狱之上的天堂,”[2]169与《上海狐步舞》一样凝聚作者对现代性的审思。只是穆的这句话揭露了上海丰富又罪恶的物质文化腐蚀人的意志,而虹影则强调,面对国难时,被殖民的大众沉迷声色的状态才使得上海沦为真正的地狱,所以于堇只能选择毁灭上海。前者将上海之恶归于物质的腐蚀性,后者归之于政治的殖民性。
而现代文明的腾飞,是在开放中才得以成就。《南京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的东南门户大开,造就了上海的另一精神特质——包容性。虹影不遗余力地描写了这一特质,但别出心裁的是,她的上海想象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外国人。休伯特远渡重洋来到上海,日子悠然。夏皮罗和所罗门则活得十分负担,一个经营国际饭店,时时思念维也纳的家,一个穷困潦倒,受到当地人的嘲弄与欺骗。因地域和文化差异造成的痛苦、欢欣、耻辱、思念,上海都一并全收。
在现代性和包容性的影响下,作家们反复地渲染城市的纸醉金迷。然而,上海的文化形态的存在方式又岂止这些?它是多元的、精彩的,不仅是富人的舞会、豪华酒店,还有贫民的棚户区。兰胡儿居住的打浦桥环境恶劣,弄堂口由于开放的便桶而充满尿腥气,男人们就袒露上身在此游荡,女人们就在这儿拍打衣被。上海的精神内核也蕴藏在这些小人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里。他们富于韧劲,无论性别、贫富,都拥有着一种对生活的倔强。“杂语”更是上海多元文化的精粹体现,小说中的加里王子如同一块海绵,将流行于上海的各种语言,如英语、市井口语等吸收杂糅,不仅是语言的狂欢,也是上海跨文化交流的开放性和上海精神内核的展现,“显露出她的‘人类性’追求:多元共存、互补互动,共享一个‘大世界’。”[7]
2.2 “上海人”:个体的生存与人性的思考
从城市的表壳深入到上海芸芸众生的心灵世界,我们可以触摸到上海的精神内核,也感悟到她对个体的生存与人性的思考。
在《上海之死》中,虹影提到了“上海派头”。“花一个礼拜上南京路三家大百货公司精挑慢拣选丝绸料子,又花一个礼拜请裁缝师傅到家来,别出心裁地做出一件新款式的旗袍,穿出去,招摇过市,打几圈麻将获得太太同道的赞美,就脱下,添入衣柜的宝藏,然后开始第二次选料……”[2]40对上海人而言,向别人展示精致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派头。哪怕身处兵荒马乱的年代,避难依然居于次位。国家的兴亡于他们而言无关痛痒,只要上海还在,他们就要讲究一番生活的情调。这无疑传承了《长恨歌》市民对日常生活审美与精致的考究,不为大环境所动,在战乱、贫穷下继续自己的小生活。像王琦瑶身处城市几轮变革之中,宛如忍冬般坚毅、平静地顺其自然。
然而,这不是虹影着力描绘的东西。虽在选角上延续了张、王等人的风格,聚焦于女性小人物的传奇,但她采取宏大叙事,给予主角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由此思考个体该如何生存。筱月桂步步为营。于堇虽有任性,但骨子骄傲。兰胡儿生活艰难,却倔强坚强。她们都是孤儿,都曾遭遇过人生的低谷。筱月桂最耻辱的时候,当不了长三当幺二,还和野鸡一同伺候男人。于堇嫁给银行家倪则仁,带着些许炫耀的心思,却发现这场婚姻是个错误。兰胡儿每日总为生计操心,还遭到二老板的阴险暗算。可是无一例外,生活越是艰辛,她们越要务实地懂得用一时的妥协换来长远的利益,一步步在上海站稳脚跟。她们没有过分关注日常琐碎,没有继承“地母精神”,但共同讴歌个体的坚强、倔强和生命的韧性。虹影写的是上海女性,何尝不是在表现上海人?强大的生存能力、精明能干、对生活的抗争与追求都浓缩在了字里行间。有趣的是,外国人来到上海,境遇和选择不尽相同,或享受,或逃离,或沉溺。个体的生存有时候并不拘泥于地域、国界和性别,而流通于世界。人性亦是如此。
文本中流露出的人性没有二元对立的善与恶、美与丑,哪怕是配角。虹影通过对人物潜意识的挖掘,写出了人性的未定型。新黛玉本质善良,因为爱而恨筱,在常爷死后将其赶走,却也帮她抚养女儿,借钱给她的戏班。在岁月的打磨下,两人冰释前嫌。所罗门人性中的自私,令他对天师班的困境见死不救,但人性的美好也促使他帮助对手。即便是身为汉奸的倪则仁,两人间的爱情也曾让于堇流露出后悔、厌恶和怀念的矛盾感情。这不仅是上海人共同的人性,更是与世界共通的人性。虹影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而提炼出的能引起共鸣的人性体验,牵引着人们对人生真谛共同的思考。
上海之所以对作家如此有吸引力,是因为其文化身份的非静态和开放。因此,它包容所有的创作、情感,上海想象总体呈现出先锋式的追求命运的动荡起伏和精神刺激,反映出国人潜意识里向往传奇生活的深层文化心理。虹影在上海想象中独具意义。她既综合吸收了前人的精粹,又以外地人的兴味锐意创新,赋予了这座城市深刻的内蕴。不仅是城和人的命运变迁,更是以切身感悟和精神想象表达对城市、群体的反思,最终指向人性、现代性等古老议题,尤其是现代性——这个作者反复强调的话题。当人类文明不断向前,人性的失落、对人本身的工具性的强调等问题接踵而来,现代文明应当如何发展,人类又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