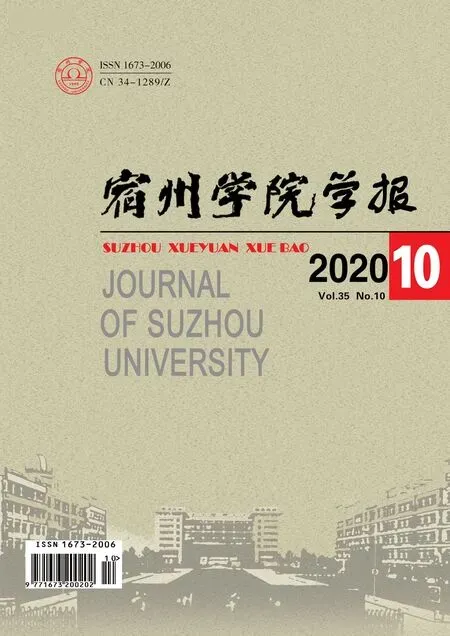运动事件框架下《画皮》三种译文的比较分析
庄娇娇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37
1 引 言
《画皮》是《聊斋志异》中广为人知的一则故事,讲述了一个恶鬼,披上用彩笔画的人皮,装扮成美女裂人腹、掏人心,最终被道士除去的故事。故事以文言文体讲述,言简意赅。汉语中有着丰富的位移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1],英语的位移方式动词也很丰富,译者对动词的翻译影响着全文的翻译质量,那么《画皮》的英译本是如何尽力寻求语义的对等的呢?本文将以词汇化模式的差异为中心对比分析《画皮》三个译本的翻译策略和翻译不足。
《聊斋志异》英译版本的数量繁多,影响也甚远,翟理思(HerbertGiles)的译本是最早的英译本,影响力最大(以下简称翟译本);美国汉学家丹尼斯·马尔(Denis C.Mair)和维克多· 马尔(Victor H.Mair)合译本注重传递中国文化,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以下简称马译本);闵福德(John Minford)曾翻译过《孙子兵法》《鹿鼎记》,他翻译的《聊斋志异》是近年来影响力较大的外国译本(以下简称闵译)。从文学、翻译、跨文化等角度,国内学术界对《聊斋志异》各种译本的研究,各有千秋。迟庆历发现翟理思的译本使用最多的是阐释手段,其次是常被作为辅助手段的注释;她认为翟译本的注释有时会非常的详尽琐碎[2]。由于宗教的原因,翟理思翻译过程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以确保译文语义之准确性。王春强认为更为本色地呈现原文是闵福德重译《聊斋志异》最先考虑的问题,同时他还认为闵采取了更为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比翟用词更准确、语言风格与原文更一致[3]。陈振霞评价到马尔译本很少使用修辞手法,即使有些地方使用了修辞,时而也会出现一些错误;他们追求直译、注重文化传递,译文不免刻板,甚至语义存在偏差[4]。
词汇化模式是认知语言学领域知名学者Lenard Talmy的运动框架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根据源语对运动事件进行再词汇化,该再词汇化过程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系列的拆解与合成。邵志洪从英汉运动事件框架表达对比与应用角度,分析了《武松打虎》中具有典型汉语表现特色的重复“运动语”(MOTION + PATH)五例表达,以及其对三种译文修辞风格的影响[5]。李雪研究了英汉移动动词的词汇化模式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她认为语际间动词词汇化模式的差异给译者带来难题,使译者陷入两难境地[6]。赵欣欣以《三国演义》中的“走”类运动事件英译为例,研究了汉英“走”类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她认为汉英翻译可采用语义融合、语义离散和语义重组的翻译策略[7]。闫丽以《葬花吟》为例,在运动事件框架下对其三种译文进行了比较分析[8]。
本文将以蒲松龄的中文版本为源语言语料,选取三个译本中故事《画皮》的英译本为目的语语料,从运动事件词汇化的角度探讨这三种译本的特点与不足。《画皮》的译本众多,选择此三者译文做研究是出于其影响力和译者背景。
2 运动事件框架和词汇化模式类型
2.1 运动事件框架
Talmy共划分出五种事件框架类型:运动事件框架、致使事件框架、循环事件框架、参与者互动事件框架和相互关系事件框架。运动事件框架具有最具体的结构。含有运动及持续性静止的情景都可以看作是运动事件(motion event)[9]7。运动事件包含四种成分:焦点(figure)、背景(ground)、路径(path)和运动(motion)。原因(cause)和方式(manner)是另外两个重要的认知因素,但是不那么具有中心地位。简而言之,焦点就是运动的事物或人,它的路径或位置需要描述;背景是运动的参照体,如起点、终点等信息;路径是指主体相对背景而经由的轨迹或方向;运动是指一个事件的活动过程,一般融合在动词中来表达[1]。方式和原因是可以不被表达的成分,途径将焦点、背景和运动联系起来,途径是框架中最重要的成分,它在运动事件中起一种框架功能[5]。
2.2 词汇化模式
焦点、背景、路径、运动、原因、方式等都是语义元素,动词、附置词、从句等都是表层元素。一般来说语义经过三种过程与表层元素结合:词汇化、删除(或零形式)及阐释[9]5。所谓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指用各类词汇形式(包括词、语素、词组)达意义或概念的过程。动词在语法和语义结构中都起着最基本、最核心的作用。动词词根词汇化有三种类型:运动+副事件;运动+路径;运动+焦点。第一种类型运动+副事件(Motion+Manner/Cause),即运动动词既表达移动,还表达方式或者原因;属于这种类型的语系或者语言有印欧语系(除后拉丁罗曼语系语言)、汉语等等,英语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第二种类型运动+路径(Motion+Path),即移动动词既表达移动,又表达路径;属于这种类型的语系或者语言有日语、土耳其语、韩语等等,其中的西班牙语最具有代表性。第三种类型运动+焦点(Motion+Figure),即动词既表达移动,又表达移动的焦点;这种模式的语言相对较少。
根据Talmy的认知语言系统,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为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s)和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英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言,大部分学者也认为汉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言。在卫星框架语言中,运动和方式这两个认知语义成分合并投射到动词词根上,路径则需要用一个小品词或者类似的成分来表达。英语和汉语同属于卫星语系,且都属于运动+副事件的词汇化类型。
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类型学理论表明,世界上每种语言的主流的运动动词都有共同的词汇化模式,而每种语言非主流的运动动词又有独特的词汇化模式[10]。这是学者在研究翻译时不能忽略的一个现象。
3 《画皮》原文和三种译文的运动事件对比
以下二分为语义翻译和语言风格两点进行对比。语义翻译旨在拆解译者对动词的运动、路径、方式的理解,识别语义要素是如何与表层形式对应的。语言风格分析,旨探索各种语言的运动事件框架的叙述风格的差异。邵志洪认为特定语言的运动事件框架对各自故事和小说的语言叙述风格会产生影响[5]。
3.1 语义翻译
例1.原文:急走趁之,乃二八姝丽。
翟译:…Wang quickened his pace and caught her up,and found she was a pretty girl of about sixteen.
马译:Running up behind,he found her to be in the bloom of youthful beauty.
闵译:He caught up with her,and saw at once that she was a girl of about sixteen.
原文中出现了两个动词:走和趁。“走”语义成分是“运动+方式”,副词“急”为其修饰语。翟理思译文中使用的是动词“quicken”,增加了相应的运动事件,却也隐含了方式信息,体现出运动的状态。马尔翻译为“run(运动+方式)”,与原文中的运动在方式信息上存在差异,即一个是走,一个是跑。闵福德并没有译出这个动词。但是,汉语倾向于将一个复杂的运动事件切分成几个片段来叙述[11]。因此,闵福德的译文在语义上是与原文对等的,闵福德将“(急)走”这一动作与下文的“趁”合并,途径与方式信息并没有缺省。原文中的“趁”解释为“赶上去、凑上去”;包含的语义成分是“运动+方式+路径”。翟理思和闵福德都译为“catch up”。“catch up”的语义成分也是“运动+方式+路径”,且“up”与“上”这两个路径是一致的。马尔将路径信息转移到run后面的小品介词“up”上,整体上是简化了此运动事件。综上所述,翟理斯的译本运动信息和原文最接近,不仅将整个运动事件的运动、方式、路径都体现出来,而且都较为正确的表达出来;闵福德将两个动词合为一个动词,后一个动词也包含前者的运动与方式,在语义上并没有缺失;马尔的译本对运动动词的使用较其他两人稍差,其所翻译的译文焦点的运动方式与原文的差异较大。
3.2 语言风格
例2.原文:径登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而去。
翟译:She walked straight up to the bed,where she ripped open Wang and tore out his heart,with which she went away.
马译:Jumping right onto the scholar’s bed,she tore a gash into his chest,ripped out his heart and run away with it.
闵译:Climbing straight up on to the bed,she tore open Wang’s chest,plucked out his heart and made off with it into the night.
该句的四个动词“登”“裂”“掬”“去”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运动事件链。翟理思、马尔、闵福德三个译本都掺杂了一些意译,都将重心放在了对鬼剖腹拿心的运动事件描写。在这一运动事件链中,第一个动作“登”不是最需要核心的运动。翟理思译为“walk”(运动+方式),相对于原文的“登”,运动偏平静了一些。马尔译为了“jump(运动+方式)”和“onto”表示路径,相对于原文的“登”,过于激烈。闵福德使用的“climb”(运动+方式)最符合原文的语境,且climb与“登”在各自语言中的用法都是非常的相似,如climb hills、登山;虽然climb在动词词根不能体现出其路径信息,但是在此语境中都表现出了一个向上的路径信息;这种由下而上,正如由地狱到人间,营造出了恐怖的气氛。“掬”释为“双手捧”。翟理思和马尔都没有译出“掬”的动作,原因是在英语中确实很难找出一个包含与“掬”运动的方式信息类似的动词。这种不对应是翻译的一大难题。Solbin的研究结果显示:翻译者遇到这种问题,要么添译,要么不译。翟理思和马尔在处理“掬”的时候都选择了不译,忽略原文的方式信息甚至运动,因此译文有失生动。闵使用了“pluck”,动词的方式信息与原文大相径庭,但修辞上更能够突显鬼的残忍。为了弥补这“掬”运动的漏译,翟理思和马尔不约而同地在“裂”上选择了添译。“裂”在原文中释为“剖开、分裂”;翟理思和马尔使用的两个动词是一样的:“tear”、“rip”,只有顺序上有差异。两个动词“rip”和“tear”,rip(运动+方式)表示“狠狠地撕”,译者添加了方式信息。“tear(运动+方式)”更侧重撕碎,也是添加了方式信息。这种添译,虽然保留原文的意境,但是略显累赘。“去”(运动+路径),翟的译为“go away”,马译为“run away”,闵译为“made off”。Go away、run away 和made off都是一个动词复合体(verb complex),away和off一样是一个小品词,表达了“路径”的语义成分,go away体现出鬼离开的平静,run away表现出鬼离开时脚步上匆忙,made off不仅体现了鬼离开时脚步的匆忙,还体现了其心里的慌张。
这一系列的动态描写,三位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都不相同,且在译文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自由发挥。关于翻译的“动态表现与非动态表现”,刘宓庆[12]认为:表现法是一个开放系统,具有无限变式,……相对自由度可以容许译者发挥动态表现(dynamic expression)优势。总的来说,翟理思的翻译多拘泥于原文,让这一系列显得过于平静;马尔的译本使用状语以突显方式信息,和闵福德相比,主要差异体现在其方式信息的准确性,如jump一词不仅方式信息稍剧烈、其路径信息也不一致;闵福德的译文自由度较大,不仅最符合原文的语义,还表达出这一系列动作的速度、展现了鬼的残忍,因此为最佳。
例3.原文:乞人咯痰唾盈把,举向陈吻曰:“食之!”
翟译:He produced a loathsome pill which he told her she must swallow.
马译:The beggar hacked up phlegm until it filled his cupped hand,then held it up to Chen’s face,saying: “Eat it.”
闵译:The beggar spat a great gob of phlegm into the palm of his hand and held it up to her mouth.‘Eat!’
原文中以乞人为焦点的运动事件有“咯(运动+方式)”“唾(运动+方式)”“举(运动+路径)”和“曰(运动+方式)”。翟理思将“咯”和“唾”合译为一个运动produce,侧重于译出“咯”,缺失了原文两个运动的方式信息,“举”的整个运动也缺失了;同时翟理思以从句的形式将原文的焦点“乞人”转为she(即王生妻子)。翟理思词句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将运动事件的静态化描写,将背景信息突出。马尔将“咯”译为“hack (运动+方式)”,hack准确解释为“不停地咳”,其方式信息与原文略有偏差;且病态化了乞人的形象,原文中乞人之形象是“世外高人”。马尔选择不译“唾”,而是将“盈”译为动词。在张友鹤、朱其铠等权威评注中,“盈”在此处为形容词。这就出现了拆前句语义添补后句语义的现象,在语法功能上并不对等。马尔译本的焦点先是乞人后转到痰再到王生妻,而原文的焦点一直是乞人;因此,译文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乞人运动信息,乞人怪诞的形象因此而被淡化了。后半句的译文,马尔采取的翻译策略与闵福德一致。闵福德也将“咯”和“唾”两个运动合译为一个运动——spat,“into”通过词汇化路径并入的方式突显了运动路径信息;闵福德没有用动词体现出“曰”,但其从另一句“Eat”侧面体现了出其“曰”运动信息。由上述可见,翟理思和马尔都选择使用从句的方式将运动事件的焦点转移;闵福德译本含有的运动信息最丰富,一系列运动连贯,进而形成了语篇的连贯,并另起一句构成另一个完整的运动事。综上,翟理思用词偏严谨,使得语言缺少些动态性;马尔译后句译文同翟理思一样,但是闵福德的spat相较于hack更准确、更富有动态性;闵福德使用的运动动词所包含的语义信息最为丰富,在运动框架下,译文显得更具体、更生动,更能体现出原文的动感。
4 结 语
翻译是一个再词汇化的过程,如何将源语言再词汇化为目标语言合适的事件表层形式是翻译界和语言界探讨的一个焦点,本文将译文的运动事件还原成最基本的认知语义结构,再从词汇化模式对三个译文进行运动事件比较后,发现:翟理思译文的动词的方式、路径信息多数少于原文;马尔译文运动事件常与原文存在运动方式信息上的偏差;闵福德译文的动词的方式、路径信息多数符合原文。因此翟理思的译文会更拘泥于原文些,马尔的译文会平淡些,闵福德的译文会灵动些。由于译者对原文语义重心的理解不同,译者选取的动词自然不同。从词汇化模式的角度来看,闵福德的译文,较少使用方式状语,多使用动词来表达路径和方式信息,更能体现出原文故事的生动形象。
译者在汉英翻译中的主观因素在所难免,应意识到不同语言的词汇化模式差异,在充分拆解、还原、合并运动信息后,再进行相应的再词汇化。本研究通过探索《画皮》中英汉运动事件翻译表达差异,以期对汉英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提供指导。当然,本研究选取的运动事件案例较少,还需要更多的运动事件词汇化语义成分实证分析来探索更深层次的译本语言特征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