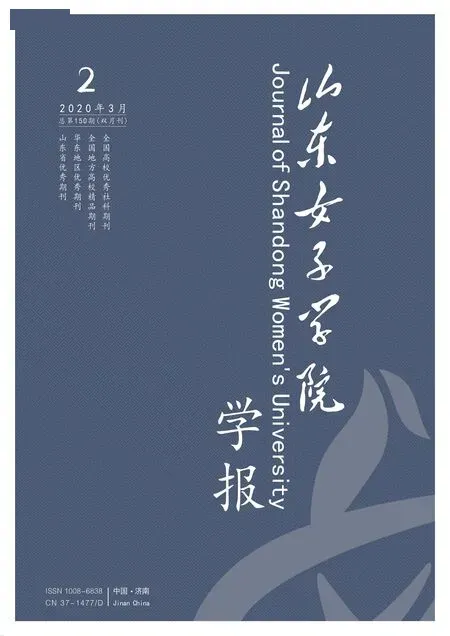《女范捷录》版本考
雷亚倩,李志生
(1.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430072;2.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女范捷录》为王相母刘氏所作,全书十一章,王相为之笺注,正文以骈体书写,篇幅短小,清人周中孚称其“行文纯乎骈体,所以便女子之成诵也。晋升所注亦复浅显易晓,如刘氏者,诚不愧乎为母师矣”[1]179。有关此书的作者及成书情况,正史未有记载,明清文人文集也少涉及,仅从此书正文前的小传,可知作者、笺注者的身份。笺注者王相为由明入清之人,字晋升,号讱菴,琅琊人,至迟生活于清康熙年间。
此书自诞生之初,便与《女论语》《女诫》《内训》一同,被编入《女四书集注》(简称“《女四书》”)中进行刊刻,从未有单行本或单独著录的情况,在流传与刊刻过程中始终保持一卷、十一章的篇数。
《女四书》在女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但目前对它的研究一般还只在对内容的探讨,对版本的研究则明显存在不足(1)如孙新梅按照《女四书》的版本流传,阐述了《女范捷录》的版本流传情况,介绍了在日本、韩国、朝鲜国内《女范捷录》的刊刻与收录情况(氏著《〈女四书〉的编纂与流传》,《兰台世界(中旬刊)》,2013年第32期,第156~157页);陈豫贞从撰写人内心蕴含的性别意识出发,采用文本解读的方式,阐述《女范捷录》的结构、内容及著述目的等,并将其与吕坤的《闺范》从章节编排、教化内容、作者著述动机与目的进行了对比论述(氏著《明代女教书的小同大异——〈闺范〉与〈女范捷录〉的性别意识研究》,《新北大史学》,2006年第4期,第137~150页);熊贤君从女子教育的角度将《女范捷录》中“母仪篇”“智慧篇”“勤俭篇”等章节与其他教育论著进行对比论述,肯定刘氏理念的价值,并提出书中部分内容有待商榷(氏著《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5~116页)。,对《女范捷录》的研究更是差强人意(2)黄丽玲将《女范捷录》的流传情况,置于《女四书》的整体流传下进行探讨,其主要使用的是藏于日本或台湾的《女范捷录》版本,并对之进行了校异。黄氏以清末《状元阁女四书》本为底本,参校了奎壁斋本《女四书集注》《古今图书集成本》、上海宏善书局《女子四书读本》,比较了不同版本《女范捷录》的文字差异。但此文参校的版本数量相对较少,对了解《女范捷录》的版本流传情况帮助有限,其文还是主要集中在对内容、思想、文章风格等的研究分析(氏著《〈女四书〉研究》,台湾南华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有鉴于此,我们查阅、收集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处所藏《女范捷录》版本共计12种,虽所见仍不够广博,但已大略涵盖了《女范捷录》的各类重要版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女范捷录》的版本情况作一考析。
一、《女四书集注》本
(一)多文堂本《闺阁女四书集注》
多文堂所刊《女四书》本,是目前文献记录最早的版本,遗憾的是,该本目前不知所踪,仅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有记载:
《闺阁女四书集注》 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多文堂刊本。
(明)王相笺注。相字晋升,琅琊人。是书前有万历八年神宗皇帝御制序。卷首题莆阳郑汉濯之校梓。九经堂刊曹大家《女诫》、仁孝文皇后《内训》二种。后多文堂刊《女论语》及《女范捷录》,为《女四书》。[2]843
依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我们可知其所著录书目的出处,还可知其著录书目遵循的所见刊印本的原则。他在寓目了多家私藏与全国各地图书馆馆藏后,逐一著录,且“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也一一采录”[2]5-6。他在过目了天启四年(1624年)多文堂刊印的《女四书》后,据该本题名,著录为“《闺阁女四书集注》”。但黄丽玲认为,胡文楷著录该本《女四书》时,添加了“闺阁”二字,意在强调此书所设定的阅读群体为女子,且对“集注”释为“‘集注’者,言王相‘集而注之’之意也”[3],但此仅是黄氏的推断而已。
又,胡书《凡例》称:
书囊无底,闻见有限,著录各书,或仅著初刻,而覆刻重刻之本,未见著录;亦有仅据重刻,而原刻不详者。而坊间石印之本,前以其不甚珍贵,未经采集,故未能一一著录。[2]10
可知胡氏所寓目多文堂本应为初刻本,而非覆刻或重刻,且亦非石印本,其版面清晰精致。《闺阁女四书集注》虽著录为多文堂本刊刻,但实则为由九经堂与多文堂两书坊合刻而成,其中《女范捷录》为多文堂刊刻。胡文楷曾寓目了多文堂本《女范捷录》,在其条目后书“见”,并对该书的卷数、章节数、作者生平进行了简单的记载,《条目》云:
《女范捷录》,(明)刘氏撰,《闺阁女四书》著录。(见)
(刘)氏,江宁人,王集敬妻,王相母。幼善属文,苦节六十年,年九十卒。
《女范捷录》一卷,明末多文堂刊本,列入《闺阁女四书》,子王相笺注。凡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十一篇。[2]196
刘氏守节六十年,著成该书,王相在编著《女四书》时,出于对母亲的尊敬,将其著作一并收录。该书无论是从作者的影响力,抑或内容价值方面(在女教书史中的地位),均无法与《女四书》中的其他三书相比拟,在流传中也不具备单独流传与生存的能力,往往被其他女教丛书排除在外,如《教女遗规》就仅收录了《女诫》《内训》《女论语》[4]。
胡氏之后,未见他人寓目或其他书目著录过多文堂所刊《闺阁女四书集注》,胡氏也未明言该书的来源与去向,其书至今下落不明。
(二)奎壁斋本、书业堂本《女四书集注》
1.奎壁斋本《女四书集注》。奎壁斋本《女四书集注》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初刻本,具体刊刻时间不详,文字不避康熙、乾隆之讳。版框大小约18cm×12.8cm,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版心书大字“女四书”后接小字各书名及页码。版面模糊漫漶处较多,《女范捷录》叶十六缺失约两平方厘米的纸片。此本封面除书名外,另有“奎壁齋訂本”“金陵鄭元美行梓”等字。前有《神宗皇帝御制女诫序》,《女论语》卷首题“琅琊王相晉升箋注 莆陽鄭漢濯之校梓”,《内训》末页、《女范捷录》末页牌记曰“莆陽鄭氏訂本 金陵奎壁齋梓”,另《女范捷录》刘氏的小传后书“金陵奎壁齋梓”六字。《女诫》首页、《宋若昭女论语》首页、《女范捷录》首页及全书末页分别有“北京圖書館藏”朱长方印。
《王节妇女范捷录》凡十一章,卷首题“男王 相晋升 訂註”,前有王相之母刘氏的作者小传,《小传》云:
先慈劉氏,江寧人,幼善屬文,先嚴集敬公元配也。三十而先嚴卒,苦節六十年,壽九十歲。南宗伯王光復、大中丞鄭潛庵兩先生,皆旌其門。所著有《古今女鑒》及《女範捷錄》行世。[5]
刘氏的寿龄为九十,因此在后世的文献中,也将其记为“王寿母”,如南清河王氏辑刻的《牖蒙丛编》本《女范捷录》,就署为“明琅琊王壽母撰”,小字“壽母江寧劉氏子相”。
关于奎壁斋,瞿冕良认为,“‘奎壁斋’又称‘奎壁堂’,为明万历间金陵人郑思鸣、郑大经的书坊名,在状元坊”[6]623。而郭明芳则认为,“明万历以降,南京有两‘奎壁’为名的书肆,一为皖南旅外的郑思鸣奎壁堂,一为福建旅外的郑元美奎壁斋,且‘堂’早于‘斋’。前人以二家同名同姓而混为一家”[7],且两书坊具有不同的刊印特征,如“奎壁斋”所刊行书籍末页常有“金陵奎壁斋”刊行的牌记,“奎壁堂”则无;又如“奎壁堂”扉页版式大多相似,“奎壁斋”则不同[7]。《女四书集注》中“奎壁齋訂本”与《内训》末页、《女范捷录》末页牌记所刻“金陵奎壁齋梓”,应指“奎壁斋”书肆,而非郑思鸣“奎壁堂”。另,《女四书集注》封面中所书“金陵鄭元美行梓”,也显示在《女四书集注》刊刻时,奎壁斋当时的坊主为“郑元美”。
对于郑元美的身份,学界也多有歧说。郭明芳认为,郑元美与郑思鸣并非同一人,郑元美为郑汉,字濯之,元美可能为别号兼开业商号[7]。尤海燕也否认郑思鸣即郑元美的说法,其理由如下:首先,郑元美的刊刻活动集中于明天启后到清康熙前,而郑思鸣出版刊刻的活动多集中在万历至天启间[8];其二,从书籍刊刻时间看,如郑思鸣是郑元美,其刊刻书籍的时间当始自明万历二年(1594年),至迟结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歌林拾翠》刊刻,其间跨度长达六十五年,由此可知,郑元美应为郑思鸣、郑大经之后的奎壁斋坊主[8];其三,郑元美当在天启后接管奎壁斋,刊刻了《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女四书集注》等书,在《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正文首页标注有“琅琊王相晋升增注 莆阳郑鉁元美校梓”一行,由此知郑元美名郑鉁,字元美[8]。
此外,尤海燕据《奎壁斋增订评注广日记故事》正文首页标注的“琅琊王相晋升增注 莆阳郑鉁元美校梓”认为,此书实际由郑元美与王相合作完成,“是奎壁斋或者说是郑元美主持这次刊刻,并把具体编订任务交给王相”[8],并由此推断,“郑元美和王相是同时代的人,他应该与王相一样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动乱时代”[8]。这一推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王相至迟生活在康熙年间,在郑元美卸任奎壁斋坊主之后仍然在世,也因此,在郑元美刊刻《女四书集注》时,王相或见过此书,其内容应较为准确、可信。
2.书业堂本《女四书集注》。书业堂本《女四书集注》是以奎壁斋本《女四书集注》为底本进行的覆刻,该本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为乾隆六十年(1795年)刻本。其版框的尺寸大小约为18cm×11.3cm,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字体为方体字,版式、字体与奎壁斋本一致。版面模糊漫漶处颇多。此本封面除书名《女四书集注》,另有“奎壁齋訂本”“書業堂梓行”“乾隆六十年秋鐫”,前有“神宗皇帝御製女诫序”。《神宗皇帝御製女诫序》与《仁孝皇后文内训》首页均有“日本政府圖書”“書籍館印”朱方印及“淺草文库”朱长方印,《仁孝文皇后内训》末页有“昌平坂学問所”墨长方印,另有朱色“文化乙丑”四字,《宋若昭女论语》末页有“日本政府圖書”朱长方印。《王节妇女范捷录》末页有“日本政府圖書”朱长方印,“昌平坂学問所”墨长方印,另有朱色“文化乙丑”四字。文字避雍正之讳,“胤”采取缺笔避讳的方式,少去右边“乚”。
书业堂本完全承袭奎壁斋本的版式与字体,但对内容进行了修改与重新校订。以奎壁斋本(简称“奎本”)与书业堂本《女范捷录》(简称“书本”)两两相校可以发现,书业堂本作了改字、删字、增字、颠倒字序等变动。改字如“奎本”《母仪篇》中的“遵母教也”,“书本”作“遵母教矣”;“奎本”《忠义篇》中的“含笑入地矣”,“书本”作“含笑入地下”。意思相近之字的改动,如“奎本”《慈爱篇》中的“明倫之本”,“书本”作“人倫之本”;“奎本”《厚德篇》中的“恭請大舜”,“书本”作“恭詣大舜”。此外还有多处改动,如“奎本”《慈爱篇》中的“季隗生趙姬”,“书本”改作“季隗生趙盾”,为确。按,季隗与赵姬同为文公之妻,故季隗所生之子为赵盾,而非赵姬,“奎本”有误。
二、《校订女四书集注》与《状元阁女四书》
清末,《女四书》受到了高度重视,其中苏州崇德书院重新校订的《女四书》和李光明庄刊刻的《状元阁女四书》,最为人所熟知。潘遵祁据坊间传本,对王相《女四书集注》进行了重校,随后交付苏州崇德书院进行了刊印;其后的光绪年间,南京李光明庄刊刻了《状元阁女四书》,该本也成为清代最流行的《女四书》版本,多家书肆如文成堂、善成堂、共赏书局、江左书林等,相继覆刻。有关《校订女四书集注》与《状元阁女四书》之间版本流传的关系,可参看王丹妮、李志生的《明清时期〈女论语〉版本考述》一文,该文在考述《女论语》版本流传情况时,一并探讨了《女四书》在清代的版本总体流传[9]。该文认为,李光明庄本以崇德书院的《校订女四书集注》为底本,或另参考其他坊间流传的《女四书》,而进行了简单的校勘,修正了崇德书院本的一些错误,但也将多处原本正确的地方错改[9]。本文即以此文为参考,对《女范捷录》的崇德书院本和李光明庄本,作一简述。
(一)苏州崇德书院本《校订女四书集注》
苏州崇德书院本《校订女四书集注》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刊刻于光绪三年(1876年),封面题名《校订女四书笺注》,内封牌记“光緒丁醜刊於蘇州崇德書院”。版框大小约17.6cm×13cm,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或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前有潘遵祁《序》,《序》文开头纸页破损,缺“詩三”两字,《序》文后署“光绪丙子初夏吴县潘遵祁序”。《王节妇女范捷录》版心书大字“女四書”,后接小字“女範”及页码。首页题“琅琊王相晉升箋注 莆陽鄭漢濯之校梓”。文字不避康熙、乾隆讳。
潘遵祁(1808—1892年),苏州吴县人,字顺之,号西圃,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后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任翰林侍读。后无意仕途,归隐邓尉,筑香雪草堂,著有《西圃集》,卒年八十五。潘遵祁《序》作于光绪丙子年(1876年),称其承圣人之重,又有感于陈宏谋对闺门之教的看重,更因坊间流传的《女诫》《女论语》等书翻刻粗陋,徒沦为村塾口授之书,不为书香世家所读,故应崇德书院之邀,重新校订王相所注《女四书》。
在版式上,崇德书院本《女范捷录》与奎壁斋本、书业堂本非常相似,且字体同为方体字。文字上,潘遵祁在校订过程中,对一些地方进行了重新改动与修订。以奎壁斋本(简称“奎本”)与崇德书院本(简称“崇本”)《女范捷录》两两比对发现,“崇本”对“奎本”进行的改动,包含了对异体字、形近而误之字、近意之字、语气虚词的改动,其见如下对比之例:
《统论篇》中,“奎本”为“比教男為尤切”,“崇本”为“比教男為尤明”。
《后徳篇》中,“奎本”为“恭詣大舜”,“崇本”作“恭请大舜”。
《贞烈篇》中,“奎本”为“守死無二”“棄官之豫章商船”,“崇本”作“于死無二”“棄官尋豫章商船”。
《忠义篇》中,“奎本”为“淮之營妓也”,“崇本”作“淮之官妓也”。
《秉礼篇》中,“奎本”为“妻曰金無主者”,“崇本”作“妾曰金無主者”。
《智慧篇》中,“奎本”为“嫉之者眾”,“崇本”作“欺之者眾”。
《勤俭篇》中,“奎本”为“省約而甘淡薄”,“崇本”作“儉約而甘淡薄”。
“崇本”虽对字进行了类似如上的改动,但并未影响文之大意。
在校订的过程中,“崇本”也出现了误校,其亦见如下对比之例:
《后德篇》中,“奎本”为“次妃簡狄”,“崇本”作“矣妃簡狄”。
《孝行篇》中,“奎本”为“漢姜詩妻龐氏”,“崇本”作“妻姜詩妻龐氏”。
《贞烈篇》中,“奎本”为“南昌巨賈謝啟”,“崇本”作“南昌巨賈謝唐”。
《贞烈篇》中,“奎本”为“元末楚中大饑”,“崇本”作“元末漢中大饑”。
《才德篇》中,“奎本”为“鄭風詩雲”,“崇本”作“齊風詩雲”。
《才德篇》中,“奎本”为“雖遇三黜”“終不敝兮”,“崇本”作“雖遇三等”“終不教兮”。
(二)李光明庄本《状元阁女四书》
李光明庄本刻于光绪六年(1880年),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封面朱墨题名《状元阁女四书》,内封刻朱色李光明庄书局的广告词“江南城聚寶門三山大街大功坊郭家巷內秦狀元巷中李光明莊重複校對自梓童蒙各種讀本揀選重料紙張裝訂發兌”。前有《神宗皇帝御制女诫序》,序文刻于红靛套印龙凤图框正中,共四页,半页五行,依序文内容提一格、两格、三格不等。叶四b牌记曰“光緒六年八月”,另有“天子萬年”四字。《曹大家女诫》首页、全书末页有“北京圖書館藏”朱长方印。版框大小约18.3cm×13cm,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上方边框下凹一字,刻“女四書”三字,鱼尾处刻大字“卷下”、小字“女範”,版心下方刻“李光明莊”四字,字体为方体字。正文及注文部分有圈点句读。书后附潘遵祁序,实为承袭崇德书院本《校订女四书笺注》中潘遵祁之序,改“跋”为“序”。全书分上、下两卷,《女范捷录》位于卷下部分,避康熙讳,“玄”作“元”。
李光明庄书局开设在南京三山街大工坊秦状元巷中,并设分肆于状元境口状元阁,所刻书籍前页多印有推广书局的告白启事,版心下刻“李光明庄”四字[6]316。
李光明庄《状元阁女四书》中的《女范捷录》部分,整体承袭崇德书院本,以李光明庄本(简称“李本”)与崇德书院本《女范捷录》(简称“崇本”)两两进行比勘,发现“李本”较“崇本”增加了三十七字,而改动的大部分,则是异体字、形近而误、语气虚词和字序变换等,这些改动对理解文意的影响较小,暂且不论。“李本”最大的改动是在《才德篇》中,“李本”在对“柳下惠之妻”的介绍中,增加了“屈柔從俗。不強察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呜乎。哀哉!魂神泄兮”等字。该句引用的是刘向《列女传》中的文字:“鲁大夫柳下惠之妻也......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亦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10]李光明庄除刊刻《女四书》外,还刊刻了其他女学书籍,《列女传》便是其中一种,故其或在校订《女四书》时,参照或引用了《列女传》中有关“柳下惠之妻”的记载,对王相所作的笺注进行了扩充。
三、《女子四书读本》
《女子四书读本》诞生于民国时期,被上海诸多书局刊印销售,如会文堂书局、上海锦章图书局、铸记书局、鸿文书局、扫叶山房、广益书局等书局。
《女四书》更名为《女子四书读本》,主要受到清末民初新式“女子教科书”发展的影响。自维新派人士主张“兴女学”“创设女学堂”始,重视女子教育与女校兴办,随之兴起了国人自编女子教科书的潮流。虽然如此,1902年和1904年清廷颁布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还是将女子教育排除在外,甚至主张由官方编写女子教科书,发放至各家各户,而其内容则仍是传统的女教书,“令各省学堂将《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女训》《教女遗规》等书,择其最切要而极明显者,分别次序浅深,明白解说,编成一书,并附以图,至多不得过两卷,每家散给一本”[11]。虽至1906年以张之洞为首的诸人倡导新编女学课本,但也始终未能打破继承封建女教的局面。
同期,爱国女校伦理教习叶浩吾先生、《女子新读本》作者杨千里,则猛烈抨击诸如《女诫》《女四书》等传统女学读本。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终于1907年,颁布了《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女子学堂章程)》,并以之为依据,开始了女子教科书规范化的编写。
袁世凯复辟帝制、尊孔复古,女子教育界又掀起了复古倒退逆流,重新鼓吹“贤妻良母主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传统女教书又得到了重刻与销售的机会。除此,《女四书》改名为《女子四书读本》,是对新式女学读本题名的模仿,这样的更名使得传统《女四书》在题名上,与新式女学教科书保持一致。
(一)上海锦章书局《女子四书读本》
此本为民国石印本,具体刊刻时间不详。封面题名《女子四书读本》,另有“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数字。首页有“北京圖書館藏”朱长方印。版框大小约17.5cm×12.3cm,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下方刻“上海錦章圖書局校印”。该本书页排序有误,首页为《女诫》,其后为潘遵祁序、《神宗皇帝御制女诫序》。字迹清晰,墨色均匀,应为初印本。书中内容全取自李光明庄本《状元阁女四书》,唯将“潘遵祁跋”改作“潘遵祁序”。此书分为上、下两卷,卷下书衣页题名“女子四書讀本下”,封面页书“女子四書讀本”“校正無訛”“珍記下”“上海錦章書局印行”,外框四角有边框装饰。《女范捷录》末页版心向内装订。
锦章书局是一家老牌出版机构,创办于1901年3月,出版的图书大多带有旧书痕迹,有的版本只不过是翻个新式花样[12]。但该本《女范捷录》摆脱了李光明庄本《女范捷录》的版式,重新调整了布局,采取页十一行、大字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行四十二字的版式,内容紧凑,字体工整但略显促狭。从印本版面情况可以看出,该本墨色均匀,字迹清晰,应是重新刻版,为初印本。
(二)上海会文堂书局《女子四书读本》
会文堂本《女子四书读本》同为民国石印本,刻于民国五年(1916年)。封面题名《女子四书读本》,另有“丙辰孟陬重鐫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等字。前有《神宗皇帝御制女诫序》及潘遵祁序。版框大小约16.9cm×11.6cm,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是书内容亦承袭李光明庄《状元阁女四书》,与锦章书局本情况相似,将潘遵祁所作跋文改为“序”。《曹大家女诫》首页、《女范捷录》末页有“北京圖書館藏”的朱长方印。
该本版式与锦章书局相仿,但采取半页十二行,大字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行四十四字的版式。国家图书馆所藏锦章书局本《女子四书读本》与会文堂本《女子四书读本》,无论从外观、书衣、封面、扉页,抑或版式等,相似度都极高,且各本墨色清晰,均为初印本。
《女子四书读本》诞生于新式女学教育潮流的背景下,以区别于《状元阁女四书》的题名与版式,形成了新的流传系列。以锦章书局本(简称“锦本”)、会文堂本(简称“会本”)与李光明庄本《女范捷录》(简称“李本”)两两比对后发现,“锦本”与“会本”大多为异体字、形近而误、调整字序、改字或增加虚词的改动,未体现出新式女学的痕迹。文字更改之例,如:
“李本”《后德篇》中,“文王之妃太姒”“高帝創洪基於草莽”,“锦本”作“文王之太姒”“高帝創洪於草莽”。
“李本”《智慧篇》中“夏寒浞弑夏帝相”,“会本”作“夏寒弑夏帝相”。
除此,“锦本”与“会本”在翻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如《才德篇》中“女尚宮宋氏”,“锦本”误作“女尚書宋氏”;《才德篇》中“《論語》成於宋氏”,“会本”误作“六經成於宋氏”。
四、结论
关于《女范捷录》的版本,目前传世的数十种,均为清刻本与民国石印本。这些版本实分为奎壁斋《女四书集注》本、崇德书院《校订女四书集注》本等两个系统。《女范捷录》与《女四书》的流传系统一致,最早的版本为奎壁斋《女四书集注》本,该本可能在王相在世时刊刻,在内容上更接近《女四书集注》的原貌。清末《女四书》受重视,潘遵祁据坊间传本重校王相《女四书集注》,其后由苏州崇德书院刊印发售。随后南京李光明庄以崇德书院本为底本,刊印了《状元阁女四书》。此后,还有多家书肆相继覆刻,如文成堂、善成堂、共赏书局、江左书林等,诸多《状元阁女四书》,都以潘遵祁所校崇德书院本《校订女四书集注》为祖本。
民国时期,《状元阁女四书》受到“新式女教科书”编写与“尊孔复古”逆流的影响,更名为《女子四书读本》,被上海多家书局重刻销售。除此,另有《古今图书集成》及《牖蒙丛编》收录了《女四书》,这些《女四书》删削了王相的笺注,严格避清帝康熙、雍正之讳,因未有相关文献记载,暂无法确定其所据底本为何。
从对《女范捷录》版本源流的梳理、校勘诸本《女范捷录》之间的文字差异,我们能够发现,诸本《女范捷录》多为字词差异,文句大意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