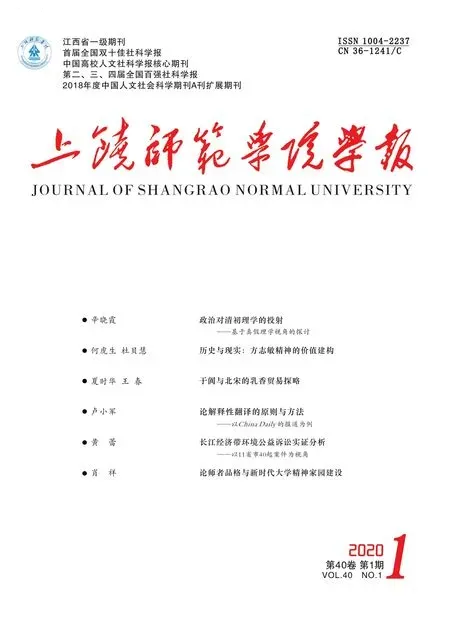政治对清初理学的投射
——基于真假理学视角的探讨
(天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4)
关于清初理学,学界相关研究皆认为清入关后“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特别是康熙尊崇朱学,使理学在清初颇为兴盛。毋庸置疑,政治的支持对学术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同时,学术在获得政治优待的同时,需要在政治的逻辑下有所调适。“假定某一学术思想是要通过政治以发挥其效用,则必接受政治领域中的法式。”[1]由此,理学逐渐失去了“道理最大”的理论底气。清初理学强调实理实行,以及理学大臣积极参与论证治统即道统,且两者合一落实于康熙,皆有政治的投射。加之政治对理学的诉求在于守陈而非推新,清初理学日趋失去思想活力。其后,更具思想吸引力的经学取代理学成为学术主流,理学衰落,其在清初的兴盛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1)“清前期,程朱理学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出现兴盛趋势。”参见:史革新《清代理学史》,广州:广州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
因此,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可以成为观察理学在清初走向的一个视角,贯穿康熙一朝的真假理学话题即突显了此点。就“真假”来说,既涉及真、假的标准是什么,也涉及由谁来制定标准的问题。而从始至终,主导权都在康熙,这意味着,政治介入并引导了理学的调整。一则,理学大臣与民间理学家共同构成清初理学主体(2)“当时的程朱理学家,有在朝为官者,有居民间未仕者。”“在清初理学复兴中,高居庙堂的理学家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理学群体。由于他们跻身于官场,有政治优势可以凭借,对于理学的提倡非一般的士人所可比拟。” 参见:史革新《清代理学史》,第158页。,理学大臣的理学倾向将对清初理学的方向产生影响;再则,官方认定的理学作为传播最广、覆盖最大的思想形态,必然对清初理学的发展具有导向意义。可以说,真假理学是一种政治性的学术现象,从中可以窥见政治对清初理学走向的影响,这是完整清初理学演变逻辑性的一个环节。
一、真假理学的政治诉求
随着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平定,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对于早就定为官学的理学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关注。关于真假理学,康熙一生曾多次提及(3)根据《康熙起居注》记载,二十二年(1683)十月、二十三年(1684)六月、二十四年(1685)四月、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三十二年(1693)四月、三十三年(1694)闰五月、三十六年(1697)七月、四十三年(1704)六月、五十二年(1713)九月、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皆提到关于真假理学的问题。,《起居注》的记载中,相关讨论最早在二十二年(1683)。
(十月)十四日辛酉。早,上御乾清宫,讲官牛钮、张玉书、汤斌进讲。……讲毕,上问:“理学之名始于宋人否?”张玉书奏曰:“天下道理具在人心,无事不有,宋儒讲辨更加详密耳。”上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色,彼此辩论益多。”牛钮奏曰:“随事体认,义理真无穷尽,不必立理学之名。”上又问:“汤斌云何?”斌奏曰:“理学者本乎天理,合乎人心,尧、舜、孔、孟以来,总是此理,原不分时代。宋儒讲理,视汉、唐诸儒较细,故有理学之名。其实理学在躬行,近人辨论太繁耳。”[2]1089
康熙由“理学之名”发问,应当是他平日里已有清晰的理学态度,所以大臣皆能准确迎合他的立场回答,表示理学之理切于日用,重在躬行,围绕于“理学”的纷争辩论不必要且繁复。
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康熙君臣提及的理学“辩论”并非无谓,从产生伊始,学者们关于理气心性的相互辩论所激发的思想活力是推动理学向精深处探索的动力。但政治对理学的诉求不在于思辨和创新,“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2]116统治者看重的是理学于治理的效用,重在实行不在空谈。因此,康熙有意弱化理学中的抽象思辨,视其为“空言”,理学大臣也积极响应。加之清初普遍认为空谈性理是明亡的一个原因,批评性理流于空、虚,不切于日用是思想主流,思想领域出现了“去形上化”的倾向(4)参见:王汎森《清初思想中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任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三分,1998年。。在思想反思和政治诉求的合力下,重实理、实行成为清初理学调整的一个方向,不过产生的弊端是思辨性日渐不足,“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3]13。
君臣关于理学的讨论结束后,康熙表明了提问的缘由:
上曰:“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张玉书奏曰:“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学只在身体力行,岂尚辞说。”奏毕,出。[2]1089
朝中多有大臣以理学自居,却言行不符,这都是假理学。进而康熙提出对真理学的理解,切实躬行,行事符合道理,言行一致。
理学自清入主中原即被定为官学,而读书科举是入仕的主要途径,可以说道学之人是政治主体的主要构成。大臣们的假理学,不仅是学术问题,更事关治理和社会教化,甚至是忠诚。鉴于此,康熙多次批评假理学,以三十三年(1694)的“理学真伪论”考试最为严厉,多名位高权重的大臣被点名斥责。
二、理学大臣的假道学
康熙三十三年(1694)闰五月初四日,康熙召试翰林官于瀛台,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考试。关于考试缘由,孟森、史革新认为直接原因是当年四月李光地未坚持按制回乡奔丧,被视为假道学,招致弹劾,此后康熙虽出面平息了风波,但决意清算假道学(5)孟森:“至闰五月初四日试翰林官,乃以理学真伪论命题,不可谓非为光地发矣。”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63页;史革新:“一时之间,朝议哗然,迫使康熙帝出面干预。风波虽然迅速平息,但是玄烨对假道学的憎恶已经不可压抑,他决心进行一次总的清算。”参见:史革新《清代理学史》,广州:广州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这一缘由未必恰当,一则,此时李光地颇受重用,特许他在任守制是康熙的谕旨;再则,李光地被弹劾,也是康熙极力保全(6)《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二列传四十九: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参见:《清史稿校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540页。。所以,康熙虽对李光地也有过假道学的批评,但“理学真伪论”未必因此而起。
且康熙对真假理学的关注由来已久,终其一朝多有涉及,“理学真伪论”考试是个必然事件,即使不在此时,也会在其他时间发生。
康熙初,圣教涵淳,人才蔚起,一时如张文端、魏敏果、熊文端、汤文正、张清恪、李文贞,皆崇尚理学,践履笃实。然矜谨自持中,尚多罅隙。如魏敏果、熊文端、汤文正、李文贞辈,皆在圣人品题之中。故三十三年,考试翰詹于丰泽园,命题“理学真伪论”,所以正人心、学术者,至为深切。[4]
从这里可见康熙朝理学的大致风貌,首先是康熙朝文教兴盛,“圣教涵淳”。其次,崇尚理学是当时风气,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所以“人才蔚起”。第三,此时的理学强调“践履笃实”的层面。第四,理学之人多言行不一,朝中大臣虽以理学自居,但行为却不似理学应有,“尚多罅隙”。最后一点也是康熙以“理学真伪论”为题考试翰林院89名官员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出的是,考试不完全为探讨学问,正学术在于为理学订立标准,正人心在于纠正理学大臣的不正之风。
试后康熙亲自阅卷,并下谕旨总结此次考试。谕旨几乎全为批评,熊赐瓒首当其冲:
谕大学士等:初四日召试翰林官于丰泽园,出“理学真伪论”,此亦书籍所有成语。熊赐瓒见此辄大拂其意,应抬之字竟不抬写,不应用之语辄行妄用。[5]758
熊赐瓒是康熙老师熊赐履的弟弟,二十五年(1686),太子十三岁,他以理学被康熙选为太子讲官。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继承人的教育,选择熊赐瓒,除了熊赐履的原因(太子六岁时,选张英、李光地、熊赐履为师),也因为康熙对熊赐瓒学问的信任。但是,在此次考试中,康熙认为熊赐瓒见题目已经觉得不如意,不解题目本意,所作之文非常牵强,不仅内容差强人意,作文形式也不规范,忽略了抬写(7)旧时一种行文书写格式。凡臣下奏章及一般文书中,遇及皇室、陵寝及天地等字样,必于次行抬头一格或二三格书写,以示尊敬。的格式,用语也不恰当。
无论是文意,还是格式错误,康熙对熊赐瓒的不满主要还是围绕于考试,对其他大臣则牵扯到人事、品德等更复杂的事项。此时魏象枢已经去世,且与考试无关,不想康熙帝翻出陈年旧事:
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亦系讲道学之人,先年吴逆叛时,着议政王大臣议奏发兵。魏象枢云,此乌合之众,何须发兵,昔舜诞,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烦用兵,抚之自定,与索额图争论成隙。后十八年,地震时,魏象枢密奏,速杀大学士索额图,则于皇上无干矣。朕曰,凡事皆朕听理,与索额图何关轻重,道学之人果如是挟仇怀恨乎。[5]758
魏象枢(1617-1687)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之一,“公为本朝直臣之冠”[6],他为官耿直,不徇私情,雍正八年(1730),诏入祀贤良祠。康熙提及早先朝廷讨论是否发兵讨伐吴三桂叛乱时,他的观点迂腐无用,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且由于与索额图因观点不合而心生怨恨。此后借地震事由,魏象枢密奏速杀索额图,让其承担地震的罪过从而推脱皇帝的责任。
地震的事发生在康熙十八年(1679),距此已十五年。从记载来看,对于魏象枢的言行,当时康熙并未有明显反对(8)《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三列传五十:(康熙十八年)七月,地震,象枢与副都御史施维翰疏言:“地道,臣也。臣失职,地为之不宁,请罪臣以回天变。”上召象枢入对,语移时,至泣下。明日,上集廷臣於左翼门,诏极言大臣受贿徇私,会推不问操守;将帅克敌,焚庐舍,俘子女,攘财物;外吏不言民生疾苦;狱讼不以时结正;诸王、贝勒、大臣家人罔市利,预词讼:上干天和,严饬修省。是时索额图预政贪侈,诏多为索额图发,论者谓象枢实启之。参见:《清史稿校注》,第8547-8548页。。但此时康熙却深感不满,指责魏象枢借公事而泄私愤,感慨道学之人却如此挟仇怀恨。关于此事,有学者认为应从满汉矛盾,借批评假道学打击汉臣的角度理解(9)参见《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心理阴影——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1-28页。。但是此谕中也批评了满臣德格勒,且结合整体语境,康熙的针对性并非满汉问题,主要还是满汉大臣们的假道学行径。
正如康熙在谕旨中所强调,魏象枢是“道学之人”,而“道学之人”不应该在公事中挟仇怀恨。则关键点,不在于他的行为本身,而是在“道学”的名义下有此行为。康熙反感的是以道学自居,但言行与道学不符的假道学大臣。从后面谕旨的内容也可发现,考试虽以“理学真伪”命题,但康熙的关注点全在道学之人。
熊赐履、李光地在康熙朝皆为理学名臣,在不同时期对康熙产生过重要影响,“左右圣祖者孝感、安溪后先相继。”[7]1531熊赐履(1635-1709),湖北孝感人,在康熙早年,他任讲官,举经筵,颇受康熙的信任和尊重。李光地(1642-1718),福建泉州安溪人,康熙欣赏他的学问、能力,恩宠甚隆,位极宰辅。即使对这两位甚为欣赏的大臣,康熙在谕中也直接以假道学相斥责。
又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曾授德格勒易经,李光地请假回籍时,朕召德格勒进内讲易。德格勒奏言,李光地熟精兵务,其意欲为将军提督,皇上若将李光地授一武职,必能胜任,反复为李光地奏请,尔时朕即疑之。[5]758
李光地是熊赐履以理学之名推荐给康熙的,但两人其后各自形成势力,相互争斗。德格勒曾向李光地学易经,且李光地以贤举荐过德格勒,两人有私交(10)《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二列传六十九:德格勒,……李光地亟称其贤。……二十六年,光地乞假归,入辞,面奏德格勒、徐元梦学博文优。参见:《清史稿校注》,第8756页。。因而,德格勒多次借机在康熙面前夸赞李光地熟精兵务,奏请授予武职,这引发康熙对于两人相互标榜,以公谋私的怀疑。
同时,由于熊赐履与李光地不和,德格勒也在康熙面前贬低熊赐瓒:“德格勒又奏熊赐瓒所学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真伪,将德格勒熊赐瓒等考试。”[5]758此类言论应当比较频繁,所以康熙说“德格勒每评论时人”[8]8756,因此特召德格勒、熊赐瓒等当面考试,验证各自的水平,并让其他大臣浏览试卷以作凭证,大臣中有汤斌,此事发生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11)《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二列传六十九:二十六年,光地乞假归,入辞,面奏德格勒、徐元梦学博文优。逾月,上召尚书陈廷敬、汤斌等及德格勒、徐元梦试於乾清宫。阅卷毕,谕曰:“朕政暇好读书,然不轻评论古人。评论古人犹易,评论时人更难。如德格勒每评论时人,朕心不谓然,故召尔等面试。妍媸优劣,今已判然。学问自有分量,毋徒肆议论为也。”参见:《清史稿校注》,第8756页。。
汤斌见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坠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时不能忍笑,以致失仪。既而,汤斌出,又向众言,我自有生以来未曾有似此一番造谎者,顷乃不得已而笑也。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今汤斌虽故,李光地、德格勒见在也。[5]758
汤斌也是清初名臣,以清廉著称,雍正时入贤良祠,三十三年(1694)已经去世。针对汤斌在德格勒文章事件上的表现,康熙以“道学之人”的名义批评他对人主和其他大臣的说辞前后不一,有违忠诚。“所谓真理学、身体力行,说到底就是对皇帝的忠诚”[3]15。因此,汤斌也非真理学。
在谕旨最后,康熙再次以“道学之人”指责熊赐履务虚名,有违道学之人的品格,“又熊赐履所著《道统》一书,王鸿绪奏请刊刻,颁行学宫,高士奇亦为作序,乞将此书刊布。朕览此书,内过当处甚多。凡书果好,虽不刻自然流布,否则虽刻何益,道学之人又如此务虚名而事干渎乎。”[5]758熊赐履著《道统》,趋承逢迎之人趁机吹捧,为其请旨刊刻,以颁行学宫,而熊赐履也欣然承之。康熙翻阅过此书,认为不无偏颇之处,熊赐履沽名钓誉,并没有相称的学术水平。
各人之间恩怨利益如何暂且不论,康熙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大臣们的假道学他了然于心,且深为反感。魏象枢、汤斌、熊赐履、李光地都是朝中重臣,皆被视为理学名臣,理应行为世范,却也是结党营私、言行不一、沽名钓誉,这每每使康熙感慨道学之人怎么如此。
不过,虽然康熙对各个大臣批评严厉,但是,除魏象枢、汤斌两人已逝不算,李光地此后位极宰辅,不必多说,对熊赐履也是多有优待,圣宠不减。
“理学真伪论”考试之后,三十四年(1695),熊赐瓒因奏对欺饰下狱,此正值熊赐履因票拟案被罢免后重新起用为吏部尚书。御史龚翔麟趁机弹劾熊赐履,奏请严惩“赐履伪学欺罔,乞严谴”[8]8538。他认为熊赐履以道学虚名欺世,前因票拟有误而故意隐瞒,被免官回乡,现在康熙不计前嫌又重用他。但熊赐履不知感恩,其弟有过,并不处罚,属于负恩溺职。“赐履窃讲学虚声,……皇上从宽,放归田里。旋赐起用,晋位冢宰,毫无报称。其弟赐瓒包揽捐纳,奉旨传问,赐履不求请处分,犹泰然踞六卿之上。乞赐罢斥。”[8]8538以假道学批评熊赐履原本也是康熙自己的态度,但就此弹劾,康熙却并不在意,且赦免熊赐瓒,“上不问,赐瓒亦获赦”[8]8538。
可见,康熙在“理学真伪论”谕旨中的斥责并非是真心否定这几人,而是借此警戒朝中大臣的假道学风气,以理学之名整顿政治,视理学真伪评定为政治治理中的一种有效手段。
三、以实济为指向的真理学
弱化理学的思辨性,强调躬行实践理学,以理学之名整顿大臣,皆透露出理学在政治中工具层面的意义。在此逻辑下,康熙更侧重从效果的角度衡量理学,治理有实效,有政绩的理学大臣,才是他认可的真“道学之人”。
在总结“理学真伪论”谕旨的最后,康熙说:“朕惟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存之于心,此等人议论又何足较也。”[5]758作为君主,康熙最为看重的是治理成效,众人“以道学为得君之专业”[9]561,但这只是仕途的起点,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应落实到田赋、兵农等实际政务中。
康熙一朝以道学之名得以居要职,政事却差强人意的事例屡见不鲜。“躬行实践,致君泽民,理学而兼名臣”[7]554的张伯行即因为治理不力被康熙视为假道学。
上曰:“尔等为秀才时,未通仕籍,每每夸大其说。及至服官莅政,平日所言,尽销归何有。即如张伯行,初任巡抚时,曾奏欲致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以报皇上。朕即以其言太过。后乃滥收词状,案牍不清,堆积千余件,牵累及监毙者甚众。苏州域外有渔船数双,张伯行疑是海贼,遂集营兵,查夜防守,骚动民间。及命巡海缉盗,又不敢往。现今地方凋瘵,民不聊生,大非南巡时景象。所谓移风易俗,家给人足者安在?故听其言,必观其行也……”[2]2215-2216
张伯行因清廉,由康熙亲自举荐,被提拔为福建巡抚(12)《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五列传五十二:四十六年,复南巡,至苏州,谕从臣曰:“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时命所在督抚举贤能官,伯行不与。上见伯行曰:“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擢福建巡抚,赐“廉惠宣猷”榜。参见:《清史稿校注》,第8570页。。上任伊始,如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他曾立志移风易俗,使百姓衣食无忧,以报皇恩。但康熙认为其在任上,办事效率低,案件积压,反而牵累百姓。如康熙对另一大臣的批评,“……刘谦平日亦讲道学,一至大位,即有事故。讲道学者,顾如此耶?”[2]2408平日里夸夸其谈,皆似能治国平天下,但一担任要职,便暴露出无能无德的问题。职位越高,类似问题带来的后果也就越严重。张伯行其后在江苏巡抚任上,误认渔民为海贼,兴师动众,扰乱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致使民生凋敝。这些都使康熙极为不满,若无才干,无政绩,理学的名声对朝廷毫无意义。
由于任上张元隆、张令涛海盗的案件,张伯行被张鹏翮等奏请夺职。鉴于张伯行平日良好的品行和学问,康熙没有立即查办,而是下旨召其入京,当面询问,以了解其中的实情,避免误判。
(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乙卯)尚书张鹏翮将原任巡抚张伯行审毕带来,召入。上谓张伯行曰:“而奏称海上有贼,缉获几人带来?”……上曰:“授尔为巡抚时,尔曾奏务使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以报皇上。今之移风易俗,家给人足者安在?”张伯行奏曰:“臣立志如此,因无才干,故不能行。”[2]2226
康熙以其曾经的许诺,当面质问,张伯行理屈词穷,以有志于此,但才干不足辩解。
朝廷推崇理学,用理学之人,归根结底看重的是实济。康熙曾批评张鹏翮说,“尔平时亦讲理学,……况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须为国为民,事事皆有实济。若徒饮食菲薄,自表廉洁,于国事何益耶?”[5]221“实济”,就是实实在在为国为民办事,有利国利民的实效。若只有操守而无能力,有修身而无实济,则作为大臣是不称职的。所以,张伯行以有心无力自我合理化使康熙更为生气。
震怒之余,康熙将张伯行的学问一起否定,“尔实无才干,并不读书。……朕几次欲将张伯行提审,念其清廉,是以中止,姑调来引见。由今观之,甚是粗鄙,直未曾读书者,不可为封疆大臣,有钱粮小地方尚可用之。”[2]2226张伯行无才干不仅是真假理学的问题,甚至被视为根本不读书,为政无实效累及对其学问的评价。由此可见,康熙是从效果的角度,衡量读书与否,理学真假,无实济则不是真理学。
以效果为标准,则才干是为官的核心要素。“上又问张鹏翮曰:‘陈瑸居官如何?’张鹏翮奏曰:‘操守好。’上问曰:‘办事如何?’”[2]2250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政治人物的品德与其事功、学术,常常被混为一谈,操守往往是评价官员的重要标准。所以,对于康熙的询问,张鹏翮首先称赞陈瑸操守好,但康熙紧接着问其办事能力如何。康熙此问意味着,居官好坏,他更关心的是办事能力。
才干、能力是康熙用人的惯常标准。官员余正健以操守好被举荐,但其在顺天府尹任上的表现,表明其处理政事的能力欠缺,因而康熙不用。当其他大臣极力为余正健争取时,康熙坚持己见。
上又曰:“余正健居官虽清,全不能办事。顺天府尹事务俱坏,即如木雕草束之人。”大学士萧永藻奏曰:“余正健办事虽迟钝,人还正气。”上曰:“不能办事,虽正亦无用。不要钱即算好官,如九卿会议处,将泥塑木雕之人列于满座,不饮不食,即以此为正,可乎?此言甚错。”[2]2360
康熙反复申明,不能办事,操守再好也不能委以要职。当然,并不是操守不重要,而是对于大臣,才干更具优先性。
康熙甚至认为若是能干,操守平常也可。“大臣则自有大臣之体,当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非徒尚操守而已。即使操守平常,民尤谅之。未若自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2]2215-2216自古清官难得,但康熙并不喜欢只是清廉的大臣,也不喜欢自恃廉洁的官员。“即使操守平常,民尤谅之”也透露出康熙强调政绩之于操守的优先性的政治逻辑。培育道德是移风易俗,建立公序良俗的有效手段,但涉及实际利益处,其重要性就要被弱化。
就理学来说,康熙固然是真心爱好,将其视为维系人心,建立正统的重要手段,也对理学大臣寄予道德风范上的期望,“提倡道学,究能养成士大夫风气”[9]561。但在实际治理中,他真正看重的是理学中有益于治理的内容和关于现实政务和行政技能的知识,理学的真正核心——理气心性的理论体系反而是次要的。在此导向下,突出理学即实学成为清初官方理学的一个理论方向(13)参见:辛晓霞《<性理精义>对理学的定位——以周敦颐著作的编排为例》,《船山学刊》,2014年第4期,第72-76页。。大臣的真假理学,也从效果的角度以实济为根本标准。由此,在政治逻辑下认定的真理学,无论是理论形态,还是存在意义,都偏离了思想的脉络。
四、政治投射下清初理学的调适
理解清初理学,政治是不能缺少的一环,其兴盛衰落,以及理论走向,都有政治因素的投射。
在思想活力渐弱的情况下,理学凭借政治力量在清初再次兴盛。其中,康熙爱好理学是一个因素,“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达之见菲薄道学,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僿见摈,则熊、李犹金台之郭隗,当居招致之功,要为人君好尚之标帜耳”[9]561。许多大臣由理学而被康熙亲近重用,“熊、李以道学逢君”[9]564,因此朝廷上下以理学邀宠,形成崇尚理学的风气,理学大臣也以自己身份的影响力做了许多推广理学的工作。
当然,推崇理学,除了君主个人爱好,更重要的是统治的需要。清朝初立,需要以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文化的支持,从而与汉政权顺利交接,并维持社会的稳定。加之,清入主中原,还面临华夷之辨的问题。此种情形下,清通过推崇理学迅速与汉文化沟通,并藉由理学重建学统与道统,确立取代明朝、统治全国的合法性。可以说,理学成为清初的强势话语,政治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理学获得政治优待的同时,也需自我调整以配合政治,除了实理实行等理论层面的调适,还要让渡出一些学术话语权。有学者认为康熙以“伪道学”打击汉人士大夫,是为争取学术上的主动权,以政治混淆学术(14)姚念慈:玄烨以“伪道学”打击汉人士大夫,争取学术上的主动权,提出“公私”字,专为臣下而设,裁断操于玄烨。然而以此虽可操学术予夺之权,其实不过以政治混淆学术。参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225页。。抛开满汉矛盾的层面,真假理学确是标识话语权的有效方式。
可注意的是,前文康熙所说张伯行治理不力并非其任上的全部,“随擢福建巡抚,赈旱荒,清海盗,纠墨吏,禁淫祠,风化大行”[7]553-554。且从张伯行逝后谥清恪,从祀文庙等(15)参见《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五列传五十二:雍正元年,擢礼部尚书,赐“礼乐名臣”榜。二年,命赴阙里祭崇圣祠。三年,卒,年七十五。遗疏请崇正学,励直臣。上轸悼,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参见:《清史稿校注》,第8571页。,可知其一生任官,朝廷对其的认可是主流。此后康熙依然优待张伯行,也表明他并非不知道张伯行的其他政绩,而是,假道学之类是他批评大臣办事不力的习惯用语,隐含的深意是理学大臣已经失去以理学自居的资格,理学话语权在君。康熙一朝真假理学对理学走向的深层影响也在于此。
清初,大臣多以理学自居,假道学的风气是其次,潜藏的政治隐患是大臣自恃理学,强调道的权威性,以道使君。“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10]士在政治层面低于君,但凭借知识和道德,士有自尊的底气,这是读书人理想的参与政治的自处立场。但当康熙以理学为名打击大臣,以不读书、假道学斥责大臣时,一则表明,君主导理学真假的标准,理学话语权在政治。再则,既为假道学,那么,大臣没有自称理学的资本,由此也失去了以道约束君的可能性。
理学得以自持还在于道统,“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者,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11]。治统和道统,一以政治,一以文化,自上古圣王之后两者分离,儒家可努力以道统制衡治统,但康熙一直将治统与道统的结合引为己任。“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2]339-340如此,则消解了道统约束君权的意义。在此导向下,理学大臣积极参与论证治统与道统合一落实于康熙(16)李光地论证了儒学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必然性,并得出唯有康熙帝可以使道统与治统合一的结论,“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参见:《榕村集·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出自《清代诗文集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5页)他的观点得到清初许多理学大臣的响应。,他们把儒者手中的道统解释权拱手交给政治。由此,政治越来越多地越界至思想领域,有清一代的文化专制也暗藏于此。
思想的变迁有其自主性,但其动向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否认。清初理学侧重实学、实理、实行,突出道德规范,少创新等特点,既有思想自身的脉络,也有政治投射的因素,两者的合力影响了理学的走向。在真假理学事件中呈现的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可以更清晰清初理学回光返照式兴盛的逻辑。在借助政治力量的同时,理学日渐屈从于政治,逐渐失去了思想得以前行的创新活力。所以,繁荣只是虚假的表象,思想吸引力的下降,使理学在康熙朝之后便不可阻挡地衰落了,只保留了官学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