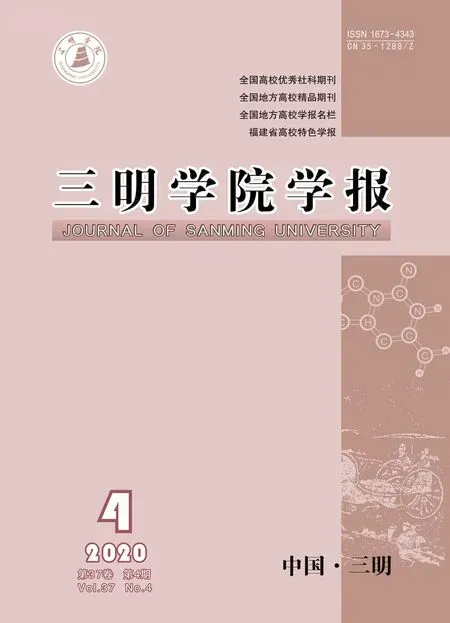民国时期商人信佛风气及对其企业管理的影响
——以简照南为中心
李栋财
(福建师范大学 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福建 福州 350007)
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政府政策朝令夕改,且战乱频繁,自然灾害多发,商人身居复杂多变的商海,亟待宗教力量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当时许多企业家都皈依佛教,较为有名者如穆藕初、简照南、简玉阶、聂云台、王一亭、刘吉生、王晓籁、方子藩、闻兰亭、玉慧观等人。他们在自我修行、推广佛教文化的同时,信仰也影响到他们在企业中的管理思想与行为。其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以对佛教事业贡献巨大、企业产值颇丰而引人关注。以简照南为中心,聚焦民国时期佛教居士群体中的信佛风气,以及考察信佛对商人企业管理的影响,既是对于民国时期“居士佛教”现象的深入探讨,也是探究宗教文化与企业管理行为之间联系的尝试。
一、民国时期商人群体的信佛风气
在民国时期的商人群体中,很多商人信仰佛教,以上海为例,“翻开20世纪30年代前的上海商会、公会的董事名单,著名人物中竟有半数以上为佛教徒或倾向佛教者”[1](P95),简照南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简照南(1870-1923),广东南海人,1905年与其弟简玉阶在香港创设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公司后更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部移至上海。该企业是当时国内最大烟草公司,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轻工业企业。作为公司永久总经理的简照南,与当时的很多商人一样,很早就参加了佛教的皈依仪式[2](P21),成为虔诚的佛教徒,积极参加各种佛教活动。具体说来,商人群体在民国时期的信佛风气有如下体现:
(一)积极创建、参与佛教社团
民国时期,信佛居士对提升自身在佛教界地位的需求增加,由此独立的在家信众学佛团体在全国大量出现,如名为居士林、念佛林、净业社、莲社的一些社团。1918年成立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较为规范的居士佛教团体,也是在同类社团中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其中大多数骨干成员为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企业家,如苏州典当业商人沈惺叔、无锡丝商周舜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上海“纺织大王”穆藕初、“味精大王”吴蕴初是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在1920年,汉口佛教会成立,知名信佛商人王森甫为会长,该会后来改组为汉口佛教正信会,成为独立的居士团体。[3](P152)1922年4月,简照南捐资建立上海功德林。上海功德林内设蔬食处和佛经流通处,蔬食处由赵云韶管理,以提倡素食来推广佛教,素食服务推广十分成功,社会人士视素食为潮流。[4](P108)佛经流通处由江味农负责,以流通佛书、法器以及其他佛教用品等为主。[5](P166)在这些商人的带领和号召下,各居士团体纷纷倡印经书、组织法会、礼请法师讲法,为中国佛教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二)热衷创办佛教书局及支持佛学刊物
很多信佛商人会利用自己的商业知识,服务于佛教文化传播事业。上海佛学书局于1930年在上海创办,由商界知名大买办王一亭为董事长。该书局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所编辑、刻印、流通佛学典籍的出版机构,其经营方针是“以宏法为目的,以营业为方法,二者相辅而行”。书局边集资边营业,“本公司股份为每股十元,盖宏法事业以普遍为原则,使各方善信均有加入之机会。凡为本公司股东者,除照例每届发给官利外,并得享受本公司对于股东之各种优待。所谓既得宏法之功,又获投资之益,诚一举而二得焉”[6](P206)。入股者大多为佛教信徒,因此在取得书局发的股息后,就会用这笔钱购买经书送人,故而书局常常以等价金额的购书优待券代替股息分红。这种做法,无疑加快书局的资金周转,取得较好经济效益。
信佛商人很重视佛教刊物,既在资金上支持刊物,还参与刊物的文章撰写。佛慈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玉慧观对佛学刊物《海潮音》的经济支持很大,《海潮音》第八卷及第十二卷的印费,全由他负担。[7](P1011)《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从 1923年3月创刊到1937年4月停刊,前后共出 43期,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是刊物的编辑和主要供稿人之一,仅1925年就收录聂云台18篇关于佛学的文章。[8](P21)
(三)在佛教扶贫济困工作中发挥带头作用
信佛商人在积攒大量财富后,常将金钱投入到佛教界组织的慈善工作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浙江、四川、江西、福建等地皆有不同程度的天灾人祸,造成流民难民增多,社会动荡不安。对此,王一亭、聂云台、施省之等信佛商人成立难民收容所,开展施药、施衣、施米、施棺木,以及其他救济的活动。这些解决大众疾苦的举措,当时受到各界好评。1918年,华北旱灾惨重,佛教界在北京成立“佛教赈灾会”,简照南一次性捐出银元10万元,委托江味农携款北上,参加救助灾民工作。[9](P355)
苏州佛教信众还成立特色慈善团体“隐贫会”,从发起人的简历资料来看[10](P88),发起人大多为商界人士,如上海庆城钱庄业主万振声、苏州保裕典当股东张荫玉、上海西门子洋行经理管趾卿等人。隐贫会不仅救助对象特别,主要是生活遇到困难的士商家庭,这些家庭被称为“隐贫户”;而且救助方法也有特别之处,采用了无利借贷救助方法。无利借贷主要面向小本经营者,每次所借数额不多,但可解除这些人的燃眉之急。
(四)极力护持庙产
清末至民国期间,社会各界关于“庙产兴学”的呼声此起彼伏。所谓“庙产兴学”,就是利用各地寺庙财产来兴办教育,包括庙产补助学费、寺庙为校等形式。为保护寺产以及协调解决佛教界受侵害的问题,以施肇曾、李云书、聂云台等商界人士为主要成员的上海佛教维持会宣告成立。佛教维持会介入多起在山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发生的侵占寺产事件,或登报谴责,或致电相关单位要求停止侵害,在维护佛教界权益方面起到一定作用。[11](P77)曾担任中国佛教会多届执行委员、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的王一亭,还上书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政府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加强对上海及其他地区寺院财产的保护。[12](P112-137)
在护持庙产的同时,信佛商人大力支持佛教寺院道场的建设。简照南是澳门无量寿功德林创建时的主要出资者,“布金买地,向葡国官厅立案,永为女众清修之所,定名曰无量寿功德林”[13](P63)。简照南在上海有座名为“南园”的大型私家花园,他生前在园中佛堂念佛不辍,还计划把花园捐出,专做佛教修行道场。简玉阶继承其兄遗志,于1926年捐出南园作为佛教公共弘法处所,并改名为“觉园”。园内经常启建盛大佛事法会以及开展讲经活动,成为全国闻名的净土宗道场。
二、信佛商人的企业管理行为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对于非专职从事宗教工作的普通信徒来说,信仰的作用往往体现在工作、家庭等世俗社会当中。从简照南等商人的企业管理行为可以发现,信佛商人在企业中的一些经营管理行为,体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一)爱国之心与佛教爱国思想相同
佛教在印度出现时就有明确的爱国理念,根据佛教《四分律》记载,弟子要到印度列国去弘法布教时,佛陀告诫他要“遵守国王法,不违毗尼行”。“遵守国王法”,就是要做个爱国守法的公民。东晋的道安法师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一原则的核心就是“依靠国家政权立佛法”。佛教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众,从而建立国家的权利与佛教大众权利的互动关系。民国时期信佛商人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觉悟,如大商人施肇曾,“坚持弘法与慈善并举,为近代居士佛教赢得了声誉,是功勋卓著的佛教大居士……始终是一位富于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建设国家、回报社会为己任的实干家和爱国者”[14](P71)。
在海外多年经商的简照南深感国人在海外地位低下,1904年“马潘夏”事件发生后,愤怒的国人发动了抵制外货的运动,简照南的国家民族使命感也油然而生。他目睹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中国烟草市场,遂决心实业救国,这就是简照南创业南洋烟草公司的本意。在1920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次股东会上,简照南就提到,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以“振兴国货,挽回利权”为创办宗旨,公司将来要“扩充改组,借群策群力,推广国货,为吾国塞一漏危”[15]。“国货”是南洋烟草公司在宣传时最响亮的口号。南洋烟草公司从开创到转型,始终都以“国货”的形象立身,“中国人抽中国烟”的口号是公司在宣传中经久不衰的标志性宣传用语。这个口号随南洋烟草公司传遍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其他华人华侨聚集的地方,这也是刺激广大国人购买其公司香烟的重要卖点,而该公司最畅销的香烟品牌之一直接名为“大爱国”牌香烟。辩证地看,吸烟是有害健康的,但在大众吸烟行为未能完全戒绝的现实里,发展民族烟草公司打破了外国烟草企业垄断,无疑是爱国的表现。
(二)注重人才的选拔与佛教的识才、用才相一致
佛教禅林中的管理者,除了完成维护道场正常运转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要有识别人才、善用人才的能力,“夫为善知识,要在知贤,不在自贤”。一些修为较高的禅师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佛学造诣,通过举止行为、语言沟通等考察可以准确掌握对方的能力水平,然后将人才安排到适合他们特长的岗位上。《禅林宝训》中就记载了相关案例,如圆通居讷禅师第一次见到大觉怀琏和尚,就认为此人将来必成大器,“斯人中正不倚,动静尊严,加以道学行谊,言简尽理,凡人资禀如此,鲜有不成器者”[16](P14)。大觉怀琏和尚后来以禅林书记的身份留在圆通居讷禅师身边,协助禅师的日常工作。经过多年历练和禅师的推荐,大觉怀琏和尚最终担任开封十方净因禅院住持,并得到宋仁宗的赏识及敕封,成为一代名僧。禅师的这种识才、用才能力,也是简照南管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时的人才工作所需要的。
为让公司突破传统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简照南力排众议,任命非家族成员的优秀专业管理人员担任高级职位。如陈炳谦曾担任英美烟草公司买办,简照南将他延聘到董事会之中,任命他为负责财务的副总经理。在陈炳谦的帮助下,创办银行及保险公司、汇兑机构为企业融资服务。买办邬挺生被聘到公司,稳定了华南市场,并重新赢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市场。陈炳谦的侄子、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企业管理专业课程的陈其均也受到重用,简照南支持他将西方式的管理制度运用到企业之中,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17](P34)在1919年,简照南首次任命8位“外姓”董事,这其中包括分别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虞洽卿和顾馨三等人,数百名上海金融界、工业界和政界精英纷纷入股,简氏家族的股份从94%稀释到60.6%。[18]正是由于这些优秀管理人员以及股东加入,实现了向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的贷款,为公司带来新的商业网络和融资途径,使得公司获得较之前更丰厚的资源,为企业的扩大发展源源不断输入能量。
著名化工实业家吴蕴初也是佛教信徒,他创办的企业与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化学技术密切相关。吴蕴初用优渥的条件选拔大批化工技术人员加入企业,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高地。[19](P117)他还邀请上海张崇新酱园的老板张逸云担任公司合伙人,张逸云为化工技术转变为商业产品投入大量资金,使得“佛手”牌味精有资本与已垄断中国市场的日本“味之素”产品进行强有力竞争。[20](P96)
(三)重视保障员工权益及福利与佛教禅宗丛林管理无区别
在禅宗丛林中,“衲子无贤愚”,每个僧人各有存在价值,佛陀曾提过“比丘幼小而不可轻”[21](P1058),沙弥年纪虽小,只要虔诚修行,假以时日,就会成为教化众生的大师。而“老僧乃山门之标榜也”,大多数老年僧人出家时间长,学修经验丰富,可以指导年轻法师,是很好的学习榜样。每个僧人都需要承担具体工作任务,所谓“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22](P236),普请即禅宗丛林中所有寺内僧众都应一起劳作的管理制度。在佛教僧团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除老病僧人外,其他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僧人之间要相互爱护,不得因为年龄、体力差别而有所轻视,年轻僧人要照顾老弱患病的僧人,丛林常住要保障他们生活上的物质需要。
简照南在公司管理中明确岗位责任,每个岗位都有适合其职责实际的公平考核制度,这与佛教禅宗丛林管理中上下平等的观念是一致的。以《包烟女工规则》为例,根据犯错大小有明确罚例,而遵守管理规则、认真工作者则往往有机会获得奖励。[23](P23-24)在赏罚严明的岗位责任制下,可以有效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使之成为激发企业生机与活力的有力杠杆。简照南还注重职工福利待遇,规定“凡属本厂男女工人,如在厂工作满6个月,一律按其所得工资加5%,此款由公司代存,每人另发1折,月息8厘。凡工人在厂内工作有病者,由厂内医生医治,药费各项,厂中供给”[23](P305-306)。当职工群体有合理需求表达时,“简照南谓工人所提各项要求,公司均可照准,惟希望以后工作加意勤力,于工人自身亦有间接之利益”[23](P323)。简照南希望公司在满足职工合理要求时,职工能够真正看到企业和自身的共同利益,一起共同努力。
曾频繁向弘一法师请教佛学的棉纺织业富商穆藕初,在管理企业中也将照顾职工视为天职。他认为:不管企业运营如何艰难,管理者都应如数按时发放薪酬;企业管理者在处理员工之间纠纷时,应该公平公正;要让员工子女实现义务教育,这样才能让他们安心工作。[24](P90)他还废除了行业中传统的封建工头制,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制定严格的厂规制度,使得奖惩都有章可循。[25](P24)
(四)热衷组织公益慈善活动与佛教慈悲思想相契合
简照南“立意将所蓄财产,为社会造福”,认为“我公司逢善必举,自问对于社会亦无大愧”[23](P422-433),而佛教慈悲思想提倡救助社会弱势群体,造福全社会大众。相比较而言,简照南等商人的想法与佛教慈悲思想是一致的。佛教慈悲思想最为特别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无差别、无条件的一种慈悲,不是因为家族血亲的宗法关系才有的慈悲。正如《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中的描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26](P312)慈悲精神在佛教中往往由菩萨这一类形象进行具体化诠释,如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等的名号和应化事迹都已家喻户晓。菩萨的慈悲抛开了世俗的、自我因素,是一种纯粹而又自然的本性流露,是高尚道德理想和精神的人格化身,是佛教徒追求的完美道德榜样。
简照南认为“金钱者多取为厉,须能聚能散,自社会取之,当为社会用之”[27](P34),这生动表达了他“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想法。1915年,珠江三角洲发生特大洪灾,简照南马上以公司名义组织赈灾机构,召集在广东的推销人员停止营业,全力参与救灾工作。他的堂弟简孔昭在越南从事米机业,此时恰好有二三十万斤安南米运到。简照南将这批大米全部用作赈灾,还派出公司“大南洋”号货船,专责运送给各处灾民。1920年,北方各省荒旱成灾,简照南又前后共捐出10万元。[23](P249)如遇各省水旱之灾,他“每举一事,所捐动以巨万计”“大大获得社会上的好评及受惠灾民的感激。救灾的规模颇大,传颂中外”[28](P73)。故民国政府于1928年委任简照南为两广赈灾委员会委员,翌年再任其为行政院赈灾委员会委员。[29](P53-54)面对政府嘉奖时,他认为这是自己作为佛教徒应做的事情:“佛言布施有三,财施为下。又因以获名,毋乃滋愧乎?盖好善根于天性,而素耽禅悦,深得慈悲之旨,有若视为当然者。”[30](P726)
简照南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在他的倡导下,公司捐巨款资助暨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及复旦大学建造校舍。还在上海与香港两地设小学,为职工子女提供教育服务。其他对各大、中、小学的不同数目资助,不胜枚举。[23](P249)简照南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熟悉中外商业情况的人才,公司于1920年开始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每年选派15名(含简照南个人资助的5名),一共选派3届。[31]无锡信佛商人周舜卿在盈利颇丰的同时,注重兴办慈善学校。他先后开办廷弼商业学堂与私立廷弼小学堂,专门招收贫困家庭子弟入学,教给学生谋生技能。商业学堂学生修业期满,绝大多数被周舜卿创办的裕昌丝厂录用,成为厂中技术人员[32](P56),从而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
三、启示
民国时期的商人群体中存在着浓厚的信佛风气,其中一些商人成为学佛居士团体骨干,是护持佛教的重要力量,对民国时期佛教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作用。佛教文化对这些商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企业管理都有所影响。被称为“商界师表,南洋菩萨”[18]的简照南,其企业管理行为与佛教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佛教文化中的智慧思想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协调政府、员工关系,吸收外部优秀人才,在社会中获得正面形象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
在谈民国时期信佛商人的企业管理行为时,不能忽视西方文化以及其他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佛教文化和西方文明兼收并蓄是当时很多信佛商人的选择,海普药厂的厂名寓意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该厂创办人张禹洲是佛教徒,厂名“海普”的背后有中西两种文化的寓意:海普是佛教教义中“普济众生”的意思,海普又也是英文“help”的中译音,意味“帮助”[33](P167)。除佛教文化外,传统的儒、道文化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商人的言行,因而佛教文化对信佛商人的企业管理行为影响会显示出众多差异性,这也是相关研究者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