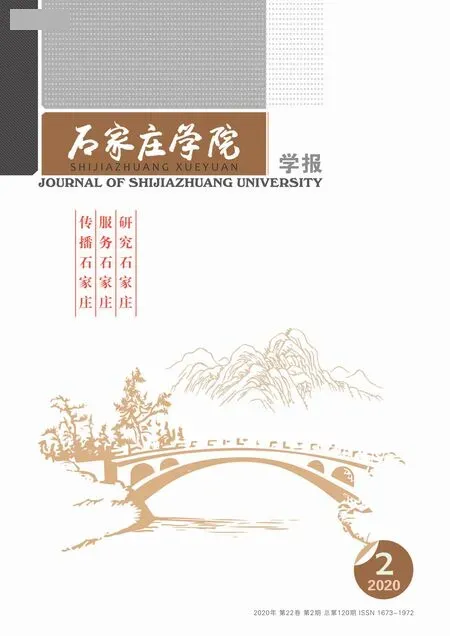沙俄侵占旅顺和大连的策略
问 昕,卢 超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取中国的辽东半岛,引起了沙俄的嫉恨。沙俄联合德、法两国,以武力干涉日本,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沙俄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要维护清政府的领土完整,而是另有企图。19世纪后半期,沙俄在中东寻求出海口受挫,就把目光转向东方,推行积极的“远东政策”。所谓“远东政策”,就是通过使用武力在东方进行扩张,尤其是觊觎中国的旅顺和大连,寻求作为俄国的不冻港。
一、俄国关于“不冻港”问题的动议
至迟在1895年4月,俄国在制定远东外交政策时,就把在太平洋攫取一个不冻港列作重要问题。新上任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致沙皇的一份备忘录中,针对俄国对外应采取的政策时提出两点意见:“一方面在太平洋上取得一个不冻港,另一方面吞并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取得方便的路线所必要的部分满洲领土。”[1]226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原件上批示“完全正确”,又在原件其他地方写道:“俄国确实需要一个终年免于冰冻的港口。这个港口必须在大陆上,而且一定要由一条陆地把它和我们现在的领土切实地连接在一起。”[2]70
1896年5月,李鸿章率清政府代表团访俄,就中俄军事同盟和向清政府“借路”修筑中东铁路一事与沙俄进行谈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与李鸿章交涉《中俄密约》时就有过这样的认识:俄国修筑铁路,不仅要考虑过境铁路行程最短的问题,还要考虑“用铁路深入南满”,“把黄海的一个不冻港与俄国的铁路系统相衔接”[3]105-106。对于此事,苏联学者罗曼诺夫指出,“有许多文件可以证明,维特对中国代表不仅提出了北满的铁路干线,而且提出了从这干线修一条南满支线到‘黄海岸上的某一海港’。维特对这点要求似乎提得十分决绝,所以没有遭到直接的拒绝”,“一八九六年五月间的维特,不仅看到了西伯利亚铁路之最短的路线,而且开始有了以铁路侵入南满的心思”[4]87。
李鸿章访俄期间,中俄就俄国向中国“借地”筑路一事达成协议,随后成立中东铁路公司。俄国为了获得一个出海的不冻港,详细研究了修筑所谓的“中东铁路支线”问题,擅自派人到中国沿海港口调查,搜集情报,最后发现位于渤海湾北部的旅顺口和大连湾是终年不冻港,是俄国作为海军基地最理想的地方。1896年5月,俄国派乌赫托姆斯基来华,表面上答谢中国派员赴俄祝贺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实际上是找李鸿章谈判,解决中东铁路支线与港口问题。由于清政府多数官员反对,乌赫托姆斯基空手而归。
由此可见,俄国政府早已惦记着中国辽东半岛上的旅顺和大连,占领旅大不冻港作为太平洋舰队的一个基地,是其“远东政策”的一部分。
1897年11月6日,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命令舰队开进胶州湾。15日,德国海军陆战队攻占了胶州城,德皇威廉二世致电尼古拉二世:“我相信,根据我们在彼得霍夫的谈话,您必定赞成我派遣德国舰队开赴胶州。”尼古拉二世复电说:“对于您派遣德国分舰队去胶州一事,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近来才知道这个港湾仅在1895-1896年归我们暂时使用而已。”[2]135俄国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既不得罪德国,又可利用清政府的恐德心理,使清政府对俄国抱有依赖心理。实际上,俄国是怂恿和支持德国占领胶州湾的,俄国可以效仿德国,寻机占领旅大作为出海口。
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感到惶恐不安。由于《中俄密约》的原因,李鸿章对俄国抱有很大幻想,希望俄国帮助大清对付德国。于是,李鸿章于11月15日,“立即赶到俄国公使馆,要求俄国予以帮助”,向俄国承诺,“无条件地同意把一切不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立即、随时、无例外地”对俄国的船只开放,“并且提出在需要时可以使用中国政府的军火库和仓库等”[5]406。但是,清政府的希望落空了,俄国不但没有援助中国,还与德国沆瀣一气,趁火打劫,乱中取利。
二、武装占领
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认为,德国的行动给俄国提供了一个占领旅大的绝好机会。穆拉维约夫建议,仿效德国占领胶州湾,在中国取得一个不冻港,最好是大连湾。
1897年11月23日,穆拉维约夫给尼古拉二世写了一个备忘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尼古拉二世在收到备忘录的当天就批准了穆拉维约夫的建议,并批示:“我们决不能失掉时机。我一直认为我们未来的不冻港应当在辽东半岛,或者在朝鲜湾的东北角上。”[2]10011月26日,尼古拉二世召集了有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海军大臣季尔托夫、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参加的特别会议,讨论关于占领旅大的问题。穆拉维约夫认为,俄国需要一个太平洋的港口,目前正是“夺取旅顺口或大连湾的时机”。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也在会上表态,“坚定地支持穆拉维约夫伯爵”。海军大臣季尔托夫“则认为朝鲜海岸的港口距大洋较近,比旅顺或大连湾更为有利作为太平洋舰队的根据地”,言外之意是,如果得不到“朝鲜海岸的港口”,也不排除占领旅大。在这次会议上,只有财政大臣维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我提醒在场诸人,我们曾宣布过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且凭借这项原则的力量迫使日本退出了包括旅顺和大连湾在内的辽东半岛。我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的防守同盟,因此负有防止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义务。我说,在这种情形下,夺取中国的港口就是极端的背信弃义和不守信用即使抛开这些道德上的原则,而完全从我们自身的利益着想,这种办法也是极端危险的。我提请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们注意到我们正在中国领土上修筑一条铁路的这个事实,我们的行动会激起中国反对我们,这样就会危害修筑铁路的大局。而且,在占领这些港口之后,是不能不用铁路和铁路干线连接起来的,这种新路线的修建又会引起其他纠纷而很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6]72-73
但是,维特的“和平”建议没有被沙皇采纳,当维特在几天以后面见沙皇时,沙皇告诉他,“已经决定占领旅顺和大连湾”,其理由是,他得到了穆拉维约夫的报告,“英国军舰已经在这两个港口外巡弋”,“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两个港口,英国人就会去占领”[6]74。
事实上,维特并不是不想占领中国的海口,而是反对“强占”的形式。维特的真实想法是,既要在中国获得利益,还要考虑国际形象。在远东政策上,维特和穆拉维约夫等人都是积极的扩张主义者,二者的差别仅在于策略上的不同,前者属于缓进派,主张在中国进行渗透;后者属于激进派,更相信使用武力。对此,俄国学者鲍里斯·罗曼诺夫在著作中讽刺维特说:“他生前用尽了千方百计,死后又用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利于制造并最广泛地散布一种神话,似乎他的政策纯粹是‘和平’性质的。”[3]6
俄国在决定占领旅大后,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训令驻北京代理公使巴甫洛夫通知清政府,“鉴于我们接受了11月15日中国提出的建议”,俄国海军少将鲁诺夫指挥的俄国分舰队已奉命驶入旅顺口,俄国“无意侵占中国的领土”,“占领旅顺口是为了保护中国,防范德国人的侵略,德国人撤退后我们就一定离开”[6]74,要求清政府“一定要发出指示,对该舰队予以友好接待”[2]112。1897年12月14日,俄国太平洋舰队5艘军舰在“保护中国”的幌子下驶入旅顺口。
俄国军舰进驻旅大的同时,为了避免德国的误会,俄政府特意通知德国,愿与德国在远东与德国“携手前进”,“以最友好的方式支持它永久租借胶州湾的要求”[7]105。事实上,俄国早已与德国就占领胶州湾一事有了秘密约定。据维特回忆,1897年12月初,维特去拜访德国驻圣彼得堡使馆参赞契尔斯基,请他转告德国皇帝,德国在惩罚了杀害传教士的凶犯后,赶快从胶州湾撤兵。对此,德皇威廉二世表示:“我从维特的话中看出来,他还不知道这件事的重要细节,所以我们不能听从他的劝告。”维特后来才明白,德皇所说的“重要细节”是什么,“那就是1897年夏季,德皇到彼得戈夫宫访问时,就已经请求尼古拉二世默许他占据胶州湾了”[6]73。据此可知,俄、德两国的内幕交易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就连位高权重的财政大臣都被蒙在鼓里。
直到此时,清政府仍然对俄国抱有幻想,把俄国的侵略视为“帮助”,并在1897年12月17日电令旅顺口守将宋庆:“俄船在旅,所有应用物件随时接济,勿听将弁伪言,致启衅端。”[8]2546这样,俄国不动用一枪一弹,顺利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造成了俄军占领旅大的既成事实。
三、外交讹诈
俄国人深知,武力占领旅大的理由是暂时“过冬”,为了给永久占领旅大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俄国使用强硬的外交手段,迫使清政府就范。
1897年12月1日,俄国外交部向驻俄公使杨儒提出“租借”旅大的问题。杨儒致电总理衙门:俄国对“德事愿效力而难于措词,或请中国指定海口,俾泊俄舰,示各国中俄联盟之证,俄较易藉口,德或稍敛迹”,“窃以为德果否因此就范,亦无把握。胶事俄先知情,貌示交好,恐不足恃”[9]2504。1898年2月28日,尼古拉二世在接见许景澄时,大谈所谓“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10]2538。
为了向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于1898年3月3日再次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旅大和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黄海海岸的问题,并限期在5天之内答复,“不容拖延”,态度十分蛮横。总理大臣们对此仰天无策,“恭(王)语塞,庆(王)稍申,余皆默”[11]3147。3月12日晚,巴甫洛夫来到总理衙门,上演了一出大闹总理衙门的剧目。巴甫洛夫“谓旅大租地开通铁路断不能改,已奉训条在此议论,限一日复,至缓两日”[11]3150。这无异于向清政府下最后通牒。3月13日,巴甫洛夫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在两星期内(3月27日前)将此事了结,缔结租约,否则将采取其他行动。
清政府一面派李鸿章、张萌桓等人继续在北京同巴甫洛夫妥商;一面又令驻德公使许景澄自柏林赴圣彼得堡,加紧同俄国的交涉。
1898年3月3日,清政府任命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驻俄公使杨儒为会办,“赴俄专论旅大俄船借泊及黄海铁路事”[12]2546。3月12日,许景澄、杨儒与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进行正式谈判,俄国坚持必须“租借”旅大和修筑南满铁路。3月15日,许景澄拜见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声称:“俄国在东方不能不有一驻足之地,现在外部所定条款及画押期限,我们早经筹定,实难改动。惟望转达贵国政府,早日允办,使他国知我两国系和衷商成,方为妥善。”[13]408许景澄将面见沙皇一事致电总理衙门,告以“旅大事与外部言难挽回”,“无可商酌”。李鸿章虽然复电要许景澄“坚持勿许”,而终无可行办法,只得建议“于大连稍参活笔”[11]3151。3月18日,许景澄、杨儒回电,称已与俄外交部“剖辩”,俄限清廷于3月27日前必须订约,“过期无复,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并表示“俄计已决,无论何国出阻,均所不计”[14]105。3月20日,许景澄再次约见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后者竟然避而不见。在交涉期间,3月18日,俄国从海参崴出动军舰13艘来到旅顺口,在陶湾登陆,合计2.5万人,大炮100余尊,以加强先期到达的俄军。
与俄国的激进派相比,维特仍然坚持推销他的“和平”外交政策。1898年元旦,俄国将军库罗帕特金代替万诺夫斯基出任陆军大臣,维特希望这位新任陆军大臣会支持他的政策而从旅顺口撤兵,但维特的希望成为泡影,因为库罗帕特金比他的前任还要激进,不但完全反对维特的意见,甚至说对中国的要求不但要包括割让旅顺和大连湾,而且连通常称为关东州的辽东半岛的那部分也囊括在内。库罗帕特金的意见得到了沙皇的支持,俄国政府决定向清政府“租借”辽东半岛36年,并修筑一条连接旅顺、大连湾与中东铁路的铁路支线。
四、金钱贿赂
李鸿章外交代表团在圣彼得堡与俄国谈判《中俄密约》时,俄国曾许诺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是迟迟没有兑现,目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回报,并以此作为把柄控制李鸿章。现在俄国又故技重施,派人秘密会见负责与俄国进行旅大问题谈判的李鸿章和张萌桓,允诺事成之后各酬赠他们白银50万两。幕后操纵这件事的仍然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维特的“和平”建议没有被沙皇采纳,但他仍然尽量发挥自己在远东问题上的作用,试图采用“贿赂”手段向清政府高层渗透,收买一些清政府的高官作为俄国的代言人,实现俄国永久占领旅大的目的。
1898年3月9日,正在中俄就旅大问题进行紧张交涉时,维特打电报给俄国财政部驻北京的代表璞科第,要他“委托代理人最好在三月十五日以前携带必需的款项到达旅顺口”[15]206,会见李鸿章和张荫桓,以维特本人的名义对李、张施加影响,让他们接受俄国提出的要求。维特承认:“我认为如果与中国不能达成一协议,很可能引起流血的战争,我于是给我部驻北京的办事员发了一个电报,让他去见李鸿章和另外一个大臣张荫桓,就说我劝他们与我们达成协议。我让办事员馈赠两位大臣以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五万卢布的贵重礼品。”[6]75
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对此评论:“谢尔盖·维特收买了卑鄙的李鸿章,他接受了这一横暴行为,为此中国将永远不会饶恕俄国。中国将永远力争将横贯满洲的铁路干线变为本国的铁路,而不是俄国的铁路。”[16]15
1898年3月21日,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致电圣彼得堡,说他“与璞科第一起”,“极秘密地”会见了李鸿章及张荫桓,向二人许诺说,如果“协议能不迟于三月十五日①此系俄历,公历为3月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17]207。
1898年3月24日,巴甫洛夫致电圣彼得堡称:“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三月十五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18]208第二天,维特迅速回复璞科第:“当事情顺利办妥时,依照您三月九日电,可付款百万两。此外,我更拨您五十万两作同一事件必需的其他支付。此宗款项可与巴夫洛夫商议后开支。如时间容许,可先征求我的同意。”[19]208
1898年3月26日,璞科第由北京致电维特:“五十万两款项中,在旅顺口及大连湾送礼用的支出需二十五万两至三十万两,此事业已与代办取得协议,特向您请示。请立即电复,俾便遵照行动。”第二天,即中俄签约的当日,巴甫洛夫致电圣彼得堡:“对旅顺口及大连湾当局送礼及补助金共需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两,请给璞科第以适当的命令。”维特在3月28日回复:“在旅顺口及大连湾的支付,可依您三月十四日电办理。”璞科第当天回复维特说:“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②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万两③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20]209-2103月29日,巴甫洛夫也致电圣彼得堡,确认“允付李鸿章的五十万两昨天已照付”[21]209-210。
尽管俄国人行贿李鸿章和张荫桓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北京早已风传此事,朝中大臣纷纷弹劾李鸿章。关于该案涉及到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荫桓,璞科第在致维特的电稿中是这样说的:“我和张荫桓机密谈判关于付他五十万两之事。他对目下收款一事非常害怕,据说,对于他的受贿已有无数控告,他宁愿等到闲话平息以后。我告他所允付他款项无论如何是归他支配的。在旅顺口仅支付一万零六百两,因为允许送礼之官员目下业已离开,稍迟当再付款。”[22]210
1898年9月,张荫桓因支持维新变法而被保守派告密,西太后下令将张荫桓抄家。直到此时,张荫桓尚未有机会得到俄国人许诺的贿款。9月21日,璞科第致电罗曼诺夫说:“由于对张的告密,他的住宅被士兵包围,财产被抄查。所以我至今尚未支款给他。”[23]211
张荫桓被捕后,最初定为死罪,后来改为流放新疆。张荫桓在临行前,要求俄国人“再付他一万五千两”。璞科第不敢擅自做主把钱给他,遂于1898年10月4日发电向财政部主任尼古拉·罗曼诺夫请示,同时又向参政大臣拉姆斯道尔夫伯爵汇报。10月10日,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回复罗曼诺夫:“我认为可以满足张荫桓的请求,因为可以使以前在他手下任事的中国官吏中,造成对我国的良好印象,也许还可能对我们十分有用。……外交部并不反对付给张荫桓一万五千两,因为可以使以前在张荫桓手下任事的中国官吏对我国有良好的印象,可能以后对我国有用。”[24]212俄国人考虑的并不是践行对张荫桓行贿的承诺,而是有更长远的考虑,将来对俄国人“有用”。
张荫桓充军新疆后,1900年7月发生庚子事变,慈禧太后翻出旧账,下令把远在新疆的张荫桓处死,贿款案就此没有了下文。
俄国强租旅大事件,给了清政府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的清政府高层已经后悔当初的“联俄”政策,但悔之晚矣。康有为的一篇日记,生动地描述了俄国强租旅大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李鸿章等人在一起的场景:“当俄之索旅大也,上大怒,面责恭邸及合肥,谓:‘汝等言俄可恃,与定约输以大利,今约期未半,不独不能阻人之来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约之谓何?’盖李合肥与俄联盟,保五年太平也。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上大怒向,西后变色,后曰:‘此何时,汝乃欲战耶?’上默然而出,遂定约。”[25]38
综上所述,俄国人在中国“借地筑路”,其初心并不是帮助清政府抵御日本的侵略,而是与日本在侵华问题上开展竞争。正如黑龙江将军恩泽所指出的那样,“强邻可以相结,而实不可以久依”,“俄为天下所共忌,其为国也,又多诈取而鲜以力攻”,揭穿了俄国的真面目。俄国的侵华行动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清政府的“联俄”外交完全破产。恩泽曾经预料,中东铁路修筑后,中俄两国在“十年、二十年之间或不致有同室操戈之事”,不料仅仅过了3年,俄国就借义和团运动之机,大举入侵中国东北,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可见沙俄阴险狡诈决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