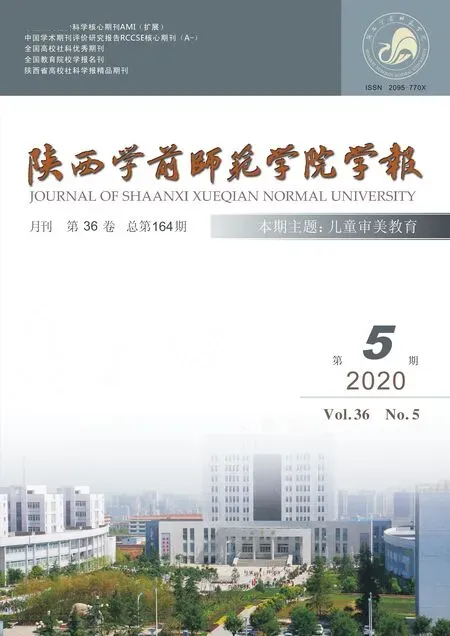形式与意义: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游戏精神
赵扬眉,张 杰
(1.成都市温江区柳城幼儿园,四川成都 611130;2.成都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主要是指在儿童作品文本中体现出的、通过人物游戏所传递的一种符合儿童心理需求和审美旨趣,并实现儿童内心愿望的精神。游戏精神主要体现在儿童文学中人物刻画方面。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包括心理、智力两个方面的因素,它生发并延续了人类的原始情感,根植于人类心灵的深处,任何年龄段和任何种族的人都能感受到它所表达的愉悦、快乐、享受、自由、热闹等一系列外在形态,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内涵。游戏精神不但有一定的美学水平,能提升儿童的美学修养,还有一定的风格个性,能陶冶儿童的情操。游戏精神对儿童文学的影响颇深,可以说,游戏精神影响了儿童文学的编创与发展。
在西方,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十八世纪就指出文学和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游戏,之后以游戏来解释文学基本上成为西方美学的一个学术传统。基于此学术传统,后来者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扩充,比如席勒、伽达默尔、斯宾塞、苏珊·朗格、和郝伊津哈等人,从心理学、教育主义、美学、人类学、哲学等多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游戏性进行了解读。在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们,已经充分注意到游戏性这一理论问题。“五四”时期,饶上达指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就是模仿游戏和化妆游戏[1]。周作人认为游戏精神就是“幻想精神”“愉悦精神”和“自由精神”。[2]202《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就是儿童的非训诫的教育书籍,表达了空灵与幻想,快乐与嬉戏,正好满足了儿童的需求[3]54。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儿童学问的游戏性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班马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开拓者,他的三部专著《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和《前艺术思想》集中体现了游戏精神的问题。孙建江的《二十世纪儿童文学导论》、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王新志的《试论林格伦童话的“游戏性”》、侯辛华的《析阿·林格伦作品的小淘气包形象》、周彦的《论游戏精神与幼儿文学》、王金禾的《论儿童游戏与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俞义的《简论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黄晨的《儿童文学游戏精神初探》、陈恩黎的《生命的欢歌:儿歌的游戏性》这些都是这一些时期集中探讨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优秀作品。
游戏与儿童之间有着有形与无形双重的关联和亲密。儿童在游戏中不断生发对外界的认识,不断探索,以游戏的手段深化对世界的认知。游戏通过外化、物化的载体,支持儿童的心理需求和生理上的生长需要,它在实质上可以说是儿童本能行为的具体体现。因此,游戏精神作为儿童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更应该融入儿童文学中去,成为儿童文学的审美支柱和重要标准。
一、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三性”理论
周作人认为游戏精神就是“幻想精神”“愉悦精神”和“自由精神”,这是对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高度概括,是“三性”理论的总纲。换而言之,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具有快乐性、幻想性、自由性三大特征。
(一)游戏的快乐性
《辞海》对“游戏”一词的解释是:“体育手段之一,文化快乐的一种。”[4]2554游戏最终目的是使得儿童更加快乐。幼儿文学作品的游戏精神,本身并不是给儿童普及知识,也不在于阐述“大道理”。而在于用高雅的手段造就儿童快乐、宣泄和释放的心理。文本的幽默、轻松、荒诞是其根本特征。
在西方,康德也认为游戏的功能在于其快乐作用。游戏不同于劳动的关键在于游戏是快乐的,劳动是困苦的[5]407。郝伊津哈认为儿童为什么喜欢游戏是因为作品本身能为儿童带来身心的快乐,所以游戏的偷悦性是文学作品的根本逻辑[6]3。在中国,有一部分学者把儿童文学的快乐性和教育性进行对立,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追求其对儿童的规劝,训诫等教育功能。把成人的知识和道德规范,通过儿童文学作品传递给儿童。长期教育性占主导地位的儿童文学,使得儿童被动学习,对儿童文学索然无趣,最终是不适合儿童发展需要的。
快乐性是从儿童需求出发的,遵循了儿童本位,以儿童为中心的一种哲学价值取向。成人创作了儿童文学作品,但是视角是成人视角不是儿童视角,不是成人训导儿童的剧本,而是儿童加入自导自演的创生的过程。快乐性满足了儿童求新求变的心理。儿童最怕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环境内,在游戏中,儿童往往借助幻想使游戏的空间有别于现实的场景,使熟悉的现实在游戏的空间内变得陌生化,在陌生的空间中,儿童充分地表现自我,体验着一种陌生感、惊奇感和滑稽感所带来的快乐。在游戏精神中,快乐是第一位的。儿童进行游戏的最初动力在于儿童需要得到一种快乐的感受,在心理上需要这种令人快乐美好的体验。游戏精神的内外在表现就是快乐,包括内在心情和外在肢体的全身心快乐[7]。儿童游戏主要受儿童主观意识的推动,不受场地和外力的限制,通过内心的自我张力进行驱动。在外在的显现中可能与现实脱节,显示出非理性的性质[8]29。与成人进行游戏的目的性、功利性不同,儿童进行游戏的目的是单纯而简单的,即“为了获得快乐”。快乐贯穿了儿童游戏的全过程,也是儿童进行游戏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儿童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游戏精神由此将“快乐”作为基本原则,将快乐贯穿于文本始末,注重符合儿童心理的游戏编创,抛开了过多先验性的、成人式的观念与思想,其目的是让儿童读者不要过多地拘泥于现实的时间、规矩、秩序和逻辑,转而尽情嬉戏畅游,以此体味心理上的快乐与满足。正如高尔基所说,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
(二)游戏的幻想性
游戏是由其幻想性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游戏只有在一个奇妙幻想的世界中才可能实现,进行游戏的逻辑基础是必须提前营造一个幻想世界。儿童在现实中的梦想难以真正实现,但在游戏环境中可以大胆想象,把愿望变成现实。亚里士多德更认为游戏是面向未来的。儿童的游戏无论是出于冲动还是精力过剩,无论是角色扮演还是模仿成人,但游戏的方向总是指向遥不可及的未来世界,既表达了现实的不可能又表达了未来的期许。在文学作品中,儿童主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创造想象的空间,用身体去建构一个模仿现实的、一种假想的另外世界。把自己身体置身于其中,获得了丰富的精神体验[9]。儿童用身体构建的想象空间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所以需要一种稳定的符号系统来代替身体的角色扮演。这个符号系统就是语言,儿童学会用语言后,他们不满住于自身身体的依赖,而是把想象置入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作品中扮演角色和富有想象的空间。这种空间具有稳固性,不被毁灭性。满足儿童的征服欲,释放其压抑的情绪,获得积极情感。在符号世界中,遐想世界,充分感受其美妙的幻想和自由的快乐。
教师如果采取讲授式的方法,将儿歌和童话讲述给儿童,儿童未必感兴趣。所以游戏精神以儿童的视角,去关注儿童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创设游戏性的情境,在儿童式的幻想中,儿童易于理解文本,才能进入文本的内容理解之中。尽管可能儿童不一定理解文本中文字的全部内涵,但儿童在情境的引导中,感受到了游戏的快乐,就已经是一种儿童文学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了。在这个“进入文本情境”的过程中,儿童体验到了玩的乐趣,并知道了如何进入幻想之中,他们处于一种原始的冲动和真诚的状态,卷入了文学体验的过程之中去[6]98。儿童游戏满足了儿童的本真愿望,使沉积于内心深处的渴望与冲动得以释放和满足,其途径之一就是就是幻想。幻想在游戏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引导儿童超越思维定势,才能从平凡生活中跳脱出来,在理想的境界与想象中自由遨游,用单纯的、探索的方式对未来作出预想和预测。
(三)游戏主体的自由性
游戏是儿童的生命,儿童天然喜欢游戏,儿童对游戏情有独钟原因在于可以逃离成人世界的约束,或者自由。正如康德所言,自由是游戏的灵魂所在。郝伊津哈也认为,游戏的天然特征是游戏者的自由性。这种自由表现在,游戏是儿童自己组织的游戏,不是成人预先设定的,游戏是儿童的一种自愿活动,不是强迫的,不是受外界因素引诱的,儿童在游戏中找到自我,找到自由,找到快乐。
在游戏活动中,儿童是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组织活动,制定游戏规则。在这里,虚弱的小男孩变成了凶猛的强盗,仍然需要妈妈照顾的小女孩变成了照顾娃娃的妈妈。在这里,儿童成为活动的主角,成年人的规则被暂时中止和放逐。
皮亚杰发现,儿童的思维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对于不能把握的事物,儿童往往采取“同化”的手段,将主观意志强加于客体,赋予客体以形式,从而实现主体精神的自由。皮亚杰说:“游戏是把真实的东西变成他想要的,这样他的自我才能得到满足。他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他解决了所有矛盾,特别是他用一些虚构的故事来补偿和改善现实世界。”[10]43儿童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在认识世界的初期,他们会对身边的一切产生好奇,并可能将自我的认识推向到其他事物上,这是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朴素的、主观的正常现象[11]9。儿童在此阶段中,有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在游戏中可能自己按照主观的意愿创设了自己的“世界”,并希望在游戏中去实现自己的所有想法。这就是儿童游戏精神中的“自由”原则,即儿童具有主观能动性,不受外界的干扰,不再是成年人敦促下进行行动的被动者,而是自己世界的“国王”或“领头羊”,有自己主导游戏过程的倾向。
二、“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形式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也是儿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游戏性则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基本属性。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要素中包括了幻化欢乐的情境、天真活泼受欢迎的形象、引人入胜的情节、幽默风趣儿童化的语言等[12]。“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创设、语言渲染等形式[13]。
(一)人物形象呈现的游戏精神
人物形象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儿童文学中的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关乎着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游戏精神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着诸多的体现,通过对人物外貌、行为、语言或心理活动的描述,可能将人物形象较为具体地呈现出来,为引导儿童进入游戏情境提供支持,也将游戏精神具体化了[14]。如《鲁滨逊漂流记》,就将主人公多年的流浪生涯展示出来,其中包含了鲁滨逊落魄的外表描述、突然进入陌生地域且无法脱身的无奈的心理描写、遇到“星期五”的曲折情节……种种描绘将儿童带入了主人公的生活情境,在推动儿童不断想象“鲁滨逊还会遇到什么事情?”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不怕眼前的困难,努力提升自我生存境遇的人物形象,实现了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15]。
通过“顽童”“小大人”、“反派”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凸显游戏精神。一是“顽童”的形象,不讨人喜欢的儿童体现在天马行空和不落俗套的行为上,儿童气的幻想展现了“顽童”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幻想的背后是儿童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理解,儿童的好奇心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超越了传统的行为方式,展现了“未来世界”中“游戏”的核心和“游戏”的类型——“不讨人喜欢”的自我,蕴含着儿童特有的能量和激情。二是“小大人”的形象,小大人都有神奇的力量或智慧,他们不怕权力,他们勇敢对抗邪恶势力,与之抗衡,在新时期以后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小大人”的形象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小大人”通常指那些看起来像大人的儿童,但总喜欢穿得深沉成熟,看不起这些同龄的“坏男孩”。具有极度自尊的性格特点,在聚光灯下,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急需他人的欣赏和认同。三是“反派”形象,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往往走“反派”的道路,制造冲突,通过主人公与“反派”的斗争,达到衬托出主人公的良好品质的目的。与“反派”作斗争的主人公也会同时得到自身的成长,“反派”往往以滑稽有趣的画面示人,这些滑稽画面有的表现在“反派”的外表和行为上,有的表现在“反派”滑稽的结局上。
(二)故事情节呈现的游戏精神
故事情节是推动故事发生发展的手段,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的编排按照多种方式呈现,但均有怪诞离奇、神秘夸张或引人入胜的色彩。儿童文学作家进行创作首要具备的条件就是要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其作品情节往往是夸张性的,或是荒诞可笑的,但却能带给儿童们不尽的快乐。如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儿童幻想小说中,作者以超凡想象为儿童构建了一个切合儿童审美心理的神秘的魔法世界,并引导儿童跟几个主人公一道在探险中无限自由地游戏、探索,进而不断成长。作者以一定的文学素养和逻辑能力,为儿童展现了一种亦真亦奇的幻想、强烈的游戏精神,使得整个作品同时具备了游戏精神和美学特质,成为了享誉全球的儿童文学佳作。
通过故事情节蕴涵的笨拙与聪明、嬉笑与吵闹、虚拟与真实凸显游戏精神。一是故事情节蕴涵的笨拙与聪明。在儿童时期,虽然儿童的生活经验相对较少,他们的思维往往处于一种软弱甚至不合逻辑的状态,他们对能者和智者的崇拜并没有减弱。通过唤醒自我意识,大多数儿童此时仍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可,甚至“鄙视”那些“愚蠢的儿童”,这种行为有时也会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当然儿童们对游戏参与的渴望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对儿童来说,任何行动都可以在游戏的路上进行。二是故事情节蕴涵嬉笑与吵闹。创作儿童文学的作者出于对儿童自然本性的尊重,在广阔的生活空间中创作出他们所熟悉和认可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样,与儿童现实生活非常接近的游戏就变成了幽默和风趣,甚至有些吵闹。三是故事情节蕴涵虚拟和真实。游戏是对现实的模拟,在游戏活动中,儿童们把虚拟创造看作是真实的存在,得到满足和快乐,比如,男孩用蝙蝠当战马玩“战争游戏”,想象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女孩为娃娃缝制衣服,这些游戏不仅是儿童们有意识的模仿行为,同时他们不断寻求新的手段来表达自己逐渐社会化的需求和愿望。
(三)语言渲染呈现的游戏精神
语言是文学的具体体现方式之一。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可幽默、可活泼,适宜制造游戏效应,容易为儿童带来游戏的快乐,且能营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意境,符合人的审美。因此,在有着明显的游戏色彩的儿童作品当中,其夸张幽默、快乐荒诞、充满童趣的语言是十分出彩的,如故事《淘气包埃米尔》中,角色语言的置换给人以深刻印象;短诗歌《小老鼠上灯台》中,朗朗上口的语言,使得“小老鼠”生动活泼而又形象地展现出来;再如台湾诗人林芳萍的儿歌创作,其作品《谁要跟我去散步?》中,文字运用了多种渲染手法,简洁明了,韵味十足,具有节奏感,深受儿童欢迎,更具清新脱俗的质感[16]。
通过语言夸张凸显荒诞美、语言颠倒凸显逆向思维、语言突转凸显惊奇,从而凸显游戏精神。首先,语言夸张凸显荒诞美。在儿童文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夸张形式是程度的扩大和缩小,增加夸张意味着程度的加深,事物的扩大,这也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夸大符号或事物,使人物或事物的形象表现出幽默的效果,增加儿童的阅读兴趣。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儿童文学中有许多夸张的故事,因为儿童有喜欢游戏和新奇事物的天性。第二,语言颠倒凸显逆向思维。不同于在现实生活,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场景、顺序,甚至角色都可能发生颠倒。真实秩序的颠倒和角色的颠倒是为了满足儿童对自由的渴望,由于儿童的思维能力比成人更直接,儿童往往通过幽默的语言更直接地获得新奇感。第三,语言突转凸显惊奇。突然变化是一系列的预测,使读者按照行动的逻辑去思考,却突然发生转向,使读者的阅读期待落空。儿童作品往往是为了创造翻天覆地、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而设计的,当故事和人物发展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时,往往会有一种突然变化的情节,让儿童读者意想不到,从而到达艺术效果。
三、游戏精神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编创的意义
游戏精神对于儿童文学编创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作品创作需要坚守“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属性和内涵所在。儿童文学的编创需注意儿童文学应有一定的认知功能,一定的审美功能,一定的教育功能和一定的娱乐功能,且娱乐功能是儿童文学的核心。而游戏精神正好具备以上几种功能,且其追求快乐和幽默欢快,是儿童文学娱乐功能的支点[17]。对比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当前中国儿童文学较为缺乏想象、略有僵化的幽默,甚至误读了“童年诗意”,最终导致缺乏游戏精神,无法吸引儿童读者。只有深入认识游戏精神,在编创中将游戏精神重新灌注入儿童文学,才能使儿童文学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18]。
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需要延续游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网络等新媒介的兴起和普及,影视、电子游戏等也逐渐进入到儿童文学的视野,儿童文学由此也面临时代转型,而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也随之出现更迭变迁,具有了丰富的、多层次的面貌和形态。对此,如何继续发扬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探讨在新媒介时代下,游戏精神与儿童文学的特定关系,才能更好地推动儿童文学的良性发展[19]16。面对现代化、多媒体时代的来临,除了应对商业化、电子化、多元化的叙事路向,还要继续秉持健康的人文情怀,尊重率真的儿童意识和游戏精神,追求表达方式和叙事路径的多样化实现,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未来方向[20]。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审美价值取向的风向标。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引导儿童去摸索、领悟自己的愿望,探索内心世界,也是引导儿童从儿童文学作品中认识自我的途径,更是积极建构儿童心灵的方式之一,游戏精神的最终目的是指向儿童童年经验的积累和审美塑造,最终超越内在自我精神[21]。由此,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终极取向所在。
(二)游戏精神对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具有重要指导功能
儿童文学作品创作长期以来形成了游戏性和教育性的二元主义。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更大程度上强调其本身的教育功能,以教育功能的大小作为衡量作品质量的主要标准。教育主义形成的渊源和背景是深刻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它是衡量事物或行为好坏的重要标准,每一种行为都受到道德观念的规范和制约,而文学往往是实现道德伦理教育的工具和手段。由于儒家思想的支持,“文以载道”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显著特征。
教育主义在儿童文学中的主导地位,长期以来都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支撑。事实上,儿童文学确实有责任给予儿童最普遍、最基本的真理知识,给予善和美,如爱、慈悲、友谊、勇敢和乐观。但儿童也需要快乐、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游戏,如果老师和家长忽视儿童的自身特点,他们完全从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出发,先入为主地把儿童的思想和行为用统一的标准规范起来,不断地对儿童的思想和行为做出决定和判断,以引导儿童走向所谓的“正确方向”,长此以往,就会扼杀儿童的天性。儿童渴望美丽快乐的故事、生动有趣的人物、虚幻夸张的情景,如此这些都只有在游戏情景下才会实现。所以,在倡导守护儿童天性,凸显作品游戏性的今天,儿童文学作品想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有一个能吸引和打动儿童的游戏元素,这是儿童文学创作的规律。换而言之,只有坚持游戏精神,儿童文学才能向更健康、更有趣的方向发展,才能满足儿童阅读知识的需要和愿望。
总而言之,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虽几经沉浮但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在儿童作品中始终存在并起着重要的作用,表现出它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不可或缺性[22]。游戏精神对儿童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且集中表现在满足儿童自我能动性,追求快乐、自由和幻想等方面。因此,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作品编创的重要依据和准则,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