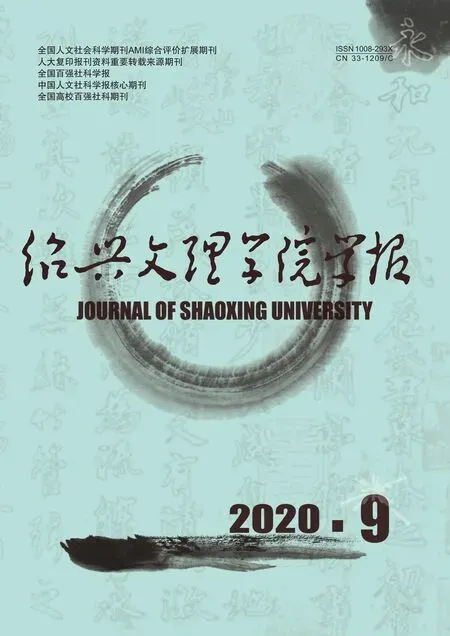《子刘子祠堂配享碑》选录标准初探
——兼论全祖望何以未选张履祥
荔强艳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沙坪坝区 401331)
全祖望,字绍衣,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学者称为谢山先生,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目前学界对全祖望“门户之见”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所作的《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子刘子祠堂配享碑》是乾隆十四年(1749),全祖望主蕺山讲席时,因刘宗周祠堂建成,为其列应配享弟子所作。全祖望以自己独特的选录标准为刘宗周选录了三十五位弟子和一位再传弟子,《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不仅确定了“蕺山学派”的师门传承,填补了一些不为后世所熟知的刘门子弟,也体现了全祖望自己的学术态度。历代学者都肯定了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对“蕺山学派”的表彰,但也提出了一些质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祖望未曾把张履祥列入配享碑,而这也被视为是全祖望有“门户之见”的表现。因此,探究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为何不列入张履祥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祖望独特的选录标准:“学行之不愧师门”
所谓“师门”,一般指出自同一老师之门,且极为重视师承关系,本文中的“师门”指明朝末年刘宗周的“蕺山学派”。全祖望在《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中直言:“顾其弟子之见于遗书者甚多,盖残明讲学,即以为声气之藉,未必真儒,勿敢滥也。若其后人所称为弟子者,又多不审,如刘公理顺、熊公汝霖皆非受业者,而滥列之。乃定其学行之不愧师门者三十五人,再传弟子一人,或反不甚世所知者。”[1]443可见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选录的首要宗旨是“学行之不愧师门”。全祖望列入《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中的人有:吴麟征、金铉、祁彪佳、彭期生、章正宸、叶庭秀、何宏仁、董标,“以上八先生,皆执弟子之礼,而子刘子则但以朋辈待之者,如蔡季通,故有疑祁虎子、章格菴非受业者,讹也”[1]445。陈尧年、章明德、朱昌祚、王业洵、祝渊、王毓蓍、潘集、傅日炯、恽日初、叶敦艮、刘应期、张应鳌、董瑒、戴易、华夏、王家勤、张应煜、赵甸、张成义、徐芳声、沈昀、陈确、周之璿、陈洪绶,“以上二十三先生,皆卓然可传于后者”[1]448。随后列入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刘汋,及再传弟子万斯选。通过梳理《子刘子祠堂配享碑》的文字发现,全祖望所谓的“学”主要分为讲学、刘宗周遗书的整理和编纂,“行”则主要是面对国破家亡时的选择和对于师门的维护,当然“学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整体概念。
弘扬“蕺山”之忠义。全祖望首先选录了“蕺山学派”的殉难义士及气节高尚的遗民。配享碑首先列入的吴麟征、金铉、祁彪佳、彭期生,四人均为殉难忠臣,《子刘子祠堂配享碑》评价为:“曰顺天金先生铉,字伯玉,甲申殉难忠臣也,祥见《明史》。伯玉之学,颇近禅宗,虽累论学于子刘子,不甚合也,而子刘子以其人雅重之。”[1]444朱铉虽学于刘宗周之门,其学也更近于禅宗,刘氏更注重其为人,显然全祖望也更关注其“甲申殉难忠臣”的身份,由此可见全氏列配享碑时对于殉难忠臣的弘扬。章正宸、叶庭秀、何宏仁三人也都参与了抗清斗争;祝渊、王毓蓍、潘集、傅日炯均为殉难义士,刘应期“丙戌后以愤死”[1]446,沈昀“独行之士”[1]447,以上都是刘门弟子中的殉难义士或是参与了抗清斗争的耿耿于故国之士。全祖望在《子刘子祠堂配享碑》还列入了戴易、张应煜、赵甸、张成义、徐芳声等不被世人所熟知的刘门子弟,即“或反不甚世所知者”。配享碑中关于戴易的记载有:“曰山阴戴先生易,字南枝,遗民中之奇者。其葬吴人徐枋事,最为世所称,然莫如其为子刘子门人也,予晚始知之,乃表而出之。”[1]446在《过戴高士南枝宅》中,全祖望叙及自己定配享碑时遗漏了戴易(戴南枝)这件事,“南枝先生蕉萃后,谁为列名汐社中?题诗桐江祭严子,卖字浒关葬徐公。固知正气返天上,长共残山表越东。学录定惭吾挂漏,偶来三迳吊蒿蓬”[1]2245。且在诗后有小注:“稼堂所作先生传,本末不甚祥,予拟搜其遗事,另为一通而未成。先生亦尝从事念台,顷议刘祠配享弟子,偶失之,当补入。”[1]2245由此可见全祖望对戴易的气节和学行都极其推重,并对自己选定《子刘子祠堂配享碑》时对其遗漏的情况表示遗憾,因此想要把戴易补入《子刘子祠堂配享碑》。更因佩服其生平大节,不满意潘耒(字稼堂)的《戴南枝传》,想要再为之作传,可惜未能完成。目前所见到的《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中果然列入了戴易,这不仅体现出全祖望列入《子刘子祠堂配享碑》时对选录对象“气节”的看重,更可见全祖望对学统的重视程度。全祖望把陈洪绶列入《子刘子祠堂配享碑》显然更关注其“大节”:“蕺山弟子,元趾(王毓蓍)与章侯(陈洪绶)最为畸士,不肯帖帖就绳墨。元趾死,章侯不死,然其大节则未尝有愧于元趾。故予定诸生弟子中,其有负盛名而不得豫配享,而独于章侯有取焉,详见予所作传。”[1]448“其有负盛名而不得豫配享”,严元照和杨凤苞都认为是指张履祥(1)严元照和杨凤苞都认为张履祥“其有负盛名而不得豫配享”是全祖望为了掩饰自己的门户之见。参见(清)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48页。,但当时刘门弟子“负盛名而不得豫配享”的又何止张履祥,与刘宗周亦师亦友的倪元璐被全祖望极力称赞,也未被列入配享碑。值得注意的是全祖望这句话的重点显然在后一句,为了凸显陈洪绶的“大节”,全祖望才会把他列入《子刘子祠堂配享碑》。
表彰“蕺山”之功臣。《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列入了陈尧年、章明德、朱昌祚、王业洵。陈尧年、章明德和朱昌祚对“蕺山学派”的重要性,全祖望在《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中有详细记载:“曰山阴陈先生尧年,字敬伯;会稽章先生明德,字晋候;山阴朱先生昌祚,字绵之,服勤于子刘子最久者。敬伯居石家池,在蕺山右,子刘子开讲,首在其塾。党祸之烈也,子刘子子贞孝君汋尚少,讬之敬伯,曰:‘子,吾之王成也。’而明德为格菴群从,白马山房之会,陶石梁弟子多异说,明德辟之力。绵之居即在蕺山下,其解吟轩,子刘子讲堂也,朝夕不离杖履,所造甚邃。”[1]445陈尧年、章明德、朱昌祚都是跟随刘宗周最久的人,刘宗周开讲,陈尧年“首在其塾”,且是其遇党祸时托孤的人;章明德和章正宸是叔侄关系,且他是“白马山房之会”时刘门的功臣,陶奭龄(石梁)为王阳明的三传弟子,“证人社”最后分为“蕺山学派”和“姚江书院派”,章明德在“白马山房之会”对陶门弟子“异说”的批评,对刘门的贡献无疑是极大的。刘宗周在蕺山讲学时大多在朱昌祚的解吟轩,他与刘宗周朝夕相处,对蕺山之学了解更深。王业洵也是“白马山房之会”时刘门的功臣,“梨洲黄氏尝言:‘子刘子开讲堂,石梁之徒三及吾门,欲摇其说。左右师席者,士美、元趾与予三数人。’则士美亦证人之功臣也”[1]445。士美,即王业洵。可见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的选录标准是对为维护刘门作出极大贡献的弟子也予以表彰。
推崇“蕺山”之传承,具体表现在《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中以讲学和整理、编纂刘氏遗书为主的选录标准。恽日初“丙戌以后,累至山阴哭祭,为之行状”[1]445-446,陈确“畸士也,说经尤谔谔”[1]447,讲学的则有叶敦艮、张应鳌、华夏、王家勤、赵甸,但华夏和王家勤最后都参与抗清,后同死,全祖望显然更重视他们为故国而死的行为。整理和编纂刘氏遗书的有董瑒、周之璿和刘汋。董瑒“手辑子刘子遗书”[1]446,周之璿“负其遗书与贞孝同避兵,中途累为逻者所厄。敬可流离播迁,谓贞孝曰:‘死则俱死,不负吾师以生’”[1]447,敬可即周之璿,贞孝即刘宗周之子刘汋,周之璿于避难之时也不忘先师遗书,可见其对刘门的贡献。刘汋身为刘宗周之子,在编辑和整理刘宗周遗书中的贡献更不用多说。至于后面提到的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余姚三黄”为抗清而组织的“世忠营”为世人所熟知,且黄宗羲对“蕺山学派”的贡献不言而喻。全祖望选录蕺山弟子时对刘子遗书的重视,从其再传弟子独选公择(万斯选)一人也可以看出来,“公择兄弟并从黄氏称私淑,其最有功于子刘子之遗书,偕梨洲而左右之者,曰公择纯笃邃密。故吾于子刘子之再传,不能遍及,而独举公择者,以遗书也”[1]448。可见谢山承认公择兄弟都私淑梨洲,均属于蕺山再传弟子,且万斯大和万季野的成就明显高于万斯选,但全祖望从对刘氏“遗书”的贡献来看,只列入了万斯选,可见在全祖望看来,刘宗周遗书对“蕺山学派”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全祖望对刘门弟子更注重“忠义”,次及刘门传承的认识与比他稍前的万斯同相同。万斯同《题松菊图为陈惕非八旬初度寿》云:
往山阴刘忠正公绍明绝学,四方士多从之游,其卓然可传于后者,大都以忠义表见。如吴磊斋、叶润山、祁世培、金伯玉、王玄趾、祝开美诸君子其尤也。其后死而坚岁寒之操以学问表见者,不过盐官陈乾初、昆陵恽仲升及吾师姚江黄太冲三先生而已。恽先生又逃之方外,其学不耑于儒。黄先生余所亲炙,信哉!为山阴之嫡传。陈先生则闻其名而未识其人,然稔知先生学最深,品最高,为乡人所矜式。[2]293
万斯同也认为刘门弟子“其卓然可传于后者”,大都以忠义表见。其次是品节高尚且以学问见长者,他认为刘门弟子中只有陈确(陈乾初)、恽日初(恽仲升)和黄宗羲(黄太冲)符合。万斯同在此也未提及张履祥,难道这也是出于“门户之见”?万氏以史学见长,对理学不甚关注,且对其师黄宗羲关于潘平格的评价不以为然。钱穆先生认为:“然梨洲之于用微,虽严斥深排,而季野固未悦。乃至理学不讲,去而穷经。”[3]58“用微”,即潘平格。钱先生认为,万斯同是因为与黄宗羲对于理学的看法不同才转去“穷经”的,这个看法显然与万斯同的志向不符,他终身致力于经史之学,于《明史》用力最深,这是万氏自己的学术追求。但是万斯同对于与黄宗羲志行不同的潘平格极力称赞,且不因黄宗羲的评价而改变,可见万斯同绝无“门户之见”。万斯同距张履祥生活的时代更近,作为蕺山再传弟子,万氏都未提及张履祥,可见张履祥在当时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对“蕺山学派”的看法,相较于重视忠义和学问的万斯同,全祖望虽然也重视忠义,但他还提及了对师门有维护之功的刘门弟子和刘氏遗书对于“蕺山学派”的重要意义,可见全祖望更具有学术史的眼光。
总之,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以“学行之不愧师门”为主要标准,关注对殉难义士和崇高气节的表彰、对“蕺山学派”的维护和传承,即以讲学和整理编纂刘宗周遗书为主。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即使全祖望认为在“蕺山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刘宗周遗书具有重大价值,但是通过全祖望选录的结果来看,他还是更注重对明清易代之际的“殉难义士”的表彰以及对崇高气节的弘扬,因为在刘门的传承中,他选录的也是气节高昂的人。换句话讲,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最重要的选录标准就是对殉难义士的表彰和崇高气节的弘扬。
二、张履祥与“学行之不愧师门”
上文已经提到,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的选录标准是“学行之不愧于师门”,更关注殉难义士和对“气节”的弘扬。吴麟征、金铉、祁彪佳、彭期生为殉难忠臣,祝渊、王毓蓍、潘集、傅日炯均为殉难义士,华夏、王家勤抗清而亡,叶庭秀、恽日初和张成义也参加过抗清活动,黄氏三兄弟的抗清活动更是广为人知。鉴于全祖望独特的选录标准,张履祥不被列入配享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张履祥“躬耕负薪”的遗民生活不符合全祖望弘扬“气节”的要求。面对刘宗周绝食而亡以及刘门弟子的殉难,张履祥选择了“生”,即不抗清也决不降清,成为遗民。他在为自己所作的《自题画像》中有:“行己欲清,恒入于浊。谋道欲勇,恒病于怯。”[4]589一个“怯”字足以概括其对生死的态度。“今日为诸生,则思进士做,若果登进士,执何具以往?岂能如昔日,坐享太平,优游贵乐乎?徒有身败名损,为人笑辱而已。弟欲于海滨僻壤,挈妻子而居,为苟全性命之计。因此修身力学,以俟天命人事之可为,则虽一命之膺,庶几得如古人所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然,躬耕负薪,亦足以没齿而无愧。”[4]263-264以上言论是张履祥的真实写照,他是明代诸生,在国变之际,他认为即便出去做官也不能达到以前的成就,反为世人讥笑,还不如偕家隐居,苟全性命,“修身力学”,即使“躬耕负薪”也无愧于家国和平生所学。因此,张履祥于国变之际隐居不仕,息影于当世,躬耕于农桑。凡此,张履祥于明清易代之际选择躬耕农桑、离群索居的遗民生活显然不符合全祖望致力于表彰殉难义士和高尚气节的标准。
其二,张履祥对“蕺山学派”的贡献也不符合全祖望的选录标准。据苏淳元《张杨园先生年谱》记载:“十七年甲申,为大清顺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岁。馆甑山。二月,如山阴,受学于刘念台先生之门。”[4]1496张履祥于甲申年(1644)二月问学于刘宗周,前后共两个多月,后归家。“归来,自谓有得,以刘先生《人谱》《证人社约》等书示门人。其后,于刘先生遗书中採其纯正者,编为《刘子粹言》。夏四月,始记《言行见闻录》。”[4]1496张履祥归家后,将《人谱》和《证人社约》传授于门人,还整理了先师“纯正”的内容编为《刘子粹言》,且记录刘宗周的言行编为《言行见闻录》,还与陈确等人一起修改先师年谱,以上都是张履祥对“蕺山学派”的贡献。但事实上,因为他当时“隐而不出”,几乎不为时人所熟知,后面又转向程朱之学,所以其学术影响的范围有限,左宗棠更有张履祥“声誉不出闾巷”[5]290的评价。总之,在全祖望看来,张履祥既没有在关键时期维护“蕺山学派”的功劳,也没有大型讲学活动,更没有产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且张氏对刘宗周的遗书只选录适合自己的言论,甚至有“《年谱》领到,当谨藏之,以为仪鹄,非一二深交之友,不敢出以同看”[4]667。张履祥认为刘宗周的某些言论不适合广为流传,对刘宗周遗书甚至到了秘不示人的地步。与张履祥对刘宗周遗书的态度相反,全祖望对刘氏遗书极其重视,认为它在“蕺山学派”的传承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张履祥对“蕺山学派”的贡献显然不符合全祖望的选录标准。
总而言之,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有其独特的选录标准,即“学行之不愧师门”,即对殉难义士的表彰和对崇高气节的弘扬,以及对“蕺山学派”的贡献和传播,其中全祖望最重视的就是对“忠义”的弘扬。以全祖望“学行之不愧于师门”的选录标准来看,张履祥既不符合全祖望致力于弘扬和表彰的殉难义士,也没有全氏看重的“气节”和“高行”,且张履祥对“蕺山学派”的贡献也不符合全祖望的选录标准。因此,与其说全祖望是出于“门户之见”未列入张履祥,倒不如说是张履详不符合全祖望独特的选录标准,毕竟黄宗羲曾言蕺山弟子三百七十六人[6]60,若以此论,全祖望未列入《子刘子祠堂配享碑》的人又岂止张履祥。
三、追溯全祖望对张履祥的认知
赞同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有“门户之见”的学者,认为全祖望不列入张履详是出于“门户之见”(2)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严元照、杨凤苞、王俊义和张天杰等。,但关于全祖望是否了解张履祥的存在这一问题,一直未被梳理。既然张履祥的存在对于全祖望是否有“门户之见”如此重要,那么梳理全祖望是否知道张履祥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张履祥与黄宗羲都师从刘宗周,两人又有许多共同好友,可见他们应彼此相互了解,但《黄宗羲全集》中却只有一段模糊的记载:“闻刘伯绳将葬,先生曰:‘吾不能执绋引路,有负亡友。’涕泪为之交下。时浙西有与伯绳友者,余约之渡江,其人漠然不应,余因叹曰:‘人情相悬固如此哉’!”[6]158一般认为这里的“浙西有与伯绳友者”是指张履祥。张履祥在《言行见闻录四》对黄宗羲却有直接的评价:“黄太冲曰:‘朋友不可以非义相成。’吕用晦称其言而曰:‘以非义相成,其后必至于相怨。’”“黄太冲,忠端公子也。忠端死于逆珰之祸。崇祯出,忠贤伏诛,奄党惧,以多金货诸忠义家。太冲叱之退,刺血上书讼父冤。朝廷感动,逮逆党李实,实之法。司寇廷鞫之日,太冲挟利锥,刺实遍身流血。闻者壮其事。”[4]958张履祥肯定了黄宗羲的品节,但也有不满于黄宗羲的评价,有“此名士,非儒者也”的评论,可见张履祥认可黄宗羲的品行,但对他“儒者”的身份不以为然。黄宗羲自视为理学正统,对张履祥只字未提,足可见其“门户之见”未化,因此全祖望无法从黄宗羲的文字中了解到张履祥。稍后于张履祥的朱彝尊(1629—1709)在《静志居诗话》中有关于张履祥的记载:“张履祥,字考父,桐乡县学生。考父撰有杨园备忘录,其讲学,以鹿洞为师,仁宅义根,言规行矩,间作韵语,不沿安乐窝头巾语。题屠处士熿邨居云:‘霍原六聘山,焦先三诏洞,渔子定迷津,只莫桃花种。’”[7]696此外,《静志居诗话》在谈吴蕃昌时也提及张履祥:“仲木,贞肃次子,师事刘念台先生,与海宁陈确潜夫、桐乡张履祥考父,讲洛、闽之学,诗非专务。”[7]684全祖望《奉万西郭问魏白衣息贤堂集书》中谈到魏璧(魏白衣)的生平概况是来自《静志居诗话》(3)魏璧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3页。:“尝言诗以达情,乐必尽乐,哀必尽哀,一切樗蒲六博,朋友燕酣,城郭之所历览,金石之所辨索,有触于怀,不期矜饰,务达而止。此见于竹垞《诗话》所述者。”[1]1701由此可见,全祖望读过《静志居诗话》,而《静志居诗话》关于魏璧、吴蕃昌、张履祥三人的记载属于同一卷。从全祖望的诗文集来看,他对朱彝尊的著作十分熟悉,并有许多补充和纠错,更因为不满于朱彝尊《经义考》中对易学的论述而创作了《读易别录》。朱彝尊《经义考》在论及陈确的《大学辨》时也提及张履祥:“《大学辨》始成,于时闻者皆骇。桐乡张履祥考父、山阴刘汋伯绳、仁和沈兰先甸华、海盐吴蕃昌仲木,交移书争之,而乾初不顾。”[8]838凡此,均可证明全祖望可以从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和《经义考》中知道张履祥的存在。且全祖望在《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刘门弟子熊汝霖”条中提到自己看过刘汋所列的刘门弟子,也可由此知道张履祥的存在。这些材料都只是提及张履祥的存在,却都没有详细记载,而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又主要关注“忠义”,更以气节为主,且全祖望对自己不了解的人不轻易下笔,因此全祖望才不把张履祥列入《子刘子祠堂配享碑》。
总而言之,全祖望虽然可能了解到张履祥的存在,但绝不会看到张履祥的著作。且全氏留意浙东文献和掌故,而张履祥却属于浙西,全氏对浙西文化的了解程度远不及浙东。上文曾提及万斯同也未曾列入张履祥,可见张履祥在当时的影响有限,更遑论全祖望生活的时代。杨凤苞(1754—1816)和严元照(1773—1817)所处的时代还要后于全祖望,况且张履祥被广泛注意到是在同治十年(1871)从祀孔庙开始的。因此,全祖望可能从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经义考》和刘汋所列的刘门弟子中知道张履祥的存在,但并不会深入了解其生平及学行,且他所处的时代对于与张履祥同时代的人物都只能通过传闻和其他学者的记录才能知道。因此全祖望不列入张履祥或是出于不了解张履祥的生平和学行,与“门户之见”无关。
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出于“门户之见”而未列入张履祥被学界普遍认同。但通过查阅全祖望的文字及张履祥的相关资料发现,全祖望未列入张履祥是因为其独特的选录标准“学行之无愧于师门”,即弘扬“忠义”和表彰“蕺山学派”的学术传承,具体表现在他对殉难义士的赞扬和对高尚气节的表彰,发掘刘门功臣和重视刘宗周遗书对“蕺山学派”发展的作用,但全祖望显然更注重弘扬“忠义”。鉴于全祖望独特的选录标准,张履祥“躬耕农桑”的息影绝世之行和他对师门的贡献、传承显然不符合全祖望的选录标准。不仅如此,由于张履祥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有限,且距全祖望生活的时代稍远,全祖望虽然知道张履祥的存在,但对他的生平和学行了解不深,这或许也是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不列入张履祥的原因,但这都与“门户之见”无关。全祖望如此重视弘扬刘门弟子中的殉难义士和有“大节”之人,与他致力于宣扬“气节”的学术追求息息相关,对“气节”的褒扬也是全祖望著作的突出特征,更是他为后人极力称赞的主要原因。